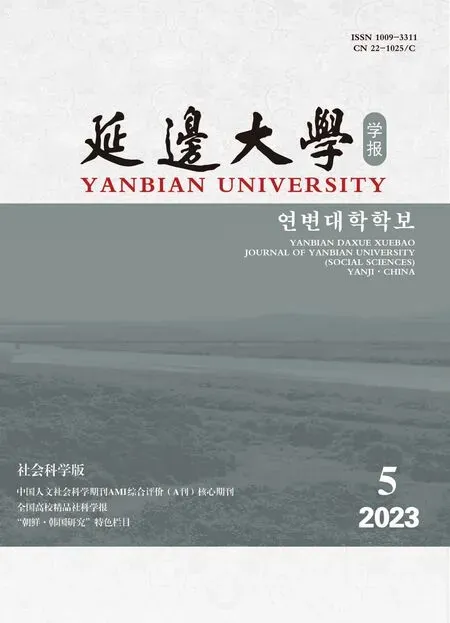共相与变异:“西园雅集”文化意象的东亚传播与视觉呈现
肖 雪
“东亚”作为一个地理区块概念与“文化圈”这一空间范畴相结合而形成的“东亚文化圈”,一般意义上指的是深受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即儒家文化影响下的东亚国家,“以中国为中心,其东接朝鲜半岛、日本群岛,在地形上从古以来成为一亲密的文化团体”。(1)[日]滨田耕作:《东亚文化之黎明》,孟世杰译,北京:北平文化学社,1933年,第1页。可见,东亚文化圈的交流与互鉴自古以来就已存在,而在这一过程中出现并流传的“文化意象”虽然在“形象化”“视觉化”的呈现上各有不同,但却保留了“在地”诠释时所需要的必要空间,既呈现出东亚文化圈的共相属性,又展示出这一文化圈内“和而不同”的特征。
在东亚文化圈中流行的文化意象以“西园雅集”最具“典范性”。尽管在中国历史上并不缺乏对文人集会活动的记载,但是这一由北宋文艺场域的核心人物如苏轼、黄庭坚、李公麟、米芾、晁补之、王诜、秦观等在元祐年间(1086-1094)举办的雅集活动,“不仅超越了时间的束缚,而且跨越地理空间的限制,成为无所不在的‘典范意象’”。(2)石守谦:《移动的桃花源——东亚世界的山水画》,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第14页。基于此,本文将通过对18世纪以来中、日、朝三国“西园雅集”文化意象的考察,探讨东亚文化圈中不同国家与地区在审美意趣、文化心理上的交融与互动、共相与变异的情况,对推动与实现东亚文化圈的文化认同有着一定的启示意义。
一、“西园雅集”文化意象的形成与塑造
普遍的观点认为,北宋的“西园雅集”是继东晋“兰亭集会”后,中国历史上又一次颇具影响力的文人集会活动。“西园雅集”既是中国古代一个重要的文化意象,又是中国古代士人文化、审美意趣以及生命态度的集中体现。参与到此次集会的北宋文人士大夫共计16人,当中既有文坛领袖苏轼、书坛大家米芾,又有擅长丹青的李公麟以及身份显赫的驸马王诜等。这些文人士大夫以苏轼为核心,构成了经纬交织且颇为庞大的人才谱系——元祐文人士大夫群体。他们时常汇聚一堂,或是在山清气润之时登高远眺、或是在公务繁忙之余赋诗酬唱、或是在私人府邸中宴饮抒怀、或是在闲暇无事时品鉴书画。
在他们开展的诸多宴饮雅集活动中,以元祐年间(1086-1094)举办的“西园雅集”最具代表性。虽然时至今日仍有不少学者对这一文人集会的真实性存在诸多质疑,(3)首先对于“西园雅集”真实性进行考察的是美国学者梁庄爱伦,他在《理想还是现实——“西园雅集”和〈西园雅集图〉考》一文中认为北宋元祐文人士大夫所举办的“西园雅集”是不存在的。此后,我国学者杨新在《去伪存真,还原历史——仇英款〈西园雅集图〉研究》一文中也指出“西园雅集”是后世的想象。但我们却不能忽视“西园雅集”对于后世的影响。正如学者胡建君所言:“这种超然物外的生活方式与内容极尽后人美好的联想与追慕”。(4)胡建君:《元祐文人圈与文人画的发展》,博士学位论文,中国美术学院,2010年,第23页。尽管元祐年间王诜遍邀名士汇聚于“西园”一事可能存在后人不断建构与想象的情况,但这些想象的起因却与苏轼、黄庭坚、秦观、张耒等人留存下来的诗词中时常提及的“西园”有着密切的关联。
事实上,早在北宋之前已有不少文人在其诗文中提及“西园”一词,如曹魏时期邺下文人集团(5)邺下文人集团以曹操、曹丕、曹植为中心,主要成员有王粲、陈琳、徐幹、刘桢、应玚、阮瑀、路粹、邯郸淳、杨修、丁仪、丁廙等人。就曾在“西园”举办过宴饮集会活动。对此,曹丕在《登台赋·序》中云:“建安十七年春,游西园”;(6)[清]严可均:《全三国文》,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39页。又在《与吴质书》中追忆起他与徐幹、应玚等文人一同在“西园”中相洽无间的美好情景,“继以朗月,同乘并载,以游后园,舆轮徐动,参从无声,清风夜起”。(7)[南朝梁]萧统:《文选》卷四十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896页。此外,在曹植的《公宴诗》、王粲的《杂诗》、阮瑀的《公宴诗》、陈琳的《宴会诗》中,“西园”既是这群志趣相投的文人宴饮欢畅、消遣心情之所,又是宾主间寄托情感、互道衷肠之地。至此,“西园”由一处集会场所逐渐沉淀为一种文化意象,并对后世的文人士大夫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有宋一代,文人雅士对于“西园”这种质朴且浓厚的情感在元祐文人士大夫群体中得以继承与发扬。其中,在苏轼的诗词中“西园”意象几乎贯穿其起伏跌宕的政治生涯与丰富多彩的生命历程。熙宁七年至熙宁十年(1074-1077)苏轼调往密州任知州于密州西园所作有《和孔密州五绝·春步西园见寄》;熙宁十年至元丰二年(1077-1079)子瞻前往徐州任知州到滕县作有《滕县时同年西园》;又在与通判田叔通的赠答诗《再次韵答田国博部夫还二首》中云:“风流别乘多才思,归趁西园秉烛游”。(8)[宋]苏轼:《苏轼诗集》卷十八,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932页。可以说,此时的“西园”对于苏轼而言是一座座风景优美且极具诗情画意的园林。
然而,元丰二年(1079)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至黄州任团练副使一职时,他在《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中提及的“西园”却在情感上与以往大有不同,词中云:“不恨此花飞尽,恨西园,落红难缀。晓来雨过,遗踪何在?一池萍碎。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9)唐圭璋:《全宋词》,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77页。苏轼的这一首词本应是歌咏杨花、赞叹春意盎然之景,但下阙却话锋一转,落红成为了杨花的陪衬,“西园”也在“离人泪”的修饰中显得萧寒寂寥。可见,苏轼笔下的“西园”意象随其仕途起落而变化,从最初的闲情雅致变为一种世事无常的悲愁之感。
无独有偶,元祐文人士大夫群体中的黄庭坚、张耒、秦观、晁补之等也有不少涉及“西园”意象的诗词存世。比如,张耒的《西园》《霜后步西园》《题西园酴醾》《西园风雨花谢》《腊日步西园》等,无不道出了他对于“西园”的喜爱之情,或是在繁杂琐碎间感受到“西园”四时之变,或是在正月里感受“西园”的热闹喧嚣,或是在春日里观赏“满园红紫春无限,尽日飞鸣鸟自由”,(10)[宋]张耒:《柯山集》卷二十三,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第280页。或是在秋风中品味“秋圃寂无有,萧条残菊枝”。(11)[宋]张耒:《柯山集》卷七,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第77页。可见,在张耒笔下的“西园”涵括了众生百态、承载了时光荏苒,既有对美好时光的感怀,又有对友人天各一方命运的感叹。
此外,秦观、黄庭坚诗词中的“西园”意象也随着他们阅历的不断增加、仕途的跌宕起伏从原有的清雅舒适沦为了对昔日元祐文人集会之事的追忆。比如,秦观在《望海潮·洛阳怀古》中云:“西园夜饮悲笳,有华灯碍月,飞盖妨花。兰苑未空,行人渐老,重来是事堪嗟。烟暝酒旗斜。但倚楼极目,时见栖鸦。无奈归心,暗随流水到天涯”。(12)徐培均、罗立刚:《秦观词新释辑评》,北京:中国书店,2003年,第7页。秦观在《望海潮》中一边对月遥想与回忆着以往“西园”中的文人集会之事,而另一边却用“栖鸦”“流水”等凄苦的意象来叹息时光的流转、世事的无常。而这在黄庭坚的《和刘景文》一诗中亦有相似的情感传递,诗云:“追随城西园,残暑欲退席。夜凉雨新休,城谯挂苍璧。佳人携手嬉,调笑忘日夕”。(13)[宋]黄庭坚:《黄庭坚诗集注》卷十六,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1000页。黄山谷在作此诗时友人刘景文、仲天贶已经离世,恩师苏轼因新旧党争而被贬儋州久久未归,原来的元祐文人士大夫群体如今已然四分五裂、散落天涯,因此,诗中的“西园”意象凝结为浓浓的愁苦寂寥之情,充满着对元祐友人共聚“西园”的无限感怀。
由此可见,当元祐文人春风得意时“西园”对于他们而言既是曲径通幽、可居可游的诗意空间,又是闲庭信步、宴饮欢畅的重要文化场所。但是当元祐文人在遭遇了仕途的变动、沦为新旧党争的牺牲品时,他们开始在诗词中借助“西园”意象将心灵深处的回忆转化为诗性的语言,以此来表达他们对同门友人的思念,传递他们对于往昔平静岁月、美好时光的追忆。
二、“西园雅集”文化图式的生成与演变
中国古人对于“西园”意象的热爱不仅存在于诗歌体裁中,还出现在绘画作品里。据郭若虚的《图画见闻志》载,东晋顾恺之绘制的《陈思王诗图》,即《清夜游西园图》,描绘的是邺下文人于“西园”的集会场景,且这一作品的稿本直至唐朝末年仍存于世。(14)[宋]郭若虚:《图画见闻志》卷五,《画史丛书》(一),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303-304页。至于该图所描绘的人物风貌虽然现已无缘得见原作,但我们却可以根据宋人董逌在《广川画跋》中的描述略知一二,文中言:“观郑彦庄所得《西园图》……笔墨奇古,摆脱俗韵。其在人物态度,犹是当时风流气习,可以想见……顾长康初以曹子建诗营此图,在梁朝入录为第一”。(15)[宋]董逌:《广川画跋》卷五,《画品丛书》(二),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415页。在这件作品中,顾恺之以文人为主体描绘出的诗意场景开启了后世画家对文人集会题材绘画的探寻之路。
继顾恺之后,(传为)北宋李公麟创作的《西园雅集图》更是将元祐文人心中的“西园”文化意象进行了视觉化的呈现。在传为李公麟(龙眼居士)创作的《西园雅集图》(图1)中,画家用白描的写实手法将参与到集会中的16位文人士大夫分成“提笔作诗”“展卷作画”“弹琴静听”“题石挥毫”“竹林论道”五组场景进行了细致的刻画,并在每位人物身边录有他们的名字以便观者分辨他们的身份。通过其刻画,既能在随处可见的古物摆件中感受元祐文人的雅致品位,又能在松柏、竹林、芭蕉等极具清幽意味的园林空间里体会到他们对于隐逸理想的追慕之情。
然而,随着宋代以后文人士大夫对于元祐文人群体认同与肯定的不断加深,在明清时期“西园雅集”题材绘画更是迎来了创作的高峰期,画家唐寅、文徵明、仇英、陈洪绶、石涛、华嵒、丁观鹏等皆绘有《西园雅集图》。在这些摹本中,画家们多是沿用了龙眠居士的图绘方式,将元祐文人的集会活动安置在方寸之内、规矩之中,在山水树石的映照下、在茂林修竹的掩映里彰显他们的高雅之趣与清逸之姿。
与此同时,明清时期流行的《西园雅集图》在雅集空间的处理与笔墨形式的表达上也极具时代特征。其中,仇英、文徵明、周天球等人立轴款的《西园雅集图》是明清文人对于“西园雅集”意象新的视觉呈现。相较于传为李公麟创作的《西园雅集图》中单以植物树木的方式来分割园林空间,仇英等人创作的《西园雅集图》(图2)最为显著的变化是在画面的右下方增添了“门”与“墙”两个园林建筑元素来强调文人集会的私密性。

图2 明仇英创作的《西园雅集图》,纸本设色,129.5×66厘米,私藏
画面上的常掩之“门”与高耸之“墙”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屏障,将园林中清幽雅致的集会活动与外部世界的世俗烦扰区隔开来,创造出一个只属于文人群体的“小天地”。正如明人汤传楹在《荒荒斋记》中言:“予与知己约,须叩门,主人当出……自知己数人外,谨谢客,弗敢见,见亦就外室,不敢延入此斋,破我荒径”。(16)衣学领:《苏州园林历代文钞》,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第74页。可见,对于明清文人而言,“入门”这一行为不仅是走进了一处景致幽美的园林空间,而更是意味着进入到一个由文人士大夫群体构成的“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理想场域,从而完成了文人士大夫之间的身份认同。
在明清时期流行的“西园雅集”题材绘画中,一部分画家如石涛、华喦等开始用苍劲有力的笔法、沉着厚重的墨色、浓郁多样的设色来表达他们的笔墨意趣。比如,石涛创作的《西园雅集图》横卷(图3)色彩淡雅、意境清幽、平远冲澹,整体章法错落有致、蜿蜒舒缓。在该作品中,画家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用疏简的线条勾勒出文人的高逸脱俗,在园林场景的点画间用缥缈的云烟、迷蒙的树影表现出形态的虚实,更添文人雅集的清润之气与空濛之韵。石涛创作的《西园雅集图》虽然描绘的是元祐文人士大夫的雅集活动,属于人物画的范畴,但其对该题材绘画进行处理的时候却未墨守成规地采用固有的图式,而是用山水画的笔墨形式来表达这一中国古代经典的绘画主题。此画中的苍松、古桧在笔墨上承袭了明末清初山水画图式的特点,疏密相间、虚实相生,山石树木的笔法细腻、皴法苍茫、收放自如。

图3 清石涛创作的《西园雅集图》,纸本设色,36.5×328厘米,上海博物馆藏
由此可见,明清时期流行的“西园雅集”题材绘画既有院体画的工致秀雅,又不失文人画的笔墨之美,是后世画家对于“西园雅集”文化意象的视觉化表达。而与此同时,明清画家对于“西园雅集”文化意象不同的图像诠释方式开始在18世纪以来的李氏朝鲜时期与日本江户时代得以继承与发扬,呈现出了“和而不同”的艺术特征与文化风貌。
三、“西园雅集”在李氏朝鲜的流行与视觉再现
作为中国的邻邦,朝鲜半岛在历史上一直与中国维持着紧密的对话与交流,“中朝文化远暨之致然,虽在远国,必以时王之制,中朝亦必嘉我慕华之心也”。(17)[朝]金安老:《中宗大王实录》,《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229页。尤其到了李氏朝鲜(1392-1910)与当时的明清在文化交流的过程中形成了“天朝礼治体系”,(18)“天朝礼治体系”是学者黄枝连在《天朝礼制体系研究》(上、中、下卷)中提出的重要概念。该文指出,明朝通过儒家的册封体制在东亚汉文化圈内建立起一个礼治体系来规范藩国的行为,以别上下、分尊卑。参见黄枝连:《天朝礼制体系研究》(上卷),《亚洲的华夏秩序——中国与亚洲国家关系形态论》,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2页。便开始把“雅集”这类极具中国特色的士人文化发展成李氏朝鲜的文化风尚,并在其相关的绘画作品中得以体现。
事实上,早在高丽时代(918-1392)便有不少集会活动的开展,只不过这一时期盛行的“契会”主体主要集中在官僚阶层中,具有明确的交际功用与礼仪意味,故与中国文人雅集所强调的雅致清旷、闲适自得的文化意涵有所不同。而这种情况一直延续至李氏朝鲜中期(1550-1700),虽然此时举行的集会活动中已经出现了文人的身影,但其本质上依旧是官僚间进行交流、彼此亲近的重要场所,可谓是“公式化雅集”。(19)韩国学者金宝敬、黄戈指出:“在朝鲜初、中期朝鲜的士大夫们常常举办各种各样的聚会,其中以官僚阶层纪念祝贺和太平宴饮的公会叫作‘胜会’。这种聚会的主要形式是在宫殿官里,参加者有严格的戒律,盛行一种近乎祭祀式的程式化的聚会,姑且称之为‘公式化雅集’……所以说李朝前半期的这种程式化的契会比较多,私人之间的雅集相对较少”。参见[韩]金宝敬、黄戈:《从中国“雅集图”到韩国“契会图”——“雅集图”画题在朝鲜半岛的历史播布与图式迁变》,《中国美术研究》2012年第3辑,第45页。因此,这一时期描绘契会之事的画作如《中庙朝书筵官赐宴图》《户曹契会图》《耆英会图》《同年宴饮图》《薇垣契会图》等,或是对官方赐宴场景的描绘、或是对同僚聚会的刻画,画面上将集会参与者的官职、姓名、籍贯等信息题写在人物身旁,以此来强化官僚群体间的内部结构、凸显李氏朝鲜上层文化的优越性。
到了李氏朝鲜中后期这一情况开始转变,宴饮集会的主体由宫廷贵族向文人群体过渡,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文人雅集。这一时期,无论是由李安讷、尹根洙等文士组成的“东岳诗坛”,还是沈师正在其书斋卧龙庵邀请金光国等人的聚会,皆为——朝鲜文人对于高雅品位的追求、对于主体精神的观照。其中,“西园雅集”文化意象随着李氏朝鲜的“朝天”“燕行”之举带回国后便成为李朝中后期文人群体争相模仿的对象。比如,在1739年6月,朝鲜士人李春跻在他的府邸中邀请了赵显命、宋翼辅、沈星镇等共聚一堂开展了“西园雅集”式的集会活动,并委托郑鄯将此次雅集之事绘成画卷。此后,1768年朝鲜文人李惟秀在其私人园林中开展的“东园雅集”更是对北宋元祐文人“西园雅集”的异域效仿。其中,参与此次集会的文人俞彦镐在《东园雅集图赞》与《东园雅集图小记》中称李惟秀的东园为“城市的山林”,而这与“西园雅集”文化意象所强调的“中隐”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妙。由此可见,李朝中后期的文人群体对于“西园雅集”文化意象的接受情况。
与此同时,李氏朝鲜画坛更是迎来了“西园雅集”题材绘画创作的浪潮。其中,朝鲜画家金弘道、李寅文等创作了多幅形制不一的《西园雅集图》来回应时人对于“西园雅集”文化意象的神往之情。其中,金弘道绘于1778年的《西园雅集图六叠屏风》(图4)采用的是横向构图,视线随着画面中大门的开启从右至左徐徐推进,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米芾于石壁前纵情挥毫的场景,紧接着是对李公麟作《归去来》诗意图的描绘。在第五叠屏风上,画家金弘道描绘出了在双松的掩映下东坡作诗的场景。随后在第六叠屏风上,画面的最下端描绘出弹阮听琴的隐逸之景;在画面的最上方展现出了竹林深处论经谈道的超然之姿。

图4 朝鲜金弘道创作的《西园雅集图六叠屏风》,绢本设色,122.7×47.9厘米,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藏

图5 日本中西耕石创作的《西园雅集图》,纸本设色,16×79厘米,私藏
金弘道笔下的“西园雅集”色彩淡雅、古雅大方、意境清幽,人物形态生动自然,线条刻画流畅有力,既体现出文人士大夫潇洒自在的风神样貌,又凸显画家对于清旷雅致园林集会的向往之情。对此,李朝文臣姜世晃在该画的题跋中写道:“余曾见雅集图,无滤数十本,当以仇十洲所画为第一,其外琐锁不足尽记,今观士能此图,笔势秀雅,布置得宜,人物俨然生动……画固不减元本,愧余笔法疏拙,有非元章之比”。(20)[朝]姜世晃:《西园雅集图六叠屏风》题跋。转引自[韩]金宝敬:《“雅集”绘画题材在李氏朝鲜的流布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南京艺术学院,2009年,第37页。通过画面内容与画作题跋所传递出来的信息可知,金弘道所绘的《西园雅集图六叠屏风》无论是在园林场景的设置、人物神态的雕琢,还是画面右下方出现的建筑元素“门”与“墙”,皆可看出是对仇英立轴款《西园雅集图》的借鉴与模仿。
进而论之,何以仇英款的“西园雅集”图绘模式会出现在朝鲜画家的笔下呢?究其原因,笔者以为或许同18世纪以来“苏州片”在李氏朝鲜的广泛流传有着密切的关联。“苏州片”指的是明清时期(16-18世纪)在苏州山塘街专诸巷和桃花坞一带制作的伪古书画,以此来满足各个阶层对雅文化的追求。(21)邱士华:《拼嵌群组:探索苏州片作坊的轮廓》,《伪好物:16—18世纪苏州片及其影响》,台北:台北故宫博物院,2018年,第346-347页。其中,最能代表中国文人风雅之貌的“西园雅集”以难以估计的数量广泛流布于民间,而当中又以仇英款的《西园雅集图》数量最多。
值得注意的是,何以在中晚明时期已经流行开来的仇英款“西园雅集”图式会在18世纪以后的李氏朝鲜王朝才得以出现,是何种原因导致了这一滞后的情况呢?众所周知,明清时期中国与李氏朝鲜一直保持着密切的使行关系,以此来增进两国的交流,但是明清两代朝廷对于使臣不同的态度与相关的政策成为他们能否接触到流行于街闾巷尾“苏州片”的关键。在明朝,朝廷始终对于朝鲜抱有一些警惕心理,与之相应的,来往中国的“朝天使”在行动上也受到了严格的限制。(22)关于明代朝廷对于使臣严格的防禁政策,参见刘晶:《明代玉河馆门禁及相关问题考述》,《安徽史学》2012年第5期,第21-28页。从某种程度而言,这便导致了他们与泛滥于“京师杂卖铺”中的“苏州片”隔绝开来。而这种情况在清朝统治者康熙后期才出现了转寰,前往中国的“燕行使”获得了更多的宽待以及相对自由的活动空间,其文化上的交流也从官方层面向私人领域中蔓延。因此,“苏州片”作坊绘制的仇英款《西园雅集图》因中朝关系的新气象由“燕行使”李秉渊等人带回朝鲜后,成为朝鲜宫廷贵族与文人群体收藏的对象。比如,1713年肃宗在位之时就曾在宫廷中目睹过《西园雅集图》,李秉渊也曾收藏了一幅不知作者与国籍的《西园雅集图》,而姜世晃更是见过十余个版本的《西园雅集图》。
由此可见,“西园雅集”文化意象在18世纪以来李氏朝鲜的传播与流行情况。一方面在中朝的交往中“燕行使”将“苏州片”版的《西园雅集图》带回李朝后促进了李朝宫廷贵族与文人群体对于这一中国传统文化意象的认知与理解;而另一方面画家金弘道等人创作的“西园雅集”文化图式所体现出的雅致意趣、隐逸之思以及文人聚会的私密性亦是对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群体生活美学与生命态度的异地再现。
四、江户时代南画家对“西园雅集”的视觉转换
“西园雅集”除了在18世纪朝鲜半岛得以传播外,在日本江户时代中后期亦能见到“西园雅集”的踪迹。其中,日本南画家中西耕石就绘有《西园雅集图》。虽然这一题材源自中国,但是在日本南画家笔下所表现出来的艺术风貌却与同一时期李氏朝鲜画家金弘道以及明清以来流行的该题材绘画作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是东亚文化圈内不同国家、民族艺术特征、文化特性的典型体现。
中西耕石的《西园雅集图》用流畅的线条、自然的墨色、疏淡色彩描绘出繁而不乱的集会场景,用寥寥数笔勾勒出一个个生动鲜活、各具特色的文人形象。画中的文人士大夫汇聚在宽阔舒缓的自然山水间,或是聚精会神展卷作画,或是若有所思提笔作诗,或是胸有成竹对石题字,或是圆柏树下静听琴音。尽管中西耕石的作品在场景设置、人物点染上不同于中国的“西园雅集”文化图式,但无论是在画面上远处高耸入云的山峰,还是近处细腻点染的小景皆可视为画家将对生命的观照、对内心的体察融入其中,而这一东瀛情韵的传递恰好与中国文人画的思想情感、笔墨意趣不谋而合。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江户时代发展起来的“南画”(Nanga)尽管有着“文人画”之称,但其本质却不能直接等同于中国的文人画,尤其是日本文化语境中出现的“文人”一词与中国儒家传统文化语境下的“文人”意涵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在中国,文人画是独立于院体画之外的绘画门类,是一种独具文人意趣的视觉呈现,是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群体文化心理结构的重要外化形式。纵观中国文人画的发展,自元祐文人苏轼提出了“尚意”之风、“诗画一律”“士人画”等观念后,“元四家”便在此基础上开始有意识地在画作中凸显笔墨自身的趣味、强调文人意气的抒发,以此来表达这一群体淡泊避世的理想与超然脱俗的态度。此后,晚明董其昌提出的“南北宗”论更是构建起了中国文人画的共同体,确立了文人画“寄乐于画”“以画养身”“天真自然”“以淡为宗”的新秩序。
而反观日本“文人画”在形成过程中似乎没有出现像中国或是李氏朝鲜一样有着明确文化身份与政治理想的文人士大夫群体。进入江户时代德川家康已经意识到“可以马上得天下,而不能马上治天下”,于是中国传统儒学,尤其是朱子学说这一能够与武家思想相制衡且亦能维护幕府统治的学说才进入到德川家康的视野中。此后,日本德川幕府第五代将军德川纲吉开启了“文治之治”的新时代,出现了学术繁荣、文化兴盛的“元禄文化”。(23)《中国文化史》载:“ところが、封建秩序が固定してきたことや、学問への社会的需要が高まってきたことなどにともない、封建社会を倫理的に支持する教学として、儒教、なかでも朱子学の有効性が意識されるようになったのである。ことに五代将軍綱吉のころから、従來の武断政治の風をあらため、文治主義の政策を採用して以來、幕府は積極的に儒学の獎励に乘り出し、羅山の孫信篤を大学頭とし、その私塾を湯島に移して学生の養成にあたらせた。”参见[日]家永三郎:《日本文化史》(第二版),东京:岩波书店,1984年,第181页。在这一系列文化政策的作用下的日本文化人、知识分子的数量开始逐渐增多,但是他们与中国文人士大夫群体依旧有所不同,既没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理想,更无“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个体道德的不断完善。
换言之,日本的文人士大夫始终处于一种缺席的状态。而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中,日本江户时代出现的“文人画”“南画”并没有明确的政治意图,也不是文人士大夫争夺话语权的重要场所。从某种程度而言,日本的“文人画”“南画”只是少数儒者、文化人,乃至武士群体谋生的手段之一。对此,江户时代的南画家金井乌洲曾在《无声诗话》中感叹道:“吾人今日,遭幸生平,身在草莽,笔耕生活,龌龊终年,故士气流成匠气,乃所以今之学者为人也。噫,不知后来高流之逸足,谁能腾踔风尘表骏骏更度越?”(24)[日]金井乌洲:《无声诗话》,《日本画谈大观》,东京:目白书院,1917年,第422页。可见,在日本南画家看来,从中国流传过来的文人画只是一种与日本土佐派、狩野派有所区别的一个画派而已。
基于此,日本南画家在接受与发展中国的文人画时更多时候是对笔墨意趣、形式内容的借鉴,从而彰显出日本这一民族善于吸纳外来艺术、兼容并包的文化特色。而这一点在南画家中西耕石的《西园雅集图》中得到了明显的展现,该画家所呈现出的“西园雅集”与明仇英的《西园雅集图》、李氏朝鲜金弘道的《西园雅集图六叠屏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仇英、金弘道笔下的“西园雅集”在画面上有意对“门”与“墙”进行营造,以此来体现出文人群体间的相互认同与欣赏,而中西耕石的《西园雅集图》则是将原本发生在私人园林中的集会场景置于自然山水之间,以此彰显清逸幽玄之美,完成了对“西园雅集”文化意象的视觉转换。
不仅如此,日本南画家还试图将“西园雅集”文化图式中的视觉元素移植到其他雅集题材绘画中,丰富与完善了南画家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意象的认知。比如,南画家富冈铁斋的《兰亭诗会图》(图6)描绘的是中国另一传统文化意象“兰亭集会”,画面布局紧凑,结构复杂,30余位文人墨客聚集在山涧,好不自在闲适。有趣的是,富冈铁斋笔下的这一文化意象在视觉呈现上却出现了“西园雅集”的身影。在画面的右下方出现了一位身着红衣面壁题字的文人,而这一形象便是对“西园雅集”中题石之人米芾的借鉴与模仿。如此一来便不难看出,日本南画家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意象存在着想象与再造的情况,他们试图将不同的雅集场景置于同一方寸之间,进而促成一种新的文化意象与视觉呈现。

图6 日本富冈铁斋创作的《兰亭诗会图》,纸本设色,144.7×59.7厘米,日本出光美术馆藏
由此可见,日本南画作为一种文化形态浓缩着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一个民族乃至一个时代的人文精神。日本南画家笔下的“西园雅集”一方面展现出了日本人对于中国文化的吸纳与创新能力,而另一方面也是向中国画坛呈现出文人艺术在异域的强烈回响。
五、结语
“西园雅集”文化意象以其经久不衰的生命力诠释着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作为承载着东亚文明传承的介质,催生着东亚文化圈的建立与发展,加速了东亚历史文明的进程,超越了不同国家与地区文化交流的表层逻辑,这既是中华民族“软实力”的彰显,也是东亚文化圈中儒家文化内在张力的典型体现。
其中,李氏朝鲜画家金弘道创作的《西园雅集图》借鉴了明人仇英立轴款的构图与场景元素,以此来表现文人士大夫群体的潇洒自在,凸显朝鲜画家的雅致品位,强调文人群体的身份认同;而日本江户时代流行的“西园雅集”文化图式则是对中国文人画笔墨意趣的继承与发扬。可以说,这种“共相”与“变异”是“西园雅集”文化意象不可分割的整体,它既保留了不同国家对同一意象阐释的空间,又展现了“和而不同”的艺术特征,呈现出文化艺术“因交流而多姿多彩,因互鉴而互补同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