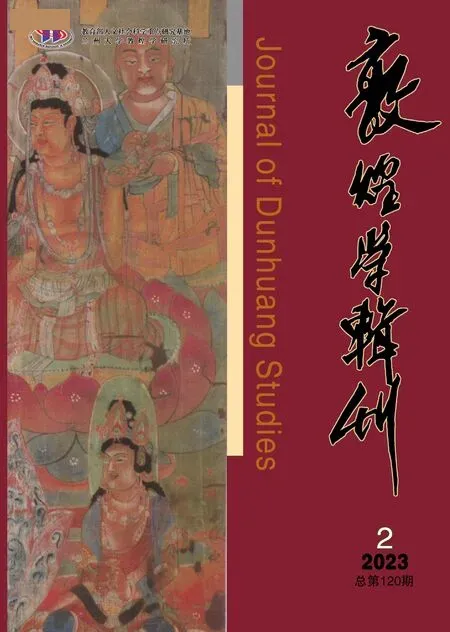佛教图像的叙事策略
——基于莫高窟第285 窟禅观思想的解读
张柘潭
(南京大学 哲学系·宗教学系, 江苏 南京 210023)
莫高窟第285 窟作为敦煌早期有纪年的代表性石窟, 历来以其独特的艺术风貌备受关注①相关研究文献综述可见李国、 夏生平《莫高窟第285 窟研究百年回顾与综述》, 郝春文主编《2014 敦煌学国际联络委员会通讯》,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4 年, 第86-116 页。 此后代表性成果包括: 宏正、 界平《佛教石窟造像功用思想研究——以凉州、 敦煌、 麦积山、 云冈等石窟造像为例》, 《敦煌学辑刊》 2014 年第1 期; 李银广《弥勒三会思想在敦煌壁画中的表达——浅析第285 窟南壁故事画的“特色” 之处》, 《华夏考古》 2014 年第4 期; 张建宇《敦煌西魏画风新诠——以莫高窟第285 窟工匠及分本问题为核心》, 《敦煌研究》 2015 年第2 期; [日] 石松日奈子著, [日] 筱原典生、 于春译《敦煌莫高窟第285 窟北壁供养人像和供养人题记》, 《敦煌研究》 2016 年第1 期; 马若琼《莫高窟第285 窟窟顶壁画题材与构图特征》, 《敦煌学辑刊》 2017 年第4 期; 张元林《从〈法华经〉 的角度解读莫高窟第285窟》, 《敦煌研究》 2019 年第2 期; 魏健鹏《元荣抄经与莫高窟第249 窟的营建关系探析》, 《敦煌学辑刊》 2020 年第1 期; 李银广《礼仪的空间: 敦煌莫高窟第285 窟石窟造型与空间布局再考》, 《装饰》2021 年第7 期; [日] 桧山智美著, 蔺君茹译《敦煌莫高窟第285 窟西壁壁画中的星宿图像与石窟整体的构想》, 《敦煌研究》 2022 年第4 期; 于向东《莫高窟第285 窟西壁两侧龛内人物身份研究》, 《敦煌学辑刊》 2021 年第3 期; 苗玲《莫高窟285 窟〈五百强盗成佛图〉 绘画空间研究》, 中国美术学院硕士学位论文, 2023 年。。 尽管大部分学者都认可该窟的禅修功能, 但对壁画主旨的解读仍有许多争议之处。在前贤的研究基础之上, 笔者尝试以佛教图像叙事逻辑的构建为入手处, 解读四壁图像的叙事主旨, 借由对第285 窟禅观思想的审视为佛教图像的叙事策略进行经验总结。
一、 西壁: 弥勒信仰与禅观思想的图像叙事
西壁的人物形象有日天、 月天、 凤车战士、 虎车战士、 毗瑟纽天、 帝释天、 四天王、 摩醯首罗天、 鸠摩罗迦天(童子天)、 毗那夜迦天(人身象首) 和供养天人等①吴健编著《中国敦煌壁画全集2 西魏》, 天津: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 2002 年, 图版说明, 第44-50 页。。 正龛内为倚坐佛像, 两侧壁各画八身供养菩萨, 旁边两个小龛塑坐禅比丘。 西壁诸天的形象糅合了佛教、 祆教、 印度教等诸元素, 是中西多元文明交流融合的表现。 与之相似, 窟顶四披的天象图有众多中国传统神话故事中的人物、 神禽和灵兽, 反映出南北朝时期儒、 释、 道三教合一的思潮, 也被认为是中国礼制祭天图像对外来文化的节制、 选择、 扬弃和消化②贺世哲《莫高窟第285 窟窟顶天象图考论》, 《敦煌研究》 1987 年第2 期, 第1-13 页; 姜伯勤《 “天” 的图像与解释——以敦煌莫高窟285 窟窟顶图像为中心》, 氏著《敦煌艺术宗教与礼乐文明: 敦煌心史散论》,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6 年, 第55-76 页。。
虽然西壁诸天吸收进佛教以外的天神形象, 并且人物形象的空间排布表现出当时中亚流行的信仰观念①姜伯勤《 “天” 的图像与解释——以敦煌莫高窟285 窟窟顶图像为中心》, 氏著《敦煌艺术宗教与礼乐文明: 敦煌心史散论》, 第70 页。, 但它们仍是在佛教叙事框架之下, 叙事主旨应当结合龛中塑像综合考察。 在南北两侧小龛中, 禅僧背后圆光及火焰纹表明他们正处于禅定之中, 龛顶的莲花宝盖暗示他们已经见性开悟, 头顶上方各有两身供养飞天, 身后还有比丘持花供养或手接花雨(图1-3), 衬托出坐禅比丘是证果阿罗汉的特殊身份。

图1 莫高窟第285 窟西壁南龛左侧二比丘(采自敦煌文物研究所《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第1 卷》,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11 年, 图121 局部)

图2

图3
《弥勒下生经》 中提到, 弥勒菩萨成佛的消息经地神传至四天王宫乃至三十三天、艳天(夜摩天)、 兜率天、 化自在天、 他化自在天以及梵天, 连魔王也率欲界无数天人至弥勒佛处礼拜。②[西晋] 竺法护译《弥勒下生经》, 《大正藏》, 第14 册, 第421 页。异译本《弥勒下生成佛经》 亦言, “诸天龙神王, 不现其身, 而雨华香, 供养于佛。”③[后秦] 鸠摩罗什译《弥勒下生成佛经》, 《大正藏》, 第14 册, 第424 页。壁画中的四天王、 帝释天、 毗瑟纽天、 毗那夜迦天等诸天皆在六欲天, 即经中提及的四天王宫、 三十三天、 艳天、 兜率天、 化自在天、 他化自在天; 摩醯首罗天和鸠摩罗迦天在色界, 经中所说的梵天即属于色界。 供养佛陀的天雨华香在诸天周围纷飞, 同时象征闻法的天时之乐。 可以说壁画上的诸天形象是对经中闻法天众的具体呈现。 尽管诸天形象融摄了佛教以外的元素, 但就整幅壁画的叙事主旨而言, 更有可能是弥勒成道后最初为众天说法的场景, 因此笔者倾向于认为中间圆券大龛中的倚坐佛是说法的弥勒。 北凉、 北魏时期开凿的莫高窟第268 窟、 272 窟和275 窟主尊以及第254 窟中心塔柱正面主尊均为弥勒, 其中第272 窟的弥勒为圆券龛倚坐形象, 与第285窟基本一致, 可见早期敦煌弥勒信仰的流行程度。
在《弥勒下生经》 中, 佛言迦叶将会辅佐弥勒劝化众生, 彼时迦叶结跏趺坐, 正身正意, 系念在前④[西晋] 竺法护译《弥勒下生经》, 《大正藏》, 第14 册, 第422 页。, 正如小龛中坐禅比丘塑像那样。 由于迦叶一直等待弥勒出世, 所以弥勒佛与迦叶共同出现应是弥勒下世的表现。 《弥勒下生经》 云, 弥勒佛来到摩竭国禅窟, 伸右手示迦叶, 向大众称颂他“头陀苦行最为第一”, 并取种种花香供养迦叶。两龛坐禅比丘身旁皆绘有比丘持花供养, 设计意涵或来源于此。 这部分情节发生于龙华三会中的“最初之会”。
迦叶坐禅像的小龛外部南侧绘一位执雀仙人, 此应是执雀问佛生死的裸形外道尼乾子。⑤王惠民《鹿头梵志与尼乾子》, 氏著《敦煌佛教图像研究》,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6 年, 第24 页。《长阿含经》 卷四载, 迦叶正是从一名尼乾子处得知佛陀已经入灭。 尼乾子的出现进一步佐证了南龛比丘为迦叶, 二者共同将佛灭与弥勒成佛联系起来。
于向东注意到, 两尊坐禅比丘像身后的倒三角形靠背在敦煌早期石窟中仅出现于交脚菩萨身后, 如北凉的第275 窟和北魏的第435 窟。⑥于向东《莫高窟第285 窟西壁两侧龛内人物身份研究》, 第85-96 页。这两尊比丘像同主尊一样被安奉在圆券龛中, 虽是比丘样貌, 却有资格与弥勒佛并置, 暗示二人共行菩萨道, 同属未来成佛之列。 《法华经》 中佛陀最先为迦叶授记, 随后应目犍连等人请求亦为之授记。 相较其他弟子, 目犍连虽先佛入灭, 却最有可能因“神通第一” 而被塑造于此, 因为神通也是禅定功德的重要表现。 犍陀罗“初转法轮” 浮雕常表现比丘结跏趺坐于佛前闻法, 他们身体微侧, 面向佛陀, 共享同一个空间。 第285 窟西壁主尊与禅定比丘的组合可能对犍陀罗艺术有所借鉴, 但过于杂糅的叙事手法显然不算成熟, 故未能得到延续。两尊坐禅比丘像对于凸显石窟的禅观功能有着十分重要的激励和典范作用, 显示出设计者的独妙匠心。
西壁的人物形象大体是围绕《弥勒下生经》 进行安排的, 细节上的处理则有较多创造性和灵活性。 如窟中禅定的迦叶除了遵循文本描述, 还借鉴《观佛三昧海经》 中“憍陈如与四比丘化作一窟”①[东晋] 佛陀跋陀罗译《观佛三昧海经》 卷8, 《大正藏》, 第15 册, 第684 页。的组合方式, 为其增加四位比丘侍者, 不仅展现出坐禅功德, 也凸显出禅法与弥勒信仰的密切关系。 《弥勒下生经》 中提到, 来至弥勒处所的首要方法就是禅观“十想”②[西晋] 竺法护译《弥勒下生经》, 《大正藏》, 第14 册, 第422 页。, 揭橥禅观是实践弥勒信仰的重要途径。 弥勒所说思惟十想的大部分内容在《观佛三昧海经》 卷二亦有详述, 确实可与“过去释迦文佛与汝等说” 相印证。
南北小龛的坐禅比丘连同窟顶四披边沿的34 身坐禅比丘也是弥勒上生信仰的反映。自东晋始, 北方流行弥勒信仰, 以道安法师为代表, 特重对“兜率净土” 与禅法的结合。 通过入三昧定而以神力分身飞升兜率请弥勒决疑, 是为弥勒上生信仰。
值得一提的是, 宿白先生推断全窟壁画并非同时完成, 绘制先后为西壁、 窟顶和南壁、 北壁和东壁三个阶段③宿白《参观敦煌莫高窟第285 窟札记》, 氏著《中国石窟寺研究》,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96 年, 第210 页。, 张建宇亦提出窟内壁画的绘制存在西壁、 东壁和北壁以及南壁三个工匠集团。④张建宇《敦煌西魏画风新诠——以莫高窟第285 窟工匠及粉本问题为核心》, 第4-14 页。不过南北两壁各有四个小禅室显然要在壁画绘制之前凿成, 故石窟功能和用途最初当有统一规划, 壁画内容的设计亦非随意为之。 覆斗形窟顶壁画交错布置着供养佛的天人诸花和象征天体的中原神祇正是将佛教的“天” 作民族化想象,整体内容并不在观想之列。 石窟的覆斗顶实摹仿自墓葬壁顶, 在顶部表现“天” 是中国古代墓葬的惯用手法⑤王洁《敦煌早期覆斗顶窟形式初探》, 《敦煌研究》 2008 年第3 期, 第22 页; 宿白《参观敦煌莫高窟第285 窟札记》, 氏著《中国石窟寺研究》, 第209 页。, 且窟顶绘制与南壁同时, 四披边沿的禅定比丘成为连接四壁观修内容与“天” 的纽带, 可见这样的设计是通过精进禅修超越生死轮回的表达。
《观佛三昧海经》 卷七“观四威仪品” 言迦叶、 目犍连等诸弟子禅坐于窟中, 以神通方式随佛去那乾诃罗国闻法, 他们化作琉璃山或雪山, “山上皆有流泉浴池七宝行树, 树下皆有金床银光, 光化为窟”。⑥[东晋] 佛陀跋陀罗译《观佛三昧海经》 卷7, 《大正藏》, 第15 册, 第679 页。四沿坐禅比丘的禅定境界和窟外优美怡人的山林风光或许即受此启发。 在此叙事语境之下, 西壁坐禅比丘作为阿罗汉成就者对于南北两壁下方四个小禅室而言具有典范意义, 不仅彰显出禅观在弥勒信仰中的重要作用, 亦与窟顶四沿的坐禅比丘上下相呼应, 在空间叙事上保持了禅观主旨的统一性。 从整个石窟的叙事架构来看, 有关弥勒信仰的禅观理念显然十分有序地贯穿于整窟壁画。 该窟壁画是以禅观为中心、 借助西壁南北两龛坐禅比丘像将弥勒下生人间和窟顶四沿比丘神升兜率两种叙事进行了“套嵌”, 共同为禅观修行营造出庄严圣妙的净土世界。
二、 南壁新解: “观修五悔” 与“法华三昧观法” 相融摄
学界一般认为, 南壁的故事画较多宣扬戒律, 对坐禅僧人具有警示作用。 这五幅故事画其实并非互不相干, 而是有着特定的内在逻辑。 如巫鸿所言, “图像程序与单独图像不可分割, ‘程序’ 解读的是画面间的联系而非孤立的画面。 希望解释的不是孤立的艺术语汇, 而是具有特定历史意义的完整作品。”①巫鸿《研究中国古代宗教美术的一些心得》, 《世界宗教研究》 2021 年第2 期, 第13 页。第285 窟南壁的图像显然也需要放置在一个符合佛教语境的特定“程序” 中分析。 鉴于僧人禅修亦需行忏法, 南壁故事画大体可与《观佛三昧海经》 中的忏悔“五法” 相应, 兼有“法华三昧观法” 的内容。
(一) 南壁东段: 故事画中的“观修五悔”
《观佛三昧海经》 卷九言观“立像” 时当发大誓愿“专求佛菩提道”, 次第行忏悔、 请佛、 随喜、 回向和发愿五法。②[东晋] 佛陀跋陀罗译《观佛三昧海经》 卷9, 《大正藏》, 第15 册, 第690 页。“观修五悔” 的内容较为抽象, 因此选择与主题相应的故事画更适合表现。 将南壁五幅故事画和相关文本进行对照分析将有利于把握绘画主题, 今试分析如下。
1. 《佛度水牛生天缘》 对应“忏悔”。 故事出自《撰集百缘经》 卷六, 言大恶水牛和五百放牛人过去由于造恶口业而不能解脱, 如今蒙佛化度而得道证果③[吴] 支谦译《撰集百缘经》 卷6, 《大正藏》, 第4 册, 第232 页。, 说明想要获得善报应当首先忏悔往昔所造恶业。 南壁东端主要表现了大恶水牛在水泽中翘尾抵角、 刨地叫吼以及被降服后长跪伏首的样子, 上方的坐禅比丘当是后来成为沙门的放牛人。 大恶水牛因为受到佛陀的开示而“深生惭愧, 欻然悟解, 盖障云除, 知在先身在人道中所作恶业, 倍生惭愧”, 不久命终之后却生忉利天, 彰显出“忏悔” 在因果律中的积极作用。
2. 《化跋提长者姊缘》 对应“劝请”。 故事最早出现在化地部律典《五分律》 中,讲述迦叶、 目犍连、 阿那律、 宾头卢以神通度化不信乐佛法僧的跋提长者和长者姊。④[南朝宋] 佛陀什、 竺道生等译《弥沙塞部和醯五分律》 卷26, 《大正藏》, 第22 册, 第170 页。壁画仅选取故事的后半段表现宾头卢以神通耐心度化长者姊的曲折和善巧。 神通虽依禅定而获得, 但只有在度化众生时使用才不算犯“突吉罗” 戒。 宾头卢尊者在《弥勒下生经》 中也是佛陀要求不般涅槃至佛法灭尽的四大声闻之一。 在斋供仪式中宾头卢尊者会被斋僧劝请降临道场作“证盟”, 还有《请宾头卢经》 专门讲解如理恭请宾头卢尊者的方法。 以不取涅槃、 护持正法的宾头卢尊者事迹表达正法久住、 法轮常转的“劝请” 之意再合适不过。
3. 两幅闻法图对应“随喜”。 《五百强盗因缘》 出自《大般涅槃经》 “梵行品”。 壁画描绘了五百强盗对抗官兵、 被捕挑目、 佛前闻法等内容, 画面占比甚大, 当有其特殊的社会历史背景。 文本提到五百强盗失去双目后啼哭号啕, 闻佛说法后不仅重获光明且俱发菩提心, 但并未言其出家。①[北凉] 昙无谶译《大般涅槃经》 卷16, 《大正藏》 第12 册, 第458 页。 另, 《大方便报佛恩经》 卷5“慈品”、 《经律异相》 卷5 和《大唐西域记》 卷6 也记载了这个故事, 均无出家情节。画面中五位在家人跪在佛前, 正是他们闻法发心的情节。 其后有五比丘亦跪在佛前, 图式与之相同, 这部分内容实来自《佛度水牛生天缘》的内容, 即五百放牛人闻法后求索出家, 于是“须发自落, 法服着身, 便成沙门”。 画面跳出旧有的故事框架, 用连续相同的构图形成一个新的图像叙事, 让一个“善” 的情节连缀着另一个“善” 的情节, 形成后者对前者随顺和认可、 对闻法功德“随喜” 的意涵(图4)。 这两个情节在更往后的“法华三昧观法” 中同样发挥重要作用, 详论留待后文。

图4 五百强盗因缘后半部分(采自吴健编著《中国敦煌壁画全集 2 西魏》, 图110 局部)
4. 《婆罗门闻偈本生》 对应“回向”。 故事出自《大般涅槃经》 “圣行品”, 讲述佛陀在过去时作大婆罗门, 为闻罗刹半偈而舍身供养。 南壁西端壁画受绘画空间所限,仅表现婆罗门求偈、 自投树下和释提桓因张臂接取等简单情节。 其实婆罗门舍身以报偈价并不是为了独享善法, 而是希望能够与众生共享, 利益无量大众。②[北凉] 昙无谶译《大般涅槃经》 卷14, 《大正藏》, 第12 册, 第450 页。这是一种具有“回转趣向” 性质的做法, 昭示出舍身行为的大乘菩萨道精神, 尤能开阔修行者的胸襟。 因此该故事画并非单纯赞颂为正法献身, 还提醒修行者求法的目的和利益, 认识到“回向” 具有扩大行为价值的利他作用。
5. 《沙弥守戒自杀缘》 对应“发愿”。 《贤愚经》 中“沙弥守戒自杀品” 原是赞叹持戒之人“宁舍身命, 终不毁犯”, 但壁画的叙事方式却更加凸显誓愿守戒的功德和成就。 壁画详细表现了剃发、 受教、 色诱、 自刎、 哭诉、 交罚金、 火化、 起塔等情节。 法显译本《大般涅槃经》 记载, 须跋陀罗于佛前“入火界三昧而般涅槃”①[东晋] 法显译《大般涅槃经》 卷3, 《大正藏》, 第1 册, 第204 页。, 沙弥火化即用象征涅槃的“火中禅定图” 表示沙弥之殒身实已尽漏成道。 沙弥恪守师嘱“若持禁戒, 必能取道” 而舍身护戒, 其内在动力在于发愿“净修梵行, 尽漏成道” 的决心②[北魏] 慧觉等译《贤愚经》 卷5, 《大正藏》, 第4 册, 第380-382 页。,这种成道的誓愿在火中禅定的形象中得以达成。 可见壁画叙事更注重“发愿” 对守戒的激励作用。 发愿也属于广义上的“发心”, 但更有针对性、 具体性, 也因誓愿的内向约束而更具自利性, 对持戒者意义甚大。
中国佛教的忏法在晋代便已有之, 道安和慧远等人均曾积极推行忏法。 宋代净源谓: “汉魏以来, 崇兹忏法, 未闻有其人者, 实以教源初流, 经论未备。 西晋弥天(道安) 法师, 尝著四时礼文; 观其严供五悔之辞, 尊经尚义, 多摭其要。 故天下学者,悦而习焉。 陈、 隋之际, 天台智者撰《法华忏法》 《光明》 《百录》, 具彰逆顺十心,规式颇详, 而盛行乎江左矣。”③[宋] 净源《圆觉经道场略本修证仪》, 《卍续藏》, 第74 册, 第512 页。《观佛三昧海经》 和《法华经》 盛行北方并影响到江南, “观修五悔” 的内容正是在轨范律仪与思惟禅定并重的时代背景下受到重视。 以上五幅故事画被有机地展现在小禅室外, 其绘画主旨以观修五悔的视角来解读, 从禅修的整体过程来看是十分可行的。
(二) 南壁西段: 对“法华三昧观法” 的融摄
在五百强盗闻法图和五百比丘闻法图之后, 随即为山林修行图, 比丘们或持经, 或辩经, 或禅定, 并且画面随着层层山峦延伸到西端的二佛并坐图, 再现了“精勤修习,得阿罗汉果, 三明六通, 具八解脱, 诸天世人, 所见敬仰”④[吴] 支谦译《撰集百缘经》 卷6, 《大正藏》, 第4 册, 第232 页。。 二佛并坐图则是对“法华三昧观法” 的展示。 “法华三昧观法” 要求正念《法华》, 思惟释迦佛与多宝佛塔中并坐, 十方化佛“各有一生补处菩萨一人为侍, 如释迦牟尼佛以弥勒为侍。”⑤[后秦] 鸠摩罗什译《思惟略要法》, 《大正藏》, 第15 册, 第300 页。可以发现, 二佛身侧带头光的胁侍比丘也出现在前两幅闻法图中, 当与观想中“有一生补处菩萨为侍” 有关, 同时勾勒出通过禅修证果成就佛道的修行次第。
虽然两幅闻法图共同构成“随喜” 的意涵, 连同山林修行图最终指向释迦、 多宝二佛并坐(图4), 但《五百强盗因缘》 的结尾落在“发心” 上; 《佛度水牛生天缘》的内核仍不出“忏悔”。 《观佛三昧海经》 “观像品” 中提到, 忏悔能够成就声闻最高果位, 观像前后或遇到观像困难都应当诚心忏悔。⑥[东晋] 佛陀跋陀罗译《观佛三昧海经》 卷9, 《大正藏》, 第15 册, 第690 页。“忏悔” 实际上伴随着观像的整个过程。 山林修行图除了是对文本中五百比丘“精勤修行” 的再现, 还与“法华三昧法”的首句“三七日一心精进如说修行” 相呼应, 因此其“精进” 意涵实乃二者共享。 五百强盗闻法图、 五百比丘闻法图和山林修行图以长卷的形式次第展开, 最终指向二佛并坐图, 展示出发心、 忏悔和精进对修行“法华三昧观法” 的重要意义。
综上观之, 《五百强盗因缘》 故事画在《大般涅槃经》 文本的基础上进行了改编,不仅杂揉进《佛度水牛生天缘》 的情节, 还融摄“法华三昧观法” 的内容。 这几个情节的衔接在叙事策略上选择用相同的人物形象消解掉来自于不同文本的人物身份, 从而融合成一个新的、 具有禅观意义的图像叙事。 北周第296 窟主室南壁的《五百强盗因缘》 同样包含山林修行情节即当以此为参考。 二佛并坐图虽然在南壁所占比例不大,但以带头光的胁侍比丘为线索, 将“法华三昧观法” 的要素套嵌在象征“观修五悔”的故事画中(图5), 一方面表明五法忏悔是实现观修成功重要的手段, 另一方面也肯定了观像忏悔除罪的功能, 二者是观像与忏悔关系在图像表达上的重要探索和创新。

图5 莫高窟第285 窟南壁内容分析一览(采自数字敦煌官网, 作者标注)
“观修五悔” 后来成为智顗(538-597) “忏悔意根法” 的基本内容, 是《法华三昧忏仪》 中止观修行与忏悔仪式的重要组成部分。 莫高窟第285 窟完工于大统五年(539), 南壁的五幅故事画与二佛并坐图是《观佛三昧海经》 中“观修五悔” 和《思惟略要法》 中“法华三昧观法” 的视觉呈现。 二者相融摄已初具智顗大师“法华三昧忏法” 的雏形, 因此南壁图像对考察中国佛教忏法的发展也有着重要的史料价值。
三、 东壁与北壁: 禅观与供养相交融的尝试
(一) 东壁: 禅观与供养的交融
《思惟略要法》 中提到, “行者若欲生于无量寿佛国者” 应当观无量寿佛。 “观无量寿佛法” 教授了两种观法, 钝根者的观法需要先观佛的身形, 然后观其身如琉璃放白光, 在光中观无量寿佛; 而利根者则直接在光明中观像。 钝根者和利根者的观想次第虽有差别, 但最终都是在光中见佛。①[后秦] 鸠摩罗什译《思惟略要法》, 《大正藏》, 第15 册, 第299 页。东壁门南北两侧各画一铺无量寿佛说法图(图6),两铺内容大同小异, 应是这两种观法的最终呈现。

图6 莫高窟第285 窟东壁一览(采自吴健编著《中国敦煌壁画全集 2 西魏》, 图154, 第146-147 页)
然而“观无量寿佛法” 并不是壁画内容的全部, 因为观法中并未提及菩萨和比丘,壁画中却有所添加。 以门北侧一铺为例, 根据榜题可知, 无量寿佛右侧为一躯尊名不详的菩萨②据石松日奈子的了解, 过去被识读为“无尽意菩萨” 的榜题根据光学调查应为“无量寿佛”, 仍是主尊题名。和一躯观音菩萨, 左侧为文殊师利菩萨和大势至菩萨; 上方右侧为阿难、 舍利弗, 左侧为迦叶和目犍连③吴健编著《中国敦煌壁画全集 2 西魏》, 第73 页。。 除了观世音和大势至是无量寿佛的两位协侍菩萨, 其他人物与无量寿佛并无直接关联。 这种罕见的组合方式或许和供养人的需求有关。
据《无量寿经》 的描述, 无量寿佛不仅在彼国七宝讲堂为诸声闻、 菩萨大众广宣妙法, 还应阿难的祈请在娑婆世界向四众示现了无量寿国所有微妙严净自然之物、 百千由旬七宝宫殿等景象。④[魏] 康僧铠译《无量寿经》 卷2, 《大正藏》, 第12 册, 第273-278 页。所以摩诃迦叶、 舍利弗、 目连和阿难等比丘众⑤《无量寿经》 和《阿弥陀经》 皆有舍利弗、 目连、 摩诃迦叶和阿难出场。理论上可以与无量寿佛及诸菩萨共处于同一时空。 东壁入口上方绘三世佛及一排小佛像, 或同为表现无量寿佛的“无著无碍”。⑥[魏] 康僧铠译《无量寿经》 卷2, 《大正藏》, 第12 册, 第277 页。更为重要的是, 《无量寿经》 为信众提供了一个往生西方净土最为简便易行的方法: “他方诸大菩萨发心欲见无量寿佛, 恭敬供养及诸菩萨声闻之众。 彼菩萨等命终得生无量寿国, 于七宝华中自然化生。”⑦[魏] 康僧铠译《无量寿经》 卷2, 《大正藏》, 第12 册, 第278 页。不过净土三经中皆未记载无量寿佛国诸声闻的具体名号, 因此将佛陀最负盛名的四大弟子与无量寿佛和诸菩萨绘在一起, 是信徒为了方便“恭敬供养” 的创造性组合, 佛像下方绘多身供养人像且有榜题和发愿文便是最直接的证明。
莫高窟第285 窟东壁整体上以“观无量寿佛法” 为思路框架, 在图像的具体呈现上同时关涉到《无量寿经》 中的内容, 使两铺壁画兼顾禅观和供养的双重功能。 二者的兼容, 反映出西方净土信仰无论是在禅观还是在供养层面都具有重要的地位, 满足不同群体的需求。
(二) 北壁: 禅观与供养的冲突
结合《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 和《伯希和敦煌石窟笔记》 了解到, 第285 窟北壁上部绘有两铺无量寿佛①《伯希和敦煌石窟笔记》 载, 第四幅“与第一幅画面的题识完全相同, 唯有后者写作‘于三途于八难’。”但由于第四铺的录文没有明确记为“无量寿佛”, 后来贺世哲认为该铺应是七佛中的拘楼孙佛。 敦煌研究院编《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6 年, 第114-117 页; [法] 伯希和撰, 耿昇译《伯希和敦煌石窟笔记》, 兰州: 甘肃人民出版社, 2007 年, 第240 页; 贺世哲《莫高窟第285 窟北壁八佛考释》, 收入段文杰等编《1990 敦煌学国际研讨会文集(石窟考古编) 》, 沈阳: 辽宁美术出版社,1995 年, 第241 页。、 一铺拘那含牟尼佛、 一铺迦叶佛, 另有三铺榜题漫漶, 其中最西端一铺绘二佛二菩萨。 下部各龛之间画千佛及供养菩萨, 底部画药叉。
据贺世哲最初的分析, 由于拘那含牟尼佛和迦叶佛自东向西分别处于第五、 第六铺的位置, 与七佛名次的排列相符, 壁画表现的应是七佛与弥勒, 并指出《观佛三昧海经》 的“观四威仪品” 和“念七佛品” 皆言及观七佛与弥勒。②贺世哲《莫高窟第285 窟北壁八佛考释》, 第241-251 页。
北壁七铺的八尊佛像若以拘那含牟尼佛、 迦叶佛为考察线索, 在次序和尊像数量上确实与“见七佛已, 见于弥勒” 的表述较相吻合(图7)。 不过更能确定壁画与“念七佛品” 关系的是, 诸佛像与下方各龛之间所绘千佛和菩萨也能衔接得上。 观想要求“见弥勒已, 贤劫菩萨一一次第逮及楼至”, 说明随后还应观想贤劫菩萨及诸佛乃至到最后一佛楼至佛。③[东晋] 佛陀跋陀罗译《观佛三昧海经》 卷10, 《大正藏》, 第15 册, 第693 页。北壁整幅壁画自上而下呈现出与“念七佛品” 相一致的观想内容,和后续文本卷十一“念十方佛品” 也能够图文相应, 为“念佛禅” 的观修次第展示出较为清晰的图像逻辑。

图7 莫高窟第285 窟北壁七铺八佛(采自数字敦煌官网, 作者标注)
然而壁画中出现的一铺二佛和无量寿佛表明问题并不简单。 张元林即认为北壁是“二佛并坐” 像与“过去七佛” 的组合。④张元林《从〈法华经〉 的角度解读莫高窟第285 窟》, 第9-15 页。贺世哲指出, 北壁原来计划画八铺说法图,再从拘那含牟尼佛与迦叶佛的排列顺序来看, 应是从东往西安排的。 但在具体绘制过程中则把西端两铺合为一铺, 变为了七铺。①贺世哲《石室札记——重新解读莫高窟第285 窟北壁八佛》, 《敦煌研究》 2003 年第1 期, 第22-24 页。张景峰进一步认为, 各铺是由不同家族作为施主和供养人绘制而成的, 但纪年表明榜题时间应是从西至东依次完成。②张景峰《窟主与敦煌石窟的开凿与重修——以阴氏家族为中心》, 沙武田主编《丝绸之路研究集刊》 第1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7 年, 第253-267 页; 张景峰《敦煌阴氏家族与莫高窟第285 窟的营建》, 氏著《敦煌石窟考古与艺术研究文集》,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16 年, 第261-297 页。
由于佛像的排列次序和绘制先后的不统一, 学界普遍认可的一种推断是壁画发生过改动。 壁画最初应是以观想为目的自东向西排布七佛与弥勒佛, 但受供养人意见的干扰在绘制过程中出现了变更, 这意味着供养人意志与禅观理念发生了冲突。 绘制在同一铺的二佛二菩萨(图8) 并不是常规意义上的二佛并坐, 因为二者只是挨得较近, 实际上相互独立, 没有像南壁的释迦、 多宝(图9) 那样共坐于同一个法座或共享伞盖。 “念七佛品” 中, 前六佛的次第观想内容较为充实, 而对释迦牟尼和弥勒的观想仅有“释迦牟尼佛身长丈六, 放紫金光住行者前; 弥勒世尊身长十六丈” 寥寥一句。 西端二佛靠得很近恰好可与文本中释迦、 弥勒的观想节奏相对应。 但供养人选择把最初相邻的两铺合为一铺应是受法华信仰影响而作出的改动, 这显然并非设计者的原意。

图8

图9
贺世哲推测东起第一铺的发愿文中写滑黑奴“敬造无量寿佛一区” 是擅自对毗婆尸佛名号的改动, 但也有可能是榜题书手的笔误。③贺世哲《莫高窟第285 窟北壁八佛考释》, 第240 页。东山健吾则较为肯定地指出, 应是供养者“改变了想法, 无视最初的计划, 加进了无量寿佛。”④[日] 东山健吾《敦煌三大石窟》, 东京: 讲谈社, 1996 年, 第85 页。该铺与佛名受争议的第四铺发愿文不仅文本相同笔迹也很相似, 且供养施主皆为“滑” 姓⑤[日] 石松日奈子撰, [日] 筱原典生、 于春译《敦煌莫高窟第285 窟北壁供养人像和供养人题记》, 第12-25 页; 徐自强、 张永强、 陈晶编《敦煌莫高窟题记汇编》,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14 年, 第284-287 页。。 姜伯勤认为“滑” 姓当是来自滑国的嚈哒人。①姜伯勤《中国祆教艺术史研究》,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4 年, 第208 页。西迁中亚的嚈哒人即以“滑” 为姓, 其政权在6 世纪下半叶受波斯和突厥的夹击而灭亡。 西魏时(535-556) 移居到敦煌的嚈哒人应是以家族集团的方式参与了第285 窟七佛说法图的部分供养。 嚈哒人敬拜光明之神阿胡拉·玛兹达(Ahura Mazda), 而无量寿佛有“无量光” 之意, 意涵与之相似。 他们把本应是毗婆尸佛和拘留孙佛的两铺尊像皆题为“无量寿佛”, 也许是当作佛教的阿胡拉·玛兹达来供奉。 这恐怕是七佛名号遭到改动的重要原因之一。
由于每铺壁画受不同家族独立供养, 他们未必在意壁画的禅观功能, 反而会为家族利益向更有信心的释迦、 多宝二佛或无量寿佛寻求庇佑, 所以改动了佛像的部分细节或名号。 虽然在形式上仍然符合最初绘制八尊佛像的设想, 但是原来规划的图像叙事思路却遭到破坏。 北壁迦叶佛、 拘那含牟尼佛与无量寿佛相并置而引发的身份辨识问题, 可以说是禅观与供养两种不同需求共同作用的结果。
四、 结语
从对第285 窟四壁内容的分析可以发现, 该窟设计以禅观为第一诉求, 兼有供养功能。 覆斗形窟顶对“天” 的表现并不属于观想内容, 但四披边沿坐禅比丘的绘制传递出通过修道成佛超越生死轮回的意义。 佛教图像中的禅观叙事, 充分展现出《观佛三昧海经》 《思惟略要法》 《弥勒下生经》 和《无量寿经》 等佛经的具体内容。 其中《观佛三昧海经》 是构建石窟叙事框架的重要依据, 启发了西壁两龛内壁供养比丘、 窟顶四披坐禅比丘、 南壁“观修五悔” 故事画以及北壁七佛与千佛的表现方式。 此外, 诸佛胸口多依“观如来脐相” “见佛心相” 而绘有宝花, 在莫高窟中数量最多②王惠民《如来卍字相与如来心相》, 氏著《敦煌佛教图像研究》, 第11 页。, 可见该经对第285 窟的营建影响最大。
西魏以佛教为立国大统, 元荣治期的敦煌时局动荡, 佛门四众愿证菩提、 求生兜率抑或往生净土成为普遍风尚, 加之中西交流、 南北疏通, 禅观的修行法门也十分多样。各种反映禅观思想的图像被创造性地融合在一起, 展现出西魏时期禅修和信仰的丰富样态, 而在融合的方式上, 则呈现出佛教图像特有的叙事策略, 兹略述如下:
(1) 佛教图像的杂糅性指向特定的叙事主旨, 来自不同文本的人物形象因其内在联系为图像逻辑的构建提供依据。 贺世哲最早指出第285 窟图像的杂糅性。 他觉察到西壁图像“是杂糅诸经、 传说, 甚至某些图像的粉本, 苦心创作的。”③贺世哲《敦煌莫高窟第285 窟西壁内容考释(摘要) 》, 《敦煌研究》 1988 年第2 期, 第54-56 页。虽然人物形象或场景的塑造受不同文本和粉本的多重影响, 但在判定叙事主旨时, 人物身份、 关系和空间语境则更有线索可循。 扬之水言, “从(石窟) 纹样的定名入手, 追索细节意象之究竟, 便如同考校诗词歌赋的用典, 出典明了, 其中多层次的表现内容也就随之浮现出来。”①扬之水《佛入中土之“栖居” (一) ——敦煌早期至隋唐石窟窟顶图案的意象及其演变》, 氏著《曾有西风半点香》,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2 年, 第7 页。这一研究思路对考察佛教图像的叙事逻辑同样具有参考价值。 无论图像如何杂糅, 厘清各形象关系显然更有助于把握叙事主旨, 而形象关系的厘清与构建可以从典籍文献中获得支持。
(2) 佛教图像的多重叙事具有互通性, 这种互通性不仅包括对各种思想理念的融摄, 也包括对禅修与供养抑或出世与入世不同诉求的接纳与满足。 第285 窟东壁和北壁诸佛图像除了用于禅观也兼顾礼拜供养, 壁画的巧妙布局使实践层面的观想修行和信仰层面的累积功德在图像叙事中得到交融, 展现出这类图像的多重叙事功能。 尽管由于禅观和供养的不同诉求会造成壁画细节上的矛盾和冲突(如北壁的佛名改动), 却十分生动地反映出禅修者与供养人两种需求的互动关系。
(3) 佛教图像中思想理念和修行法门的表达通过不同情节的连缀、 杂糅或套嵌来实现。 这是敦煌壁画极具特色的创作手法, 也为佛教史研究提供宝贵的图像资料。 作为禅观实践的视觉呈现, 第285 窟南壁图像将多情节故事画进行穿插排布以呈现观修次第, 反映出佛教史中观修五悔和法华三昧观法相结合的尝试。 此外, 南壁将两个不同出处的“佛前闻法” 以相同的图式连缀并置建立“随喜” 的叙事意涵, 西壁两龛坐禅比丘像将兜率净土和未来人间净土两种不同语境的图像叙事相“套嵌”, 均是极为突破常规的表现方式。
构建各图像之间的逻辑关系是把握它们如何阐释佛学理念的重要途径。 以上对第285 窟图像叙事策略的分析可以为佛教图像研究提供一种更贴近佛教自身的宗教学视角。 对叙事逻辑的梳理和构建, 其意义并不在于去找寻一种程式化的解读范式, 而是借助其叙事方式和语境更全面地认识佛教中国化进程中的宗教实践和信仰世界。
附记: 文章主体内容曾于2021 年10 月“陆疆与海疆: 多元文明的交流与共生”博士生学术会议上作口头报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