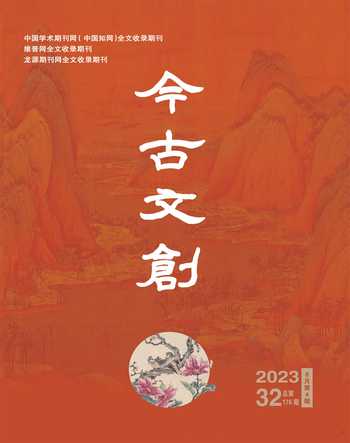张爱玲小说中的服饰描写
【摘要】当服饰中的文化逐渐成为一种符号,其代表的含意也会被人们接受,成为一种有意韵的表达。张爱玲的小说中对服饰的描述具有很强的叙述性,小说中人物的服饰描写都是她精心设计的,在张爱玲的笔下,服饰和人物是和谐共存的,服饰已经成为人物灵魂的一部分。这其中不仅有她个人的审美意蕴,还有很强烈的象征意义,从中可以看到人物的性格和命运。本文以张爱玲小说《金锁记》和《沉屑·第一炉香》为例,探究张爱玲小说中的服饰描写。
【关键词】张爱玲;服饰描写;叙事艺术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3)32-0032-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3.32.009
从人类文明发展的角度来看,服饰是人类作为高级灵长类动物区别于其他动物的一个特点。最初以树叶蔽体到穿上各式各样的服饰,服装从原料到穿到人的身上就已经不再仅仅是自然价值,当基本达到了御寒蔽体功能之后,人们对于服装的颜色造型等创造,就具有了文化意义。
一块布本身没有完整的意义, 但将其做成服装穿在人的身上,就不仅具备御寒遮羞的实用功能,日积月累起来的各种文化符号进入服饰系统中并得到确认,服饰就具有了越来越多的象征含义。沈从文就曾直接地指出“装扮又是一种内心思想的持续表现,一种语言,一种象征”。[1]当服饰中的文化逐渐成为一种符号,其代表的含意也会被人们接受,成为一种有意味有韵味的表达。在张爱玲的小说中人物的描写都是她精心设计的,不仅有她个人的审美意蕴,还有很强烈的象征意义。
一、张爱玲的服饰研究
在20世纪40年代,上海的众多作家都热衷于写上海这座城市中的物质和欲望,这是一个被金钱和欲望笼罩的城市,看不清城市中的饮食男女,看不见城市下的人,具有七情六欲的人。张爱玲是站在更接近人的生活角度去创作。[2]
结合张爱玲早年的生活经历,她对服饰充满热爱和迷恋。小时候看到母亲梳妆打扮,引发了她对服饰的憧憬。但是继母的出现让她不仅没有机会实现自己的梦想,反而只能穿继母的旧衣服,这种压抑在当她有了自己购买衣服的能力之后,她不断地穿着自己搭配的衣服,有令人惊艳的奇装异服,也有时尚流行的旗袍。服饰是一个人个性的表现,张爱玲也不例外,她用服饰来表达自己。最出名的是她的散文《更衣记》写了三百年的中国服饰变化。她认为一直穿同样式样的服饰是一件令人厌烦的事情,在清朝女人没有时装可言是被压抑的。[3]在成名之后,张爱玲更加喜欢有设计的衣服,每次她的装扮都能让人惊艳。
二、服饰描写的叙事艺术
张爱玲小说整体的叙述风格都是客观叙述,她只是一个冷静的叙述者,对于小说中的人物命运没有太多的情绪判断,即使最终女性的命运是以悲剧结尾,但是作者没有对她们进行批判,而是淡淡的叙述,对于人性中的恶和不美好她是接纳的,所以在叙述完之后是一声悲而不哀的无奈叹息。
张爱玲这种叙事风格同样表现在她对服饰的描写,对小说中人物服饰的描写最多的就是用全知视角,作者可以随时随地从各个角度来描述人物的服饰,并且描写的直接、细致,服饰的形状、材质、颜色等都做出了描写。作者的叙述语言本身来看,是客观冷静的,正是这种客观描述,让读者更直观的通过语言在内心构建出一个完整的人物形象。
在中国传统小说中,运用全知视角描写人物服饰最多的是《红楼梦》,《红楼梦》作者用大量的篇幅描写人物的服饰[4],如贾宝玉和林黛玉第一次相见是对宝玉的服饰描写:头上戴着束发嵌宝紫金冠,齐眉勒着二龙抢珠金抹额;穿一件二色金百蝶穿花大红箭袖束着五彩丝攒花结长穗宫绦,外罩石青起花八团倭缎排穗褂;蹬着青缎粉底小朝靴。同样是全知视角叙事,《红楼梦》中曹雪芹是将人物的形象全盘托出,描写贾宝玉的服饰,从头上的装饰,身上的衣服,脚上的靴子,还有配饰,一一描述详尽,读者立马就能在脑海中形成贾宝玉一个富家公子的完整形象。与之不同的是,张爱玲小说中的服饰描写是分段式描写,人物并不是從头到脚完整地站在读者面前,而是将人物的服饰描写穿插安排在故事的发展中,不同阶段的描述重点是不一样的,伴随着人物的动作一同描写。
比如《金锁记》中对曹七巧的服饰描写,第一处是在曹七巧第一次出场的时候,对她的服装描写是:“窄窄的袖口里垂下一条雪青洋皱手帕,身上穿着银红衫子,葱白线香滚,雪青闪蓝如意小脚裤”,伴随的动作是“一只手撑着门,一只手撑了腰”,[5]还有一句简单的面部描写:“瘦骨脸儿,朱口细牙,三角眼,小山眉”,[5]至此大家可以看到的是一个人物的大体形象和着装,曹七巧的形象是模糊的,就好像人们第一眼看到一个人那样,从上到下看到的是一个人整体的着装打扮,是一个整体的映入眼帘的模样。在此对曹七巧的头饰配饰等细节还没有描写。作者在这里描述了一个一手撑着门一手撑着腰的七巧,她不是一个温柔贤淑的形象,更像一个叉着腰在街头指指点点的妇人,这里对她的身体动作和服装描写就足够了。果然在接下来七巧话语中可以看出她的抱怨和不好惹。[5]
她和三少爷季泽抱怨自己的丈夫是个不健全的人,随即顺着椅子溜下去,当她蹲下去之后,读者的目光便是由上至下,随着七巧的动作聚焦在她的头饰上,至此作者才对七巧的头饰进行细致描写,只看见“只看见发髻上插的风凉针,针头上的一粒钻石的光,闪闪制动着。发髻的心子里扎着一小截粉红丝线,反映在金刚钻微红的光焰里。”[5]
当季泽说要走之后,她自嘲道“难不成我跟了个残废的人,就过上了残废的气,沾都沾不得?”[5]这是作者的笔触落在了七巧的耳坠上“耳朵上的实心小金坠子像两只铜钉把她钉在门上——玻璃匣子蝴蝶的标本,鲜艳而凄怆”[5],这里承接上文描述她有一个骨痨的丈夫,把她钉在这个家里,不是残废的气息而是像蝴蝶标本一样,即使她带着金色的精致小坠子,但是却那么凄凉。在这一场景里,作者前后用了不止一次地服饰描写才将这次出现的一个完整曹七巧的穿着打扮展现出俩,从衣着首饰到头饰耳饰,依次随着人物的动作和情节的发展描写。[6]
在曹七巧的女儿长安和童世舫彻底决绝的情节讲述中,对于长安的服饰描写也是分段式的。长安在母亲几次诋毁后“悄悄地走下楼来,玄色花绣鞋与白丝袜停留在日色昏黄的楼梯上”[5]这里只描写了长安的鞋袜,其他部分都淹没在了黑暗中,在这场景下读者看不到长安鞋袜以上的装扮。因为母亲的言语,她没有出现,她带着一丝期盼走了出来,又走进了没有光的所在。长安最终和童世舫告别的时候,她站在童世舫面前,直面描写了她的旗袍“藏青长袖旗袍上有着浅黄色的雏菊”[5],站得远远的,这里对长安的衣服描写十分简短,再联系前面鞋袜的描写,一个朦胧的长安全像展现在我们面前。[7]但是就凭这寥寥几句,大家就能感受到长安的悲凉和无助,她就像旗袍上浅黄色的雏菊,即使有顽强的生的意志,却还是那么弱小。
张爱玲对于人物服饰的描写是十分精细用心的,因为她本人对于服饰的热爱,在她笔下的人物各个都是精心打扮的,并且服饰描写不是她小说中程序式的一部分,对人物的服饰描写不是和人物割裂开的。人物出场之后不会一次就将人物的服饰全部描写完毕,像一幅静止的画面展现在我们面前,而是随着人物的动作、心理和事件的发展,有重点有聚焦的逐渐描写,读者在读了很多内容之后,才能在脑海中拼接出一个完整的形象。这种描写方式会让人物的服饰更加贴合人物形象,服饰和人物是和谐共存而不是仅仅是人物的外在装饰,服饰已经成为人物灵魂的一部分。
三、服饰中的人物性格和命运
服饰成为一种文化符号之后,通过服饰能够看出一个人内在心理,作为一种外在表现,人们会通过服饰来展现自己的个性和魅力,也会通过服饰来表达自己的价值观和追求。用过张爱玲的作品中人物服饰的搭配精巧细致,我们可以透过着这些张爱玲精心设计的服饰中独特的款式,窥见人物的性格和当时的心理,这些服饰也安排了人物的命运。
如果不按照《金锁记》中作者的叙述顺序,而是从曹七巧的人生经历来看她的服饰变化,从中可以看出七巧从一个明媚朴素的少女逐渐变成一个偏执的“病女人”。
年轻时候的七巧穿着“蓝夏布衫裤,镜面乌绫镶滚”,是十分清爽简洁的颜色,可以看出七巧少女时代的美好,但是有着镶滚的设计表现少女时期的七巧追求美丽。那时候的七巧有着浑圆的手臂,带着翡翠镯子,展现了丰润美好的少女体态。七巧穿着这样的衣服去买菜,肉铺的朝禄会叫她“曹大姑娘、巧姐儿”,她一巴掌打在钩子上。这是一幅充满生机,明亮青春的场景。
当她嫁入姜家之后,她依然没有放弃对美的追求,在一大家子面前出现的时候,她是这样的“窄窄的袖口里垂下一条雪青洋绉手帕,身上穿着银红衫子,葱白线镶滚,雪青闪蓝如意小脚裤子。”首先颜色从蓝夏变成了雪青、闪蓝、银红,不再是简洁大方的青春,而是夺人眼球的颜色互相搭配,颜色的种类也变多了,七巧希望能够用这些亮眼的颜色引起注意。除了衣服颜色上的搭配,七巧的衣服的设计也是不俗的,上身衣服下身裤子是当时流行的款式,衫子上是葱白线香滚。面对患病的丈夫,七巧的婚姻是畸形的,所以她的内心对爱是十分渴望的,她将这种内心对爱的渴望和呐喊释放到了外在的穿着打扮。面对姜季泽不合适的爱无法实现,就像她发髻上风凉针头的钻石,闪着微弱却明亮的光,就像扎在发髻心子里的那一小节分红色的丝线,是一丝微红的光焰,在压抑的姜家大宅中对季泽的爱是她少女激情的最后一丝光焰。[8]
曾经美丽活泼的少女,在结婚之后真正可以说是走进了坟墓,她没有体会到美好的爱情,被黄金枷锁桎梏住自己。耳朵上的实心小坠子将她钉在了门上,在如此情境之下不得动弹。她就像一只没有生机没有办法翻身的蝴蝶标本,即使她努力不放弃自己的美丽,但是她无法改变被命运钉死无法翻身的凄凉。[9]
当丈夫死后分家那天,七巧的装扮散发出和以往不同的气息。她穿了黑色的裙子,但是还穿了白香云衫,虽然简单却掩盖不了她以为自己可以迎来完全不同的生活的期盼,这里描写她的脸不再是“瘦骨脸儿”,而是像抹了胭脂似的,颧骨烧得火热。
最后当七巧想要拆散长安和童世舫的时候,是以这样的装扮出现的:穿一件青灰团龙宫织缎袍,双手捧着大红热水袋,身旁夹峙着两个高大的女仆。青灰色是一种偏暗的颜色,缎和纱、布相比也是一种沉重的面料,龙代表着权利和控制。[10]穿着青灰色缎袍的七巧捧着一个大红色热水袋,青灰和大红两个产生强烈视觉冲击的颜色同时出现,着实让人看到一个疯狂的女人,令人毛骨悚然。如今她作为家中权利的掌握者,她要主宰女儿的命运,当她看到长安沉浸在爱情中面色逐渐红润之后她是无法接受的,她是一个被婚姻摧毁的女人,长安和童世舫新式的恋爱刺痛了她,她无法为自己的婚姻做主,长安却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人并和他在一起,这是她一辈子都无得到的,她要亲手毁了长安的幸福,最终使长安走向了没有光的所在。
《沉屑香·第一炉香》中梁太太的性格也能从她的服饰装扮体现,在葛薇龙去见她的时候,梁太太在小说中的出场也是颇有特色,特别是她的装扮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黑草帽沿上垂下绿色的面网,面网上扣着一个指甲大小的绿宝石蜘蛛,在日光中闪闪烁烁,暗的时候便像一粒青痣”。蜘蛛通过结网来捕获猎物,蜘蛛象征着梁太太,她就像一个结网捕获年轻女子为自己满足。当葛薇龙去求她的时候,“梁太太不端不正坐在一张金漆交椅上,一条腿勾住椅子扶手”“高跟织金拖鞋荡悠悠地吊在脚趾尖”,价值不菲的金漆交椅,不端庄的坐姿,可以看出她是一个不受拘束的女子,和曹七巧在封建礼制之下的压抑不同,梁太太是一个不羁的女人。她把芭蕉扇子盖在臉上,透过扇子观察着葛薇龙,从这一刻起就开始对葛薇龙进行算计。
最初的葛薇龙是一心求学读书的,面对梁家那大坟似的房子,她觉得自己即使走进去也不会被沾染,别人说什么便说吧,自己只要认真念书就行。但是面对一柜子金翠辉煌各个场合都会穿到得到衣服,面对灯红酒绿的生活,她迷失在了衣柜的衣服里。
四、结语
张爱玲小说中对于服饰的描写是她创作中她十分重视也是非常具有艺术性的一部分。每个人物的服饰都是她根据人物特定的性格和命运精心设计的,随着人物的动作语言逐渐展开描写,使在脑海中缓缓拼出一个完整的人物形象,每一部分都有细致的描写,所以最后人物可以完整清晰地站立在读者面前。
《金锁记》和《沉屑·第一炉香》中人物的服饰也随着她的人生发生改变,从颜色到搭配,包括象征性的描写,无一不在讲述着人物的命运。对服饰的描写是张爱玲小说的独特之处,用她独特的美丽辞藻为人物穿上他们独一无二的服饰,使小说中的人物优雅美丽地站在读者面前,这正是张爱玲文字的魅力所在。
参考文献:
[1]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增订本[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6.
[2]翟兴娥.20世纪40年代上海沦陷区女作家小说服饰研究[D].武汉大学,2013.
[3]贺玉庆.重复:张爱玲的服饰叙事策略[J].河南社会科学,2014,(11):5.
[4]陶小红.张爱玲与《红楼梦》研究述评[J].红楼梦学刊,2008,(4):36.
[5]张爱玲,金锁记[M].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05.
[6]贺玉庆.张爱玲小说中“服饰”的叙事艺术[J].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37(4):3.
[7]贺玉庆.张爱玲小说中“服饰”的叙事艺术[J].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37(4):3.
[8]王璟.张爱玲作品中的服饰心理意义解析[J].艺术百家,2011,(A01):3.
[9]王志鹏.浅析张爱玲小说中的意象文学——以《金锁记》为例[J].汉字文化,2021,(18):140-141.
[10]李添艺.封建桎梏下女性的挣扎与反叛——《金锁记》中曹七巧形象分析[J].名作欣赏,2021,(23):144-145+176.
作者简介:
廖静文,女,汉族,江苏盐城人,江苏海洋大学,硕士研究生,文艺学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