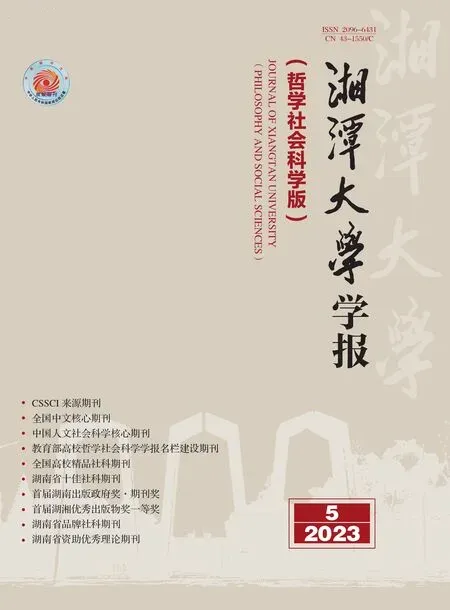毛泽东“半益农”概念考论*
王文兵,胡冬华
(湘潭大学 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 湘潭 411105)
在1925至1926年间,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两文中,毛泽东分析中国农民阶级时皆使用了“半益农”概念。学界关于毛泽东使用“半益农”概念的研究基本上都是基于《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版本变迁的视角,揭示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直接将“半益农”并入“贫农”修改的意义,认为这提高了理论的准确性。(1)这方面的代表性成果主要有:施金炎主编:《毛泽东著作版本述录与考订》,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5年版,第39页;王建国:《不同文本〈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之比较》,《毛泽东思想研究》2003年第4期;邹卫韶:《“开篇之作”与“首要问题”——剖析毛泽东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文本修改的深刻内涵》,《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22年第5期等。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学者从其他视角对毛泽东使用“半益农”概念情况进行研究。有学者指出,“半益农”是“半贫农”之误。其主要依据是:第一,从概念内涵来看,“半益农”在1951年版《毛泽东选集》中对应的是“一部分贫农”,这“一部分贫农”较贫农中的另一部分贫农生活好一点,贫得还不够彻底,依“自耕农”和“半自耕农”的习惯,将“半益农”理解为“半贫农”顺理成章;第二,从版本变迁来看,就新中国成立前《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的三个版本而言,尽管每个版本的文本内容都有改动,但涉及“半益农”部分的论述并无改动,所以“半益农”第一次出现就是“半贫农”之误,直到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才进行改正;第三,从字形来看,《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发表在《中国农民》和《中国青年》两个报刊中的“益”与“贫”的字形十分相似,进而不排除当时的排版工人一时疏忽而出现“半益农”的疏漏。[1]另有学者认为,毛泽东在给第五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讲课时向学员介绍了湖南衡山等地农民运动的经验,讲了《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半益农”是当时湖南衡山等地对农民成分划分的名称,其经济地位介于半自耕农与贫农之间。[2]114,119还有学者推测,“‘半益农’,当指来自日语的‘分益农’”[3]。据笔者考证,发现前两种观点都有待商榷,“半益农”概念并非只有毛泽东使用过,在毛泽东之前陈独秀就使用了这个概念,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其他人也使用过这个概念。至于第三种观点,目前尚无确切的史料证明“半益农”是何人何时从日语中传播而来,这还需在今后的研究中进一步探索与挖掘。
一、中共早期农民阶级分析话语中的“半益农”概念
在中共早期的农民阶级分析话语中,陈独秀和毛泽东都使用过“半益农”概念。陈独秀在1923年7月就使用了“半益农”,这比毛泽东早了近两年半的时间。通过比较发现,陈独秀、毛泽东都重视对“半益农”经济状况的分析,尽管在认识上存在差异,但是也可以看出此时毛泽东的农民阶级分析话语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陈独秀的影响。
1923年7月1日,陈独秀在《前锋》创刊号上发表了《中国农民问题》,他在文中将佃农兼雇主和佃农统称为“半益农”,采用了“半无产阶级”“农业的无产阶级”等阶级概念将地主与农民分为五个阶级、十个类别[4]51:



(十)雇工 —— 农业的无产阶级
相较于党的二大提出的将地主归入农民阶级的农民阶级分析话语,此时的陈独秀已经不再将地主纳入农民阶级的序列,而是明确将地主与农民分开,开始形成地主——农民二元对立的阶级分析框架和阶级意识,在党内首次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话语同中国传统的农民分析话语相结合,对农民阶级作了相当细致的划分。
陈独秀在该文中对农民阶级进行分析时使用了“半益农”的概念,从“半益农”的内部结构、生活状况和阶级属性三个方面进行了深入分析。首先,从“半益农”的内部结构来看,他认为“半益农”内部包含了两个类别:依据是否需要雇佣他人帮忙分为“佃农兼雇主,是向地主,租地耕种而劳动力不足,雇用别人帮忙者;纯粹佃农,乃由一家族任(人)工作不雇用他人者。”[4]53即佃农兼雇主和纯粹佃农两种;依据是否占有地权又分为纯粹无地权者和半有地权者,这两者最大的区别在于地主是否可以随时收回租出之耕地,“纯粹无地权者,地主随时可向佃农收回其租出之耕地”,而“半有地权者”因其存在转租的情况,所以地主“除出资购回此半佃权外,不能自由收回耕地另给别人耕种。”[4]53其次,从“半益农”的生活状况来看,他认为“半益农”受地主的压迫,每年向地主缴纳“至少须在收获物三分之一以上”的数量,“不能全收劳其动所得之利益,丰年尚可勉强供给一字(家)生活及农作上的需要,荒歉时则衣食且不足,又加以地主追缴租课,不胜其困苦”[4]53。最后,从“半益农”的阶级属性来看,他认为“半益农”“虽不占有地权或只占有半地权”,但是“仍占有生产工具及收得并管理其劳动所得之一部分生产物”[4]54,所以属于半无产阶级。
1925年12月1日,毛泽东在《革命》半月刊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2)1989年第1期的《党的文献》重新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的最初版本,即1925年12月1日发表在《革命》半月刊的版本,本文中涉及《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革命》版)的引文皆出于此。详见沙鹤闻:《关于〈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的最初版本》,《党的文献》1989年第1期。中也使用了“半益农”这个概念。从其概念内涵看,毛泽东认为,“半益农无土地,然有比较充足的农具及相当数目之流动资本。此种农人,每年劳动结果自己可以得到一半或一半以上。不足部分,种杂粮,捞鱼虾,饲鸡豕,勉强维持其生活。”[5]不难看出,根据毛泽东的上述论述,所谓“半益农”就是指“每年劳动结果自己可以得到一半或一半以上”的“农人”或“佃农”,着眼于其“耕种土地收益”而言,反映出当时的地租情况。从其阶级属性来看,毛泽东认为,半自耕农、“半益农”和贫农同属于半无产阶级,依经济状况差异,可分为上中下三类,“半益农”在这三者中居于中间地位。毛泽东还依据三者之间的经济状况差异,对他们的革命态度作了比较分析:半自耕农是“租于别人的部分虽只收获一半或且不足一半,然自有的部分却可全获”[5],生活优于“半益农”,故其革命性不及“半益农”;贫农“既无充足的农具,又无流动的资本,肥料不足,田地歉收,送租之外,所得无几。”[5]生活苦于“半益农”,故其革命性优于“半益农”。另外,毛泽东认为,手工业工人因有其自有工具是一种自由职业者,其经济地位与“半益农”相当,同属半无产阶级。[5]
通过陈独秀和毛泽东关于“半益农”论述的比对,可以发现陈独秀对毛泽东关于农民阶级的分析是有一定影响的,他们都将“半益农”定性为“半无产阶级”,都认为“半益农”的生活是举步维艰的。但是他们关于“半益农”的认识也存在诸多差异。陈独秀认为,“半益农”是“不占有地权或只占有半地权”,是“占有生产工具及收得并管理其劳动所得之一部分生产物”[4]54的农民;“半益农”包含“佃农兼雇主”和“佃农”两部分,一部分是租种地主土地因劳动力不足而需要雇佣他人,另一部分是不需要雇佣他人。陈独秀认为,半有地权者还存在“曾出等于当时地价半值之金额向地主租得耕地,其后能以同等金额或较少之金额辗转租给别人耕种,原地主只能向现时耕地之佃农收取地租”[4]53。在陈独秀看来,一部分“半益农”存在通过转租耕地给其他佃农以盈利的行为。这同毛泽东关于“半益农”的认识是明显不同的。第一,毛泽东认为,“半益农”是不占有地权的,“半益农无土地,然有比较充足的农具及相当数目之流动资本”[5]。很明显是否占有土地,这是两者理解和界定“半益农”概念的最大不同之处。第二,毛泽东认为,佃农是包含了“半益农”和贫农两部分,而在陈独秀那里则是“半益农”包含了佃农,两者的从属关系截然相反。陈独秀和毛泽东关于“半益农”概念的不同理解和界定,反映出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农民问题特别是农民阶级内部构成的认识尚未达到高度统一。相比而言,毛泽东通过对不同阶级的经济状况进行分析,进而分析其革命态度以明确中国革命的敌我友的问题,进一步深化了对农民阶级及其与中国革命关系的认识,而陈独秀当时主要聚焦于分析农民的经济状况。
从陈独秀、毛泽东对于“半益农”概念的不同理解和界定来看,所谓“半益农”是“半贫农”之误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二、毛泽东使用、弃用和修改“半益农”概念
从毛泽东使用、修改和弃用“半益农”概念的历史过程来看,“半益农”也不是一开始出现就是“半贫农”之误,而是一个具有特定历史内涵的概念。
据学界目前的版本考证来看,《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先后经过4次修改,共有5个版本:第一个版本是于1925年12月1日发表在国民革命军第二司令部主办的《革命》半月刊第4期;第二个版本是于1926年2月1日发表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农民部主办的《中国农民》第2期;第三个版本是于1926年3月13日被共青团中央主办的机关刊物《中国青年》第116、117期连载的版本;第四个版本是1951年5月被编入《六大以前——党的历史资料》的版本;第五个版本是1951年10月被编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的版本。[6]为行文简便,本文将以上5种版本简称为《革命》版、《中国农民》版、《中国青年》版、《六大以前》版和《毛泽东选集》版。
毛泽东在《革命》版、《中国农民》版、《中国青年》版中都使用了“半益农”概念。从毛泽东对这三个版本的修改情况来看,不可能是因为“益”与“贫”字形非常相似,造成排版工人的失误,进而产生“半贫农”之误。在1925年至1926年间,毛泽东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进行了两次修改,其中《中国青年》版的修改幅度最大,“毛泽东对这次修改比较谨慎,包括对一些提法、文章的构架和文字等都进行了加工,这些修改反映出毛泽东对一些重大问题的思考”[6]。《中国青年》版是毛泽东“为了避免引发中共党内同志的误解,也为了向中共党内同志更准确地表达自己的见解”而专门为中共党内同志改写的。[7]在上述三个版本中,毛泽东不仅仍然使用了“半益农”概念,而且对这三个版本中关于“半益农”的论述都做了修改。如在获得劳动结果方面:《革命》版中的“半益农”是“每年劳动结果自己可以得到一半或一半以上。”[5]而《中国农民》版中的“半益农”则是“每年劳动结果自己可以得到一半。”[8]8在占有生产资料方面:《中国青年》版和《革命》版中的“半益农”是“有比较充足的农具及相当数目之流动资本”[5],[9]459。而在《中国农民》版中的“半益农”则是“有比较充足之农具及相当数目的流动资本”[8]8。1926年1月1日,毛泽东在《中国农民》第1期发表的《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一文中又使用了“半益农”的概念。该文关于“半益农”的论述和上述《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三个版本中关于“半益农”的论述基本一致,只是在提及半自耕农、半益农和贫农三类农民人数总和略有变化,上述《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三个版本都是“共计一万七千万”,该文则是“大概自一万五千万至一万七千万”[10]17-18。
通过比对上述三个版本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及《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发现《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的每次修改都涉及“半益农”的论述,并不如学者所言,“涉及‘半益农’的部分没有改动”[1]。可以推断,毛泽东当时很重视对“半益农”概念的理解和界定,如果“半益农”是“半贫农”之误,毛泽东当会勘误更正。
自1925年至1926年间毛泽东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进行修改以后,直到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中央决定重新编印《六大以前——党的历史材料》重要文献汇编时,毛泽东才依据《中国青年》版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进行再次修改(3)逄先知指出,《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收入1951年版《毛泽东选集》第1卷时是以《中国青年》版为基础,毛泽东是在此基础上编辑修改的。在人民出版社1951年5月出版的《六大以前——党的历史材料》一书中,《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的落款时间是1926年3月。这和《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刊发在《中国青年》的时间是完全一致的。,并在此时将“半益农”修改为“一部分贫农”。
从1927年3月毛泽东发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开始,毛泽东就不再使用“半益农”这个概念,而将“半益农”这一概念指称的这一部分农民列入贫农之中。在该文中,他将贫农分为“赤贫”和“次贫”两类,其中关于“次贫”的定义是“半无业,即略有土地或略有资本,但吃的多,收的少,终年在劳碌愁苦中过生活的,如手工工人佃农(富佃除外),半自耕农等”[11]2065。由此可知,此时的“半益农”包含于“次贫”中,是贫农的一部分。1930年5月,毛泽东在《寻乌调查》中把贫农分为四个阶层,“半益农”在此时对应的是“佃农中之较好的”贫农,该文指出“他们有牛,有犁耙,也多少有些活动本钱,但没有一点土地。他们的特点在于有牛,大多数有一条牛,极少数也有两条、三条牛的。他们比半自耕农穷,即比半自耕农更不够食,但比别部分贫农却要好些。”[12]132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直接将“半益农”并入“贫农”之中。推其缘故,或可这样解释:“半益农”概念主要反映佃农耕种土地的收益情况,而“贫农”概念则主要反映农民土地占有状况,两者划分标准不同,相提并论容易造成某种分类混乱。故此,毛泽东后来不再使用“半益农”这个有点“另类”的概念而将之归于“贫农”概念之中。依此而言,从毛泽东使用“半益农”这个概念到不再使用这个概念再到后来修订弃用这个概念,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革命实践中对于中国农民阶级内部构成认识的深化和统一过程。
三、“半益农”是一个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广泛使用的概念
如上所述,“半益农”这个概念不是只有毛泽东在使用,陈独秀在1923年7月就已经使用过。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半益农”这个概念,不仅陈独秀和毛泽东使用过,当时社会各界也在广泛使用。据此可以判定,“半益农”当时并不是一个特指湖南衡山等地农民成分划分的“地域性”概念,而是一个比较通行的“全国性”概念。
1928年10月,唐仁在《农民问题大纲》中同样使用了“半益农”概念,他关于“半益农”的论述与毛泽东非常相近:“佃农又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半益农,这种农民虽没有土地,然有比较充足的农具及相当数目的流动资本。他们每年劳动结果,自己只能得一半;而他们生活的不足部分,便以种杂粮,捕鱼虾,饲鸡畜等来勉强维持。所以他们生活之不安,比半自耕农更甚。”[13]491929年11月,高希圣与郭真在其合著的《社会科学大纲》中也使用了“半益农”概念,其论述和唐仁完全一致,一字不差。[14]19从其关于“半益农”的论述来看,唐仁、高希圣、郭真主要分析了“半益农”的生产资料占有与生活状况,除了没有对“半益农”的革命态度进行分析外,其关于“半益农”的相关论述同毛泽东的论述是相似的。1930年,赵承信在对其家乡广东新会慈溪进行土地调查基础上写成的《广东新会慈溪土地分配调查》一文中也使用了“半益农”概念,指出“佃农亦有称半益农的”[15]74。赵承信在该文中主要是对其家乡广东新会慈溪的土地分配状况进行调查,依据土地产权、使用权的分配,将“与农业有关者”分为“地主、地主兼佃农、地主兼自耕、自耕兼佃、自耕农和佃农”[15]75。赵承信认为,佃农就是“半益农”,这同毛泽东关于“半益农”的认识明显不同。
1931年4月21日,《大公报》(天津版)的记者王镜铭在该报上发表题为《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之二 游民与农村社会地痞流氓为害甚烈》中也使用了“半益农”概念。该文直接引用了一组关于中国农民问题研究调查的数据:“半自耕农五人、半益农六人、贫农六人”,并强调“这是民国十四年一个调查。”[16]将其同毛泽东在1925年12月1日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进行比对,可知该文引用的调查数据与《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对应的数据是一致的。同年6月11日,另一篇刊发在《大公报》(天津版)的《农村之不安总分析》一文,也使用了“半益农”概念。该文指出,“可想知矣,有田者,能为水平面以下之生活,既如上述矣,其为半自耕农、半益农、贫农、雇农及乡村手工业者,或亦有同样之情形。”[17]这主要是强调“半益农”生活状况极其艰难。1932年10月,姚素昉在撰写《中国古代土地制度研究》时,就如何解决中国土地问题的研究中多次引用了毛泽东《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一文中的观点,并直接引用了“半益农”这个概念。[18]116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国民政府的文献中也使用了“半益农”概念。在中国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农人部编著的《十六年以前的国内农人运动状况》(4)该书出版社、出版时间不详,但从书名可知,该书当在1927年后出版。一书中,提到浙江农民人数构成时指出,“浙西以半益农与贫农佔多数”,“浙东则以半益农佔最多数”。[19]
四、“半益农”是否源于“分益农”概念
如上所述,有学者推测,“半益农”当指来自日语的“分益农”,属于“和制汉语”。但目前尚无史料说明“半益农”最早出自何人何时何处,也未发现史料以确证“半益农”源于日语“分益农”概念的猜测。不过,单纯从其概念内涵而言,“半益农”与“分益农”具有密切关系。“分益农”是阐释近代中国分益雇役制、分益制租佃方式的核心概念,被学界广泛使用。一方面,“分益农”概念集中反映了实物地租中分成租的分配方式,其概念内涵可以包括“半益农”这一群体。另一方面,从近代中国学界关于“分益农”概念的用法上来看,“分益农”具有两层不同的内涵:其一是指缴纳一定比例的收获物于地主的佃农,这是处于被剥削的一方;其二是指处于地主于佃农之间的“二地主”,即通过将土地转租于佃农以获取收益,这是处于剥削的一方。
笔者曾专门向厦门大学梁心老师请教。她说她只是猜测毛泽东使用的“半益农”源自日语的“分益农”概念。(5)梁心老师给笔者回复的邮件:我当时在读到《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这篇文章时,也比较疑惑“半益农”到底是什么意思,似乎也没有见到其他人使用这一术语。但是“分益农”这一术语后来较为常见,且也符合《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所说的“没有土地”“只收获一半”的特征,所以我就猜测这可能是当时翻译尚未定型的结果(“半”和“分”均有取其部分的意思)。虽然这种猜测尚无确切的史料支撑,但是这种猜测,一定程度上也具有某种合理性。陈独秀先于毛泽东使用了“半益农”这一概念,不排除毛泽东使用“半益农”概念是受到了陈独秀的影响,而陈独秀早年留学日本,深受日本文化影响。就此而言,或可推测陈独秀使用的“半益农”概念出自日语的“分益农”概念。
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学界广泛使用“分益农”概念来阐释当时地主与佃农间的租佃关系,这也可能是推测“半益农”源于“分益农”的一个重要线索,因为“半”与“分”都有取其部分的意思。“分益农”概念,集中反映了近代中国社会佃农与地主两者之间实物地租中分成租的分配方式。1930年,高希圣等人在编辑《社会科学大词典》时指出,分益农制度是指“佃农对于地主不支付租地费,而以收获物之一定分量(普通为二成五分)交给地主的制度。”[20]1051931年,唐启宇在《农政学》中指出,“凡租他人之土地,而于每年或数年缴其一部分之收益于业主者,为分益农。”[21]69在1939年版的《中国农村经济常识》中,薛暮桥指出,“在西北各省,例如山西、河南、陕西,流行着一种‘二八分种’制度,或称分益雇役制。这种佃农同永佃农民恰恰相反,他们非但没有‘田面’,而且连耕畜、农具、种子、肥料都由地主供给。所以他们介于佃农和雇农之间,也可以说是一种变相的雇佣劳动。田地上的收获,地主分到八成,佃农分到二成,所以普通称为‘二八分种’;但是也有三七分的。地主所分到的八成,名义上是地租,实际包括着农业的成本和利润;佃农所分到的二成,也可说是一种实物工资。因为他们多少带着一点雇佣性质,所以这种租佃关系很不稳定,年年可以变更。”“分益制流行于全国各省,它的特点是把收获中的一定成分(普通是百分之五十)来做缴给地主的地租。分益制有三种不同的方式:第一种是一切农本全由地主供给,佃农仅出劳力;这就是上面所说的分益雇役制。第二种是地主供给一部份的农本;例如地主和佃农各出一半种子,一半肥料,收获所得粮食、柴草等等,也是对半分拆;这是最典型的分益制度。第三种是一切农本全由佃农供给,收获也是按成分拆。”[22]39就此来看,“分益农”就是佃农租种地主土地,不是支付货币地租,而是以一定比例的收获物作为实物地租缴纳给地主,至于比例的划分,则是根据地主与佃农之间约定的农本份额来确定。可以说,当时学界普遍认为“分益农”是以收获物的一定比例缴付于地主。由此可知,“半益农”突出的是地主与佃农在收获物上的对半分成,这个“一定比例”就是特指五五分成,而“分益农”则是既包括了“半益农”的五五分成,也有二八分成、三七分成、四六分成等其他分成比例。显然,“分益农”的概念内涵与适用范围较“半益农”的概念内涵与适用范围更为广泛。
同时,学界又存在关于“分益农”的另一种用法,这种用法同上述“分益农”的用法大不相同,两者之间形成鲜明的对比。1934年,陈翰笙对广东的农村经济进行调查时使用了“分益农”概念,他指出“富商巨绅往往在投耕办法下包佃了数千亩至数万亩的沙田,自己固然不耕也不去经营,只是再分批地转租给好些‘分益农’或‘分耕仔’。这些‘分益农’也只是分益而不从事于农业的。他们更将沙田转租给‘大耕仔’或佃户。”“‘分益农’大多数是从包佃者批了田亩,有直接转租给‘大耕仔’的,亦有转租给二重‘分益农’后再转租给‘大耕仔’的。”[23]23这里的“分益农”是指介于地主和佃农之间的中介即所谓的“二地主”,不直接参与农业生产,而是将租来的土地再转租于佃农以分得土地收益。1937年,黄菩生在《广东粮食问题研究》中指出“土地多由中间阶级所垄断,如包佃者之剥蚀地租,每亩由二三元至十数元,甚至有二三路地主者,又各分益农之以资本榨取农民所有土地,由分益农向业主大量租出,分于佃农耕种,地租、牛只、种子等,均由分益农负担,收获后,先扣出种子,然后分益农取其百份之七十五,佃农只得百份之二十五”[24]33-34。显而易见,这里的“分益农”具有一定的资本,不仅通过转租土地,还向佃农提供耕畜、种子等以分取土地的大部分收益。这与薛暮桥等人笔下的“分益农”具有很大的差异性,从剥削关系来看,薛暮桥等人笔下的“分益农”是处于被地主剥削的地位,而这里的“分益农”则是指所谓的“二地主”,他们通过将土地转租于佃农以获取利益,处于剥削佃农的地位。这种“分益农”概念与“半益农”概念不是一个类别,难以相提并论。
五、结语
综上所述,毛泽东曾使用的“半益农”概念既不是“半贫农”之误,也不是湖南衡山等地农村划分农民成分的地域性概念,而是一个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广泛使用的通用概念。目前尚难以对“半益农”进行更为深入详细的词源考证,也尚未发现确切史料以证实“半益农”出自日语“分益农”的猜测,但是这种猜测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半益农”是特定历史语境下的产物,是具有特定内涵的概念。毛泽东只在1925年至1926年间使用了这一概念,随后就不再使用。作为“构建人类知识大厦的基石”[25]5,概念是话语体系的基本元素和重要标识。概念的变迁与新解,本质上反映了话语体系的创新与转变。从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关于农民阶级的分析话语来看,既有中国传统的农民分析话语,如自耕农、半自耕农、佃农、半佃农和半益农等,又有马克思列宁主义农民阶级分析话语,如富农、中农、贫农;大农、中农、小农;农村资产阶级、农村小资产阶级、农村半无产阶级和农村无产阶级等;两种农民分析话语同时并存,既相互阐释,使人容易理解,又难免存在某种分类混乱,造成一定误解。陈独秀、毛泽东对于“半益农”概念的不同理解和界定表明,“当时中共内部还没有统一的阶级概念和阶级划分标准,大体是各自理解和各自表述。”[26]这也反映出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斗争实践中把马克思主义农民阶级分析话语同中国传统农民分析话语结合起来,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农民阶级分析话语,必然要经历一个长期探索的历史过程,而不可能一蹴而就。有学者指出,“概念,像个人一样,有着自己的历史,并且镌刻着无法磨灭的岁月风霜。”[27]本文考察毛泽东等人使用“半益农”概念的情况,不单是为了说明“半益农”不是子虚乌有、不是“半贫农”之误等问题,而是旨在通过“半益农”概念的历史变迁这一“概念故事”来激发我们探究中国共产党人是如何将马克思主义农民阶级分析方法和话语同中国农民具体实际问题相结合、同中国传统农民话语相结合的历史过程,为在新时代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话语体系建设提供历史经验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