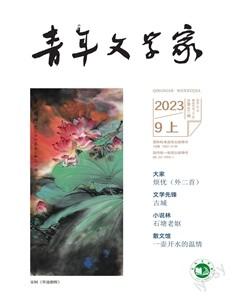东西笔下弱势戏剧的先锋小人物
毕然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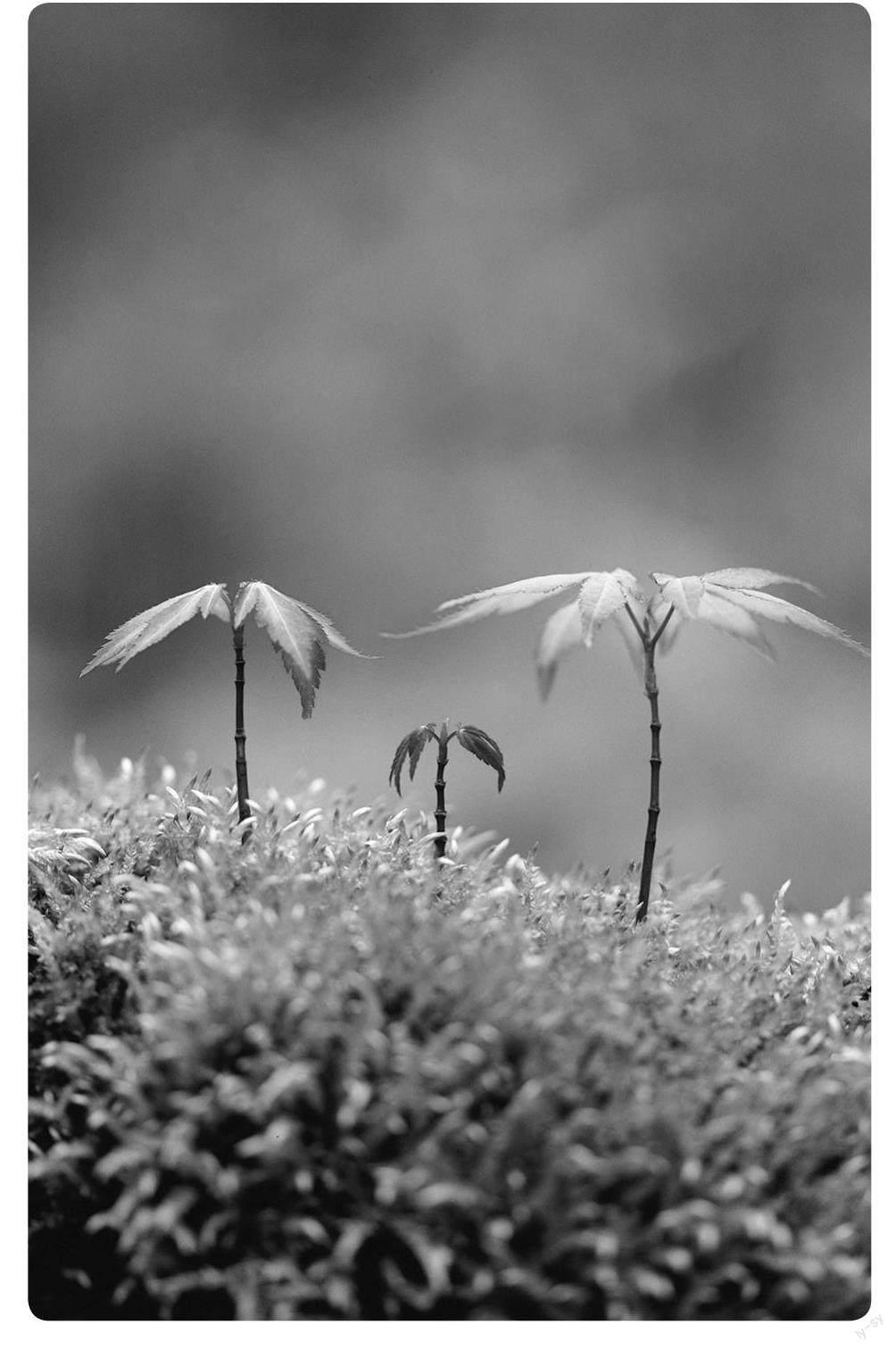


东西认为,一部小说能否较好地展现自身内在的精神内蕴,以及较好地进行话语表达,关键就在于小说中的人物塑造,因此在创作中应当由人物来掌握虚构的权力,写作者如果自身掌握过大的写作权力,无异于过度专制,由此必然会限制小说作品中人物作用的发挥。赋权给小说中的人物,使写作者的权力尽可能被弱化,确保其权力始终等于或者小于人物,以此来塑造更加完整的人物形象。因此,东西的作品中的“不在场感”非常浓重。除此之外,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背景发生了重大变化,正在由集体性叙述视野逐步转变为个人化写作模式,而东西所塑造的人物却不拘泥于宏大的社会背景以及家族、家庭的使命,都是完全顺其自然地在故事的推移中完成人物建构。东西小说作品中的人物形象非常丰富,通过人物夸张的动作将人生荒诞而又真实的一面淋漓尽致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很多小人物苟且在社会最底层,虽然奋起抗争且力不从心,始终无法逃脱命运的束缚。这些人物世世代代懦弱而又无力,在苦苦挣扎中实际上是对命运不可承受之重的生动演绎,生如蝼蚁的懦弱灵魂在悲剧之中降生,又在悲剧的纠缠中陨落。我们不能单纯以具有荒诞行为模式的符号来对他们进行认知,而是应当将其视为能够与生活困境奋力抗争的、活生生的灵魂,他们竭尽全力在社会底层踽踽独行且仍旧无法改变生活的困窘,最终葬身于悲剧的牢笼,或者是将下一代视为突破命运枷锁的希望,但是这种希望又好比是坟墓而无情地将上一代埋葬。他们虽然看起来荒诞无比,但是又活在现实当中。通过深入地刻画具有荒诞悲剧的小人物群体,所揭露出的是他们性格的懦弱以及社会地位的卑贱低下,实际上是荒凉命运底色的反映,充分彰显了东西对个体生命的关怀,更是通过人物深入窥探了其所代表的一类人的存在状态。因此,东西在先锋探索的过程当中的垫脚石就是其笔下行为荒诞、形色各异的底层小人物。
一、荒诞戏剧般人物
《双份老赵》中以具备交易属性的商品来物化人物。小说的主线就是老赵和妻子小夏的婚恋生活,老赵天生就有一副“思考的表情”,小夏拥有大量的倾慕者,但是这些男人却多少显得有些幼稚和轻浮,所以在老赵的成熟稳重面前自然不堪一击,只能甘拜下风。恋爱旅游是对老赵最好的“试金石”,老赵做事脚踏实地、计划周密而又细心无比,按照两个人的标准准备上山物品、房间,所以这种无微不至的照顾完全俘获了小夏的芳心,这也为他们喜结连理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婚后的老赵亦是如此,他买了一对完全相同的玉镯,两人各留一只,但是没有告知小夏自己所珍藏的另一只,因此当这只收藏的手镯被小夏发现时,竟然导致小夏产生了老赵出轨的想法。此时,老赵竭尽全力地证明自己的清白,说出了自己的癖好就是喜欢收藏两份东西,这显然已经打破了寻常的小说情节,从而将故事娓娓道来。两人有了自己的女儿后,便有了为其购置新房的打算,此时做事滴水不漏的老赵自然肩负起了装修新房的重任,而小夏却一直未参与其中,直到有一天小夏忽然发现老赵双份存物柜当中空空如也,她在柜底竟然找到了隐藏其中的新房钥匙。小夏凭借着自己的第六感猜测老赵还有不可告人的秘密,小夏拿着钥匙打开了新房大门,发现新房与现居房在布局、装修等方面完全一样,而新房主卧当中更是有个神秘女子和自己相貌完全相同,且左手也戴着同样的玉镯。此时,老赵所复刻的不再是单纯的物品,而是变成了人,这个过程的实质就是将人以及人生物化,当我们能够完全复制替换每个人的人生时,个体人生也将会失去其应有的意义,人生被物化且充满了机械性,这实际上所暗示的就是一种荒诞性。
东西笔下的人物的行为充满了荒诞性,从而使得价值、意义的呈现得到了消解,外界在人们不明所以,对自己、未来等一无所知的情况下,无情地将人切割,这样的人生巡演变得毫无意义,被撕裂的人变得伤痕累累,甚至“不知道我是如何消亡”的,人的命运是悲惨而又惊心动魄的,但是较之于20世纪80年代先锋小说纯消解意义的形式实验,东西写作的目的在于通过营造荒诞以呼吁人们关注更深层面的底层生存。
二、底层边缘化人物
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首次使用的“底层”一词,他认为所谓的底层主要包括欧洲主流社会之外的社会群体。直到1956年,中国文学界也开始使用“底层”一词,即蔡翔先生所创作的散文《底层》,其基于自身的成长生活经历,将农村与城市的发展历程进行了对比。底层出于本能而谋求富裕的生活,这些善良的人们在灯红酒绿的社会中努力打拼,但是上层的余羹却与他们毫无关系,反而在物欲横流中利欲熏心,导致本有的善意消失殆尽。从20世纪90年代之后,各个文学评论家认为底层所处阶段的不同,其也对应着不同的内涵,但有着相同的本质,即以深层的社会结构层面为指向。东西在创作中始终关注底层,这些底层既有生活在农村的小人物,同时也有努力挣扎在城市边缘的小人物。东西所创作的底层主要由两类构成,一类是存在生理缺陷的残疾人,因为被社会所排挤而苦苦挣扎;另一类是心理层面上受到社会的腐蚀和影响而败坏道德的人。东西着力描写刻画这两类底层边缘人,实际上是在关注人生存命运,处处彰显了关爱个体生命的情感。
一是因为生理缺陷而自我逃亡者。小说《没有语言的生活》中就对彼此协助生活的三个身体残疾之人,小说主要包括三个叙事浅层。第一节故事中,一场意外彻底改变了王老炳与自己的聋儿子王家宽的生活。父子二人在除草时,父亲意外地将蜂巢打破而被群起攻之,虽然他声嘶力竭地呼救,但是儿子因为耳聋而无法听到父亲的呐喊,直到口渴找父亲时才发现父亲变得奄奄一息,此时才大声疾呼。
文中描写道:“当王家宽的喊声和哭声一同响起来时,老黑感到事情不妙。老黑对着王家宽的玉米地喊道:‘家宽……出什么事了?老黑连连喊了三声,没有听到对方回音,便继续他的劳动。老黑突然意识到家宽是个聋子……”
家宽因为自身的缺陷才导致没有能够在第一时间救治父亲,由此致使父亲双目失明,这同样也彻底改变了原来的生活状态。第二节故事中,王家宽对同村女子朱灵爱慕已久,由于自己没文化,所以送给朱灵的情书也有由小学老师张复宝代写,但是张复宝却以自己名义写信给朱灵。原本怀揣着梦想的王家宽却不想成了情书传递者,忙碌的白天只是为他人搭桥牵线。张复宝已经成婚却还依然与朱灵偷情并导致后者怀孕。朱灵想要将王家宽作为“替罪羊”,而王家宽在大家的误解中也知道了事情的真相,所以果断将朱灵放弃而选择了蔡玉珍这个哑巴新娘。由于耳朵听不见,所以家宽便被人们区别看待,对家宽欺侮甚至恶言相向。家宽听不到外界的声音,所以在蔑视和嘲笑面前表現得浑然不觉,并且将所有的攻击谩骂看成正常的聊天儿,甚至还报之以微笑。虽然三个人加起来在生理功能上与正常人大概相等,但是意外又再一次打破了重归平静的生活。朱灵在没有归宿的情况下选择了自杀,而朱灵父母却认为女儿的死亡归根结底在于王家宽的所作所为。为此,朱灵母亲杨凤池对王家宽恶语相向,甚至诅咒其“不得好死”“全家死绝”。这一家三口对于这种恶毒的攻击毫无还手之力,所以不得不选择了逃亡,他们将新房建到了河对岸,希望能够与村里人保持足够的距离,以消极避世的态度来逃避歧视。
第三节故事中,外来者对蔡玉珍的性骚扰而破坏了三人的隐居生活。蔡玉珍由于不能张口说话,导致在受到侮辱时难以及时求救,王老炳虽然能够听到异响,但是无法将睡得像死猪一样的王家宽叫醒,命运并没有因为他们的逃离而发生任何的改变,即便是再天衣无缝的配合,也无法与健全人相抗衡,所以蔡玉珍所生的健康男婴王胜利就成了全家人唯一的希望。“家宽、玉珍和我终于有了一个声音响亮的后代,但愿他耳聪目明、口齿伶俐,将来长大了,再也不会有什么难处,他能战胜一切,他能打败这个世界。”王胜利虽然像正常人一样接受教育,但是人们依然嘲笑他是残疾人的儿子,由此导致他终日缄默不语,再健全的生理也弥补不了精神上的打击,所以王胜利的精神灵魂与自己的家人并无二致。这一代代人始终被悲剧命运所羁绊,这几乎成了底层边缘人的宿命,这些人不仅缺衣少食且无法获得健全的生理,既会被同类健全人所歧视,也难逃命运的捉弄,只能以逃避的方式替代反抗。同样,处于底层的健全人也需要面对各种各样的压力,比如生存的压力、环境的压力等,所以无论生理是否健全,只要处于社会最底层,那么都无法逃脱小人物的命运,他们必须在社会的夹缝中苟延残喘,同时又在积极追求光明,不断进行自我的救赎。
另一类底层边缘人物就是在物欲横流世界里的沉沦者。现实社会充满了纸醉金迷,个体精神在这种社会背景下被蚕食渗透,社会经济资源在各个社会阶层中分配不均,由此导致底层小人物愈发渴望获得更多的金钱。《肚子的记忆》医师姚三才自身由于对学术缺乏深入的研究,也不具备高超的医术,所以始终无法获得更高的职称。王小肯暴食呕吐而无法自已,姚三才却束手无策,于是他想到了要通过论文的形式来研究王小肯的病症,希望能够以此来获得晋升和改善生活,并且还不惜斥巨资向王小肯贿赂,希望能够签字来证明自己论文中的莫须有病症,对名利的追逐使其忘记了医者仁心的初衷。《篡改的命》中的农村姑娘贺小文心地善良淳朴,与汪长尺婚后开启了市民生活。他们沉浮于光怪陆离的城市,由于丈夫遭遇不测而难以继续工作,家里失去了仅有的经济来源,在巨大的生活压力之下,张惠为贺小文指了一条路,即为上层人士提供性服务的按摩女。虽然贺小文起初对此嗤之以鼻,但是生活让其不得不低头而选择了妥协,虽然感觉愧对于自己的丈夫,但是又从工作中得到了金钱和肉体上的享受,由此又使得其以养家糊口之名而对性工作沉迷,甚至于不工作就会感觉到头晕目眩。她为了获得更多的赔偿款,便怂恿自己的丈夫对包工头实施敲诈勒索。人们原有的善良在现实的摧残之下而消失殆尽,这种沦丧是在现实逼迫之下的主动沉沦,人在纸醉金迷当中失去了人性。
较之于那些已经习惯于悲剧命运的荒诞戏剧小人物而言,这些处于社会底层边缘的人物已经有了反抗的主动意识,希望能够改变命运以及生存的环境,或者是随波逐流。沉沦只能使悲剧变得更悲,反抗没有任何的意义,所以人物在现实面前从希望走向了绝望,最终崩溃。
三、不堪一击的崩溃者
人们生活在现实当中,就必须面对复杂的社会关系和人物,而人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个体性格所决定的,这种导向力的作用力就是人生际遇对性格再塑造的强大后挫力。人始终处于寻求平衡的过程当中,而人们自我修复和协调这种平衡的过程,就是确保人生稳定、向上状态得以维持的最有效方式。而东西所追求的并不是这种平衡机制下各方稳定、幸福的状态。不可控的失衡状态才是其作品当中的主旋律,他笔下的人物往往表现出一种极端化的行为、感知,当产生不平衡点时,个体的极端认知模式会导致其不平衡状态的行为反应加剧。一旦这种不平衡不断加剧,进而达到临界点时,最终会导致人物产生生无可恋的崩溃。人物极端化性格具体反映在自身脆弱的本质上,将自己封闭在狭小的空间,对外界保持一副冷漠的态度,注重情感却脆弱无比。
个体封闭自我,以冷漠的态度对待周边的人和事,在行动力上充满了荒诞戏剧性,导致其极端荒诞疏离的意味充斥于同外界的联系中。在小说《我们的父亲》中,主要讲述了在三个孩子家短暂停留而又离开的父亲,最终消失在茫茫人海,以至于生命陨落也无人知晓。“我们”的父亲来“我”家时正值妻子怀胎三月,“我”此时因临时安排而不得不与领导长达20天出差在外,“我”回家后得知父亲已经离开且原因是担心抽烟会对妻子小凤肚子里的孩子产生影响,但事实是迫于小凤的逼迫而不得不离开。
冷漠无情的小凤使得父亲不得不选择另一个孩子为依靠,但又屡次碰壁。“我”急匆匆地追到二姐家,但是二姐却告诉“我”已经吃过饭的父亲离开了,但是真相是父亲因为二姐吃饭分发筷子“第四双筷子,姐姐没有擦酒精”而心生不满选择再一次离开。父亲的存在就如同风一样不被人关注,完全被淹没于儿女的麻木和现实当中。只有“我”还尚存着一丝对父亲的关爱。父亲的生命终止了,而这个消息还是来自一个掩埋过无人认领尸体的工人。但是当“我们”将埋葬父亲尸体的土坑挖开时却发现里面空空如也,父亲“永远失踪”了,我们也不知道“我们的父亲到底到哪去了”,而人与人之间的感情也随之失踪了。小说抽丝剥茧,发出了“我们的父亲是谁的父亲?”“我们的父亲到底到哪去了?”“我们的感情究竟在何处?”的灵魂拷问。而其中所揭示的就是血浓于水的亲情,最终走向了彼此疏离的冷漠。
东西还将另一个极端可能性赋予了笔下的人物,即情感至上,人将爱视为唯一的信仰,他们与现实生活维系完全依賴于感情,并且他们人生平衡也是以情感为支柱,情感一旦失去平衡便会导致产生人生危机,此时他们的生活完全寄希望于别人的情感补给,或者是精神在绝望中崩溃,最终以灭亡而结束。《抒情时代》中,“我”在一年夏天经历过6次失恋,当“我”变得对爱情不自信的时候接到了女孩陈丽的电话,对于这个“线上恋人”,“我”充满了依赖,通过电话相互慰藉,实质是以此来使自身状态的平衡得到维持,一旦失去了依赖对象便会导致个体发展失衡,而基于这种个体极端化性格特征,如果失去了这种情感维系,就必然会导致无法逆转这种失衡状态。因此,此类群体生活的支柱点就是情感补给。由此不难发现,东西笔下主要描写了两类极端化的人物形象,一种是麻木个体,他们高度认同人生无意义;另一种是对情感过度依赖的群体,他们一旦失去了情感,便会变得脆弱不堪。
性格上的脆弱和不堪一击,加上行为的荒诞戏剧化,使得处于社会最底层的群体被推向更加暗无天日的深渊。人生在性格和行为模式的影响下而受到了强大的反作用,使得性格崩坏的速度加快,命运在宿命的安排下而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正如西西弗斯的巨石诅咒,每当他快要达到山顶时,巨石总会在一步之遥间掉落,命运使得其与成功的距离总是无限接近而又不可得。因此,人们总是在无限的希望和失望当中落入宿命的安排之中。这类个体小人物反复经受宿命式的悲剧命运,总是被无情地困于牢笼之中,当命运的枷锁将牢笼锁住之后,生命的脆弱更是不堪一击,最终绝望而陨落。通过塑造荒诞人物,实际上是东西进一步继承了20世纪80年代的先锋思潮,在宿命论中塑造荒诞戏剧性的人物,又进一步创新了先锋思潮。因此,东西在对先锋人物塑造的过程当中最显著的风格就是荒诞极端的人物与现实困境的碰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