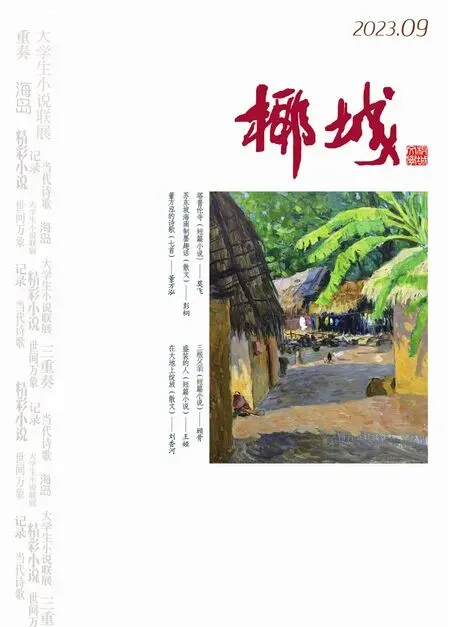从童年的阁楼到空中楼阁
◎金克巴
我家里屋的阁楼是我家的藏“宝”之地,沿着一架木梯爬上去,就看到楼板上摆放着十余件曾作为母亲嫁奁的宝贝,有长颈瓶、凸肚坛之类,靠墙叠放着几口红漆木箱。再看看我家的所在,一个屋舍俨然的庞大天井院落,青石板铺砌的小巷和晒台,石材取自于影影绰绰的远山,得力的梁柱都是硕大的木材,堂屋的木墙板用红漆刷过,就连屋里也铺着木地板,跫跫的足音犹在我耳边——如今却付之阙如,衰颓的迹象触目惊心。从村名“当铺金”便可窥见它曾经辉煌的草蛇灰线。据说我们祖上的发迹与他们在城里开设的鼎盛一时的当铺有关,甚至还演绎出“黄鹤楼飞金”的传说:有个纨绔子弟在蜗角虚名的怂恿之下从黄鹤楼上向楼下的人群撒金叶子,他那忘乎所以的虚荣似乎为村庄的式微埋下伏笔。时至今日,只有数堵高耸的马头墙还在透露些许鲁殿灵光般的矜持,黛瓦灰墙的严整已然舛落。
穿过幽深而不失色彩斑斓的蹉跎岁月,我又回到群山环抱的老屋,幽邃、亲切,曾是我不可或缺的地磁中心,至今仍维系着我的恋地情结。村里人在某次闲聊中说到:你奶奶就是在你家里屋的门槛上去世的,我也从未因此惴慄恂惧,反倒感到有一种隐然的力量庇护着我。身在天国的奶奶,您知道吗?我一次次坐在您生命终结之处,怀着有些陌生的孺慕之情想到素未谋面的您。既无叔伯,终鲜姑舅的我,却感到邃古以来祖祖辈辈的众多。
假如将我家老屋比喻成一个人,那他就是一个蕴藉含蓄的人,这种特质的核心就是窈然而深藏的阁楼。一般来说,阁楼属于家庭成员,对外是禁脔之地。只有在红白喜事的特殊日子,因其得天独厚的爽垲,才被临时辟为客人的宿息之处。在那些人们只能徒然想象山外世界很精彩的年月,我们的村庄却呈现出一派人丁兴旺的盛景,因为人烟稠密,阁楼也就不乏用武之地,屡屡被改造成高悬的卧室。有时我去探访同村的总角之交,就得沿着木梯爬到他家阁楼上,那真是一种毫不设防的信任,因为阁楼上大抵收藏着一个农家顶重要的财富,相当于《水浒传》中的“白虎堂”,却毫无保留地向我敞开。
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在我们的神话里腾云驾雾的神仙总是居于垂直空间的上方。在我的人之初,头顶的阁楼也曾表现为如斯诞漫的一个场所:每每入夜便成了老鼠的舞台,它们凭借黑夜的掩护在阁楼上恣肆地奔跑着,更深人静的时候不时发出强聒不舍的磨牙声,即便置身于万物灵长的卧榻之侧也大有一种莫余毒也的猖獗。人们大抵拿这种狡狯的啮齿类动物莫之奈何,竟然还虚构出老鼠嫁女的传说,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十二生肖里面原本卧虎藏龙却偏偏让区区一鼠拔得头筹。看来令人切齿的鼠辈,自有卓荦不群的智慧,实在是不容小觑。鼠类在阁楼上的欢腾曾让我的思绪飘向另一个与高尚和价值无关的平行世界,那儿的生灵同样有着心无所羁的欢乐,有着轰轰烈烈的爱情,甚至还有所谓的家庭责任……就像荣格所说,人与严格意义上的动物都是上帝身上微小的部分,只不过独立出来罢了,因而能够随心所欲地走动和选择居所。神秘的爱也是这样吗?我们拥有的爱只是作为整体大爱的一个微小部分,爱控制着我们,而不是我们控制着爱。我凭什么说鼠类的欢腾就是盲目的?它们只不过是顺应着爱的自然。它们适才在阁楼上乐不可支地来回奔逐,大人被惊醒的反应,只是重重地拍几下眠床,又沉入梦乡。村民对老鼠没有好感,但也从未想到要将它们赶尽杀绝。因此,从古到今都延续着人鼠共存的“和谐”局面。
鼠也有悲戚的时刻——当它们与貌似慵懒的猫不期而遇。有时,猫与鼠——这对据说与生俱来的冤家对头在阁楼上猝然相遇,继而上演一出猫捉老鼠的戏码,生死攸关的紧要关头,慌不择路的老鼠发出吱吱的叫声。所幸,邻家的花猫总是被瘸脚老太照顾得好好的,她从池塘里捞小鱼侍候它。有了老太的悉心照料,花猫大可以在她厨房里犹如闲庭信步,优游卒岁,也就从貌似慵懒过渡到真的很慵懒。大白天寻常可见的一幕是,花猫十分安逸地趴在灶膛边酣睡,被人不小心碰到才不情愿地睁开眼。倘若它会说话大概还会抱怨,为何扰人清梦?但沉湎于岁月静好的温驯的花猫也有张狂得不能自抑的时候,那便是它发情的日子,接连几夜都在我们头顶“喵喵喵”地诉说着它荡漾的春心,从阁楼到屋檐。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随后几天它还跟老太不辞而别玩起了失踪,令她一时怅然若失。
早年的阁楼是一个幸福的所在,庋藏着我家最珍贵的物什,除了母亲的嫁奁,还有来自土地的各种收获:五谷杂粮、粮油米面,箱子里装着被褥布料,那时几尺“的确良”就堪称稀罕之物。总之,一间小小的阁楼汇聚着一个农家物质生活的精华。偶尔,我也跟妈妈玩失踪,或者是一次捉迷藏,我跟家人闹起了莫名其妙的小情绪,悄悄爬上阁楼,竖起梯子——制造出阁楼无人的假象。我呆在阁楼的这段时间,由针尖与麦芒针锋相对时激起的不容察觉的微澜早就归于平复,我怔怔地望着屋顶上斗大的蜘蛛网,一粒花生米大小的园蛛稳坐于中军账,它可以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却惮于我青萍之末一般的气息对它的惊扰,让它一时彷徨狼顾。这时,终于有人喊我吃饭,尽管我的肚子在咕咕地鼓噪,我就是不吭声。但诸如此类的小把戏只能偶一为之,倘若故伎重演,母亲准会如囊中探物一般在阁楼里找到我。
在阁楼上寻宝?也是有可能的。加斯东·巴士拉说,纯粹的回忆没有日期却有季节。但对我来说,有的回忆就连季节也不复存在,那是日光浏亮而柔和的某一天,我待在小阁楼上,眼前一个墙洞吸引着我。我们当地民居的墙壁大多是由三寸厚的青砖砌成的,中空的墙体填入了泥灰。时日一久如果出现墙洞,里面大抵曲折迂回,我不知道洞里隐匿着什么:一个雀窝,一个鼠洞,甚或住着一条令人毛骨悚然的家蛇?是的,我们都把与村民处在同一个屋檐下的蛇类称为家蛇,委实说,我这个山村的孩子曾与花色各异的蛇不期而遇,但极少听说过谁被蛇咬伤,被咬致死的事更是闻所未闻。总之,初生之犊不怕虎,在轻度无聊和重度好奇的怂恿下,我的手一点点伸进墙洞里,灵敏地感受着指尖的触碰。突然,我碰到了什么,冰凉、坚硬,肾上腺素顿时飙升,我把它拽出来,是一串约有二十余枚的铜钱——都是清代孔方兄的子嗣,被时代捐弃之后被人用来当成蚊帐上的饰物,再往后就尘封于此。一晃经年,拂去尘埃,铜绿难掩黄铜的光泽,我知道它们历经无数人掌心的辗转,一定曾有人为了这么一串铜板而汗流浃背,备尝艰辛,最后它们才出现在我眼前。这是冥冥的因缘,通过它们,少不更事的我似乎触及一段过往的岁月。它们也就成了我的藏品之一。在阁楼上我还有着另一次惊奇的发现,有一次翻箱倒柜,我在一个木匣子里发现一张写在正丹纸上的地契,由于年代久远,纸质已经脆变,鲜艳的红色变成酒红色,我小心地展平,只见纸上的墨迹光亮如新,好似一群人不久前在商议之后慎重写下的。地契说的是我爷爷过继给一个族人,族人没后一切田产悉由爷爷继承,末尾是一干证人。执笔人是我的一位宗亲——时至今日,他的大名和轶事还一直在村里流传。在那个残阳如血的时代,“礼”依然闪烁着耀眼的光芒,这位宗亲是遵从传统礼数的代表,受人尊敬的乡绅,还当上了县长。人常说,富贵不返乡,如锦衣夜行,但这位宗亲即便衣锦还乡也还近乡情怯,每次回村总是大老远就下马缓行,见了乡亲就热络地打招呼,到了村口将马拴在下马石上,决不会趾高气扬一路驱驰,到了他家门口才翻身下马。——现在,那张地契也是我的私人藏品之一,偶尔发箧一读,眼前便浮现出早就消逝的一幕,仿佛看见几个温柔敦厚的人围炉而坐。
九岁那年,阁楼之于我有如南枝北枝,让我惊诧于人间的冷暖与荒诞。一桩为纯朴的心灵所忽略的医疗事故夺去了父亲性命。在乡卫生院,淋了一场秋雨而感冒的父亲因为心悸,被一个初来乍到的实习医生注射了一剂镇静剂之后就再也没有醒来。因为我们的维权意识尚未萌芽,父亲仓猝地撂下了他热爱的三尺讲台撂下了倚仗他为家中顶梁柱的妻儿,不明不白地走了。对于我,倘若在那之前适度的孤独还只是内向和腼腆的孪生兄弟,那么现在他们仨因为饱尝爱别离苦的滋味已然合体,成了真正的孤独——饱满成熟的孤独,孤独的核心是过早地充斥着哀愁,与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少年闲愁无关。阁楼成了我“遁世”的一方净土,我与自己的第二人格在阁楼上坦诚相对;我似乎感到再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伤害到我;我不时翻看着父亲留下的一摞摞书,里面那我反复摩挲翻阅过的《古文观止》,时至今日它依然是我不时翻阅的一本书。只是那时我浑然不觉,与村里同龄人相比我多了一点什么,那就是父亲珍藏的大量书籍,实在是一笔隐形的佳贶。我极度需要安全感,而阁楼便是可以给我安全感的地方。我一次次爬上阁楼,收拢梯子,伪造楼上无人的假象,似乎只有那样才不被任何人找到。
几乎与联产承包到户同时,大地上刮起一股文学的东风,一时之间,我周遭到处都不乏文学爱好者,各种文学团体如春笋怒发。我接触到林林总总的油印刊物,小学老师组织我们创办了一份油印小报,且美其名曰《栀子花》,寄寓着它像栀子花一样洁白芬芳。我尝试着写下自己的心里话,不同于写作文时因为要顾及思想正确从而粗制滥造虚构出来的好人好事。因为爱上另类的“作文”,我屡屡在阁楼里潜伏下来。童蒙的我竟然就在冥然不觉中追蹑前贤的人生轨迹:比如陶渊明当了八十一天的小官后就兴味索然地决意皈依田园,从此安于采菊东篱下和带月荷锄归;康科德的梭罗只身拎着一把斧头到瓦尔登湖畔缚茅而居,在两年多里过着物质极简的生活;被放逐的斯宾若莎,毕生的工作就是在阁楼上精心地打磨镜片,不为挣钱,只为在忙碌的手工之余可以思考上帝;分析心理学大师荣格一直有一个为自己营建塔楼的梦想,经过一番鸠工庀材,他的塔楼终于伫立在苏黎世波林根湖边,里面没有什么现代化设施,荣格亲自劈柴生火,在塔楼里,他感到自己终于回归自然,并与之融为一体。他认为,自己本身就是上帝身上极微小的一部分,个体之于上帝是最为直接的体验。再看看我,童年的阁楼终将平滑地通向空中楼阁,而我此生将久久地沉浸其间。
阁楼局促,但足够容纳我和我的孤独。就像德富芦花那个只有十平的小院,院落小,亦能仰望碧空,信步遐想,亦能想得很远很远。我的阁楼虽小,却宜于清梦,宜于湛思,宜于幻想,俨然是人体的上层建筑——头部。
阁楼的南墙有一个小小的瞭望窗,高度刚到我眼睛的位置,斜角朝外。从某种意义上说,我的阁楼好比博尔赫斯笔下的阿莱夫,只是在我这儿它是一个小小的空间,透过长宽不盈尺的瞭望窗可以望见南边被村民美其名曰“金盆山”的坡地,耸然而特立的东山,还有远处影影绰绰的巫山。有时我长时间伫立在瞭望窗前,观察着眼底的动静,而此时,却无人知道这个观察者的存在。我感到阁楼的安全、内敛和神秘。有人进而将我们天井院落的这些特性与我们这一支族人的出处联系起来。两千年前,我们的赐姓始祖——匈奴休屠王子金日磾还只是一个孩子,一场生死攸关的危机已经迫在眉睫。霍去病统率的大军压境,是战是降?匈奴两部落的首领休屠王与浑邪王莫衷一是,在随后的内讧中休屠王一命丢空,经过血风腥雨洗礼的金日磾似乎朝夕之间就长大了。他审时度势,顺应历史的潮流,带领族人融入中华民族的大家庭中,他自己则成为被汉武帝倚重的顾命大臣。时到今日,还有金氏后裔把代代传承的建筑形式所表现出来的含蓄蕴藉和某些神秘特质都归之于集体潜意识的流露。
父亲溘然长辞之后,我家又发生了诸多变故。有一天,我的一个总角之交在一处墙根凑到我跟前,神秘兮兮地对我说,“XX到你这了。”其实他说的并不是什么秘密,只是说话的神色似乎意味着他说的是不便张扬的话,所以他才按捺不可名状的兴奋来向我求证。是的,一个据说可以照顾我们的男人来到我家,最终,那个人让他所扮演的徒有其名的角色而黯然失色,让一艘破船驶向另一片并不风和日丽的海域。那种生活带给我的不适有如一块坚硬的石头一直硌得我生痛。在别人眼里,我稚嫩、无知,是一株可以漠视的自我意识薄弱的草本植物,只有当我和孤独一起,我才是我自己。我不说疼痛,植物似乎没有痛感,遑论加大号的疼痛,我只说普适性的孤独,一阵风来,晃动的枝叶就抑制不住的孤独。孤独是一杯越来越绵醇的液体,我偷偷地喝得酩酊大醉。我躲在阁楼里沉浸式地读书,一遍遍地读艾青的《大偃河——我的保姆》,读他的《生命》:
有时
我伸出一只赤裸的臂
平放在壁上
让一片白垩的颜色
衬出那赭黄的健康
生命是什么?在庄子看来,是生之不能却,其去不能止。是帕格森喻之为不可遏止、不断绵延的爆炸。人,落草于斯,并不曾跟自己的父母确认,彼此是否真的确认过眼神,他们选择了我,我便没心没肺地应允。否则他们为何要青睐驽钝庸常的我,而我实则加剧了他们的劬劳,使他们过早地透支自己的身心?大抵流于一种自然的态势,苦着乐着不必怨天尤人,从此,纯然无私地相亲相爱,坦然地接受命运的安排。在阁楼上,艾青的诗化作一场甘霖洒向混沌初开有些焦灼的我,阵阵情感的雨花沾溉着我。文学的种子在心底悄然落地生根,只待合适的墒情就破土而出。对于我,寂静的阁楼就是催动它萌芽的温床。十岁那年,我尝试着写一种分行的文字,据说,它叫做诗。但诗大概会说:只有本质上是诗才是诗,分行只是我的形式。好比同样是词语的流水,在河床上流淌的是汩汩的河水,在海里晃荡个不停则是汹涌的波涛。我躲在阁楼上着迷地涂抹着,写下一本又一本不曾感动别人却不时感动我自己的“笔记”。阁楼俨然是我生命密不可分的一部分,如同炼金术士的密室。
荷尔德林说过,请别过早将人从草棚中赶出去,童年曾在草棚中流逝。我无力这样说:时光啊,你慢慢走,别过早将我从阁楼上带走。遭逢物是人非的变故,成长的过程对于我就像熬鹰一般格外难捱。所幸我有一爿阁楼,所幸阁楼上还有父亲留下的馈贫之粮——书,所幸还有在我们存在之前就已经存在着的具有先在性和可以穿透意义的语言……使得我在晃荡不定时犹可与它们相遇,进而粗拙地拼凑着自己的一苇之航。
成年之后,在一浪接过一浪的漂泊中,我的阁楼置换成空中楼阁。我人生的第一个空中楼阁是一处山居,是精神物质相爱的结晶,只是物质的水平极低,真正体现了“审容膝之易安”,因而不能简单地说它只是一间出租屋,它也是我的梦之居。从精神的层面来说,我的空中楼阁就像德富芦花那个令他恬然自适的小院。因其所大而大之,则万物莫不大,如此看来,湫隘和局促就是我的空中楼阁的优点。
再后来,梦之马驮着我向曾经流传着朱雀玄鸟的南方一路驱驰,便有了游骑无归的彷徨,马瘦毛长的落寞,穷猿奔林的狼狈和窘迫。青春的美好情愫在艽野之境屡屡零落成泥辗作尘,而我的梦也一度舛落沉沦。在辗转淹留过的南方工业小镇,在茫茫人海,我又蓦然想起童年阁楼上那一摞摞曾经反复摩挲过的书,似乎有个声音在殷切地召唤着我。一如荣格初识弗洛伊德的时候,他的第二人格便隐隐地诉说着它的迷茫。我也在迷茫中跟自己对话,于是,在无所适从的迁徙中,我酽念着自己的梦之居。
飘蓬断梗的生活让空中楼阁的出现甚为魔幻,有时在海边,有时在闹市,有时在山里,有时藏身于一个地名土得掉渣的蝶变中的城中村,可能是一楼、三楼、十二楼、铁皮房、劏房,可能是闹市,可能是筷子楼深处的一间,可能濒临荒野——一幢墙皮斑驳陆离的正在窳败的居所,却因为芊绵的草木和丰富的天籁让我愉快安宁。我爱着自己的空中楼阁,而不是爱着被爱伦·坡称为方块状赘疣的人造建筑当中的某一间。它物质至简——只有四壁和一床而已,却因为梦想的加入而不失其丰赡,我络绎不绝地请回那么多有趣的灵魂,在楮先生的撮合下与古往今来的他们相识重逢。倘无这些奇妙的邂逅相遇,我大可以想象一种意义寥寥又兴味索然的生活——造夕思鸡鸣,及晨愿乌迁——曾经在茫茫大块和悠悠高旻之间是一种人虽然活着却几乎与生活无关的真实写照。
我的日常便有了这样一些不期而来的朋友:一只在窗外的锡兰肉桂树上与我近在咫尺彼此对视的麻雀,一只白天贸然闯入颉之颃之的报喜斑粉蝶,或一只凌晨时分已经飞得精疲力竭的迷航的蜜蜂。让仓促主人的我一时不知如何是好。且说说那只蜜蜂吧,它于一片漆黑中望见我室内这盏炳辉的灯光,便误以为那是光明的先导,是朋友的慷慨邀请,是归巢的集结号,便径直飞到台灯下绕着灯泡飞过一圈又一圈,翅膀不停地拍打着罩壁,扫下些许微尘,有时它就落在灯罩边缘。我能感受它找不到出路的穷窘蹇滞,便有心帮它离开。我关灯片刻,嗡嗡声停下,我以为它已经投向窗外无垠微光的怀抱,然而,当我再度开灯,熟悉的嗡嗡声又响起来,它仍然围着台灯跌跌撞撞地起舞。我只得将台灯再次擎向窗外,蜜蜂也跟着飞走,我关上灯,希望可以将它留在窗外。然而,过了片刻当我再度开灯,它又飞了进来。我只得重复上面的操作,直到终于成功地将它请到窗外。我为自己没有亵渎它心上无羁的信任而长舒一口气。
这些年来,紧挨着流水线的边缘是我口腹自役的生存方式,让我在活着与生活之间找到一种微妙的平衡,为活着的苦加一点糖,为生活的甜加一点盐,让它从不至于甜得腻人或苦得令人绝望。我想到米什莱曾说过:“要是我的父母顺应理智的想法,让我当工人,以拯救他们自己,那么我是否就此完蛋了?不,在所有工人中间我看到不少事业卓有成就的人,他们的聪明才智足以与文人相侔。”这种依法,的确可以给我些许安慰,说明世间各种各样的生活当中未必有一种生活会必然导向海德格尔所说的“绝大多数人的沉沦倾向”,即便沉浸于平凡的工作本身也是不凡的人生修行和救赎,是出于爱生活而不是爱着冰凉的铁和塑胶齁人的气味。
我在后工业时代的多个南方小镇辗转迁徙,唯一不变的是,我一直拥有一个挪移的空中楼阁,它简陋,与家庭无关,离开某个琐碎的中心之后我会在这个楼阁中找回自己。有一天,我在费尔南多·佩索阿的《惶然录》中读到他所讲述的梦的外形,顿时觉得:天啦!它俨然就是我在自己的空中楼阁里无声长啸时所听到回声,他说:“如果道拉多雷斯大街上的办公室对我来说代表了我的生活,那么在同一条街上我就寝的第二层楼房间,就代表了艺术。是的,艺术和生活,在同一条街上,却是在另一处不同的房间里。有多少次,我看见自己的梦想获得物体的外形……”读到这段话,我的微躯不由地为之一震,他所说的,不正是我低到尘埃的生活吗?!极繁冗极轻逸,试图触及尘世生活的两个极性。终于,有一只掠过了铁和塑胶的彩蝶令我蓬荜生辉。在那边,不到三百米远的地方,机器的喧豗如时响起,在所谓的旺季彻夜响个不停,它是我作为一个流于表象的行动者长久淹留的处所;在这边,让我窈然而深藏的地方,一股看不见的流水在汩汩地流淌,不绝如缕地冲刷我。会让我在某个时刻想到克维多的“唯易逝者永存”,他说的不正是不舍昼夜却永不消逝的流水吗?在我的空中楼阁我同时感受着短暂和永恒的两极,并且有一个小小的野心:在有生之年由灵魂和肉体这两种单独的元素所构成的我,在空灵之水的流动中,送走一个个乔装成“我”的他者,不断迎来个人精神中的一抹新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