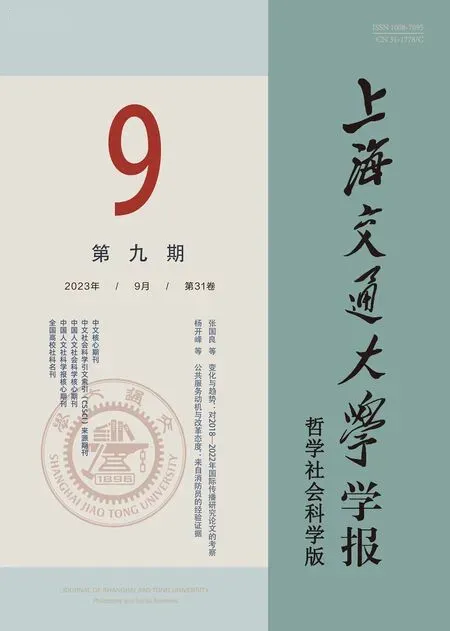市民服务热线中的政府回应:以上海市X区为例
秦川申 张弘力
(1.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上海 200030;2. 上海交通大学应急管理学院,上海 200030)
一、 问题的提出
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不断增长,在民主法治、生态保护、社会公平等方面提出了多样化的诉求。面对日益多元且复杂的诉求,如何精准回应、采取有效措施成为回应型政府建设过程中面临的重要问题。政府对公民诉求的高效回应有赖于高效的政民沟通。(1)Karl W. Deutsch, The Nerves of Government: Models of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and Control, New York: Free Press of Glencoe, 1963.近年来,全国各地陆续设立多种公民参与渠道,以便收集公民意见、了解民意民情,进而切实回应公民诉求。截至2022年,全国各地政府已开通345条12345市民服务热线,这也成为公民意见表达的重要渠道。市民服务热线推出后受到广泛关注,意见收集与回应卓有成效,成为畅通民意诉求、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的有力杠杆。(2)吴国玖、金世斌、甘继勇: 《政务热线: 提升城市政府治理能力的有力杠杆——以南京市“12345”政府公共服务平台为例》,《现代城市研究》2014年第7期,第98—102页。2022年5月16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推动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与110报警服务台高效对接联动的意见》(国办发〔2022〕12号),(3)相关政策文件还有: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优化地方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的指导意见》,2021年1月6日,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21-01/06/content_5577419.htm,2023年1月15日。要求进一步优化政务服务热线,整合服务资源,提升协同联动处置效率以提高服务实效,为地方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的优化指明探索的方向。
然而,在全国各地的实践中,有的地方政府出现了回应力不足、回应信息不完备和选择性回应的现象。(4)李传军、李怀阳: 《公民网络问政与政府回应机制的建构》,《电子政务》2017年第1期,第69—76页。在选择性回应中较为典型的是对情绪的选择性,政府往往更加关注带有强烈情绪和群体性行动特征的表达方式,并对此做出回应。事实上,个体的负面情绪并不必然导致舆论事件或集体行动,单纯关注个体的激烈情绪表达并不能有效识别普遍诉求、纾解群体情绪、防范舆论事件。公众基于共同的利益、情感、经历和价值产生共情,可能形成群体性负面情绪。当个体间共同的诉求长期积压得不到回应,可能演变为群体的激烈情绪,这是导致集体行动的原因之一。(5)冀翠萍: 《突发事件政务舆情回应的偏差与回应能力提升研究》,《领导科学》2021年第13期,第100—103页。在研究中有必要将个体情绪与群体情绪进行区分,讨论其对政府回应性的不同影响,为政府部门更好关注、识别、回应公民情绪提供参考,进而帮助构建更加和谐有序的政民互动格局。本研究结合政府回应研究中的避责行为解释,基于群际情绪理论讨论政民互动中个体和群体的情绪特征对政府选择性回应的影响,提出以下两个研究问题: 公民参与中的情绪特征是否影响政府回应性?其作用机制是怎样的?既有情绪与政府回应相关研究中并未区分个体与群体的情绪,本研究的主要贡献在于厘清个体情绪与群体情绪的概念区别,明确负面群体情绪作为集体行动的重要前因变量,以对负面群体情绪的关注解释政府回应性的差异。
二、 文献综述与研究空间
(一) 政府回应性与市民服务热线
政府回应指政府对公众接纳政策、提出诉求做出及时有效反应,采取积极有效措施解决问题的过程。(6)格罗弗·斯塔林: 《公共部门管理》,陈宪等译,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从表现内容角度,政府回应可以分为话语性回应、行动性回应和制度性回应三类,话语性回应指政府对公民诉求作出解释说明或承诺,行动性回应是政府通过实际行动满足公民诉求,制度性回应则为通过行政立法、执法回应诉求。(7)李放、韩志明: 《政府回应中的紧张性及其解析——以网络公共事件为视角的分析》,《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第1—8页。在市民服务热线互动的实践过程中,由个体公民诉求推动政府立法的制度性回应案例较少,本研究关注的是市民服务热线互动实践中的话语性回应和行动性回应两种方式。对我国政府回应动力的讨论可以分为两个方向,一是自上而下的压力,包括领导重视、(8)李锋、马亮: 《领导重视与数字政府回应力——基于双重差分与合成控制法的实证分析》,《公共管理评论》2021年第3卷第1期,第68—90页。问责压力等;(9)邵梓捷、杨良伟: 《“钟摆式回应”: 回应性不足的一种解释——基于S市地方领导留言板的实证研究》,《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20年第1期,第114—122页。二是自下而上的动力,包括政府伦理责任、(10)张则行: 《政府责任重构与公共服务授权——回应型治理的一个分析框架》,《福建行政学院学报》2015年第1期,第29—37页。集体行动和舆论事件压力等。(11)Jidong Chen, Jennifer Pan, Yiqing Xu, “Sources of Authoritarian Responsiveness: A Field Experiment in China,”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60, no.2 (April 2016), pp.383-400.在上述动力机制下,我国政府开设了多条公民意见反馈渠道,作为常态化、制度化的政民沟通方式,收集民意民情并作出反馈,主要的渠道有市长信箱、市民服务热线等。
国内现有对市民服务热线与政府回应的相关研究较少,主要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从各地12345市民服务热线实践案例出发讨论政府回应现存问题。例如在政府内部存在政务热线职能定位不明确、管理体制机制有待完善、人才队伍有待加强等问题;(12)吴国玖、金世斌、甘继勇: 《政务热线: 提升城市政府治理能力的有力杠杆——以南京市“12345”政府公共服务平台为例》,《现代城市研究》2014年第7期,第98—102页。在外部也出现社会力量参与不足、诉求表达私利化等情况。(13)雷望红: 《被围困的社会: 国家基层治理中主体互动与服务异化——来自江苏省N市L区12345政府热线的乡村实践经验》,《公共管理学报》2018年第15卷第2期,第43—55页。此外,虽然12345市民服务热线推动了政府回应工作回输属地并在基层解决,但是也导致行政压力承担的基层化,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基层治理的自主性。(14)陈锋、宋佳琳: 《技术引入基层与社区治理逻辑的重塑——基于A市12345政府服务热线的案例分析》,《学习与实践》2021年第4期,第84—94页。另一类研究关注政务热线运转中的微观政民互动,使用市民服务热线的工单数据,讨论影响政府回应性的特征。既有研究对影响因素的讨论主要涉及三方面: 诉求特征、公民话语及区域特征。诉求特征包括议题类型、涉及范围、办理成本、诉求复杂度等,(15)张会平、邓凯、郭宁等: 《主体特征和信息内容对网民诉求政府回应度的影响研究》,《现代情报》2017年第37卷第11期,第17—21页。公民话语包括诉求话语、是否提供个人信息等,(16)颜海娜、谢巧燕: 《公民诉求对政府回应话语的影响探究——基于F市G区12345平台数据的实证分析》,《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23卷第1期,第78—86页。区域特征则包括地理环境属性、市民参与热情、人口复杂情况、组织复杂情况等。(17)赵金旭、王宁、孟天广: 《链接市民与城市: 超大城市治理中的热线问政与政府回应——基于北京市12345政务热线大数据分析》,《电子政务》2021年第2期,第2—14页。
(二) 影响政府回应性的公众情绪因素
有时候公民为获得政府关注和回应,策略性地选择“闹大”的方式,借助负面情绪表达利益诉求。(18)韩志明: 《利益表达、资源动员与议程设置——对于“闹大”现象的描述性分析》,《公共管理学报》2012年第9卷第2期,第52—66页。从政府回应的动力机制看,自下而上的社会压力是政府有效回应公民诉求的重要动力之一。(19)Gary King, Jennifer Pan, Margaret E. Roberts, “How Censorship in China Allows Government Criticism but Silences Collective Express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107, no.2 (May 2013), pp.326-343.(20)Gary King, Jennifer Pan, Margaret E. Roberts, “Reverse-engineering Censorship in China: Randomized Experimentation and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Science, vol.345, no.6199 (August 2014), p.891.既有讨论情绪与政府回应的研究主要基于情绪评价理论等视角,将公民的负面情绪同舆论事件、集体行动倾向关联,进而解释负面情绪对政府回应的刺激和促进作用。(21)曾润喜、黄若怡: 《地方政府对网络问政的信息注意力分配的层级差异研究》,《情报杂志》2021年第40卷第8期,第127—135页。情绪是舆情危机等网络群体性事件的主要表现形式,(22)李杰、王雪可、刘力宾: 《医保欺诈事件舆情传播的情感焦点与情感倾向演化研究——基于舆情客体视角》,《情报科学》2020年第38卷第4期,第77—82页。政府的组织干预和决策是影响事件发展和消解情绪的重要途径。(23)周建青、刘佳文: 《政府回应视域下公共事件次生舆情形成机制与防范策略——基于情绪评价理论的分析》,《学习论坛》2022年第2期,第77—84页。负面情绪的聚集可能引发舆论危机,若政府采取避责的方式应对舆论危机,则可能损害政府形象,影响政府公信力,(24)唐雪梅、袁熳、朱利丽: 《政务舆情回应策略对政府形象修复的影响——情绪认知视角的有调节中介模型》,《公共行政评论》2021年第14卷第1期,第114—131页。由此产生的压力可以促使政府对公共事件作出积极回应。(25)钟伟军: 《公共舆论危机中的地方政府微博回应与网络沟通——基于深圳“5.26飙车事件”的个案分析》,《公共管理学报》2013年第10卷第1期,第31—42页。当公共事件突然爆发并广受公民关注时,地方政府在规避上访、公开投诉等动机的推动下,对公民激烈的情绪采取更为积极的措施作出回应,有学者将这一类突发事件的政策议程触发模式总结为政策议程的“突发—回应”模式。(26)杨云舒: 《回应性政策议程触发模式: 对我国特有政策议程模式的一种尝试性阐释》,《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20年第22卷第3期,第136—144页。在这一模式下,公众对事件的关注和负面情绪的表达对政府回应发挥着重要的刺激效应。
然而,既有研究并未区分个体情绪和群体情绪对政府回应性的影响。个体的负面情绪并不直接与舆论事件、集体行动产生关联。(27)Charles R. Seger, Eliot R. Smith, Zoe Kinias, et al., “Knowing How They Feel: Perceiving Emotions Felt by Outgroup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vol.45, no.1 (January 2009), pp.80-89.群际情绪理论指出,个体和群体的情绪在影响行动倾向时发挥着不同的作用,个体情绪影响个体的行动倾向,并不直接影响群体行动的倾向,而群体的情绪直接影响群体行动倾向。个体的愤怒、怨恨等情绪反应,可能导致个体产生对抗或攻击性行为,但并不能直接导致群体行动。但群体共同的不平等或相对剥夺遭遇,会引发群体的愤怒或恐惧等群体情绪,进而催生不同的群体行动倾向。(28)E. R. Smith, “Social Identity and Social Emotions: Toward New Conceptualizations of Prejudice,” in Diane M. Mackie ,David L. Hamilton, eds., Affect, Cognition and Stereotyping, Amsterdam: Elsevier, 1993, pp.297-315.在个体情绪和群体情绪的联系方面,个体的情绪可以通过传染、共同认知、交流评价等方式在群体内部共享,聚合成为群体情绪,导致群体情绪的趋同。(29)E. R. Smith, C. R. Seger, D. M. Mackie, “Can Emotions Be Truly Group Level? Evidence Regarding Four Conceptual Criteria,”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vol.93, no.3 (February 2007), pp.431-446.从这一关系看,个人情绪在聚合、共鸣的条件下,可能形成群体情绪,间接影响群体行动。(30)V. Yzerbyt, M. Dumont, D. Wigboldus, et al., “I Feel for Us: The Impact of Categorization and Identification on Emotions and Action Tendencies,”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vol.42, no.3 (December 2003), pp.533-549.但若个人的情绪不具有普遍性,没有形成群体的情绪,则不能关联群体行动的倾向。因此在对群体行动的预测中,群体情绪是一个更加直接的变量,并不能简单将个体情绪与群体行动挂钩。本研究区分个体情绪与群体情绪,在规避舆论事件和集体行动风险的视角下,讨论其对政府回应性的影响。
(三) 研究空间
既有公民情绪与政府回应的相关研究中,主要将公民情绪作为一个整体的概念,鲜有对公民情绪的类别进行更细致的讨论。但在实践中,公民情绪包含个体情绪和群体情绪,群际情绪理论等相关讨论也将群体情绪与个体情绪区分,目的是讨论二者在解释群体行动中的不同作用。(31)J. C. Becker, N. Tausch, U. Wagner, “Emotional Consequences of Collective Action Participation: Differentiating Self-directed and Outgroup-directed Emotion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vol.37, no.12 (May 2011), pp.1587-1598.在政民互动中,公民具有个体的情绪,在群体层面上也可能存在共同的情绪,形成公民群体情绪。既有文献主要通过舆论事件或集体行动压力视角解释公民情绪对政府回应性的影响,但个体与群体情绪在其中的作用存在差异,将公民情绪作为整体概念并不足以充分解释其不同影响。本文的研究空间在于,在政府回应的研究中,关注微观、具象的政民互动过程,对公民的个体情绪与群体情绪分别进行讨论,进一步阐释公民参与中情绪特征对政府回应性的影响机理。
三、 研 究 假 设
无论是对个体情绪还是群体情绪的回应,都出于特定的动力机制,从地方政府回应公民诉求情绪的行为逻辑和动力机制出发,可以探究政府回应性与公民情绪间的深层关系。已有研究指出“邀功”和“避责”的逻辑广泛存在于地方政府治理行为中。(32)倪星、王锐: 《从邀功到避责: 基层政府官员行为变化研究》,《政治学研究》2017年第2期,第42—51页。地方官员的晋升与问责由中央控制,形成了我国官僚体系的纵向控制。(33)张程: 《数字治理下的“风险压力-组织协同”逻辑与领导注意力分配——以A市“市长信箱”为例》,《公共行政评论》2020年第13卷第1期,第79—98页。地方官员在不同情境下感知到晋升激励或问责压力,进而形成不同政策行为动机。(34)文宏、杜菲菲: 《注意力、政策动机与政策行为的演进逻辑——基于中央政府环境保护政策进程(2008—2015年)的考察》,《行政论坛》2018年第25卷第2期,第80—87页。不同的政策动机形成差异化的地方官员行为逻辑,并外显为政策要素冲突中政策行为的差异。“邀功”和“避责”的政策动机受到风险的不确定性、信息的模糊性和不对称性以及问责压力的影响,当短期问责压力大且信息明确时,地方官员会优先考虑避责的策略,反之则优先考虑邀功策略。(35)章文光、刘志鹏: 《注意力视角下政策冲突中地方政府的行为逻辑——基于精准扶贫的案例分析》,《公共管理学报》2020年第17卷第4期,第152—162页。
在地方政府回应过程中,公民通过具体渠道向政府表达诉求,政府基于诉求内容作出回应。邵梓捷和杨良伟基于“压力—回应”逻辑提出了地方政府回应民众诉求的分析框架,指出基层部门回应的主要动力是上级政府的制度压力。(36)邵梓捷、杨良伟: 《“钟摆式回应”: 回应性不足的一种解释——基于S市地方领导留言板的实证研究》,《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20年第1期,第114—122页。对于地方官员而言,制度压力主要来自在社会治理过程中可能引发上级政府问责和惩罚的政治风险。在政民沟通互动的过程中,一方面,公民诉求的内容、情绪特征在沟通过程中是可知的,回应好公民诉求和情绪、维护社会稳定的目标也是清晰明确的;另一方面,没有回应好公民诉求和情绪,以至形成集体性行动的后果和问责压力是巨大的。在短期较大问责压力和信息明确可知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回应过程是基于“避责”行为逻辑的组织决策,通过作出回应以避免政治风险事件发生,进而避免上级政府问责和惩罚。
综上所述,在政府回应的过程中,地方政府受到来自上级政府问责的政治风险压力,会采取“避责”行为逻辑。已有研究根据应对态度和问责时间节点两个维度,将决策者的避责行为分为四类,并指出在职位权责明确、政治风险较高的情况下,决策者会采取有为式预估策略,在问责启动前采取积极的预防行为。(37)彭宗超、祝哲: 《危机决策者避责策略的四种模式及关键影响因素分析》,《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8年第19卷第4期,第93—101页。在群体事件“一票否决”制度的影响下,集体性行动相关的政治风险要素是地方政府关注的主要风险,在政府回应中则表现为对具有集体性行动倾向的公民诉求配置更多注意力,以防范政治风险,维持社会稳定。就公民角度而言,公民情绪与集体性行动倾向密切相关。(38)Helena Flam, Debra King, Emotions and Social Movements, London: Routledge, 2005.公民向政府表达诉求过程携带自身情绪,若与诉求相关的负面情绪未获回应,情绪逐渐积累可能导致诉求中的负面情绪传播扩散。当个体层面的情绪获得群体层面的认同和共鸣,则可能产生集体行动。(39)韩志明: 《信息支付与权威性行动——理解“闹决”现象的二维框架》,《公共管理学报》2015年第12卷第2期,第42—54页。因此政府注意力配置会关注诉求的情绪特征,当诉求呈现明显负向情绪时,地方政府对该诉求配置更多注意力,表现更强回应性以期规避潜在的集体行动风险。
故有H1: 政府回应性强度与公民诉求包含的负面情绪强度正相关。
根据群际情绪相关的讨论,群体情绪与群体的行动倾向密切相关,群体的愤怒、蔑视、内疚等负向情绪可能导致其采取集体行动。(40)Martijn Van Zomeren, Russell Spears, “Metaphors of Protest: A Classification of Motivations for Collective Action,”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vol.65, no.4 (Novermber 2009), pp.661-679.(41)Martijn Van Zomeren, Russell Spears, Agneta H. Fischer, et al., “Put Your Money Where Your Mouth Is! Explaining Collective Action Tendencies through Group-based Anger and Group Efficac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vol.87, no.5 (November 2004), pp.649-664.公民群体的负面情绪需要宣泄渠道,而行动是消解情绪的重要途径。若群体负面情绪没有得到有效回应,发展成为集体行动,将产生严重的社会后果(42)狄小华、冀莹: 《民意表达与政府回应机制之完善》,《政治与法律》2009年第7期,第58—64页。。在政府视角下,公民群体采取集体行动的一项必要条件是空间上的集聚,区域内密集、激烈的负面情绪表达可能预示了集体行动的风险。归属于同一区域的公民群体通常具有共同的人际关系网络或利益,若个体负面情绪没有回应好,则很可能在区域内通过沟通、人际关系等方式传播形成负面群体情绪。因此出于规避集体性行动的动机,地方政府对于具体区域内公民群体的整体负面情绪配置注意力,对来自整体负面情绪更强烈区域的诉求配置更多资源,表现更强回应性,以切实回应公民,纾解公民群体情绪。
故有H2: 政府回应性强度与公民诉求来源区域负面群体情绪强度正相关。
四、 研 究 设 计
(一) 研究对象与数据来源
本研究的研究对象是上海市12345市民服务热线平台派单至X区城市网格化综合管理中心的工单。上海乃是我国具有代表性的一线城市,其社会治理存在典型性,且在政务热线建设和整合工作中走在全国前列。X区城市网格化综合管理中心是上海市12345市民服务热线的重要组成部门之一,主要负责对接X区城市运行综合管理体系,其职责包括将辖区内各类公共管理、服务和安全问题派单至对应部门,并严格巡查、督办辖区内工单的办理,监察、检查辖区内企业与其他经济组织的安全生产情况。
本研究选取上海市X区城市网格化综合管理中心2017年11月14日至12月13日间的工单数据作为原始数据集,原始数据记录包含208 307条数据记录和352项属性。参照字段说明文件,通过人工筛选在原始352项属性中选取14项与本研究核心变量相关的属性,并删除14项属性中包含缺失值的数据记录,经数据清洗获得20 647条数据记录。
(二) 变量测量
政府回应性测量地方政府对诉求的回应程度,由数据集中的对应属性字段直接析出,根据投入资源和回应实效,将所有办结情况分为三个水平: 实际解决、解释说明、不办理退单。
自变量个体情绪特征由原始数据中问题描述字段析出,使用Python的Jieba库对原始诉求文本进行切词,并对照BosenNLP数据库情感词典,计算对应诉求文本的情绪得分,将其作为该诉求对应的情绪特征。
自变量负面群体情绪测量政府感知到的来自特定群体的负面情绪,本研究根据地理行政区划,将同一街道(或乡镇)的公民作为同一群体。归属于同一行政区域的公民在地理空间上邻近,一方面可能具有共同的情绪和利益诉求,它们通过人际关系网络在群体内传播;另一方面,地理上的邻近也使其具备参与集体行动的客观条件,地区负面情绪的聚集可能导致出现地区性群体事件。本研究的负面群体情绪变量通过来自对应街道(或乡镇)所有负面诉求的情绪得分求和计算得出。
控制变量诉求紧急程度、诉求议题类别、诉求来源、诉求受理时间均由对应数据字段析出。具体含义及测量方式如表1所示。

表1 研究核心变量
(三) 数据分析
如上所述,本研究根据公民所属行政区域划分公民群体,进而计算群体情绪特征。所使用的数据来自不同行政区域,不同行政区域的公民群体可能具有区域独特的利益诉求和情绪特征,进而导致数据呈现分层特征,即负面群体情绪变量与其他变量处于不同层次。考虑到因变量政府回应性为三分类变量,不办理退单、解释说明、实际解决是地方政府回应公民诉求的不同策略,本研究分别取政府回应性取值为0和1、0和2、1和2三组样本,比较地方政府每一对策略选择是否在公民群体上具有分层特征。首先使用分层二元逻辑斯蒂模型,运行空模型并计算组内相关系数(Intra-Class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ICC)检验组间差异显著性。若数据分层特征显著,则使用分层二元逻辑斯蒂模型检验研究假设;考虑到政府回应的实际解决、解释说明、不办理退单三个取值实际上是政府不同的行为策略选择,本研究通过两两对比,具体分析情绪特征对行为策略选择的影响,因此若数据分层特征不显著,本研究使用常规多分类逻辑斯蒂模型进行检验。
五、 数据分析结果
(一) 描述性分析
本研究选取的样本为上海市X区城市网格化综合管理中心2017年11月14日至12月13日间20 647条工单数据。在本研究选取的样本中,所有诉求均按规定及时处理。但其中实际解决诉求占14.14%,54.05%的诉求通过解释说明进行回应,另有超过31.81%的诉求由于诉求过高、诉求不合理等原因被退单。由诉求办理频数分布可见,现阶段X区政府回应公民诉求以解释说明为主,主要为公民提供咨询、解答、建议等帮助。由于公民诉求的复杂性,政府难以满足每一位公民的诉求,因此存在部分诉求未经受理,退单处理。
样本数据的诉求紧急程度、诉求来源、诉求议题类别情况如表2所示。

表2 诉求基本情况
如表2所示,本研究采用的样本中,80.59%的诉求为建设交通类。由于建设交通类包含道路建设、公共交通、绿化市容、城市规划等议题,相较其他类别更具日常性、普遍性特征,因此该类别诉求数量显著高于其他类别。其次为社会管理类,包含市场监管、社保政策等议题,也具有一定日常性。其余五类诉求所占比例相对较低,但绝对数量均符合分层逻辑回归对观测值数量的要求。至于紧急程度,绝大部分诉求并不紧急,仅极少部分诉求为紧急或非常紧急;样本诉求主要来源于市民服务热线,少数诉求来自突发事件或系统性部件。总体而言,提交至12345市民服务热线的诉求呈现出日常化、非紧急的特征,反映了市民生活中碎片化的日常需求。
本研究样本的情绪特征均值为1.56,中位数为2.02,诉求情绪得分越高表明诉求的情绪特征越积极,总体而言诉求样本中积极情绪稍强。对于极端情绪,样本中负面情绪强度最高的诉求情绪得分为-66.14,正面情绪强度最高的诉求情绪得分为51.18。正面情绪得分诉求主要包括提出表扬、友善建议、理性期望等,负面情绪得分诉求主要包括对现状不满、对行政效率的质疑等。
(二) 多分类逻辑回归分析
本研究首先使用空模型对诉求来源群体差异的显著性进行检验,以此判断政府回应性在群体层面上是否有显著差异,采用组内相关系数作为衡量诉求来源群体间差异显著性的指标。根据Heck等人对组内相关系数的讨论,0.05通常被认为是表示数据存在分层的常规阈值,(43)Ronald H. Heck, Scott Thomas, Lynn Tabata, Multilevel Modeling of Categorical Outcomes Using IBM SPSS,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2013.国内也有学者将0.138作为“高度关联强度”的阈值。(44)温福星: 《阶层线性模型的原理与应用》,北京: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9年。无论采用何种阈值,各模型的组内相关系数均远小于阈值,样本数据分层特征不明显,本研究采用多分类逻辑回归检验假设H1和H2。
对于前述三组样本,考虑到情绪特征及负面群体情绪绝对值过大,因此使用其Z分数进行回归。本研究使用多分类逻辑回归模型,分为政府回应性取值“实际解决”“解释说明”“不办理退单”两两组合的回归系数结果如表3所示。

表3 政府回应性逻辑回归结果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情绪特征对政府回应性的效应在实际解决和不办理退单以及解释说明和不办理退单组上,在99.9%的置信水平上显著;对于实际解决和解释说明组,在99%的置信水平上显著,且上述系数均大于0。表3中每对选择的参照组均为政府回应性较低的类别,系数为正表明诉求情绪特征越积极,政府对该诉求回应性越强,该结果与本研究的H1相反。
负面群体情绪对政府回应性的效应在实际解决和不办理退单组上在99.9%置信水平上显著;在解释说明和不办理退单组上,在99%置信水平上显著;但在实际解决和解释说明组上不显著且系数小于0。负向的系数表明政府回应性与诉求来源地区的负向群体情绪强度正相关。相较于不回应,政府更倾向于对诉求作出解释说明或实际解决,以表达关切、回应群体情绪,规避集体行动。本研究H2经检验成立。但对于实际解决与解释说明的回应策略选择,群体情绪并没有显著的作用。
本研究使用替换模型方法和加入控制变量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对于替换模型方法,本研究使用多项Probit模型和有序Logistic模型进行回归。对于加入控制变量方法,本研究在原多项逻辑回归模型中加入变量“诉求服务类别”,以检验模型稳健性。“诉求服务类别”变量反映了该诉求期望服务的性质,包括求助类、投诉类、意见建议类、咨询类和其他类。稳健性检验结果显示,在所有的三对组别上,诉求情绪得分均与政府回应性显著正向相关;在实际解决和不办理退单,解释说明和不办理退单两组上,负面群体情绪均与政府回应性显著负向相关,本研究关键结果通过稳健性检验。
六、 讨论与结论
(一) 结果讨论
群际情绪理论认为,个体情绪与个体行为倾向和意图相关,群体情绪与群体的行为倾向和意图相关。(45)Eliot R. Smith, “Social Identity and Social Emotions: Toward New Conceptualizations of Prejudice,”in Diane M. Mackie and David L. Hamilton, eds., Affect, Cognition and Stereotyping, Amsterdam: Elsevier, 1993, pp.297-315.在实际社会治理中,地方政府出于“避责”的逻辑,在上级政府问责压力和集体行动一票否决制下产生规避集体行动的回应行为导向。(46)章文光、刘志鹏: 《注意力视角下政策冲突中地方政府的行为逻辑——基于精准扶贫的案例分析》,《公共管理学报》2020年第17卷第4期,第152—162页。(47)张程: 《数字治理下的“风险压力-组织协同”逻辑与领导注意力分配——以A市“市长信箱”为例》,《公共行政评论》2020年第13卷第1期,第79—98页。相对于群体情绪,个体情绪与集体行动产生的关联并不密切,而是作用于个体参与集体行动的选择。(48)Eliot R. Smith, Susan Henry, “An In-group Becomes Part of the Self: Response Time Evidence,”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vol.22, no.6 (June 1996), pp.635-642.故负面的个体情绪不必然导致集体行动,也因此不会成为地方政府回应选择过程的关键影响因素。回归结果显示,个体情绪与政府回应性存在正向关联,可能的解释是个体的诉求情绪特征可能与其诉求合理性、明确性和复杂性存在关联,情绪特征积极的诉求可能具有更高的合理性和条理性,而负面情绪的诉求可能侧重于宣泄情绪,对诉求本身说明较少。在另一方面,正面情绪的诉求通常不涉及复杂纠结的利益关系,办理成本较低,议题较为单一。例如描述性分析展示的正面情绪诉求,其核心议题在于表扬一位公职人员并期待回复,实际解决该诉求只需由受表扬者对信件进行回复即可,议题单一且办理成本低。既有研究指出地方政府更倾向于对低成本、单一议题的诉求做出回应。(49)Zheng Su, Tianguang Meng, “Selective Responsiveness: Online Public Demands and Government Responsiveness in Authoritarian China,”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vol.59 (September 2016), pp.52-67.因此在个体层面,诉求情绪特征越积极,获得回应性越强。
群际情绪理论的另一个重要观点是,群体情绪与集体行动倾向密切关联。同一街道或乡镇的居民在地域上相邻近,具备形成集体行动的客观地理条件。若区域居民群体反映负面情绪普遍较强,地方政府感知到来自该群体的集体行动风险,在避责动机的驱使下会采取措施对负面群体情绪作出回应。但地方政府财政、人力、行政资源有限,(50)陈家建: 《项目制与基层政府动员——对社会管理项目化运作的社会学考察》,《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2期,第64—79页。诉求办理受到资源制约。且部分诉求本身存在不合法或不合理情况,地方政府对公民单方提出的诉求难以做到有求必应。因此地方政府将根据诉求实际情况采取实际解决或解释说明的策略进行回应,侧重于通过“做出回应”的行为方式对公民诉求表达关切,回应公民情绪。在回归结果中表现为群体情绪对政府回应的效应在“实际解决和不办理退单”组以及“解释说明和不办理退单”组上显著,但在“实际解决和解释说明”组上不显著。在政府视角下,采取实际解决和解释说明策略回应公民诉求均为对公民情绪的有效回应,是与公民进行沟通、纾解情绪的有效方式。
(二) 研究局限及展望
第一,对于因变量政府回应性的内涵有待更深入具体的探讨。政府回应过程存在多种方式,负责程度也存在差异。诉求办理中的政民互动内涵并非仅包含实际解决、解释说明、不办理退单这三种策略,也包括政府对公民回应的负责性、及时性以及政府对公民诉求以外的发展利益的关切。第二,对于群体情绪的测量和计算精度较低,本研究认为处于相近地理区域的公民,其联系更加密切,更易通过传染、交流评价、共同认知、共同利益等方式形成群体情绪,因而本研究按地理位置区域划分公民群体、计算群体情绪。然而在群体情绪形成的过程中,具有相似经历或共同利益的个体可能在同一议题、同一事件上形成共同的情绪并采取行动。个体情绪的极端表达,也可能引发诸如“借机泄愤”式的、非相关性的群体情绪,这一类群体情绪是部分集体性行动的诱发因素之一,但并非本研究关注的重点。第三,结构化数据中析出信息有限,数据转录导致对集体行动的分析存在困难。一方面,市民服务热线数据的诉求文本经接线员转录得到,保留了大部分的原始情感信息,部分敏感信息被隐去,文本中集体行动相关信息反映较少,限制了对公民群体集体行动倾向的进一步讨论。另一方面,由于数据可得性原因,数据中缺失值较多,部分控制变量有待进一步挖掘。例如本研究实证检验发现,地方政府对不同受理时间诉求的回应性存在显著差异,但造成该差异的原因在结构化数据包含的字段中难以有效体现。且数据样本在时间跨度上仅为一个月,主要集中在冬季,诉求内容可能因时间跨度单薄存在季节性特征。
结合上述讨论,未来的研究可以关注以下几个方向: 第一,关注政府回应性的内涵,从负责性、实效性、公民满意度等维度综合讨论政府回应性及其动力机制。第二,关注群体情绪的外延,在定义上,对基于共同经历和利益的群体情绪、基于地域和社会关系的群体情绪、“借机泄愤”式的非相关性群体情绪进行更深入的探讨;在操作上,可以更加精准地划分群体、测量群体情绪,并讨论其与集体性行动、政府回应性等变量的关系。第三,在数据来源上,可以通过爬取市民服务热线网站上的市民投诉信件进行研究,并结合对市民服务热线工作人员开展访谈等方式收集更丰富的数据,检验基层行政人员在回应过程中的选择性及其动机,进一步讨论政府回应这一过程中微观个体的偏好及能动性。
(三) 结论与启示
本研究基于政府回应性研究中忽略群体情绪这一研究空间,在讨论中区分公民个体诉求的情绪特征及群体的情绪特征,进行实证分析,得到两条结论: 第一,公民诉求情绪特征越积极,政府回应性越强;第二,政府回应性与公民诉求来源区域负面群体情绪强度高度正相关。研究结论的实践启示在于: 第一,新时代城市治理的复杂性对政府回应能力提出新的要求,地方政府应当切实提高回应能力和水平,在解释说明的基础上实际配置注意力与资源,力求实际解决更多合理合法的公民诉求,提高政府回应性。既有研究指出,回应时长显著负向影响公众参与,实际解决率则对公众参与无显著影响(51)常多粉、郑伟海: 《网络问政时代政府回应如何驱动公众参与——基于领导留言板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社会发展研究》2023年第10卷第2期,第139—159页。,这一结论与本研究一致,因而通过解释说明等方式及时对公民诉求做出回应是做好政府回应工作的重要策略之一。在回应好议题单一、办理成本较低的合理诉求以外,也应根据实际情况酌情办理相对不紧急或办理成本相对较高的诉求,重视不办理退单诉求的解释说明工作。对于不合理、不合法的诉求应当根据实情说明不予办理的原因,并切实告知投诉人,避免极端个体情绪发酵引发极端行为。第二,在政民互动平台建设过程中,应当更加注重前端对于情绪、诉求等特征的预处理,对具有普遍性的诉求内容和较大规模的群体情绪,需要在前端及时进行分类汇总,并在后续的响应工作流程中加以关注。既有研究结合政府对新冠疫情防控的回应策略开展实证研究,指出政府在回应公民诉求工作中,既要丰富亲民话语体系,精准、清晰传递信息缓解负面情绪;也要深入分析网络舆情,对公民情绪、关注议题、话题焦点提前跟进收集、分析汇总(52)刘冰、张航: 《基于民众需求与情感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政府回应策略研究》,《情报科学》网络首发,2023年6月16日,https://kns.cnki.net/kcms2/detail/22.1264.g2.20230615.1008.002.html,2023年8月2日。。在市民信箱等线上反馈渠道中,结合自然语言处理等技术手段,分解识别诉求内容和情绪特征,将公民情绪的回应工作前移,在市民服务热线等传统反馈渠道中,加强接线员培训,做好接线记录阶段的识别分类工作,对具有相似情绪特征和诉求内容的公民意见,可以集中进行办理回复,形成全流程高效回应机制,进一步提高政府回应工作实效。第三,地方政府在关注负面群体情绪、规避集体行动风险的同时,也应注重多途径纾解群体情绪。有学者将现行的全量、全部门、全层级回应模式称为政府日常治理的“全回应”模式,即通过及时对公民诉求“近乎全量”的回应,及时疏导群体情绪(53)张楠迪扬、郑旭扬、赵乾翔: 《政府回应性: 作为日常治理的“全回应”模式——基于LDA主题建模的地方政务服务“接诉即办”实证分析》,《中国行政管理》2023年第3期,第68—78页。。对存在集中负面情绪的区域或群体,应当通过细致解释说明、实际回应诉求、表达政府关切、提供情绪疏导等多种途径回应情绪,同时也要切实反思、改进工作流程中的不足,避免将解释说明作为回应公民情绪的“万金油”,避免政府回应“治标不治本”的现象,提高政府回应能力,建设以人民为中心的回应型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