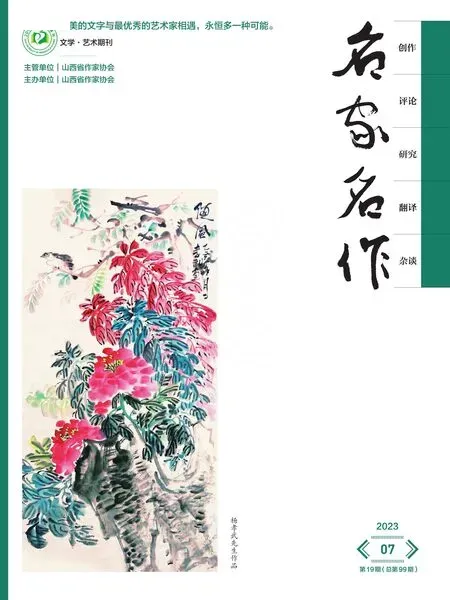“迷失”与“复位”:托马斯·品钦小说《梅森和迪克逊》中的价值理性管窥
张 艳
一、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
关于科学技术活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关于科技统计国际标准化的建议案》中作了明确阐述:“科学技术活动是指所有与各科学技术领域,即自然科学、工程和技术、医学、农业科学、社会科学及人文科学中科技知识的产生、发展、传播和应用密切相关的系统的活动。”(国家科委综合计划司, 1990: 6)由此可见,科技活动既包括自然科学活动,也包括社会科学及人文科学活动,是融知识、技术与生产于一体的一种人类实践行为。针对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人类实践行为,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提出“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加以区分。人类在改造未知世界的过程中运用科学技术手段以期达到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目标,这种实践行为反映在思维方式上就是工具理性思维,反过来,“工具理性思维又占据、主导着人的认知行为与方式”(周家荣,2007:36),形成工具理性行为。相对于强调手段和目的的工具理性,价值理性是“通过有意识地对一个特定的行为……无条件的固有价值的纯粹信仰”(韦伯,1997:56)。也就是说,价值理性更注重行为本身的价值,表达人在社会实践中所持有的价值判断和伦理诉求。价值理性以“人”为本,尊重人的需要,守护人的精神成长,关注人生意义与生命价值的实现。
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相互依存、缺一不可。片面追求或无限夸大任何一方都会造成一定程度上对人性的摧残和对社会发展的阻碍。从古希腊到中世纪再到文艺复兴时期,在泛灵论、有机论及宗教神学思想的影响下,人们大都相信自然具有一种内在的神秘力量,充满了精神和智慧,而技术只是人类改变生存条件的工具。所以,在这一时期,“技术并不被认为是独立自主的,受到社会体制或宗教体制的管束”(波兹曼,2007:13)。进入近现代,伴随着工业化大生产技术的普及,现代科学技术不再仅仅是帮助人类摆脱蒙昧、进入文明时代的简单工具和实践手段,而被赋予了征服自然、控制自然和为人类增添财富的新使命,也因此拥有了至高无上的地位。技术的“无所不能”使人们对技术的依赖程度逐渐加深,科学技术开始偏离人文的轨道,走向“唯科学主义”和“技术至上主义”,失去了应有的人性温度。离开了工具理性的价值理性只是虚幻的“空中楼阁”,但离开了价值理性的工具理性势必引发技术异化的恶果。
二、价值理性“迷失”的表现及其后果
《梅森和迪克逊》(Mason & Dixon, 1997)是美国小说家托马斯·品钦(Thomas Pynchon,1937—)创作的第五部长篇小说,出版于1997 年,讲述了英国天文学家、工程师查尔斯·梅森(Charles Mason)和他的助手、勘测员杰里迈亚·迪克逊(Jeremiah Dixon)于1763 年奉英国皇家天文学会之命前往美洲大陆执行勘察宾夕法尼亚州和马里兰州地界,并测定梅森-迪克逊线的传奇经历。《梅森与迪克逊》以真实的历史人物和事件为题材,反映了18 世纪美国独立战争前北美殖民地时期的社会面貌。18 世纪正是西方以理性主义和高涨的科学兴趣而闻名的一个世纪,天文观测与勘察测量技术体现了理性时代的智慧与进步,小说的内容就是在这样的时代大背景下展开的。梅森-迪克逊线的勘察与划定构成了小说情节的主线,成为“美国文化区域的标志和美国奴隶制的历史记忆”(王建平,2015:300),因为后来人们发现,在殖民地时期,它将奴隶殖民地和自由劳动的殖民地分开来;在19 世纪上半叶,这条线又将自由州和奴隶州隔离开来。小说中的梅森-迪克逊线不只是一条地理分界线,还被赋予一定的政治和伦理寓意,成为品钦表达技术伦理批判话语的一个重要隐喻。
《梅森和迪克逊》不仅仅是一部“历史小说”,因为“它不仅记录了已经发生的事情,还生动地再现了可能发生的事情”(Hinds,2005:4)。在小说中,品钦将历史事实与文学想象相融合,同时他还展示了一个现实以外的想象中的18 世纪。这个想象中的18 世纪与20 世纪后现代主义的印象非常相似:会说话的狗、法国厨师爱上机械鸭子的情节显得荒诞不经,人物间以戏谑式的油腔滑调进行互动,“对地球的漠视”与“对偏执的关注”(Hinds,2005:5)引发读者对20 世纪人类生存状况的共鸣。形形色色、性格迥异的小说人物悉数登场:除了头顶“理性光环”的梅森与迪克逊,权力加身的宗教团体、党派贵族,还有身受鞭挞的黑人、无助的土著印第安人、街头卖艺的女人、渴望重建家园的民众、逃避耶稣教会追捕的中国地卜者和乔装打扮成樵夫的密探等。透过浮生百态众生相,品钦引导读者“重新思考和定义殖民地时期美国和当代美国的理性思想和理性话语”(McEntee,2003:186),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关系三个层面对科技理性进行价值反思,剖析价值理性的“迷失”现象,“预见”工具理性极端发展的当代后果——人性的异化和道德的沦丧。
(一)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导致和谐共生关系的破裂
自然科学在实践中进入人的生活,它的发展充分表现了人与自然之间相互依存、休戚相关的联动关系。但是,伴随着自然科学在实践中成为人实现社会目标的有力工具,并为人类创造了大量物质财富,技术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发生了变化,科学技术开始成为人们赞美和崇尚的对象,而不再只是为人服务的工具。在利润、战争等因素的驱动下,人不再以自然界为精神食粮,而是转头滥用科学技术对自然界进行无情的资源掠夺。此时,科学技术的价值理性已经“迷失”,人与自然的关系日渐疏远,发生异化,人与自然之间和谐共生的关系就此破裂。
在《梅森和迪克逊》中,天文学家梅森和勘测员迪克逊运用天文学、地质勘探学知识和精密仪器设备对新大陆进行测量并勘定分界线。谈到划定疆界的勘测任务,迪克逊引用书中读过的一句话解释,“直线是人类在这个星球上存在的证明”(Pynchon,1997:219)。在他看来,直线代表“科学”和“理性”,体现了人类征服自然、驯化自然的能力。这呼应了18 世纪以后主张“以理性取代神性,以科学取代迷信,以线性取代轮回,以进步破除天定”的线性历史观(李帆, 2015:107)。梅森和迪克逊带领勘探队从欧洲、新大陆的东海岸到“荒野”的西部,横穿美洲大陆,相信理性和文明之光会指引人们驱散西部的“蒙昧”和“荒蛮”。但是随着勘测的推进,梅森和迪克逊发现勘察与测量的理性化和工具化直接导致地理和自然景观被人为野蛮地分割和宰制,引发新的不确定性和灾难性后果。
小说中有一条“武士之道”,呈南北走向,是印第安人祖祖辈辈按照天然的地标,顺应着水流山势踩出来的山间通道,来自不同地方的人们通过它增进彼此的交往和沟通。在这种状态下,天、地与人亲近交融,以自然有序的方式循环运转,形成一个和谐的整体。然而,东西走向的梅森-迪克逊分界线通过技术手段,人为强行阻断了本来通畅的“武士之道”,截断了人们世代交流和沟通的通道,也打破了人与自然之间业已形成的平等、有序的生态循环。通晓风水的华裔张船长评价梅森和迪克逊的勘测工作是“在龙的身体上砍上一刀”,是“对自然法则的公然蔑视”。在他看来,世界上的分界线都应当顺应大自然的天然界定,就像海岸线、山峦和河岸一样,它们无一不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历经千年才得以形成,“龙的精气无处不在”,是大自然内在“龙脉”的外化表现,这也正是地图历史学家约翰·亨德森(John Henderson)所描述的“坐落的位置要顺应融聚于山川溪流之间的能量(‘气’)的流动”(Henderson,1987:216)。但是,如果非要人为设置一条分界线横亘阻隔,大自然的“气脉”势必断裂,从而导致不堪设想的严重后果。品钦以间接的方式预言了南北战争,并暗示了“梅森-迪克森线在下一个世纪的道德经济中可能变成的样子”(Cowart,1999:349)。的确,在人类征服自然的过程中,技术文明的背后隐藏着人类空前膨胀的贪婪和欲望,人类变得冷漠与一意孤行。科学与理性不再仅仅是能够赋予人们力量和自由的技术工具,已成为打破人与自然和谐秩序、破坏人类生存家园的帮凶。梅森-迪克逊线代表的“科学”与“理性”并没有给予自然足够的尊重,而是把自然视为实现自我目的的手段。片面追求物质成果、割裂科学与责任伦理关系的人类文明进步往往是以自然生态的破坏为代价,人类因此丧失了对技术伦理价值的合理判断,人与自然的亲密关系也随着工具理性的恶性膨胀而渐行渐远,最终迷失在贪婪与无知之中。
(二)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异化导致社会的对抗
技术与人的发展具有内在的统一性,二者相互渗透、相互依赖、相互促进。技术进步创造出来的物质世界本应该是一个富有精神内涵和人文内涵的人化世界,因为技术进步本身渗透着人文情怀和人文精神。但当人与人之间彼此的价值变成彼此拥有物品的价值,而不再是作为人的生产劳动的价值时,人与人之间本应包容、平等的关系开始解体并发生异化,彼此间的冷淡、敌对关系得以确立,以“相互掠夺”为基础的人际对抗关系使社会陷入无序、混乱中。
在《梅森和迪克逊》中,梅森和迪克逊奉命执行勘察测量任务的初衷是调停宾西家族和巴尔的摩家族之间的地界纠纷,但是当勘测队员和工人在宾夕法尼亚州和马里兰州之间崎岖不平的土地上开辟和划定出一条真实的边界线时,梅森和迪克逊却发现越来越多的边界纠纷和诉讼案正沿着这条边界线产生,由此,他俩也开始对划定疆界的意义和合理性产生了怀疑。围绕边界线的诉讼案件不断增加,这其中就包括因测量员没能及时预测月食而威胁提出诉讼的罗迪·贝克(Roodie Beck),还有陷入困境的雷辛格女士(Frau Redzinger),她一直向宾夕法尼亚州纳税,但在新的边界划定下,她的财产竟被归入马里兰州。由此看来,旨在利用科学技术解决地界纠纷的目标不但没有真正达成,反而制造出了新的人际冲突和社会混乱。
美洲大陆本是一片充满生机的富饶之地,资源丰富,美洲印第安人世代居住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与自然和谐相处。但是随着16 世纪早期欧洲殖民主义者的到来,美洲大陆原有的平静被殖民主义者的入侵打破了,他们为了掠夺资源、拓展疆域,不断向内陆扩张,砍伐森林,赶走部落赖以为生的大型野生动物,并时常毁坏当地印第安人种植的庄稼,对当地的土著印第安人实施了武力镇压。在小说《梅森和迪克逊》中,梅森和迪克逊目睹了“暴君”奴役下的土著印第安人的苦难生活。他们曾前往印第安人居住的兰卡斯特镇,在那里曾经多次发生白人与土著人之间的冲突,手无寸铁的无辜百姓遭到屠杀和掠夺。面对西部大片“人迹罕至”且“尚未被纳入帝国版图的土地”,“欧洲文明人”要做的就是占有,而内心充满恐惧和愤怒的土著印第安人却不知道如何才能抵挡住梅森-迪克逊线化身的“怪兽”。“欧洲文明人”打着“科学”和“理性”旗号,掠夺并占有了土著印第安人原本安居乐业的家园,将其变为征服者的乐园。在这里,科学知识与技术是为强权者服务的工具,大英帝国无耻且露骨的剥削本质大白于天下。
(三)人与自身关系的异化,导致人的主体地位丧失
马克思曾指出,“科学绝不是一种自私自利的享乐。有幸能够致力于科学研究的人,首先应该拿自己的学识为人类服务”(马克思、恩格斯, 1979:128),所以技术的价值要通过人来实现,一切技术活动的目的最终指向的都是现实的人。随着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社会不断壮大,但人类的个体能力与价值却在强大的社会力量面前不断被削弱。特别是当人过度追求技术的“工具性”和“力量性”,忽略人作为个体的发展与价值需求时,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开始出现某种失衡,其表现就是工具理性的片面凸显与价值理性的日渐式微。被赋予明显功利主义色彩的技术呈现出单一化、片面化的特征。人与自身关系的异化直接导致人的主体地位的丧失,表现为人越来越不自由、人格趋于分裂、本能受到压抑、生活失去目标与意义,最终沦为马尔库塞所说的失去创造性和批判精神的“单向度的人”。
在小说中,梅森-迪克逊线对土地的“理性”分割和划定加剧了“物的世界”对“人的世界”的包裹与入侵,生活在其附近的百姓无路可退,开始过起“被动”的、身不由己的生活:宁静、温馨的家庭生活被无情打破,人口遭分割,家园被破坏。梅森-迪克逊线横穿了普利斯夫妇的房子,房子被分成两半,一半在宾夕法尼亚州,而另一半则属于马里兰州,普利斯太太因此跟丈夫调侃说,既然他们是在宾夕法尼亚州结婚的,那么他们的结婚证书在马里兰州就失效了,由此她也就无须履行妻子的义务和服从丈夫的“发号施令”。这个情节看似滑稽可笑,令人哭笑不得,但恰恰是普利斯太太这样一番荒诞不经的玩笑话揭露了工具理性权威对价值理性的漠视与放弃,以非人道的暴力控制和剥夺了人类追求公平正义和自由发展的权利。梅森-迪克逊线压根没把民众的生活福祉放在眼里,其分割了土地,剥夺了人的归属感,成为象征毁灭性力量的“邪恶的通道”。
小说主人公之一梅森是皇家天文学会的天文学家,作为美洲殖民地地界勘察划定任务的重要执行人,他与勘测员迪克逊一起勘测地界、绘制地图,工作涉及数学、天文学、勘探学及测绘学等方面的原理与知识。梅森对科学技术表现出执着的追求和崇拜,他与迪克逊不辞辛劳地先后完成了金星凌日的观测和美洲殖民地分界线的勘测任务,甚至不惜以牺牲自己的家庭为代价。梅森一直自诩为“科学家”,对科学知识的痴迷让他身上表现出的“理性”远远超出了“人性”。事实上,就是在这样一位堪称“理性”典范的科学家身上出现了精神机能障碍的症状,包括精神忧郁、行为怪异、情感障碍等。在小说中,迪克逊把梅森称为“浮士德”不无道理。歌德笔下的浮士德满腹经纶、饱读诗书,代表着近代社会科学发展给人们带来的理性思维追求,但学术上的成就并不能使他收获内心的满足,他长期对生活感到迷茫和不满,不知道何去何从。像浮士德一样,梅森饱受情绪抑郁的折磨,他的痛苦恰恰来自理性追求和感性需求之间的冲突,一面是对科学知识的痴迷,一面是情感的羁绊,失去妻子丽贝卡的过度悲伤常常让他陷入幻觉之中不能自拔。梅森一直挣扎在孤独、焦虑、迷惘和恐惧感中,始终无力以他的理性逻辑推理了解亡妻的讯息,看来科学技术并非万能,当工具理性强行超越自己的应用领域时将无可避免地遭遇失败。面对一个迷失本性的自己和一个意义失落的世界,梅森唯有寄希望于通过幻觉和疯狂弥补理性无法触及的人性的本质。评论家杰森·麦肯特(Jason McEntee)指出,梅森与迪克逊对现实的质疑表明,他们已经与理性发生了冲突,与此次勘探任务的目的发生了冲突,而“这些冲突将导致他们在理性和对理性的厌恶之间游走”(McEntee,2003:190)。
三、呼唤人文关怀回归,“复位”价值理性
在《梅森和迪克逊》中,围绕着数学、物理学、天文学、地理学、地质勘探学等知识领域,出现了大量繁杂高深的科学概念与原理,品钦描绘出一个被技术浸染的世界,在这里,人们的生活、生产和思维变得与技术密不可分。《梅森和迪克逊》直接将历史坐标定位于美国独立战争前欧洲人在美洲大陆进行科学勘测的18 世纪70 年代,此时的科学技术远未形成20 世纪科学技术垄断与恶性膨胀的态势。真实史实的重现让这部小说初看起来像是一部记录18 世纪科技理性“开疆扩土”的历史小说。美国小说家科拉格桑·博伊尔(Coraghessan Boyle)指出:“如果传统历史小说试图复制一种生活方式、语言和服装,后现代主义版本只寻求成为这样一种版本。”(Boyle,1997:9)历史小说《梅森与迪克森》也不例外,其具有鲜明的“自我指涉”的特征。通过对一本正经的正史的戏仿,品钦将读者置身于小说的历史细节和宏大叙事中,探讨科技与人类之间相爱相杀的依存关系,同时借助文学想象和虚构,预见现代社会工具理性恶性膨胀、价值理性沦落的严重后果,提前揭开生态环境危机与科技异化的面纱,危机四伏的未来跃然纸上。
品钦化用科技知识的行文表达他对现代科学技术负载的伦理价值的思考:一方面,科学技术进步为人们带来最新的知识成果和实践手段,“为实现人类自由、反思生命意义、创造美好生活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陈多闻,2022:59);另一方面,在追逐功利与霸权的过程中,“人在技术自主性面前丧失了自主性”(Ellul,1980:256),原本作为人的劳动延伸和本质表达的科学技术在现实发展中摇身变成对抗人的异己力量。对于工具理性膨胀与扩张可能给人类生存和发展带来的威胁和破坏,品钦深感担忧,但是他并没有因此对未来报以悲观失望的态度,更没有选择逃避或者放弃科学技术,因为“危险的不是技术,而是人将其置于超出个体控制,甚至可能超出人类控制的统治地位,最终造成人类失去对自我存在的正确理解”(Gorner,2002:31-32)。针对科技异化现象,品钦强调人的价值与尊严,表达了对技术社会中人的处境的观照,呼唤对人的终极价值和生命意义的追寻。
(一)以诗意地栖居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解
“栖居,即置身在平静中,意味着在自由和保护中持守在平静里,这种自由让一切守身在其本性之中,它贯透整个栖居领域。”(海德格尔,1990:149) 通过海德格尔的话我们可以看出,栖居的本质显现在栖居者对家园的寻觅和对自由的追问中。那么人之栖居并非简单的物质层面的居住,而更多的是从精神层面上显现人本身的存在。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自然性”成为人的第一属性。来自自然界的人类依靠自然完成了自身进化并获取了生存所必需的栖息地与资源。人从属于自然,大地是家园,自然才是人类栖居之地。即使在现代技术的促逼之下,人类也需要按照其本真的状态存在,摆脱技术的任意摆置,在实践活动中尊重自然、保护自然,并在彼此之间形成不可分割的物质变换关系和持续的精神互动关系,最终回归自然性倡导的世界。
在《梅森和迪克逊》中,美洲被描绘成一块充满生机和复杂性的处女地,在这里“没有原来的界线”“没有篱笆”“没有街道”,就是“一个多边的世界”。在特拉华山脊地区,“有着不为人知的世界”,“密密麻麻的青纱帐”中有着各式各样的“小路”和“空地”,人走进去后几分钟就会“迷失”其中。显然,面对自然天成的山脊地形和美洲大陆的复杂性,梅森和迪克逊想要以一条理性的“直线”来界定地界的确是一项无法完成的任务。在这里一片喧嚣,充满人间烟火气,置身大地、天空、山峦、树木的包围之中,人恢复了活力,克服了人性分裂,成为自己的主人。“真相也在想象力支配的地方悄然而至——尤其是多视角的想象力。”(Cowart,1999:358)品钦通过“孕育着生命的矮树林”发出召唤,当人性重新回归到“和谐”与“静穆”的自然境界,恢复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有效沟通时,“人的本质力量”才能得以重构。
(二)以求真向善的价值取向对抗技术异化
在《梅森与迪克逊》中,品钦一如既往地以滑稽夸张的创作手法塑造人物形象,其中既有像梅森、迪克逊、富兰克林、华盛顿等真实的历史人物,也有以故事讲述者威克斯·切里科克(Wicks Cherrycoke)为代表的一系列虚构人物。穿梭于历史与虚构之间,透过文字的丛林,品钦窥见工具理性膨胀与扩张引发的严重后果以及其代理人的残忍和野蛮,同时也目睹了观测金星凌日或荒野勘探等看似无害的科学技术探索行为对人类自然生存状态的威胁。书中有这样一个情节,当奴隶主残忍地殴打黑人奴隶时,迪克逊走上前抓住监工的鞭子进行制止,并将其狠狠地教训了一顿。后来,迪克逊保留了这把鞭子作为战利品,并把它带回了科克菲尔德,在那里它一直被视为“家庭珍宝”。其实,梅森与迪克逊都知道一时的善意之举虽出自善心却未必有益,从监工手里夺过的那把鞭子并不能帮助奴隶获得真正的自由。迷茫沮丧之际,迪克逊想知道:“一个有良知的人该怎么办?”那么什么是良知?黑格尔称“良知”是“一种道德天赋”(黑格尔,2013:403),它“赢得的是充实的事情本身”(黑格尔,2013:394)。那也就是说,良知并非一种纯粹理性的道德思辨,而是富有实在内涵且与现实行动相统一的“一种真正意义上的道德行动”(黑格尔,2013:391)。当人对焦伦理,思考、关心并重视人的命运、情感、生存状态时,人文关怀的光芒便会从心灵与良知的交汇处迸发。
人文关怀表达了人类对生存意义和生命价值的关注与追求,是人文主义和人文精神的具体体现,也是价值理性的现实诉求。人文主义是一种以人为中心和准则的“思想态度”(《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编辑部,1986:761),强调人的价值、尊严与自由,倡导人文关怀。西方人文主义思想的发展先后经历了古希腊先哲重学术(自然哲学、伦理学)、轻技术的源起阶段;文艺复兴运动以人为中心而不是以神为中心的人文主义思想复兴时期;启蒙运动提倡科学、自由和平等,呼唤用理性的阳光驱走现世黑暗的人文主义思想的成熟阶段;再到近现代伴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开始反思技术工具理性霸权的危害,继续宣传自由和平等思想的进一步发展的阶段。不难发现,在西方人文主义的历史演变过程中,科学技术始终伴随左右,虽然两者的关系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发生着微妙的变化,但彼此依存、互为补充。
“哪里有危险,哪里便有救渡。”(海德格尔,1990:107)当梅森和迪克逊目睹欧洲殖民者打着科学勘探的旗号在南非和美洲大陆残忍屠杀黑奴和土著人,并无耻侵占印第安人的家园时,虽然他们在“理智”的支配下不得不屈从殖民命令,但他们的内心却一直备受煎熬,他们对上级表现出的极度冷漠而感到沮丧,并开始对科学勘探的“目的”产生怀疑,这种不信任表现出他们对工具理性和西方价值观的质疑。在良知和道德的驱动下,他们承认“印第安人愿望的正义”,认为梅森-迪克逊线正如张船长描述的那样,是一条“邪恶的通道”。旅途中,他们倾听他者并对观察到的情况进行反思,迪克逊使用“怪兽”一词来描述分界线,表达了印第安人对入侵者的恐惧和愤怒。因此,对迪克逊来说,欧洲白人正是他们“自己最糟糕的梦境中的野蛮人”,而印第安人才是美洲大陆这片广沃土地真正的“所有者”。虽然迪克逊与梅森同为勘探梅森-迪克逊线的执行者,但他对友人的关心和对土著人和黑奴的同情赋予他一种求真向善的品质,与殖民者冷漠和残酷的侵略和杀戮行为形成了鲜明对比。求真向善的价值取向正是科技活动价值理性在审美和道德维度的体现,成为对抗工具理性异化的利器,为实现人类自由、感悟生命意义、追求美好生活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可以说这一宣言不仅适用于美国独立战争,还昭示了人们未来超越工具理性的霸权定位,以对自然的敬畏,对真善美的向往“复位”价值理性。
在《梅森和迪克逊》中,品钦以当代视角,穿越回18 世纪美国独立战争前的北美殖民地时期,“把过去的生活当作现在的前历史来书写”(Lukacs,1963:53),以发展的眼光看待现代科学技术的过往、现状与未来,从价值理性的视角考量科学技术实践与人类、自然及社会的伦理关系和价值意义,直击现代社会技术理性霸权的种种危害,从而追问现代技术的本质。在小说中,品钦对历史的重建与其说是为了揭示真相,不如说是为了激活赋予科技活动的审美与道德价值因素,找到抵抗西方技术异化的驱动力,实现技术在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上的真正统一,在处理好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及人与自身关系的基础上真正造福于人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