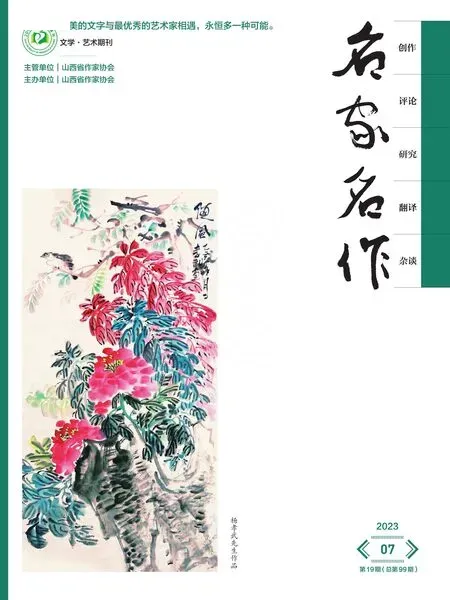《汤姆叔叔的小屋》和《宠儿》中女性权力创造的房子
顾晓璇
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和《宠儿》在创作背景上有许多相似之处:《宠儿》的主要情节发生在比切一家居住的辛辛那提附近,斯托在这里也获得了她的写作材料。此外,《汤姆叔叔的小屋》和《宠儿》的最初目的都是为了回应《逃奴法案》,两位作者都回忆并利用奴隶历史来创作他们的叙事。因此,将这两部小说联系起来研究是合情合理、有迹可循的。哲学家兼美学家阿瑟·丹托指出,“房子对我们来说是统治权、所有权、掌控和力量的象征。”他还指出,“房子”一词的古英语词根是“hus”,“与huden 同源,用来隐藏、庇护、遮盖”,展示了“我们作为居民的自我形象中脆弱、受威胁、被暴露的一面”。因此,揭示女性奴隶或前女性奴隶如何创造自己的“房子”,并对他人及其周围环境行使女性权力,是一个有意义的话题。
一、《汤姆叔叔的小屋》中女性权力创造的房子
(一)凯西创造的房子
女性在房子里的“工作”通常是无偿的,而且她们的“房子”总是被男人构建和所有。可以说,尽管房子是一个女性空间,但它总有被男性侵入和腐蚀的危险。因此,斯托希望通过女性现已拥有的权力来提高女性的地位,尤其是母亲的地位,并建立一个“家庭国家”(family state)(Stowe 和Beecher,1979:13)。许多学者讨论了《汤姆叔叔的小屋》中“房子”和家庭的影响,他们认为其是赋予女性权力从而改变他人和世界的有效方法。正如让·耶林(Jean F. Yellin)所说的奴隶制和女性政治无能为力的问题最终是不可分割的,《汤姆叔叔的小屋》通过描写女性角色创造的“房子”和房子里的琐事,有意识地将家庭和政治联系起来,深刻揭示了美国崇尚自由、民主、平等的民族政治理想与女性和奴隶的个体价值之间的矛盾,也展示了她们获得主体性、改变世界的力量和意愿。
《汤姆叔叔的小屋》中描述了很多次“房子”,小说第三十二章的题词中介绍了西蒙·莱格里的房子:“地上黑暗之处,都满了强暴的居所。”(Stowe,1962:350)对这间房子结构和布局的叙述都反映了房主从物质到精神的彻底堕落,但小说中的女奴凯西在被授权将阁楼改造成她的“房子”后,改变了这所房子的一部分,可以说她创造了一个领域,并从她男性化的、物质主义的主人那里获得了权力。
此外,斯托在小说中还通过建立一个乌托邦式的贵格会中心,表达了她对改革社区、社会甚至世界的期望:那里的男人是边缘人物,他们“在角落里,进行着反父权的剃须活动”。通过这个中心,女性将能够获得并行使她们的权力,让自己、周围的人和周围的环境做出改变。
(二)斯托倡导的女性权力
事实上,在父权社会的影响和思想引导下,女性的服从和被动往往隐含着一种颠覆的力量。《汤姆叔叔的小屋》里的许多白人清楚地了解奴隶制的罪恶,但他们都自觉或不自觉地遵守奴隶制的原则。相反,是没有政治、财产和话语权的女性站出来表达强烈抗议:小说的第九章中,伯德夫人强烈批评了禁止人们向有色人种提供肉类和饮料的“可耻、邪恶、可憎”的法律,并表达了她抗议的决心。
斯托不仅称赞女性是男性的道德上级和榜样,而且相信女性拥有改变家庭、社会制度和世界的力量。因此,她拒绝使用暴力来消除邪恶,坚持认为女性的影响可以取得更好的效果。斯托将大量的篇幅放在了描述母爱上,她认为这是所有形式的女性力量中最强大、最神奇的力量:凯西击败格里高利的智慧来自她对艾米莉的母爱,而奥菲利亚改变托普西的关键也是用母爱对待彼此。简·汤普金斯(Jane Tompkins)指出,斯托并不反对通过法律或其他途径废除奴隶制,但她认为仅靠这些措施可能是无用的,因为“产生奴隶制的道德条件仍然有效”。因此,只有从根本上改变道德条件,奴隶制才能被根除。
(三)“房子”和斯托理想的局限性
然而,凯西的房子存在于一个白人拥有的房子的角落里,在白人的控制之下。这种理想社会只是存在于普遍奴隶制的一个小角落,为奴隶提供了一个看似安全却只是暂时的庇护所,并不能给奴隶带来真正的自由,让他们获得主体性。
事实上,奴隶制和基督教的双重男性统治与同谋,产生了压倒性的力量,尤其体现在女性角色及其特征上:一名杀害孩子的妇女不得不被描述为有点疯狂,因为她的行为违反了“正常”的社会道德;当凯西能够与家人团聚时,她的人物形象必须被削弱,才能“立即,用她的整个灵魂,受到每一个好的影响,成为一个虔诚而温柔的基督徒”(Stowe,1962:443)。
此外,这种父权权力的束缚也表现在作者本人和她笔下的黑人人物身上。她在小说中塑造的纯正的黑人角色往往是刻板的,就像汤姆叔叔这样忠诚顺从的形象,或像山姆这样傲慢的小丑形象。此外,小说的结局似乎表明了斯托对殖民计划的认可,即将黑人迁移到非洲。究其原因是这些黑人不符合斯托的“浪漫种族主义”思想,即认为黑人因为种族而“仁爱、宽厚、大量”,就像女性因为性别一样。斯托似乎只是想结束奴隶制,而不是结束种族不平等,更不是结束一个多种族的美国社会。她还打算安排主人公向非洲的黑人传播基督福音。总的来说,斯托的理想仍然依赖于种族和性别差异,并持续了白人奴隶主作为一个阶级凌驾于奴隶之上的现实。
二、《宠儿》中的女性权力创造的房子
(一)宝贝·萨格斯创造的房子
在《宠儿》中,宝贝·萨格斯将博德温赠送的废弃房屋打造成“124 号”。在她的创造和奉献下,124 号不仅是一个居所,还变成了一个神圣的“中途站”,它是一个永恒的公共中心。萨格斯创造了一个公共领域,它不仅是一个远离大社会的庇护所,更是民众在社会面前的公共权力表达:“……124 号曾是一座欢快热闹的房子……炉子上不是一个而是两个锅在炖;灯整夜都在烧。陌生人在那里休息,孩子们在那里试鞋。人们在那里留言,因为需要留言的人一定会在不久的某一天来到这里。”(Morrison,1987:86-87)尽管外界对她提出了批评,但是萨格斯还是以她坚强的意志完成了改造:“她说她不在乎人们怎么说她把一栋两层楼的房子修得像只能做饭的小屋一样。……她说,她才不会理他们呢。”(Morrison,1987:207)萨格斯成功地创造了自己的领域,并将她的权力运用到其他人和社区上。
在萨格斯去世后,124 号的家庭成员试图在不与外部社区连接的情况下建造一栋自给自足的房子。但他们失败了,因为124 号闹鬼了,这表明他们被困在奴隶制和父权制度的记忆中。只有在丹佛走出家门,与社区重新联系,塞丝的家人设法有所作为时,124 号房子才成为他们最终可以获得自由和主体性的房子。
(二)宝贝·萨格斯和塞丝的困境
萨格斯充分意识到,这个社区的人们需要教会他们要有点自私。人们需要爱他们“哭泣、大笑的肉体;在草地上赤脚跳舞的肉体”(Morrison,1987:88)。通过这种方式,人们最终可以声称拥有了自己。尽管白人的入侵让宝贝·萨格斯意识到,在一个用户奴隶制的社会里,她的公共区域和人们的自我主张都不被视为理所当然,但她充分发挥了自己的女性力量来影响他人和周围环境。
小说中的另一个女性角色也展示了她希望获得和行使权力的意志和斗争——塞丝。人们希望塞丝因为“太浓”的母爱而发疯,然后像凯西一样被驯服,但不是做一个骄傲的女人,并且可以在没有他们的情况下保住自己的工作。塞丝拒绝接受社会的期望和他人身上的教训,她拒绝听从保罗·D“少爱一点”和埃拉“什么不爱”(Morrison,1987: 92)的建议。所以塞丝最初重新获得了爱的自由,她不能再允许学校老师或其他人侵犯和占领她的孩子。但宠儿的出现反映了塞丝和124 号中每一位家庭成员的不安全感,因为她代表了父权制和奴隶制的记忆。宠儿将保罗·D 赶出家门,以此削弱他的男子气概。她还说服了塞丝,即她唯一适合的领域就是作为一名女性存在在房子里:“世界就在这个房间里。这就是一切,也就是我需要的一切。”(Morrison ,1987:183)
(三)莫里森理想的房子结构
莫里森对各种女性家庭的塑造都反映了她对女性自我意识和主体存在方式的不断探索。凯特·米利特(Kate Millett)在《性政治》一书中指出,男女关系也是一种政治关系,表现为男性对女性的统治。在斯托的理想中,女性似乎可以摆脱家庭内部的这种政治关系,然而,莫里森在她的小说中表明,一个绝对的女性主导的家庭只能是父权社会中的乌托邦,而两性平等和相互支持似乎是一条理想的出路。因此,保罗·D 重返124 号将意味着这座房子和这个家庭的最终完成。现在男性气质将被重新定义:保罗·D将保护塞丝,让塞丝重新找回自己:“你是你最好的东西,塞丝。你是。”(Morrison,1987:273)至于塞丝,她勇敢地解放了自己,克服了自己不正确的母性以及奴隶制和父权制的阴影。当塞丝选择向白人跑去时,宠儿就消失了,这表明当塞丝直接攻击父权制的代表时,她被奴役的化身,也就是宠儿,就会消失。通过保罗·D 的回归和塞丝的成长,莫里森似乎向我们展示了一个理想的家庭应该是一个抛弃父权传统疾病、男女和谐共处、共同养育后代的家庭,这种理解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女权主义试图将男性置于“他者”地位的局限。
此外,通过124 号内外的相互交往,黑人社区还创造了一种新的共同力量,鼓励社区中的每个人真正寻求他们的自由并获得他们的主体性。当丹佛克服恐惧,走出124号时,社区发现了萨格斯建立的纽带。最后以埃拉为首的女人们做出了她们在塞丝被捕时拒绝做的事:“……某种声音的披肩就会迅速地裹上她,像手臂一样一路搀扶她、稳住她。”
三、结语
斯托和莫里森都敏锐地意识到父权文化对女性和奴隶获得的自由和主体性的影响,两位作者对此提出了不同的理想和解决方案。斯托设想通过重塑房屋和家庭来解决这一问题,并将其作为世界女性赋权的一种新形式。事实上,这种看似摆脱了父权制束缚的理想家庭在父权制文化背景下不可能长期存在。如果她的母系社会理想能够长久持续下去,斯托主张的将家庭权力移交给的女户主将继续在父系奴隶主和父系上帝的控制下经营房屋和家庭,父系社会的基本结构不会改变。而莫里森真正重塑了这个基本结构。她重新进入这个结构,并展示了如何从根本上改变父权制家庭的权力结构,即一个完美的房子和家庭应该是一个男人和女人可以分享自己故事,从而社区中的人们可以自由地宣称自己并建立自己的主体性。
很难说斯托和莫里森提出了合理的理想和有效的解决方案,或者可能根本没有完美的答案。女性和奴隶长期以来丧失了一系列社会身份,他们不仅被剥夺了相关的权利和义务,而且缺乏应有的社会认可、尊严和安全感。这种问题长期存在且难以改变,而且作为受到不公平待遇的人,他们几乎没有力量去改变。因此,凯西和塞丝的奋斗应该是变革的开始。女性力量应该联合其他在社会中受到不公平待遇的力量,形成具有颠覆性的力量,这样才能真正看到希望的曙光,实现跨越式、永久性的变革。不仅如此,女性的力量不应局限于家庭。除了通过影响家庭成员或社区的人间接改变现状和世界之外,女性的力量还可以跳出社会规范的限制,走出家庭,打破旧有的枷锁,为自己和他人发声。当然,不可否认的是,《汤姆叔叔的小屋》和《宠儿》中的女性作为充满希望的开端,她们充分发挥自己的力量,积极改变身边的人和环境,是有益的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