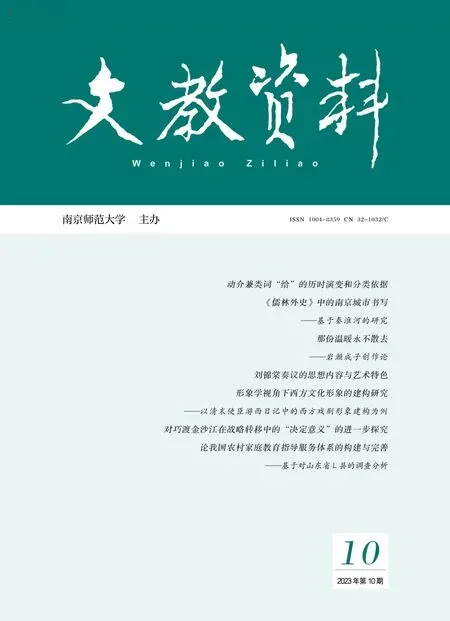形象学视角下西方文化形象的建构研究
——以清末使臣游西日记中的西方戏剧形象建构为例
李茵溢 夏若彤 计 杰
(南京师范大学 强化培养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
一、形象学视角下戏剧转述的研究现状以及研究价值
清末使臣是晚清极为特殊的一大群体,他们于儒家文化中熏陶成长,又在坚船利炮的影响下开眼看世界。他们出游西方,既代表着官方权威立场,又渗透着个人态度和审美性情,因而其记录充满个性化认知的多样性与东西方文化冲突的矛盾性,内容涉及军事、科技、政治、文化等多个方面。本文以西方戏剧为切入口,从异质性文化层面进一步解读使臣日记。
目前,关于清末使臣游西日记中西方戏剧的研究十分有限,主要研究成果也都停留在两个层面:一为使臣戏剧观研究,对使臣们如何观赏戏剧、如何理解戏剧进行分析,如尹德翔的《晚清使官的西方戏剧观》;二为西方戏剧的中国化研究,包括西方戏剧对中国戏剧的影响及后续改编作品的分析,以认可中西方戏剧文化的交互性关系为前提。如孙宜学所说,“在中外文化交流中,一个民族既定的文化传统常常构成接受另一种文化影响的背景与前提,与自己的传统相一致的,则充分借鉴,与自己的传统不能融合的,则拒绝或进行想象的改造”[1]。
以上研究大多视角单一,往往只侧重文化交互中的一方,且对于戏剧本身的专注度不高。基于此,本文引入形象学研究的视角,从戏剧记录本身出发,强调作为注视者的使臣们在西方戏剧文化形象的生成中所起的巨大作用,以期具象化呈现自我与他者的异质性关系与交往,为该领域研究提供全新的思路,弥补以往研究的不足。
本文所提及的“形象学”是指比较文学意义上的形象学,即研究一国文学中对“异国”形象的塑造或描写,最早由法国学者卡雷提出。该理论的核心在于对他者形象的定义,重点涵盖以下四个方面:①注重文本内部研究,将文本内部分层的同时关注形象的多样性与流变性;②注重对“主体”的研究,不仅研究被注视者的形象,而且研究注视者一方;③注重“我”与“他者”的互动性,从注视者与被注视者的简单关系扩展到“自我”与“他者”、“本土”与“异域”的互动性关系,使研究更具普遍性与流动性;④注重总体分析,在形成对于异质文化看法的基础上,真正理解这种看法是文学化与社会化的过程,理解形象产生的社会因素与后续的社会影响。
形象学理论对于异质性文化的敏锐观察,对于形象变异过程的强调十分关切。戏剧是西方的大众文化,清末使臣在观剧过程中出于不同的文化立场与社会影响会潜意识地加入自己的理解与态度,从而形成对于西方戏剧的创造性想象和自我性建构,使记录不仅成为异质性文化艺术形象的展示,也成为呈现文化心理结构与社会集体想象物的媒介,展现中西方文化内核差异的平台。
本研究立足于形象学理论,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开辟出较为新颖的研究方向,即清末使臣对于西方戏剧艺术的创造性接受以及汉化西方戏剧形象的建构,紧紧围绕“形象”展开,探究形象特点,分析形象意义,在研究中展现交互性关系与世界性眼光。
二、形象分析
(一)使臣眼中的西方戏剧:对西方文化异质性认识的初步形成
早期游西使臣出于语言障碍、交流应酬等,对戏剧的理解往往止步于猎奇心理带来的感官刺激,但随着观剧经验的不断丰富,使臣能够逐渐摆脱猎奇带来的刺激,形成一定的理性认知。通过对游西日记的研究发现,使臣对于西方戏剧的认识呈现出逐步完善的过程,由外而内、由浅入深,关注点从“剧院设施及观剧风俗”逐步到“表演艺术、思想主题”,不断深入。与此同时,使臣对于西方异质性的认识初步形成,其眼中的西方戏剧形象也逐渐鲜明。
首先,使臣不仅关注到剧院规模差异以及公私之别,而且关注到西方剧院的内部设计,如装饰的华丽、功能分区的明确等。除此之外,他们对剧院文化有一定程度上的理性思考,如张德彝在《八述奇》中已然意识到座位安排所存在的等级秩序。同时,使臣也对西方戏剧相关风俗进行了较为简练的罗列,如首演、消食风俗等,其中也涵盖观剧礼仪、戏单、观剧价格等细节情况。可见,使臣在长期观剧过程中逐渐完善了眼中西方戏剧的物质形象。
其次,由于中西方戏剧差异显著,使臣对西方戏剧表演技术层面的独特性记录甚多。
其一,意识到演员服装与人物身份地位、性格品德之间特意为之的对应关系。
其二,对舞台效果的长期关注,这与使臣早期的猎奇心理有密切关系,舞台灯光效果因其与彼时的新兴科技发展相关,成为使臣笔下的重点关注对象。与此同时,与中国戏曲布景差异极大的西方戏剧布景自然而然地引起了使臣的关注。
惟高山皓月,长江石桥,舟车鸟兽,花影天光,及旧石柱粗二三围,高二三丈者,以双眼千里镜望之,真假难辨。更有彩云疏星,荷风槐日,仙女数十,飞腾半空。其中固有真人纸画,然久看之,假水起波,纸人亦动,妙甚。[2]中国戏曲布景简单,多需要凭借观众的想象与演员的动作言语提示来互动完成。而“真假难辨”“妙甚”等词汇透露出作者对西方戏剧布景复杂、真实,讲求“再现”特点的准确把握,也体现其对西方造景之逼真的赞赏以及此时较为包容的心态。
其三,中国戏曲讲求“唱念做打”,戏曲评论重视对于演员自身技艺的评价,而使臣则关注到西方表演形式的特殊之处,如加入“动物参演”等。在相当多的使臣记录中,戏剧演出常常与杂技演出相继进行。如张德彝记录的一次观剧过程乃是先观车技,再观马戏,进而才是观剧,这一点在使臣群体的接受中有所不同。如张德彝所持乃是较为宽容的态度,记录中也仅仅是呈现雅俗共赏的文化氛围。戴鸿慈则有对剧院专业性的质疑,其虽对杂技高超技艺给予赞赏,却提出“剧院布置亦未得宜,所演皆为杂出”[3],已然有明确的对西方戏剧的区分意识。
最后,使臣意识到了西方戏剧与中国在主旨倾向上的差异。
中国妇女重节孝而贱淫妒,故演各戏以教人警人。西国男女之间最重情爱,故大小戏园所演故事,或真或假,无往而不讲情爱者。于是男子有因嫉妒而死者,有男女因情而同时自尽者,从未见演孝顺翁姑、随夫殉难、守贞守节、强奸顺奸、害夫背夫等戏者。盖西国儿媳无侍奉翁姑之礼,其他各节因多见而不为奇也,亦不欲以之警人也。[4]在这段记述中,张德彝总结西方戏剧中心在于“情爱”,而中国戏剧中心在于“节孝”。虽有一定的鄙夷情绪在其中,但仍可见其对于西方戏剧主题与中国所异之处有所思考。
通过对使臣眼中西方戏剧形象的分析可以发现,其关涉角度不断完善,在一定程度上理性认识到中西文化的异质之处,但流于表面未形成理论总结,多数是对物质性、附加因素的认识。因为科技上的卑弱使得物质条件上的异质之处尤显突出,他们对于戏剧表演形式、剧院等的描述总是不吝惜笔墨,但依旧未曾逃离“天朝上国”的旧梦,文化上的傲慢导致他们“俯视”西方戏剧,于戏剧内容本身的思考总流露着“不过尔尔”的意味。正如戴鸿慈在写下“谚有之好事多磨,中外一致”一句时的心态:将这些戏剧的内涵缩小,全部纳入自身坚韧的“传统”,从而确认自己的存在,彰显自己的力量。这样并未完全进入文化语境的理解导致他们在转述时不自觉地采用近乎完全汉化的叙事策略。
(二)“汉化”西方戏剧形象的建构
1. 话语规则的改变
分析使臣的剧本转述不难发现,使臣的话语规则是完全中式的。他们并未对西方的文化语境进行深入了解,在转述时也任由自身语境侵入文本。
(1)人物称呼的处理。早期较为粗糙的处理方式是直接忽略人物姓名,只以“某女”“甲”“乙”称呼。如《唐·璜》剧本转述中只以“甲”称呼男主人公;在《灰姑娘》的记述中以“某甲”称呼其父,以“女”称呼灰姑娘。分析同类转述可发现,“甲”“乙”一类称呼方式多是按人物出场顺序安排的。而到后期,使臣则能够具体地以人物姓名称呼角色,如“马斯亚”“赛藕色”等。
(2)概念的置换。使臣记述中用中国语境中的概念对西方同类概念进行置换,如以“继室”置换“后母”,以“神仙洞府”置换“天堂”等,这样的概念置换对文章的意义并未有较大影响,却在无意中掺入了中国概念自身所带有的文化意涵。这从侧面印证了使臣对于西方文化认识的缺乏,脑海中对人物身份、环境地点设计缺乏相应概念,遂以中国概念勉强形容。
(3)叙述笔法的选用。这也是剧本转述中最为突出显著的特点。使臣在对西方戏剧进行记述时,常常使用中国古典程式化的话语。如张德彝在《欧美环游记》中便以“见有少女,首冠盔,手持剑,往来歌舞如旋风,转喉比娇莺,体如飞燕,‘楚腰一捻掌中擎’,悉不过是也”[5]来描绘女演员的表演技巧。其中“转喉比娇莺,体如飞燕”是描述女子的传统比喻。在记述戏剧布景时,这一点更是体现得淋漓尽致,“木楼雪景,六出缤纷”[6]“惟高山皓月,长江石桥,舟车鸟兽,花影天光”等,使得西方的布景也染上了中国意象所带有的独特意味。而张德彝在《四述奇》中的“子年未及冠,女字而未嫁”[7]则更体现他以东方话语虚指西方事物,因为西方并不存在“冠”与“字”的风俗,这只是中国的传统。作者以这两项活动背后的年龄含义来对西方戏剧中的人物年龄进行指示,是中国古典叙事文学中程式化语言的进一步运用。
同时,使臣在语句的形式上也多化用顶真等的古典诗歌形式,使得语句更为活泼,如“主既坐而仆亦欲坐,仆将坐而椅不见,椅既不见而桌面随之亦空”[8]。在人物对话上更是运用中国的对话模式,如“鲁见虽惧而无法,勉强问其何来,一神答曰,无他,欲知尔所欲耳。鲁曰,我等所欲者点心而已。神曰,在此。转瞬之间,列满桌面,珍馐满而山神去”[9]。这样的叙述笔法的选用,多是因为使臣长期接受中国古典文学的熏陶及其优秀的古文功底以及以东方眼光观察西方。
(4)中国叙事文学特色的浸染。使臣在对戏剧进行转述时,一方面多采用客观叙述,这与清代中国古代小说叙事的发展倾向一致,即客观的呈现逐渐代替说书人的主观讲述。使臣叙述戏剧情节时,多以旁观者的视角,未掺杂主观情感,至多在转述结尾加以情感表露。另一方面是极富个性化和动作化的过程叙事,如,马斯亚见而祸心生,入夜刺死,焚其尸,纵其马,而毁其车,乡人罕有知者……当斯时也,众皆欢喜歌舞,马则不言不笑,目瞪足软,忽坐忽立,痴呆无神。[10]
张德彝在描述中借用凝练叠沓的排比式话语对舞台人物的动作进行描绘,具有一定的音乐性,铿锵有力。这一点与使臣对西方戏剧的内容理解多侧重情节的完形的倾向相辅相成。使臣对情节的完形多依赖于动作的转变,如早期“所演系俄罗斯伯多罗王在荷兰学铁木匠,工成回国,百官来迎,荷兰始知为王故事”[11]仅串联重要情节,而在张德彝其后的出使资料中可见,观剧记录篇幅加长,细节增多,描写不再局限于简单的动作变换,而是添加了心理描写以及逻辑推理。与此同时,出于情节完形的更高要求,使臣对于戏剧叙事的艺术手法有所关注。在关于《八十天环游地球》剧本的记述中,若仅仅出于情节的完形,张德彝不需要记录“甲买手套而有所迟,却仍在约定时间前到达”[12]的“险情”,只需要记录甲准时抵达即可。但实际上张德彝关注到了“情节的延迟”这一艺术手法并加以记述,使得读者在阅读时也能对观众的紧张情绪有所体验,展现了其观剧的逐渐深入。
同时,使臣在转述时借助中国古典叙事的截断突转对戏剧本身的戏剧性做了保留。如在《唐·璜》一剧的转述中,主人公狼狈逃离的画面被生动呈现,“甲怒,举灯操剑自往。未及门,见石人立,抛剑奔回”[13]。而主人公胆小怯懦的性格也被生动复刻,“随言爬匿桌下,自隙睨之”[14]。同样地,现场紧张的氛围也得到了渲染,“忽报款门,仆去即来,魂魄丧失,齿欲相击,强言‘石人来矣!’随言爬匿桌下,自隙睨之”[15]。虽只是三言两语,却把握住了精髓,使读者借助想象能够还原现场,体现了使臣在动作过程的叙事上敏锐的洞察力。
2. 叙事逻辑的偷换
除了在话语规则上汉化的改变,在叙事逻辑方面使臣也在无意中做了偷换。这样的偷换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使臣对于戏剧本身的“误读”。
(1)中国叙事模式的套用。中国古典叙事文学中存在丰富多样的叙事模式及母题,如“才子佳人”“黄粱梦”等,这些母题在历史长河中不断地被抒写,自身内涵不断丰富。而由于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熟读,处于晚清的清末使臣能够接触到更多且更为厚重的母题,这使得他们在观看西方戏剧的时候不自觉地会以这样的叙事原型进行套用。如张德彝在《四述奇》中就曾转述了由华盛顿·欧文小说改编的戏剧《瑞普·凡·温克尔》的内容,在他的转述中充满了“烂柯人”的原型意味:“甫一杯,辛即醉卧山顶,二十年方醒。醒则须发皆白,衣已化灰,身动,衣灰飞去,惟存汗衫短裤皮鞋,色已成土。立起,四肢酸楚不易屈伸。枪尚在旁,持时,柄木朽坏,只馀铁筒而已。”[16]当然,这一戏剧还嵌套了别的情节,但在张德彝的转述中“烂柯人”母题的相关细节却得到了较为详细的描述,这样的倾向或许是张德彝对此内容更熟悉所致,并由此形成了故事情节的梳理与串联。
而由于固有叙事模式的影响,使臣在梳理戏剧的内在逻辑关系时也会出现“硬套”的情况。如在《浮士德》一剧中,浮士德试图服毒自杀却被误读为“登山采药”,玛格丽特受到哥哥诅咒而去教堂祷告,把命运交给天使和上帝,灵魂得以升天的情节却被记作“女由是乃疯,寻亦故去”,这些表述在中国古典叙事文学中十分常见,既体现出作者对西方宗教传统认知的极度缺乏,也体现出固有叙事模式驱使下武断的杂糅。在《基督山伯爵》一剧的认识中甚至出现了主角混乱的荒唐情况,原属“唐泰斯”的情节完全被置换为“弗尔南”。
(2)中国传统观念模式的渗透。逻辑误读所潜藏的危险在思想主题的体悟上得到了爆发。乍看使臣对于主题思考会发现他们往往只停留于感性体认,缺乏深入思考,如戴鸿慈在《罗密欧与朱丽叶》中感叹:“一双情男女,并命俱死。谚有之好事多磨,中外一致,亦可惨已。”[17]这样的归结略显浅薄。若有再溯因由者,也总是流于“天意”“因果报应”等老生常谈。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是中国传统观念模式的渗透。
中国传统的观念模式有因果报应说、轮回说等,在多个剧本转述中均有体现,如戴鸿慈在《灰姑娘》一剧的转述中,用“于是天与机遇,遂成眷属焉”[18]解释了结局的发生;张德彝在《八十天环游地球》一剧的转述中,“报德说”意味浓重;张德彝在《艾米丽》中认为“泰西不谈报应,司悌佛触险,恰被哈木援出而死,岂非天乎?”[19]由此可见,正是受限于传统观念模式而不自知的处境,使使臣处于思维较为封闭的定势状态,未能以一种开放、探求的眼光看待戏剧,在戏剧批评时无意识窄化了文本的思考维度。正如张德彝对于《瑞普·凡·温克尔》主题的认识,只较为浅显地关注到所谓“大团圆”的结局,而未曾意识到戏剧所蕴含的逃离社会规约、反对主流意识形态、保持个人独立性乃至民族独立性的深刻思想;对《浮士德》更是抛却本身所要讨论的人的追求、灵肉矛盾、自强不息等问题,而代之以返老还童、神鬼色彩、天定天赐、爱情悲剧、父母之言、父兄决斗,以神权、族权的面貌遮盖了普世的追求,完全改变了戏剧的侧重点与主题,以片面的中国元素、中国理解“重写”这些戏剧。究其原因,乃是固有观念模式看似合理的主题涵盖力对戏剧内核的引导与扭曲。
以上两点,从叙事的表层和深层分别对“汉化的转述”起到了重要作用。正是由于表层和深层的同步互动,读者在初步阅读游西使臣的戏剧转述时能够感到扑面而来的“中国味”。这在很大程度上淡化了西方色彩,也从中钳制了西方戏剧自身的逻辑链条,用中国使臣自身的逻辑思维方式所取代,从而造成了叙事逻辑的偷换。这一“偷换”更加契合中国人的阅读习惯,因而难以为人所察觉。“西方戏剧将对历史、现实的思考熔进对人物性格的刻画和心理分析之中,而中国则纳入伦理情感模式。”[20]这样的习惯差异导致使臣在看待西方戏剧时乐于将其纳入某种自己熟悉的模式,从而窄化甚至忽略某些内涵。
三、形象意义
经由形象分析可知,使臣经由西方戏剧观察的不断完善,由早期关注“附加因素”到后期对西方文化的异质之处形成一定理性思考。但在转述这一形象时,使臣所呈现的却是重新建构过的汉化的“西方戏剧”形象。采用这样的转述策略,一方面是阅读接受角度的顾虑,使臣的日记在回国后多要呈览帝王或刊刻出版,在转述中难免需顾及中国人的阅读习惯;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文化中心”观念作祟。
在出使过程中,使臣作为“注视者”观察西方国家这一“他者”,而西方戏剧作为契机可从文化层面较为深入地透视注视者与他者的关系。使臣记述中对西方戏剧所涉先进科技大加赞赏,却顽固忽视其文化内核,甚至一有机会便加以贬斥。如张德彝在对西方重情爱而导致“强奸顺奸害夫背夫”之事的因果判断中可窥视其自我文化的优越感。这种科技上的谦虚和文化上的自大是契合时代变局中使臣特质的。即使西方的炮舰利艇迫使他们面对国家的颓势,但于他们而言仍是“身外之物”般的外在弱势。深受封建文化熏陶的使臣在文化上是“绝对自信”的,并未摆脱“华夷之辩”“天朝上国”的旧梦,仍将自己视作文化的中心。或许正是技术力量上的不平等与卑弱,也或许是西方文化的冲击所加剧的心理不平衡,使他们更需固守文化的强势,从而以一种“求同”的视角去观看西方戏剧,寻找共性以验证自己“强势”的力量。这样自然只能看到“同”,而不能深入领略“异”,更遑论体悟其独特性。
这样一来,使臣转述中所建构的“西方戏剧”的形象是有中心的建构,是在自认强势的中国话语下所建构的形象,全然以中国话语言说西方,并未真正进入其文化语境,更企图用自己强势的文化传统,使西方成为“无声的他者”,将其纳入自己的范围内。可这样的汉化建构并不彻底,西方戏剧所用到的电灯等提示使臣西方拥有中国所没有的东西,这使得使臣在转述中必然涉及对西方戏剧布景等外在部分的赞赏。但使臣汉化的企图并未就此消退,而是在对戏剧主题的描述中瞬间复苏,从而造就了矛盾的注视关系,既赞赏又贬低。
除去这一倾向,仍可见使臣不断进入异文化语境的努力,即使这样的努力多因故步自封而未取得根本上的成功,仍被裹挟入大势中。但这样的努力不仅是个人态度能力的变化,而且是文化兼容并蓄、交流互鉴的前兆。游西日记无疑为庞大腐朽的帝国带来了一丝清新的域外之风,这些传统士大夫出身的使臣虽对西方文化有所贬斥,但依然看到了戏剧在社会教化上的作用。张德彝虽贬低戏剧中的爱情,却也并未否认戏剧本身的社会作用。戴鸿慈的论述更是将西方的日新月异归因于戏剧:盖由彼人知戏曲为教育普及之根源,而业此者,又不惜投大资本,竭心思耳目以图之。故我国所卑贱之优伶,彼则名博士也,大教育家也。媟词俚曲,彼则不刊之著述也,学堂之课本也。如此又安怪彼之日新而月异,而我乃瞠乎在后耶?今之倡言改良者,抑有人矣。顾程度甚相远,骤语以高深微眇之雅乐,固知闻者之惟恐卧必也。但革其闭塞民智者,稍稍变焉以易民之观听,其庶几可行欤。[21]
虽说使臣的记述并非戏曲改良的必然诱因,但这恰恰与有志于改良国家的先进者不谋而合:改良者已知宣传对救亡图存的作用,也知文化启蒙的势在必行,戏剧以大众性与文化性成为二者的最佳载体,使戏曲改革成为时代所趋。游西日记的记述为戏剧改良的方向提供了一种潜在可能,助力了后来的五四运动及国剧运动。改良者充分利用其中的异质性为中国戏剧由传统戏曲向现代话剧发展奠定了基石,如良好票务经营模式的形成、外国题材的增多、外国主流观念的借鉴以及西方戏剧理论的化用等。这一趋势自然而然地波及文化领域的其他方面,进而席卷整个社会,使中国人的戏剧观念、心理人格、文化生态也在潜移默化地走向更新与成熟。
这样的建构倾向离开“戏剧”这一物象,依旧活跃于游西日记的其他部分,最终完成了使臣对于西方国家形象的整体性汉化建构,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等时代主流观念遥相呼应。游西日记作为认识西方的媒介进入彼时中国的大语境时,自然而然地引导了国民对西方的想象。使臣在无意中强调的西方异质透露出后来更新国民形象、新造国家形象的蛛丝马迹。
四、结语
使臣处于中西文化交流的前期,在被迫地打开国门的情境下,他们对于西方国家形象的观察建构是具有一定局限性的。于今看来,他们所秉持的文化等级观念固然不可取,但他们在中西文化交流方面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使后人能够走得更加踏实也更加正确,一步步探寻文化交流的正确途径。而今天,我们对于异质文化的认识应建立在充分尊重的基础上,进入其文化语境,了解其独特性,从而形成良性互动,汲取异质因素,丰富文化生命色彩。
——明清朝鲜使臣汉诗整理与研究(20BWW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