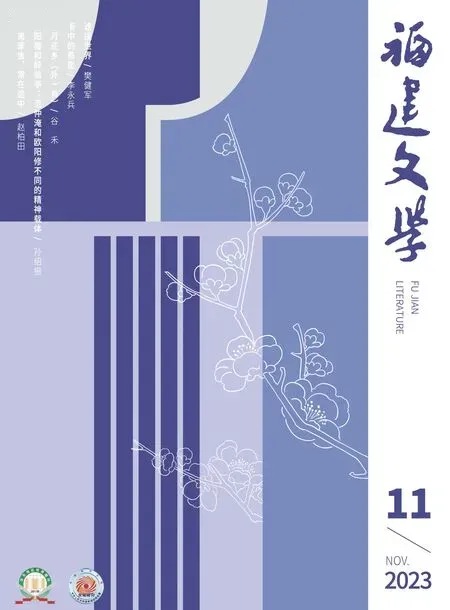随笔五题
狄 青
普通话
从前听单田芳评书,觉得勉强能算作带有东北腔的“普通话”。但评书艺人的口音本身就带有“口头文学”的特点,无法以播音员视之。也不单是单田芳,袁阔成、刘兰芳、田连元等,只要听声音人们就能辨出这段书是他们中的哪个说的。这无疑凸显了他们吐字发音的特点。
当然也有问题。比如在评书《隋唐演义》里,尉迟恭是太原人,窦建德是河北衡水人,二人在说书人嘴里肯定都说的是“普通话”;秦琼跟单雄信虽说都是山东人,可秦琼是济南历城人,单雄信是菏泽曹县人,这两个地方我都去过,说出来的话不挨着,但在评书里也不方便用语言来区分。一来听众未必听得明白,二来隋唐时各地都说什么话,怕是说书人也整不明白。
有人对《水浒传》后半部梁山好汉征方腊那几回描写有疑义。因为梁山这批好汉即使放到北宋前后的历史上,武功也是不差的,怎么到方腊手下,就死的死伤的伤?感觉是一群“假”梁山好汉。我却想,这里面难道就没有语言的因素吗?梁山好汉虽有108 人之多,但基本上都来自北方,且从籍贯上看,以山东、河北、河南籍的为主,其方言有区别,但相互沟通想必没有问题。而方腊的手下全部来自江浙甚至是福建、广东,与梁山好汉照面,原本该各报家门才是,此番却似“鸡同鸭讲”,只能少说多做,直接上家伙,结果便是双方英雄皆死伤惨重,此一“南北过招”可谓没有赢家。
有语言学家认为,中国古代其实是有“普通话”一说的,否则当年孔子带那么多的弟子,根本就没法去“周游列国”。《荀子·荣辱篇》中说:“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论语·述而第七》中也道:“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两者综合,意思是说越人有越人的语言,楚人有楚人的语言,像孔子这样的人在正式场合使用雅言。也就是说,从周朝开始,在社会上层的统治者中间,便已形成了属于自己的一套标准华语体系,谓之曰“雅言”,而知识分子要想进入社会上层,首先便要学习雅言,因而像孔子以及他的学生们应该普遍掌握雅言。换句话说,雅言即是当年的“普通话”。缪钺先生在《读史存稿》中也讲:“当时于方言之外,必更有一种共同之语言、如今日所谓‘官话’或‘国语’者,绝国之人,殊乡之士,可借以通情达意,虽远无阻也。”
那么,雅言又该怎么说呢?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指辞令之美,然亦可解为“不学《诗》则不能说雅言”之意。由此可见,要了解雅言的发音与节奏,可去研习《诗经》。而相比《诗经》《吕氏春秋》等古籍,一般认为《墨子》一书行文中多杂庶民口语,换句话说,想了解古人口语发音的可多多研习《墨子》。
就目前我所看到的影视剧,表现秦国或秦朝的还没有使用陕西话的。秦国上层应是以雅言沟通,但秦国下层军民该是以何种语言交流?显然不是目前的陕西话。的确,自秦汉以后,中国历史历经“八王之乱”“南北朝对峙”“安史之乱”“五代十国割据”等,导致大量北方少数民族进入中原、关中地区,民族融合几乎一刻都没有停止过。与此同时,北方大批汉人南迁,现在广东、福建一带的客家人就是当初北方迁移过去的汉人,可是他们说的话,如今的北方人根本就听不懂。许多人都认为当年秦国的语言应该与如今的广东话比较接近,因为秦始皇曾派50 万大军征讨南越,而当秦朝被汉朝所取代,这些军人便留在岭南,成为岭南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粤语被很多人说成是古汉语的原因还有一个,那便是粤语具有完整的九声六调,较完美地保留了古汉语的特征,留有古代汉语中入声字的痕迹。但是否就此认定粤语便是2000 年前的“普通话”?却还是不好定论。
三国时还没有四川话的概念。而且,刘备、张飞和赵云都是河北人,关羽是山西人,诸葛亮是山东人,其成年后在豫南鄂北一带活动。可以说蜀国上层多系北方人。四川地理上属南方,但如今的四川话却属于北方语系,不知道这和三国时北方人在此建立政权有无关系。但我一直对当年诸葛亮舌战群儒那件事颇感兴趣。请来看诸葛亮的“对手”——张昭、顾雍、陆绩,江苏苏州人;虞翻,浙江余姚人;步骘,江苏淮阴人;薛综,安徽濉溪人;严峻,安徽彭城人……我总想能够还原彼时之情景:张昭是如何讽刺诸葛亮“弃新野,走樊城,败当阳,奔夏口”且自比管仲、乐毅的?而诸葛亮又是如何驳得东吴众谋臣一个个哑口无言的?关键的问题在于,这些人相互间听得懂对方是在说什么吗?
要知道,吵架拌嘴这事儿,用字正腔圆的“普通话”是一种样式,用南腔北调的方言则肯定会是另一番的效果啊!
蹭热度
波兰裔法国著名作家内米洛夫斯基在她的《契诃夫的一生》一书的结尾处,引用了高尔基的一段回忆——那是1914 年的时候,高尔基想起了十年前契诃夫去世时颇具荒诞意味的葬礼。许多人都以为,那列从远东地区开过来的火车载着的那具棺材里,装的是封疆大吏凯勒尔将军的尸体,而不是作家契诃夫的。于是乎许多所谓的达官显贵都赶来参加葬礼。这些人谁都不认识作家契诃夫,多半人甚至也没见过凯勒尔本人,但他们却都清楚凯勒尔在沙皇军队体制内的尊崇地位,于是纷纷前来“蹭热度”,并希望在场的记者能注意到他们。葬礼上甚至还奏响了军乐,而那些赶来蹭热度的人们则在私下里相互谈论着“自家宠物狗的智力”,炫耀着“自己的别墅如何舒服,附近的风景如何美丽”……在引证完了高尔基的回忆之后,内米洛夫斯基笔锋一转,她如此写道:“然而,在这些无动于衷的人群里,契诃夫的妻子和母亲紧紧地依偎着,她们相互搀扶。在这个世界上的所有人当中,契诃夫曾经真正深爱过的,唯有她们俩。”
显然,彼时的契诃夫还没有像后来那么知名,虽然他已经在俄罗斯文坛上占据了重要地位,他的死对俄罗斯文坛来说是一个重大损失,但文人显然比不得达官显贵,不会有多少人来蹭一个文人的热度。当然,文人们也不热衷于这种场面上的热度,尤其是极具思想内涵的俄罗斯文人们。不过,随着时代的发展,事物也在发生着转变,“文人明星化”即是其一。“我的朋友胡适之”这个典故想必很多人都了解吧,那是大家一起去蹭胡适的热度,以提高自己的身价。前些年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时,一时间冒出来一大帮蹭他热度的人,有人说自己曾和莫言喝酒喝醉过,有人讲自己帮莫言买过卧铺票,还是下铺。王小波红了以后,也有不少蹭王小波热度的,倒是王小波的家人及时站出来说,王小波当年最困难的时候,别说写的小说入不得所谓“主流刊物”编辑们的法眼,就连出本书都是家里人拿钱自费帮他出版的,你们这帮人当时都在哪了呢?结果再没人敢出来蹭王小波的热度了。
想当年唐玄宗喜欢吹拉弹唱,颇有些音乐天赋。《新唐书·礼乐志》载:“凡乐人、音声人、太常杂户子弟隶太常及鼓吹署,皆番上,总号音声人,至数万人。”唐玄宗“自教法曲于梨园,谓之皇帝梨园弟子”。按照陈寅恪先生的考证,唐玄宗时梨园有两处,一处在长安光华门北面,一处在蓬莱宫旁边,核心的梨园弟子加起来有数百人。但在唐玄宗时,几乎所有和吹拉弹唱沾点边儿的人都称自己为“皇帝梨园弟子”,蹭这个热度倒是挺能唬人的,就连安禄山的叛军后来见到了都十分优待,据说是作为文艺人才安排到叛军的“军乐团”里去了。
因为在实体店购物图便宜因而曾被动下载过几款APP,于是我便总是被热情推荐“某某某同款的衬衣”“谁谁谁同款的鞋子”,倒不是喜欢不喜欢的问题,也跟贵贱关系不大,而是商家说的某某某跟谁谁谁我是一概不了解,连是男是女都存疑,想来我凭什么得去蹭他们的热度?要说我也不是个自甘落伍的人,想当年虽说是不追星吧,但是对多数“星星”们的姓甚名谁还是有所耳闻。可谁想到如今造星的门槛实在过低,出名的频率未免太快,计划真的是赶不上变化啊!方听说某某因为出轨而被爆出了偷税问题,那厢又被推送的新闻告知:谁谁因与陌生男子出双入对被偷拍而爆出有私生子的猛料……可是啊,对于某某、谁谁皆是何许人也、都是哪方神圣,到底偷了多少税,私生子的故事有多狗血,我已然连搜索一下的兴趣都没有了,更甭提蹭热度了。
我小时候,日本电影《追捕》曾经十分火爆,服装摊儿推出杜丘同款风衣,理发店推出“矢村头”,眼镜店推出真优美同款墨镜,那时候只是觉得挺有意思的。前一时因为“乘风破浪的姐姐”风靡,便紧跟着冒出来“披荆斩棘的哥哥”“势不可当的大叔”蹭热度,意思嘛,实话说一点都没觉出来,只是觉出来了无聊。
带相儿
年少时,我在企业工作过一段时间,常听老师傅说某某干活绝对错不了,看着带相儿;而某某不行,不带相儿,指定手潮。我就奇怪,这种事情难道也可从相貌中分辨出来?后来发现,老师傅看的实际上并不是“相”,而是凭多年经验从对方身上捕捉到的一种信息,感受到的一种气场,准确率却八九不离十。
刘备小时候上不起学,有个叫刘德然的人资助他,对刘备比对亲儿子都好。刘德然的媳妇不干了,老刘说,我看刘备这孩子面带富贵相,日后必成大器。后来刘备与关羽、张飞结拜,有叫张世平、苏双的两位大商人恰巧路过河北涿郡,因久闻刘备大名,特来拜会。见到后,觉得刘备眉宇间带着成大业的相儿,便赠予刘备大量钱财马匹。这两人在《三国演义》里只出现过一次,仿佛就是特意来给刘备送钱的。还有糜竺,同样是汉末少有的大款,起初是在徐州陶谦手下,后一见刘备,便认定刘备能成大业,于是陶谦死后,糜竺第一个站出来“率州人迎先主”。后来袁术和曹操夹攻刘备,吕布与刘备反目,又是糜竺最先站出来。史书载:“先主转军广陵海西,竺于是进妹于先主为夫人,奴客二千,金银货币以助军资;于时困匮,赖此复振。”糜竺也是拼了,搭上了自己的全部家当和人马不算,还搭上了自己的亲妹妹,从此跟定了刘皇叔。
清代选举子,倒是的确有一套“相术”的讲究,即所谓的“同田贯日、身甲气由”八字标准。“同田贯日”的意思也就是“方脸(含长方脸和短方脸)、头大身长、胖瘦适中”,这样的人方可入选;“身甲气由”的意思是倘若是“身”字脸,则身体必倾斜不正,“甲”字的意思是脑袋大身子小,“气”在这里为一个肩膀高一个肩膀低的意思,“由”则是说这个人身体太胖,总之,凡是带这种“相儿”的皆不可选。这倒让我奇怪,刘罗锅当年又是咋被选中的呢?
以相貌取人,这事儿咋说也不靠谱,但古人多深信不疑,哪怕经常被打脸,经常看走眼,典型的例子可举明末的光时亨。光时亨为崇祯七年(1634)甲戌科进士,任兵科给事中,觐见崇祯,毫无压力。面对崇祯提问,光时亨开口就是治国事理,令崇祯激动得站了起来——“上(崇祯帝)为起立,注视者三”。《桐旧集》中收录的第一首诗便是光时亨的《南楼誓众》:“人臣既委质,食禄当不苟。受事令一方,此身岂我有。即遇管葛俦,尚须争胜负。矧今逢小敌,安能遽却走。仰誓头上天,俯视腰间绶。我心如恇怯,有剑甘在首。读书怀古人,夙昔耻人后。睢阳与常山,不成亦匪咎。沥血矢神明,弹剑听龙吼。”简直是字字铿锵,通篇展示了好男儿为家国社稷抛头颅洒热血的无上勇气!
李自成陷大同,崇祯便想南迁,是光时亨激烈谏阻乃至于痛哭流涕。1644 年三月初一,李自成兵抵京郊,李明睿上书崇祯移驾南京,群臣赞成,光时亨出列怒吼道“不杀李明睿,不足以安人心”,把提南迁者皆称作卖国贼,抢占道德制高点;三月初三,李建泰上书愿奉太子赴南京监国,又是光时亨声泪俱下大骂众臣卖国,把爱面子的崇祯活活地“将”在那里,不得不表态以死守社稷。光时亨给提南迁者扣的帽子是:“将欲为唐肃宗灵武故事乎?”他把太子比作当年自立为帝的唐肃宗。于是乎崇祯皇帝和太子都丧失了南迁的最后机会。而当北京城破,崇祯自缢,令谁都没想到的是,一脸“忠臣相儿”的光时亨却急慌慌地投降了李自成。
美国汉学家魏斐德在《洪业——清朝开国史》中谈到“南迁”被阻时有这样一段话:“这对后来清占领北京时的形势产生深远影响。清比较完整地接管了明的中央政府,拥有了他们最缺乏的东西,由此接手了明几乎全部汉族官吏,依靠他们接管天下,并最后征服南方。崇祯帝的决定还导致诸多皇室宗亲继承权利的暧昧不定,以致派系倾轧,削弱了南明政权。”
清兵入北京,李自成西撤,光时亨又只身逃亡南明,结果被马士英弹劾:“给事中光时亨力阻南迁,致先帝身殒社稷;而身先从贼,为大逆之尤。”遂留下一个史无前例的罪名——“阻南迁”罪。光时亨死得不冤,他常让我想起陈佩斯、朱时茂表演的小品《主角与配角》,陈佩斯说:“你这个叛徒!我原来一直以为,只有我这模样的能叛变——没想到啊没想到——你朱时茂这浓眉大眼的家伙也叛变啊!”
当真与不当真
有一段时间,我身边一些年轻人说话总爱拿腔作调,不是“本宫近日肠胃不适,订外卖定清淡些的尚可”,就是“朕昨日偶染风寒,中午就不陪你们这些小奴才去打羽毛球了”,等等。后来才知道这些话都源自网络和荧屏上热播的“宫斗剧”,大家拿文艺作品里角色的对白相互调侃,可见其喜闻乐见之程度。我虽说不以为意,可也常会因此而想起当年读过的《宫女回忆录》,感觉宫女们记述的清宫仿佛与如今各种文艺作品里的清宫完全不是一个所在。宫女们口述实录里的清宫,别说是嫔妃乃至丫鬟动不动就跟皇帝插科打诨了,就算不说话,站着都不能摇来晃去,搞不好就是一顿板子伺候。而一般的妃子,即便是皇上爱看的,见了皇上也低眉顺眼,哪有喜不自禁满脸跑眉毛的可能?不过,我倒并不对此特别当真,明白许多人爱看这类作品就是图个乐呵,要的就是嘻嘻哈哈叽叽喳喳,真想研究清史的怕不会有谁从这类“宫斗剧”里找参照,或就像有人说的那样,这种东西原本就是“不当真,只当乐”的,随便看看罢了。
还有可以不当真的。有朋友请客,说是清宫御宴,饭店老板的祖上当年在御膳房干过,所以家里藏着乾隆过年时宴请文武百官的菜谱。对这种事儿我最多在心里“呵呵”两声,并不当真,因了手头就有乾隆71 岁那年于除夕夜宴请文武百官的所谓菜单。以猪肉为主,用了65 斤,还有少部分牛羊鸡肉,完全没有蔬菜。意想不到的是烹饪过程——大锅白煮,除了稍许盐,不放任何调料。大过年的,苦了一大帮文武百官。倒是一旁伺候的太监精明,早早地把草纸浸泡在酱油等调料中,于宴席中再将草纸卖给面对白煮肉大眼瞪小眼的大臣,以供他们蘸白煮肉吃。要不是史料里言之凿凿,我也想不通乾隆怎么会让满朝文武除夕夜一起陪他吃白水煮肉,皇帝老儿的脑洞果然是比较大啊!
有没必要当真的,自然就有必须当真的。在网络文学中,最早的所谓“架空”,是指既搞不清具体年代,也没有具体历史人物参照,完全靠漫无边际的想象而创作出来的故事和作品。但后来又冒出来所谓“半架空”,就是用历史上的真实人物,辅之以编造出来的故事。之前某些作品对康熙、乾隆、刘罗锅等人的演绎其实走的都是这条路子,但一般未出大圈儿,甭管是下江南还是微服私访,就算许多事情没有实锤,至少有传说,或编出来的故事无伤大雅。但之后的某些所谓“半架空”就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儿了。
对明史感兴趣的人多半都知道李定国。他原是张献忠的干儿子,后投南明,遂成南明最后的擎天之柱。曾在桂林之战和衡阳之战连斩清亲王两名,歼清军10 万,打破自努尔哈赤辽东起兵数十年八旗兵野战无敌之神话。后保护永历皇帝退至缅甸。永历帝被吴三桂掠走杀害后,在云南和缅甸一带坚持抗清的李定国悲愤交加,染疾而亡。就是这样一代抗清名将,却有作品将其“改编”成杀妻弑女并剃发易服归顺清朝的人,作品还“设计”了清宫某太监为李定国孪生兄弟,而李定国的爱女则爱上了康熙……实在想不出还有比这更大胆更狗血的改编了,看着或许热闹,可对这样的剧情不当真,怕等想当真的时候都来不及了。
还有的问题在我看来与当真不当真的关系不大。比如说李白的长相,本来李白长啥样儿不是个问题,至少我之前就从没想过这一问题。唐人魏颢是李白粉丝,曾在《李翰林集序》中说李白“眸子炯然,哆如饿虎”,意思是眼睛如大灯,大嘴如老虎。在《酉阳杂俎》中,段成式通过唐玄宗的嘴,一会儿说李白“神气高朗,轩轩然若霞举”,一会儿又说“此人固穷相”,不知是唐玄宗说话有问题,还是李白长得不好形容,抑或是段成式记录有误。李白自己在《与韩荆州书》中曾自述“虽长不满七尺,而心雄万夫”。唐朝的尺有大尺和小尺之分,参照考古发掘的唐尺,其长度从29.4 厘米到31.7 厘米不等,以30 厘米的居多,李白自称“不满七尺”,其身高应在2 米左右。
不知道是不是因了这些不靠谱的记载,才有了李白系汉人还是西域人之争。但在我看来,李白无论是中土汉人还是西域人,都是当时盛唐治下抑或中华文化影响下的中国人无疑,其人其文早已和中华文化融为一体,他的伟大与他的高矮胖瘦无关,只与他的艺术成就和文化贡献密不可分。
没那么多人注意你
计划经济时,物资相对匮乏,那时城里人不是住大杂院就是住胡同,家家都是一间屋子半拉炕,谁家包饺子剁肉馅,谁家炖肉熬鱼,瞒是瞒不过的。门可以关上,味道却关不住,想不让人注意也难。那时关注点少,人们注意力集中,一条胡同谁家小子第一个穿喇叭裤,哪家丫头第一个穿超短裙,人们都会当个新鲜事儿念叨好多天。20 世纪80 年代初,广告刚开始兴盛那会儿,“苹果”牌牛仔裤曾风靡一时,有人买不到所谓正版,就拿红布剪了个苹果图案缝在屁股兜上,走在大街上倒是引起不少人的注意,注意的倒不是别的,而是那只“苹果”剪得里出外进,像是被许多人啃过。
记得多年前,有个朋友打电话告知我当天的一份报纸第2 版最下方的一条消息里人名排序排错了,他的名字被排在了另外两个人的后面,“乱了规矩”。这事儿如果他不四处告知,我相信肯定不会有人注意。因为根本没那么多人注意他,且不说是一张发行不过万的行业报,即使是大报,看这条第2 版报屁股消息的能有几人?而且一个行业协会理事排名,在意排名先后的又有几个?但我还是很认真地回答他道:“没事儿,下次再发消息的时候让编辑改过来就是了。”
曾经有几年,因常写文章,我被问起的第一句话往往是稿费多少。而当我如实回答后,对方就会露出较为复杂的表情,接下来的话便是:“弄这玩意干吗?点灯熬油又不赚钱,而且还耽搁仕途,关键是这年头你写得再多,又会有多少人注意你?”
“谁会注意你”这句话也可置换成“有什么用”。可这世上总不能只留当官一条路可走,而不做无用之事,又何遣有涯之生?做自己喜欢的事,是对生命负责。而至于有没有用,有没有人注意你,那是另外一回事,与我们有关亦无关。
意大利有句谚语是说威尼斯那地方有“毒”。意思是在其他地方火爆的事物,到威尼斯就无声无息。1913 年5 月,美国大诗人埃兹拉·庞德来到威尼斯,彼时他的诗在伦敦、巴黎、罗马文学圈皆引起巨大反响,然而在威尼斯,似乎没人拿他当一位著名诗人看待,他所住的宾馆服务生更是没对庞德多看一眼。这令庞德想起了他的前辈——美国著名作家亨利·詹姆斯,19 世纪70 年代曾在威尼斯居住,而令詹姆斯懊恼的是,作为在英美已成名的作家,在威尼斯却没什么人包括媒体注意到他。这种懊恼,我能理解,但却并不认为庞德或者詹姆斯真的会拿这些当回事儿,他们多半只是调侃。
曾看到个链接——一个人头攒动的卖场,一帮保安手牵手拉成人墙,护着个看不清男女的年轻人挤过人群,原来该年轻人是个网红,正在卖场做个活动。近年来,我对层出不穷的“网红”“小鲜肉”的了解基本都源于他们因各种原因出事之后,而同时也了解到,这些我甚至连名字都没听说过的“网红”“小鲜肉”竟然动辄身价就十几、几十个亿!我没注意他们,当然不代表别人没注意他们,但还是想不通这些半大小子黄毛丫头们有何过人之处,能圈这么多钱。
著名登山家克拉考尔在他接触登山之前,是一名记者,文章有一定的影响力,但他希望通过自己的登山之举来获取公众更广泛的关注。1996 年5 月10 日,克拉考尔成功登上珠穆朗玛峰峰顶并安全下山,然而就在他下山后数小时,19 名在他之后的登顶者在下山途中突遭局部暴风雪,其中12 人遇难。1997 年,克拉考尔将他所见所闻写成《进入空气稀薄地带》一书,该书之后被翻译成20 多种文字,成为最畅销的登山图书之一。在书中,克拉考尔旗帜鲜明地反对任何形式的商业攀登行为,同时他说,8848米与8749 米的风光有何不同?我们是要给自己证明还是要引起他人崇拜?如果是后者,我劝你还是算了吧。而另一位著名登山家马克德怀特在他的《极限登山》一书中认为,人类最伟大的壮举就是生存,而其他都不是最重要的,“你登顶的光环,实际上人们只会关注它一会儿,最多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