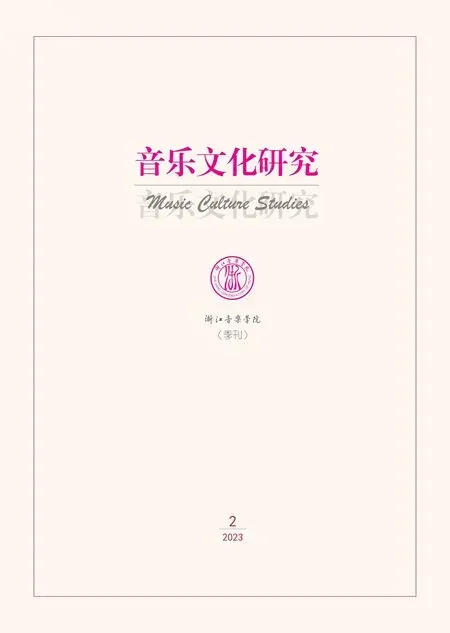用音乐言说
——马勒《第二交响曲》的叙事布局与结构寓意
张 晨
内容提要: 文章以叙事和话题理论为出发点,以马勒《第二交响曲》为分析对象,试图在音乐文本、结构分析中揭示马勒隐含其中的叙事内容和手段,解开马勒使用音乐语言隐匿的谜题。马勒的复兴与时代审美改变息息相关,他的作品于20世纪60年代起持续火热,与其说这是1902年预言的实现,不如说是历史剧变及文本理论兴盛所带来的效应。伴随着接受者对马勒音乐审美判断的改变,之前被视为音乐和文化融合的弱点,如今成为它真正的力量,作品具有历史上“不可衡量”的意义,能够嘲弄所有以前的解说和绝对音乐的风格类别。
奥地利晚期浪漫主义作曲家古斯塔夫·马勒(Gustav Mahler,1860—1911)的交响曲是19、20世纪之交该体裁步入最后辉煌阶段的代表,他的音乐游走于绝对音乐和有解说的音乐之间。即便撤销了乐曲外部的说明,马勒的作品依旧显示出其内在解说的可能性。这为马勒的音乐蒙上了更加神秘的面纱。音乐能够言说吗? 它怎样言说? 在说些什么? 从后现代风靡的“读者中心论”角度,解决文本意义问题的关键是将马勒隐匿在作品中的叙述阅读出来。2021年是马勒逝世110周年,他的作品在后现代持续发力,热度仍旧走高。尤其是经历了20 世纪60 年代的文本理论思潮后,对于马勒的解读更加丰富多元,他的名言——“我的时代即将来临”的确应验了。他的交响曲延续了贝多芬交响曲和瓦格纳乐剧的基因。尽管马勒没有创作歌剧,但他每年指挥瓦格纳的作品数十次,能够自由运用瓦格纳式的管弦乐色彩和纹理而避免复杂的半音和声。在这方面,马勒与理查·施特劳斯加速、不断发展的和声结构背道而驰。他的音乐具有真实生活的体验,能够从中听到遥远的、不同音调的混合,独特的表达方式使其跻身于早期现代主义作曲家的行列。勋伯格在突出讽刺和戏仿层面很接近马勒①,比如《月迷彼埃罗》(1914)和《小夜曲》(op.24,1920—1923);在马勒去世后的几天里,勋伯格完成了他著名的油画《古斯塔夫· 马勒的葬礼》(Burial of Gustav Mahler)。贝尔格则是更直接的信徒,他对马勒《第九交响曲》的溢美之词在1912年一个未发表的片段中被发现,《三首管弦乐曲》(op.6,1914—1915)也有明显的马勒音调风格。②20世纪60年代以后,许多作品投射出马勒的身影,比如,布里顿《大提琴交响曲》(1963)、亨策《轻歌曼舞》(1963)和《巴萨里茨》(1965)、沃尔夫冈·里姆《放弃》(1986)、施尼特凯《第五交响曲》(1988)、拉赫曼《卖火柴的小女孩》(1998)等。
一、理论立意:叙事与话题的介入
《第二交响曲》是马勒的早期作品,也是他独特叙事话语作曲的开端。作品于1888年开始创作,于1894年完成,起初是没有人声乐章的,前三个器乐乐章于1895年3月由柏林爱乐乐团演出,同年12月,作品以完整的形式与听众见面。之后,马勒为乐曲提供了一个说明。《第二交响曲》由一个庞大的弦乐组、17 件木管乐器、23件铜管乐器、6架定音鼓和其他打击乐器、4架或更多的竖琴以及1架管风琴组成,此外还有女高音、女低音独唱者和大型合唱队。马勒在1903年对这部作品进行了修订,他每次指挥自己的交响曲都会进行修改,作曲家最后一次编辑的时间是1910年9月,其中的许多调整是为了适应音乐会的音响或是人员问题。作曲家非常看重这部作品,1907年11月24日,马勒在维也纳举行了正式的告别音乐会,上演的正是他的这部早期作品《第二交响曲》。这预示着他将在大洋彼岸浴火重生,开启一段新的人生。在乐队奏毕后,台下的观众热泪盈眶,维也纳人用海浪般起伏的掌声颂扬、告别马勒,仿佛是此生最后一次鼓掌似的恋恋不舍。指挥家足足谢幕了30多次。
马勒的音乐有一个特点——在有解说的音乐与绝对音乐之间摇摆,外在解说和内在解说同在。广义地说,“有解说的音乐”术语意味着异质创作,受到音乐之外想法的启发,包括个人经历、存在主义问题、哲学和宗教思想、视觉表现、文学作品和历史事件。“有解说的音乐”于1850年后开始在德语音乐中出现,之后蔓延到法语国家。19世纪的欧洲音乐史学发端于“绝对音乐”和“有解说的音乐”的对立,汉斯立克是绝对音乐创造的坚实捍卫者,他于1854年提出了名言“声音运动的形式”。在有解说的音乐领域里,柏辽兹、李斯特、理查·施特劳斯是杰出的代表,但他们对于相似的基本问题的回答却大相径庭——柏辽兹受到音乐戏剧的启发,李斯特受到“哲学时代”的启迪,理查·施特劳斯受到文学、音乐自传、符合他个人风格的说明性有解说的音乐材料影响。马勒和理查·施特劳斯共属一个时代,施特劳斯会把预期的要求强加给听众,在前两部早期交响曲之后的作品总是标题性的:假定听众拥有一定的知识;试图引导他们的想象力沿着一条特定的道路进行;让受众去探索主题和音乐之间的关联。施特劳斯从柏辽兹和李斯特那里获得灵感,他非常尊敬李斯特,从一开始就采纳李斯特的原则。在被施特劳斯视为贝多芬遗产的有解说的音乐中,他找到了一条“我们的器乐音乐的独立发展”道路。像李斯特一样,施特劳斯相信内容(诗意的思想)优于形式,赞同新思想能够创造新形式。他认为,音乐是一种表现艺术,并断然拒绝了汉斯立克的自主美学。但在部分理念中,施特劳斯将自己与李斯特拉开距离,首先是通过音乐插图,然后通过不基于文学模型的虚构程序进行初始设置。③
马勒对于标题的态度是模糊的,他甚至有一些退缩。他告诉施佩希特(Richard Specht),自己的音乐应该“被误解,而不应被视为纯粹的理性主义,实际上是作为一种说明性的有解说的音乐”④。马勒的交响曲以内在标题为基础,直到《第四交响曲》,他都公开分享了这些标题。此后,他正式与有解说的音乐划清界限。从一开始,批评家们就嘲笑他的解释学表达,使他开始意识到语言程序很容易遭受误解,之后他删除了说明,也刻意和理查·施特劳斯有解说的音乐保持距离。马勒的包容性体现在他的作品来源有图像、诗歌、自然的声音、个人经历、文学、宗教和哲思,这些都在他的音乐中得以实现,他很重视音乐的可塑性和表达能力,其名言“用交响曲创造一个世界”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马勒的音乐叙事既有他律性也有自律性:一方面,他的音乐语言可以叙述音乐之外的东西;另一方面,音乐形式和语言叙述了音乐存在本身。相比早先的有解说的音乐,马勒的标题是个人的、不能公开的。因此,使用文学的而非内在程序来理解马勒的作品是片面的,他的音乐具有“自传体”性质,比如《第一交响曲》开头和谐的声音象征着自然,这需要运用更广泛的视角来看待音乐的语言。音乐独特的语言包括惯例和流派此类比较广泛的话语修辞,作曲家可以运用具有可识别的风格和特征来表达音乐运动自身的类型和题材,比如,声乐起源的音乐惯例(器乐朗诵、咏叹调、合唱、赞美诗、无词歌)和器乐传统惯例(进行曲、葬礼进行曲、牧歌和马勒个人最喜爱的“来自远方的音乐”)可以运用于分析马勒的作品。此外,还包括一些常见的舞蹈元素,比如连德勒、华尔兹、圆舞曲、小步舞曲,每一种类型都有自己的语义场,作曲家通过形式实现了用普遍类型的交响乐反映人类和世界基本问题的意义。
马勒的诗歌意图以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为范例,作曲家同样在交响曲中运用了“词”,使用独唱和合唱。马勒在贝多芬的基础上,结合了他同样崇敬的作曲家瓦格纳的整体(综合)艺术观念,还有意将这些原则与理查·施特劳斯的戏剧艺术结合起来。然而,调和二者是有挑战性的,正如马勒1896年3月26日写给马夏尔克(Max Marschalk)的信中所说:
我相信,现在我们正站在一个重要的十字路口,这个十字路口很快就会将交响乐和戏剧音乐这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永远分开。懂得音乐本质的人都明白这一点。即使是现在,当你把贝多芬的交响乐和瓦格纳的声音结构进行比较时,你会发现他们本质上的潜在对比。没错,瓦格纳采用了交响乐的表达方式,就像作曲家会有理由、有目的通过瓦格纳的生活和工作为音乐所获得表达能力一样。从这个意义上说,所有的艺术都是相互关联的。事实上,艺术甚至与自然有关。但到目前为止,这个问题还没有得到充分的思考,因为我们对这个问题还没有一个明确的视角。⑤
马勒承认,他并不是构建这一体系的人,但他仍然坚持自己在创作《第一交响曲》之时已经形成了这种观点。音乐叙事通过声音本源表达声音本体,形成声音本色。《第二交响曲》是马勒体裁混用的典型,它通过对歌曲的关联、声音的扩展拓展了交响曲的表达域,作品通过时间和空间构筑起了一个有关生死的故事,无论是选材还是音乐本身的话题特征均和死亡相关。这种思考是独特的,因为他区别于布鲁克纳纯宗教式的虔诚。在对待生命和死亡的问题上,马勒的作品掺杂着世俗思考,包括反讽与嘲笑,这是最悲惨的恸哭,笑着流泪比哀号更让人痛彻心扉。
尽管音乐可以叙事,但它并不能过于具体,应以曾经风靡一时的音乐修辞传统的最后衰落作为前车之鉴。帕特里克·麦克雷利斯(Patrick Mc Creless)指出:“正是因为对修辞格的过分强调而最终导致了修辞学的消亡。曾经充满了活力的公共修辞学传统,开始给枯燥的修辞格的背诵和识别让路……到18世纪初,尽管修辞学仍旧处在大多数欧洲教育体系的中心位置,但它已僵化成一种沉重的正统学说而丧失了其活力。”⑥因而,对于马勒音乐的解读需要有独特的叙事和言语分析,笔者还将借用“话题”理论:一方面,如果旋律或伴奏音型可以让人辨认出某种风格或体裁,它们便有了话题的音乐特征;另一方面,情感组成了话题的部分意义。
音乐话题在学科属性上隶属于符号学的范畴,它与日常使用的“话题”不同,在分析中应保持其本身的音乐性征和开放性。莱纳德·拉特纳(Leonard G.Ratner)出版于1980 年的《古典音乐:表现、形式与风格》是话题理论的开端,他认为:“18 世纪早期的音乐发展出了一套具有特性的音型,它们与崇拜、诗歌、戏剧、娱乐、舞蹈、仪式、军事、狩猎、下层社会的生活相关……其中有的音型与各种感受和情感相关;有的则犹如描绘图画一般……话题有可能指某种成型的作品,即体裁,也有可能指乐曲中的音型和进行,即风格。”⑦在音乐分析中,乐谱是间接材料,感受是直接材料。听众通过聆听捕捉到内容,通过经验获得信息。识别和解读话题也就是在尝试解读音乐的表现内容。马勒在音乐进程中插入了不同的话题,读者(听者)识别出话题的基础特质,便为理解作品的情感表现提供了更多参照。当异类话题的出现并不符合原语境的时间和位置时,便会引发关注,也更具有分析价值,为叙事带来更多冲突与推动,促使故事向前发展,块状模块的设置、阶段性展开和重置同样是有力的叙事手段。马勒和布鲁克纳的结构都有断层,并且不设置黄金分割点,这样就能插入更多的阶段性话题,推动力的应用在螺旋式上升中展开。
二、叙事布局:提出命题——葬礼与流浪
巴洛克时期风靡的“感情程式论”是音乐领域最为重要的成果之一。作曲家在创作音乐作品时,就对乐曲的种种构成要素进行预先的理性化编排,使音乐在表现情感时可以受到理性的控制。修辞学在古罗马时期之后脱颖而出,其目的是让听众在聆听后,在理智和情感上接受并认同演讲者的观念和论点。⑧音乐的最终目的是要表达情感,感性通过理性析出获得意义。而音乐的构成根本和语言学的基本目的在某些方面一致——逐层结构的连接和意义。音乐的结构不是静态的,而是一个状态向另一个状态的不断变化,读者将一部作品作为“过程”来理解,是使用“三段论”和修辞语篇结构这一分析视角的重要理论根基。从强调共性结构的“规则性”转向“语篇性”(textuality),是将音乐结构的研究扩展到各结构层级之间的逻辑性研究。这一分析理路主要“解释”的是各级结构之间的“连贯”“衔接”等问题。⑨在《罗马修辞手册》中的“六重结构原则”:“列出观点”“陈述事实”“展示有利于自己的观点”“举出证据”“驳斥与辩论”和“得出结论”,适用于通过减缩后展现的“开篇、中介、终结”三部结构。
马勒的作品在整体结构设计时借取了文学叙述的原则,《第二交响曲》最核心的模式是在五个乐章的安排中体现出整体的三部性结构。马勒是一位文学音乐家,他是博览群书的人,而且阅读的都是很有价值的书。这在他的朋友、同事和早期传记作家那里得到了证实,包括恩斯特·德西(Ernst Decsey)、保罗·斯特凡(Paul Stefan)、规多·阿德勒(Guido Adler)和布鲁诺·瓦尔特(Bruno Walter)。一方面,马勒的作品常常需要借助文字来传达他的音乐理念,比如第二至四号交响曲;另一方面,他认为音乐所能表达的远比文字要多得多。尼采语言的音乐性使马勒震撼,海涅优雅抒情的一面始终保留在他敏锐的听觉中,对歌德的崇敬体现在《第八交响曲》宏伟的诗篇,瓦格纳精神同时在他的意识流中流淌。
马勒交响曲的中心是生死,这是浪漫主义最爱和至高的议题之一,也是人类最具哲学性的话题,它赋予艺术最富魅力和深度的思想。创意通过主题(动机)、体裁、题材、演出场合展现,形式的选择、基本元素的选取需要遵从音乐的功能表现原则。从歌词脱离出来的纯器乐,具有更加广阔的想象力和原创性。从18世纪起,器乐逐渐从声乐中解放出来,直到浪漫主义文学与音乐的关系通过柏辽兹、李斯特到达了瓦格纳,最终在“无词《指环》”中得到了永生。马勒延续瓦格纳乐剧思维进入交响曲作曲,他看待带有歌词的交响曲的态度如同瓦格纳看待乐剧。歌词对于他们不是附属品,而是脚手架——一旦房屋盖好后便需要拆除。马勒对于文学的兴趣不再拘泥于表面的设置标题、与文学挂钩,也是从这部作品开始,他转变了自己的“标题观”。1901年12月18日,他在德累斯顿写给阿尔玛的信中指出,《第二交响曲》的节目单是“写给一个肤浅的、头脑简单的人读的,那里面涉及的仅仅是这部作品中最为外部的、完全表面化的东西”。他认为,即使是“启示录”也是最多揭示小部分真理,“直到最后,作品本身和它的创作者为一般认知所曲解”⑩。他撕毁了已经写好的说明,在写作方式上延续了贝多芬的表现感情多于景色描绘的理念,并试图在音乐叙事中达到文学无法企及的生命力。
在《第二交响曲》的开始部分,作曲家表明了态度,他抛出的话题必须能够引起受众的注意,死亡与不祥首当其冲出现,成为未来论述的关键词。在建构和发展的过程中,主题和它所支持的、反对的因素构成立体空间,通过逻辑组织实现完整过程。作曲家对这个命题进行了判断。第一乐章的葬礼进行曲所表达的悲剧性元素及死亡所暗含的哲思成为音乐的起点。马勒从来没有停止过对于生与死的思考,但局限于每部作品中产生的效能各有不同。这里所埋葬的英雄是《第一交响曲》中的那个巨人,所用的旋律纯朴而细腻,他说:“我称第一乐章为‘葬礼’,如果你想知道的话,我是在给我的《D 大调交响曲》的主人公送葬,我从一个更高的角度看到他的整个一生,仿佛从洁净无瑕的镜面中反映出来。同时,它也提出一个重大的问题:你为何生存? 又为何遭受苦难? 这一切是否不过是一个巨大而可怖的玩笑?”⑪就这样,马勒以材料所影射的“葬礼”为开篇,奠定了全曲的基调,接续的各乐章是一个解答、思索的过程,最终的答案蕴藏在第五乐章。
第一乐章整体进行以横向线条为主,对于主题的运用、发展比较传统。马勒构成“英雄的葬礼”的核心音调——主题的来源复杂,让人回忆起很多事情,唤起了贝多芬、布鲁克纳、瓦格纳的独特叙述。从马勒的发展手法可以看出:首先,晚期浪漫主义的代表人物马勒的作品是在一种创新性的“匮乏”中发展的,尤其是主题的创造,不仅是这部作品,还有他的《第八交响曲》和《第九交响曲》第一乐章的主题都不是“原创”的,但这能连接起作品间所蕴含的相关概念,比如《第二交响曲》开头对于葬礼、英雄性的唤起。其次,从主题的创造来看,1908年起,勋伯格的无调性作品也是对主题创新性的思考,马勒非常欣赏勋伯格,但同时承认与这位年轻人的观念之间存在距离,二人所面临的是同一困境——对于主题构成的创新性匮乏的焦虑,只是解决的方式有所不同。最后,是对作品的评价方面,如果在主题不是独创的前提下,音乐有没有可能获得成功? 这涉及美学评价,尽管作曲家写作主题的原创性受到质疑,但在这一点上,勋伯格对马勒的非原创主题的作品给予了充分肯定,他认为乐曲最终的优劣与评价标准取决于整体性是否高于个别主题的设计。通过如上分析可以看到,世纪之交的作曲家马勒在乐曲开篇思索死亡的同时所面临的创作困境。
在音乐领域,追踪艺术作品之间的相关性是分析和批判性干预的常见工具,通过识别代码、流派、主题、调性、形式系统或策略,受众得以从当下的作品中识别到已经存在的作品。音乐文本之间的明显联系的分析卓有成效,作者或多或少有意地从一个文本引用到另一个文本,构成“引喻”。马勒的“新音乐”常常和旧音乐结合,或是使旧的声音变新。他将过去的音乐实践结合当下,重新设计延伸的音乐,不断创造出听起来“不像以前听过的任何音乐”的音乐。虽然他关注早期现代主义趋势,如瓦格纳主义、尼采的思想、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历史主义、讽刺和幽默,但他觉得没有必要借鉴它们。
除了对于死亡的思考,作曲家反复采用的某种手法一定是其有意为之。马勒对于舒伯特的继承除了艺术歌曲体裁,还有大师诸多作品中反复运用的“流浪节奏”(或“流浪意向”),这也可理解为极具个性的修辞现象。早在1886年,马勒就把这个世界描述为一个“注定要不停地流浪”的地方。19世纪90年代初,他开始塑造孤独的流浪者形象,同时也表达出对孤独这个概念的矛盾心理。音乐主题中四(五)度的空旷感、分解六和弦模进带来的游移,都是这方面的体现。这与舒伯特的艺术歌曲、马勒自己早期在声乐套曲《流浪徒工之歌》(Lieder Eines Fahrenden Gesellen,1884)中塑造的形象是相关的。马勒曾在一封写给友人的信中提到创作《流浪徒工之歌》的目的:“我欲借此套曲来告诉她——其正是表现一个流浪汉走进冷暖无常的世间开始漂泊的自传故事。”⑫“流浪”一词暗示了一种具体的行为:在等待的同时来回走动。“流浪者”形象在《大地之歌》中达到了高峰,第一乐章开头的重复四度音型便确定了这种游荡的、寻找的姿态。这是一种渴望——对无限的渴望——几乎贯穿了作曲家的所有作品。马勒在创作中有一条延续的主线,它发源于早年的艺术歌曲:在一个冷漠的世界里体会着失去、孤独和悲伤;对自然的崇拜,因对真正的共情痛苦的病态怀疑而变得复杂,因记忆和认为死亡是一种出路而加剧;在一种无所不包的遗忘中幸福地消失。艺术歌曲与马勒交响曲的关联不仅是音调上的,还有平行的意义。
三、风格修辞:争议点——狂欢的扭曲舞蹈
用于语言文字的“修辞”原指对文字词语的修饰,以此彰显语言表达的准确鲜明,使之生动有力。20世纪90年代,随着后现代叙事理论的出现,修辞凸显出具有语言结构功能的特性,它和叙事的关系也变得更为相依:叙事是否充分且圆满,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修辞的有效并成全与否。声音修辞的实现依托于结构因素、方式以及声音的衔接与叠置;音响叙事通过结构驱动的声音修辞成就音响事件。⑬音乐形态的修辞使风格偏离。马勒的交响曲通过感性作用于理性,将自发的、无序的情感条理化,向有逻辑和理性的感情靠拢,在浪漫主义自发的、自我的抒发之外走向了另一个维度的理性。这种理智将音乐视作与文字同功能的手段,乐音作为一种暗语,使得作曲家能够像演说家一样完成音乐的叙说。音乐叙事夹带有理性化的情感因素,其目的是使音乐成为表现人类情感生活的艺术。音乐中的谋篇布局通常指对音乐整体结构的设计及音乐推进流程的计划,具体包括主题的呈现方式、发展或对比手段、再现时机、调性布局等。表达过程应和音乐中心话题相称,通过过程达到对听众的劝说目的。作曲家首先提出问题,之后解决问题,这个过程中会出现设定的阻碍、矛盾和冲突,即争议,是由作曲家设计并希望在作品最后得以解决的问题。争议点很重要,也是新侵入的要素,并必须被化解。
《第二交响曲》开始的“死亡”命题是一个真命题吗? 它是否经得起推敲? 之后,一个假设的话题被引入,它以全新的姿态颠覆了原始的假设命题。这是一个论辩的过程,预设的虚假、狂欢的假象是这个伪命题存在的意义。第二乐章至第四乐章便是这样的一个反射命题,形成“间奏曲”,其中出现了多元的、庞杂的因素。第二乐章“行板”结合了连德勒舞曲与圆舞曲的风格。民间元素一直为马勒提供养料,带着粗俗、狂放,甚至笨拙的舞曲是他反讽的源泉。规多·阿德勒(Guido Adler)试图传达马勒的音乐和存在给他留下的印象本质和深度,认为他在时代中建立了可靠的传统,在他的作品中可以感受到即将到来的时代脉搏,并以家乡的声音和所属国别的方式构筑了艺术殿堂的基础。他给予马勒音乐如此多维的评价:“你会看到被天使包围的孩子,面对逆境的年轻人,陷入斗争和搏斗的男人,表现出极大勇气的战士,为挚爱而痛苦的妻子,以及为不朽而奋斗的人类。你偷听了大自然的编织,绿色的草地,朦胧的小树林,森林里的动物,混乱和混杂的恐惧。你把我们提升到自身渴望的敬虔境界。”⑭马勒的音乐包含了多种元素,风格混杂是他的独特品质。拉特纳的风格话题分类首当其冲便是“军事与狩猎音乐”⑮,由弦乐、管乐、键盘模仿的号角声和猎号声的表现内涵为:宫廷卫队在小号声和鼓点中行进;(德国市镇)各种仪式上的市镇乐队;作为贵族消遣的狩猎;回响在田野的号角声;用在开场或暗示离别;也可用作戏剧效果。⑯拉特纳将风格层级划分为三种:高风格(高贵、典雅),以小步舞曲、萨拉班德、加沃特为话题;中风格(活泼、愉悦),以布列舞曲、吉格舞曲为话题;低风格(粗粝、直接),以对舞、连德勒舞曲为话题。每一个舞曲话题和社会文化背景有紧密联系。这个观点源于沙依贝(Johann Adolf Scheibe,1708—1776)在1745年出版的《音乐批评》⑰中的论述:低风格的气质和性格是粗野的,和声简单,乐思、旋律少装饰,情绪表达自如,象征了下层社会和阶级。⑱沙伊贝所论述的作曲家不是虔诚的“音乐诗人”,而是18世纪中叶的启蒙运动的器乐作曲家。他最为清晰地阐明了音乐修辞格的演变中所体现的核心历史现象:原本在声乐音乐中与歌词有关的表现意义,最终可以获得解放并且可以在器乐音乐中独立发挥作用。⑲
第三乐章“谐谑曲”的无穷动的风格带来了全新体验,它来源于马勒之前写过的收录于《少年魔号》中的一首声乐曲《圣安东尼对鱼的说教》。由于这首歌曲的加入,使得谐谑曲的特征更加明确,成为该作品的亮点。他对《圣安东尼对鱼的说教》的引用属于戏仿手法,也是低风格的表现,风格的偏离或重建成为一个“音乐事件”。器乐没有了要表达的歌词,关注点从歌词讲述的故事转变为动机、乐汇到整个乐章的音乐构成。器乐对于歌曲进行了修辞,引喻是描述器乐音乐的普遍方式。在文本和马勒的原创音乐之间,听者会捕捉到祷告的讽刺和徒劳。这种叙述方式带来了双重体验,使音乐语言的“双关性”得以彰显。双关语(paronomasia)在修辞学中是指“一定的语言环境中,利用词的多义和同音的条件,有意使语句具有双重意义,言在此而意在彼。其用法有两种:语义双关和谐音双关。语意双关是借用同义的词语类表达一个双关的意思;谐音双关是利用同音或近音的条件而构成的双关。双关语的意义在于表达语句中的内藏的含义”⑳。摘引来的材料与作品风格不协调,成为“戏仿”,这本身就是一种音乐修辞格。听众在体验到差异后,会对两部作品产生联想或反差。在《圣安东尼对鱼的说教》中,讽刺情绪在歌唱中被突出;在《第二交响曲》第三乐章中,音调由于木管乐器的独特声效,造成了更加强烈的“正话反说”感受,作曲家以此强化了音乐修辞。值得注意的是,马勒的选题与瑞士画家阿诺德·博科林(Arnold Böcklin)于1892年创作的画作《安东尼的布道》(Der heilige Antonius)具有的呼应的效果,将其作为捕捉自然的模型。㉑马勒的音乐因此扩展出更大的维度。
20世纪60年代开始,马勒作品再掀浪潮,作曲家卢恰诺·贝里奥摘引了马勒《第二交响曲》第三乐章“谐谑曲”作为《交响曲》(Sinfonia,1968—1969)的背景,在此基础上拼贴历史上的(包括他自己的)近百部作品,这是对马勒音乐的再加工和与前辈的对话。也是在这一乐章的背景下,现代听众得以重温马勒庞大的交响曲计划中某些最激进的方面。贝里奥在对该乐章的“分析”中展示了连续性与间断性之间极为重要的关系,他那精心的“评论”最终揭示了马勒的独特之处。㉒他认为,马勒的谐谑曲像一条河流,“它沿途经过不断变化的景色,有时通到地下,而在另一个完全不同的地方露出来;有时,它的旅途很明显,有时完全消失;它或者是以充分可辨认的形式出现,或者只看到一些微小的细部,而迷失在周围大量的音乐现象之中”㉓。贝里奥因此封闭了最初的材料,首先为大量评论的材料提供空间,但之后作为一个自主的过程只留下了一个马勒式的碎片的骨架。它是增加的删除,给这个乐章提供了一个大规模的形状。㉔贝里奥在马勒的基础上的创作,是以借用方式作曲的极致。它的产生与20世纪60年代整个大环境的审美和思维有关——它与“互文性”理论同时盛行,也是马勒作品复兴的一大动因。此时的音乐和文学在文本的彼此关联中成长。贝里奥认为:“像文学文本那样,不管哪种音乐文本都由彼此互为条件的文本组成。实际上,在音乐创造性的情况下,互文性的条件可以成为一种潜在力量,以至于‘谈话者’越多(或感到他们)‘被谈论了’,他们就越失去勇气去谈,就越以沉默来逃避谈话。作曲家不说话了,他完全用了‘别人的’或‘自己说过’的话来讲话。”㉕
《第二交响曲》第四乐章“原始之光”同样体现了文本关联而带来的意义交流。它来自《少年魔号》中的最后一曲,标题来自阿尔尼姆和布伦塔诺收集编选的民歌集《少年魔号》中的一首同名民歌。因此,在谐谑风格与“互文性”写作的部分中,马勒以“反讽”叙事达到了言在此而意在彼,它迂回地、用否定的含蓄方式展现了深刻的意义,在承受语境压力的同时构成一种“修正”,“反讽”的不确定性使主体及其关联摇摆,当主体被扭曲后产生出的张力恰恰是其美学层面的价值,欢乐和戏谑的背后实则是无以名状的苦痛。无论是“互文性”还是“反讽”,都预示着未来潮流滚滚而来,这种趋势无人能阻挡。混杂的材料令人回忆起过去,不管是欢快的还是虔敬的,都为乐曲带来不安与矛盾,这是一个19世纪末作曲家的幻想,一个内心极为不安的人的独白。在微笑中流泪,在欢愉中苦痛,是该部分的核心。
四、情节模式:从死亡到达了天国与永恒
贝多芬交响曲中从斗争走向胜利的“情节模式”被浪漫主义作曲家加以改造,布鲁克纳在以《第五交响曲》为代表的该类体裁中完成了世俗与宗教的融合,他通过音响效果、宗教素材的运用达到了个性体验。马勒渴望通过交响曲与上帝或者听众建立某种神秘的联系,在这个层级上,音乐和语言是同等的交流工具,音乐的创造者或者演绎者会有效传达某种信息和概念,它是人类思想交流的媒介,言说目的是引起听者的共鸣。音乐是一种特殊的语言,它无法如文学小说般指向具体的事件、过程、结局,而它自成一体的系统、词汇和语法是独一无二的,意义上的能指和所指是绝对具体的。马勒《第二交响曲》的终曲乐章是声音、象征、戏剧集于一体的巨兽,它的叙述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引入和展开以慢节奏为主导;爆发性的发展,意在唤起“死者走向审判的行进”;以及康塔塔式结尾的漫长渐强,合唱和独唱者引领听者进入人性复活的狂喜。马勒最终取消了为交响曲写作的说明,但最后的音乐文本揭示出所有听者需要知道的事情。
第五乐章由合唱、独唱与乐队共同完成的,是全曲规模最大的乐章,往往紧接着第四乐章演奏,无任何打断(folgt ohne jede Unterbrechung der 5.Satz)。乐章开头与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的开头相似,由独唱引入合唱的做法同样是向贝多芬致敬。在人声进入之前,乐队营造出了渐次的阶段性声浪,“谐谑曲的速度、狂野的节奏”是乐章开篇的表情标记,在低音提琴的上行音阶的强力度走句后,乐队在降B音上建立的小三和弦营造出一种不安的情绪,第14小节起的F调长号的四度音程是在找寻,同时呼应了第一乐章的开头。之后的音乐,阶段性进行非常明显,这里的断续比布鲁克纳还要频繁,而当第43小节的五度代替四度之时,圆号那光亮的上行音调似乎找到了一个出口,随之被双簧管弱力度的迂回下降的音型抹杀。随后第51小节,圆号的五度音程又出现,却又消失在不确定的音型进行中。如此浮沉了多次,音乐迷失了方向,在片段式的、跌跌撞撞的找寻中,核心失去了意义。此时,马勒需要找到足以表达音乐的出口和宣示“永生救赎的辉煌境界”的合唱歌词,如同贝多芬在《第九交响曲》终曲以席勒的《欢乐颂》来传达“四海之内皆兄弟”的理想境界。㉖至此,这个恢宏的乐章引导乐曲进入另一个领域,它可以分为器乐的前段与声乐的后段两部分:器乐部分爆发出暴风雨般的效果,体现出20世纪人类在精神和肉体上的痛苦;后段以女高音独唱和合唱为主导,徐缓而庄严地唱出了充满神秘感的18世纪德国诗人弗里德里希·戈特利布·克洛普施托克的《复活节颂歌》。
第289—313 小节多次出现了“末日经”(Dies Irae)主题,它在第一乐章的展开部(第270小节)已经预言过,此时的乐器分配(第289—296小节)由小号代替了长号。这个末日审判和复活的构思一直贯穿于整个乐曲的设想,作曲家在乐曲结尾加强并突出了该话题的思考力度。当复活之音响起,钟鼓齐鸣,庄严的风琴加入乐器和人声的大合唱中时,各色音效融为一体,形成了强大而欢乐的高潮,“复活”信念为人类带来了对未来的美好设想。㉗对“末日经”的采用可以联系历史语境进行理解,它与“悲伤下行四度音列”一样,在器乐作品中的使用可以使听者感受到迥异于音乐进行原本的氛围,并由特定的意义产生关联,唤起某种相关的风格,形成一个特殊性部分。㉘马勒的典型音乐类型体现在进行曲高潮和崩塌后的沉寂(第325 小节)。悲叹的、节奏不规则的旋律后来被女中音定义为一个恐惧的信徒的声音,它缓慢上升,逐渐呈现出更多的内容和形状。突然,它的进程被遥远的游行乐队声音打断。㉙在这一乐章演进将尽时,救赎终于到来,狂喜、宏大的气势照亮了永生的画面,是一种全能之爱照亮了生命。整个乐曲的调性布局形成了意外修辞现象:“c小调—降A 大调—c小调—降D 大调—降E 大调”五个乐章的调性安排的螺旋式上升构成了一个积极的寻找过程,从小调到大调的归宿是乐曲从试探、摸索,到最后找到肯定的答案。作曲家对调性的安排是为了获得想要表达进阶上升的内容的途径之一,人类的心灵可以超越肉体的死亡,在死后继续存在。马勒音乐中的文本和理念能够引起当代人的兴趣,还包括其中高度复杂的情感潜台词,涉及生命和死亡,以及它们如何被聆听者重新驾驭。
在交响曲的结语部分,马勒到达了天国想象,观念得到归纳和提升,通过尖锐搏斗、疯狂扭曲的狂欢,人类最后的栖居之所应是心灵的平静。当灵魂升入天堂,万物皆为美好。贝多芬在《第九交响曲》末乐章加入合唱是对交响曲体裁的一种突破,作为一种体裁修辞,他影响到了身后的作曲家,也使该体裁萌发了浪漫主义色调,拓宽了表达域。贝多芬和马勒相信崇高和灵魂不朽,用音乐赋予人类灵魂以信仰的力量。贝多芬的做法对于传统的交响曲体裁而言是出人意料的,之后,这种方式被顺畅接受——柏辽兹的戏剧交响曲《罗密欧与朱丽叶》,李斯特的《浮士德交响曲》和《但丁交响曲》,马勒的第二、三、四、八号交响曲都加入了合唱。合唱对于纯器乐体裁带来的情感烘托与意义深化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也有很强大的听觉冲击力。㉚这种扩展方式在浪漫主义的“习以为常”恰恰体现了体裁修辞作为一种惯用方法已经为人接受。
马勒《第二交响曲》的最后乐章省略了颂歌中明显和教派有关的诗句,加入他自己的素材,使这一乐章的普遍性信息得到加强。这种做法类似作曲家后期作品探索性的宏大乐章,《第二交响曲》结尾处的升华在《第八交响曲》中获得了更具宗教性的虔敬结局。如果说,《第二交响曲》是个人的、世俗的,那么,《第八交响曲》则是普世的、神圣的。作曲家的谋篇布局体现了文化观念以及19世纪的德奥文化与浪漫主义精神。他使听众产生了联觉与共鸣,改变了受众头脑中固有的联想、态度和观念,达到了万物合一的境界。马勒的交响叙事并非偶然,比如,晚期作品《第八交响曲》和“永恒”与“爱”相关,通过一个音调弥合了9世纪毛鲁斯大主教的拉丁语圣诗《来吧,创造的圣灵》与歌德《浮士德》终场“山谷”的裂痕㉛;《第九交响曲》通过“告别音调”的发展,叙述了一个从“思考尘世的死亡”“丑陋的魔鬼狂舞”到“对天堂的憧憬和到达”一系列进程。马勒参与了死亡崇拜,从而参与了彼得·贾德森所说的哈布斯堡帝国的“文化战争”:马勒属于“奥地利的德国自由主义者”,他创造性地部署了文化符号,从克洛普施托克到歌德,为其思想和审美议程创造了一个文化空间。同时,作曲家由此形成了一个包含“我”并脱离“我”的叙述过程,一切音乐表达终将成为独立的言语和封闭的故事。
汉斯·艾斯勒认为,马勒与舒曼、瓦格纳、理查·施特劳斯代表了传统资产阶级的浪漫主义音乐,他们与革命性的贝多芬不同,他们的创造意义只是为了表达一种个人的、私密的世界观。㉜马勒的音乐在他去世后被忽视了50年的真正原因,并不是作曲的冗长、困难和夸张,而是在他的作品中讨论了人们不想也不愿讨论的事情——死亡。首先,家人的离去、自己的病痛,使马勒离死亡越来越近,这反映在他一贯的作品中;其次,是调性的死亡,对作曲家而言,这意味着他了解和热爱的音乐本身的死亡,对此他无力反驳,被迫欣然接受;最后,也是最重要的观点,就是社会的死亡,浮士德文化的死亡。马勒在他的音乐文本中传达了一切,音符成了信息。时间证明了马勒对理查·施特劳斯的预言“当他的时代结束,我的时代将会到来”㉝。
结语
作品的整体布局、细节构成暗示了文本言说的内容,音乐可以通过声音修辞成就音响叙事,作品的工艺结构、音响结构力与感性结构力共同成就了作品的意义。布克霍尔德认为:“规则是一直变化的,如果规则打破的姿态反复地被使用,那么它就会变成一种惯例。”㉞马勒《第二交响曲》的调性布局、乐章安排、加入声乐均使用了“打破规则”的个性化修辞。《第二交响曲》叙述了一个多元、复杂的故事,音乐的姿态和结构暗含了马勒对于事物和人生的态度,由此作为一个阶段性的叙事方式的起始,在抛弃外在标题之时,音乐可以作为一种语言说出它想说出的言语。交响曲是一种能够精确表达作曲家世界观的体裁,马勒以九部交响曲和一部声乐—交响套曲《大地之歌》重振交响乐辉煌,体现了他对于纯乐队形式、乐队与声乐结合形式的探索。可以说,这些都来源于贝多芬,但对其内涵的解读会更加复杂。事实表明,真正的浪漫主义的绝对音乐作曲家并不等于不懂文学,马勒在作品的结构和情节塑造中找到了非同寻常的灵感,完成了一种极端、反讽和大胆的叙事创新。马勒的事业经历了欧洲文化史上一段独特的时期,音乐家和文学家认为,他们的艺术目标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统一,小说家更多追求创作小说,作曲家从文学的叙事力量角度来构思音乐。从贝多芬到瓦格纳,直到19世纪末,作曲家坚持以一种独特的姿态展示交响曲最后的辉煌和独创性。马勒的技法预示了勋伯格,但形式却终结于此;他和理查·施特劳斯走上了两条不同的路;同西贝柳斯引导了西方音乐未来发展的截然不同的方向。站在这个十字路口,马勒的交响曲一方面回望浪漫主义,一方面指向了未来。
注释:
①马勒最晚在1904年就认识了勋伯格。当时,勋伯格和策姆林斯基邀请马勒参加他们成立的“维也纳创意音乐家协会”,这是他们对维也纳分离派在音乐上的回应。从那时起,这三位作曲家就开始了零星的社交活动,马勒则冒着相当大的风险,不顾评论界的愤怒,公开对年轻同事们的音乐和组织工作表示了支持。
②包括《沃采克》(1925)中酒馆场景怪诞的现实主义(第二幕第四场)和充满感情的后浪漫主义的交响结尾,让人直接想起马勒。
③Constantin Floros,“Mahler and Program Music,”in:Edited by Charles Youmans,Mahler in Context,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21,p.110—112.
④Richard Specht,Gustav Mahler,Berlin:Schuster&Loeffler,1913,p.172.
⑤SLGM,179/GMB2,172.转引自Constantin Floros,“Mahler and Program Music,”in:Edited by Charles Youmans,Mahler in Context,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21,p.117.
⑥帕特里克·麦克雷利斯著,任达敏译:《音乐与修辞》,载托马斯·克里斯坦森编:《剑桥西方音乐理论发展史》,上海音乐出版社,2011,第809页。
⑦Leonard G.Ratner,Classic Music:Expression,Form,and Style,New York:Schirmer Books,1980,p.9.
⑧赵海:《巴洛克时期的“音乐修辞学”及其蕴含的美学理念》,载《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99年第4期,第3页。
⑨王旭青:《基于古典修辞学结构体系的音乐修辞批评研究》,载《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18年第1期,第34页。
⑩[奥]古斯塔夫·马勒著,曹立群、庄加逊译:《亲爱的阿尔玛——马勒给妻子的信》,东方出版社,2011,第80页。
⑪转引自[德]卡尔·达尔豪斯著,刘丹霓译:《绝对音乐观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第132页。
⑫Selected Letters of Gustav Mahler,The original edition by Alma Mahler,Enlarge and edited by Kunt Martner,Faber and Faber,1979,p.362.
⑬韩锺恩:《通过声音修辞成就音响叙事》,载《交响》,2021年第3期,第10页。
⑭ Adler,“Ein Fruendeswort,”in:Stefan.Gustav Mahler,p.3—4.转引自Edited by Charles Youmans,Mahler in Context.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21,p.159.
⑮拉特纳将风格话题分为:军事与狩猎、歌唱风格、华丽风格、法国序曲、风笛曲与田园曲、土耳其音乐、狂飙突进、感伤风格、严格风格、学究风格、幻想曲。
⑯何弦:《音乐与意义的桥梁——莱纳德·拉特纳的“音乐话题理论”及其发展》,载《音乐艺术》,2018年第4期,第156页。
⑰ Der critische Musikus;1736—1745年期间以单独的期号发行的音乐刊物,1745年出版了合集。
⑱同⑦,第7、11页。
⑲同⑥,第827页。
⑳同⑧,第6页。
㉑ Martina Pippal,“Mahler and the Visual Arts of His Time,”in:Edited by Charles Youmans,Mahler in Context,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21,p.140.
㉒ Thomas Peattie,Gustav Mahler's Symphonic Landscape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5,p.1.
㉓ Columbia公司唱片(编号MS7268)封套说明书。转引自钟子林编著:《西方现代音乐概述》,人民音乐出版社,1991,第189页。
㉔ David Osmond-smith,Playing on Words:a Guide to Luciano Berio's Sinfonia,Royal Musical Association London,1985,p.39.
㉕贝里奥(Luciano Berio)著,刘经树译稿:《多个文本的文本》(Text of Texts)。
㉖[英]爱德华·谢克森:《马勒》,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第74页。
㉗徐轶玮、刘昕:《艺术之约·马勒》,山西教育出版社,2015,第92—93页。
㉘刘禹君:《音乐修辞:分析与批评——以布鲁克纳〈第五交响曲〉为例》,载《星海音乐学院学报》,2018年第1期,第37页。
㉙ Marilyn L.McCoy,“Mahler and Modernism,”in:Edited by Charles Youmans,Mahler in Context,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21,p.148.
㉚陈鸿铎:《论音乐分析中的音乐修辞分析》,载《星海音乐学院学报》,2018年第1期,第17页。
㉛即使是最早、最受欢迎的歌德传记之一(由乔治·亨利·路易斯于1855年出版,马勒在一封信中提到过),也认为《浮士德》第二部在诗歌上失败了,因为它在哲学概念上牺牲了语言美。1906年,马勒在他的《第八交响曲》中将其和中世纪赞美诗《来吧,创造的圣灵》(创作者:赫拉巴努斯·毛鲁斯,c.780—856)一起,改变了它的接受史。
㉜ Hanns Eisler,“Über moderne Musik,”in:Materialien zu einer Dialektik der Musik,Ed.Manfred Grabs,Leipzig:Reclam,1973,s.41.
㉝ Gustav Mahler to Alma Mahler,January 31,1902;Gustav Mahler:Letters to His Wife,Ed.Henry-Louis de La Grange and Günther Weiss,in collaboration with Knud Martner,trans.and rev.Antony Beaumont,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5,p.100.
㉞ J.彼得·伯克霍尔德著,陈鸿铎译:《打破规则作为修辞的一个标志》,载《天津音乐学院学报》,2017年第3期,第4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