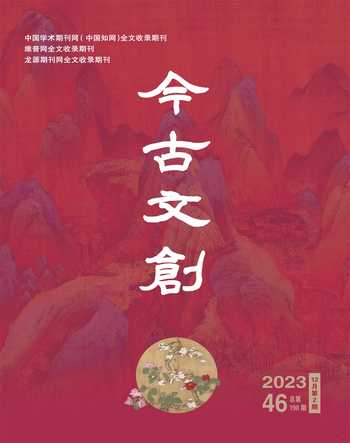浅论国学经典在外译中语义与交际的结合
殷悦莉
【摘要】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国学经典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代表,其翻译与对外传播将对中国提升国际影响力,增强文化自信起巨大推动作用。在国学经典外译的过程中,本文發现当通常意义下侧重语义翻译即“作者第一”的文学作品翻译被置于对外传播的背景下时,译者作为沟通双方的媒介与桥梁,常常需要兼顾语义与交际,国学经典中的深奥的汉字文言从而会经由译者的阐释而渐渐走向显身,同时,由于国学经典独特的文本特点,译者如何基于文本通过创造性叛逆达成语义与交际的双重目标也成了值得思考的问题。《千字文》作为国学的经典之作,极具传播与研究价值。本文以瑞士著名汉学家林小发《千字文》德译本为例,结合纽马克翻译类型理论,期望通过分析译者林小发对国学经典代表作《千字文》的独特处理为后续国学作品外译提供借鉴与参考。
【关键词】国学经典外译;文本类型理论;创造性叛逆
【中图分类号】H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3)46-0118-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3.46.036
一、引言
国学作为中华民族的精神遗产,作为独属中国人的精神文化符号,其包罗万象,蕴含丰富的哲学思辨、历史人文、天文地理知识,铸就了华夏之根、华夏之魂,认识国学、学习国学、传承国学是我们华夏儿女义不容辞的责任。
然而,由于时代,过去中国更多是从西方引进优秀文学作品,相较而言中国国学经典的外译总量并不大;加之国学经典因其自身负载的特定文化而颇具特殊性,国学作品的译者常常需要在语义翻译的基础上兼顾交际的顺畅,即向西方读者阐释中国意象与文化,在这一过程中,精深微言的汉字文言会在译者有意识创造性叛逆的阐释下走向显身,而语义与交际双重目标的叠加则使这一过程极具难度与挑战性,因此高质量外译国学经典要求译者要有深厚的双语文化积累,一时难以为时下兴起的机翻、人工智能所取代。
综上,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欣赏、品鉴现有的优秀国学经典外译本颇具学习与研究价值。本文将围绕家喻户晓的国学经典《千字文》,以备受好评的瑞士翻译家林小发《千字文》德译本为窗口,企图通过向读者展现这部优秀的德译作品,感受国学经典在外译过程中基于其文本类型、特点是如何被阐释并走向白话化的显身,从而希望有助于国学外译研究的进一步研究、借鉴并发展。
二、《千字文》独特价值与对外传播
(一)《千字文》简介与文化价值
《千字文》(以“天地玄黄,宇宙洪荒”开篇)为南北朝时期梁朝周兴嗣所编纂而成,是一千个汉字组成的韵文,句式整齐,全篇由四言、二百五十句构成,且“千字不重”。[1]其文有天文地理(如“日月盈昃”“金生丽水”),又引志怪传说、上古神话(如“珠称夜光”“有虞陶唐”),还含伦理道德、封建纲常(如“恭惟鞠养”“男效才良”),从“天”“地”,讲到季节、自然现象、动植物,人文历史再到人生哲理。文辞精美,对仗工整,以精炼的文字包含了众多传统文化与典故,韵调和谐,朗朗上口,极具文学价值。
此外,其在书法教育史上也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唐代张怀瓘的《书断》与同代的《徐氏书法记》虽在细节上有所分歧,但都认为是武帝取王羲之书法的一千字,并命令周兴嗣将千字编撰成篇。[1][2]因其集书圣王羲之书法而成,且本身千字不重,是极好的临摹练习法帖,也难怪后世历代书法家纷纷临摹。它是书家日课的首选,之后更是被列为古代蒙学之首。
另外,其在漫漫历史长河中除去学术价值艺术价值外,在日常生活中还有很大的应用价值,因其千字不重且都为常用字,所以常用于科场、号舍及民间计簿等等的编次,许多藏书都以千字文编号,如明代文渊阁的藏书,一些大部头的图书如《佛藏》,也往往用千字文编次。[3]
由此可见《千字文》文化内涵之丰,流传与应用范围之广,是中国历史文化长河中不可忽视的一部作品。
(二)《千字文》以德语为译介的传播历程
《千字文》以德语为译介走向海外最早可以追溯到1840年,译者霍夫曼(Johann Joseph Hoffmann)的Das Tsiän Dsü Wen,其与前言中简要考证《千》的来历和语篇特征,译本采用逐句翻译,之后被收录进西博尔德编纂的《日本书目》(Bibliotheca Japonica)第三卷;之后便是1925年汉学家郝爱礼(Erich Hauer)将《千》译成德语,译文发表在当时柏林大学的东亚语言研究期刊中,译者在前言中介绍考证了中国的各式书法字体和起源,译本由三部分组成,分别为编号版本的汉蒙注音对照文本,再是德语译文和作者阐释,最后是对文中部分汉字的考据和解释[4]。
到了21世纪则主要为两个德译版。一为瑞士译者Babara Maag在其个人主页上发布的德译本,译者逐句翻译,并未附加任何注释与考证。[5]二为瑞士汉学家林小发(Eva Lüdi Kong)于在雷克拉姆(Reclam)出版社出版的Der 1000-Zeichen Klassiker,该译本备受好评,《法兰克福报》(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将其纳入“适合圣诞节阅读”的推荐书目。[6]译本由导言、译文与附录三部分构成,导言部分介绍了成书的时间与年代背景,以及作品基本的基本信息;导言与译文间还附有一张1801年的楷书《千字文》书法作品图片;译文部分的编排可谓别出心裁,左页为对应插图,右页由四个纵列组合而成,分别为单个汉字对应翻译、汉语注音、汉语原文、与基于四字句整体的翻译,并且每幅插图下方还附有相关文化专有词的注解;附录部分则包括后记、书法抄本参考文献、汉字索引三部分。汉学家、苏黎世大学教授冬玛柯(Marc Winter)评论说,“该译本既是翻译又是两个阶段的训诂,文本成为一个可读的德语文本,第二阶段以注释的形式提供了对中国古代世界的更深入的洞察。为读者打开了一扇进入一个看似遥远的思想世界的大门,林成功地将一个远离西方读者的主题,诸如中国蒙学,变得可以理解和掌握。”[6]
三、《千字文》文本类型研究与译者创造性叛逆的
实践
(一)《千字文》文本类型与翻译类型的选择
英国著名翻譯理论家纽马克(Peter Newmark)将翻译视为科学与艺术的结合,认为翻译类型的选择取决于这三大因素:一为作者以及译者的交际意图,即翻译目的;二为文本类型;三是读者类型。针对文本类型,他基于三类语言主要功能(分别为:表达功能(expressive function)、信息功能(informative function)和呼唤功能(vocative function))总结归纳出了三大文本类型:表达型文本、信息型文本和呼唤型文本。[7]当然,很少有文本是纯粹的某一种类型,大多数文本是这三种类型的综合,只是有重点的区分。
从翻译目的来看,原文作者文本目的与译者目的有所不同。原本是作为梁武王“以教诸王”(《书断》)“以赐八王”(《徐氏书法记》)用于进行书法教育的范本[8]。后世则因其文采绝妙,内涵丰富,朗朗上口且音节数量少故便于儿童以之为训练材料学语发声而成了经典的蒙学教材。译者林小发显然也关注到了这一点,她在前言中便指出其为最早的蒙学教材且跨越千年其价值依旧不减(“Das Besondere am Tausend-Zeichen-Klassiker ist, dass es sich um die älteste Grundschulfibel handelt, die über nahezu eineinhalb Jahrtausende unverändert erhalten blieb und kontinuierlich gelehrt wurde. Spätestens seit dem 11. Jahrhundert war dieser Text Pflichtlektüre für jeden Grundschulunterricht.”);而译者将此类经典翻译并引入西方是为了向西方介绍中华文化,正如她在接受采访时所说的“尝试为中国和欧洲之间的文化交流搭一个桥梁”。[9]
其次,从读者类型来看,她面对的是对纲常观念文化知识有较强的疏离感的、对中国传统文化和世界观的陌生的外国读者,译者作为沟通的桥梁时应当肩负起部分“教师”的职责,面向海外进行作品的讲解,引导并帮助其构建中华文化知识背景网。国学经典本身对当代中国普通大众而言也非浅显通俗,在海外传播过程中更是需要综合各种知识背景为读者搭好通向各个传统知识区块的链接,这对译者来说是一份额外的工作量,但是也正是由于《千字文》之包罗万象,它才更能够提供更为广博的视野,更能够成为海外读者了解中华文化的窗口。
然后是文本特点,《千字文》作为国学经典,虽是由当时的常见字所编撰而成,但由于历时久远,中外读者对其的理解都隔着文言文与白话文词义上的横沟;且基于文言文本身的特点,常常是于简练一字中融汇了多重含义。因此,对《千字文》此类古代经典个别词义的精准理解、阐释与说明是十分必要的。笔者会在后文继续展开探讨译者林小发的处理方式。
综上,笔者认为,基于作品本身启蒙教育,译者对借此促进中欧交流的希望以及其文本特点,译者对《千字文》的翻译不能像对待大多数文学作品一般遵循“作者第一”的原则进行表达型文本式的语义翻译——它也应当关注与读者的交互是否到位,也要着重“读者第一”的呼唤型文本式的交际翻译,这也恰好与译者林小发采取的方式相契合,正如她所说的“最大的挑战是,如何将充满画面感而又搭配紧凑的文言文翻译成逻辑严密、精确详尽的现代德语”。[9]笔者认为,国学经典的外译要兼具原文的风格与美感又要将深赜的文言文进行白话化的阐释,让美感与易懂并驾齐驱,这是对译者的重大挑战。
(二)译者基于《千字文》文本特点的翻译实践
从林译《千字文》前言部分我们不难发现译者对《千字文》文本特色的清晰体认,译者也在其中点出了其文本的一大特色——字即意象,字与字能构成生动的画面,四字成句则能构成一段简短的叙事,且常常融汇大量典故(《千字文》用典颇多,全文1000字,光是典故便有63处,而对于典故的阐释则对于读者体认中国文化与意境而言颇为重要)。[10]
综观全篇,《千字文》字句之间彼此勾连,内涵机理,共同构成特定的文化内涵,因此,单纯的逐字直译并无法贴切展现以句为单位构建的文化图景,会显出词不达意的缺陷,比如前有译者Bauer采取直译策略,以开篇为例Bauer将“天地玄黄,宇宙洪荒”二句译为“Der Himmel, die Erde; ersterer düster, letzere gelb. Raum und Zeit, gewaltig aber brachliegend. “该译者试图遵循对原文的忠实,却无法对不具备东方文化思维与背景的外国读者精准传达意义。原文所描绘的是一种无边无际、混沌蒙昧的远古时代,是人类的起源。西方读者普遍接触的是《圣经》的《创世纪》,因此普通读者恐怕难以通过“暗沉的天”“黄色的地”“巨大的空间”“荒芜的时间”此类的简单表达而在脑海中用这些分离的、失去文化勾连的元素组合出东方世界宇宙与人类的起源;此外,他们更无从得知作者此句是对《易经》“天玄而地黄”的化用;他们也无法理解汉语文字多重的引申与象征意蕴,如“玄”在汉语中除去黑色之外试图营造出的悠远而深不可测的意境,直译反而丧失了对原文的忠实。
而译者林小发基于对原文文本特点的分析,则选择了对原文的文言四字句采取归化的翻译策略,并使用意译、仿译等翻译方法,正如她在前言中提及的“... wird im Deutschen jedes Schriftzeichen zu einer kurzen Verszeile ausgeführt”,她将每一个汉字都对应译成一行德文诗句,将每个四字句拓展连成一段德文四行诗。[11]其使用的解释法或者说释义法(Paraphrase)是的文言文走向白话化,便于读者正确理解,十分贴合译者翻译的目的,此外,译者还增添了直译的单个德文词翻译版本供读者参考,使译本兼具信达雅。在翻译过程中,译者林小发也灵活地调用了各种翻译技巧,如:增译、分译、转换等等。以下将以增译(amplification)与转换(shift)法的结合运用为重点,节取译文片段鉴赏译者林小发的创造性叛逆实践。
增译即指根据原文上下文语义、逻辑关系以及译文语言的句法特点和表达习惯,在翻译时增加原文字面没有出现但实际内容已包含的词、句或段落。主要是用于清晰表达、语法需要、使音韵整和或是用以增添文化背景知识等等。转换即把原文的语言单位或结构转化为目的语中具有类似、对应或异质属性的语言单位或结构的过程,如语义层面由具体到概略的转换等等。
林译《千字文》为打破文化壁垒,是将字拓成句,在此过程中通过对原文本进行灵活的增添和转换,从而使东方文化和意蕴在现代化文字中走向外显。以“律吕调阳”为例,“律吕”指的其实是律管和吕管中国古代用来校定音准的一种设备,类似于现代的定音器,古代将一个八度分为十二个半音,有低至高每半个音为一律,奇数律称作“律”,偶数律称作“吕”,因此十二律由“六律”“六吕”组成,简称“律吕”,相传黄帝时伶伦制乐,用十二根竹管作为律吕音管,由于竹管空心,里面可以灌满用苇子膜烧成的灰,即暇莩,如此埋入西北阴山,便可候地气,感受地下阴阳的变化,如冬至时,阳气生,第一根竹管的灰飞出伴有声音(称为黄钟),由此其声音可以用于定时间,律历合一,对照月份调阴阳变化。因此在单字直译列中,译者林小发便指明“律”为“六律”(6 Ganztöne),“吕”为“六吕”(6 Halbtöne),在四字句翻译列中译者林小发增添了文化背景,将物“律吕”拓展并转换为古代“律历合一”的传统文化,她写道十二个月份对应十二个乐音“Zu den zwölf Monden Passen zwölf Töne”。[11]其实是对中国传统天文律法的阐释,且在右页加以注释将其文化内涵更为深入地展开;面对“调阳”,她也敏锐地关注到并非只是“调和阳气”,而是“协调阴阳”。如此必要的增补与转换,明晰的阐释,就算是部分对中华传统一无所知的读者也能在这种增补中达成较为精准的理解。
四、结语
正如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所言“翻译始终是解释的过程,是翻译者对先给予他的语词所进行的解释过程”,国学经典走向海外将对中国走向世界,增强文化自信发挥重大作用,而其传播必然依赖翻译者,于是便走向了伽达默尔所提出的“谈话双重化”,一方面是翻译者同对方的谈话,另一方面是自己同翻译者的谈话。[12]国学经典译文是用于向外彰显中华文化之美的,故其应当兼备原文的形神,同时,它是用于传播推广,走向世界,走向大众的,因此其译文也必然包含一定的阐释,如此,其含义意蕴也将由深奥的汉字文言到通俗易懂的白话现代语,在如此阐释中走向显身。兼具语义与交际即原文意蕴美感与交际传播之便,是国学经典翻译传播的难点,而林译《千字文》却凭借译者的深厚文化底蕴、文学素养、精心的编排组合与注解将这双重追求较为完美地结合为一体进行展现,这给予了后世对国学经典的翻译、出版重大借鉴意义与参考价值。
参考文献:
[1]李绰.尚书故实(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O].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2]张彦远.法书要录[O].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86.
[3]徐梓.《千字文》的流傳及其影响[J].中国典籍与文化,1998,(02).
[4]刘明远. 《千字文》百年西译史与中国文化走出去[J].宜春学院学报,2022,44(07).
[5]Babara Maag.http://www.barbara-maag.de/Qianziwen.htm.[E].2021.
[6]刘明远,徐群.《千字文》的德语译介与中华文化对外传播[J].牡丹江教育学院学报,2023,(02).
[7]Newmark.Text Book of Translation[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1.
[8]史湘萍.《千字文》研究[D].东北师范大学,2012.
[9]余靖静.一位瑞士女汉学家的“取经路”[N].新华每日电讯,2019-02-25.
[10]辛志凤.蒙学教材《千字文》的用韵与用典[J].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04).
[11]Eva Lüdi Kong.Qianziwen:Der 1000-Zeichen-Klassiker[M].Stuttgart:Reclam,2018.
[12]迦达默尔.真理与方法[M].洪汉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