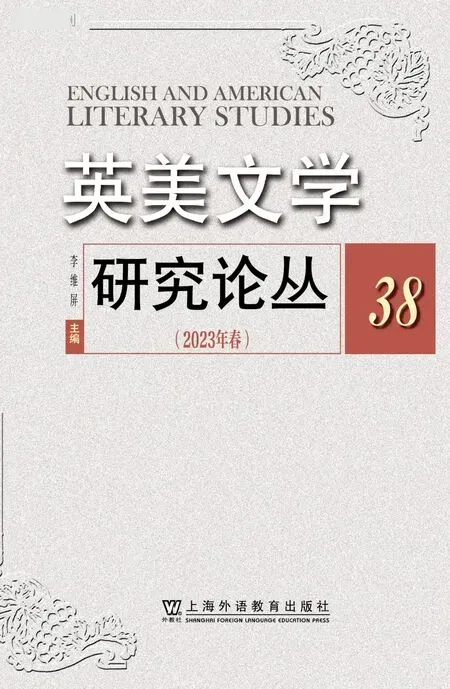创伤记忆与“伪文献”
——多克托罗《但以理书》中罗森堡间谍案的文学再现和历史反思*
王弋璇
内容提要: 20世纪50年代的罗森堡案件对美国冷战时期的政治生态带来了深远影响。许多美国作家着墨于这件富有争议性的事件,意图通过文学再现透视官方叙事。多克托罗作为一名“激进的犹太人文主义者”,通过其含混的文学语言表达了他对事件独特深刻的反思。论文指出,作为“创伤小说”的《但以理书》从“老左派”和“新左派”两代人的创伤记忆入手,巧妙融合历史真实与想象构思,聚焦、放大事件内在的精神脉络,指明语言的“伪文献”实质及其所具有的双重力量:“自由力量”和“政权力量”,进而证明多克托罗的所秉持的观点: 小说不仅和政治相关也具有艺术复杂性。而作家的文学再现成为干扰或者拆解其中“政权力量”,进而解构美国神话的手段,给读者带来深刻的历史反思。
1949年,因为酗酒、赌博和投机交易而声望一落千丈的美国国会参议员约瑟夫·雷蒙德·麦卡锡(Joseph Raymond McCarthy,1908—1957)为了保住他在国会的位置,于1950年2月发表了《政府内部的敌人》(“Enemies from Within”)的演说,声称他掌握着一份共产党和间谍网的205人名单。这篇演说无异于扔下了一颗原子弹,在美国政界、外交界和其他部门煽起了一场来势汹汹的反共浪潮,接着又波及全国,带来了一场全国性的反共“十字军运动”,历史上被称为“麦卡锡主义”(McCarthyism)。麦卡锡主义发生在美国20世纪50年代初,是一场政治上被极右势力操控的反共、反民主的政治运动,带来了社会动荡和法西斯主义抬头。罗森堡案件正是这一政治背景所衍生出的具有争议性的法律和历史事件。而历史是文学的基础,文学是历史的升华,本文采用历史视角,通过对再现罗森堡案件的文学作品《但以理书》(The Book of Daniel,1971)的分析,展现案件所带来的创伤记忆及作家人文主义理念下的批判意识和历史反思。
一、“麦卡锡主义”与罗森堡案件
1939年,麦卡锡通过虚报年龄参加了区巡回法庭的竞选,成为区法院的法官,他充满欺骗与谎言的政治生涯由此开启。1946年11月,他通过大肆渲染自己在军队的经历,迷惑选民,当选了威斯康星州参议员。麦卡锡担任参议员期间,滥用职权,大肆进行投机交易,加之他还有赌博和酗酒的恶习,人们渐渐了解到这位演讲时慷慨激昂的政客的另一面,由此麦卡锡的声望一落千丈。1949年秋,麦卡锡竟然公开站在屠杀美国士兵的纳粹党徒一边,为他们的罪行辩护,公众舆论为之哗然,麦卡锡民意尽失,被评为当年“最糟糕参议员”。意识到自己的政治地位岌岌可危的麦卡锡迫切需要一根“救命稻草”帮他保住在参议院的位置。经过策划,他决定在美国总统林肯的诞辰年纪念日(1950年2月9日)那一天发表具有“轰动效应”的演说,即后来他在西弗吉尼亚州惠灵市发表的演讲《政府内部的敌人》。其中,麦卡锡泾渭分明地将西方世界同共产主义世界对立起来:“西方基督教世界同无神论的共产主义世界的最大区别并非政治方面的,而是道德观上的。[……]然而,真正和最基本的区别在于[……]由马克思发明、被列宁发展至狂热并被斯大林推向难以想象极致程度的非道德主义(immoralism)。”他这时公然宣称,手中掌握“一份205人的名单”,“这些人全都是共产党和间谍网的成员”,而且,“国务卿知道名单上这些人都是共产党员,但这些人至今仍在草拟和制定国务院的政策。”①参见http://historymatters.gmu.edu/d/6456(2019-8-2)。麦卡锡演说之后,美国上下一片哗然。之前一直谨小慎微的小人物麦卡锡一夜之间成为全美政治明星。他接着组织了麦卡锡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发动了对美国国务院、国防部等要害部门的大清查。由此,麦卡锡主义在20世纪50年代初盛行于美国,美国政界出现一股极端反共、反民主的逆流,造成风声鹤唳、人心惶惶的政治氛围,历史上将这种气氛称为“红色恐慌”。
“在这种‘恐红’、反共氛围下,麦卡锡和麦卡锡主义的出现不是一种偶然现象”(金衡山等72),美国政府彻查了所有美国社会可能潜藏的间谍活动。罗森堡案(The Rosenberg Case)浮出水面,并在美国进而在国际社会引起了极大的关注。美国国内及国际社会一部分人都认为罗森堡夫妇(Julius Rosenberg,1918—1953;Ethel Rosenberg,1915—1953)无罪,请求政府对他们宽大处理,并组织了抗议活动。国内外的自由人士大多认为以罗森堡夫妇的政治观点作为证据来判决死刑的做法是对法律尊严和公民自由权的极大挑战。为此,很多社会名流也纷纷为罗森堡夫妇鸣不平,其中就包括科学家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1879—1955)。1953年1月,爱因斯坦写信给美国总统德怀特·戴维·艾森豪威尔(Dwight David Eisenhower,1890—1969),在信中他写道: 出于良心驱使,我请求您减轻对罗森堡夫妇的刑罚,免除死刑。然而,抗议浪潮没能阻止罗森堡夫妇免于死刑。1953年6月19日,罗森堡夫妇被执行电刑。他们从始至终始终不认罪,无论官方如何威逼利诱,只要认罪就可以免于死刑。但信念和信仰让他们慷慨赴死。罗森堡夫妇死后,美国国内的麦卡锡主义达到了高潮,他们的亲戚担心遭到反共人士的报复,都不敢收留夫妇俩的两个孩子。“罗森堡案作为冷战初期最为引人注目的案件之一,从一个独特的视角揭示出冷战意识形态在当时美国政治社会中所占据的主导地位,对于我们理解这一时期美国的政治文化和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具有重要意义”(李昀123)。这场饱受争议的案件和人间悲剧成为本文用来投射美国20世纪50年代状况的一面镜子。
二、多克托罗与《但以理书》
文学与历史互鉴,成为彼此的关照,文学叙事和历史记录以不同的方式为后人带来深刻的启示。对于罗森堡案件聚焦关注,并以小说的形式进行文学再现的作品很多,而E.L.多克托罗的(Edgar Lawrence Doctorow,1931—2015)的《但以理书》堪称其中具有代表意义并对美国文化进行深刻反思的力作。
多克托罗是20世纪美国文学领域的重要人物,他的创作以历史小说著称,被誉为20世纪最重要的小说家之一。他1931年出生于纽约布朗克斯的俄罗斯犹太移民知识分子家庭,家里浓厚的艺术气氛让多克托罗爱上写作,他的名字——埃德加·劳伦斯·多克托罗来自作家儿时所仰慕的作家埃德加·爱伦·坡(Edgar Allan Poe,1809—1849)。多克托罗作品创作题材丰富而深刻,其犹太身份和对创伤历史的深入分析使得他的创作独具一格,虽有晦涩难懂之处,却能引领读者进入精神反思的曲径通幽处,多克托罗善于描写特定历史时期下美国民众面对挫折、创伤和剧变的心理状态,作品中蕴含着对民权运动的关注,他创作丰富,成为诺贝尔文学奖的热门人选,共发表12部长篇小说和3部短篇小说集。其中为他奠定当代美国文学大师的地位的是其代表作《但以理书》(The Book of Daniel,1971)、《拉格泰姆时代》(Ragtime,1975)、《比利·巴思盖特》(Billy Bathgate,1989)和《大进军》(The March,2005),这些佳作连同其他长篇小说①比如《欢迎?来到艰难时代》(Welcome to Hard Times,1960)、《大如生命》(Big As Life,1966)、《潜鸟湖》(Loon Lake,1980)、《世界博览会》(World's Fair,1985)、《供水装置》(The Waterworks,1994)、《上帝之城》(City of God,2000)、《霍默与兰利》(又译《纽约兄弟》)(Homer&Langley,2009)、《安德鲁的大脑》(Andrew's Brain,2014)等。以及数部短篇小说集一起构成了多克托罗创作的万花筒,从中人们可以看到美国社会光怪陆离的表象背后的精神内核,并使他获得了包括全国书评家协会奖、美国国家图书奖、国家人文科学奖、笔会/福克纳奖、美国艺术与文学院豪厄尔斯奖、美国小说国会图书奖等众多重要奖项,成为美国文坛备受尊重的犹太作家。
道格拉斯·福勒(Douglas Fowler)在《理解E.L.多克托罗》(Understanding E.L.Doctorow,1992)中指出,多克托罗的小说是典型的历史小说,覆盖了美国自内战以来的所有历史阶段(Fowler 5)。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1934—)在《后现代主义,或者晚近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Postmodernism,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1991)一书中提到,“E.L.多克托罗是个诗人,用史诗描绘了美国的激进过去如何逝去,也描绘了美国激进传统背后更为久远的传统和时代带给他们的压抑和抑制”(Jameson 24)。多克托罗的创作以纽约等城市为背景,“将人物置于特殊的城市空间,描摹世事,品味人生,字里行间可见现实主义的细腻逼真,……在多种元素和不同风格的杂糅和融合之中,描写反映当代美国都市生活的多侧面,通过小说的虚构性折射真实社会,对历史和现实生活进行富有哲理的思考”(虞建华2017a:1)。约翰·帕克斯(John Parks)在他的著作《E.L.多克托罗》(E.L.Doctorow,1991)中反对给多克托罗贴上“政治小说家”的标签,认为这样的归类对一名伟大的历史小说家而言,不仅简单化,而且有误导,好像这个作家只是在推动或贩卖某种意识形态。这样的标签“对多克托罗的小说是一种贬低和损害”(Parks 11)。
多克托罗用敏锐、犀利和深刻且更具人文主义情怀的目光,聚焦罗森堡案件,透视事件背后的美国文化肌理,引导美国民众对事件抱有深刻反思的态度。多克托罗本人更希望以“激进的犹太人文主义者”(radical Jewish humanist writer)①多克托罗将自己定位为“激进的犹太人文主义者”,并以此为荣。他曾对一名采访者说过:“如果我不属于这个传统,那我一定要申请加入它”(转引自Fowler 1)。对于什么是“激进的犹太人文主义”这一问题,作家在访谈中解释为其“本质是从正统的犹太教义中发现弊端。你拥护那种文化,珍视那段历史,但拒绝那种神学。弗洛伊德和卡夫卡就属于这种传统,还有爱因斯坦,以及伟大的批评家本雅明,等等。在美国,其代表人物为无政府共产主义运动领袖爱玛·戈尔德曼和诗人金斯伯格”(陈俊松88)。来定位自己。国内外评论者也从这个角度对多克托罗继承犹太文化传统背景下的人文主义思想进行了分析(Clayton 1993;金衡山等2017;李俊丽2008)。作为犹太民族的文化战士,多克托罗的作品充满了政治批判意识。他在访谈中说道,“无论何时,当我开始讨论政治的时候,我总是被政治牵引过去。我不太喜欢用那些政治化的陈词滥调,那让我感到窒息”(转引自森森)。多克托罗作品中的少见“政治化的陈词滥调”,他的政治意识是用史诗般的叙述进行表达的。他描绘美国冷战时期的精神荒野景象,在政治批判中融入强烈的人文主义批判意识。
多克托罗这位“犹太人文主义”战士,秉承欧美现实主义文学传统,认为文学创作同社会生活息息相关。他说,“我从来都认为我的小说继承了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1812—1870)、维克多·雨果(Victor-Marie Hugo,1802—1885)、西奥多·德莱塞(Theodore Dreiser,1871—1945)和杰克·伦敦(Jack London,1876—1916)等大师的社会小说传统。这个传统深入外部世界,并不局限于反映个人生活,不是与世隔绝,而是力图表现一个社会。”他继而嘲讽说,“近年来,小说进入家庭,关在门内,仿佛户外没有街道、公路和城镇”(转引自叶子145)。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多克托罗在创作之初就带有鲜明的批判意识,很多作品涉及冷战中美国的社会心态。“‘冷战思维’不等同于‘冷战’。它隐藏在背后,流行于无形,既无处不在,又难以捉摸,是一种观看问题的框架,一种逻辑模式,一种政治无意识”(虞建华2017b:3)。多克托罗剑指冷战这段历史时期下蕴藏在美国“文化精神”中的冷战思维和“非我即敌”的冷战意识,对这种思维定式进行了揭示和批判。
《但以理书》是多克托罗的第三部小说,被誉为美国当代最优秀的政治小说,并获得1972年国家图书奖提名和1973年古根海姆奖。作为纽约出生和成长的第三代俄国移民,多克托罗深受犹太文化的影响,作品中浸润着宗教思想和对真善美的追求。小说书名来自《圣经》中的《但以理书》卷①《圣经》旧约全书中该卷据传由但以理(Daniel,625 BCE—530 BCE)本人所写,其名意为“神是我的审判”。但以理生于耶路撒冷,公元前605年被掳到巴比伦,改名为伯提沙撒,意思是“王的保护者”,他因才能出众在巴比伦受到重用。但以理具备先知的能力,能为国王解梦,被提升为巴比伦省长兼国家总理,管理巴比伦一切的哲士。但以理的一生对上帝顺服忠诚,教导犹太人在被迫害流放中也要坚守对上帝的信仰。,小说故事由此同圣经形成互文关系。小说以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为背景,其中也穿插叙述了发生在四五十年代的事情。作品以罗森堡夫妇为历史原型,再现了这段被“红色恐怖”毒雾笼罩的历史:
在麦卡锡时代歇斯底里的政治氛围中,小说主人公但以理的父母被指控犯有间谍罪,双双被送上电椅。成为孤儿的他带着妹妹生活,不得不承受巨大的心理创伤,在都市漫游中既希望找出真相,替父申冤,也试图逃避现实,寻找抚平创伤的慰藉。漫游的过程是他不断矫正自身的异化、走出阴影的过程,最后努力与自己、他人和社会达成了某种程度的和解。(虞建华2017a:2—3)小说将历史中罗森堡夫妇的两个儿子化身为但以理兄妹,他们同样在幼年遭受重创,一生都在挣扎着摆脱创伤记忆,走向“和解”。而作为具有宗教情怀的后现代犹太小说家,多克托罗“有着一双饱含忧郁的眼睛,骨子里都对人类的命运和前途有着浓重的忧患意识”(斯巴格22)。他在小说中贯彻了作为一名“激进的犹太人文主义者”的立场,继承同时也批判犹太文化传统,秉承正义、善良和诚实的宗教理念,用后现代的写作手法刻画现实,揭露精神危机下的人间百态,反思在信仰危机时代信仰存在的意义,为作品注入了深刻的人文主义价值。《但以理书》以其现实关怀和丰富的思想内涵,被视为多克托罗的代表作。小说透过对罗森堡间谍案受害者家庭的虚构书写,重访历史,再现历史,进而透视出冷战时期美国国家意识形态对个体带来的创伤。
三、“伪文献”: 《但以理书》创伤记忆
多克托罗曾强调,“小说家在离群索居状态下会将自己一分为二,成为创造者和记录者、述说者和聆听者,协力将集体智慧以自己的语言传递出来,掩盖其对现实世界富有启迪性的先入之见”(Doctorow 1983:21)。作家以这种设身处地的方式进入他人的生活情境,同描写对象建立认同,并将认同的情感传递给读者,就更能激发共鸣。小说《但以理书》围绕艾萨克森夫妇(影射现实中的罗森堡夫妇)子女的生活展开叙述,视角在现在和过去之间切换,不仅呈现了案件的直接后果,也表现出其带来的长远影响。虚构的艾萨克森夫妇的儿子与真实人物是有反差的,但很好地服务于小说叙事试图反映的更加广泛的主题,另外,小说的主人公与历史事件中的罗森堡夫妇的两个儿子有所不同,小说的主人公是一对兄妹,名叫但以理和苏珊。但以理背负着为父母申冤的巨大精神压力,无法逃脱创伤记忆的折磨,生活痛苦不堪;苏珊则有自杀倾向,难以摆脱抑郁的精神状态。作者这样的艺术改写,加强了事件带来的创伤程度,表达了对冷战意识下极权政治更为强烈的控诉。“多克托罗希望将但以理的时代同他父母时代中的左翼思想进行对比。备受折磨的但以理和苏珊一起卷入了反越战运动,他们甚至建立了自己的革命基金会,用来纪念被杀死的父母”(Freedland vii)。多克托罗的叙述语气看似平静而散漫,从一个时代跳跃到另一个时代,但叙述背后始终涌动着强烈的情绪和政治反抗的力量: 创伤记忆带来的痛楚、意识形态被压制的愤懑和对强权反抗的意愿及冲动。
评论界一般把《但以理书》看作一部编史元小说(historiographic metafiction)。根据琳达·哈钦(Linda Hutcheon,1947—)的定义,“编史元小说”指“既具有强烈的自我指涉性,又自相矛盾地宣称与历史事件和人物有关”的后现代创作(Hutcheon 5)。因此可以说,编史元小说包含两个元素,即“自我指涉性”和“与历史事件和人物”的相关性,两者是带有矛盾性的结合。前者针对的是文学传统本身,对小说的虚构传统进行了反思;后者指向历史记载的传统,也就是将小说虚构同历史书写并置起来,以此揭示出两者存在的共同的语言建构本质。编史元小说是后现代小说的一种,其理念在于不赞成对过去投射当下的信仰和标准,同时暗示了“事件”和“事实”之间的鸿沟。
《但以理书》将罗森堡案件这一真实的历史事件融入作家的个人想象,塑造了但以理这一特殊人物,凸显事件对下一代造成的持久创伤。但以理“被他未曾目击的事件——父母被国家以叛国罪电刑处死,更宽泛地讲,被他自己错过的感知所纠缠。这一错过的感知时刻在创伤叙事中反复出现,造成目击过去事件的可能性”(陈世丹、张红岩23)。小说叙述穿插在过去和现在之间,历史成为主人公脑海中挥之不去的创伤记忆。作品两次呈现了1967年美国阵亡将士纪念日(通常为五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一)的情景,形成了时间上相互呼应(Doctorow 2006:3,67)的叙事。第一次的时间描写的是但以理去医院看望苏珊的情景,这是一个“塔楼形、黄砖建造的公立医院,这里收治的是精神病患”(同上6),苏珊就在这里就诊,她状况极差,身形消瘦,精神麻木,看到妹妹的但以理难掩悲愤,发出了对“他们”的控诉:“啊,苏珊,我的小苏珊,你做了什么,你就这么容易受国际道德宣传机构的哄骗吗!他们把你塑造成为道德瘾君子,扯坏你的头发,夺去你的老奶奶眼镜,还让你穿上病号睡袍。哦,看看他们对你做了什么,苏珊,看看他们对你做了什么!”(Doctorow 1971:12)小说在开场将“他们”作为主人公剑指的控诉对象。那么“他们”是谁的问题也成为吸引读者深入阅读的一条主线。而“对于但以理及他的志同道合者而言,这是个艰难的时代,因为他们在充满敌意的环境下只能是二等公民”(同上13)。医院的压抑场景和人物的悲愤情绪凸显了罗森堡案件给冷战时期的两代人带来的深刻创伤。
真实的历史中,罗森堡夫妇被判处死刑后,他们的两个年幼的儿子罗伯特和迈克尔,在父母行刑前站在辛辛监狱的高墙外,举着“请不要杀死我的爸爸和妈妈”的牌子,希望为父母争取一线生机。当时,外界声援罗森堡夫妇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甚至爱因斯坦等名人纷纷出面为赦免罗森堡夫妇呼吁,一些美国著名律师也全力支持他们先后六次向美国高等法院上诉,但最终,上诉一次次被无情驳回,所有的努力都无济于事。虽然当局告知罗森堡夫妇只要认罪就可以免除死刑,但是,罗森堡夫妇宁死不屈,拒不认罪,慷慨赴死。这桩历史上的争议审判带来的持续影响令美国官方始料未及。
而不幸事件给罗森堡夫妇的两个儿子带来了最直接的影响,创伤阴影致使他们一生都无法完全卸下记忆的重压。他们生活在养父母家中,童年在担惊受怕中度过,为免受进一步的迫害隐姓埋名。成人后他们始终坚持为父母的冤情奔走。兄弟二人为纪念父母撰写了自传《我们是你们的孩子: 艾瑟尔与朱利叶斯·罗森堡的遗产》(We Are Your Sons:The Legacy of Ethel and Julius Rosenberg,1975)。哥哥罗伯特还写了另一本书《父母死刑: 一个儿子的旅程》(An Execution in the Family:One Son's Journey,2004)。为了帮助更多有类似经历的孩子,他创立了罗森堡儿童基金(The Rosenberg Fund for Children,RFC)①罗森堡儿童基金是一个非营利的公共基金,由罗森堡夫妇的儿子罗伯特创立,旨在为美国进步激进主义者的子女提供资助,同时也帮助由于自己参加了进步基金活动而受到指控的青年。。正是这些亲历者对创伤往事的回忆,激起了怀有正义感的人文主义作家的共鸣。他们执笔创作出的一批作品,成为构成重建美国五六十年代文化记忆的一部分。《但以理书》是其中富有代表性且反思极其深刻的一部。
多克托罗生活在冷战时期,他目睹了冷战对人们思维方式带来的影响,作家希望了解在这样的氛围中的人们的思想状况。正是在这样的动机下,他开始着手《但以理书》的创作。小说一开始,主人公但以理去医院看望妹妹苏珊,医院里冷凝压抑的气氛和苏珊几近崩溃的状态直接让读者感受到了冷战的社会氛围及其带来的影响。
小说《但以理书》戏仿了真实案件对后代带来创伤性影响这一主线。小说中的兄妹同真实历史中受害者的后代一样,一生无法摆脱父母被电刑处死这一事件的影响,但小说人物的生活更加潦倒。妹妹苏珊被创伤记忆折磨精神失常被送进精神病院接受治疗,最后用自杀的方式结束了年轻的生命。但以理则被过去记忆的梦魇折磨,变得行为异常,甚至虐待妻儿,难以享受正常的家庭生活和平静的精神世界。他自述道,“苏珊和我,我们是仅剩的人。所有的生活都是试图逃离亲人,我在逃离的过程中思绪繁杂,但不管什么样的方式,他们都是你遇到生命转角的际遇”(Doctorow 2006:37)。
但以理年幼时曾目睹了一场事故,他在叙述中呈现了事故后惨烈的情景: 满地破碎的玻璃片,牛奶和妇女的鲜血混合在一起。交通事故的记忆,使他的创伤想象具体化,将未曾亲眼看见的恐怖的极刑场面重现于脑海中,成为挥之不去的噩梦。多克托罗在小说中对第二代的心理创伤进行了戏剧化的演绎,浓缩了苦难,用略带夸张的描写凸显人物行为背后的扭曲心理,“增强了冷战期间美国国内紧张的恐怖气氛,突出了‘红色恐怖’给他们带来的严重的心理创伤,更加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冷战期间人们极端歇斯底里的情绪。让人们深刻意识到‘红色恐怖’和麦卡锡主义的罪恶及这种极端思想给人们带来的伤害”(胡选恩、胡哲156)。
多克托罗在一篇题为《伪文献》(“False Document”)①该文收录在多克托罗的评论文集《杰克·伦敦、海明威及美国宪法》(Jack London,Hemingway and the Constitution:Selected Essays,1977—1992)中。的论文中指出,“当然每部小说都是伪文献,因为它是辞藻的合成品而非生活。但是我特指的是小说家创造性否定的行为,他借此提供的文本出现了额外的权威性,因为他并无意于书写的权威,他宣告书写权威是不可能的”(Doctorow 1983:20)。小说《但以理书》以超越意识形态疆界的深刻反思意识,将批判和抗议的靶子直指冷战时期美国政治话语的虚构性。从语言作为叙事媒介的角度出发,提出了“语言具有两种相互对立和统一的力量: 一个是政权的力量(power of regime),另一个是自由的力量(power of freedom)”,他认为,“政权的力量就是语言对客观世界所具有的反映功能”(同上16—17),而“自由力量是存在于个人或理想的世界里,具有表现想象的力量。语言的这种力量是不能为人所证实的,因而也是自由的,它是为小说家和诗人服务的”(多克托罗、胡选恩223)。前者的功能是指定性的,后者则具有联想功能。多克托罗强调说,历史话语和文学话语都无法将作者直接带入过去的历史中,读者只有以文本为媒介接触历史事实。在多克托罗看来,“小说不完全是理性的话语方式。它给读者提供了超过信息的东西。复杂的理解,不直接、本能的和非言语所表达的思想都通过作者和读者之间仪式性的互动,从故事的言语中生发出来”(Doctorow 1983:16)。
多克托罗从语言的使用角度出发,探索和发现作用于语言背后的权力关系,并以此为依据对历史及历史编纂的真实性提出质疑。“历史带有虚构性,我们生活于其中并寄希望于继续生存下去。小说属于推测性的历史,或许可称作超级历史,构建超级历史所用的素材要比历史学家们所认为的更具有丰富性和多样性”(Doctorow 1993:162)。多克托罗在此提出了他著名的“作为‘超级历史’的小说”的概念。他同琳达·哈钦的观点异曲同工,共同起底历史背后的权力关系,揭露历史的虚构性。
小说《但以理书》切换在但以理父母亲生活的20世纪四五十年代和但以理生活的60年代两个时间段之间,揭示二战后和麦卡锡主义盛行的年代笼罩在美国的“红色恐怖”、被冷战思维破坏的家庭关系和人物支离破碎的内心世界。小说着重描写了兄妹二人的心路历程。但以理在阴影下艰难成长,成为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研究生,但他性格上的缺陷也显而易见。在一次出行的路上,他以80多英里的高速行驶汽车,当着自己孩子的面虐待妻子,情绪失控。小说还反映了阶级地位差异带来的不公平,我们从书中看到了艾萨克森家族生活的贫困,他们住在布鲁克斯的家里(Freedland ix)。我们从中看到了家族对阶层不公的愤怒情绪乃至于多克托罗对书中人物的同情。小说的场景切换也让读者应接不暇,从冷战期的美国到苏联,从马萨诸塞州的精神病院到加利福尼亚的迪士尼乐园。每个场景的切入都有引人入胜的画面感和时期代入感,使得读者身临其境,能以同感之心深刻体会主人公彼时彼刻的内心世界,唤醒读者对历史事件的反思以及对文献中的非真实性的怀疑,创伤记忆固然不堪回首,而将讲述创伤记忆的语言“具有两种相互对立和统一的力量”揭示出来,张扬其中“自由力量”,批判分析其中“政权力量”,这正是作家人文主义思想的集中体现。
四、《但以理书》的文学再现与历史批判
《但以理书》中运用大量笔墨描写其中人物的内心世界,包括经历者、他们的后代和所有关注这一事件的人的所思所想和他们感受到的愤怒和痛苦。小说以对细节的选择性呈现言说案件带给下一代的苦难,更多通过后一代人对历史的“回看”,呈现处于歇斯底里状态的美国冷战政治。多克托罗将麦卡锡主义盛行的冷战初期称作“猎巫时代”,言语间不乏尖锐的反讽:“在猎巫时代中,当人们(如福斯特[William Z.Foster,1881—1961]、吉恩·丹尼斯[Gene Dennis,1905—1961]①吉恩·丹尼斯,笔名尤金·丹尼斯(Eugene Dennis)和提姆·莱恩(Tim Ryan),美国共产主义政治家和工会组织家,他曾长时间担任美国共产党的领导,以“丹尼斯诉合众国案”闻名于世。“冷战时期,美国共产党总书记丹尼斯等12名高级领导人被联邦司法部指控散布教唆和鼓吹以暴力推翻和破坏美国政府的煽动性言论,并被联邦地区法院依据《史密斯法》判罪。丹尼斯等人认为他们并没有任何主张以暴力颠覆政府的实际阴谋,并援引宪法修正案第一条对言论自由的保护提起上诉”(Dennis v.U.S.,详见https://baike.baidu.com/item/丹尼斯诉合众国案/7986930)。)因政治信仰被送进监狱,这将是对集会自由权利的胜利肯定,也将会是进步主义和文明力量的伟大时刻”(Doctorow 1971:58)。小说运用了反讽的修辞手段,讥讽官方意识形态隐藏在“爱国主义”的外衣下,躲在事件背后推波助澜、封杀异己。多克托罗对历史事件的切入路径与其他作家不同,他更少直接涉及事件本身,却将事件带来的影响以多层丰富的叙事展现出来,用小说的虚构故事照亮隐藏在喧嚣躁动表层叙事之下的黑暗地带,通过对事件的想象性重构表达对美国官方历史记载的质疑。乔伊斯·卡罗尔·欧茨(Joyce Carol Oates,1938—)曾经不惜笔墨地赞扬说多克托罗的《但以理书》是一部“几近完美的艺术佳作”(转引自The Book of DanielStudy Guide)。这一盛赞是大作家之间的惺惺相惜和对小说艺术表现力及深刻主题的极高评价。本文通过冷战语境深刻介入的文外解读可以看出,作家的批判态度并非止步于此,他的批判同时指向“受害者”一方,他更希望通过冷静的旁观者姿态,揭示以但以理父辈为代表的“老左派”和以苏珊为代表的“新左派”所信奉的激进主义内核的双刃剑实质。
作为犹太人,多克托罗更希望将文学叙事同犹太移民文化的最后遗迹相联系,他认为自己深受犹太人文主义精神所滋养。他也确实试图在小说创作中凸显人文精神和正义诉求。多克托罗如前辈现实主义作家一样,以现实主义的创作初衷真实再现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的激进主义风潮,浓墨重彩地描写了但以理的父辈们,也就是罗森堡夫妇一代的激进主义思想,他们胸怀大志,勇往直前,为了他们期待的社会理想在泥沼中艰难跋涉。而小说中但以理对两代左派的激进主义态度都保持一定距离,秉持批判性认识的态度。正如评论者所言,“无论老左派和新左派,他们更多的是在追求一种‘形象’,一种姿态,一种体验,一种激进思想的实践。在丹尼尔(但以理)看来,这多少让他们的革命有了一种悬空的味道”(金衡山等221)。多克托罗独特冷静的人文主义立场由此可见,他曾在采访中曾谈到,“人文主义意指精神和道德生活不是对超自然的因素的信仰,也就是说人的问题要脚踏实地在地球上加以解决,而不是从天堂里寻找解决的方法。社会必须从显示的角度面对一些不完善的地方,为了更广泛的正义而奋斗……人文主义是对认识的渴望,科学的、美学的、历史的和人文的。在人文主义看来,人具有能够理解现实的能力”(陈俊松86—91)。
作家所秉持的中立冷静的人文主义态度使他的文学再现和带有更加强烈的反思意识,他对美国神话的深入思考照亮了语言的双重力量:“自由力量”和“政权力量”,作家对历史事件的文学再现成为干扰或者拆解其中“政权力量”的手段,对隐藏在美国文化表象下的神话进行鞭辟入里的历史反思。多克托罗将自己的人文主义态度注入但以理这位真相的探寻者身上,他运用含混的语言和清醒的反思为罗森堡审判这一历史事件提供了意识形态的背景,而事件与背景之间的关联性暗示则打破了官方话语中的“爱国主义”高调,揭示了动机背后暗藏的私利、虚伪和恐惧。多克托罗的后现代历史叙述重新呈现美国近代史中隐晦暗淡的一面,为审视罗森堡事件提供不同于官方话语的视角和思考。因为“小说提出建议,它沟通了现在和过去、可见与不可见。它分散了苦难,并告诉我们必须将自己编织入故事之中以求生存,否则将有他人替我们这么做”(Doctorow 1986:46)。《但以理书》带领读者走进美国冷战时期的创伤记忆,拨开纷乱模糊的文学叙述,“伪文献”这一概念的内涵无疑成为理解多克托罗深刻历史反思的一把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