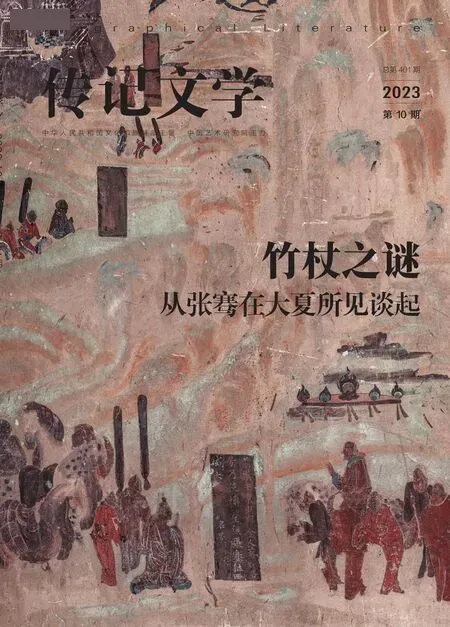长忆谨留纸上声
—— 怀念柯灵先生(一)
陈青生

几年前,得知上海复兴西路147 号建筑经修葺改装后作为“柯灵故居”对外开放,我特意与一位朋友前往参观。这里是柯灵先生下半生的居所,有近二十年时间,我经常在此出入。由于改成纪念场所,室内通畅开朗,窗明几净,布置的照片、实物展品,展示了柯灵先生一生的生活经历和文学贡献,然而,我却为此情此景已不复柯灵先生生前模样而深感遗憾,就连二楼客厅进门左侧墙壁正中悬挂的那副对联“读书心细丝抽茧,炼句功深石补天”,尽管文字依旧,却已是面貌神态天差地别的替代品。离开时,我的心情五味杂陈,有对管理方维修、设置柯灵先生故居和社会尊重文学、文化与作家的真诚感谢,也有“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的黯然感伤……

柯灵先生故居
交往的开端
《电影艺术》1981 年第8 期发表了我写的《“孤岛”时期的上海电影》一文。这年9 月30 日,我收到柯灵先生请《电影艺术》编辑部转交的一封信,信中说,《“孤岛”时期的上海电影》中有一处引用署名“陈浮”的文字,系先生当年所写,自己已经遗忘,目前因病住院医治,行动不便,希望我提供全文,信末还为“不情之请”表示歉意。这时,我进入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不久,刚刚起步于研究工作,但知道柯灵先生是著名作家,心仪已久,况且作为文学所“孤岛”文学研究组一员,在两年前的1979 年,就看到先生给我们全组的公开信《关于“孤岛”文学》,给我们的工作予以指导。待国庆节假期结束,我就赶到徐家汇藏书楼,上海图书馆收藏的现代报纸杂志多存放此处。这时,复印机刚刚引进国内不久,还没有普及,藏书楼尽管也配置一台,但复印一页的费用将近一元(当时我每月工资五十元左右),且许多报刊不准复印;藏书楼也提供拍照服务,使用的是135 胶片,拍摄一张胶片的费用是一元贰角,通常交付时间较长,需一卷胶片拍完才一起冲印。因此,当时在藏书楼查阅报刊,遇到需要的资料,读者大多靠逐字手抄,我亦如此。由于手抄费时费力,对有些重要资料是全文抄录,有些则重点摘抄,而且往往仅抄一份。“陈浮”的那段文字,就是摘抄的。这次调出相关报刊,找到相关文章,按柯灵先生的需要,全文抄录下来,然后付邮寄给先生。过了一段时间,又接到先生的信,说他已出院,但早先给他寄到医院的那页“陈浮”旧文,回到家却找不到了,可能出院时忙乱中遗失,希望我再抄一份给他。我随即照办。这件事成为我和柯灵先生交往的开端。
求教解惑
在沉浸于藏书楼翻阅多种上海旧时报纸杂志,寻觅、收集“孤岛”文学资料时,我陆续看到刊载的不少作家书信,其中大多为居住在大后方或陕甘宁边区以及海外地区的作家,写给时在上海的友人或家人的,或介绍居住地区目前的生活或抗战状况,或介绍当地的文学活动情况等,内容丰富,文笔多彩。我想,将这些书信加以收集整理,可以作为“孤岛文学”研究的一个专项课题,是中国作家虽然散居各地,却休戚与共、同赴国难的直接体现,也是了解和印证“孤岛”文学与抗战时期中国文学紧密联系的重要资料,对于作家研究、文艺思潮研究、文艺运动研究等也有重要参考价值。于是,我便留心从当时上海报纸杂志收集这类作家书信,又从当时的武汉、重庆、广州、桂林等地报纸杂志上,收集刊载上海作家写往当地的书信。就这样,到1983 年年初,我陆续收集“孤岛”时期报纸杂志刊发的各地作家与上海作家的书信150 余通,涉及60 余位作家。由于当年上海已处于被侵华日军四面包围的险恶局势,当年上海报纸杂志刊载作家书信时,或隐瞒收信人姓名以“xx”代之,或删除书信中有些文字以“……”替换。为了核查被删隐的文字,我分别致信能联系到的书信写作者或接收者求教,以便了解和复原相关书信的完整内容。

1983 年2 月22 日,柯灵先生致本文作者信,肯定辑集“‘孤岛’作家书简”这个工作很有意义
柯灵先生在上海“孤岛”时期先后编辑过《文汇报·世纪风》《文汇报晚刊·灯塔》《大美报·浅草》《正言报·草原》等报纸副刊,在这些刊物中,经手发表过46 通外地作家寄到上海的书信,约占我搜集到的“孤岛”报刊登载作家书信总数的将近三分之一,自然也是我的求教者。1983年2月中旬,我写信给先生,希望拜访先生,面聆释疑。没几天,时任文学所现代室负责人的洪荒先生向我转告柯灵先生话,说“时隔久远,难以记忆”,我当时以为这是先生的婉言相拒。洪荒先生在20 世纪40 年代后期,一度担任过柯灵先生的助编,此时为“孤岛文学”研究工作时常拜访柯灵先生。柯灵先生知道他是我的直接领导,也就请他带话给我。我不甘心,当天晚间再致信先生,详细汇报书信搜集情况,还择要报告了向几位相关作家求教的结果。此信寄出后仅仅过了五六天,我收到柯灵先生的信,信上说:“辑集‘孤岛’和上海沦陷时期的作家书简,这个工作很有意义。但要将缺文恢复全貌,是不可能的事,能做到适当补注说明,就不错了。我编的报刊上刊载的作家书简,时间相隔过久,已很难确忆,看了具体内容,可能唤起回想。我最近较忙,匀不出时间来。等你辑集整理完成,我们再约时见面如何?”这封回信给了我希望,就像在黑暗中看到了前方的光。不久,在我的期待中,再次得到洪荒先生的转告,说柯灵先生约我某日下午四时到五时去他家面聆释疑解惑。于是,在4月底的一天,我按约定的时间,第一次走进先生的家门。
面聆释疑
柯灵先生的寓所在一幢西班牙式黄色小楼的第二层。我从面街底层的大门沿右手楼梯曲折而上,到二层左转,敲开紧挨楼梯正对过道的房门,开门的恰是柯灵先生。这也是我第一次面对面见到先生。先生那时已经七十岁出头,个子不高,一米六十左右,身材清瘦,灰白色的头发梳理平整,慈眉善目,精神矍铄,衣着朴素整洁,仪态端庄文雅。他将我领进家门右侧的会客间,让我坐到右边的单人沙发,自己则在对面的长沙发落座。看我忙不迭地讲话,先生说:“我耳朵不好,让我戴好助听器。”然后一只手拿着助听器收音端,伸越两个沙发的间隔距离,尽量靠近我的嘴,听我说话,神情专注认真。此后岁月里我多次走进先生家门,几乎每次都坐在这个座位,而我们的每次谈话,先生几乎都是这样的姿势。我告诉先生,打算将收集到的书信汇编成集,作些注释,希望以书信集形式出版。先生逐一翻阅我抄写的当年经他之手发表的书信,对当年删隐的内容有的给予确切解答,有的说实在想不起来了。对于汇编书信集,先生说这项工作是有意义的,但要全部核实当年删隐的内容,恐怕不可能;能核实的填补上去最好,不能核实的也没办法,可以保持发表时的样子,不要随意补加,等等。对先生编发过的一封巴金先生致友人信,他想不起收信人,就介绍我找李济生先生持此信抄件请巴金先生回忆。先生最后约我书信集基本定型后再谈。先生说江南音的普通话,慢声细语,言简意明,不重复,不唠叨。柯灵先生的告诫,成为我后来编注工作的原则之一。这次见面时间不长,说完正事我就告辞了。
走出家门,柯灵先生不顾我的婉拒,坚持送我下楼。下到一半时,他打开墙壁左侧的一扇小门,小门外有一段露天台阶通往街道,先生告诉我以后可以走这段楼梯上下,然后看我下到路面才关门回家。以后我再拜访先生,几乎全走这段楼梯,因为这样可以不打扰一层居民,而连接街道的楼梯口旁也方便我停放自行车。
为书稿作序
1984 年年初,书信集编注大体成型,我写信向柯灵先生报告,并请问先生是否可以为它作序。不久得先生复信说:“嘱为‘孤岛’时期作家书信集作序,我可以勉为其难。但百事丛集,估计二、三月后始能措手。”我随即将全部书稿送交先生,供先生撰写序文参考。书信集先曾拟名《孤岛飞鸿》《“孤岛”书简》,先生建议还是直接用“书信”,说集名花哨不如直截了当,最终定名为《“孤岛”作家书信集》。这年6 月初,先生写信告我序文写好,我去寓所领取序文和书信集文稿时,先生又对编注工作讲了改进意见及相关回忆。这年8 月,先生所作序文《与读者书》在上海《文汇报》发表,次年又见于香港《文汇报》。大概是考虑到与“书信集”体例一致,先生的这篇序文采用的也是书信形式,以“尊敬的读者”开头,然后从书信的发明和多方面价值讲到古人书信趣话,从“孤岛”作家书信的多重意义与价值,到人类历史第三次浪潮的信息社会,依然会有用书信方法以满足人间情愫交流、心灵感应的需要,最后表达了对于世界和平、祖国兴旺、社会进步的祝愿,眼界恢弘,气势坦荡,情理交融,文采斐然。柯灵先生是中国当代散文大家,和《与读者书》同样精彩的篇章比比皆是,先生为自己或他人作品集写作的序文也不在少数,而查《柯灵六十年文选》所收58 篇序跋中,采用书信形式的仅《与读者书》一篇,由此也可窥见先生写作此文的格外用心。
1985 年3 月,我接到先生的一封信,信中说“闻重庆《抗战文艺》(期刊,刊名或有误)有南溪文谈‘孤岛’作家通信”,问我“见及否”,随信还有作者署名“南溪”的《“孤岛”作家书简与“孤岛”文学》一文复印件。几天后,我到先生家中,告诉先生这位“南溪”就是不佞,因为我在部队服役时,部队驻地在四川省南溪县,为纪念从军岁月,故用“南溪”作为我的一个笔名;刊载拙作的刊物是四川社科院文学所主办的《抗战文艺研究》,是份季刊。柯灵先生说,我以为别人已经把“孤岛”作家书信的收集研究工作做得很多了,同样重复的事你可以不要做了。这件可做趣谈的小事,也反映先生对“孤岛”作家书信收集、整理、编辑、研究工作的关心。
《“孤岛”作家书信集》的出版屡遭挫折,而柯灵先生对《“孤岛”作家书信集》的问世一直关心。起初一家出版社表示有意接受出版,后以一些缘由拒绝。1985 年3 月,柯灵先生写信给我,建议我与洪荒、陈梦熊两位先生联系,争取将书信集列入海峡出版社的“抗战文艺”丛书出版,这套丛书由柯灵、林淡秋、王元化、朱雯等先生担任主编,而洪荒、陈梦熊先生具体负责。我随即照办,经各位前辈认可,书信集列入上述丛书的第五辑。不料丛书第四辑出版后,海峡出版社领导班子改组,先前的出版计划调整,“抗战文艺”丛书停止续出,《“孤岛”作家书信集》与已定另外九种文集无缘问世。几年后,一位同事告诉我,她几天前陪同一位前辈作家看望柯灵先生,其间一位出版社编辑造访,向柯灵先生约稿,先生却向这位编辑推荐《“孤岛”作家书信集》,而此事柯灵先生却一直未曾与我言及。90 年代后期,一家出版社委托我代为编辑一套“文坛漫忆”丛书,我请柯灵先生将他的有关文章汇编成集,柯灵先生在给我的复信中反建议我将《“孤岛”作家书信集》纳入,说:“你编的抗战时期作家通讯,是极好的新文学史料,当合‘文坛漫忆’体裁,是否可列入丛书,争取问世?无形湮没,未免太可惜了。”由于种种缘故,这部书信集到柯灵先生去世都未能出版。为此我一直深感对不起先生关心,对不起先生那么精彩的序文。进入21 世纪后,总算争取到一笔经费,将《“孤岛”作家书信集》以“研究资料”名义印制成册,虽然不是公开出版物,总比“无形湮没”稍好。这时距柯灵先生去世已经六年,我只能将这册书信集交到陈国容师母手中,以此聊慰先生在天之灵。
课题组“顾问”
1985 年秋,丰子恺先生故居“缘缘堂”在石门镇修复竣工,丰一吟女士邀请文学所同人前往参加庆典活动。这天在石门镇遇到也应邀前来的柯灵先生夫妇,我们都说是意外之喜,当地一位采访记者一旁听到,为我们在丰先生故居前留影纪念。这是我与柯灵先生的第一次合影。
回上海几天后,我为先生送去记者邮寄来的合影照片,同时送去一册文学所新近印制的所刊《资料与研究》,它是现代室编的“上海‘孤岛’时期文学史料专辑”,里面收入我整理的“关于‘鲁迅风’杂文问题的论争”文选三十八篇,费万龙先生整理的“关于梁实秋的文艺‘与抗战无关’论的论争”文选十一篇,以及我写的《“孤岛”文坛的“鲁迅风”论争》和费先生写的《梁实秋的文艺“与抗战无关”论在“孤岛”上海引起的一场论争》。柯灵先生一直关心抗战文学研究,也曾委托我帮助收集现代文学历史中有关散文写作、散文运动的资料,我便送去这本作为“内部资料”的小册子。1986 年10 月,柯灵先生的《现代散文放谈》刊载报端。这篇文章包含三节,分别是“现代散文发展的三个时期”、“‘鲁迅风’问题论争的一大优点”和“关于梁实秋的‘抗战无关论’之我见”,其中两节采用了那份《上海“孤岛”时期文学史料专辑》的资料。这篇文章谈的三个问题都有柯灵先生的独到见解,尤以第三节着重谈到抗战时期发生又沿袭多年的对于梁实秋“与抗战无关论”的诟病、谴责,实在基于梁实秋当年所言本意被断章取义的曲解;文章明确反对将文学创作简单当成宣传工具,绝对化、单一化地规定某种题材,主张承认人的多样、世界的多样、事物的多样,认为散文写作题材的多样化,不仅是社会生活实际的反映和需要,也符合文艺创作规律。此文面世后,一度被视为先生为梁实秋历史冤案的“平反”,在中国大陆乃至海外文坛和学术界都引起极大震动。几天后我去看望先生,告诉他我对于此文的读后感和听到、读到的其他反响,先生说,这个问题有必要从理论上进一步深入探讨,希望有其他理论文章参与研讨,并对现代文学史著中已有“定论”的几个问题,简要谈了他的不同见解。先生所谈的具体内容可惜我当时没有记录,现在也想不起来了。

2006 年,以“研究资料”名义印成的《“孤岛”作家书信集》

下图:《资料与研究》1985 年第1 期

右图:1985 年,本文作者(左一)与柯灵先生夫妇留影于桐乡丰子恺故居
在80 年代以前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中,都没有涉及“孤岛”文学乃至抗战时期上海文学的内容,因而,文学所的“孤岛”文学研究工作,具有填补学术空白的意义。这项工作在洪荒、陈梦熊等几位前辈学者的勤奋努力下,仅短短几年,便在史料收集、整理方面,取得一批成绩,如定期汇编辑集的油印本《上海“孤岛”时期文学史料》,先后出版的《上海“孤岛”文学回忆录》《上海“孤岛”文学报刊编目》等,引起学术界的普遍关注和好评。在此基础上,我觉得“孤岛”文学固然有其特色,但它是抗日战争期间上海文学的一部分,如果扩展研究视野,将先前的淞沪会战期间及此后的上海沦陷期间的文学活动合并研究,可以更全面地考察、梳理、揭示整个抗战时期上海文学的发展轨迹和时代特点,也使得填补学术空白的意义进一步扩大。1986 年年底,文学所领导听取采纳了我的建议,同意将原先的“孤岛文学”研究扩展为“抗战时期上海文学”研究。
“抗战时期的上海文学”课题,起初是集体项目,设想由几个分课题组成,即对于不同作家、不同文学样式作品或文学活动作专题性研究,其成果分别组成几部论文集。课题参加者都是现代室成员,每人分别承担某一部论文集的写稿、组稿等工作。由于洪荒先生此前已经离职休养,陈梦熊先生接近退休年限,为保持课题延续性,遂指派我担任牵连各方的联络人,还委托我邀请柯灵先生担任文学所“抗战时期上海文学”课题组的顾问。柯灵先生欣然接受邀请,并在以后几年间,就这项研究课题的工作,给予许多建议和具体指导。1987 年1 月中旬,我到柯灵先生家,向先生汇报课题组设想的研究规划,柯灵先生认真倾听,基本认可。说到文艺期刊、文艺副刊编目工作,先生主张对所收入的各个刊物的简要介绍内容中,除了主编者、出版机构、始终刊时间等,还要增加出版背景、基本立场倾向。说到编著战时上海作家论工作,先生建议我们先打印一份拟选作家名单,广泛征求各方意见。我问先生能否提供这样的名单时,先生说“让我想想再告”。不久,我将课题组的《战时上海作家论》拟定80 余位作家名单寄给先生,先生很快寄还给我,除了在名单上添加几位作家外,还在信中对几位作家情况加以说明:

柯灵先生为“抗战时期在沪作家名单”增补作家及说明信件
开明书店的徐调孚,《文学集林》编者;周振甫,切实的学者和老编辑,似应有。
刘以鬯、董鼎山,现在海外有影响,开始写作即在上海“孤岛”时期。沈毓刚、晓歌(坦克),当时写作都较勤。黄裳初期笔名宛宛,上海沦陷后去渝,黄裳笔名,最初似见于《古今》。
武桂芳没有走出习作阶段,以后又搁笔了,似可从略。当时比武桂芳强者尚多,质、量俱较胜,如匡沙、海岑等,后来失去影响,也就算了。
战时留沪作家,情况各不相同,介绍繁简,幅度也可较大,专写、合写,方式似都可根据实际加以考虑。
这年年底,我向先生汇报课题组一年来的工作情况,说到课题部分内容有所调整,如取消原拟的《战时在沪作家》一书,先生认为可行。我们制定具体课题的几次改动、逐步充实,都得到柯灵先生不分巨细的悉心指点。在这个过程中,先生这个“顾问”做得尽心尽力,尽职尽责,而我们却没有支付过一分钱的顾问费。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