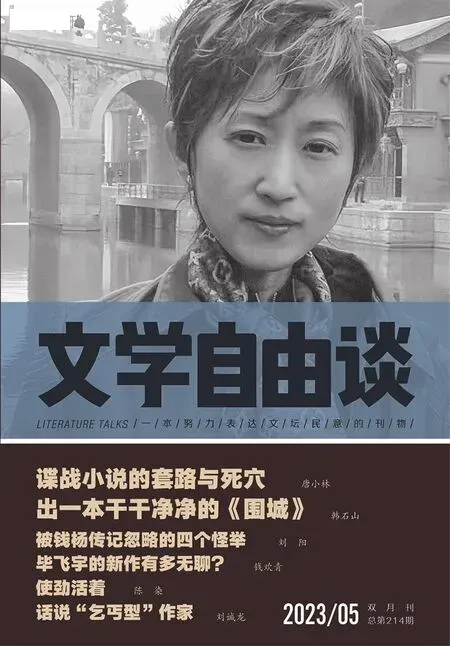祖慰、火鸟及落羽杉
□李建军
今年四月,朋友海蒂发信息来,说武汉有个采风活动,想邀我一起参加。
哦,武汉!我当然想去看看,看看她浴火重生的模样。三年睽隔,劫后重来,也许会有别样的感受和发现吧?
来到一个地方,就难免会想起这个地方熟悉的人和有趣的事。
在武汉的几天时间里,我总是想起祖慰先生,想起我们相聚的情景。
然而,我却再也见不到他了。
就在我来武汉的一个多月前,即3月3日,祖慰先生以八十五岁的遐龄,离开了人间。
我知道祖慰先生,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那时,他是一个极活跃的著名作家;但与他见面,却是很晚的事情。2014年7月的某一天,李文子女士发微信给我,说祖慰先生来北京了,并说他在大型文化杂志《领导者》上,读了我的一篇长长的诗歌评论,很想见个面,一起聊聊天。7月26日中午,我终于见到了祖慰先生。他比实际年龄看上去要年轻很多,虽年逾七旬,但谈锋甚健,了无倦容,像五十多岁的中年人一样精力弥满。
祖慰先生是一个豁达而乐观的人。他了解自己的气质和性格,认为自己是“多血质和胆汁质混合型的”(祖慰:《扬弃与“”》,广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98页)。他热情而坚韧,的确是一个兼具多血质和胆汁质的混合气质的人。
他的人生并不平顺,甚至可以说,充满了坎坷和不幸。他出生在中华民族苦难深重、血泪交流的1937年。死亡的阴影笼罩着这个出生只有84天的婴儿。为了免遭敌人的毒手,哭声震天的他,差点儿在苏州河上被抛弃掉。四岁那年,父亲被汉奸枪杀了。从此,他便跟着母亲,东躲西藏,四处漂泊。很年轻的时候,他又因为文学创作而受尽磨难——他被戴上种种“帽子”,被发配到咸宁农村接受审查和劳动改造,被分配到当阳长坂坡的一个工厂当工人。然而,无论是中岁以前的种种坎坷和磨难,还是将近二十年的域外萍漂,都不曾改变他见棱见角的性格,也不曾污损他干干净净的人格。他历尽劫波,却依然故我,一如既往。他还是那么热情,那么爱说,那么爱笑。
祖慰先生镇定地接受自己所承受的磨难和痛苦。他超越了自己所遭遇的不幸和挫折。他总是回忆起襁褓中的自己在苏州河上的哭声:“是的,像交响乐开头要呈现出全曲的主题一样,他在苏州河上的哭声,定下了他人生的基调。几十年来,他总想喊出、唱出、写出自己的声音,不大考虑这声音会惹出什么麻烦。他的欢乐和苦闷,无不源于此。”(祖慰:《扬弃与“”》,第302页)在祖慰先生看来,他自己的基本性格和人生态度,在苏州河逃难时,就已定型了。自此后,无论父亲的横死,还是自己的横祸,都没有使他成为缪塞式的感伤主义者,也不曾使他成为卢梭式的自我中心主义者。
祖慰先生是一个早慧的人。十五岁那年,他就写出了十几万字的论文《人有天才吗?》。他博览群书,好学深思,懂文学和艺术,也懂建筑和设计。他写了很多风格独特的小说和报告文学作品,曾三次获得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但是,在他身上,你看不到一丝一毫的傲慢和自负,看不到一丝一毫的嚣张和跋扈。他与人交谈,态度真诚而热情,脸上满是专注的神情和温暖的笑意,显示出对他人由衷的尊敬。他的气质是高雅的。他的谈吐和举止,显示出少见的风度和教养。与他比起来,那些颐指气使的“执牛耳者”和卑躬屈膝的“操牛尾者”,简直就像土鸡瓦犬一样狼犺和猥琐。
当然,祖慰先生也绝不是那种平庸而无个性的人。相反,他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一个具有思想家气质的作家。他不喜欢人云亦云,也不愿意屈从权威。他总是在思考,总是在提出问题。他按照自己的方式,思考自己感兴趣的事情,并按照自己的认知和风格,来表达自己的疑问和思考。
祖慰先生的小说创作和报告文学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在在显示着自觉的启蒙意识、巨大的改革热情和积极的科学精神。在他的作品里,你可以感受到典型的“八十年代精神”和“八十年代气质”。对未来的信心,探索生活的热情,强烈的责任感,赋予他的创作以鲜明的时代色彩。像那个时代的许多作家一样,他想给读者提供一个“全新的人生世界”(祖慰:《扬弃与“”》,第10页)。
幽默感和探索性,是他的小说写作的两个特点。他是一个有趣的人,讨厌一切做作和无趣的东西。他倾向于用有趣的方式来塑造人物和讲述故事。读他的小说,你会感受到一种个性化的东西,会感受到一股压抑不住的激情和自信,会感受到他思想上的活跃和情感上的喜悦。他的小说作品的基本主题,就是探索一种更好的生活方式,建构一种更加健全的人格。具体地说,就是摆脱那种僵硬的、无趣的生活,进入一种更有趣的生活状态和更健康的心理状态;就像他的短篇小说《老画家的情态》所说的那样,人们应该摆脱心理上的“负”状态和“零”状态,进入健康的“正”状态。
在报告文学写作中,他将关注的目光投向教育界,投向科学界,投向改革的前沿和特区深圳。他写了至少两篇报告文学,来描写深圳的“经纬”和“T细胞”;写了至少四篇报告文学,来讲述三位改革型的大学校长的故事。在《晶核》和《扬弃与“”》两篇作品中,他细致地讲述了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的教育改革和人生历程;在题为《朱九思引力》的报告文学中,他将当时的华中工学院院长朱九思当作主人公,赞扬他在科学研究上“全力竞争,当仁不让”的进取精神;在《现代活力的“诊断”》中,他将焦点集中在另一个“特殊人物”——上海医科大学副校长朱世能——身上,从多个角度,通过多声部对话的方式,塑造了一个“谈不清爽”的人物,一个“点子多、实心干”的改革者形象。城市形象的现代化塑造和农村的经济改革,也是他的报告文学写作所关注的问题。
祖慰先生既外在地观察和叙述他者的生活,也内在地观察和分析自己的创作。在《智慧的密码》一书的自序中,祖慰先生将自己对象化,在人物与作者的“我报告了他,他报告了我”的共生关系中,分析了“我”的深层心理结构。“我”试图拓宽报告文学的边界,为报告文学争取更大的表现空间,而报告文学所描写的“他”,则应该是“载着未来方向的真人真事”(祖慰:《智慧的密码》,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9页),应该是一个体现“时代本质全息的‘他’”(祖慰:《智慧的密码》,第14页)。那么,报告文学中的“我”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呢?祖慰并不认为报告文学作家是一个完全客观的记录者。在他看来,报告文学作家在写人物的同时,也表现自己,表现自己的审美意识和人生价值观,并视之为“报告文学的灵魂”(祖慰:《智慧的密码》,第16页)。这是一个很深刻的观点。无论多么客观的文学写作,都是作者自己的写作,都必然要显示作家自己的趣味、人格、思想和价值观。祖慰先生又从感知方式和文学气质等方面,分析了作为报告文学作家的祖慰——他是一个“用哲学思辨式的感知方式”写作的作家,而他的文学气质则见之于“语言风格”和“叙述方式”两方面。他说自己无论写小说还是写报告文学,都使用“三元(哲理性、幽默感、知识性)杂交的语言”(祖慰:《智慧的密码》,第18页);他甚至详细地分析了自己的几种叙述方式。
在文学创作方面,他有很多很怪、也很有趣的思想。他认为传统的现实主义文学,已经发展到极限了,无法再超越了。他从生命科学得到启示,领悟到“文学生命要出新,必须要像动植物要出新品种那样杂交”;他将自己的形式很怪的小说,命名为“骡子文学”(祖慰:《婚配概率——祖慰的怪味小说》,长江文艺出版社,1985年,第8-9页)。他甚至将数学图、物理图、交通路标和幽默画插入自己的小说作品。
他的这些文学观念,是有新意的,但也是偏颇的。他似乎中了进化论和科学主义的蛊。他按照这想法写出来的小说,虽然与众不同,但也曲高和寡。进入他的小说世界,你会发现,作者是一个思维活跃、刻意创新的人;你还会发现,这些小说有一些共同的特点——作者形象大于人物形象,理性内容大于感性内容,“可写性”大于可读性,特殊品质大于普遍品质。这样的小说,离作者和批评家比较近,但离普通读者却有点远,所以,就很难成为被普遍接受和赞赏的作品。如果你想验证我的判断,不妨拿他的短篇小说《抽象“人”》做个个案解剖。
是的,祖慰先生的现实主义文学观念,是大可商榷的。受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去现实主义”思潮影响,受某些蔑弃传统、自我作古的“现代主义”观念的蛊惑,他对现实主义的态度是消极的,对文学创新的理解则是简单的。现实主义文学,就像大地上的道路一样,谁都可以在上面行走,谁都可以沿着这道路到达自己的目的地。哪有别人昨天走过的路,自己今天就不能再走的道理?哪有别人跑步走过的道路,自己就不能散步走过的道理?后代作家要把接受固有经验的“影响”,当作一件自然而必要的事情。一个作家要想成熟起来,要想创造出真正有价值的作品,就不能否定和排斥前人的伟大经验。因为,一切积极意义上的创作,都是一种合作性的“共创”,是后辈作家与前辈作家一起完成的创作,是赋予旧的方法以新的表现力的创作。完全否定旧文学传统和固有的经验的所谓探索和创新,不过是文学认知和文学创作上悲观的放弃主义和取消主义罢了。
好在,祖慰先生是一个有着成熟的自反批评意识和自反批评能力的作家。他喜欢观察和分析自己,常常把自己当作批评的对象。这样做是对的。每一个人,尤其是作家,应该经常性地进行自反批评。因为,一个不懂自反批评的人,是不可能成长和进步的;因为,一个不能清醒地认识自己的作家,也不可能深刻地认识他人和生活。
祖慰先生后期的创作,主要是思想化的写作。在我看来,祖慰先生最有价值和生命力的著作,也许不是他的味道怪怪的小说,也不是他的得了三次大奖的报告文学,而是他的充满问题意识和思辨智慧的思想著作,是他的充满“大哉问”的《黑眼睛对着蓝眼睛》和《天问》。这两部思想著作所讨论的主题,几乎全都是大问题——是世界性和人类性的大问题,是现代文明如何融合与发展的大问题,是涉及“人的千古困顿”的大问题。
《天问》是艺术之问,是哲学之问,是文明之问,最终要“叩问40000年人类文明裂变史”;《黑眼睛对着蓝眼睛》记录了作者“巴黎十七年的逸思遄飞”,谈论的是人文的复活与人类的自我拯救,是如何确立人类共同的“价值基准”,是如何克服人类的“跨文化误读的双盲悲剧”,是如何禁绝对人的生命尊严的蔑视和践踏。他终于发现了“人文价值”解码的“奥秘”:“人文价值最核心的价值,天经地义是人与人之间的爱。爱是群体有效合作与和谐共存的根基。……因此,在人文之爱没有真正扩展到整个人类之前,根本就不会有人文的‘历史进步论’之论,只会是西西弗斯的上升与坠落。”(祖慰:《黑眼睛对着蓝眼睛》,第280-283页)这思想,多么朴素又多么深刻!这答案,多么简单又多么重要!
在这两部思想著作中,祖慰先生讨论问题的方式,既是哲学性的,也是诗性的;既充满思想的力量,又充满了修辞的力量。一旦打开这两部书,你会感受到一股巨大的吸引力——一股思想与美感合力形成的吸引力。充满智慧的深刻思想,充满美感的流丽表达,使你油然想起杜甫的两句诗:“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在这两部厚重而妙趣横生的作品里,思想家祖慰和作家祖慰终于和谐地融为一体。他不需要借助“怪味”来显示自己的个性和风格,也不需要在叙事和议论之间大费周章。
祖慰先生是一个充满理性精神的作家。他爱这个充满未知性的世界,总是表现出强烈的求知欲望和探索激情。任何东西都不能使他放弃自己的理想,放弃对光明和美好事物的向往,就像他谈到自己的性格和理想主义热情时所说的那样:“贫、病、乱,这个不幸的童年生活中的三元素,应该把他的性格塑造得沉郁、自卑和对明天什么也不想。可是,他偏偏有个想入非非的精神世界,就像安徒生童话中的卖火柴的姑娘一样,即使在冻馁而死那一刻,还有着一个自己神往的光明而温暖的精神世界。”(祖慰:《扬弃与“”》,第304页)虽然吃了很多苦头,但他仍然是理性的乐观主义者,仍然是乐观的理想主义者。
进入消费主义时代,文学越来越被理解为一种满足人的外在需要的文化现象。它以快乐为动力,也以满足快乐需求为目的。于是,文学便越来越成为一种轻飘飘的、无足轻重的东西。然而,祖慰先生却反乎是。他认同和接受“诗可以怨”和“文穷而后工”的古老观念。他说:“文学史是一部殉道者的历史,苦役人的实录。”(《扬弃与“”》,第311页)他的这句话里,隐含着这样的认知:文学是不幸者的盟友,是苦难的结晶;不曾体验过苦难的折磨,不曾品尝过失败的滋味,就很难成为一个真正的作家。
俄罗斯流传着一个关于火鸟的故事。孤女玛鲁什卡温柔娴静,刺绣功夫无与伦比,闻名遐迩。她的手艺和名声,让邪恶黑巫师“不朽卡舍伊”心生恨意。她让玛鲁什卡变成一只火鸟,而她自己则变成一只巨大的黑猎鹰。她用自己的利爪攫住了玛鲁什卡。为了给人们留下最后的记忆,玛鲁什卡决定抖落掉自己美丽耀眼的羽毛:“虽然火鸟在黑猎鹰的利爪下死去了,她的羽毛却留在世间,落在大地上。它们可不是普通的羽毛,而是富有魔力的羽毛,只有那些爱美并试图为他人创造美的人才能欣赏到其光彩。”祖慰的内心世界,也有着玛鲁什卡的愿望和激情。虽然备尝艰辛,虽然历尽苦难,但他内心的光焰,依然灼灼如初。他要用自己的作品,用自己的精神之火和思想之光,照亮这个世界和人们的心灵。
武汉的采风活动安排,张弛有度,很有章法。在市区和厂区里的快节奏的参观之后,就会带大家到江边、绿地和樱桃园放松一下。
这天下午,大巴车缓缓地停在了两边都是油菜地的公路上。
我一下车,就被公路两边的挺拔而优美的大树吸引住了。
我拍了照片,进入“形色识花”小程序搜求它的名字。
看到“落羽杉”三个字,我简直要惊呆了——
多传神啊,这名字!多优美啊,这名字!
那个想出这三个字的植物学家,简直就是诗人呀!
落羽杉的样子美极了。它的枝叶,仿佛一根根美丽的绿色羽毛——不,它比羽毛更美丽,更像一件艺术品。它的身形,像银杏一样挺拔,却比银杏还要颀秀。它也不像银杏那样枝叶繁多,那样给人一种太过密匝的感觉。至于喧闹的白杨树,臃肿的悬铃木,邋遢的女贞树,更无须与它相并比。它的一切都显得恰到好处——树干亭亭玉立,枝叶排列有致,色泽温润嫩绿。它端端正正地向上伸展,高耸碧霄,简直要摩天拿云了。
哦,落羽杉,你这长江边临风的玉树!
哦,落羽杉,你这树林中清峙的君子!
看见落羽杉,我仿佛看见了祖慰先生。
它简直就是祖慰先生的人格和风神的物化形态。
然而,我却再也见不到祖慰先生了。
愿你在另一个世界,一切安好——落羽杉一样风神秀雅的祖慰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