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以世界为舞台
何承波

1976年1月15日,美国华盛顿,基辛格在新闻发布会上发表讲话
当一个作家写了一本书,名叫《世界秩序》,读者会觉得,这多少会有些自以为是了。
除非他亲自参与过世界秩序的缔造。除非他是基辛格。
当然,把基辛格定义为作家,是有失偏颇的。他既是书斋里的学者,也是叱咤风云的政治人物;是深谋远虑的战略大师,也是专营谄媚的政客;他获得过诺贝尔和平奖,却也被称作“战争罪犯”而接受公众的审判;他拥有罕见的智慧与才华,但也出人意料地缺乏安全感。
我们这个时代,没有任何一个人,会像基辛格这么复杂。
理解基辛格,要采用立体主义的认知方式。就好像名画《亚威农少女》,需要多个角度去观察,才能真正理解毕加索—复杂的20世纪,诞生了复杂的毕加索,这同样适用于基辛格。从艺术领域回到现实世界,也只有20世纪,才能缔造这样难以定义的基辛格。
当然,对于基辛格来说,政治的、道德的种种维度与立场,并不重要。世界于他而言,是个巨大的舞台。仅此而已。
这位生于1923年的德国犹太人,走过魏玛时期的混乱与崩溃,历经二战和纳粹大屠杀,在冷战中纵横捭阖,在新世纪的人工智能时代发出警世预言。2023年5月27日,他度过了100岁生日,此时的他,依然活跃在世界舞台的中央,参加白宫的会议,出版一本针对当今世界领导人的书—《领导力》,用丰富的经历去论证领导人将何以决定历史。
今年11月29日,亨利·基辛格在美国康涅狄格州的家中去世,享年100岁。一位世纪老人,一个典型的美国人,终于离开了他的舞台。
来自动乱
百岁基辛格,似乎依然对这个世界忧心忡忡。
去年12月,针对俄乌战事阴云,99岁的他,在《旁观者》发表文章《如何避免另一场世界大战》称,人工智能和全自动武器的时代,计算机成为战略的主要执行者,世界将发现自己置身于一种没有既定概念的状态,世界领导人将如何展现克制,文明将何存?现在,没有任何理论可以指导这个不断被蚕食的世界。
他似乎跟茨威格产生了某种共鸣:一个昨日的世界,被两次世界大战彻底毁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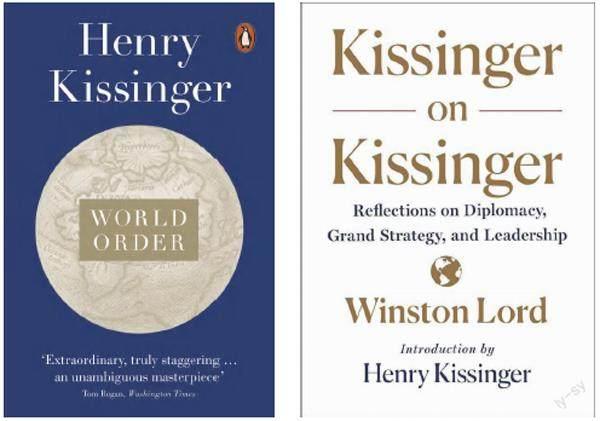
基辛格著作《世界秩序》《领导力》(英文版)

2023年6月20日,德国巴伐利亚,在基辛格100岁生日庆祝活动上,儿童合唱团向基辛格唱“生日快乐歌”
在今年的媒体访问中,他又补充了自己的论点:高科技技术加持下,如果找不到一个平衡的秩序,他们可能会诉诸武力,“我们正处于一战前的典型局面”。
基辛格的论述,依然是大开大合,同时又带有某种敏锐的感性。在《旁观者》的文章中,他回顾了自己出生前几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在他看来,一战是欧洲的文化自杀。用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弗·克拉克的话说,欧洲领导人们,梦游般地走入了一场冲突。
他似乎跟茨威格产生了某种共鸣:一个昨日的世界,被两次世界大战彻底毁灭。这种动荡,给茨威格带来的落差是巨大的:昔日荣光,再也回不去的太平盛世,一个精神上的欧洲,至此毁灭。
但不同的是,基辛格正是生于动荡本身。他以海因茨·基辛格之名,在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巴伐利亚长大。这是一战中德意志第二帝国溃败后,短暂成立的政体,是一次告别帝制、走向共和的尝试。但混乱的废墟中诞生的政府,注定发育成一个怪胎,魏玛很快陷入了无休止的泥沼。
1923年基辛格出生时,魏玛恶性通货膨胀达到了顶峰。裂缝中,希特勒和纳粹也很快找到了可乘之机。
作为犹太人,在纳粹德国长大—很多研究者尝试在童年中寻找到基辛格的人生底色,仿佛某种无法预测、也无法抗拒的暴力,会在他身上定下价值基调。再或者,魏玛的崩溃,是否铸就了他心中的文化悲观主义?
但基辛格对此讳莫如深。1958年,他回到故乡巴伐利亚菲尔特时宣称:“我在菲尔特的生活似乎没有给我留下什么深刻印象,有意思的事、好玩儿的事一件都想不起来了。”
1974年3月,他接受记者采访时,轻描淡写地承认,在纳粹德国生活期间,他经常在街上被人追赶、痛打。但他很快补充道:“那段童年经历说明不了任何问题。”
海因茨·基辛格降生的1923年,世界各地暴乱不断。德国也动荡不堪,先是大罢工,接着是各地不间断的分裂运动。到了11月,名为阿道夫·希特勒的年轻人,在慕尼黑的一家啤酒馆发起了暴动。
海因茨的父亲,路易斯·基辛格,是菲尔特当地一名教师。这个家族曾对德意志帝国忠心耿耿。信仰犹太教的父亲也一样,洋溢着爱国主义的热情。不过,海因茨却越长越叛逆,做出很多违背犹太教教义的举动,12岁就闹出许多风流韵事。父亲路易斯爱读席勒和蒙森的名作、写地方志;而儿子最爱的是足球。
作為狂热球迷和足球运动员,海因茨很快展现了他排兵布阵的天赋:“逼着对方球员不让他们进球,把他们都逼到后面当防守队员……10个人在球门前一字排开,对方很难进球。”
他的如痴如醉,令父亲大为光火,以至于禁止他去看球。
菲尔特犹太人的其乐融融,并没有维持多久。事实上,早在1925年9月,纳粹在菲尔特就举行了隆重的集会,演讲嘉宾名流荟萃,其中就有希特勒。他发表演讲称,德国人已经沦为犹太人的奴隶。不过,这期间他们并没有掀起太大的波澜。
时间迈入1930年代,菲尔特和德国其他城市一样,大萧条来临,经济迅速恶化,工人失业率激增。狂热的德国民族主义,在希特勒那种煽动性的言论下,迅速发酵。1933年1月31日,希特勒被任命为德国总理。
这年的3月9日,纳粹政客施特赖歇尔的助手卡尔·霍尔茨宣布:“从今天起,巴伐利亚大清洗就开始了。即便是菲尔特,这个完全犹太化的红色城市,我们也要再次把它变成一个干净诚实的德国城市。”
世道变得太快,威胁赤裸裸地袭来,家族中连续有人被捕、遭到毒打。对于年幼的海因茨来说,看球赛的风险急剧上升。“如果你去看比賽被人认出来,肯定会被暴打一顿。”
1838年8月,“水晶之夜”大屠杀前几天,基辛格一家四口撇下大部分财产,逃离了故土。临别前,海因茨去看望得了癌症的外公,外公说,这不是诀别,过几个星期,他会去看望海因茨。但海因茨知道,他再也见不到外公了。
最终,一家人辗转英国伦敦、南开普敦,搭乘“法兰西”号,到了美国纽约。那些留在欧洲的亲人,有将近30人被害。
1945年,基辛格以美国军人的身份,回到成为战场的故乡。在一封家书中,他如此写道:如果时光倒流13年,我们重新来过那种充满仇恨和偏执的生活,那么我会感到那是一条漫长而艰辛的道路,每一步都充满屈辱,每一步都充满失望。
新世界与旧口音
对海因茨来说,美国是一个矛盾的地方。
“有时候我爱它,有时候又鄙视这里的生活方式。”
这里令人眼花缭乱,同时又粗俗不堪。给老朋友的一封信中,他如此谈到自己的新家园:光明的一面越大,阴暗面也越大。世界顶级豪宅与世界最龌龊的小屋并存,巨富与赤贫同在。
但他不得不艰难地适应下去。他把名字“海因茨”改成了“亨利”。他爱上了棒球和美式足球,他和伙伴们一起追扬基队和巨人队。他们还打网球、学舞蹈、学开车。自然,追女孩子也是青春期的重头戏。
幽暗的岁月里,他用德语给心爱的女生写情书,说自己从理想主义者变成怀疑论者。95%的理想都搁浅了,他在苦苦追寻一个长远的奋斗目标。
然而,新生活的适应始终有个难关:亨利始终改不掉自己的中欧口音。其他难民子女都改掉了,唯独他不行。这一点,的确耐人寻味。这么聪明、这么有抱负的年轻人,为什么却倒在了语言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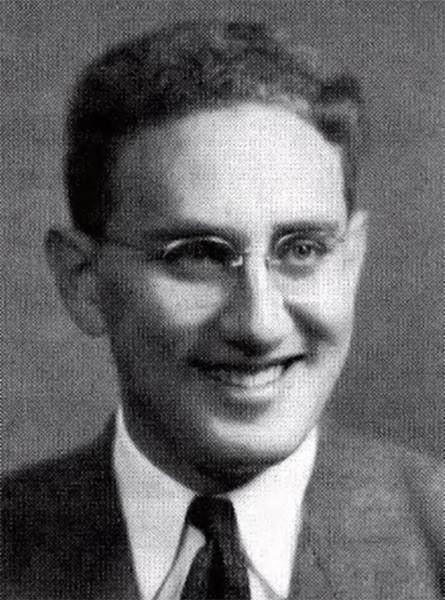
1950年,27岁的基辛格

1973年9月22日,基辛格(左二)宣誓就任美国国务卿
成年后依然说不出一口流利的美式英语,是他最难为情的地方。
现在哈佛的毕业论文篇幅限制,被称为“基辛格规则”—不得超过此文的1/3。
在新世界里,乡音,某种程度上是一种自卑。成年后依然说不出一口流利的美式英语,是他最难为情的地方。
或许正是如此,他才拼命学习语言之外的技能(比如数学),让自己出人头地。高中毕业后,他申请了纽约城市大学的会计专业。但这是他的人生终极理想吗?他并不确定。他跟一位纯朴的纽约姑娘稳定了关系,人生可能一眼望到了尽头:在华盛顿高地当一名会计,一生清清白白,默默无闻。
但历史总是会适时插手。
而基辛格的思想潜力在于:“一种透过现象看本质的迫切愿望,他想理解事情的真相。”“对历史有美妙的感悟力。这种能力不管你多聪明都学不来,是天赐的。”
两人后来一起共事,常聊历史,也聊现实政治:如何当好政治家,如何处理价值与行为之间的关系。克雷默警告基辛格:不要效仿“聪明的”知识分子和他們不流血的成本效益分析。
“只有不‘算计,你才能真正拥有区别于小人物的自由。”
1943年,基辛格进入84步兵师(第970反情报军),担任德语翻译兵,并以谍报部队的身份,前往对抗纳粹的欧洲战场—德国。

1972年,美国马里兰州,基辛格和尼克松总统在讨论越南局势
道德的不确定
故乡是不堪的,残垣断壁、满目疮痍。在家书中,他如此感慨:当年战争废墟里的人,如今身居高位,野蛮而残忍。
显然,他们再次制造了一座座废墟。
战争是残忍的,“这就是20世纪的人类。人们蒙受了深重的苦难,生死难辨,动静不分。那么,谁是死者,谁是活人?”
但是,战争也点燃了他的野心,训练了他的反击、争辩和防御能力。此后,基辛格极少在公共场合暴露自己作为犹太人的弱点,不谈及童年与故乡的创伤。一个深谙政治操控之道的战略家,即将登场,开始呼风唤雨。
他所在的84步兵师,横扫了欧洲。美国占领区的工作,为基辛格提供了迅速担任要职的机会,这让他兴奋不已。一位战友回忆说:“基辛格比我见过的任何美国人都更像美国人。”
1945年,基辛格参加了解放阿勒姆集中营的行动,因击溃一支纳粹潜伏小组,他获得铜星勋章。1947年,退伍复员的他,根据士兵法案,进入哈佛大学,打算学习政治学和英国文学。
早期的基辛格,其实并不喜欢现实政治的论调,相反,他更热衷康德这样的“历史哲学家”,以及阿诺德·汤因比、斯宾格勒等文明衰落解剖学家。从这些思想家那里,基辛格拼凑出了自己的历史观:历史不是自由进步的故事,不是阶级意识的故事,也不是诞生、成熟和衰落循环的故事;相反,历史是“一系列毫无意义的事件”,在人类意志的作用下,昙花一现。
胜利者翻阅历史,寻找类比,为自己的胜利锦上添花;而被征服者,则只能努力寻找造成不幸的根源。
基辛格的本科论文,写出了一个惊人的篇幅—全文383页,堪称哈佛本科学生之最。现在哈佛的毕业论文篇幅限制,被称为“基辛格规则”—不得超过此文的1/3。
在这篇《历史的意义》的论文中,可以看到基辛格深受时髦的存在主义的影响,他还引用了刚转入哈佛的萨特:道德取决于行动。但哲学家的理解是,行动创造了个人与集体责任的可能性。而基辛格则有相当务实的阐述—道德的不确定性是人类自由的一个条件。
在这个阶段,基辛格很懂如何增值自己的履历。他搞了一场哈佛国际研讨会,邀请世界各地的年轻政要和名流齐聚一堂。这是一个影响力巨大的关系网,帮助他日后打开了一个舞台。

1978年1月13日,基辛格参加NBC新闻特别节目
无法入局参与全球势力制衡的小国,在基辛格眼里,似乎就没有那么重要了。
他的履历,几乎是根据美国国家安全量身定制的。他的博士论文研究维也纳会议,向华盛顿的读者展示了一个明确无误的历史类比:英奥帝国遏制拿破仑的方法,可以为美苏对抗提供借鉴,甚至,开篇他就直言不讳地点出了热核武器。
1957年,基辛格出版了《核武器与外交政策》一书,奠定了他作为公众人物的地位。该书认为,艾森豪威尔政府需要在常规战争中使用战术核武器,并力陈有限核战争学说。
到了50年代末,基辛格已经无须纠结于做一名学者、公共知识分子,还是官僚或者政治家,因为他在每一个领域都获得了巨大的声誉。
此外,基辛格还通过恩师威廉·埃利奥特,攀上了石油大亨约翰·洛克菲勒的儿子。拿到哈佛终身教职后,他抓紧了外交政策的钻研,同时也开始帮助洛克菲勒竞选总统。肯尼迪政府的国家安全顾问团队也聘请他担任顾问。
只不过,彼时,学术界和思想界很看不上他。他的博士论文没什么文献注脚,也没有原始研究,是一篇风格奇特的散文,而非论文。哈佛的同事们则认为,他关于核武的著作缺乏学术性。人们把他看作低级的“国防知识分子”:在演讲厅和兰德公司(服务美国军方的智库)之间,自由穿梭、游刃有余。他也会像其他低级国防知识分子那样,抱怨学生抗议,用幻灯片展示核武,简直令人震惊。
跟基辛格观点接近的,是现代外交政策现实主义之父汉斯·摩根索。两人在哈佛大学认识,持续了几十年时好时坏的职业友谊。摩根索以畅销书《国家间政治:寻求权力与和平的斗争》而声名鹊起,他和基辛格都认为,不能把外交政策交给那些拿着流程图和统计数据的技术官僚。
但不同的是,摩根索不愿为了政治影响力而牺牲自己的现实主义原则。作为约翰逊政府的顾问,摩根索公开批评越战,因此遭到解雇。基辛格开始为越战辩护,而私下,他则跟摩根索说美国根本打不赢。
两人都不愿意承认自己是现实政治的实践者,基辛格对此更是深恶痛绝。
但其实,这是一个很灵活的概念。在普鲁士崛起的过程中,政治思想家们提出了很多种战略思想:外交不能再为皇室的奇思妙想和争斗所左右;审慎的外交政策,需要调动国家所能支配的一切—公众支持、商业、法律—以向对手展示强国形象。
接下来,就到了“基辛格时间”。

1972年4月18日,基辛格在华盛顿白宫和中国乒乓球运动员交谈
历史的意义
1968年,基辛格和反精英主义的尼克松,达成了“天作之合”。
这年尼克松当选总统后,在参议员亨利·洛奇的推荐下,基辛格进入尼克松政府,次年担任国家安全顾问,而后又担任国务卿一职。基辛格来到了个人职业的巅峰。
事实上,早在大选期间,基辛格就成了尼克松阵营的秘密线人,向其竞选团提供了约翰逊政府在巴黎和谈中的机密内容。1968年,尼克松凭借尽快结束越南战争的口号当选总统。
在其后结束越南战争的《巴黎和平协约》中,基辛格发挥着关键作用,并于1973年获得了当年颇具争议的诺贝尔和平奖。
他的现实主义,是一杆巨大的指挥棒,在其后美国的外交政策走向和世界局势的改变上,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比如,在他和尼克松导演之下,推动美国签订了美苏限制战略武器的条约,他还助力谈判结束了1973年以色列与诸邻国的赎罪日战争等。
1971年7月9日,基辛格取道西贡、曼谷、新德里,辗转到了巴基斯坦的拉瓦尔品第。他以生病为由,谎称自己“到喜马拉雅山脚下一个巴基斯坦的避暑山庄躲了48个小时”。但实际上他已秘密飞往了北京,这场代号“波罗一号”的行动,无疑是基辛格外交生涯浓墨重彩的一笔。
最终,这场破冰之旅,促成了一份尼克松访华的声明草案。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成功,同年5月,美苏首脑峰会召开,尼克松成为第一位到达莫斯科的美国总统。
如其所愿,基辛格改写了世界的格局—世界逐步达成了权力的均衡,一个多极世界正在到来。
不论手段,只看结果,基辛格的确带来了某种和平与稳定。
但那些无法入局参与全球势力制衡的小国,在基辛格眼里,似乎就没有那么重要了。诸如对于柬埔寨的轰炸、对智利白色恐怖的支持、支援阿根廷的“肮脏战争”等,尼克松和基辛格这对组合,招致了无数非议。
“如果让我在正义与混乱、非正义与秩序之间作出选择,我总是会选择后者。”这是基辛格的自我辩护。
对“不择手段”的拥护,对“普世道德”这一“中世纪概念”的轻率否定,这种尖刻的现实政治,让基辛格成为众多分析家的攻击目标。其后,大量解密文件记录了他在全球各地的行动,也为公众指控他提供了依据。

1973年,基辛格获诺贝尔和平奖后的肖像照
与黎塞留一样,基辛格也认为,每个国家都在为自己的私利而奋斗,并与竞争对手相互抵消。
1976年,尼克松下台,基辛格也换了自己的舞台,退出内阁。他写书,到处演说,充当一位活跃的公共事务评论员,是外交政策和安全事务论坛的常客,为美国总统和议员提供意见。
随着时光远去,当年那些尖锐的批评者,也走向了政治的中心,批判的热情,在消退。基辛格似乎也不再那么广泛地引起美国人的憎恨了。
当黎塞留于1642年去世时,据说教皇乌尔班八世宣布:“如果真有上帝,红衣主教黎塞留会有很多罪责。如果没有……那么,他的一生是成功的。”
基辛格喜欢这则轶事,还在个人著作中引用了。
黎塞留是17世纪初的法国政治家、外交家,也是小说《三个火枪手》中的头号人物。作家大仲马是以一位真实存在的牧师为原型,塑造了他。在长达二十年的时间里,作为法国国王的首席大臣,他不惜与新教暴君站在一起,在神圣罗马帝国制造混乱,以保持法国的卓越地位。
与黎塞留一样,基辛格也认为,每个国家都在为自己的私利而奋斗,并与竞争对手相互抵消—这样的秩序,是任何教会或帝国都无法比拟的。
对基辛格理论的支持者来说,这将是一个更加冷酷无情的世界,但或许也是一个更加稳定的世界。
1998年出版的《大外交》中,基辛格不无钦佩地写道:“他(黎塞留)无视甚至超越了他那个时代的基本信仰,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这也許是一种投射。
基辛格的一百年,对于芸芸众生来说,已经很漫长了,对于一个文明存续来说,却显得短暂。现实主义者的战争,破坏力是否真的大于理想主义者的“为世界和平而战”?这可能是基辛格留给世界的最大疑问。
一如那篇鸿篇巨制般的论文《历史的意义》中,27岁的年轻人,曾如此感悟道:“文明无一能永世长存,热望无一能完美实现。这是必然性,是历史的宿命、世人的困境。”
责任编辑吴阳煜 wyy@nfcmag.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