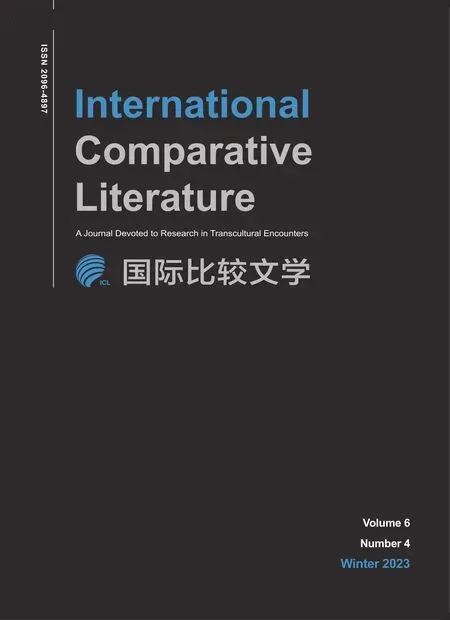记录性演述的定性及演述的区隔框架与叙述主体
——与赵毅衡先生商榷*
伏飞雄 重庆师范大学
陈玲 重庆师范大学
国内叙述理论界从一般叙述学(广义叙述学)角度讨论演示叙述,只是近10年左右的事,不少问题尚处于探索阶段。本文尝试就以下基本问题展开新的思考:如何定性记录性演示叙述?如何理解演示叙述的叙述框架,其边界在哪里?有哪些类型的主体参与了演示叙述的建构?与前述问题紧密相连的问题,又涉及哪里寻找“源头叙述者”,如何定性表演者,演示叙述有无叙述者,若有,属于什么意义上的叙述者,“源头叙述者”与“次叙述者”构成什么样的关系等等。
一、影视等记录演示类叙述的定性
影视等记录演示叙述的定性最易引发争论。赵毅衡先生这样解释道:
现代媒介造成了一个非常令人恼火的叙述学混乱:现代媒介使演示叙述与记录叙述趋于同质……“新媒介”是人类文化中刚发生100 多年的现象,不是人类文化的常态。新媒介承载的演示叙述,本质依然是演示叙述,只是添加了存储功能。录下的演示叙述,其叙述的“此地此刻”本质实际上没有变:哪怕被叙述的故事是过去的,哪怕叙述行为也已经过去,叙述行为与叙述文本的关联,依然是同时的。1赵毅衡:《广义叙述学》,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39~40 页。[ ZHAO Yiheng,Guangyi xushuxue (A Generalized Narratology),Chengdu: Sichuan University Press,2013,39-40.]
也就是说,赵先生把影视等记录演示叙述定性为演示叙述,而不是看成如书面文字记录的戏剧剧本那样的记录叙述,或者既看成记录叙述又看成演示叙述。他认为,观众在观看影片时,直觉上会认为记录演示叙述“此时此刻”展开,情节正在发生,而不是旧事记录。的确,这种理解有着欧美电影符号学、电影叙述学的传统。不过,这种传统的理路及其局限,是需要再省思的。
20世纪60年代初,法国电影理论家A.拉费(Laffay)在专论“电影时间”时指出,书面文字小说讲述的是无可挽回的过去的事件,而电影作为一门新颖的艺术,其独创性就在于能够以无与伦比的力量呈现出其“现在时艺术”(art du présent)的效果,即“电影中的一切总是处于现在时,这是此在的时间”(que tout est toujours au présent au cinéma,ce qui est le temps même de l’existence)2Albert Laffay,Logique du Cinéma: Création et Spectacle(The Logic of the Movies: Creation and Performance)(Paris :Mason,1964),18-22.。在他看来,不同于照片摄影艺术,电影这种“三维艺术”(un art de la troisième dimension)的独创性就在于,它既在空间中展开,又在时间中展开(赋予时间节奏),它通过摄影的逼真性与运动的精确性将现实主义推得比任何一种艺术都要远。尽管他也承认电影的目的是给人们制造一种幻觉,但又强调在严格的意义上不是这样,因为电影中的一切感觉起来是真实的。
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以来,法国电影符号学家C.麦茨(Metz)也表达了类似看法:“在影片中,一切都是现在时”3(法)克里斯蒂安·麦茨:《电影表意泛论》,崔君衍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第65 页。[ Christian Metz,Dianying biaoyi fan lun (A General Discussion on the Meaning of Movies),trans.CUI Junyan,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2018,65.]。在《论电影中的真实印象》一文中,他作了较为详尽的探讨:(1)从观众感知接受层面说,“电影观众看到的不是‘曾经’在此,而是活生生的此在”,这与照片摄影的“我们始终知道摄影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不是真正的‘此在’”不同;(2)从被感知客体即影片呈现层面讲,“呈现在观众眼前的是事件发生时的外貌”,影片影像具有运动性。麦茨深入分析了影片影像的运动性与观众观看影片之现在时感受之间的关系。在他的理解中,这种现在时感受完全与影片影像运动带来的真实印象叠合在一起。感知行为始终以或多或少的现实化方式领会真实性的标记,相对于照片摄影来说,电影为真实性增添了或包含了完全真实的运动这种标记,正是影片影像运动的现实性造成了一种强烈的真实印象——运动赋予物象一种实体性与自主性,物象似乎“实体化”了,这样,影片中活动起来的影像作为一种真实的显现,与现实生活场景中的运动一样,用埃德加·莫兰(Morin)的话来说就是,“运动的真实性和形式的表象相结合,引来具体的生命感和对客观真实性的感知。形式把自己的客观结构赋予运动,运动使形式有了实体感”,简言之,“运动带来立体感,立体感带来生命”4同上,第7~10页。[ Ibid.,7-10.],从而“观众总是将运动作为当下现实来感知”。(le spectateur perçoit toujours le mouvement comme actuel)5And André Gaudreault,François Jost,Le récit cinématographique: film et séries télévisées(Film Narratology: Film and TV Series)(Paris: Armand Colin,2017),156.“actuel”这个措辞很有意味,它既含有“当前的”“现时的”意思,又含有“现实的”意思。综合来说,影片带来了时间、体积再现、视为生命同义的运动这些完全给人带来真实与现实印象的标记。
不过,需要指出,麦茨这里所说的“观众总是将运动作为当下现实来感知”,还只是一种“真实印象”,而不是“真实感知”。这里的“运动”,也有着他个人化的理解:“运动是‘非物质性的’,纵然可见,但无从触摸,所以运动不会分占可感真实的两个层面:‘实物’和摹本。”6(法)克里斯蒂安·麦茨:《电影表意泛论》,第10 页。[ Christian Metz,Dianying biaoyi fan lun (A General Discussion on the Meaning of Movies),10.]他反对把触觉作为真实性判断的最高标准,反对把“真实性”混同于“可触性”。这种反对,基于他对现实世界实际场景这种现实(包括实物)与“故事体”即电影影片世界虚构故事的真实的严格区分。在文章的末尾,他点明了这种区分:
需要更加明确区分(包括术语,譬如“现实的”一词就够伤脑筋了)两个不同的问题:一方面是故事体、虚构世界和每门艺术特有的“再现内容”引发的真实印象,另一方面是各门艺术用于再现形式的材质的真实性;一方面是真实印象,另一方面是对真实的感知,即真实性标记的所有问题,这些标记包含在每门再现艺术拥有的材质中。正是因为戏剧艺术使用的材质过于现实,所以就不容易相信故事体的真实性。而影片材质完全是不真实的,故事体反而可以获得一些真实性。7同上,第14页。[ Ibid.,14.]
他所肯定的,是影片再现艺术创造的“现实幻象”这种真实性,即“非现实化的现实化”,而不太认同戏剧表演艺术制造的幻象真实,因为后者嵌入现实时空,让观众只能感觉到真实本身或实物,而且还具有过于明显的人为性。在他看来,影片创造的这种真实性,属于真正的艺术真实性。这种看法,类似于J.康拉德(Conrad)、M.普鲁斯特(Proust)、W.福克纳(Faulkner)等小说家的观点,他们都强调想象真实高于经验真实8Robert Scholes,James Phelan and Robert Kellogg,The Nature of Narrative (fortieth anniversary edition,Revised and expande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263.。正因为如此,尽管麦茨也提到照片摄影、绘画电影都由影像构成,观众都把它们感知为影像,不会把它与现实场景混淆9(法)克里斯蒂安·麦茨:《电影表意泛论》,第15 页。[ Christian Metz,Dianying biaoyi fan lun (A General Discussion on the Meaning of Movies),15.],他还是未能真正从现象学角度阐明影片叙述艺术与戏剧等演示叙述的本质差异与联系。他的这种不无争议的观念具有一贯性,在后来写的《当代电影理论问题》一文中,他在反驳让·米特(Mitry)的戏剧舞台表演观(每次重演都是当时完成,时演时新,现时感更强)时说到,戏剧表演几乎是重复同样内容,都是自身封闭的过去时表述,而影片却不一样:
电影演员只演一次,他的表演是现在时的。影片或许是十五年前拍摄的,但是当时的现在时已固定在胶片上,如果说用“现映”(而不用“重演”一词)表示放映一部影片最为恰当,这是因为每次放映时,这个过去的“现在”都重新变为现在,重新呈现出现实形态。10同上,第302~303页。[ Ibid.,302-3.]
然而,麦茨也不得不承认,影片是过去拍摄的,但他并没有充分重视这一点。也正是这一点,启发了其他电影理论家的进一步思考。戈德罗(Gaudreault)与若斯特(Jost)在讨论“叙述的时间性与电影”时指出,从根本上说,电影的时间性针对两个层面,一个是“被拍摄之物”,一个是“影片的接受”:作为产品的影片是过去时的,因为它录制一个已经发生的行动;影片的画面是现在时的,因为它使观众感觉到“在现场”跟随这一行动11And André Gaudreault,François Jost,Le récit cinématographique:film et séries télévisée(Film Narratology: Film and TV Series),155.。他们并没有简单认同影片画面现在时这个流行看法,而是把它看成电影双重叙述的悖论。一方面,从法语“语式”(mode)看,电影画面对一个过程(运动)加以现时化的语式是直陈式,这种语式中的动词既可表达发生于现在的事件,也可表达发生于过去或将来的事件,其动词时态可为现在时、未完成过去时、简单过去时等八个种类。换言之,“现在时”并非过程(运动)现时化的特性。另一方面,从“语体”(style)来说,影片画面的特性更在于展现事物进展的未完成体,即展现在观众面前的影片画面属于正在完成的叙述过程,不管是否认为影片画面反映了现实的一个已经过去的时刻即录制的时刻12Ibid.,157.。于是,影片画面的“语式”与“语体”出现了一个不可避免的悖论:即使语词在述说已经结束的事件,画面却只能向观众展现它们正在进行。
其实,戈德罗与若斯特关于电影的时间性的讨论所涉及的两个层面的理解,实质性地触及了记录性影视艺术的双重性。国内一些电影学者已经对影片叙述与电影表演的分离有所关注。电影叙述学学者兼电影导演刘云舟在评述麦茨关于叙述作为一种话语的定义时指出,话语与现实世界对立,现实要求现时在场,作为话语的叙述则只有在事件发生后才开始,这种情形也适用于电视直播与影片放映,“观看电视直播,其中的人和事也是在电视画面上展示的,不等于在现实的现场活动的人和事。在电影院放映的影片自然更远离事件发生的时空现场。”13刘云舟:《电影叙事学研究》,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4年,第56 页。[ LIU Yunzhou,Dianying xushixue yanjiu(Research on Film Narrative),Beijing: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Ltd.,2014,56.]王志敏在为麦茨的《想象的能指》的汉译本写的“序言”中,直接强调了电影艺术与戏剧表演的一些基本差异:在戏剧表演中,演员和观众处于同一场所,同时在场,但在电影中,演员在观众不在(=拍摄)时在场,观众在演员不在(=放映)时在场14王志敏:“中译版序言:麦茨论”,克里斯蒂安·麦茨:《想象的能指》,王志敏译,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6年,第14 页。[ WANG Zhimin,“Zhongyiban xuyan:Maici lun”(Preface to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On Metz),Christian Metz,Xiangxiang de nengzhi (Imaginary Signifier),trans.WANG Zhimin,Bei jing: China Radio and Television Publishing House,2006,14.]。这些讨论,完全有着经验上的支撑。
笔者认为,从根本上说,问题的症结在于麦茨未能完整理解胡塞尔现象学的感知理论,尤其未能注意到这个理论的局限。胡塞尔在考察人在体验蜡像的例子时说道:“这是一个在一瞬间迷惑了我们的玩偶。只要我们还处在迷惑之中,我们所具有的便是一个感知,就像任何一个其他感知一样。我们看见一位女士,而不是一个玩偶”15(德)胡塞尔:《逻辑研究》第二卷第一部分,倪梁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795页。[ Edmund Husserl,Luoji yanjiu,dierjuan diyibufen(Research on Logic),Volume 2,Part 1,trans.NI Liangkang,Beijing: Commercial Press,2015,795.]。在他看来,错觉中的感知也是感知。那么,幻觉破灭后人又如何体验蜡像呢?胡塞尔紧接上文继续说道:“一旦我们认识到这是一个错觉,情况就会相反,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表象着一位女士的玩偶”,即错觉破灭之后,我们对蜡像的体验依然是一种感知(立义),只不过,“被感知之物具有那种引起有关单纯表象的实践作用。此外,被感知之物(玩偶)在这里也不同于那个应当借助于感知而得到表象的东西(女士)”(《逻辑研究》A 版)16同上,第795~796页。[ Ibid.,795-96.]。也就是说,错觉破灭后对蜡像的感知,完全不同于对女士本人的感知。两者感知立义的方式发生了变化:对女士本人的感知以“感知表象”的方式进行,对女士蜡像的感知则以“单纯表象”的方式进行。所谓“单纯表象”,指“客体化行为”中的“变异的行为”,它不带存在信仰,而一个绝对未被纳入的感知,则不具有与“这里”的联系,若是纯粹想象,更不具有与“这里”和“现在”的联系17倪梁康:《胡塞尔现象学概念通释》,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第498~499 页。[ NI Liangkang,Huseer xianxiangxue gainian tong shi (General Explanation of Husserl’s Phenomenological Concepts),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2007,498-99.]。因此,在这种变异的感知中,女士本人当下不在场、不显现,只能“代现”,属于当下化直观或非本真直观。与之相反,对女士本人的感知,则属于当下直观或本真直观,女士本人直接生动显现。
这样看来,胡塞尔现象学对幻觉破灭后人对蜡像的感知的区分,还是较为清晰的。若以此框架考察影片画面叙述与演员拍摄现场表演,还是能对它们做出基本的区分。可麻烦在于,他的“错觉中的感知也是感知”这个论断,准确地说,是这个论断与幻觉破灭后对蜡像的感知之描述的缠绕,严重影响了对类似现象做出严格、有效的现象学描述或说明。“错觉中的感知也是感知”这个论断在这里颇为搅局,颇能支持麦茨等人的观点。其实,这也正是胡塞尔感知理论的局限所在。这一点,已被丹麦学者丹·萨哈维(Sahavi)正确指出:由于胡塞尔认为在真实的感知和非真实的感知(比如说对一个幻象或幻觉的感知)之间的区分与现象学无关,他“无力区分幻觉和感知”18(丹)丹·萨哈维:《〈逻辑研究〉中的形而上学中立性》,段丽真译,靳希平、王庆节等编:《中国现象学与哲学评论——现象学在中国:胡塞尔〈逻辑研究〉发表一百周年国际会议特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第161页。[ D.Sahavi,“Luoji yanjiu zhong de xingershangxue zhonglixing”(“Metaphysical Neutrality in Logical Investigations”),trans.DUAN Lizhen,eds.JIN Xiping,WANG Qingjie et al.,in Chinese Phenomenology and Philosophical Review—Phenomenology in China: Special Edi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100th Anniversary of Husserl’s Logical Investigations,Shanghai: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2003,161.]。在笔者看来,胡塞尔与此问题紧密关联的“图像表象”或“图像意识”问题,比如他对照片、雕像、电影、小说等观看、阅读体验的简略描述,似乎也存在类似的混淆。他有时把它们看成一种当下化的直观行为,有时又把它们视为与“符号表象”一样的非直观行为、非本真表象19倪梁康:《胡塞尔现象学概念通释》,第500 页。[ NI Liangkang,Huseer xianxiangxue gainian tongshi (General Explanation of Husserl’s Phenomenological Concepts),500.]。其中的犹疑不决,至少表明这些问题还需要做进一步的思考。无论如何,这里有两点应该是清楚的:(1)在符号哲学的理论框架中,影片叙述,包括其基本叙述形式的运动画面,只是电影演员现场表演的替代性符号,正如蜡像只是女士真人的替代性的“物质-符号”一样,或者,借用胡塞尔关于知觉与想象等意识行为的区别,可以把影视画面动作理解为电影演员现场表演的一种“再现”(“代现”),人们对电影演员的现场表演的感知属于“当下”拥有,对影视画面动作的“感知”则只是“当下化”的;(2)观看电影时,观众心里明白看到的是曾经拍摄好、录制好的影片运动画面,一般不会认为自己处于错觉中,即使电影始终在制造幻觉真实。也就是说,电影观众一般不会糊里糊涂地把对电影运动画面的感知等同于对电影演员拍摄现场表演的感知。
论述到此,或许可以做出如下结论:从归类或定性上说,记录性影视叙述具有双重性,或者说具有交叉性、跨界性。这个叙述类型概念表述本身,已经明示了这一点。这种定性,无疑要求我们在研究这种叙述类型时,不能仅仅从演示叙述角度把握,毕竟,戏剧舞台表演等现场演示叙述类型的许多基本特征,它并不具有,还需要同时从记录叙述类型解释。既然一般叙述学的叙述定义或叙述分类已经涉及媒介这一维度,就不能无视影视叙述经过了媒介录制这个环节的事实。忽视这种媒介性,会面临无法精细有效区分诸多叙述类型的麻烦,比如影视与戏剧表演的差异,文字媒介的戏剧、影视剧本与戏剧表演的差异,影视叙述与即时生活小视频的差异,不同视听媒介对同一故事框架、甚至某一个故事主题的“卫星式叙述”衍生(增生)式叙述的基本差异等等。只有对这类叙述的双重性进行分别与综合的观照,甚至在与书面文字记录叙述类型比如剧本的比较中,才能真正全面阐明它的特征。
二、演示叙述的叙述框架与叙述主体
西方现代叙述学主流把包括戏剧在内的故事演示类排除在叙述外的基本理由,就是认为它没有叙述者,比如,浦安迪(Plaks)认为“戏剧有场面和故事(scenes)而无叙述人”20(美)浦安迪:《中国叙事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8 页。[ Andrew H.Plaks,Zhongguo xushixue[ Chinese Narrative Studies],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1996,18.],苏珊·兰瑟(Lanser)强调“没有叙述者,就没有故事;反之,没有故事,也就没有叙述者”21Susan Sniader Lanser,Fictions of Authority: Women Writers and Narrative Voice,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1992,4.,专门从事戏剧理论研究的基尔·伊拉姆(Elam)也明确认为,表演被直接观看而没有叙述中介,表演本身没有叙述者22(意)基尔·伊拉姆:《符号学与戏剧理论》,王坤译,台北:骆驼出版社,1998年,115~123 页。[ Keir Ilam,Fuhaoxue yu xiju lilun (The Semiotics of Theatre and Drama),trans.WANG Kun,Taipei: Camel Publishing House,1998.115-23.]。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赵毅衡先生立足于广义叙述学既以扩大叙述定义的方式把戏剧、影视等故事演示类包含在叙述范围内,又探索了广义叙述者的一般形态,提出了“叙述者框架-人格二象”论。此论无疑为演示叙述这个大类的理解提供了一个具有相当说服力的解释框架。不过,它似乎也留下了一些疑问。
综合赵先生发表于各处的论述,主要有以下三个疑问。第一,演示叙述,尤其是虚构型的演示叙述,如戏剧表演、影视故事的叙述框架的边界到底在哪里?与此密切相关,演示叙述的“源头叙述者”到底去哪里找,其是谁,与框架边界问题能否一致?赵先生指出,所有的演示叙述都有一个叙述框架,有了框架标记,叙述才开始,比如,戏剧表演的舞台隔断了实在的日常生活世界,帷幕升起、舞台灯光转暗即表明表演马上开始23赵毅衡:《演示叙述:一个符号学分析》,《文学评论》2013年第1 期,第143 页。[ ZHAO Yiheng,“Yanshi xushu:yige fuhaoxue fenxi”(“Demonstrating Narration: A Semiotic Analysis”),Wenxue pinglun(Comments on Literature)1(2013):143.]。但在讨论叙述文本如电影须臾不可离的“源头叙述者”时,他又指出其是电影制作团队人格,“他是一个做出各种电影文本安排,代表电影制作‘机构’的人格,是‘指令呈现者’。电影用各种媒介(一般认为是八个媒介:映像、言语、文字、灯光、镜头位移、音乐、声音、剪辑)传送的叙述符号——都出于立他的安排,体现为一个发出叙述的人格,即整个制作团队‘委托叙述’的一个人格”24赵毅衡:《广义叙述学》,第99页。[ ZHAO Yiheng,Guangyi xushuxue (A Generalized Narratology),99.]。显然,这个作为“源头叙述者”的电影创作团队主体及其叙述行为与不少叙述信息,并不在电影表演比如观众观看到的影视画面叙述的框架内。第二,演出式虚构叙述的表演者到底是不是叙述者?一般情况下,赵先生认为不是,“表演者不是叙述者”,他/她只是“演示框架(比如舞台)里的角色”,“哪怕他表演讲故事”——也就是在表演故事文本内作为某一层次的讲述者讲故事,也只是“与人物合一的次叙述者”,即类似于书面文字小说叙述中的叙述者兼人物的情形,顺此逻辑,赵先生只是把演示叙述故事文本中的副末开场、希腊悲剧合唱团、说书人、电影画外音叙述者等看成第二层次的叙述者25同上,第98页。[ Ibid.,98.]。但是,赵先生有时又把叙述框架邀请的扮演角色表演故事的主体,即参与叙述直接影响叙述进程的演员、运动员、裁判、游戏者等看成是“表演者—次叙述者”26赵毅衡:《演示叙述:一个符号学分析》,第143 页。[ ZHAO Yiheng,“Yanshi xushu:yige fuhaoxue fenxi”(“Demonstrating Narration: A Semiotic Analysis”,143.]或“次叙述者兼参与者”27赵毅衡:《广义叙述学》,第100页。[ ZHAO Yiheng,Guangyi xushuxue (A Generalized Narratology),100.]。可以肯定,这两个概念与前面提到的“与人物合一的叙述者”并不同义,并不指称叙述学中同类的叙述主体,他已经明确把演员、运动员等表演者或参与者看成了叙述者。那么,如何理解这里的矛盾呢?第三,若“表演者—次叙述者”或“次叙述者兼参与者”这样的概念能够成立,其与“源头叙述者”一起,各自对演示叙述承担了什么样的功能?
欧美当代“跨媒介叙述”代表理论家玛丽-劳拉·瑞恩(Ryan)反对把叙述性问题与叙述者概念捆绑在一起,认为这种捆绑会把非语言的叙述形式排除在外,并指出电影里也有叙述者如画外音,但无法根据基于书面文字媒介的小说叙述学的叙述者观念去理解它28Marie-Laure Ryan,“Cyberage Narratology: Computer,Metaphor,and Narrative”,ed.David Herman,Narratologies:New Perspectives on Narrative Analysis,Columbus: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96,117.。瑞恩的话有两个要点:(1)叙述性而非叙述者才是叙述文本的本质与判断标准,没有叙述者的文本也可以是叙述文本,反之亦然,叙述文本可以没有叙述者,这样的叙述文本属于非语言文字媒介类型;(2)即使沿用叙述者概念去称呼电影的画外音,也绝不能简单套用小说叙述学的叙述者观念(叙述者概念基本源自对书面文字小说的研究)去理解它,“画外音”伴随有声电影艺术产生,其种类与功能(旁白、心声、解说及画外对白等)与文字媒介小说的叙述者概念有不少差异。S.查特曼(Chatman)是叙述理论界少有的正面讨论戏剧是否属于叙述的理论家,在他看来,无论小说还是戏剧,都有一个共同的核心或具有一个基本特征:都有故事,都属于故事或叙述,即无论“讲述”(telling)还是“展示”(showing),都属于以符号形式“呈现”(present,transmit)故事的行为,虽然其符号种类及其组合形式不太一样29Seymour Chatman,Coming to Terms: The Rhetoric of Narrative in Fiction and Film,Ithaca &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0,109-13.。这启示我们,戏剧表演者也在用符号直接“讲述”故事,他本来就是一种叙述者。
笔者认为,把叙述者作为叙述判断的基本标准,或者认为戏剧根本没有叙述者的看法,明显受限于西方现代叙述学,其经典叙述的“语言文字中心主义”视野30从形态上说,直接以口语、文字讲述发生于过去的事件自然属于语言文字产生以来最直观、最典型的叙述形式,其媒介化叙述再现过程与方式很容易得到辨识,属于人们最直接、最普遍的历史与生活经验,很容易成为欧美现代叙述学发端时期的宠儿。,这种看法既有硬套基于口述、书面文字小说建构的叙述学之叙述者概念框架的嫌疑,又有简化戏剧等故事演示叙述类型之叙述主体存在形态的倾向。暂且不说不少书面文字戏剧剧本中对故事开端背景、人物等的介绍、甚至描写等,到底属于熟悉戏剧剧本写作与表演程式的戏剧作者还是叙述者的问题,一些传统的或现代的书面文字媒介的中西戏剧,本来就有着明显的借鉴小说叙述模式的痕迹,如《伪君子》(莫里哀)、《雷雨》(曹禺)、《绝对信号》(高行健)等。至于现代影视故事片,则既存在不少现身叙述者兼人物(荧屏形象)的现象,也存在不少以画外音形式出现的种种叙述者的情形。总的来说,与书面文字小说相比,包括戏剧表演在内的故事演示文本的创作机制、存在形态等非常不一样,后者明显复杂得多,根本无法简单搬用小说叙述学的叙述框架、叙述者观念等去理解与解释它。因此,本文站在一般叙述学立场,主张灵活理解与运用叙述框架观念,在从参与演示叙述创作与接受的主体的角度提出“叙述主体”概念的基础上,有限度、限定性地使用叙述者这一概念。
先回答上述第一个疑问。笔者尤其看重赵毅衡先生在定义区隔框架时说到的一个点,它“也是随着文化变迁而变化的体裁规范模式”31赵毅衡:《广义叙述学》,第74页。[ ZHAO Yiheng,Guangyi xushuxue (A Generalized Narratology),74.]。不过,据笔者考察,目前关于戏剧表演、影视等演示叙述区隔框架的讨论,似乎并没有完全回到这种体裁本身,不少学者在为此类体裁设定规范、抽绎模式时,不同程度存在沿用小说叙述框架的倾向,尤其是沿用经典叙述学立足书面文字文本(即封闭文本)设定叙述框架的倾向。基尔·伊拉姆认为,“剧场演出的文本区为表演过程设置框架”32(意)基尔·伊拉姆:《符号学与戏剧理论》,第17~18页。[ Keir Ilam,Fuhaoxue yu xiju lilun (The Semiotics of Theatre and Drama),17-18.],这是从剧场演出与观众分界、演出与日常生活分界来说的,其立论基本上立足于结构主义符号学,这种框架设置显然无法回应戏剧表演艺术整体的基本机制,比如导演艺术、舞美艺术等。在赵先生的“叙述者框架-人格二象”论中,演示叙述的框架倾向于“叙述者极端框架化”,即仅仅作为“准人格化”的区隔标记,例如舞台、影视画框,似乎也有此痕迹——这种理解,对于舞台、影视画框等较为抽象的“叙述者框架”来说,有其合理性。既然所有的演示叙述都有框架标记,其框架又是叙述开始的标记,那么,就应完全回到这种叙述体裁本身思考它的框架标记到底是什么,在哪儿,等等。笔者认为,舞台这个“准人格化”的区隔标记只是标记了演示叙述故事文本的开端,只是涉及故事文本内的叙述主体(故事主体),而不涉及演示叙述故事文本的“源头开端”。换言之,如果演示叙述仅仅以舞台或影视画框作为区隔标记,则排除了舞台外实际参与、甚至某种意义上主导演示叙述创作的团队主体,即作为“源头叙述者”的创作主体。
回到演示叙述这种体裁本身会发现,无论从其创作涉及的社会与文化机制、创作发生的方式与过程、凭借的符号媒介种类、创作参与主体类型、文本接受与交流的情形等方面来说,都远比书面文字的小说叙述复杂。其实,谈到小说叙述,也涉及是否完全突破经典叙述学封闭文本讨论叙述框架、叙述模式等局限的问题。对于信守经典叙述学范式的人来说,文字媒介的虚构叙述只能由“写作作者”(或“执行作者”)虚构的叙述者开端,不管第一层次的叙述者是否现身,是否只是“准人格”的框架叙述者。但对于不再封闭文本进行文学阅读与解释的人来说,文学叙述的开端或源起就会涉及“写作作者”的构思与写作,毕竟,叙述者本身、叙述者讲述故事的模式等的选择,叙述者讲述的故事,都是由“写作作者”这个符号主体构思或执行的。布尔迪厄(Bourdieu)说到,“根据场域概念进行思考就是从关系的角度进行思考”33(法)布尔迪厄、华康德:《反思社会学导引》,李猛,李康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121 页。[ Pierre Bourdieu and Loïc Wacquant,Fansi shehuixue daoyin(An Invitation to Reflexive Sociology),trans.LI Meng and LI Kang,Beijing:The Commercial Press,2005,121.],这无疑启示我们,要还原性地理解现象在社会实践中的具体运行,需要注意场域中各位置上的主体的相互关系,以及各种力量间的相互作用。如此看来,对小说叙述框架的思考须完整立足于小说文本发生的整个场域,而小说文本世界中故事讲述者的讲述与“写作作者”构思、写作一起,才完整构成了小说叙述发生的整体场域。从区隔理论来说,从事小说构思与写作的“写作作者”的人格结构、精神状态不同程度与其日常生活中的情形不一样,其间存在区隔,只是其标记不是有形之实体或物质上的,而是相对抽象、观念性的。这种整体场域视野下的框架观,对于演示叙述这种立足于多场域、立体化/异质化时空、多/异质时空主体与多符号媒介参与创作的叙述形态来说,显得异常基础与重要。还原到演示叙述这一体裁的创作机制与场域,会发现被舞台这个区隔框架排除的舞台外的各种参与叙述建构的主体的重要性。因此,笔者建议把剧本作者或改编者、导演、角色造型师、舞美师、灯光师等创作主体,甚至某类观众都明确纳入演示叙述的叙述主体范围内,他们不同角度、不同程度对演示叙述的文本建构贡献了主体力量与声音。这些叙述主体进入虚构演示叙述创作场域的状态,已经与其居于日常生活实在世界的状态构成了一种区隔,就像舞台演员与日常生活中的他或她构成的区隔一样。他们作为“源头叙述者”,并非“准人格化”的,而是使其创作烙上风格标记、鲜活的主体人格。
当然,戏剧表演剧本的改编者、导演、摄影师、舞美师、灯光师、化妆师、道具师等叙述主体,一般都不会出现在表演框架内,更不会出现故事文本世界中。不过,对于那些不只看表演故事的观众来说,他看到的,显然不只是舞台角色表演的故事。舞台角色当然是故事文本信息的主要与直接发出者,但内行观众的眼光也并没有完全被角色表演的故事所淹没,他同时也看到与明白,剧情设计或改编,演员选择,角色打造,舞台设计诸如布景、灯光、道具、音乐、化装等构成的故事氛围或元素,是导演、编剧、舞美师等叙述主体的意图与创作的直接产物,他们也是舞台世界某些基本信息的直接发出者。这些信息往往与角色人物演示的故事有着这样那样的联系,比如成为故事发生场景(背景),甚至就是故事的构成要素或潜在构成要素。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才把舞台外参与演示叙述文本建构的各种主体称为舞台文本世界的“源头叙述者”。这一点尤其提醒我们,不能以文字小说文本的眼光来看待戏剧表演艺术,戏剧表演文本或舞台世界并非只有文字文本意义上的故事世界。在书面文字的戏剧剧本中,舞台提示由剧本作者承担,这个剧本作者以或隐或显的方式存在于戏剧文本内外,他熟悉剧本写作与戏剧表演程式。在戏剧舞台表演中,这些舞台提示往往由角色人物直接演示,或者由导演、化妆师、舞美师、灯光师等这样的叙述主体在“影视画框”外完成。对于戏剧舞台表演的故事(剧情)本身来说,他们是隐身的,属于“不在场的在场”(直接不在场,潜在在场)的叙述主体。这有点类似于影视中的“大影像师”机制。A.拉费认为,“大影像师”并不显示自身,是“一个虚构的、不可见的人物……他在背后为我们逐页打开相册,其隐蔽的手指引导我们注意这个或那个细节。”34Albert Laffay,Logique du Cinéma : Création et Spectacle(The Logic of the movies: Creation and Performance),81-82.戈德罗与若斯特认为,解决这类不显示自己的叙述主体的方法有两种,或者自下而上,在场情况或多或少可被感知到与得到辨认,或者自上而下,即先验提出叙述运作的必要机制35And André Gaudreault,François Jost,Le récit cinématographique: film et séries télévisées(Film Narratology: Film and TV Seiers),54-55.。具体来说,戏剧表演原始剧本作者在剧本中的一些舞台提示,一般由角色表演者或“演员+角色”表演者用自己的身体符号、行为动作等表演叙述出来。但有些舞台提示,比如舞台道具、布景,甚至剧本作者对人物外在的介绍、人物生活环境的叙述等,恐怕就要由导演、舞台道具师等设计出来。化妆师、舞美师等实际上就是在从事角色人物外在形象塑造、动作设计、与剧情有关的舞蹈设计等创作。而且,在现代戏剧表演与影视作品创作中,编剧,尤其导演,扮演的叙述主体的角色越来越重要。著名演员焦菊隐曾这样说道:“我们常说,没有好剧本和好演员,就没有好戏。现在我愈发明白了,没有一位才能与思想都攀上高峰的导演,好剧本和好演员的本领也是枉然。”36苏永旭:《导演文本:戏剧叙事学研究不可忽略的重要的“中间转换形式”及其理论归宿》,《河南教育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2 期,第9 页。[ SU Yongxu,“Daoyan wenben:xiju xushixue yanjiu bu ke hulue de zhongyao de ‘zhongjian zhuanhuan xingshi’ jiqi lilun guishu”(Director’s Text: An Important “Intermediate Transformation form” and its Theoretical Destination that cannot be Neglected in the Study of Dramatic Narrative),Henan jiaoyu xueyuan xuebao(Journal of Henan Institute of Education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1999): 9.]总之,这些在小说叙述中由不同种类的叙述者(包括隐身叙述者)作的事情,都可能由这些舞台外的叙述主体主导。
无论如何,舞台上的一切都是戏剧表演这个叙述文本的信息,这些信息都应该有叙述信息的发出者。这也符合米克·巴尔(Bal)对作为“素材”(fabula)的事件的理解。在她看来,事件属于由事件、行为者(actors)、时间、地点这些可以描述的成分组成的集合体37M.Bal,Narratology: Introduction to the Theory of Narrative(3rd edition),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1997,5-9.。也就是说,舞台上所呈现的由非角色表演者本人所演示的一切,都属于被表演的故事的构成因数。当然,也需要清楚,就像在书面文字叙述文本中要区分哪些是叙述,哪些是非叙述一样,戏剧舞台表演中出现的一切,并非都属于叙述的形式与内容。也就是说,要区分哪些东西不属于狭义的叙述成分,哪些属于描写的成分等等,正如热奈特(Genette)在《叙述的界限》一文中对叙述与描写等所作的区分一样。这个问题,在传统小说叙述理论研究中重视不够,对于舞台表演等演示类叙述来说,要弄清楚更是比较困难。也正是在此意义上,米克·巴尔对事件的界定还是显得宽泛了些。
当然,以上讨论还局限在传统戏剧表演上。对于不太注重剧本基础、排练、固定舞台、演员与观众固定关系等现代实验戏剧来说,情形已有很大变化。没有剧本的即兴表演,或者有一定剧本基础又重视现场表演的临时发挥,重视与观众互动,甚至人物角色、导演、舞台工作人员与观众角色互换,舞台空间延伸,与观众空间、生活空间交叉或互换等情形,基本就是在尽可能挑战传统舞台表演的一切程式。比如,挑战表演场外的叙述主体与场内表演者的关系,挑战人物角色与观众的关系,挑战舞台空间与观众空间甚至生活空间的关系,挑战剧场幻觉等等。它们之间关系的转换,导致了具体演出中的主体位置与功能的转换。正是这些转换,使这些作为演示叙述的基本机制、基本结构(包括区隔框架)与元素构件的含义或功能与传统不完全一样。当然,之所以能够谈转换,也是在与这些基本结构、元素构件或名称之传统的含义或功能的对照下说的。不然,一切都处于混乱之中,无从谈起。在这些情形中,即兴式的“生活表演”的叙述框架,尤其容易被弱化或虚化。甚而至于,对于某个人偶然观察到的纯粹生活事件来说,演出文本界限与生活界限并没有区分,演出者就是作者与表演者合一,其叙述框架似乎只在该事件与其他事件、与非叙述对照的情形下发挥作用。当然,把某些纯粹生活事件看成叙述演出,已经是从广义叙述的角度来说的了。
第一个疑问解答了,后面两个问题就变得容易得多,它们之间具有问题逻辑的关联性。前文有关查特曼关于戏剧与小说都以符号组合形式“呈现”故事的解释已经暗示出:“表演者”显然也是一种叙述者,即用身体、动作、行动、言说等符号媒介“讲述”即“演述”故事的叙述者。为了与小说叙述者概念有所区别,又不至于与模仿小说创作的那类电影的故事世界里的叙述者,或者不同种类的画外音叙述者发生混淆,笔者建议用“演述者”称呼。这样,既合理延续了小说叙述学的概念框架,又遵循了演示叙述的特点。这些“演述者”都是相对于故事文本外的各种叙述主体这样的“源头叙述者”而言的“次叙述者”。这里的“次”非指“次要”,仅指先后顺序的“次”。因为,无论怎样强调表演框架外的叙述主体(上文只是道出了这种叙述主体对于哪些舞台世界信息的直接贡献),“演述者”的角色功能一般情况下总是处于演示叙述的核心,因为一般观众期待要看的、看到的,主要还是表演的故事本身。不过,历史地看,表演场外的叙述主体与“演述者”的划分(他们都属于广义“表演场域”中的叙述主体),及其主次作用总是相对的。在不少原始仪式与戏剧中,比如在古希腊戏剧引入少量演员因素之前的戏剧中,非角色表演者意义上的、参与叙述文本意义建构的主体的重要性较为明显,因为角色表演者的“戏份”不重,仪式或表演多体现为一种框架性设计,显得较为程式化。不过,也要清楚,即使如此,其中的表演者依然承担了较为重要的叙述功能。毕竟,是他们的表演在面对观众。同时,某些演示叙述类型如前文提到的即兴虚构表演、纯粹生活事件,其角色表演者几乎是唯一的叙述主体,他/她并没有要听从的像导演等这样的“源头叙述者”,或者说,他/她本人既是某种意义上的“源头叙述者”,也是一个演述者。
对于人物角色表演者在舞台表演中的具体情况,也要视具体情形而定。在中国戏曲表演中,演员与角色有明显区分。不少学者都提到中国传统的说唱艺术,尤其是戏曲表演中演员自身的本色身份,“演员以自身的本色身份,站在第三者立场或者说以第三人称口吻所统领的‘说唱’式‘叙述’”38吴文科:《曲艺综论》,北京: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5年,第6~7 页。[ WU Wenke,Quyi zonglun (Comprehensive Research on Quyi),Beijing: Beijing Times Chinese Bookstore,6-7.]。京剧表演甚至出现作者、演员合一的现象,因为其异常重视故事演示时发挥演员演技本事和唱功(唱念做打的综合表现)39袁国兴:《非文本中心叙事:京剧的“述演”研究》,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30 页。[ YUAN Guoxing,Fei wenben zhongxing xushi: jingju de“shuyan”yanjiu (Non-Text Centered Narration: A Study of the “Narrative Performance” of Beijing Opera),Guangzhou: Guangdo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2013.30.]。这一点,可以在表演结束后演员出来谢幕时体现出来。演员谢幕提示“演员”身份,使观众明白了其演员身份。在西方戏剧表演中,多追求演员与角色合一,角色表演者的功能就相对明确得多。
综上所述,可以这样总结演示叙述的叙述框架与叙述主体:演示叙述有两个叙述框架,一个以舞台为标记区隔开角色演员的演述与舞台外的世界,区隔开角色演员叙述主体与其舞台外(包括日常生活中)的形象,另一个叙述框架是抽象的,这个抽象框架区分了舞台外的各种叙述主体之参与的演示叙述创作与其日常生活状态,从而也就区分了这些叙述主体不同境域或世界中的主体形象;演示叙述的叙述主体并非只有角色演员,还包括导演、编剧、摄像、舞台工作者等舞台表演或演示文本世界外各种参与了演示叙述文本建构的主体,他们往往属于具有鲜活主体性、鲜明风格标记的“源头叙述者”;演示叙述的角色演员属于某种意义上的叙述者,即演述者,记录性演示叙述的叙述者除了故事世界的叙述者外,主要体现为各种“画外音”类型的叙述者。
结语
上文只是从理论上阐明了影视等记录性演示叙述的定性或归类问题,即认为影视等记录性演示叙述首先具有记录叙述类型的一些特征,其次才具有演示叙述的一些特征,而后面这两种叙述类型的部分特征如何体现在记录演示叙述形态上,或者说它们的部分特征如何以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方式或直接或“变形”地体现在记录演示叙述文本中这样的问题,还没有得到展开。要研究这个问题,又需要首先弄清楚后面这两种叙述类型各自的特点与相互联系。从笔者有限的视野来看,真正突破经典叙述学、甚至欧美所谓“跨媒介叙述”研究的视野或范式局限,立足于一般叙述学(广义叙述学)的视野来研究此二者的,并不多见。因此,还需要学界的大力关注与系统研究。
另外,上文一再强调回到演示叙述实践本身提出问题、构建概念与理论框架的必要性。比如,有论者认为,“书籍的标题,序,插图,出版文本,电影的片头片尾,商品的价格标签等都可以被视为副文本,它是文本的‘框架因素’,往往落在文本的边缘上,甚至不显现于文本边缘”40胡一伟:《论戏剧演出的三类伴随文本》,《四川戏剧》,2018年第6 期。[ HU Yiwei,“Lun xiju yanchu de sanlei bansui wenben”(On the Three Types of Accompanying Texts in Dramatic Performance),Sichuan xiju (Sichuan Drama) 6(2018): 15.],这种理解,主要还是局限于书面文字文本,“副文本”“叙述框架”等概念主要就是以此为基础提出的,有其合理性,但在一般叙述学的视野中,在对各种叙述形态之综合考察之下,到底如何定义副文本,哪些故事演示的叙述框架落在表演之外,哪些落在表演之内等等,还是需要具体分析的问题。
由于欧美文论的偏见,传统及现代各种仪式、戏剧等演示叙述形态,历来未得到重视,现代新兴的记录性影视叙述,由于长期深受欧美影视叙述学与经典叙述学一些偏见的影响,它的不少基本问题也没有得到更为有效的解释,但它们无疑是现代叙述理论必须面对并有效解释的叙述形态,只有有效解释了它们,一般叙述学的理论大厦与批评实践才会具有较为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