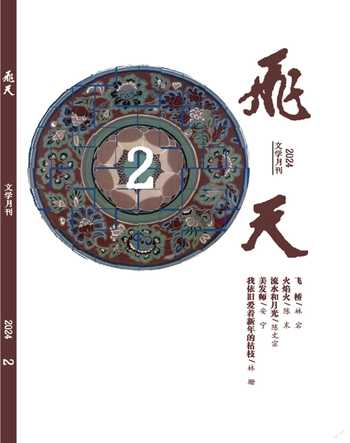飞桥
林宕
乌苏拉正奇怪牛奶煮了那么久怎么还没开,她揭开炉上的奶壶盖一看,里面全是蛆虫。
——加西亚·马尔克斯
一
雪纺衫上的银丝在闪亮,平底浅口的黑白纹鞋在带起几缕似有似无的白尘——很快,秋月自家也变成了一缕若有若无的白尘,最终消失。
事后,兴长对人说,你只要转两记头颈,自家女人就立刻不是你的了,所以,你不要认为万事都是笃定的。
那日,村窠西面的木太家办喜事,兴长带了秋月去吃喜酒,才坏事的。坏事后,兴长才对人讲了那句话的——不过,他转了两记头后,应该立刻立起来,在他女人还没有变成若有若无的白尘前追上去,可他没有这样做,因为望上去她像是去解决内急的。
后来,他似乎醒转来了,在酒席还没有散之前,立了起来,走到了路上,路上空无一人。他朝他家走。很快,他跨进客堂,打开房门上的铜锁,又推开房间里间隔墙上的木门,跨到床边,在秋月的被窝里摸一记,摸出一把香味。
他对自家说,对的,她是朝西走了,我没有吃多酒。
半个钟头后,他立在了发亮家的场门前。兴长对正要朝外走的发亮说,我……女人跑了。发亮说,一共困了几趟?兴长说,其实,其实还不能说是我的女人。发亮说,我问你,统共困了几趟?兴长说,秋月跑了,不过你放心,欠你的钞票,一有,我就还。发亮说,操那,我这么小肚鸡肠?我是这样的人的话,当初也不会借你钞票。
借钞票那日,发亮把兴长叫到了香花桥镇上的一家小酒馆里,倒像是发亮有事要求他。没吃几口老酒,两家子就讲到了女人。发亮的眼睛比平时亮,他要兴长也出笔钞票,让赵梅花给他领个女人过来(这几年,赵梅花给人介绍的都是外地女人了),给他捂脚节头。发亮说,你女人走了长远了。他又说,这里的人,上一点岁数,就开始练童子功了,不能这样的。
几口老酒吃进,发亮终于讲出了关键的一句:你就不要肉疼钞票了,假使暂时拿不出,我先给你垫。
兴长已是面红耳赤,他高声讲点啥?声气都有点像吵相骂了,可发亮清楚,兴长脾气好,永远不会真正跟人吵相骂。
兴长朝自家杯子里筛特加饭,一抬头吃了。他用手背揩揩嘴,又眼神定定地望着发亮。本地人都清楚,发亮他是个“放”钞票的人。可他不随便“放”,他不想“放”的人,给他磕头也没有用。兴长又是一个受不了别人对他好的人,很快点头,瓮声瓮气地说,放心,我借你的钞票一定会还的。
发亮哪能不清楚兴长的为人和情况呢?兴长的责任田就要被工业园区征用了,到时兴长会有一大笔土地补偿费,所以,“放”钞票给兴长,发亮困得着。不过,这钞票是要付利息的。发亮大方地对兴长说,你就付月息吧……这可是远远低于鱼塘上的人付的利息了!
发亮从身边的黑色人造革包里摸出合同纸,让兴长签字。望到合同纸,兴长的酒醒了大半,拿着水笔的右手僵住了,说,可我,岁数……发亮的两张嘴唇皮碰出一声“啧”,说,六十岁,讲小不小,讲大不大,你更不能浪费辰光了。发亮还说,以前是穷,你有想法,也没有办法;现在呢,日脚不一样了,眼看着你的田要被征用了,你就要成为一个有钞票的人,现在就怕有了钞票,没了力气,到时还是有想法,却没有办法……
兴长手里捏着的水笔落到纸上。
这时,在发亮家的场门前,发亮的胳膊里仍夹着那只边角已磨损的黑包。在好多本地人的心里,发亮就是一个胳膊夹着黑包走村串户的人影子。这个夹包的身影望上去是孤独的、匆忙的,可就是这个身影,却从容地、坚定地把好多人的命运夹在了自家的胳膊间。
现在,发亮就把兴长夹在了自家的胳膊里。兴长急匆匆地赶过来,额角上全是汗,好像担心讨不回钞票的不是发亮,倒是他兴长。兴长说,你放心,欠的钞票一定会还。发亮拍一拍兴长的肩胛,说,别人我不放心,还能不放心你吗?他突然很大度地一挥手,又说,利息减半吧,你竹篮打水一场空,我不能再踏你一脚。兴长说,那好,我走了。发亮却一把拉牢兴长,要他陪自家一道去横泾村的鱼塘上。
鱼塘承包人是一对外地夫妇,他们既养鱼,又在石棉瓦小屋里“养”着一批人,因为这批人之间出进钞票,发亮就跟他们有着切不断的关系,这关系也让钞票给维持着,让“放”与“收”这两个方向相反的動作给维持着。
兴长不想去,讲还有事。上趟,兴长也是先陪发亮去了鱼塘上,然后再到香花桥镇上去吃老酒的。吃老酒的结果虽然不是醉,却与醉一样,让兴长不能把持自家了,最终在发亮的合同纸上落笔了。他还醉了似的,望到那张合同纸上出现一张面孔,当然不是他已过世的老婆的面孔,甚至不是一张他曾见过的面孔,可这张面孔却是他所熟悉的,每当他想女人时,这张年轻的、他在现实生活中从来没有见过的面孔就出现了,花一样的。以前,它一出现,他就会用一只想象中的手朝它挥一记,把它挥去。这次,他却招手了,他记得那天望着那张合同纸时,他招手了,结果就招来了秋月。
秋月来了,又走了。
秋月的面孔在他的生活中消失时,尽管表面望上去他是平静的,可他的内心却是翻江倒海的。这跟在他的挥手之下那张花一样面孔的消失,是不同的。没办法,真面孔与假面孔就是不同。
二
离开发亮不长远,兴长就到家了,他走进房间,又推开间壁墙上的门。
他的心跳加快了,用手背使劲揩揩眼睛后,他掀了掀床上的印花被,又盖上。他望到了二十多年前的菊花,二十多年前,他女人菊花跟他吵相骂后,就会蒙头困在床上。他的鼻头有点酸,床上是秋月——她没有消失,又回来了——突然让他有“自家女人”的感觉了。秋月跨进他家门的这一个礼拜来,尽管这里的人都晓得他有女人了,可他的心里,还没有秋月是“自家女人”的感觉。对于他来说,自家女人是一个受气后蒙头困着的女人,而在她蒙头困觉时,房门总是开着的。可恰恰在秋月进门后的一个礼拜来,他们不但分床困觉,而且两张床之间的间壁墙上,门要么被锁着,要么上着门闩。现在好了,秋月非但没有逃脱,而且在困觉时没有闩上门,这表明了啥?
兴长再次在床边弯下腰,他的呼吸粗重起来,来不及脱衣裳,他就钻进了被头里。被头里的热气和暖气同样让兴长回到了二十多年前,那时的兴长手到擒来,现在的兴长却被重新推到了床底下。
秋月在床上坐好,呼哧呼哧喘气。她说,我讲过的,不要碰我。兴长说,可你没闩上门。
秋月的面孔红彤彤的,像烘熟了的番芋一样红。秋月又说,欠你的钱我会还的。兴长说,我不要了。秋月望着兴长,像是在想啥,突然捩转身,伸手,把兴长重新拉到了床沿那里。
秋月的粉红针织内衣歪斜了,领口敞得很开,敞出的一片白色和她的面孔交相辉映。辉映出的光泽像是再一次撩拨了兴长,他一下子掀倒了秋月。旋即,秋月用掌跟、用拳头去推、去顶兴长的胸膛。兴长叽咕一声,那你做啥拉我?
他重新被秋月推下了床。
三
兴长问阿六头,啥地方去呢?
阿六头说,本店打麻将去。
阿六头在村西头开着一家小店,正走在路上,被兴长撞上了。
兴长又问阿六头,他的店里有没有退热药。
阿六头摇摇头说,被工商查了,不卖药了。
兴长是来给秋月买药的。半个钟头前,他第二趟被秋月推下了木床,却很快,再次被秋月从床下拉到了床上。重新坐到床上后,兴长终于冷静了,觉得秋月的手很烫,再望望秋月红彤彤的面孔,才感觉到了不对劲。
秋月病了。今朝中午,离开木太家的酒席台时,秋月确实是想上一趟茅厕,在路上时,见兴长没跟上来,她就神使鬼差地朝西走了,而没有朝有着茅厕的东面走。这样,她也就把离开这里、离开兴长的想法付诸行动了。可即便这样,她心里还是认定兴长就要追上来的,她边走边等着兴长追上来。让她想不到的是,在她走了六七分钟后,兴长还是没有追上来。她开始奔起来,路两边是刚谢了花的耧斗草以及刚长了星形花朵的龙胆草,它们在快速后退。
秋月想,只要奔到那条南北向的马路上,她就能成功离开兴长、离开这里了。有一点她有把握,如果她向一辆正行驶着的车辆招手,这车基本会停下来,迅速带上她,除非驾驶员是女的。可不幸的是,就在她朝前奔了几十米后,她的肚皮突然痛起来,她停住了脚步,在路上蹲下来。她掐算了一下日脚,“老朋友”还不该来。她全身发冷,额角头上却在冒汗。她也全身发软,好像刚才的一阵奔跑已经用光了她的力气。我病了,我怎么在这一刻病了呢?她问自家,无望地四处望望。她身体的右侧有一条垄沟,一些苍白而有毒的秋水仙正在里面微微摇曳。
我怎么在这时候病了呢?秋月再一次问自家。这时候突然病了,只能表明这一点:老天爷不想让她从这里逃走,至少是现在不想让她从这里逃走。秋月决定回转,她忍着痛开始朝后走,走了一歇后,肚皮痛居然消失了。可她的身体却还在一阵阵发冷。她想尽快回转去,回到她在这个地方暂时安身的那条被头里。
现在,兴长望着阿六头的后背,想起了那个常年在村农贸市场门口转悠的中药行贩,他就朝村农贸市场那里走,想买些芦根,给秋月熬汤退热。他肚皮里涌上了一股水,那股水叫做柔情蜜意。他突然对秋月产生柔情蜜意了。他想起秋月第二趟把他拉到床上的情景,那时,他反而平静下来,心头不再有欲念。不过,让他想不到的是,秋月却捏牢起他的手,放到自家的胸口上。他的手碰到了一片软和暖。可奇怪的是,碰到这片柔和暖后,兴长身上竟然不再像先前一样热血澎湃,他心里涌上了一股委屈的情绪,他的手指有些僵硬,有些想代表他本人表示出一点反抗的意思。他的手刚要朝后缩,秋月就拉牢,紧紧按在那片柔和暖上。看来,在兴长和秋月之间,秋月是“只许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了。秋月说,我先要想办法还你钱,如果实在还不出,再用这身体抵,你说几趟就几趟,你说一生一世,我就做这里的村民。这话,一个礼拜来,秋月已重复过几趟。兴长的手却缩了回来,心里那股委屈的情绪泛滥得更厉害了。秋月用力咳嗽。兴长就立起来,说,我去给你买药。
此刻,泛滥在兴长心头的那股委屈情绪已变成了柔情蜜意。对女人,你一旦有委屈的情绪产生,却还在为她办事,那委屈的情绪只能变成柔情蜜意。
兴长终于拎着芦根跨进家门。他的额角头上有点汗,鼻头有点酸,他的柔情蜜意里又产生了一点委屈。他跨进房间,又推开间壁墙上的门,望到那条荷花被翻转了过来,床单上空荡荡的,像要专门接纳他那股带了点委屈的柔情蜜意。可兴长立刻转过了身,重新向屋外走。
在场门前,兴长仍拎着那只装着芦根的马甲袋。他朝路的西面望着,好像望到了秋月的背影,嘴角上慢慢露了笑。他来这里,好像就是为了望秋月走开时的背影的,秋月的背影是一道好看的景色,他嘴角上的笑更明显了。
四
兴长再次回到了秋月的床铺边。床是新床,散发着秋月留下的淡淡脂粉气,也散发着竹木店里带来的那股淡淡清漆味。
秋月到的第一日,就对兴长说,大叔,不,大哥,你给我另外找个睡觉的地方吧。兴长一呆,晓得自家是碰着前来“借钞票”的女人了。在本地,别的男人也碰着过“借钞票”的女人。其实,一开始,男人就得有两手准备,就像对待春耕,你落下的种子可以让你收获饱满的谷粒,也可以让你收获瘪谷。可是,兴长只有一手准备,他说,不行。话音一落,就把秋月拉近自家,开始了两家子第一趟的短兵相接,却以兴长的落败而结束。秋月最后喘着粗气说,我是没办法,才“借”你的,到时我会连本带利地还你。兴长说,不行,我不“借”鈔票给你,你都把这里的男人当成啥啦?
兴长把话讲大了,他不能代表这里的男人,他只能代表他自家,所以,秋月没有搭理他的话,要朝外头冲。兴长抱牢她,把她朝后拖。秋月犟着,说,你那么用劲,是在抱你的钱,你不要用那么大的劲抱,你放心,你那钱不会丢!
秋月闭上嘴,自家朝后走了。兴长瞪眼望她,叹一口气,说,好,你先待在这里吧。然后,他在间壁墙的门上上了锁。
兴长坐到床沿上,像是秋月仍旧困在床上的被头里,他开口说,还我?一脱手,我就不想要了。
他突然听到了脚步声,心跳加快。他想是秋月听到他的话了,听到他的话后就朝他走来了。他立起来,转身,一步跨出间壁墙上的门洞。他没有望到啥人。走出家门后,他望到了春妹和她八岁的儿子涛涛,他们从西隔壁走来,走到了他家的场门前。他觉得刚才听到的脚步声就是他们俩的。
涛涛望到他,像小鹿一样奔上来,说,带我上香花。
这里的人,把去香花集镇叫做上香花。涛涛的手拉牢兴长的衣角,春妹含笑立在边上。
兴长说,你们哪能晓得我要上香花?
他的目光从涛涛身上移到了春妹身上,目光里似乎还有着一句话:所以,你把涛涛搀过来了?
春妹还是含笑不语,这含笑不语就是肯定的回答。所以,兴长立刻抓牢涛涛的手,开始与涛涛一起上香花了。和曾经有过的几趟那样,他们又走在了通往香花集镇的向阳河河岸上。秋天的向阳河水泛着清亮的色泽,岸边的水柳树里,一只鸰鸟在发出“不苦不苦”的叫声。岸边的红门兰和铁线蕨间,螽斯发出的声音像无数的钟表在嚓嚓走动。在他们身体的左侧,拥挤而肃穆的稻谷子迎风而立,一只麻鸟盘旋在金黄的稻田上方。
村里人上香花白相,就是去吃“小吃”,去望“人轧人”,去听“人吵人”。吃了、望了、听了,也就轧好了闹猛,上香花的目的达到了。多年来,村里人常用“上香花”、用吃、望、听这三样东西来放松自家、犒劳自家的。好多辰光,这三样东西也成为了乡下人节假日的主要组成部分。
可是,今朝上香花,兴长还有另外一个目的。昨日夜里,兴长又寻了发亮,对他说,还你那笔钞票的日脚看来还要朝后拖。发亮挥挥手,说,你不是来讲过一趟了吗?兴长说,秋月又跑了。
秋月又跑了,跟还钞票的日脚又要朝后拖有啥关系?发亮认为没有关系。不过,秋月在同一日里跑了两趟,这让发亮感到奇怪,不过想想又没有啥可奇怪的——村上来了又走、走了又来的女人还少吗?开小店的阿六头曾对别人说,本店已经测算过,六趟!六趟啊!想跑的女人在我的店门前来回路过六趟后,如果永远不看见了,就不再跑走了,像坐藤的瓜,在横泾村这条藤上就坐实、坐牢了!
阿六头的小店开在马路和村路的交叉口。他还说,六,这是个很灵的数字,只要碰到这个数字,一切就见分晓了。而昨日夜里,发亮在兴长面前再次大度地挥挥手,说,我哪能会担心在你这里的这笔钞票呢?他还把嘴巴凑到兴长耳朵边,说,你到香泰路上去寻寻看!如果秋月没有朝老家跑,那么,你应该去香泰路上寻寻看,最近,一些外来妹都朝那条路上跑。发亮继续说,她们认为自家是滴水,香泰路是条河,结果在香泰路上的一家歌厅里,小阿荣还是寻到了他刚讨进门的外地娘子。
香花集镇迎接兴长和涛涛的是一个古老的高大牌楼,穿过牌楼是香达路。路两旁布满摊位,好多摊主手拿电喇叭在高喊,结果啥人也听不清啥人的招揽声。嘈杂声让涛涛兴奋起来,面孔通红,走路都在跳了。在路边,兴长给涛涛买了一串烤羊肉,涛涛就举着这串烤羊肉,跟着兴长转了个弯,走上了香泰路。
相比于香达路的拥挤、嘈杂,香泰路冷清了好多,路两边的香樟树像困了一夜的女人,伸展着慵懒的胳膊和大腿。白天的香泰路确实有着一份慵懒和冷清,而到了夜里,歌声和笑声会使这条路变得很闹猛,灯光和月影也会使这条路变得迷离多彩。这是一条两边布满着歌厅、汰脚店、按摩房的马路,这条马路在夜里走到了香达路的背面,是香达路的白天,却又呈现出了与白天的香达路不一样的闹猛,香泰路用灯光的手势,让属于它的闹猛里有了一股暧昧的气息。
可在白天,香泰路同样走到了香达路的背面,是夜里的香达路,显得文静、冷清。几个年轻女子穿着拖鞋、蓬松着头发,从一家歌厅里走出来,她们是几个被允许在歌厅里过夜的领班,困了晏觉的她们把衣裳晒到了歌厅门前的一根细铅丝上,一些或粉红或藕白的内衣变成了招展的旗帜。
搀着涛涛的手,兴长在香泰路东侧的海通电器厂门边立定。电器厂的对过是一家门头很大的汏脚店,招牌上“君代子足浴”这五个铜字在阳光下闪闪发亮。
涛涛说,我们望猢狲赤膊戏去。
演猢狲赤膊戏的外地人集中在香达路南端的李子园里。
兴长说,好,好。
可他的双脚仍旧立定在原地,目光还是盯在“君代子足浴”店的门口,好像他要寻找的目标就要从门口里走出来。
涛涛用大人一样的声气说,你来这里,就是要发戆吗?兴长说,好,好。涛涛说,猢狲都要跑光了呢。兴长说,好,好。
海通电器厂传达室里的老伯把头探出窗口,对兴长说,是想来厂里寻工作的?哪能不进来呢?进来坐一歇。
老伯面孔浮肿,上面有着一种过于专注、近乎执迷的表情。有时,一个传达室的老伯是需要这种表情的。刚才,在兴长的面孔上,老伯发现了同样的表情。两种相同的表情似乎有着一种引力,老伯和兴长走到了一道。进传达室后,兴长面孔上的那份表情已经涣散,可老伯面孔上的那份表情仍在。其实,这两种表情还是不同的,属于老伯的是一种隔夜醉的表情,属于兴长的是一种梦游者的表情。现在,兴长的梦醒了,而老伯仍醉意朦胧。
老伯盯着兴长,说,你坐。我叫永泉,我回头你,最近厂里刚招进了一个仓库保管员,最近厂里不要人。
兴长在椅子上坐了,涛涛还是立着。永泉的眼乌珠慢慢转了一圈,像是在想啥。一歇后,永泉问兴长,你孙子?兴长摇头,他又问,儿子?涛涛在一旁开口,你才是他儿子呢。
涛涛眼睛里带着挑衅神色。当兴长搀起涛涛的手,打算离開这里时,永泉把面孔凑上来,怕人听见似的轻声说,九月底,九月底你过来就能寻到工作了。别人不清楚这一点,我清楚。
在李子园围篱入口处的一个摊位前,兴长把一块梨膏糖递给涛涛,又缩回手,四处望望,说,叫,叫一声阿爸。
叫一声阿爸就给东西吃——横泾村里好多男人都喜欢这样,他们用这种方式讨取嘴巴上的便宜。可是,涛涛却不肯随便给兴长这种便宜,他说,你不愿给我吃糖,就给里头的猢狲吃吧。兴长说,我就想给你这个小猢狲吃。涛涛说,你想给我吃就提条件了?兴长说,那我还是给里头的猢狲吃。
兴长开始朝李子园里走,涛涛在他背后掼下一句话:你就一家子去吧。然后,他朝李子园一侧的香风路上一窜,跑起来。
兴长叫一声,你这只讨打的小猢狲!
他转身追上去,很快捉牢了涛涛。涛涛犟,可兴长的右手已经捏牢了他的胳膊。兴长的左手把已经捏扁了的梨膏糖朝涛涛手里一塞。
涛涛说,不要我叫阿爸了?
兴长说,不要叫了,阿爸不阿爸的又不是叫了算数的。
五
在香风路边的一个院子里,兴长寻到了媒婆赵梅花。赵梅花说,我只管把她交给发亮,让他把她领给你,其他,我就管不着了,你总不见得要我相帮你生儿子吧?兴长说,我啥也不怪你,我哪能会怪你。赵梅花一面孔迷惑,说,那你来做啥?兴长问,你是从哪里把秋月领来的?赵梅花耷下眼皮,说,哪一个行当没有规矩?你不该来问这一句话,你一定要问,就在我把她交给发亮前问。
兴长望着赵梅花,眼神有点吓人。赵梅花举起手,在兴长的面孔前晃了晃,说,你要做啥?要吃我吗?我不该给你介绍那么年轻的女人。
赵梅花叹了口气,从木椅子里立起来,又开口,你不该问我是从哪里把她领来的,不过,我可以回头你,你那女人一定是碰着绕不开的难处了,否则,肯随随便便来“借钞票”?
这里的人把碰着难处后前来“借钞票”的女人叫“白馒头”,不带馅子。“白馒头”进你的家门时,是不带心的,她的心还是在别的地方。秋月也是“白馒头”,所以她跑了。她甚至一开始就在面孔上表现出了要跑的意思。上趟,她离开木太家的酒席,朝外跑时也是不慌不忙、从容不迫的,正是秋月表现出来的这种从容不迫让现在的兴长心里有了一种讲不清的感觉。这姑娘,哪能一开头就像熟人一样不吓我?在这一点上,她像涛涛——涛涛对他,一直在犟,一直在“挣脱”,明目张胆地,一点也不掩饰。涛涛的这种“挣脱”,其实是建立在对兴长的依赖之上的,那么秋月明目张胆、从从容容的“挣脱”,是建立在什么之上的?他一时想不清楚秋月的“挣脱”是建立在什么之上的,可这不妨碍他心里生出一种毛茸茸的感觉,这种感觉他在面对涛涛时是常有的。秋月那天说,我是想来问你“借”钞票的。兴长说,那你干脆直接来借,做啥还要走赵梅花这扇门?秋月说,不走这扇门,你肯借我?听,她自说自话、自作主张的声气就是涛涛的。
赵梅花把面孔凑近兴长,说,要不你到香泰路上去寻寻看?
她与发亮一样,也认为秋月很可能去了香泰路,不过随即,她表达了一个跟发亮相反的观点:现在,香泰路就好比一根扔在路边的香肠,女人们就是蚂蚁,你想在密密麻麻的蚂蚁里寻出自家想寻的那一只,是烦难的。
不过再烦难,兴长也想寻。他低着头,从赵梅花屋里走出来,再一次来到了香泰路上。正是下昼,香泰路上不见人影子,只望到不少车子在这条路上冷漠而快速地来往。但是,到了夜里,这些车子肯定会在这条路上慢下来,停下来,最后,香泰路两边的香樟树下会停满车子。到那时,香泰路会像困醒过来的人一样,发出大大的声息,这声息里带着酒精和脂粉的气味,这气味就是香泰路的真正气味,所以,白天的香泰路不是真正的香泰路。
兴长走到了香泰路南端的太平桥上,望着落在河面上的夕阳。夕阳胭脂一样涂在河面上,让河水变成了一张姑娘的面孔。兴长对着河面的目光有点呆滞。
一阵风刮过,桥墩子边的一片菖蒲叶摆动了一记,河面上阳光的胭脂没有了,好像就是菖蒲叶的摆动使天色陡然暗了下来,兴长望着河面的目光也暗下来。他抬起头,神情茫然地四下望一望,走下了太平桥,又顺着与香泰路相交的河滨路朝西走几步,在一家杂货店里买了一瓶特价饭,接着进了隔壁一家点心店。
兴长边吃面边吃酒。点心店的老板娘也不怪兴长,她的店里不是没有过这样的人。当兴长把筷子搁到空酒碗上时,两个年轻女子进了点心店,带进一股香气。兴长呆了呆,不过很快醒转来:左边这个穿吊带裙的女人不是秋月,面孔虽像,腰身却比秋月粗。女人的吊带裙是用光感面料做的,很亮,反而把面孔和裸露的肩膀衬黑了,这一点也不像秋月。另一个,更不像了。
点心店的老板娘早已习惯了男客面对美女时的样子,兴长那眼神,让她嘴角处露出一丝宽容的笑,可啥人能肯定这笑里没有讥讽的意思呢?
走出点心店,兴长重新立在太平桥东侧的河滨路上。薄暮下,他抬头,望到三两结伴的年轻女子正由东而西款款走来,她们走到河滨路和香泰路交界的地方,向右转弯,走上了香泰路。她们是来给香泰路制造鬧猛了,香泰路夜里的闹猛就是她们制造的。兴长觉着天地间好像又亮了起来,还感到先前河面上的那些胭脂从水里升了上来,变成了姑娘们肩胛上的粉纱和面孔上的浅笑。在黑暗真正来到前,这些粉纱和浅笑代替了湖滨路上的路灯——这有点让人吃惊,也有点让人兴奋。在香泰路和河滨路交界的地方,兴长想不到会望到这么一种好看的粉红色光亮,他都有点忘了来这里的目的了。
顺着姑娘们的来路一直朝东望过去,大约在千米开外的地方,有一个居民小区。被河滨路一分为二的这个小区是个老小区,建造于20世纪80年代初,姑娘们就是从那里走出来的。从自家的出租屋里出来后,她们点亮了薄暮下的河滨路,也点亮了兴长的灵感:只要等在香泰路和河滨路的交界处,这些姑娘就是主动让他辨认来了,她们扭动着好看的腰身,要让兴长来辨认自家是不是秋月。
像一根系绳的木桩,兴长立在河滨路上,眼睛一眨不眨地朝前望着。可很快,他觉着他的辨认是在瞎起劲,姑娘们的面孔突然变一样了,他觉得是一个姑娘变成了许多姑娘在朝他走来,朝香泰路和河滨路交界的地方走来。他就像是在雾中辨雾,除了感觉到白茫茫一片外,没有别的感觉。他明白自家需要坐下来,从中午到现在,他只在点心店里坐了一歇,其余辰光都是立着的。
可他还是没有坐下来,坚持立着。后来,他用想象把秋月的人样子加塞到了那些走动着的姑娘当中。秋月穿着一件嵌银丝的雪纺衫,脚上是一双平底浅口的黑白纹鞋。她的着打还是到木太家吃喜酒时的着打,她走路的样子还是那样从容不迫,不像是去香泰路上上班,像是要去那边白相。
兴长走上前去,一把抓牢秋月。他抓出了一声尖叫,香泰路口顿时乱作一团。兴长一愣,结结巴巴地说,对不起,认错人了,认错人了。
姑娘们四散开去,一阵香风也四散开去,随着这香风一道散去的还有几句骂声,虽然凶,可也是香的。
看来真要坐下来,坐下来后再慢慢地把秋月从姑娘们中认出来。阿兴意识到寻找秋月是桩烦难事,不是一歇歇能寻到的。要他一直立着,他这把老骨头可吃不消。到哪里坐下来呢?最好的地方还是海通电器厂。它离香泰路和河滨路交界的地方只有十来米的样子,它的斜对面就是那家“瀑云”洗浴中心。
興长走进了电器厂的传达室里。一见他,永泉就说,你哪能现在就过来了?我要你九月底过来的。不过,我猜到你会提前来的。兴长说,你们传达室要人吗?永泉说,你不是想到仓库里上班吗?兴长说,我就想到传达室上班。永泉拍了拍大腿,说,你来对了。我对我阿侄讲。
永泉的阿侄就是厂长,厂长正想给传达室再添一位门卫——永泉又向兴长透露了这个信息。
兴长和永泉同时坐到了一条长椅上,两家子身上散发着同一股“气味”,这是一股讲不清楚,却能够让人意会的“气味”。这“气味”让一个胖子目光里露出了忧虑的神色,胖子正路过门口,他忧虑的目光落在永泉身上。他就是厂长小阿福。
六
兴长上班了,他在海通电器厂传达室里把永泉顶了下去。和所有守传达室看门的人一样,兴长的夜饭吃得早,却辰光吃得长。也和所有“老传达”一样,兴长就着简单的小菜吃老酒。在他吃老酒的辰光,工人都已走光了,厂里很静,可他耳边却仍响着永泉对他说过的话。永泉说,你不要认为守传达室省力,我回头你,你半夜里一打瞌睡,就有人会爬墙头。不过,我已经是“老传达”了,我打瞌睡的话,也没有人敢爬墙头。因为我困着了,也望得见东西。永泉还压低声气说,我望到过厂里发生的好多事呢。他回头兴长,他望到子刚和小英上昼还在厂里吵相骂,中午却“头碰头、脚碰脚”困在仓库里了;他还望见他阿侄小阿福、堂堂的厂长竟然跪在了女工阿花的脚跟前,他做啥要跪下来?因为阿花只穿着一条花短裙;他还望出,啥人下班出门时口袋里藏着厂里生产的智能开关,啥人口袋里没有藏。
兴长不清楚,永泉讲的这些,是他醒着时望见的,还是困着时望见的。兴长想问,可最后还是没有张开嘴。最后,永泉拍拍兴长的肩胛,说,慢慢来,慢慢来,你啥都可以望见。
听永泉这样说,好像兴长不是来上班,是来望啥东西的。确实,他是来望东西的,可他不想望别的,他只想往香泰路上望,他只想望着秋月——一个钟头后,他就差点望着秋月了。
吃好夜饭后,兴长拎出一把小竹椅,坐到了路边。刚上班,他就像一个“老传达”了。在工人们走后,“老传达”总要坐到厂门外,让身后的钢管滑栏半开着,自家则摆出一副懒散的样子,面孔上露出一种散淡的表情。可是,啥人望得出藏在这懒散、散淡后的机警呢?啥人清楚坐在小竹椅里的兴长是在香泰路上认人呢?接着,兴长眼前出现了下面的情景——
先是三个高挑的姑娘,她们边走路边嗑着瓜子。当中的那个拎着一只马甲袋,用来收集三家子嘴巴里吐出的瓜子壳。她穿着湖蓝色的V领针织衫、印花裤子,她左边的那个穿着荧光色的针织衫、皮革迷你裙,右边那个上穿透视的网纱上装,下穿糖果色紧身锥形裤。
接着,又结伴过来三个姑娘,她们的衣着与前面三个一样鲜亮、时髦。她们中,一个穿着褐色矮帮靴、一个穿着T字凉鞋、一个穿着粗跟方头的笨笨鞋(这次,兴长注意了她们的脚)。她们的步子是悠闲而轻快的,她们还向兴长散发过来一阵香气。姑娘们走远后,一个留着板刷头的小伙子揽着一位小姑娘的腰,走过来了。都夜里了,小伙子竟然还戴着墨镜,姑娘的头歪在小伙子的肩胛上,露出的半张面孔像半个括弧,却很饱满,也很白。两家子慢慢走远,小伙子的后背宽阔,姑娘的腰身纤细。姑娘穿着一件雪纺衫,脚上是平底浅口的黑白纹鞋。她的着打是秋月的着打,是秋月在木太家吃喜酒时的着打,而秋月的半张面孔也是又圆又白的。
兴长一下子从小竹椅上弹立起来,小竹椅发出一记响亮的“吱嘎”声,他感觉这声音是从他的胸膛里发出来的,这声音是一声催促。他迅速朝那两个背影奔去。可是,还没上前几步,他就觉得全身发软,脚步慢下来,双脚被啥东西牵绊着似的,走得跌跌撞撞起来。
兴长的秋月就在他前头不远的地方,可是,因为秋月边上有个小伙子,他感到浑身发软,感到根本不能缩短自家和他俩之间的距离。其实,这段距离就是他与小伙子在岁数上的距离,所以,他不怪自家。可是,不怪自家,又怪啥人呢?他望着小伙子的后背,有一只坚硬的拳头从他的脑子里伸出来,朝那个后背打过去,既想打倒那个后背,又想打碎他与那个后背之间的距离。可事实是,他的两条胳膊却一直软绵绵地荡在身体两边。最后,兴长望着小伙子揽着秋月的细腰走进了“花都”歌厅。他在路边的一棵香樟树边立停,说,好,好好,你有了新“花头”,还进了这种地方。他虽然开口了,却讲得有气无力。他吃不准秋月是不是真在歌厅这种地方上班了——就算是上班了,哪能在上班路上还有小伙子陪着?有小伙子陪着,哪能还要进歌厅?
兴长决定等,等秋月和小伙子重新从歌厅里走出来。歌厅门头上的霓虹灯像轻浮女人的眼睛,朝兴长一眨一眨的。顺着树干,兴长的后背滑下来,他坐在了地皮上。他的屁股感受着地皮的凉意,耳朵里则有点温热,这温热是歌厅里传出的歌声在他的耳膜上制造的。他的耳朵在捕捉、在辨别,他觉得哪一种歌声都像是秋月发出的,却又不像是秋月发出的。捕捉与辨别让他耳朵里的温热感更明显了,慢慢地,这温热让他的脑子混起来。
后来,兴长望到了三十几年前的自家。三十几年前,他逛到了他对象菊花那个村窠里,他以后的老婆菊花正跟一帮女人在田里耘稻。她们边耘稻边唱着田歌,歌声带着湿漉漉的水汽在稻田的上方飘荡。耘稻要唱耘稻歌,两腿弯弯泥里拖,眼观六路要看稻里稗,香草黄草一纳掳……他辨出了菊花甜美的声音,却没有辨出了自家一段既甜美、却更苦涩的婚姻——他跟菊花成家后,菊花一直没有生养,她自家比兴长更加急,四处问医求药,后面,她终于死心了,经得兴长同意,从老家的堂姐那里抱养了一个七岁的男孩。差不多一年半后,男孩溺水身亡了。从此,菊花的身体变得很糟,她又开始了四处问医求药的经历,身体却一直不见好,三天两头生病,终于在一个冬天的夜快,菊花永远闭上了她的眼睛,也让兴长走出自家始终充满着一股药味的婚姻。
兴长被响亮的刹车声惊醒,晕乎乎地立起来,以为自家是在凌晨家里的床边立起来,还伸出右手,做出一个推门动作。结果,他的手在空中胡乱抓了抓后重新缩了回去。过一歇,兴长才彻底醒转,原来他是在这里等人,等那个小伙子和秋月从对过的歌厅里出来。
秋月和那个小伙子终于出现在歌厅门口了!兴长马上立直,呼吸也变重。小伙子仍旧用手臂揽着秋月的腰。他终于等到秋月了,他就要与秋月照面了。他朝小伙子和秋月走去,不过,他的大腿在发软,人在摇晃,望上去,他是一个从树边爬起来的醉鬼。望到这个醉鬼在摇摇晃晃地走上来,小伙子和秋月马上立定了。
小伙子眼睛里满是狐疑和警觉。
兴长说,秋月。
秋月说,神经病。
哦,她原来不是秋月。她的眼角那里有一颗痣,秋月没有痣。
七
夜里,查岗的副厂长就立在厂门口,身体呈现出一种等候的姿势,他在等候兴长被迅速开除的命运。
第二日一大早,兴长就卷铺盖走人了。他神情漠然地走到了香泰路上。早晨的香泰路是一个刚刚困觉的女人。她来不及卸妆,就疲惫地困着了,安静而又芳香。她虽然不会因你而醒来,却也不会像海通电器厂一样赶走你。在昨日夜里坐过的那棵树下,兴长立定。对面,“花都”歌厅门头上的霓虹灯已熄灭,可门还开着,他慢慢朝那里走去。在门口带着莲花底座的白色柱子前,保安小伙子用狐疑的目光望一眼兴长,问,寻啥人? 兴长问,秋月在里头上班吗?小伙子回答,里头人多了,谁清楚她们每个人的名字?
兴长回到了家里。过了中午,他又开始在香泰路上来回走动。夜快,他去了湖滨路上那家点心店。又一次,他就着面条吃了一顿特价饭。七点钟左右,他回到了香泰路上,这条路已经醒转,无数霓虹灯重新眨起了风情万种的眼睛。
在原来的那棵树下,兴长坐下来。这时,两个姑娘在他前头走过,她们都把头发染得像灯光一样红,都有着烟熏眼妆,左面那个穿着一身光泽度很高的黑色紧身衣服,样子有点像《蝙蝠侠》里面的猫女;右面那个上身穿着宽口袖镶珠片的衬衫,下身穿黑色西裤,脚蹬一双马蹄跟高跟鞋。她们没进歌厅的门口,继续落北走去。之前,他还望到过两个把头发染成橘黄的姑娘和一个把头发染成棕色的姑娘,她们也落北走了。他意识到,姑娘们的头发是开在香泰路上的另一种路灯,同样照亮了香泰路,也装扮了香泰路。她们藕色的手臂、玉色的头颈、漂亮的衣裳,她们的一切,把香泰路装点成了一个香艳的通道,许多男人乐此不疲地走在这个通道里。可这个香艳的通道与兴长无关,他只是猎人一样守在这个通道边,等待着他自家的“猎物”。
“猎物”终于出现,兴长的呼吸粗重了。秋月正由南朝北走来,他很奇怪,她今朝哪能一家子过来了,他转转头,目光在她身边寻找昨日的那個小伙子。没有,她的身前身后都没有一个男人。这就对了,她应该是一家子的,她哪能可以在马路上随随便便被别的男人揽着腰呢?在她的眼角上,兴长清清爽爽地望到了一颗清晰的黑痣。他的心里涌上一股暖流,感觉到面前的姑娘就是秋月,她是有痣的秋月。那颗痣像夜里的星星,在闪亮。
兴长迅速跑到有痣的秋月面前。秋月立定,望着兴长的目光温润而又柔和。她的目光与昨日夜里不同啦,里头有了一样东西,这东西到底是啥,兴长不清楚,可这东西让他觉得可亲,有着这东西的目光就是秋月的目光。
可是,有痣的秋月突然转身,兴长还来不及对她讲啥,她就转身了。兴长想伸手捏牢她的手臂,可他的手只是在半空中胡乱抓了一抓。
有痣的秋月又立定,惊吓的神色在她的眼睛里闪过。兴长突然说,你回家。
有痣的秋月朝歌厅的门口大声喊,啥人让精神病人过来的?
保安小伙子跨出来,辨认了一下兴长,大声说,走开,走开!
保安没有推兴长,可像推了一样,兴长向马路的当中倒去,倒地的一霎那,他转头,望到秋月正在进入歌厅的门里,她就像狐仙进洞一样,在最后的一霎那,实际上已经显形——她不是他想寻的那个人,可兴长的凡眼认不清这一点。他躺在地上,心里还在怀念着他那有着一颗痣的秋月。
八
兴长打开家门,一股沉闷的粉尘气息扑鼻而来。他拉动灯绳,屋里刚亮,掩上的前门就“吱呀”一声开了。
春妹已经站在门框里头,望着兴长,眼睛里有话。兴长侧转身来。春妹开口说,她来了。
兴长像是没听懂她的话。春妹嗫嚅道,前日下昼,秋月来过,你不在。她又说,她、她公公、别人讲你在香泰路上发病了,我不太相信。春妹还回头兴长,她讲是来跟你了结一桩事的,她不在香泰路上上班,不过,她也没有讲出她到底在啥地方,她只是让春妹一见兴长后,立刻打电话给她。
秋月给春妹留了电话。春妹望着兴长,他的平静让她觉得意外。不过,一歇后,兴长面孔上的表情还是起了变化,眼睛突然变细、聚光,他捏牢春妹的手,想讲啥,却久久讲不出来。
秋月是在第二日凌晨来的。兴长正在困梦头里,被弄醒时,迷迷糊糊地以为自家还是在香泰路上的那棵节疤累累的树下。他被人拉了拉,然后,他望到了秋月。房间里的灯也已经亮了。他在秋月的左眼角上寻找那颗痣,还认为自家是在一个梦里寻找秋月眼角上的那颗痣。在这个梦里,秋月显得既美丽温柔,又一反常态地积极主动。她说,我来还钞票了。
她脱掉了上身的短袖衫,也脱掉了下身的印花九分裤,倒下来。她的手臂绕牢兴长,全身的温热和柔软也绕牢了他。兴长喘着粗气,觉得手脚很重,也感到自家像是被啥东西压牢了,心里产生了一个要挣脱出来的强烈念头。
秋月突然说,照理,你的钱是买了我一世的,可我也想说,我的身体不止这个价,我的身体没有价。
她呜呜呜哭起来。她松开手臂,兴长就在床铺上直起上身,她抓牢他的肩胛,说,你不动?兴长说,我不动。她眼神迷惑地说,你不情愿?
兴长下床,两只脚在地上找寻拖鞋,胸部一起一伏,嘴巴里嘀咕了一声。他想立起来,可秋月的手又抓牢了他的手臂,他就在床口上坐下。秋月也起身,坐在了床沿上。秋月说,你讲啥?兴长结结巴巴地说,你、你不是她。
秋月瞪眼望着兴长,像是想让他再重复一趟刚才的话。兴长又牵动一下嘴唇,却没有开口。秋月说,老头,你脑子进水了。
兴长已经不是原来的兴长,秋月,也已经不是原来的秋月。秋月穿上衣裳,理理头发。兴长也立起来,说,我要去香泰路上寻秋月。
秋月的眼睛里浮上惊愕的神色,她像是想了想,又抚抚兴长的肩胛,说,秋月平时不在那里。兴长说,在哪里?秋月说,在乌雀桥的西边。
话音一落,秋月突然有点鼻酸,她突然有了一种想倾诉的欲望。她重新在床沿上坐下,拉一拉兴长,兴长也重新坐在了床沿上。秋月说,秋月在那边帮人种花、养花呢。在那边,秋月大部分时间忘记了她的苦恼,因为,那些花都是她的客人,更是她的朋友。那边是个花的世界啊,不光有秋月种养的花,也有好多野花。看到这里有人养花,野花都过来了。
兴长一动不动,眼睛也似乎眨得少了。他在认真听了,鼻翼翕动一下,像是闻到了花香。
秋月说,你晓得吗?我们老家人都把花当作客人,老家人来到这里养花,还是让各种花有一个客人的称呼:月季是痴客,丁香是情客,兰花是幽客,瑞香是闺客,含笑是侒客,素馨是韵客,腊梅是寒客……好多花也有一个朋友的称呼:瑞香是珠友,海棠是名友,芍药是艳友,梅花是清友,菊花是佳友,荼蘼是韵友……
最后几句话,秋月讲得像是自言自语,也讲得越来越轻。当她的嘴巴里终于没有声音发出来时,她又在床沿上立起来,然后抬脚。
九
兴长倒下来,倒在了他走向乌雀桥的路上。一个好心的小伙子发现了他,把他送到了医院。
刚到医院,兴长就睁开了眼。大约半个钟头后,春妹来了。过了半钟头,又有一个人来了。
兴长起先没有认出这个新来的人,后来认出了,她竟然是面孔上没有痣的秋月!她是真正的秋月!真正的秋月竟然也来了!兴长黯淡的眼睛亮了起来。可刚亮起来,她就消失不见了。哦,她原来还是没有过来,她原来只是出现在兴长的幻觉里。
医生也没有给兴长查出啥毛病,最后,给他开了一些药后,让他出院了。春妹照顾了他一日,第二日,兴长好多了。
第二日中午,春妹端来了饭菜。然后,她坐到了兴长家的屋檐下。红澄澄的阳光涂抹在兴长家的场门前,一个小泥凼发出一片金黄透明的光泽。吃好中饭,兴长也坐在屋檐下,双脚都放在光滑的踏脚石上。涛涛就在那个小泥凼边玩白相。
春妹的腿上放着一件粗线毛衫,右手拿着的一根钩针快速抖动着。涛涛两只手上都是烂泥,他走上来。春妹说,去汏一汏。兴长从藤椅里立起来,似乎想去帮涛涛汏。他的精神望上去确实好很多了。毫无疑问,医生开的药对兴长的身体还是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春妹说,让他自家去汏。
话音刚落,她面孔上的表情僵住了。她望到场角上出現的两个人影。一下子,她就认出了秋月,秋月搀着一个高个子男子,男子戴着墨镜。春妹不认得他。她立起来,样子很慌乱,好像秋月和男子就要给她带来某种危险。可在离春妹几步远的地方,秋月立定了,面孔上露出了友好的微笑。她让墨镜男子立在原地,然后,自家径直走到了兴长身边,把手放在兴长的肩胛上,说,我,我是你的女人。
这是面孔上没有痣的秋月。秋月举手,指着立在场地上的墨镜男人,又说,不过过几日,我就要做他的女人了。
这次,她是对春妹说的。她转转头,要墨镜男人把墨镜摘了。她的面孔一直微笑着。男子就把眼镜摘了,春妹死死地盯着男子的面孔。她确定了,他是一个瞎子。
秋月面孔上的微笑终于消失了,她说,因为我想给这个瞎子钱,让他家能……而我却没有,所以我来你们这里“借”钞票了。有一次,我是真心想做一次兴长女人的……因为,我恨这个瞎子。
春妹眨着眼睛,想着秋月给瞎子钞票和她来横泾“借”钞票之间的关系,也想着恨这个瞎子和真心做一次兴长女人之间的关系。春妹认为她想出来了,一歇后,却又认为自家没有想明白,就又想。这时,远处传出几声药士代的叫声,打断了她的想。
秋月举手,指指瞎子,又说,我恨这个瞎子。
可她返身走到了瞎子身边,再次搀牢瞎子。
春妹又开始想了,想秋月搀牢瞎子和她说恨这个瞎子之间的关系。春妹微微笑了笑,望上去是想明白了。
瞎子已经重新戴好墨镜。他也在笑,他的笑像是对春妹的笑的回应——他的心,望到了春妹的笑。他又转一记头,把笑对牢兴长。这时,几乎不用想,春妹就望出来,瞎子对兴长的笑是一种胜利者的笑。瞎子的心,认出了兴长,他的心,也应该望到了秋月最初想瞒着他的横泾之旅以及兴长的香泰路之旅。
秋月转身,被她搀着的瞎子也转身了。他们重新朝场角上走去。对着两人的后背,春妹张开了嘴巴,想讲什么,却终究没有出声。
十
第二日,春妹坐在兴长家的屋檐下、涛涛在场门前玩白相的画面又出现了,兴长当然也在这个画面中,他坐在春妹的右侧。
当两个人的影子出现时,一刹那间,春妹以为秋月搀着戴墨镜的瞎子又来了。可很快,她望清楚了,走上来的是两个穿着制服的警察。
涛涛有点吓,跑到了屋里。他的举动让春妹也紧张起来。可两个警察却是和颜悦色的。
高个警察把面孔转向兴长,说,那只“白馒头”呢?她在吗?
警察居然也用“白馒头”来称呼那一类外来姑娘,这让春妹心里的紧张感稍稍得到了缓解。
春妹代兴长回答,她走了。高个警察问,清楚她去哪里了?
春妹张了下嘴,却没有出声。她的目光投向了兴长,兴长开口说,去了乌雀桥的西边。
两个警察像是没有听清楚兴长的话。矮个警察问,哪里?兴长说,乌雀桥的西边。春妹问,哪里?
兴长不回答了,他似乎不屑于回答第三趟。
两个警察倒像是清楚了兴长的话,笑了,不过他们面孔上的笑很快就消失了,面孔上的神情变得有点严肃。矮个警察说,我们了解到你们这里来了只“白馒头”,所以,先来摸摸情况。高个警察突然用有点自吹自擂的声气说,这种女人,我只要望一眼,心里就会清楚,她是来“借钞票”,还是纯粹来骗。所以,我只要望一眼,就能确定,要不要把她带走。
矮个警察问,乌雀桥的西边,这范围也忒大了!
矮个警察记起,有一年秋天他曾去过乌雀桥的西边。在桥堍那里再朝西走一点路,是兴业稻米合作社的轧米厂。除了这家轧米厂,乌雀桥的西面就是无边的稻田和无数的农村房子。农村房子被一条踏白了的泥路串了起来。泥路靠田的一边,布满着香豌豆、三色堇、野菊花。
春妹抬头,说,她再回转的话,我第一辰光来回头你们,打你们电话。
十一
高个子警察姓陶,矮个子警察姓韦。陶警察说,其实,我不恨那些到这里来的“白馒头”。韦警察说,要你恨不恨的做啥?做我们这个行当的,最好不要用这个词。陶警察说,你有个亲妹妹,让她去做做“白馒头”看?韦警察说,不要拿我打比方……我们回去吧。陶警察说,不过,既然他说了……我们还是去一转吧。
最近,单位领导正打算提任陶警察,所以,他在工作上正处处积极着。好在韦警察没有反对他的提议。两家子就朝着乌雀桥的方向走去。
没过一歇,两家子就立在了乌雀桥上。这是一座高大的三孔石拱桥,不清楚建于哪个年代,栏杆、栏板都残缺了。可是,残存的栏板上雕刻着的黑色麻雀却还是那么栩栩如生。桥顶上的一块紫石板上,也雕刻着两只乌雀,这两只乌雀比栏板上的乌雀明显大得多了,它们正在飞翔,张开的肌扇差不多占满了整块紫石板。陶警察的一只脚踏在了桥顶的紫石板上,就踏在了一只乌雀的肌扇上。一刹那间,陶警察有一种腾飞的感觉,他也突然想起,他脚下的这座桥原来还有一个名字,叫“飞桥”。好多年前,他来过这里,忘记了是来办案还是怎么的,当时他还上了桥。一位老人同时跟他上了桥,老人脚步蹒跚,陶警察就搀扶了他一下,老人就用漏风的嘴巴跟他讲起话来,说,老代里,这乌雀桥还被人叫做“飞桥”。老人的一只脚踏在了乌雀的肌扇上,身体摇了摇,那摇晃就像是飛之前的摇晃。在陶警察的眼里,老人当然没有真的飞起来,可在老人自家心里,他认为他已经飞起来了,因为他又说,上了桥顶,只要踏在乌雀的肌扇上,你就飞了,你和我现在就飞了,我们只要走下这块石板,两只脚踏到对岸的泥地皮上,我们就飞到了十年后的今朝。
那么,脚下的“飞桥”让人飞过的是“时间之河”了,这条“河”的宽度是十年。陶警察低一低头,望着乌雀桥,也就是“飞桥”下面的河水。乌青的河水在慢慢地流动,不过望上去,是河水上的浮萍、荇菜、没有沉下去的树叶在朝前流动。陶警察又抬头,天上,白云朵朵,它们似乎在快速移动,它们快速移动还似乎带出了猎猎风声。飞的感觉真像袭上了陶警察,他感觉不到了自家的重量,而以前那位老人的话又在他的耳边响起:只要走下这块石板,两只脚踏到对岸的泥地皮上,我们就飞到了十年后的今朝。
陶警察终于抬脚,走下桥顶的紫石板,朝着对岸走去。韦警察跟上。两只脚一踏上对岸,陶警察对韦警察哈哈笑一声,说,小韦,我们飞到十年后的今朝啦。
可十年后的西岸和现在的东岸是一样的,是一条发白的泥岸,泥路的两边长满着马唐草、鬼针草、菖兰、杜鹃等花草。陶警察又哈哈笑一声,说,这些野草野花哪能还是十年前头的?
对陶警察的话,韦警察不明就里。他没有碰着过以前的那位老人,也不晓得乌雀桥又叫“飞桥”。不过,对陶警察的话,他没有出声表示啥。
有一条东西向的煤渣路连接上了南北向的西岸。韦警察说,铺煤渣了,以前是条泥路。
立在煤渣路的顶端,陶警察转头四顾,望到的是大片的荒地,荒地上长满着车前草、狗尾巴、牛筋草等野草。野草里布满着碎砖瓦砾、被人遗弃的破碗旧席。几只野猫在小鸡草丛中抢夺着啥,在相互追逐。突然间,它们似乎感受到了陶警察的目光,纷纷向着一旁窜去,转眼消失不见了。陶警察突然感到有点恍惚,他记不得他有没有望到过眼前的这大片荒地,也记不得他在这片荒地上有没有望到过大片房子。他笑着摇摇头,还是觉得这是正常的,无关传言中的“飞桥”。确实,这一两年,这个地方,一夜之间,会有好多房子被拆掉,然后腾出大片的土地等待建造“工业园区”或“现代化农业园区”,可由于种种的原因,开工的日脚被拖延了下来,甚至是被无限拖延了下来,腾出的土地就荒芜了,长满了杂草,出没着野猫野狗——韦警察的话印证了他脑子里的想法,韦警察说,这里也拆迁了,我上趟来,还都是稻田和农村房屋。
煤渣路把那片荒地一分为二。在荒地的最西面,也差不多是煤渣路的最西面,陶警察望到了一幢四方形的高大房子,灰黑色的墙面,灰白色的石棉瓦顶。灰房子位于煤渣路的北面。南面是一条长长的弯弯的竹篱笆,朝南延伸到一条小河边。
陶警察在煤渣路上走起来,韦警察跟在他后头。两家子走了不长远,闻到了一股淡淡的香气,也听到了乐器的声音。这时候,两家子还望到一些人在灰房子和竹篱笆之间走动。
两家子又朝前头走了几步,晓得他们是碰到办丧事的人家了。韦警察有点迟疑,提议回转。陶警察说,既然来了,就去望望。
终于到了灰房子的边上。灰房子的门口,立着一个面孔瘦削的高个子男人和一个胖嘟嘟的妇女。男人的面孔侧转着,妇女则用警觉的目光望着陶警察和韦警察。陶警察对她笑笑,说,没关系,我们在河那边办事,办好后过来散脚头的,就望望,你们忙你们的。
妇女的神情松缓下来。妇女穿着暗红短衫,深灰长裤,她的神情开始变得淡漠。煤渣路南面的竹篱笆围着的原来是一个花圃,很大。平时,陶警察只认得有限的几种花,现在更是觉得眼前一片五颜六色,就把头了开去。灰房子的门口朝南,也是朝着煤渣路。里头有几个穿着黄袍的光头男人在转圈,他们手里拿着不同的乐器,演奏着。他们演奏的是“扫头”。两个警察是听不明白的。他们也没看清楚道士们围着的那个长方形的堆满着鲜花的东西是啥。或者正因为堆着鲜花,让他们一下子没看清楚。可也就是眨几趟眼的工夫,他们清楚了那是啥。靠墙的两边,各坐着一排男女,都戴着孝,有重有轻。望到门口的两个警察,有几家子的眼睛里露出不安的神色。陶警察摆摆手,面孔上再次露出笑来——尽管他觉得这笑与灰房子里的气氛是不搭的。不过,他的笑还是让里头那几个人安定了下来。有一个妇女拎起脚边的一只小篮头,走上来,摸出两只用苏木水染成紫红的蛋,递给陶警察和韦警察。两家子摇头,表示不吃。在妇女放回红蛋时,陶警察觉得她很面熟,却一时又想不起来在哪里见过她,他开口说,你面孔熟。妇女说,你也面孔熟。
陶警察觉得立在灰房子的门口总归影响人家,不大好,就在道士们停止演奏、开始念经时,转过了身体,韦警察跟上。陶警察见刚刚碰到的那个面孔瘦削的男人已经立在了花圃里,正在抽烟。他还是侧转着面孔。他的右边,是一排盆栽的月季,有红的,也有黄的,花枝在微风里抖动。月季,陶警察认得。男子左边,种在地上一团团粉色的花,陶警察就不认得了。往南面不远处,有一排三个塑料棚子,望过去,三个棚子里都是红红绿绿的。
陶警察走到了男人边上,说,这个地方动迁了,就要开发,哪能让你们种花了?男人说,反正这地也闲着。男人感觉到了陶警察没有一点坏意,就放开了说,我们租了边上的轧米厂,就可以顺带着搞个苗圃了。
陶警察转头望望灰房子,突然想起,他曾听说,这个地方有的老厂房由于建造年代久远,被列为工业遗产,即便周边动迁,也不能拆除。那这座老旧的轧米机厂就是面前这个男人临时跟香发集团租的,可一个外地人,哪能有那么大的本事跟香发集团搭上关系呢?
陶警察觉得他是想多了,又突然想到自家来到这里的目的,就大声对那男人说,你接下来不要出声,不要讲一句话,你只要出声,我就对你不客气。
男子显然被吓住了。望上去,他像是在脑子里搜寻着近期发生在他身上的事,表情显得既惊愕又紧张。
陶警察说,你跟你老婆的花圃以前在别的地方,几年前,搬到了这里。你们还把河对岸的一个老人接到了这里。今朝,你们在为这个老人操办丧事。
男子的嘴唇皮在动了,几乎就要张嘴了,可是,还没等这张嘴巴里发出声音,陶警察就再次警告男子,你想讲啥?讲好了你不要出声的!
男子的嘴巴抿拢,眼仁朝上翻,不再出声。
陶警察还想对着男人讲啥,却只是向边上的韦警察挥了挥手,说,我们走吧。
两个警察走上了煤渣路。陶警察说,你有没有注意刚刚要给我们红蛋吃的那个妇女?韦警察说,哪能讲?陶警察说,你觉得面熟吗?韦警察说,是的。陶警察说,我们在过乌雀桥前,望到过她。
韋警察的表情显得懵懂。陶警察又说,你注意到了刚刚那个男人的眼睛没有?韦警察说,没有,你在跟他说话时,我在看着暖棚边上的文竹、大丽花、东洋荷花和暖棚里的康乃馨和夜来香。陶警察说,你居然识花的?韦警察说,识的。陶警察说,他的眼睛是有问题的。韦警察说,啥?陶警察说,我估计他看不清东西的,他可能是个瞎子。韦警察说,可他听得清话,他不是聋子。
两家子走完了煤渣路,走到河岸上,可他们没有过桥,他们就在西岸上朝南走。西岸靠河的这边,全是从河里爬伸过来的东洋草的藤蔓梢头,碧绿生青。
陶警察说,这几年,他们照顾了那个死去的老人。可老人,做了这个男人的眼睛。
两家子身体左边的河里,突然发出一声响,原来是一条白水鱼跃出了河面,又突然重新钻回河面。白水鱼发出的动静像是一道光亮,照亮了韦警察的大脑。他不再懵懂,像是啥都清爽了,说,那个女人就是在河东的那一个,跟我们说过,要第一辰光来回头我们,打我们电话。
原来,韦警察也晓得乌雀桥又叫飞桥。
责任编辑 赵剑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