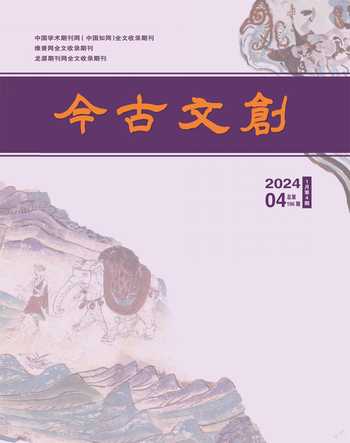萧条与破灭下的微光: 《人鼠之间》中的“希望” 书写
刘玉
【摘要】20世纪30年代,美国经济大萧条,诸多美国人梦想破灭。约翰·斯坦贝克笔下的《人鼠之间》以出色的情节安排,用悲剧形式让读者感同身受,表达了黑暗之中仍有希冀的观点,反向鼓舞了与书中主角一样梦想破灭的人们。他通过描写普罗大众在艰辛中前进的生活,刻画出他们身在无间、心在桃源的人性光彩——善良、坚韧、为生存而战的绝勇,让读者感受到了梦想、情感以及人性三个层面的希望,鼓励他们在磨砺中不失本心。
【关键词】约翰·斯坦贝克;《人鼠之间》;希望书写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4)04-0023-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4.04.007
一、引言
20世纪30年代,美国经济大萧条,粉碎了无数美国人的梦想,那时,美国人的幻灭感随处可见,但萧条与破灭之下仍然闪烁着希望的微光。
约翰·斯坦贝克(John Steinbeck)被称为“人性价值的捍卫者”[1],“他善于描写人类在贫苦艰难的物质条件下各种生存状态”。[2]他笔下的《人鼠之间》以出色的情节安排、用悲剧形式让读者感同身受,表达了黑暗之中仍有希冀的观点,反向鼓舞了与书中主角一样梦想破灭的人们。《人鼠之间》(Of Mice and Men)讲述了精明的乔治(George)和轻度智障儿莱尼(Lennie)的故事。两人从小一起长大,在加州一富人农场工作。他们努力奋斗,梦想终有一日可以攒够钱买一块自己的土地,种菜养鸡,过上安宁生活。然而,钱快攒够时却发生了意外,梦想最终幻灭,莱尼也因此丧命。《人鼠之间》以其悲壮的结论而闻名,向读者展示了人类关系的复杂性和严酷的生活现实。结局虽悲,书中却贯穿了许多底层人民积极向上的希望元素,主要表现为梦想希望、情感希望以及人性希望,对当时正在经历萧条打击的读者来说具有不可忽视的鼓舞作用。
二、梦想希望:生活动力
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梦,不仅是在灰暗日子中继续生活下去的动力,也是角色之间形成友谊的催化剂和黏着剂。
共有一个土地梦犹如枯木逢春。由于莱尼是一个低能儿,时常惴惴不安,乔治为了安抚莱尼,编创了一个美好的土地梦,并且多次同莱尼描述梦幻中的精妙家园,反复畅想着一个只需600美金就能成真的看似触手可及实则虚幻的梦想。这个共同的梦想成了乔治和莱尼友谊开端,也成了支撑他们在一贫如洗的生活中吃苦耐劳坚持下去的动力。
会做梦的人是心中还有希望的人。乔治和莱尼之间有一种正常人与低能儿的对比,这一对比衬托得土地梦更加难能可贵。作为正常人的乔治一开始并不觉得这个梦想有实现的可能,更多的是把它当成是幻想,因为“一个幸福的人从来不会幻想,幻想只发生在愿望得不到满足的人身上”[3]68,他知道像他们这种社会底层的农工是根本购买不起土地的,他们最多只能在属于别人的土地上累死累活地劳作,正如黑人克鲁克斯(Crooks)所说“我看过太多想要自己买地的人了,他们没有一个人成功过”。[4]52但当乔治重复讲述土地梦时,他情不自禁地对这个梦添砖加瓦,把细节雕刻得越来越清晰,以至于他也陷了进去。他说:“我们有一个未来……我们将拥有一块大菜地、有兔与鸡。”[4]10
然而,在低能儿莱尼眼中,这个梦想从一开始就是可以实现的,这对他来说就是触手可及的希望,是真实可见的未来。为了这个美好的未来,莱尼逆来顺受任劳任怨,只知道埋头苦干拼命干活;有人对他言语侮辱,他忍气吞声,有人对他拳打脚踢,他绝不还手。因为在他那单纯清澈的脑海中,他并不在乎其他,只想等待梦想实现的那一天。土地梦是莱尼活下去的动力,也是他生活里的全部目标。他不像其他农工那样,工资一到手就去消费,到酒吧喝酒、去下等妓院过夜、去赌场赌钱。这显得他与别人格格不入,但是莱尼“根本不是精神失常,而是代表所有人的模糊而强烈的愿望”。[5]218低能的他无法自知梦想无法实现,因而被困于精心装饰的梦想房屋里,坚信所有苦难终将远离,他甚至比这个梦想的编造者乔治更相信其实现的可能。如果把莱尼同乔治对梦想的态度放在一起对比,那么,与其说莱尼是一个智商欠缺的低能儿,不如说他是一位坚定的理想捍卫者。穿上梦想的铠甲之后,痛苦仿佛离他很远。这样一个不受现实所扰的他,是幸福的、有盼头的、也是有生命力的。
可见梦想的作用是伟大的,土地梦将乔治和莱尼捆绑在一起,让他们不至于孤单无助;同时,土地梦也联结了农场里的其他农工,延伸出友谊纽带,包括坎迪(Candy)和克鲁克斯(Crooks)。从此,以乔治和莱尼为中心的农工小团体中涌动起了一股温馨潮流,被命运掌控无法翻身而麻木不仁的他们有了情感寄托和希冀,使他们在苦难艰辛的劳作生涯中看到了一丝微光。
三、情感希望:友谊纽带
令人畅想的土地梦衍生出了友谊的纽带,为农场中的弱势群体带来了情感的希望,让他们感受到人际间的温暖,不至于在麻木不仁的日子中迷失自己。
在农工小团体中,最坚固的友谊紐带当属乔治与莱尼,他们之间的友谊被苦不堪言的日子衬托得格外珍贵。小说开篇,乔治一直为莱尼说话,牧场老板对他们的关系持怀疑态度:“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人给另一个人惹那么多麻烦。我只是想知道你的目的是什么”。[4]15他认为,人和人之间只有利用和被利用,并且二者之间总是有等级制度的。从老板的角度来看,莱尼是一台赚钱的机器,乔治帮他说话只是想利用他来拿走他的工资。老板认为所有的工人都是为了工资而工作的,而不是为了人的依恋或者人的情感。乔治与莱尼之间的情感纽带在不被认同的环境中显得更加坚固了。这段友谊让他们即使身处前途未卜的悲惨命运中,也坚信自己是与别人是不同,至少他们还可以当对方的倾吐对象,可以给予对方被农场中的人视为异类的罕见关心。正像乔治说的那样,他们是有“未来”的人。[4]10
莱尼虽然是低能儿,但在乔治的生命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对乔治来说,他口中所谓的“未来”其实建立在他自发地对莱尼身为弱者的保护欲和责任感之上,因为这種友谊的责任感是他能够避免麻木堕落的精神支撑,也是他能够存下钱的基本前提。农场工人们忍受着严酷工作,每日在酒精和性之中麻痹渡过。作为一个底层劳动者,乔治受教育程度不高、经济能力有限,如果乔治没有莱尼,他更倾向于与大多数农工一样麻木度日,正如他所自述的那样:“月底我可以带上我的五十块,进城去买想要的东西……可以整晚呆在猫屋,可以去任何想去的地方吃饭,点任何能想到的食物”。[4]8而乔治在于莱尼相依为命的日子里却并没有做过这些事,所以,乔治因这段友谊变得坚强,日子也有了盼头。因而,在中篇小说的结尾,莱尼的死才会成为击垮乔治精神寄托的直接原因。当乔治失去这段令他变得更好的友谊的时候,他便也失去了生活的希望与动力。虽然他仍然有机会与坎迪一起继续为土地梦奋斗,但他拒绝了坎迪的提议,又过回了没有目的的麻木生活。可失去了这段友谊的乔治“正在宣判自己与其他孤寂地在农场上漫无目的游荡的人一样的命运”。[6]260可见,友谊纽带是乔治劳碌奔波生命中的一丝光明,带给他的希望是至关重要、不可抽离的。
残疾老人坎迪渴望着友谊给生活带来的温馨。坎迪是一名年迈的农场清洁工,在一次事故中,右手意外被机器碾碎,因此只能在农场打杂。其他人上工时,坎迪只能扫一扫工栅。他在这个世上没有任何亲属,唯一陪伴在他身边的,是一只牧羊犬,却因为上了年纪瞎了眼被人处死。他从牧羊犬年老体弱的悲惨命运中预见到了自己的未来。随着衰老的临近,坎迪担心当他对农场主完全失去价值时会被抛弃。坎迪意识到自己处境是如此的不稳定,非常希望能平静地度过余生。就在此时,坎迪无意中听到乔治与莱尼对自己拥有一个农场梦的描述,这个梦实在让人无法自拔,坎迪随即将其视为希望,拿出毕生积蓄与乔治与莱尼结盟,积蓄中甚至包括他意外断手的补偿费。加入乔治和莱尼的行列后,坎迪不知不觉对他们产生了依恋,认为他们是可以依靠的家庭成员,因为其他农场工人只把他当作无用的残疾老人对待,而乔治和莱尼给了他朋友般的关心和照顾。坎迪心中的不安之感也因此减少,他在乔治和莱尼身上看到了自己能够安享晚年的希望,希望可以结束此前老无所依老无所养的孤苦状态。
马厩长工克鲁克斯也得到了友谊纽带给他带来的情感希望。克鲁克斯是位黑人,肤色决定了他无可避免地比别人多了一重压迫——种族歧视。农场主眼中,他是一位“黑鬼”,只要一发火就拿他发泄脾气。克鲁克斯的住所非常简陋:一个狭小的、靠在牲畜屋舍墙壁上的马具房。他不被其他农工们待见,只有在圣诞节的时候才被允许进出他们的工栅。在这样的情况下,克鲁克斯被彻头彻尾的孤立,根本无法与他人取得一丁点的沟通,也无法获得交心朋友。好在他这种积郁多年的压抑与孤寂感被莱尼打破了。莱尼的单纯、善良和迟钝让克鲁克斯放下了戒备心理,由于莱尼的处境也并不乐观,因此克鲁克斯在他身上看到了自己,得到了安慰。莱尼不会主动攻击任何人,不会因为克鲁克斯是黑人就歧视他,莱尼这就成了克鲁克斯唯一的、特殊的、不会受威胁的倾吐对象。一个常年积郁的人是需要排解的,否则只会在无休止的精神内耗中抹杀自我。敞开心扉地对莱尼诉苦,让克鲁克斯得以排解他的苦楚、创伤和郁闷。
友谊纽带对莱尼、乔治、坎迪、克鲁克斯的作用是巨大的,那是一种与伙伴同在的希冀,一起面对苦难会使苦难减半。友谊,让他们在无边黑暗的日子里尝到了一丝甘甜。
四、人性希望:纯善尊严
乔治与莱尼的共同梦想以及友谊纽带的延伸唤醒了农工们麻木的心,让他们相信这世间并不是一无是处,也存在着人间真情与真爱,乔治与莱尼也成了展现人性尊严与纯善的两处高光点:莱尼守护了人性的纯善、乔治捍卫了人性的尊严。
善良与同情无疑是治愈苦痛的良药,莱尼的单纯和天真激活了乔治的爱心与责任心。即使乔治会经常数落抱怨莱尼,但他对莱尼的关爱从没有减少,他们的关系至纯至善。这段美好的情谊也感染了其他农工,年老的坎迪愿意奉献毕生积蓄助力土地梦;一开始对莱尼乔治的友情持有鄙夷态度克鲁克斯,在听闻他们二人已经快要凑够购买土地的钱财时,愿意免费帮他们干活,因备受孤立而一向对世界有着警惕心理的他,也相信了善良的乔治与莱尼会拿他当伙伴,相信了人性的纯善。年老农工坎迪和黑人克鲁克斯的一举一动都证明了乔治与莱尼梦想与友谊的巨大号召力与感染力,人性的纯善光辉得以在麻木黑暗的天幕上划破一道裂缝,透出光亮,铺散开来。
然而,处于社会底层农工们即使是纯善的,却是难以获得尊严的。小说中最悲伤的情节莫过于土地梦在就快要实现的时候化为泡影,这一情节设计揭露了农工们拼尽全力也逃不脱被压迫的悲惨现状。莱尼失手杀死了农场主儿子科利(Curley)的妻子,科利得知后声称要以惨无人道的方式报复莱尼,乔治为了帮莱尼躲避迫害,只好开枪杀死了他。
表面上看,莱尼的智力缺陷与精神问题是他死亡的原因,也宣告了他和乔治情谊的终结;但事实上,莱尼一直受到牧场等级的压迫。作为一个无法为自己发声也无法适应环境的他者,他被边缘化了,也被剥夺了思考个人需求的权利。莱尼无法理解他人,也无法理解自己。只有在乔治的陪伴下,莱尼才能找到短暂的生存空间,因为乔治是唯一能与他交流并且产生共鸣的人。
莱尼作为人的尊严被乔治完好地捍卫了。为了将莱尼从科利痛苦的复仇中拯救出来,乔治才向他开枪。这一过程与卡尔森(Carlson)处决坎迪的狗相似,但二者本质却不同。牧场工人尔森要求坎迪把他的老牧羊犬赶走,因为它闻到了小屋的气味。卡尔森认为牧羊犬变得令人讨厌,而且太老没有用处。“我会替你开枪打死他。那样就不会是你干的了”。[4]30尽管卡尔森认为杀死这只狗可以帮助它摆脱痛苦,但这揭露了他残忍和功利性格。卡尔森射杀这只老狗的时候,包括首领斯利姆(Slim)在内的所有其他工友都秉持同意态度,支持卡尔森最好杀死这只牧羊犬,而不考虑坎迪对同它的深厚感情。“这只老狗毫无用处,令人不快,阻碍了平房和牧场社会的顺利运作”。[7]326可见,坎迪为他的狗求饶是徒劳的,因为情感依恋在麻木和逐利的环境中没有任何意义。
卡尔森杀死坎迪的老狗,是趋利避害的争利益谋杀,而乔治无奈射杀莱尼,是捍卫尊严的反压迫谋杀。只有乔治欣赏莱尼的温柔和人性的纯善,但他必须杀死莱尼,因为这是防止莱尼遭受更多虐待的唯一方法。在惨烈的命运跟前,乔治并没有缴械投降,他手中的枪化身成了他与命运对抗的武器,宁愿从此以后独自忍受无尽的自责与痛失好友的巨大悲苦、独自麻木不仁地继续在这世间游荡,也不愿意让自己的朋友失去尊严地死去。乔治深知,压迫者往往喜爱将自己的愉悦感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不堪之上,一旦莱尼落入科利手中,必然会遭受无尽的折磨。因此,乔治射杀莱尼的那一枪,是反抗农场主压迫的毅然决心,也是爱与恨的交织,爱莱尼的单纯与善良,也恨世界的不公。
在故事的结尾,乔治枪杀莱尼扼杀了他们的梦想,但却没有扼杀他们的人性之美。土地梦终将幻灭,正如海德格尔说的那样,“当代世界遭到技术时代的威胁,技术日益把人从地球上剥离开来,人丧失了存在的根”。[8]122买一个小农场的梦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莱尼工作和赚钱的能力,而这一项能力是他从莱尼身上获得的。因此当他失去莱尼时,又回归了以往堕落的日子,赚不到足够的钱。他们的土地梦想也许永远无法实现,但他们的友谊却已经永恒在人们心中。感人肺腑的深沉友谊并不会因死亡而告终,因为它处处闪耀着人性的光辉,揭示了苦难之下友谊尚存的人性尊严,终将变成人们心中坚定不移的信念和勇往直前的追求。
五、结语
《人鼠之间》讲述了经济大萧条背景下农民的苦难,约翰·斯坦贝克揭露了美国底层人民的真实情况,他替穷苦人发声,为受迫者申辩,通过描写普罗大众在艰辛中前进的生活,刻画出他们身在无间、心在桃源的人性光彩——善良、坚韧、为生存而战的绝勇,让读者感受到了梦想、情感以及人性三个层面的希望,鼓励他们在磨砺中不失本心、重燃对生活的斗志。
参考文献:
[1]刘芳宏.闪耀的人性光芒——解读《愤怒的葡萄》中的人性魅力[J].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2015,34(01):112-114.
[2]高绮.从《人鼠之间》两种汉译本的对比赏析看剧本小说的翻译[J].今古文创,2021,(34):117-118.
[3]戴维·洛奇.二十世纪文评论[M].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68.
[4]Steinbeck,J.Of mice and men[M].New York: Penguin Books,1993.
[5]董衡巽.美国现代小说家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218.
[6]Cardullo,R.On the road to tragedy:George Milton’s Agon in Of Mice and Men[J].CLA Journal, 2011,54(3):257-267.
[7]Owens,L.Deadly kids,stinking dogs,and heroes:the best laid plans in Steinbeck’s Of Mice and Men.Western American Literature,2002,37(3):318-333.
[8]王岳川.二十世纪西方哲学性诗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