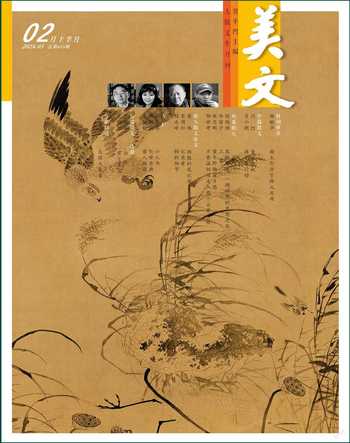百业图【小人书】
蔡小容
七叶一枝花
前些年,夷陵广场边的古玩巷子里卖旧小人书的店还在,我每次回宜昌都会去店里盘桓一番,这本《七叶一枝花》大约是十多年前在那里买的。画的是长阳县的故事,长阳属于宜昌,画家也是宜昌籍贯的汪国新。1980年代初,汪国新夫妇为创作长篇连环画《长江三部曲》,二十次沿江采风,从长江源头到入海口,一路担着婴儿,行程十万里,颇为动人。那是后来的事了,这本《七叶一枝花》是1974年出的,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据店主说,湖北版的书要贵一些,因为印数少,其实不少,印了20万册。我看中这本书,不光因为宜昌、长阳,以及画中出现了的武汉长江大桥,主要还是画面生动质朴,一丝不苟,好看、耐看。画家的早期作品里面有他的初心。
七叶一枝花是一种草药。这本书情节简单,讲一位乡村赤脚医生不畏艰险攀山采药,跋涉千里给群众送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情节我常视而不见,我看进眼里的都是画中的景致、情趣,仅“七叶一枝花”这个美丽的草药名,已引发我无限的遐思。
这位乡村医生叫张思群。文字描写她“短发圆脸,英姿飒爽,朴实敦厚”,图画中的人物形象果然如此,圆脸,衣服略带土家族特色,背药箱,穿草鞋,裤腿挽起,双手正往脑后系头巾,确实有股飒爽的精神劲儿。这是亮相的静态,动态则取脱跳的一瞬间——她听说有人摔伤了正在抢救,马上丢下锄头,抄近路向山下奔去。她抄近路是踏过山中涧流,水中的一排山石,她前脚准确地跳在其中一块上,后脚在动势中后跷,可预见马上也会快速踏上前一块石头。她奔跑的姿态紧凑、有力,充满动感和美感,可见画家凝练的功夫。
凝练是一种简约概括,而书中画面最突出的特点,是繁复曲折。比如张思群走到大队卫生室门口,一个社员告诉她有人摔伤了,画面是怎样安排的呢?大队卫生室是在一个院子里,“向阳大队卫生室”几个字写在院中正屋的门楣上,思群扛着锄头,正踏上正屋前的台阶,一个社员是从侧面的木楼梯上走下一半来跟她说这句话。说句话,格局这么有趣,一点也不平铺直叙。我有时从老巷子走过,看着巷子两边的人家,这边二楼门廊里的人一边择菜,一边隔空跟那边三楼晒台上的人说话,觉得实在有趣。书中还有后面思群在家中写信的一幅。她家的结构是房间靠大门,院子在后面,画家从后院这边取景,左厢房的门朝过道,右厢房的门朝后院。我们看见思群坐在右厢房里写信,与她隔了房间的墙,大队书记正要走进大门,而她还不知道——曲折深致,空间的分割与布局太有意思了,我真想走进这房子里去。
大队卫生室的院子里,斜着的木楼梯下方还画了几个簸箩,晒着药材。这几个簸箩不是必须有,但有就不一样,它们是鲜活的细节,使画面饱满。思群赶到药房去看受伤的大娘,画家并没有跟进药房去,而是在门外,从门框里画出她查看大娘伤情的情景,同时画出了门外加工药材的一些木器、工具,以及透过窗户看见的一格一格的中药材抽屉。
伤情紧急,她们用担架抬起大娘,走出药房。这里,侧面取景,我们看见的是药房外走廊的横截面,她们抬担架穿过,药房的砖石结构与木结构,砖、石、梁、柱、栅栏、屋檐,繁处不少一笔,简处则从略,疏密有致,避免坠重,稳固的房屋衬托她们行动的迅疾。走出大门,刚要上山,忽见山顶开来一辆大卡车。山势绵延,山路迂回,此时看着像是在对面山上的车,是将要开到她们这边来的,下一幅她们招手拦车,画面留出一半给她们身后的一长条石阶,通向来时的药房——那么,这幅就像是补叙,照应前图。从来“人贵直,文贵曲”,婉约的文字、曲折的景致、多重的层次,都比平白直接要引人入胜。


《七叶一枝花》,根据长阳县文艺创作组同名小说,来层林改编,汪国新、王文华绘,湖北人民出版社1974年2月第1版
长阳是山区,风景秀美,如果常居此地,何须采风,放眼望去,横看成岭侧成峰,只看如何选取最佳角度,来配合情节、人物的呈现。司机帮忙抬大娘上车,掉转车头快速向山顶开去,这幅是低视点取景,低于卡车,高视山峰,近处的一棵大树也在仰视中分外繁茂。司机开车离去,不远处层峦叠嶂,中间留白,模糊了距离。
司机留下话说,有人需要七叶一枝花治病。张思群为此跑遍了前山后山,她和同伴在山坡上,视野中有前山,也有后山,还有低处的房屋和田,田间的树高低错落,到处找不到七叶一枝花。她们决定上岩落峰去寻,岩落峰是天险,云遮雾绕,攀爬着陡崖的思群和她的同伴真像上仙山采灵芝的白娘子。她们在百花丛中终于采到了七叶一枝花——此花奇异,一茎七叶,一圈轮生的叶子中间生出一朵花,花分内外两轮,外轮酷似其叶,状如重楼,内轮在花萼花蕊之外又生出丝带般的花梗。七叶一枝花是藜芦科重楼属草本植物,生长于海拔1800 ~3200米的林下,多产于云贵川藏,湖北的宜昌、恩施、襄阳等地也有分布。
采到了,晒好了,思群天天盼着司机来取。这幅很有韵味,思群站在屋外的一片坝子上,向我们看不到的远方瞭望,天空辽阔,思绪辽远。他怎么老不来呢?那么,我去找他吧!
傍晚,彩霞满天,社员们收工了,从田垄上走来。他们蜿蜒走在地势较高的一片田的边沿,下面几层梯田的轮廓清晰可见,田边有高大的松树矗立,贯通了上下层,营造出集体向上的凝聚力。远处的几座山上也是一层层的梯田。低处的田边有房屋,群鸟从屋后飞起来,在空旷处盘旋。
2023.11.7— 9
板凳宽,扁担长
在我能给家里打酱油的年纪,家里的醬油都是我去打。那家副食店离我家只几十米,不知道是国营还是合作,卖烟酒糖醋、零食果品,是我经常光顾的店。鸡蛋糕、桃片糕、桔红糕,高粱饴、芝麻饴、酥心糖,我爸爸抽的最便宜的“金鸡”牌、“圆球”牌香烟,这些东西我最熟悉不过。那时候酱油都兴打,自家带了空酱油瓶去,店员接过把瓶口对上酱油桶边的一根弯管,底下的把手摇到底,接满正好一斤。后来瓶装酱油普及了,可以买,也可以“换”——带了空瓶去再买一瓶,空瓶可折一个价。到商店买东西是件有意思的事情。

《红色下伸店》,姚忠礼原著,姚忠礼、姚美芳改编,陈纪仁、庄根生、方昉绘画,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 年3 月第1 版;
《红色下伸店》里就有这幅打酱油的图:“一位顾客向店堂里喊道:‘老周,给我拷两斤酱油,另外买五斤盐、两块肥皂。’”画上店员老周正娴熟地握着把手“拷”酱油,瓶子快满了。店里还有许多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供销社里常见的物件:算盘、账本、公平秤、簸箩、筐篮、坛子、圆的方的玻璃罐子。
这本小人书的封面很吸引人。新来的店员小李,和老周一起一人挑着一副扁担,扁担筐里装满了各种小商品,他俩大步流星,兴冲冲送货下乡去。背景是一条河,河上有桥,河里有人划船放鸭,桥头有间商店,就是他们的“红桥下伸店”。小李刚来,以为工作只是站柜台,卖东西,发货收钱,上班了才知道远不止这些。店里常年为农民代修各种小农具,回收废品,收购鸡鸭蛋兔,业务范围很广。为了给农民节约时间,经常要送货下乡,不是有什么送什么,而是要多方了解他们的需求,想得比他们早、比他们远,提前预备,额外加班,未雨绸缪。比如,老周在他们店子附近盘了一块半亩见方的“除虫预报田”,种了五花八门的各种粮食、蔬菜样本,旁边摆了糖醋钵头,每天去观察里面诱杀的螟蛾,发现什么虫害,就对症进什么农药,送去五里八乡。这不仅是增加工作量,还增加了工种,精细麻烦,费时费力且技术含量高,全靠责任心维系。农药货物送到了乡里,再顺便回收农民家中的废铜烂铁、破布头、牙膏壳子,甚至肉骨头,挑回来分拣处理。一个郊区供销社,要做的事情有这么多,难怪小李初来有些情绪。等他犯下小错,险些酿成事故,经过老周的耐心教育引导,提高了认识,才精神抖擞,挑着担子走向乡村和田野。
“发展经济,保障供给”,这条充满希望的道路并非平坦通途。《红色下伸店》里有个人叫曹阿四,曾是有名的投机倒把分子,从前他常到镇上抢购紧张物资,套购计划物资,贩到乡里卖高价,后来下伸店办起来,他失去了市场,就想搞破坏。他偷偷地往除虫预报田的糖醋钵里放碱,使它失效,捕不着飞蛾;但这伎俩太拙劣,很快就被识破,他这只害人的“大飞蛾”也被揪出了。一盆糖醋,能值几何,味道没有了就换一盆,他总不能天天去放碱。“现在消灭一只飞蛾,等于将来消灭几万条螟虫啊!”
另外一本题材、内容都十分相似的小人书《扁担的故事》,里面倒叙了一段关于斗争的往事。我在玻璃橱窗里看到它的封面,两个年轻姑娘,挑着扁担,画面是仰视取景,她们的身姿既昂扬,又秀丽,意气风发,天高云淡,画面色调很美,我不看内容就买下了。解放前,山里没有商店,农民们要买点东西都要受到奸商的残酷剥削,一斤药材换一盒火柴,一张狍皮换一斤煤油。解放后,政府在山里办起了商店,店小人少,里里外外都靠老经理一把手。一天,老经理在送货下乡途中,被埋伏的奸商歹徒围攻,他举起扁担与他们搏斗,为了捍卫人民的利益,“流尽了最后一滴血”——这句话使我猛然想起,这本书我小时候看过!我一直记得这句话,因为小时候的我把这句话的比喻意义理解成了实在意义,深刻惊心。现在重看,个中的隐喻并非不真实,因为利益攸关可以是性命攸关,利益的争斗会有殊死的搏斗,生活中的平常事物很多都是前人拼尽全力争取得来。这条连接城乡、打通供给的路,付出了鲜血的代价,老经理的女儿接过父亲手中的扁担,继承父亲遗志,挑着农民需要的化肥、农药、农具零件、生活用品给他们送去,沿途时而跳下稻田查看虫害,时而去生产队、农技站了解情况,把什么都记在心里。
一根扁担,能挑百斤,能走百里。好过一张板凳,坐着不动,坐在店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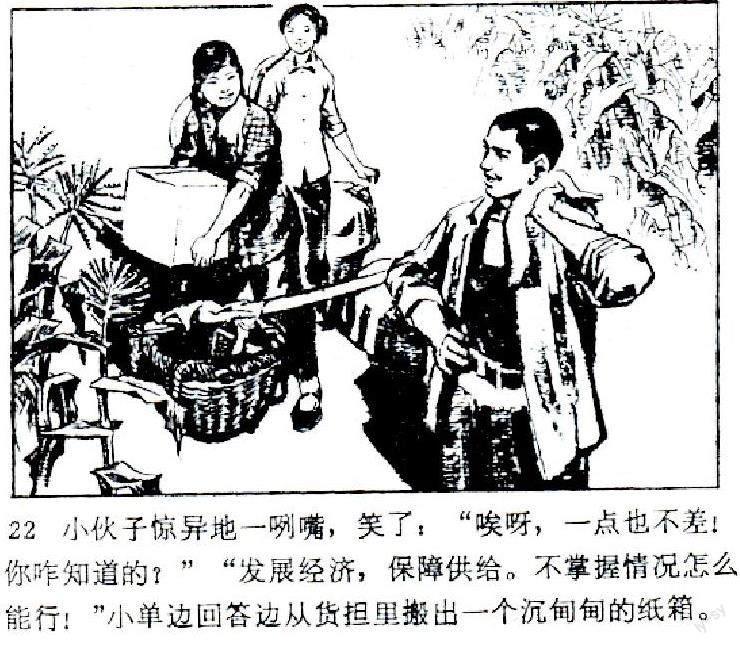
《扁擔的故事》,岳长贵原著,赵希良改编,石呈虎绘画,人民美术出版社1974年12月第1版)
几十年沧海桑田,供需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老问题消失,新问题产生。如今的人们买东西不爱去商店了,就坐着不动,在手机上划拉;店家也不出门,也在手机上划拉,外加在库房里扑腾;只有不挑扁担的货郎们,把大大小小的纸盒堆到电驴后架上,在路上风驰电掣,快些快些再快些,电话打个不停接个不停。不出门,不见面,不看到东西就买了,这样好么?这情形,好像一桩事情的某种内里被抽走了,虽是简单快捷,不麻烦就不珍贵。
今年夏天,我们在黄山脚下的一个小村子里转悠,在一个三岔口看见两间铺面,我脱口说:“哎哟,这是个供销社!”坐在门口的老人说:“对哟,这是个供销社!”它居然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保留至今,水泥剥蚀的墙面,烟熏火燎的后院,老家什,老货架。有些商品,我疑心是从七十年代一直摆到现在。
2023.10.20 — 22
(责任编辑:马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