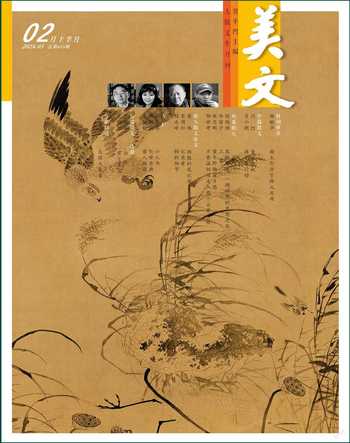自照与自省
李浩
温庭筠《菩萨蛮》其一“照花前后镜,花面交相映”两句我特别喜欢,还记得叶嘉莹先生曾引《华严经·论法界缘起》中的一段话阐释此词“众镜相照”的意趣:“犹如众镜相照,众镜之影,见一镜中,如是影中复现众影——影中复现众影,即重重现影,成其无尽复无尽也。”叶先生对宋词的阐释发明颇多,对此篇也能孤明先发。及至读书渐多,才知有关的“镜喻”在东西方艺术史上形成了悠长而深远的传统,相关例证俯拾皆是,故有人又用“镜渊”来称谓此现象。法国文学家安德烈·纪德对“镜渊”的阐释形成了一大套理论,西方艺术界受此启发,争先恐后,推波助澜,在创作和理论阐发方面大显身手,极大地丰富了这一理论,中国现当代文学和艺术创作中也有回声荡漾。本文不想就此再做叠床架屋式的赘述,仅仅想以此为话头,作为捆束以下三篇自序的一根绳索,当然也想借此机会再看一眼镜中的自我,不是自炫自恋,而是想通过自省获得一点自我的觉知。
《流声:中国姓名文化》自序
姓名是人类社群组织中个体的识别性符号。
人类早期的姓名符号具有很强的区别性作用。对于某些阶层的成员,姓名甚至是个体的唯一性符号。随着时代的发展,一个个体可能被赋予多种称号,不同的个体也可能会有类似甚至完全相同的称号,于是姓名的唯一性被破坏,姓名的区别性功能被减弱,但它的丰富性、复杂性、人文性、技术性却在不断增加。
进入现代社会,由于社会交往量的增加,社会管理需要对个体成员的流动进行精准的统计和管理。依靠传统的姓名,只能做模糊的统计和管理,但现代组织利用各项专门科学和技术的进步,通过对个体姓名的精细标注和系统处理,形成了个体区别和识别的一系列新方法和新技术,于是姓名的民族性在减弱,而时代性、普适性、技术性在迅速增加。
当前,世界各国都可以通过姓名的数字编码、生物特征识别、基因与化学识别、感应与光学识别等技术,实现对人类个体唯一性的精准标注、编辑和跟踪。传统的隐姓埋名、改名换姓已全然达不到隐遁的目的。在电子探头和虹膜扫描仪面前,更换衣服与换马甲都没有用,易容与换肤也未必能逃脱追踪。从理论上说,传统姓名的作用在不断减弱,人工智能时代的个体能够在全球畅行无阻,精准便捷地获得各种贴心的服务,其实依靠的不是识别文字书写的姓名,而是通过搜索姓名文字和字母后台的那个庞大的错综复杂的大数据系统。
宇宙大爆炸之后,由爬行动物演化而来的智能生命的人属分支是如何获得群体徽号姓氏,并进而被賦予每个个体的区别性符号?又是如何形成超人文的数理编码、遗传数据?未来人类的姓名是否会消失?机器人是否会有姓名?硅基生命未来是否不需要姓名,仅用数据编码或体纹特征来识别?随着奇点临近,大数据滞涨,姓名文化的研究和传播有何新特征和新作用?这是笔者在阅读传统姓名文献、关注姓名古今变化现象时所思考的一些问题,读者朋友如对这类问题也感兴趣,就请随我开始这一趟姓名文化之旅吧。
一
坊间的姓名学和姓名文化读物已经不少了,仅以汉语姓名文化来说,诸如萧遥天先生的《中国人名研究》,爬梳钩稽,资料富赡;纳日碧力戈先生的《姓名论》,尝试从社会文化人类学的视野观照姓名现象,独出机杼,新意不少。其他专题著作更多,如姚薇元先生的《北朝胡姓考》,林宝撰、岑仲勉校记、郁贤皓等整理的《元和姓纂》(附四校记),不仅仅是姓名学,同时也是古代文史研究的案头书。我在撰写本书过程中及上一版修订中已经吸收了不少,在相关叙述中也向他们表达了致意。
既如此,我为什么还要写这一册小书,并不断地修改增订呢?
首先,本书的写作缘起是很早以前的事。我在本书三联版后记中已经如实交代,本书原稿应该是我著述生涯中成形的第一部书稿。当时是应一部丛书编委会的邀请,按照丛书的体例编写的。彼时处于改革开放前期,文化建设也像一个基建工地,大干快上,但整体都比较粗放匆忙,包括本书在内的文化类著述,也留有那个时代的一些痕迹。随着时代的推进,本书也与那个时代一样逐渐淡出。进入21世纪以来,新一轮的文化热特别是中国传统文化热方兴未艾,本书的三联版推出后引起各个方面的关注以及读者的热情,出乎我的意料。有感于此,对这部还有一些市场的小书,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修订,是一个作者应尽的责任。
其次,目前的姓名读物,包括本书的原版,仅仅立足于对古典姓名文化的介绍。也有些出版物重点是向普通读者兜售取名的技巧和改名的方法。对于多层级的文化消费市场和需求各不相同的读者来说,乐此不疲地从事这方面的工作,也值得肯定。
但笔者不想与时俱变,再赶这个热闹。在这一版修订时,笔者敏锐地意识到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认为应该从当下信息革命来看姓名文化的现状和发展,用现代信息学和编码学来统摄古典姓名学和大数据视野中的姓名文化。这种认知,对处身于后全球化时代的国人,似乎未觉得有什么新意,但对于姓名学本身以及姓名文化研究来说,这还不仅仅是三千年未有之巨变,更是从人类有血缘的人文徽号以来,指定和识别系统即将要发生另外一次重大变革的前夜。“文变染乎世情, 兴废系乎时序”(刘勰语),笔者和这一代学人有幸或不幸生活于此际,将时代文化和最新科技的内容囊括到姓名学学科中来,重新透视受到信息学、符号学、编码学、基因学、计算机与人工智能技术、未来学以及大历史学冲击的传统姓名文化,是一个学人的正常学术反应。
二
作为专名学的两个分支姓名学和地名学,其实也与我个人的学术成长息息相关。
犹忆早年在大学时期,曾修习过历史地理学和都城学之类的课程,后来撰写硕士研究生论文,关注作品中的地名以及作家交游的地理空间问题。撰写博士论文时,便进一步从文化地理学和文学地理学思考地域文学和家族文学问题。此外,我早年就开展的唐代园林文学研究,也是从辑录唐代文献中出现的园林别业地名入手的。当时碰碰磕磕,瞎打瞎撞,以为自己是在不同的领域作战。老来忆旧,回顾起来,实际上是一个领域的不断拓展。
我对姓名学的研究,起步于帮助大学时代老师做一部有关姓氏的童蒙读物的注释,随后就是应编辑之约撰写了本书的原稿。今天看来,这两项工作都是一些通俗普及类的工作,学术意义很有限,所以我也没有特别在意。但后来由此萌蘖出家族文学和士族文学研究,就进入了我学术研究的主要领域。我目前新开拓出的新出石刻文献研究,研究内容仍与姓名学、家族学丝丝蔓蔓,剪不断,理还乱,因早年在这方面曾下过一点功夫,故进入这一全新的领域,虽然小心翼翼,稳扎稳打,但也不是特别恐惧害怕。
我自己一生治学,兴之所至,跌跌撞撞,貌似佚出文学的畦径,但回顾起来,实际上仍是游走于专名学的两端,借了一些新理论、新方法来激活古典国学中的基本内容,在现代语境中做了一些新的梳理和解说,如此而已。我在此坦诚地解剖自我,一是希望不断反省和自我总结,另外也想将自己的肤浅认知捐献给当代学术史实验室,作为一个标本,供进入此领域的更年轻的朋友随意解剖,希望年青的一代能规避我的不足和缺憾,在自己专攻的领域做出更大的成就。
三
本书的修订和补写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对本书的关键和主旨的适当调整。由原来客观叙述传统姓名文化内容,调整为以信息学、符号学、基因学、计算机与人工智能技术、未来学以及大历史学为光束,透视传统姓名学,重新阐释汉语姓名文化,对于由作为区别符号的姓名所衍生出的各种新的识别方法、识别工具和识别技术也给予高度重视。
二是补写了自序和第五章,改写了第四章和第六章。
三是对全书的叙述内容和文意,根据新的主旨做了梳理,对于一些生僻的史料做了删节,对于一些烂熟的例证做了更换,另外新补了一些书证和例子。
《濡羽编:讲辞、讲稿与讲纲》自序
一
近二三十年来,除了校内的正常教学外,也曾不断被邀请出席相关的交流活动及专题讲座,有些话题我事先有些准备,先后讲过多次,稍微主动些。也有些话题是应主办方要求,为他们的活动专门准备,只讲一次,但花的时间精力,并不比写一篇论文少,而且因时间所限,总是匆匆忙忙,留有不少遗憾。也有的活动,超出自己专业范围,出席为了友情,发言也仅仅是客气和礼数。这些内容,就不想收入文集了。其他与学术相关的内容,实际上是学术的拓展和外溢,与学术工作是一个整体,故将这些内容纳入本书收录范围。收入前两部分的内容较杂乱,只能按照话题粗略地划分。
第三部分是追忆自己的师承以及在学术成长过程中过从较多的几位师长,收入这部分的不是全部师长,仅仅是受邀参加一些活动并发过言、写过文章的部分。
二
近读唐君毅先生在《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一书中说:“吾不欲吾之哲学成堡垒之建筑,而唯愿其为一桥梁;吾复不欲吾之哲学如山岳,而唯愿其为一道路,为河流。”诚获我心。1961年,唐先生发表《说中华民族之花果飘零》一文,两年多后,他又发表《花果飘零及灵根自植》,就相关问题反复申述:“一切民族之自救……必须由自拔于奴隶意识而作为自作主宰人之始……。故无论其飘零何处,亦皆能自植灵根……。其有朝一日风云际会时,共负再造中华,使中国人之人文世界花繁叶茂,于当今之世界之大任者也。”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由于外力造成中华文化的花果飘零,期待有朝一日风云际会,花繁叶茂,这是唐先生的文化梦想,但自植灵根是我们每个人在当下都能践履实行的。
一百年前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晚年著名演讲《以学术为业》结尾有一段话:
在课堂里,唯有理智的正直诚实,才是最有价值的美德。然而诚实也迫使他们指出,对于这么多期待着新的先知和圣徒的人来说,他们的境况,同以赛亚神谕所包含的流放时期以东的守望人那首美丽的歌所唱的完全相同?
有人从西珥呼问我,守望的啊,黑夜如何。守望的说,早晨将至,黑夜依然,你们若要问就可以问,可以回头再来。([德]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韦伯的两篇演说》)
对于今天的读者,马克斯·韦伯所强调的“学术志业”和以赛亚神谕,都晦涩难懂,这里就不展开了。还是看《旧杂譬喻经》卷上第二三的一则寓言故事。
昔有鹦鹉,飞集他山中。山中百鸟畜兽,转相重爱,不相残害。鹦鹉自念: “虽尔,不可久也,当归尔。”便去。却后数月,大山失火,四面皆然。鹦鹉逢见,便入水,以羽翅取水,飞上空中,以衣毛润水洒之,欲灭大火。如是往来。天神言: “咄!鹦鹉!汝何以痴:千里之火,宁为汝两翅水灭乎?”鹦鹉曰: “我由不知而灭也?我曾客是山中,山中百鸟畜兽皆仁善,要为兄弟,我不忍见之耳!”天神感其至意,则雨灭火也。
《舊杂譬喻经》,吴康僧会译。故事情节虽简单,但却美丽动人。佛典中除《旧杂譬喻经》外,《阿育王譬喻经》和《杂宝藏经》也载有这个寓言。其中元魏吉迦夜所译《杂宝藏经·佛以智水灭三火缘品》:
过去之世,雪山一面,有大竹林,多诸鸟兽,依彼林住。有一鹦鹉,名“欢喜首”。彼时,林中风吹两竹,共相揩磨,其间火出,烧彼竹林,鸟兽恐怖,无归依处。尔时,鹦鹉深生悲心,怜彼鸟兽,捉翅到水,以洒火上。悲心精勤故,感帝释宫,令大震动。释提桓因以天眼观:“有何因缘,我宫殿动?”乃见世间有一鹦鹉,心怀大悲,欲救济火; 尽其身力,不能灭火。释提桓因即向鹦鹉所,而语之言:“此林广大,数千万里,汝之翅羽所取之水,不过数滴,何以能灭如此大火?”鹦鹉答言:“我心弘旷,精勤不懈,必当灭火。若尽此身,不能灭者,更受来身,誓必灭之。”释提桓感其志意,为降大雨,火即得灭。
《杂宝藏经》中还给鹦鹉取了“欢喜首”的名字,欢喜者,是佛家尊者名,为释迦弟子。其他二经中都将受鹦鹉感动而降天雨的记为天神,而《杂宝藏经》则归美于释提桓。“释提桓”即“释迦提桓因陀罗”,是住在须弥山顶的能天主。
南朝刘宋时期刘义庆《宣验记》中有一篇《鹦鹉》,情节袭取于此。此外,刘敬叔所著《异苑》中有一篇《鹦鹉救火》也与此相类。
有鹦鹉飞集他山,山中禽兽,辄相贵重。鹦鹉自念:“虽乐,不可久也。”便去。后数月,山中大火,鹦鹉遥见,便水濡羽,飞而洒之。天神言:“汝虽有志,何足云也。”对曰:“虽知不能救,然尝侨居是山,禽兽行善,皆为兄弟,不忍见耳!”天神嘉感,即为灭火。
另,《太平御览》卷九一七也曾记载一则与鹦鹉灭火绝似的故事,亦见于《宣验记》。记中云:“野火焚山,林中有一雉,入水渍羽,飞以灭火,往来疲乏,不以为苦。”其实也是源自佛教传说,详见玄奘《大唐西域记》卷六中的《雉王本生故事》,亦可参见《智度论》卷十六。
刘敬叔所编撰的《鹦鹉救火》故事是《旧杂譬喻经》的删改本,表明这个寓言故事对南北朝志怪小说的影响。鲁迅、余英时等的著述中也曾引用了《异苑》中的这个寓言故事。
我在此不厌其烦地引述一个寓言故事的母题及其衍变,是想证明文化记忆的强大作用。在《杂宝藏经》版故事的最后,鹦鹉说:“我心弘旷,精勤不懈,必当灭火。若尽此身,不能灭者,更受来身,誓必灭之。”与本土的《列子·汤问》中“愚公移山”寓言主题遥相呼应:“虽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孙,孙又生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孙;子子孙孙无穷匮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平?”
鹦鹉救火的故事感人,濡羽、渍羽的意象也很新奇。作为一种文化记忆和文化模因,昔哲今贤前后相续,千年以来不断复述改编,积淀成一个丰厚的文化岩层,我借过来作为本集的题目,是否唐突,希望读者朋友有以教我。
《慢耕集:纸上的春种秋收》自序
这是一册汇报自己几十年来读书心得的小书。作为个人精神食粮的主要部分,这几十年的阅读总量当然不止这几十种书,但我也没必要为了炫耀博学在这里给朋友们报书单,背金句。本书汇报的主要是在专业工作和学术交流过程中,留下书面笔记的极小部分阅读文字。
一
读书的话题没有难度,几乎人人都能谈,但言人人殊。我自忖无甚高论,先抄前人的两类看法作为话头。一类是强调读书的好处,以北宋黄山谷调子拔得最高:
士大夫三日不读书,则义理不交于胸中,对镜觉面目可憎,向人亦语言无味。(苏轼《记黄鲁直语》,《苏轼文集·佚文汇编》卷五)
南宋翁森《四时读书乐》组诗写一年四季的读书乐趣。宋代优礼文人,士大夫们自我感觉都很好,整天幻想着与官家共治天下,读书的环境又这样好,不乐何如?下面抄标题为《春》和《冬》的两首。
山光照槛水绕廊,舞雩归咏春风香。好鸟枝头亦朋友,落花水面皆文章。蹉跎莫遣韶光老,人生唯有读书好。读书之乐乐何如,绿满窗前草不除。
木落水尽千崖枯,迥然吾亦见真吾。坐对韦编灯动壁,高歌夜半雪压庐。地炉茶鼎烹活火,一清足称读书者。读书之乐何处寻,数点梅花天地心。(厉鹗《宋诗纪事》卷八一)
另一类意见貌似相反,以现代倡导“平民教育”的陶行知的《春天不是读书天》为主。
春天不是读书天:关在堂前,闷短寿缘。
春天不是读书天:掀开被帘,投奔自然。
春天不是读书天:鸟语树尖,花笑西园。
春天不是读书天:宁梦蝴蝶,与花同眠。
春天不是读书天:放个纸鸢,飞上半天。
春天不是读书天:舞雩风前,恍若神仙。
春天不是读书天:放牛塘边,赤脚种田。
春天不是读书天:工罢游园,苦中有甜。
春天不是读书天:之乎者焉,太讨人嫌。
春天不是读书天:书里流连,非呆即癫。
春天!春天!春天!什么天?不是读书天!(《陶行知全集》第7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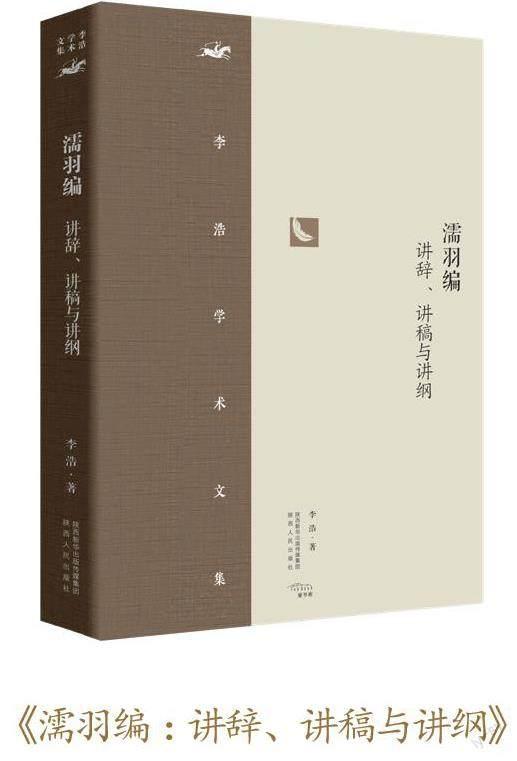

據说陶行知先写出歌词,又请赵元任为本词谱曲。赵说为了乐曲的完整,就又补了最后一行的文字。表面上看,这是两位现代教育名人借写词谱曲玩成人游戏,真是“精致的淘气”,故意与流行的包括《四时读书乐》之类的读书有用论唱反调,揶揄讽刺,幽默挖苦。但如按字面理解的话,可能就误解了陶先生的用心良苦。
其实陶先生不是反对读书,而是反对读死书、死读书,他提倡读活书、活读书、读书活。“花草是活书,树木是活书,飞禽、走兽、小虫、微生物是活书。山川湖海,风云雨雪,天体运行都是活书。活的人、活的问题、活的文化、活的武功、活的世界、活的宇宙、活的变化,都是活的知识宝库,便都是活的书。”(《新旧时代之学生》,见《陶行知全集》第2 卷)这与他倡导的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的教育思想是一致的。与陶先生的“活书”说类似的,还有张舜徽先生的“无字书”说。
天地间有两种书:一是有字书,二是无字书。有字书即白纸黑字的本子,无字书便是万事万物之理,以及自然界和社会上许多实际知识。有字的书,人人知道重视它,阅读它;无字的书,人们便等闲视之,很少有人过问它。特别是过去研究中国文、史、哲的学者们,平日除伏案阅览、写作外,不愿多和社会接触,形成“两耳不闻窗外事”,与世隔绝。由于他们平日所接触的书本,绝大部分是古代的,受古人的思想影响很大,潜移默化,便不期而然地与古人接近和今人离远了。偶与物接,便会格格不入。不独言论、行事容易流于迂腐,知识领域也是很狭隘的。(张舜徽《自强不息 壮心不已——略谈我在长期治学过程中的几点体会》,见《张舜徽学术论著选》)
可见陶先生反对的是只会读前人留下的纸本的小书,他鼓励人们学会读天地自然这本大书。犹如时下所说的把论文写在大地上,不是反对写论文,而是用自己的行动和生命谱写一篇能彪炳史册的大文章。从这个意义上说,屈原最好的作品不是《离骚》,而是他投汨罗江的壮举。简言之,陶先生的意思与历代谈读书的意见并不矛盾,而是对这个话题更深刻、更智慧也更有现代感的引申发挥,是读书有用论的20 世纪升级版。
二
我出生在偏僻的陕北,幼年时期遭逢“文革”,当时停课闹革命,学校课程无压力,没有家庭作业,也没有家长的要求,虽然身心没有学习的压力,但荒废了读书特别是机械记忆的黄金时期。
1977年恢复高考,这一届对于外语等单科的成绩要求很低,以后逐年增加难度,规范要求,我于1979年在浑浑噩噩中进入了大学,算是挤上了改革开放以来高考“新三届”的末班车。读本科、读硕士、读博士,一路读下来,完成的都是规定的动作,与同辈齐步走,少有乐趣,也无可称道处,更不敢夸口青春无悔。
年来老境将至,除了应付工作外,懵懵懂懂地意识到要为自己读书,读自己想读的书。惜觉醒得太迟,大好光阴已被轻抛掷,现年龄老大,眼睛昏花,记忆力衰退,读书仿佛在河水上写字,刚刚划下浅深不一的印迹,河面上却丝纹不动,连个泡沫也没有,更谈不到“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的宏大场面。希腊神话中说西西弗斯推石头上山,至山顶石滚下。他周而复始,反复不断。其实面对衰老和死亡这个定数,我们每个人都是西西弗斯。故威廉·福克纳评价加缪的话既适用于西西弗斯,也适用于我们每个人。
如果人类困境的惟一出路在于死亡,那我们就是走在错误的道路上了。正确的路迹是通向生命,通向阳光的那一条。一个人不能永无止境地忍受寒冷。因此他反抗了。他就是不能忍受永无止境的寒冷。他就是不愿沿着一条仅仅通向死亡的路走下去。他所走的是惟一的一条可能不光是通向死亡的道路。他们遵循的道路通向阳光,那是一条完全靠我们微弱的力量用我们荒谬的材料造成的道路,在生活中它本来并不存在,是我们把它造出来之后才有的。是的,活下去。([美]威廉·福克纳《福克纳随笔》)
俞曲园老人说自己“骨肉凋零,老怀索寞,宿疴时作,精力益衰,不能复事著述。而块然独处,又不能不以书籍自娱”(俞樾《茶香室丛钞》序),我颇能理解老人家的痛楚心情。
三
往昔对于读书,有一种崇古的观念。韩愈讲“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南宋学者家铉翁说“三代以还唯有汉,六经之外更无书”(家铉翁《圯上行》),明代的一批文人更公然喊出“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作为一种站队和表态,可以理解。但后人不必较真,更不必存看齐意识,亦步亦趋地模仿。
康德《人类历史起源臆测》指出:“在历史叙述的过程中,为了弥补文献的不足而插入各种臆测,这是完全可以允许的;因为作为远因的前奏与作为影响的后果,对我们之发掘中间的环节可以提供一条相当可靠的线索,使历史的过渡得以为人理解。”([德]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
就我个人而言,倒是觉得几位现代学者对读书的一些建议平实有用,如陈垣曾以几部重要的笔记为例,做史源学的研究,并总结了几条读中国古籍的原则。“一、读书不统观首尾,不可妄下批评。二、读史不知人论世,不能妄相比较。三、读书不点句分段,则上下文易混。四、读书不细心寻绎,则甲乙事易淆。五、引书不论朝代,则因果每颠倒。六、引书不注卷数,则引据嫌浮泛。”(陈智超编《陈垣史源学杂文》)
余英时强调读书要谦逊。“我们读经典之作,甚至一般有学术价值的今人之作,总要先存一点谦逊的心理,不能一开始便狂妄自大。这是今天许多中国读书人常犯的一种通病,尤以治中国学问的人为甚。他们往往‘尊西人若帝天,视西籍如神圣’(这是邓实克1904 年说的话),凭着平时所得的一点西方观念,对中国古籍横加‘批判’,他们不是读书,而是像高高在上的法官,把中国书籍当作囚犯一样来审问、逼供。如果有人认为这是‘创造’的表现,我想他大可不必浪费时间去读中国书。倒不如像鲁迅所说的‘中国书一本也不必读,要读便读外国书’,反而更干脆。不过读外国书也还是要谦逊,也还是不能狂妄自大。”(余英时《怎样读中国书》)余先生的话可能会让有些人听起来感到困惑,只要联系在余之前,陈寅恪已经讲过:“窃疑中国自今日以后,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之思想,其结局当亦等于玄奘唯识之学,在吾国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终归于歇绝者。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见《金明馆丛稿二编》)
当代学人刘跃进则总结说:“我发现上述大家有一个学术共性,即能在寻常材料中发明新见解,在新见资料中发现新问题,在发明发现中开辟新境界。”(刘跃进《从师记》)
袁枚的这两句诗我比较喜欢。“双眼自将秋水洗,一生不受古人欺。”(《随园诗话·补遗》卷三)其实古人没有欺骗我们,是我们自己太幼稚,太简单,错解了古人。所以,這个板子不能打在古人身上,应该打在你自己身上。
犹忆童年时随外婆住在乌审旗尔林川乡下,当时乡下没有电,要用畜力推石磨舂米磨面,为防止驴子偷吃,推磨的驴一般都被蒙上眼罩。驴走慢了,站在旁边看磨的就用笤帚打一下驴屁股,挨了打的驴第二圈转到此,仍然保留着挨打的记忆,于是条件反射般快跑几步。外婆爱唠叨,常用此案例教育我:驴挨了打都有记性,人不能不长记性,不断重复错误。惭愧的是,我自己不断摔跟头犯错,也不断看到现实中和书上别人摔跟头犯错,就是不如驴子有记性。借用网络新生代朋友的一个表述,人类傲慢地使用蠢驴、蠢猪这样的字眼,动物世界的异类朋友会集体抗议的,它们会认为这是“物种歧视”,因为人类干的蠢事并不比动物们少。及至从书上看到黑格尔老人曾说:“我们从历史中得到的唯一的教训就是我们从没有从历史中得到过教训。”(《历史哲学》绪论)罗素也重复着说道:“人类唯一的历史教训就是忘记了历史的教训。”我这才稍稍释然,原来不长记性和贪嗔痴恨爱恶欲一样,是人类的共病,也是我们的原罪。这样想想,个人的负罪感也就减却了不少。
四
收入本书的文字分为四类。
第一类是拜读学习师友著作的心得体会。多年来,我从阅读他们的著作中获益匪浅,但引述和评介未必允当,只能是受益人个人的感受。
第二类是由我挂名和兼任各类丛书、编著的主编、责任人以及合编、参编人所写的一些说明文字。上大学前,我曾在一个文艺团体做过几年舞美工作,朋友戏谑地说那叫“拉大幕”,专业术语叫“司幕”,与大型活动中的“司仪”的功能近似,故我借用过来作为这一辑的题目。
第三类是我为我的学生所写的书序和前言,主要是硕博士研究生和博士后,参与了他们项目的开题和答辩,也见证了他们的成长。他们未来学术道路的顺逆穷通,主要还要靠个人的努力,但因我曾与这些年轻朋友有过一点学术交往,故也愿借本辑存留一点学术记忆。
第四类是我为自己的几本书写的序言和后记,这几个集子将来不会再重印了,留一篇前言后记,就像在笔记本里保留几片植物标本。失了水分的干花干草也就没有了真香生色,留一点岁月的印痕吧,取名“自照”,典出温庭筠“照花前后镜,花面交相映”。当然,读者朋友也可以理解为“猪八戒照镜子”。
其中,前两类阅读笔记,我在书名上还统一加了一个提示性的正标题,以示推荐和揄扬。后两类因为是写读学生的书和自己的书,就没必要刻意地自我广告了。
我读书有限,本集提及的未必都是很好的书,我的阅读体会各位也未必认可,老话说的开卷有益未必都是指精装版的经典名著,董桥《夏先生》一文中曾说夏先生对他提点道:“夏先生说读书乐趣不外一叶知秋,腹中有书,眼前的书不难引出腹中的书,两相呼应,不亦快哉。”(董桥《一纸平安》)
末了,引唐甄《潜书》中的一段话用以自勉,也送给年轻和年长的读者朋友。“我发虽变,我心不变;我齿虽堕,我心不堕。岂惟不变不堕,将反其心于发长齿生之时。人谓老过学时,我谓老正学时。今者七十,乃我用力之时也。……老而学成,如吴农获谷,必在立冬之后,虽欲先之而不能也。学虽易成,年不我假;敏以求之,不可少待。不然,行百里者,九十而日暮,悔何及矣!”
(责任编辑:孙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