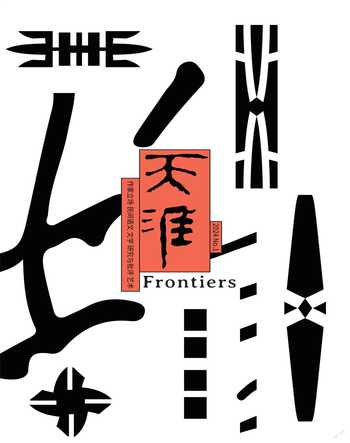正午(外二篇)
于坚
太阳照亮了花小芳摆在铺子门口的几箱蔬菜,它们露着头,发出一种散漫、温暖、阴阳交织的光,与周围小区建筑物的规范、整齐、一根根笔直线条里透出的冷漠格格不入,相当显眼。一只瘸腿的白猫闻了闻那箱从澄江的水田里拉来的藕,转身走了(它是老邻居了,住在后面的烂尾楼里)。藕身上糊着黑泥,“这么脏,也不洗一洗?”一位讲普通话的顾客说(字正腔圆)。“泥巴糊在上面才保鲜呢。”花小芳说。“没听说过。”顾客还是拎起一截扔在秤板上,“多少?”“三块二毛,算您三块。”两人沿着人行道走过来,一边走一边聊:“你要相信,我活得到一百岁。”“何必说,必须的。”“等下,我去拿包烟。”年轻点的男子跨进花小芳的店,要了一包大重九,“记在我账上。”外面,一辆刺目的闪闪发光的黑色本田车正在大道中央按着喇叭。花小芳走出去一看,几个戴着灰色牛津布渔夫帽的“队员”(她把这一类人都叫做“队员”)在路中央支着个黄色的三脚架,挡住了路。司机又按了几声,一个队员走到他车窗前:“大哥,耳朵不好,您莫按了,没看见我们在工作?等一下嘛,马上就好。”司机点了根烟抽着,另一只手吊在车窗上,看着他表演(他们的那一套规定动作很像是排练过的)。车子后面跟着一个闪闪发光的车队,有的按喇叭,有的没按。约摸十分钟,“队员”将东西搬到路边,重新支好。汽车赶紧开,一辆跟着一辆,路面又空了。“队员”们继续干活。一位“队员”低着头眯着眼睛紧贴黄色架子顶部的一台白色仪器朝一个方向看,随即说出一个数字,站在旁边的队员就在一个本子上记下来(花小芳不知道这台仪器叫做水准仪,是用来测量物体的空间距离的)。花小芳想问问他们在干什么,却欲言又止,王姐姐喊她了,她就走回自己的店去。
花小芳在“前进之城”租了一家铺面,卖蔬菜、豆腐、米线、水果、盐巴、鸡蛋、打火机、纸巾、牛奶什么的。她和她丈夫经营了快十年。她终日站在门口,那儿支着一张松木写字桌,上面放着一台电子秤。写字桌的抽屉以前是放钱币的。白天,分币钞票胡乱扔在里面,收摊后她才整理,找了几根橡皮筋,将钞票分类扎好。现在,抽屉大部分时间空着,只放着她的梳子、镜子和记账的本子、圆珠笔这些,还有一盒子即将过时的镍币。两年前,顾客忽然就不再用现金付款了,都是用手机扫码。她留着这些找不出去的镍币(从元到分都有),她有点珍惜这些黄灿灿的、像是金子的、会叮咚作响的“五角”,它们仿佛是纪念章,总是给她一种充实光荣的感觉。微信付款有点怪怪的,交易在黑暗里完成,看不见一张纸币,从前从纸币散发着的令人兴奋的“铜臭味”消失了,付款成了一个难以令人放心的假动作(就那么用几个指头在手机上按几下,真的就会到账吗)。她在外面忙碌的时候,丈夫吴小耕在里面负责案板上的活计(他们也卖猪肉)。儿子放学就来店里做作业,在隔板下面支把椅子,刚好够铺开作业本和教科书,笔掉到地上,伸手就能捡回来。“妈妈,你的肚子有点大了。”“莫乱说!”有时候花小芳她妈妈也会从村子里过来帮忙,坐公交车,下车后走十分钟便到她的店。她像个老母鸡似的站在店里,背着手转来转去,看着顾客往塑料筐子里放菜,将掉下的菜帮子拾起来(有些顾客抓起一棵白菜,咔嚓一声就掰下一片,那儿只是抹了点泥巴。他们并不介意,这种斤斤计较的顾客倒是不多),收到一只蓝色塑料箩筐里(她要带回去喂猪)。或者坐在小板凳上,将白菜、韭菜什么的择干净,脚边堆着一堆败叶。他们早上七点钟开门,晚上八点关门。将铝合金卷帘门放下来,一家四口坐着那辆用来运货的二手面包车回村去。老妈坐副驾,吴小耕开车,花小芳和儿子坐在后排,儿子将书包搁在腿上。村子离小区有七公里,他们差不多八点半到家,一家人又开火做饭,要到十一点才熄灯。
花小芳的店就叫“花小芳”,在前门小区深得人心。菜新鲜,货物充足。她善解人意,知道要进什么货,清楚顾客喜欢什么。别家进货想着的是顾客的钱包,她进货想着的是自己,“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鸡蛋她只卖土鸡蛋,蔬菜她进没施过化肥的。无论谁进了店,花小芳都要打招呼,搭讪几句,问好请安。她是村子里来的,她们那里还保持着传统的礼仪(这一家子行事的风格透着尊重、淳朴、灵性、善意,还有点慈悲,有人就猜莫不是仙人下凡?小区开盘已经二十年,邻里之间还是陌生人,从来不打招呼、不联系,路上彼此碰到视若无睹,只顾看自己的宠物(这些家伙不会让人,当着你的面就揸开胯撒尿)。只有在花小芳的店里,陌生人才会点头,让让(她的店子小,两个人过,一个就要让另一个)。“买菜呵!”“买几个鸡蛋。”“这个苹果味道不错。”“天气不错呵!”……出了门,彼此重新恢复不理不睬。花小芳却是随时要理睬进来的每个人的,不只是理睬,还带着一点点见到远房亲戚和老邻居的味道。“来啦,好点没有?许久不见,瘦了。”那胖子就心中一热。“还是半斤米线,二两磨肉?”“这套衣服好好看呢!最合您穿。”“您要的肥皂到货了。”“手机别忘了。”……他们觉得每个人都面善,“恶人只在你自己心中。”吴小耕当了一辈子乡村小学语文老师的父亲说的。花小芳将她的各种蔬菜水果摞成一座座小型金字塔,石榴金字塔、苹果金字塔、菠萝金字塔、宝珠梨金字塔,番茄金字塔、白菜金字塔、洋葱金字塔、土豆金字塔、茄子金字塔……洒点水,一堆堆闪着光,似乎旁边是一条青色的尼罗河。那些堆不成型的,她就整整齐齐码在塑料箱子里,韭菜、香菜、折耳根、蘑菇、辣椒、茭瓜、大葱、豆角、土豆……也洒点水,让它们保持新鲜。有些菜还要动手去掉渣子、败叶,拣得干干净净,好让人家买回去在水龙头上涮涮就能下锅。靠墙的是几排货架,上面摆着酱油、胡椒粉、小粉、土鸡蛋、干辣椒、草果、八角、花生米、粉丝、咸菜(花小芳她妈妈自己腌的)、面条、香油、白糖、蜂蜜、昭通酱……还有一张肉案。他丈夫负责卖肉,每天进半头猪的量,按部位改刀成块、条什么的,排骨、腰花堆在一边。总之,她的店不贪心,没有一般店铺的那种只盯着钱包的铜臭味。一心一意为大家服务,赏心悦目,令人信任、放心、高兴。“还不够,还要打整。”吴小耕说。他在盘算着要将铺子里的墙面都装上木板,让店面看上去像个小宫殿——蔬菜水果宫殿。“春节的时候就动工。”“这可得一大笔钱咧!”“不怕,这是长久之计。”吴小耕说。夫妇两个热爱这个营生,这个店是他们的衣食父母,不仅养着他们一家,也令他们心旷神怡、广结人缘。每天一醒,天还不亮,两口子就直奔店上,吴小耕一边开着他那叮叮当当响的旧面包车,一边还哼着曲子。他们店旁边也开过几家同样的店,店主们并不喜欢这营生,临时抱佛脚,怎么都行,只要有钱赚。只想赶快赚了钱走人。赚这种钱很难速战速决,必须细水长流,这是一辈子的营生。赚不到大钱,赚小钱他们没有耐心。百货店、高尔夫用品店、情趣店、五金店、卖牛肉面的店、卖烧饼的店、卖包子的店……都有人开过,开一家倒闭一家。后来的租户连招牌都懒得换了,卖米线的,挂的招牌是“前进之城美容中心”。花小芳和吴小耕不在乎赚钱,只在乎过日子,赚的钱够过日子、够过到老就行。“钱不要一个人赚了,大家都赚点,个个都要活嘛!”花小芳她妈对大腹便便的周婶说(周婶是深圳过来的,在小区有一套联排别墅,儿子买的,老两口在夏天过来住个半年。360平方米的房子,太大了,待不住,得闲就往花小芳的店里来)。周婶听了这话,吃了一惊:“啊哦,你是菩萨心肠,我倒是希望钱越多越好。”说完拎着一块豆腐、一盒鸡蛋走了。列文一条腿支在人行道上,一只手扶着自行车:“吴先生,给我五两里脊肉。”小耕在里面听见了说:“好咧!”就仔细割好,秤够,用个塑料袋装着拎出来递给他。她接过他的手机去扫码。“你家儿(昆明话会在“家”后面儿化一下,意思就成了“您”)的密码是多少?“764532。”花小芳不会打听顾客的名字,是列文主动告诉她的。“我是列文,来自俄克拉荷马。”花小芳哦了一声。列文(他们叫他“那个老外”)在小区里住了两年,每次来店里都是买几个洋葱、几个番茄。“怎么只要这么点呢?瞧瞧这些南瓜多好,这菠菜多新鲜,看看这个黑油油的建水茄子,今天现摘呢!”花小芳说。“我做不来嘛。”列文说。过了几个月,列文说:“你们可以来找我学学英文,只收半价。半年,你们就可以去美国了。”小耕问:“去美国干什么?”列文耸耸肩。过几个星期,列文又说了一次。小耕说他太忙了,沒时间。列文就没再吭声。一个“肤若凝脂”的女子趾高气昂(穿一双乳白色的高跟鞋)问:“有没有奶酪?”“没有。”(花小芳进过货,基本上没有人买,亏了)“有没有猫屎咖啡?”“没有。”“真是一家土杂店呢!”再也没来过。晚上,花小芳和吴小耕洗洗脚上床,各看各的手机。有时候说说白天的事,他们私下为常客取了诨名,“胖子”“雪茄”(他来买菜总是叼着一根雪茄)“林黛玉”(苍白,弱不禁风)“猴子”“老头”“战马”(高大雄伟的篮球运动员)“轱辘”(感觉如此)“鸡蛋壳”(感觉易碎)“花瓶”(一个婆娘)“高音喇叭”(一个退休干部)“四川人”“稀泥大学”(悉尼大学。花小芳没听懂。她儿子在那里学中文,话间经常提到)“猫”(说话呢呢喃喃)……他们也会拿顾客的言语、行为开开玩笑,评论评论。笑一阵就睡了。花小芳忽然想起早上儿子的话。“我这肚子是不是显眼了,娃娃都看出来了。”“显眼又怕哪样,现在又不搞计划生育。”(花小芳以前流过产,生娃娃让她心有余悸)流行微信付款后,她的店里随时响着一个声音:微信收款××元!本来没有这个声音,后来发现有人会用指头在手机上按一通,其实一分未付。花小芳不喜欢这个声音,显得她斤斤计较。她收钱只收整数,电子秤显示某某元某某角某某分,她只收到元,角、分忽略不计。有些顾客于心不忍:“你不容易呢!”依然是付款到分。花小芳一家赚的钱,只要够用就行,所谓的够用,就是一日三餐管饱,孩子能够交上学费。房子倒不花什么钱,他们住她父母的房子。他们早年在自家的宅基地上盖了一排平房。老两口住一间,中间那间是看电视的,小两口和娃娃住一间,还有一间厨房,一间厕所(被炮仗花簇拥着,不容易看出来)。平房前面是一个院子,养着十多只鸡,三头猪(她爹负责喂),种着一棵石榴树、一棵板栗树、一棵桂花。他们是原住民,几百年前就住在这里,皮肤被高原上的太阳晒得黝黑,像是印第安人。嘴唇厚,鼻梁高,肌肉结实,普通话说得根歪绊倒(昆明方言,做事情做不好的意思)花小芳一枝独秀,不是“肤若凝脂”,也没有“杨柳腰”,古铜色皮肤,健康、结实、丰满(有点圆)。“她会生一窝娃娃。”村里的老人说。
他们租的铺面临街,由于地基下沉,铺面的阶梯已经开裂,倒塌了几段,楼也斜着(几厘米)。有时患着慢性抑郁症的诗人提着裤子、歪着走过来,一路念叨着:“荒凉呵!荒凉呵!”有人就问:“你找谁?”“谁也不找!”那人就奔去报告保安。诗人继续念叨:“荒凉呵!荒凉呵!长铗归来乎,食无鱼!”住在“橡树庄园”那个小区的、皮肤白皙的孟尝君过来了:“闭上你的臭嘴!喜欢荒凉就赶紧搬走,莫在这里穷酸。”“就是荒凉嘛,走了两公里,没看见一条鱼。”“这里是高档住宅区,才不会养着你们这些二流子。”诗人说:“你有没有看见那条鱼?”孟尝君说:“没看见。”踩了一脚油门,开走了。这个诗人叫步落次鸡,他也自报大名:“我叫布罗茨基。”“步落次鸡?外国名字吗?”“笔名!”有时来店里买一袋牛奶,一打鸡蛋,一袋白糖。统统收进一只塑料袋。坐下来,在靠门的那个塑料凳子上坐半小时,低着头看那些从菜堆里爬出来的蚂蚁。保安来了,看見是他,呼哧一笑,走了。
铺面的租金不贵,每月三千。一晃十年过去了,许多顾客都成了熟人,见面要打招呼,逢年过节,有人还要往花小芳的店里送点什么,月饼、茶叶、咖啡豆、玩具……到了春节,花小芳就关门,一关就是半个月。她一点也不着急开张,她们一家要回到村子里,初一到十五,有许多大事要做,祭祖先、拜四圣(孔子、老子、释氏、毛老人家)、祭土主庙,做火锅、做咸菜、腌腊肉、走亲戚、帮着花小芳她爹挖地啦……倒是她的顾客们担忧起来,会不会就此一去不返?每个春节之后,小区的店都要关门一批,如果她的店关门大吉,对许多人都是一个重大打击,倒不是买菜打酱油的问题,这件事与心情有关。正月十五一过,花小芳一家拉着满满的一车子蔬菜、水果、鲜花、鸡蛋又回来了。
铺子里比较清静的时候是上午九点以后,娃娃在学校里上第二节课。顾客少,吴小耕在里面算账(专科毕业,几个粗糙的指头几乎捏住了圆珠笔头,写得一手娟秀的字)。花小芳坐在门口择菜,将那些黄叶子去掉,抖干净泥巴。隔壁,三十四岁的傣族姑娘小丽坐在椅子上看手机(她是上个月才租了铺面的,开了间理发店,之前她是在福安小区,拆了,才搬到前进小区来。“我这个人运气不好,一辈子就是搬来搬去,搬到那儿那儿拆,都搬了七回了。”)隔壁,卖高尔夫球服的小李在玩手机。再隔壁,做窗帘的招娣姐在玩手机。再隔壁,修鞋的梁师傅在看手机。再隔壁,洗衣服的赵大哥在看手机。再隔壁是15栋,一楼的铺面正在装修,一会儿敲打,一会儿锯木,一辆卡车停在门口。“那个安徽人租下了一楼的五间铺面,听说要开一家超市。”小丽说。
那三个“队员”扯开了一卷皮尺,贴着地面拉开。
花小芳问小丽:“他们在搞什么呀?”
“测量。”
“量了搞什么呀?”
“不知道。”
花小芳忍不住了,终于走去问那个正眯着眼朝测距仪里看的小伙子:“你们搞什么呀?”
他歪着头看了花小芳一眼:“测距。”
“量了搞什么呀?”
“盖房子。”头又端正了朝测量仪里看。
“这处不是有房子吗。”
“危房,要拆掉。”
“什么时候拆?”
“不知道。”
“要不要喝点水?”
“不消。”
花小芳还是走回店拿了三瓶矿泉水给他们。在一旁做笔记的队员接着。
花小芳走回去告诉吴小耕。吴小耕正在案板上改刀半头猪,猪脸闭着一只眼睛,像是刚刚开口笑就挨了一刀。刀子在龙骨、里脊和勒条之间游走着。他昨晚躺在床上用手机看了庄子的《庖丁解牛》,对里面的刀法心驰神往,他要学会这一手。
听了花小芳的话,吴小耕停下手来说了句:“管它呢,到时候再说。”继续游刃,刀歪了一点,割到了手指头,他把它放进嘴巴,舔了舔。
花小芳走回去坐在那个绿色的塑料板凳上继续择菜(还剩半堆)。这次择的是一堆菠菜,早上吴小耕从小屯蔬菜批发市场拉来的,相当新鲜,都不需要择,花小芳只是抖抖根部还没有干掉的泥巴。
所谓故事,就是发生过的事,故去的事。一个人这一辈子要发生多少故事呐,但是如果不讲出来,这些事就没有发生过,只是你自己的黑箱。如果讲出来,那就不一样了,那是世界的事,又叫做历史。通常每个故事都会有三种反应:第一种是笑个不停;第二种是不喜,反感。还有一种面无表情,不置可否。这个故事我很少讲,也就讲过几次吧。而且每次都是三个人在听,三个人都是我自以为算得上是肝胆相照的朋友。第一次讲是在我三十二岁某天晚饭期间(那时我已经成了作家),听的人有马奎、大朱和张高尚。马奎每次都笑得死去活来,我讲一回,他笑一回。春天的时候笑了一次;夏天又笑一次;冬天,他儿子生日,请我去吃饭,我又讲一次,他又笑了一次,笑得前仰后合。我总是忘记我已经讲过,总是一高兴就要讲一遍。大朱也笑,他的笑与马奎不同,微笑,眯着眼睛,像个弥勒佛。张高尚从来不笑,这个人天生没有笑容。
第三次讲完,张高尚和我吵了起来。他说,王建国,你这个人太庸俗了,居然和猪搞在一起。这些家伙好吃懒做,到处拉屎,毫无上进心,那个晚上是你这一辈子堕落的开始。我气了,说:“你吐屎!我冷成那样,几乎冷死,是猪救了我,给我温暖,我才没有被冻僵。”“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你连这点儿苦都吃不了,将来必是个甫志高。”“我要怎么样?到车头去挺着,当英雄?”“是的,这种时候,你应该独立寒秋,挺身而出。不能躲在猪窝里一声不吭,狼狈为奸。如此龌龊的事,你还好意思讲出来,还得意洋洋!”我一拳就打过去,他捂着眼睛跑了,一边跑还一边叫:“你是猪!你就是一头俗不可耐的猪!”大朱说:“是猪又咋地!你是不是骂我?”张高尚说:“我咋个敢骂你,我骂的是那头猪。”我追过去飞起一脚(我中学时练过少林拳),踢在他的腰上。他跌跌撞撞跑掉了。他跑到李申(社会学博士)那里去诉苦:“王建国这个人的老底嘛,我太清楚了。”“什么老底?”“和猪睡过。”张高尚一走,李申在电话里就将他的话告诉了我。“这个张高尚你要小心呢!”张高尚后来将这个故事发表在他编的报纸副刊上,最后一句话彻底惹恼了我:这是一个关键时候就叛变、与猪为伍的胆小鬼。我从此和他断交。
好吧,猪的故事,你们从来没有听过,我再讲一遍。
那是1970年的冬天,十二月左右。当时我父亲在陆良的一个地方劳动改造。他接到通知,历史问题已经解决,可以回家了。他写了一封信给我母亲,让我下去搬东西。他的骨头断了几根,无法负重,走路要人扶着。我就坐长途汽车来到陆良。父亲急不可耐,已经找好了一辆黄河牌大卡车。小曹开的,小曹是他的四川老乡。小曹这次的任务是拉一车活猪到昆明去,他们单位过节要分给职工,顺便也带上我们。父亲决定连夜就回昆明。驾驶室可以塞两个人,坐着父亲和小曹单位的一位领导,那是一位梳着长辫子的女干部,冷得像块冰,她不太乐意我们坐她的车,但是我父亲级别比她高,副厅级,而她只是个科长。我一个人坐在后面的车厢里。车厢里装着七头黑乎乎的猪,个个肥头大耳,喘着粗气,不怀好意地看着我。我刚满十七,瘦骨嶙峋,壮着胆穿过它们,坐在父亲的行李上——用油布裹着的被子、铺盖和枕头。
我們先开去一个村子吃晚饭。吃饭的人有二三十个,站在一个院子里,围着一口支在院子中间的大锅,里面煮着猪肉。肥肉、姜块、八角、沫子在表面翻滚着,一只木瓢搁在锅沿上。有人扯线挂起了一个汽灯,那是一种老式灯具,将煤油在灯座里打成蒸气,点燃,可以发出很亮的光,比灯泡亮很多,一般开会的时候才用。汽灯挂好后,队长站在一个矮凳子上说:“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今天来吃饭的不仅有我们村的同志,还有物资局的同志。大家欢迎。”全体人就朝我们几个鼓掌,然后猪肉就熟了,一个光着胳膊的壮汉用木瓢舀出来,朝案板上一扔,还烫手,他抄起菜刀就切片,猪肉一片片倒下来,一摞摞装在洗脸盆里。热气腾腾,嬷嬷抬到一张矮桌子上。嬷嬷才刚退,大家一拥而上,筷子像兵戈一样在盆里翻搅碰撞,第一盆马上见底了。第二盆上来的时候,那位讲话的人大喝一声:“大家让开,让物资局的同志先吃。”围着的人端着碗让出了一条路,我走上去取了一片,那是一块巴掌大的带皮肥肉。我狼吞虎咽,满手是油。这是我一生中吃过的最香的肉了。队长又站上矮凳子问:“吃好了没有?”“吃好了!”众人齐声回答。“现在请物资局领导讲话,大家欢迎。”女领导就撸了撸围巾,站到小凳子上说:“大家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鼓掌。然后天就黑透了。
我们再次上路。黑漆漆的平原,远处有几个比星星还遥远的亮点,传来几声枪声。
“你玩过?”
“玩过。”
“什么枪?”
“手枪。第一次打,枪的后坐力将虎口撞伤了,流了点血。”
猪站在我身后,每头都高过我的腰部,老虎般地看着我。我很害怕,想着这些野兽会不会咬我,毕竟我刚刚吃了它们的同类。车开到半夜,正冷得索索发抖。忽然,一头猪绕到我身后,扒上车厢板,两只蹄子蹬着地板,身子几乎悬空。我跌跌撞撞扑过去抓它,它的背脊光滑,根本抓不住,扒着车头的厢板朝黑暗那边吼着:“救命!”忽然屁股一抬就跳下去了。前轮凸了一下。我大喊:“跳下去了!跳下去了!”黄河牌大卡车是个聋子,只顾自己轰隆向前,根本不理睬我的叫喊。我用拳头使劲砸驾驶室的顶,砸了好一阵。小曹终于听见,卡车熄火慢下来,停住,顷刻间静悄悄。什么也看不见,车厢里有一股猪屎味。小曹和那个女领导摸着黑走了几步去找猪,大地黑麻麻,什么也看不见,他们一筹莫展。父亲在座位上抽着烟,想了一下说:“到村子里找老乡来帮忙。”小曹就拿着手电筒朝黑夜走了。
剩下的三个人在黑暗中等着,一言不发,父亲在思考,他是个除了睡觉都在想问题的人。那位女领导熬不住了,慢慢倒上我父亲肩头,我父亲支着她,不让她倒下。我独自在车厢里看星空,猪在我脚边躺着。夜空巨大浩瀚,流星掉下来,还没有着陆就暗淡了。“美应该从大自然和人的道德中寻找。”“世上最使我们震撼的是头顶的星空和我们心中的道德。”这些话是康德说的,张高尚转述于我。因为他告诉我这些格言,我和他成了朋友。其实他这个人不好玩,不吃肉,不游泳,不谈女人,不喝酒,洁身自好。而我无肉不欢,游泳、打架、酗酒、交女朋友……我会玩的多了。我和他关系好起来是因为他读过康德,经常引用《判断力批判》的原文,令我佩服。茫茫人海,碌碌时代,谁会告诉你这些?“结交须胜己,似我不如无。”他是一个值得交往的人。我又想起康德的话,仔细地将头顶的天空看了几遍。此刻冷得难受,我跺脚、搓手、呵着气。我真希望这个没有丝毫怜悯之心的星空马上变成一只火炉。实在看不下去了,我蹲下来,靠着车厢板,让那个康德独自留在星空下。
小曹带着几个农人从黑暗里冒出来。他们是大地上的行家里手,很快就找到了那头企图自杀的猪,它受了伤,默默地躺在沟里。四个老乡把猪捆住,抬过来,打开后面的车厢板,扔进来,它躺着不动,一声不吭。曹师傅将放在车厢里的篷布拉开,盖着,以防它们再次逃跑。我一个人孤伶伶露在外面。曹师傅说:“小王,你在后面冷不冷?”我说:“不冷。”
我们继续赶路。十二月的夜,越来越冷。黄河牌大卡车一路咆哮,月光将道路照得明晃晃,路上没遇到一辆来车。
我靠着车厢板站着,冷得要死,深切明白了何谓“冷酷无情”。风冷酷无情,从无数的缝隙里割进来,刀子一般锋利。月光冷酷无情。大卡车冷酷无情,只顾前进、前进、再前进。坐在下面车厢里的人冷酷无情,看不见他们,仿佛这辆卡车是自己在无人的月球上行驶。我蹲下来,用力扯那块盖住车的篷布,试图拉一角盖着点,但根本拉不动。我将半个身子钻进里面去,半躺着,头靠着父亲的行李。身子暖和了一点。但还是冷,实在熬不住,干脆钻到篷布下面,这才暖和了。几乎要睡着了,又被颠醒,发现我已经挨着一头猪,它的身体相当暖和,就向它靠过去,它身上温暖如春,最后干脆钻进猪窝,和它们睡在一起。在猪窝里,我是个异类,穿一身衣服(夹克、毛衣、长裤、胶鞋),不像它们是全裸的,一丝不挂。它们一点都不害羞,一点都不排斥我,还趱了趱,与我贴得更近(马奎笑得捂肚子)。身前身后都贴着猪,左边是一排母猪奶,右边是另一头猪的脊背,头顶着一头猪的肚子,脚藏在一头猪的腹部。我温暖如春,感激涕零,念叨着伟大的猪呵、温暖的猪呵,善良的猪呵,仁慈的猪呵、胖乎乎的猪呵,色迷迷的猪呵,亲爱的猪呵(马奎笑得捂肚子。“哎呦,哎呦,要笑死了!”)……全身热乎起来,几乎要出汗了,猪说,睡吧。我就在它们中间睡着了。
下车的时候,曹司机看见我身上到处是猪屎,说:“怎么搞的,不至于吧。”父亲递过来一张纸,说:“擦擦。”女干部见不够,就去办公室抱了一叠来让我擦。
“可以吗?”
女干部说:“可以,不怕的,都是过期的报纸。”我用了十多张,将身上擦干净了,还是有轻微的味道。(马奎笑得流眼泪,大朱也罕见地笑出了声,张高尚面无表情。)
挨着坐了一夜,女干部李红梅和父亲聊了一夜,后半夜开始聊的,开始他们一言不发,直到猪跳车事件之后。他们在黎明中交换了家庭住址,用钢笔写在各自带着的小笔记本上。“改天来家玩。”
把车子洗干净!李红梅吩咐小曹。
我扛起行李,提着包袱,跟着父亲走回家,天大亮。
父亲问:“冷不冷?”我说:“差点冷死。”“我知道,也没有办法。”
马奎说:“太好玩了。太好玩了。”
第三次讲完,张高尚突然说了一句:“完全是堕落之旅!”
我愣了,原来他是这么想的。我最恨的就是“堕落”二字。无论是谁,只要一说这两个字,即刻高人一等,而对方像是被判了刑一样。“你吐屎!”
张高尚被“吐屎”这两个字震怒,气得说不出话来。
大朱第三次听完这个故事,过了半年就过世了。他喜欢吃油炸干椒,一盘菜总是有许多干椒剩下,他全部戽到碗里,他笑眯眯地一只一只吃掉,他这一生都不吃蔬菜。我们说,不能这么吃,会得癌症的。他不怕,死的时候五十二岁。
马奎后来笑死了。他是一个觉得一切都好笑的人,我很喜欢他。我们在一起笑过几百回。有一天他笑得前俯后仰,眼泪横流,胡子乱抖、面红耳赤。半小时后,心脏骤停,停止了呼吸。没人相信他是笑死的,医院只承认他是心脏病发作。
张高尚一边跑一边高喊:“我要去告!我要去告!”我那一拳正中他的鼻子,当场喷血。
不知道他告了没有,又到哪里去告,我和他不在一个单位。惴惴不安等了三个月,并没有电话打来追究我,后来也没有打来。然后我就把张高尚忘了——肤色、长相、身高、口音,忘得一干二净。当然,我也忘了康德,他更容易忘,我根本没见过此人。
我唯一记得的就是那些明晃晃的肥肉块,那个夜晚的满天星子,那种彻骨之寒,那种来自猪身上的温暖,还有我父亲和那个女干部坐在车厢里的样子,距离很近。还有小曹,他正趴在糊满泥浆的车头上,用一块抹布揩着它,后裤兜里塞着一双棉线手套。
他体内藏着一股恶臭,味道就像饭馆门口的泔水桶。特别是在熬夜之后,她一接近他,即刻过敏,时间长了,慢慢适应,才好些。她从来没有皱过眉头,也没提醒过他。她无条件地崇拜他、依赖他、信任他、爱着他。他挣钱,养家,说起话来妙语连珠,坚信“进化论”。达尔文是谁,她不知道。任何话,只要他说出来,都是对的。他长期患有口源性口臭,她查过百度,这是由于口腔中有未治疗的龋齿、残根、残冠、不良修复体、不正常解剖结构、牙龈炎、牙周炎及口腔粘膜病等引起的。他的每一句话都从这张奇臭无比的嘴巴里说出来,她全部接受,绝对崇拜。他一点也没有觉察到她总在屏住呼吸,还以为那是她幸福得发红的表情。他们就是传说中的那种模范夫妻,夫唱妇随。年轻时她想过戴口罩,想想也就算了,怎么可能嘛!献身于他那张嘴是她的福分,她只是悄悄地练习调整自己的呼吸方法,尽量降低臭氧的浓度。她从来没有劝他去医院,何况这味道也不是完全无益,医务室说,它可以转换为松节油。
她是个喜欢收拾的人。家里面永远收拾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什么都要盖起来。家里有各种各样的盖子,电视机罩子、马桶盖、瓶盖、床罩、书封(他带回来不看的书,她都用废报纸为它做一个书封)、证件套……她家的各种证件,比如户口簿、煤气供应证、房产证、身份证、存折什么的,她都要给它们戴上一个塑料套子,即使原来有的,也要再套一个。他们家的一切证件永远像刚发的,全新的。这给她一种满足感,这些证件会比其他人的用得更长。餐桌就不用说了,永远耸立着各种盖子,吃不掉的剩饭、剩菜、汤水,马上盖起来。看上去就像一桌子蘑菇。没有一只苍蝇会光临她家,就算来了也什么都吃不到。她是个贤妻,这一点他是知道也感激的。
他在单位沉默寡言,只在开会的时候才开口。没人愿意私下与他交谈,他的口臭令人无法忍受。同事们在距他一米开外就赶紧将要点说完,然后掩鼻而去,仿佛他是一个厕所。他以为这都是彬彬有礼、拘泥于繁文缛节所指,他宽宏大量,任他们唯唯而退。回到家才打开话闸子,滔滔不绝、千言万语、口若悬河、说长道短、津津乐道、侃侃而谈、大言不惭、绘声绘色、眉飞色舞、喋喋不休、甜言蜜语……说的都是单位上说过的:计划全面推动了建设,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升,对物质的要求也越来越多,企业生产更加繁忙,满足了市场的供给需求。对于生产型企业,其安全性更加重要,只有全面保证安全生产,才能形成可观的经济效益,推动企业快速良好发展。其生产过程非常复杂,任何一个生产过程,都存在危险性,只有全面保证安全,才能避免生产事故。化工企业生产安全管理至关重要,其安全运行对企业正常运转,起到推动作用,安全是化工企业最为重要的基础工作。化工企业日常生产过程复杂,其安全因素也较多,要把安全生产抓在日常,把预防放在平常,只有全面维护好日常生产,保证生产安全,注重安全管理,及时进行安全事故预防,才能防患于未然,杜绝各种安全生产事故发生,避免伤及员工人身,保证企业快速发展……她一句也听不懂。他不知道她天天洗耳恭听的,是一门外语。从新婚到现在,他在她耳边(饭桌前、看电视的时候、她梳头的时候、她炒菜的时候、同床共枕之际等)说了四十三年。
到他们相敬如宾四十三年的时候,小区发生了一场传染病。物业公司在小区门口贴了告示,要求住户必须24小时戴着口罩。机会来了,她欢天喜地,立即跑去小区旁边的药店买来一打口罩,付款后就取出一个马上戴起来。她感到空气前所未有的清新,一股好闻的福尔马林味。他回家的时候,并不见外,也没有取下单位发的口罩。他担心她是潜在感染者。现在她可以光明正大、理直气壮地戴着口罩了。他们出门戴着,在家里也戴着,吃饭的时候戴着,在客厅里看电视的时候戴着。两口子干什么分开一米,为此还再买了一张餐桌。睡觉的时候例外,口罩是戴着的,但是在一米以内,她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新鲜感,戴着口罩做那件事,她激流滚滚。
五月的一天,物业公司贴出告示,这次的传染病已经结束,大家可以取下口罩了。一取下口罩,居民们就盟军进城般地彼此拥抱,唇齿相依。他也取下了口罩,根据新的文件,继续戴着口罩有碍于小区形象。可是,她的口罩取不下来了,那个口罩长进了她的脸,如果要取下来就必须去整容。他们这里经常有各种超现实的事情发生,比如,他们家外面,昨天晚上还是一片树林,今天早上起来,就变成了购物中心。大家对奇迹司空见惯。整容要花很大的一笔钱,他们负担不起,她从此就日日夜夜戴着口罩,口罩令她比她本人还好看。大家都很高兴,她成了小区里的卫生模范和学习样版。一个活着的纪念碑,时时提醒人们记着那些血的教训。
他们很幸福,一个戴着口罩,另一个没戴。他越来越严重的口臭再也不会令她窒息。他们一直没有小孩,现在奇迹发生了,戴着口罩同床共枕半年后,她怀孕了。
于堅,诗人,现居昆明。主要著作有《棕皮手记》《0档案》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