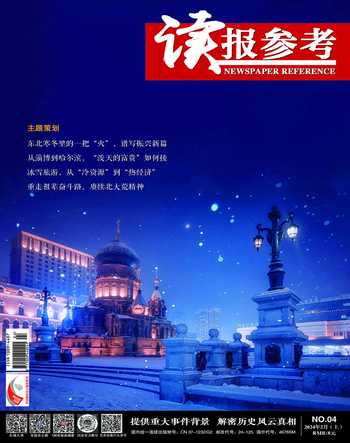“气候特使”解振华:谈判桌上十六年
霍思伊
2023年底,在阿联酋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大会(COP28),是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解振华感到“最困难的”一届。但他还是一如既往的坦率,不照本宣科,也不用外交辞令。十几年来,他的形象似乎没有变化过——笑起来显得宽厚、亲和,但当严肃起来,没有人能忽视他。
“没有人会怀疑他在真诚地投入”
在国际气候谈判舞台上,少有人可以像解振华这样同时获得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信任。“关键阶段,他可以使事情顺利解决。”这是来自一位老对手兼老朋友托德·斯特恩的评价。2009-2016年担任美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的斯特恩对解振华十分熟悉,两人共同经历了全球气候谈判历史中最重要的几次大会——从哥本哈根、坎昆到德班和巴黎。
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解振华是“发展优先权”的坚定捍卫者。邹骥曾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在2000-2015年深度参与气候谈判。到现在,他还记得解振华在2011年南非德班气候大会最后时刻对发达国家的抗议:“大幅度率先减排,减了吗?要对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你提供了吗?……我们是发展中国家,我们要发展,要消除贫困,要保护环境,该做的,我们都做了,你们还没有做到,你有什么资格在这里讲这些道理给我?”
他的语速明显加快,声音上扬,右手频繁摆动。话毕,现场爆发出热烈掌声。这段话后来被中外媒体反复引用,作为当年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激烈矛盾的历史注脚。从2009年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开始,此后几年的谈判焦点都在如何理解“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1997年通过的《京都议定书》只要求发达国家承担减排义务,因为它们是历史排放大国,但后来,世界经济格局悄然发生变化,欧美开始要求中国等发展中国家也接受约束性减排指标。
面对这种要求,当时,解振华明确回应,要求中国在工业化过程中、在人均GDP只有3000多美元的情况下,承担更多减排责任,这显然是不合理的。“中国自主采取的减排行动没有什么谈判余地。”发达国家还将减排和援助问题绑定到一起,提出“发展中国家采取减排行动,是获得资金和技术的前提和条件”。这才有了德班的一幕。其实,在解振华的气候谈判生涯中,这种正面交锋的时刻并不多见。“在德班时,我们就开玩笑地说,解主任可算是在大会上发了一次飙。”邹骥回忆道。
他认为,解振华的谈判风格并不是对抗性的。遇到分歧时,他首先想要“解决问题”。他会要求双方各自亮出自己的红线,“什么是不能碰的,什么是中方决不会让步的,什么又是可以商量的”。在维护中国及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大是大非”上,他坚持原则,姿态强硬,决不含糊。同时,他清楚意识到,气候危机是全人类的危机,没有国家可以独善其身,这是所有缔约方的“共同语言”。在这个根本“共识”下,谈判是“要寻找各方的最大公约数”。
“将国际国内结合得非常好”
多位受访者都说,解振华不仅眼看世界,更难得的是,他还非常体察中国国情,这与他1970年代初以天津知青身份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插队的岁月有着很深的关系。在生态环境部宣教中心原主任贾峰看来,他在基层历练过,才能真切认识到中国不同地区差异巨大的面貌,“这也让他在国际谈判时更容易理解不同国家的各自立场”。以同样的视角看待中国,解振华常对邹骥说,你没了解过中国,就搞不明白中国的气候问题。
解振华后来被国际社会广为赞誉的一点,是不仅推动全球在气候问题上走向共识,而且能将全球气候变化应对进程,转化为国内气候政策的驱动力;反过来,中国自身积极推动能源转型,也成为他国际谈判的基础和底气。“解振华把国际国内结合得非常好,既考虑到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些现实需要,也考虑到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上的国际形象。”中国气候谈判首席代表苏伟说。
结束知青生涯后,解振华在1973年进入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毕业后留校从事科研工作任助教。1980年代,他进入国家环保局,此后历任人事司司长、副局长、局长。1993年6月,他接任局长时只有43岁,此后在这个位子上一干就是10多年。2006年末,解振华担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分管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领域,正是在发改委期间,他开始关注气候变化,参与国际谈判,并参与制定国内低碳转型政策。
邹骥在六年后成为了解振华的直接下属。在解振华的牵头下,2012年,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成立,邹骥是中心的副主任。他介绍,这是一个国家级智库,他到任后从“老解”那里接到的第一个任务,是研究不同国家历史上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和人均GDP的关系;结果显示,所有经济体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都随着人均GDP“先增后减”,呈一条倒U型曲线,曲线的拐点就是现在所谓的“达峰”。“我们发现,中国其实可以不走发达国家的老路,通过能源转型等方法,以较低的人均GDP水平达到较低的排放峰值。”邹骥说。这项研究为中国后来提交“国家自主贡献”奠定了部分科学基础。
“讲一个道理让各方都能接受”
2009年12月,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发生了非常戏剧性的一幕:美国时任总统奥巴马和国务卿希拉里带着一众美国代表团的高级外交官在没有提前约好的情况下,强行闯入了“基础四国(中国和南非、印度、巴西,英文简称BASIC)”领导人正召开闭门会议的房间内,要求中国作出更有力的减排承诺。
这次大会最后只形成了一份不具法律效力的《哥本哈根协议》,有评论认为 “这是一次彻底的失败”,一些西方媒体将失败归咎于中国在会上说“不”。但事实上,大会召开前,中国就公布了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行动目标:到2020年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要比2005年下降40%-45%。解振华说,这一目标已经体现了中方“所能做的最大努力”。
外部的壓力在一定程度上源于中国自身的快速发展,与1992年刚加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时相比,中国当时在全球的经济地位,以及国际社会对中国的看法,已经彻底不同。21世纪的前10年,中国经济增速经历了高速增长,2010年,GDP总量已超过日本,居世界第二。经济高速增长带来能源消费和排放的增加,“一些西方国家很担忧中国的排放成了脱了缰的野马。”邹骥说。
《巴黎协定》顺利达成后,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能源和气候专家王韬等人撰文指出,这见证了中国“在这个最重要的全球环境治理舞台上”成为领导者的华丽转身。据生态环境部统计,中国已提前超额完成了2020年气候行动目标,2022年碳排放强度比2005年累计下降超过51%。同时,中国在能源转型上也体现出更积极的姿态:2020年9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联合国大会上首次宣布了中国的“双碳”目标: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在“2030年左右达峰”上更进一步。
2023年11月4-7日,解振华与美国总统气候变化事务特使克里,在美国西海岸加州的安纳伯格庄园举行会谈。这里有一个更广为人知的名字——“阳光之乡”。解振华和克里谈到深夜、谈到“加时赛”,但也抽空在加州的阳光下一起扔飞盘,散步聊天。
最终,双方团队达成《阳光之乡声明》。这是中美2021年重启气候变化谈判以来的第三份联合声明,也是随后举行的COP28大会期间最为世界瞩目的文件之一。自从《巴黎协定》达成后,中美之间能否达成“联合声明”,几乎成为全球气候变化合作能否取得重大突破的关键风向标。
在刚结束的COP28上,有外媒谈到了解振华和克里之间的特殊关系,并对未来的中美气候合作以及中美关系表达了担忧。解振华回应说:“他(克里)今年已经80岁,我今年75岁了,我们不会离开这个领域,我们还会尽我们的努力来推动这个领域的进程。”
(摘自《中国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