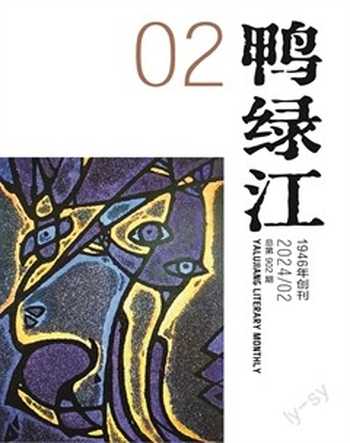禾之路(散文)
插秧
清明一过,时雨时晴,秧苗噌噌直往上长,不出一月,便是青绿一片。戴月伯蹲下身子,扯出一蔸秧苗,数了数秧叶,已快长到第五叶,自语道:“插秧早,收成好,该是插秧的时节了。”
戴月伯年近七十,头发白成了一堆雪。婆娘花英婶也有六十好几,身躯干瘪得如同一根老丝瓜。孩子们一年到头在外打工,只有春节才回家数天。家里共有三亩二分田,租出两亩多,仗着身子骨还硬朗,走得动的,余下的一亩多,两人便自己种。到底是老了,一亩多田,犁田耙田,施肥播种,以前只需三五天便样样忙活完,现在却花了十多天,累得两人骨头像散了架。
插秧插时,最需要人手,可现在寨子里全是些老人和小孩儿,谁也帮不了谁。无奈,天还麻麻亮,戴月伯就和花英婶下田扯秧了。他们一个背着黑蓑衣,一个披着白薄膜,冒着纷纷细雨,俯首弯腰,反着右手不停地扯着秧苗根部,每扯一扎,就递给左手,扯至三扎,便拢成一把,双手紧握,将根部朝水中不停抖动,直至洗净泥巴,根须收缩成尖尖的一绺,这才略微直起身子,从面前抽出两根稻草,在秧颈上缠绕几圈,系紧扎牢,抛至身后,随即又俯下身子继续扯秧。两公婆一边扯秧,一边畅谈着以前寨子里插田的热闹情景。
以前男女老少都在家,插秧时节,都是三五家组成一群,十几个劳力互相换工,互相帮忙,一家一家去插秧。到谁家去插秧,主人只管酒饭,不计报酬。大家在一起插秧,热热闹闹,有说有笑,阿哥阿妹还对唱山歌,以歌传情,再苦再累也觉得快活无比。还记得谁家插秧,这家男主人必在田间烧香化纸,敬拜天地,同时还会呜呜呜地吹响牛角,唤醒谷魂,请它快快来到田中,呵护秧苗茁壮成长,祈祷五谷丰登。女主人则必唱《开秧歌》:“四月插秧行对行,感谢亲友来帮忙;插个星子配月亮,插个小妹配情郎。”按习俗,第一把秧须由女主人亲手插下后,大家方能开始插秧。这时,女主人一边唱着《开秧歌》,一边开始插秧,插完这第一把秧,她便拔腿向田尾猛跑。大家为了让她跑得更快,便不停地拿起坨坨泥巴朝她身上投去,还有人不停地朝她身上戽水,歌声、呐喊声、欢笑声响彻田野。据说女主人跑得越快,她家的秧苗长得也更快,稻谷也结得更多。有时,大家正埋头插着秧,不知是哪个阿哥兴起了,便会对旁边一个阿妹喊道:“来来来,给你一坨糯米粑粑吃!”说着,便拿起一坨泥巴朝她身上投去,这阿妹立即拿起泥巴回击。很快,空中便泥团横飞,泥水四溅,大家互相打起泥巴仗来,个个都满身花花点点,泥迹斑斑,活像女娲捏出的活泥人,惹得笑声一片。
戴月伯和花英婶回忆起插秧打泥巴的情景时,两人不由得都笑出了声。戴月伯问花英婶:“婆娘你还记不记得,那年我到你家插秧,大家一起打泥巴仗,我没站稳,不小心四脚朝天倒在田中,你忙去拉我,大家都笑起来。你羞得满脸通红,想缩回手,我却紧拉着你的手不放,你用力想挣脱,不料一个踉跄,竟也跌倒在田中,和我滚在了一起,大家又是大笑,你又羞又恼,爬起身子,双手捂着脸跑走了。 哈哈,这我可记得清清楚楚。”花英婶听了像个少女样脸露羞涩,嗔怪道:“你还好意思说,这还不全怪你,让我出了洋相。”“你的手那么软和,我哪舍得放手。”“你这个老不正经的,都七老八十了,还说这样的话,小心被别人听见了。”“听见了也不怕,你本来就是我婆娘……”呵呵,放心,空山不见人,山野里说话,只有鸟儿虫儿听得见,它们叽叽喳喳,怎么羞笑都无所谓。
说笑归说笑,但人插起秧来,两腿半蹲,就像练马步那样,屈腰弓背,左手握秧,右手尖着三指,不断从左手分出一株株秧,插入泥水中,边插边慢慢退步后移,时间一长,腰身痛得就像被折断了一般,浑身直冒虚汗。古人在一首《插秧诗》里写道:“手把青秧插满田,低头便见水中天。心地清净方为道,退步原来是向前。”诗写得好,可却没写出插秧的艰辛,估计这位诗人一定是没真的插过秧。当然,年轻人腰软力大,插起秧来,又直又快,面前转眼便是排排整齐的秧苗。戴月伯两公婆插着插着,便渐渐慢了下来,他们颤颤巍巍地站在田中,手脚也不再灵活,插秧的动作有点像是慢镜头。不一会儿,两人便气喘吁吁,只好停下来歇息。
树老根多,人老话多。戴月伯坐在田埂上,又对花英婶说道:“婆娘你刚嫁给我时,十五湾的人哪个不夸你长得乖,都把你比作天上的织女下凡,我那时也壮得像条牛,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唉,没想到转眼我们就老得不像样子,连插秧都没有力气了,也不知我们还能有几年秧插。”“老了就老了,秧有力气就来插,没力气就莫插嘛。”花英娘答道。“你看现在寨子里的人越来越少,我是担心以后还有谁来种田。”戴月伯又说。“你就是个死脑壳,人总要吃饭的,我们死了,总会有人来种田的。”戴月伯想想,觉得也是这个理,只是觉得婆娘说话没遮没拦,竟一连说了两个死字,多少有些晦气。抬头见时候已是不早,便站起身,伸伸腰,直说腰痛得厉害,嚷着要回家,花英婶本来就对他心疼不已,自然同意收工回家了。蹒跚地走在田间小道上,戴月伯抬头一望,刚好望见寨子后面那条细肠似的山路,在云雾中若隐若现,七拐八弯,一直延伸到山顶那片树林深处。那树林也是墓地,依了寨里的古老习俗,那兒每棵树下都埋着一个死去的人,自己不久也将如一蔸秧苗被插入泥中一样,被埋葬于山顶的某棵树下。唉,只可惜秧入泥是为了更好地活着,人入土却是永远地死去,心里顿时备感悲凉。
寒来暑往,转眼就是两年。戴月伯和花英婶虽又老了两岁,身子骨却还不错。时节一到,他们又有说有笑,下田开始插秧。插完秧没几天,绿油油的秧苗一望无边,层层梯田如同铺了一层翠绿的地毯。戴月伯那天去田里看水,不料竟滑了一跤,一头倒在插满禾苗的田中,再也没有爬起来。
守灵之夜,世花道公一边绕着戴月伯的棺木抛撒着白米,一边吟唱着祭祀亡魂的《指路经》:“自古有大地,天下万物生;万物在繁殖,万物在老去;天地日月星,也要死一回;有生必有死,寿终要归根……”花英婶则伏在漆黑的棺材上,伤心地哭泣道:“我们才插了秧,谷子都还没长出来,你怎么就去了?”
世花道公宽慰道:“戴月伯坐化在禾田,跟了谷魂去,这可是他前世修来的福分。”
薅舞
“击鼓薅秧,歌舞神欢。”这一古老的薅田方式,就是十五湾莫家人的薅舞。
“呜呜呜,唪唪唪。”每年立夏一过,莫家人便会吹起芦笙,敲起长鼓,开始下田跳薅舞。在一个名叫米姑舞师的指挥下,大家三五一群,排成行,手拉手,双脚合着鼓点儿在禾苗间不停扫动,身子有节奏地摇摆不已。大家一边跳,一边唱起绵绵山歌。“清早起来云层层,敲起长鼓请谷神;为人莫把谷看贱,谷公谷婆养万民……”这是年长者在唱。“跳起薅舞好唱歌,薅草好比剃脑壳;只要哥心合妹意,明天就去请媒婆……”这是阿哥阿妹在唱。在米姑舞师带领下,人们跳得越来越兴奋,歌声不断,笑声不断,禾田很快便成了一片歌舞的海洋。当然,米姑舞师看见田草薅得差不多了,定会唱歌作谢:“今天薅草都发狠,好像天门大交兵;男的赛过赵子龙,女的赛过穆桂英;一声长鼓一股劲,一字长蛇敌千军;汗水淋淋如下雨,丘丘田里出黄金;大家薅田辛苦了,杯杯美酒谢亲人。”
莫家人就这样以禾田为舞台,将艰辛的劳作变成欢乐的舞蹈,既亲近了大地,也慰释了疲惫。他们双脚不停扫动,便是巧妙地用脚趾代替锄头,在禾苗间进行“翻田”,去杂草,活根系,让禾苗快快成长,祈求丰收。
米姑舞师可是众里挑一的好角色,不仅人长得乖,能歌善舞,性格也泼辣大方,能说敢做,天生是块当导演的料。每回指挥大家跳薅舞,她必先下田跳一场给大家做榜样。只见她手持长鼓,举过头顶,仰首凝神看天,像是在虚无里看到了什么,接着嘴唇轻轻抖动,默念着无人听懂的咒语。忽然,她猛叩一声长鼓,身子一抖,长发一甩,如换了个人似的,双脚开始不停扫动,合着鼓声全身跳动起来,鼓点时慢时快,动作也时缓时急,什么佛坐莲台、孔雀开屏、金鸡啄米,都展现得惟妙惟肖。很快,她身上的薄衣衫早被汗水浸透,湿漉漉地紧贴肉身,映衬出凹凸起伏的优美曲线,随着动作更加急促有力,长发如黑色火焰般在风中高高飘扬,如同稻花娘娘神魂附体、投胎一般,直让大家都看得张大嘴巴,目光发直。
米姑舞师指挥众人下田跳起薅舞时,如同魔法师般,常会想出种种法子调适大家的情绪,时而插科打诨,来段笑话,时而敲起长鼓,数快板似的唱首《怪怪歌》:“好久没唱怪怪歌,牛生蛋来马生角;茅草窝里鱼打籽,清水塘里鸟絮窝。”要不就是动员年轻阿哥阿妹对唱山歌、互表情意等,总会让大家激情满怀,兴奋不已。
米姑舞师也是热心肠,在指挥薅舞中,每发现某对阿哥阿妹有那么一点意思了,定会马上去双方家中撮合,自是做一对成一对,她又成了十里八乡有名的媒婆。
米姑舞师是土生土长的十五湾人,家里就她一根独苗。十八岁那年,她去山那边的山寨跳薅舞,被一位叫阿柴的后生看上了,竟主动入赘到她家,心甘情愿做起了上门女婿。阿柴瘦得确像根细柴火,却有一身使不完的力气,犁田挖地、砍柴割草样样能。两人从不红脸吵嘴,生下两女一男,生活苦点累点不要紧,只要家里常有笑声,苦水也会变成蜜。哪怕到了大年三十除夕夜,家里穷得买不起肉,炖一锅萝卜,两口子照样猜枚划拳喝几杯。
那年米姑舞师身怀六甲,却遇上了难产,抱着肚子痛得在床上直打滚,可就是不见儿子拱出来。痛了一天一夜,急得阿柴团团转,只好跪在神龛面前又是烧香化纸,又是叩头许愿。他抬头一望,忽然看见神龛上那具乌黑油亮的长鼓,顿时计上心来,连忙捧起长鼓跑进房中,对着婆娘敲响长鼓跳起薅舞来。米姑舞师听着看着,好似被什么唤醒了一般,竟一下有了力气,她猛然一使劲,“哇——哇——”一个白皙如米的胖小子终于落了地。传说长鼓正是莫帝老爷的一根骨,夫妻两人喜不自禁,为感恩祖神福佑,便将儿子取名为鼓生。
山里娃娃养得贱长得快,鼓生一岁能在田埂上爬,听蛐蛐吟鸣,看蝌蚪戏水;三岁不到便能在田埂上追鸟雀、捉蝈蝈;五六岁就放着牛儿满山跑了。耳濡目染,鼓生自小便跟着母亲到田里打长鼓、跳薅舞,成了一个人见人爱的小舞师。脑子灵光的鼓生进了学堂,功课成绩好,连老师也夸他真是“响鼓不用重捶——一点就明”。那年果然考上了大学,成了寨子里飞出的一只金凤凰。
米姑舞师两公婆看到儿子长大成人有了出息,更加心生感恩,夫妻两人不仅常去莫帝庙叩拜莫帝老爷,对家中神龛上那具老长鼓更是视若神明,初一十五必烧香化纸,作揖敬奉。米姑舞师每每跳起薅舞来,也更加用心,更加投入,一招一式,都似在与神灵语,人们都说她跳舞时真能把稻花娘娘引下凡来。
已在城里谋生安家的鼓生,回家越来越少,米姑舞师和阿柴也越来越老。空空的寨子里只剩下老人和为数不多的孩子,人们早已不再去田里齐跳薅舞,只剩下米姑舞师两公婆还在继续跳。他们在禾田里跳,也在神龛前跳,还在梦乡里跳。虽然动作越来越迟缓,越来越笨拙,但他们的神态却还是那么专注,那么虔诚。他们说,摸着长鼓就如摸着儿子,敲响长鼓,儿子一定知道爹娘在想他。还说,他们肉身离土越来越近,只有敲响长鼓、跳起薅舞才能不迷失回去的那条路。
两公婆再好,总有人会先走一步。那日,阿柴在神龛前敲着长鼓,米姑舞师和着鼓点跳着薅舞,他们似乎看見堂屋里长满了青青的禾苗,随风起伏,荡起层层波浪,阳光跳荡,粼光闪闪。长鼓响声忽然停了下来,阿柴怀里紧搂着老长鼓,面带笑容,仿佛在梦里踏上了那条长满禾苗的路……
孤身一人的米姑舞师变得更加老了,眼花耳背,脑子也有些糊涂。她整天紧抱着那具老长鼓,目光无光,神情呆痴,似睡非睡。眼前的人和事她已无法记得,只记得过去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琐碎小事,譬如某年她在田中滑了一跤,阿柴如何将她从泥水里抱起;譬如某年她第一回背着鼓生在田里跳薅舞,鼓生先是被吓得哇哇大哭,后来却变成开心地笑,再后来如不背着他跳舞,就整夜哭闹不睡觉。鼓生把娘接到城里住,将娘带到城里的医院看病,医生给她做了一大堆检查,身体没查出任何毛病,就说脑子有病,诊断上写着:“初步诊断为中度阿尔茨海默症。”医生告诉鼓生,就是老年痴呆。鼓生心疼娘,怎么连儿子都不认识,背着娘四处寻医求方,尽管现在科学已发达到连人都可造出来,却无法医好人脑子里这个痴呆病。
“唪啪唪梆、唪唪梆——”幸好,米姑舞师只要一听见这长鼓声,立刻会笨拙地跳起自己熟悉的薅舞来。如同从一个古老的长梦里苏醒过来,似乎只有跳着舞的米姑舞师才是一个正常人。她一边跳,一边说自己的身体好得很,还可回寨子种几年禾。
护秋
缺巴头戴破斗笠,身披棕蓑衣,疾步行走在田埂上,一边叮叮当当地手摇响筒,一边哟嗬哟嗬地大声吆喝,惊飞起群群偷啄稻谷的鸟雀。不一会儿,缺巴便气喘吁吁,汗如雨下。有人见了,好心递上一瓢水,给他解渴消乏。可当他捧起水瓢还没喝完,鸟雀们在天空盘旋一圈,竟又纷纷飞回来,落进了稻田里,好似在和他捉迷藏。他不得不又连忙吆喝起来。那人接过瓜瓤,禁不住摇头叹道:“唉,护秋赶鸟还真是个苦累活儿。”
入秋后,云梯岭层层梯田被阳光涂抹成一片金黄。山风拂来,稻浪滚滚,如掀起簇簇火焰,燃遍整座山岭。稻子悄悄地壮籽落色,谦逊地鞠躬弯腰,向大地致以深深的谢意。藏在暗处的鸟兽们伺机窥探着,稍不注意,就来啄食与践踏。为驱逐鸟兽,以免收成受损,护秋便成了眼下最要紧的一件事。
缺巴是个鳏夫,因天生一兔唇,嘴巴老关不住风,说话口里就像含了一个大红枣,口齿不清,含含糊糊,常被人笑话,人們都唤他“缺巴”。沉默惯了的缺巴站在人堆里,只喜欢听别人絮叨,自己却从不说话,就像立着一根木头。大多时候,缺巴都是一个人犁田挖地,一个人砍柴割草,一个人吃饭睡觉。人们见他为人实诚,做事认真,便推举他为十五湾寨的护秋人,秋收后每家分他半斗谷子算是报酬。
为了驱赶鸟雀,缺巴会在稻田里扎个稻草人,和他一样,也戴顶破斗笠,穿件烂衣裳,手上插根长竹竿,竹竿上挂着花布条,风一吹,随风飘扬,还发出呜呜呜的声音。乍一看,活像个大怪人,鸟雀自被吓得不敢靠近。只是久了,精灵的鸟雀才发现这只是个假人,没什么可怕,便再次飞来,无所顾忌地啄食稻谷。有胆大的,甚至落在稻草人身上,叽叽喳喳叫个不停,仿佛在嘲笑人的愚蠢,末了,还朝稻草人头上拉一泡屎。越是临近秋收,鸟雀就越是胆大,缺巴只好将自己扮成一个活的稻草人,四处不停追赶,直累得精疲力竭。
野猪、野狐、野猫、野狗,都像长了夜眼一般,一到黑夜,便成了山林的主宰,纷纷成群结队,溜至田间地头,胡乱践踏稻谷与庄稼。缺巴便掮了鸟铳、牛角、梆子、响筒、电筒,早早来到山中寮棚,支起两耳,睁大双眼,警惕地观察着周遭的一切。凡有什么风吹草动,他立马吹响牛角,或是摇响响筒,口里还不停发出“噢噢噢”的呐喊声。呜呜呜,叮叮当当,顿时响声大作,草丛里很快传来“唰唰唰唰”的声音,吓得兽物们撒腿就跑。若没有什么动静,缺巴则会如更夫一样,时不时敲响梆子,“哆哆哆——哆哆哆——”山野愈显寂静。
也有饿得慌的野猪,并不畏惧这些人造的声响,仍斗胆来到田间,四处践踏。缺巴便走出寮棚,悄然而至,端起鸟铳,远远地瞄准了,“砰”的一声,野猪应声倒地,当场毙命。那年却遇上了一只大野猪,全身皮毛又厚又硬,缺巴一铳射去,竟没打中要害,受了伤痛和惊吓的野猪立刻循着铳声,如猛虎般他扑来,缺巴赶紧丢下鸟铳,像猴子样爬上一棵大树躲避。这野猪围着大树转了几圈,便哼唧着用大嘴巴使劲拱刨起树蔸根部的泥土来。很快,大树开始摇晃,眼看就要倒下,缺巴只好朝对面一棵大树狠命扑去,不料失手坠落,重重地摔在地上,一条大腿当场骨折。后来虽经能识草药的痣苟阿公精心治疗,骨头是接上了,但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终是落下了残疾。
莫家人自古认为,人间万物各有其命,众生平等,缺巴摔成残疾,正是杀生遭了报应。自此,缺巴再也不敢端着鸟铳去打兽物了。为更好地驱赶鸟雀野兽,缺巴还砍来青竹,精心制作出许多小水碓,安放在溪涧谷壑旁。溪水流过,小水碓便会上下运动,如小鸡啄米般,反复叩击碓头下的石头,发出空空空的声响。缺巴还在树上悬挂盛有玉米稻谷的竹篓,吸引鸟雀来啄食。缺巴在田间驱赶鸟雀跑累了,就索性将自己隐藏在某个稻草人旁,一动不动,待鸟雀来啄食稻谷时,他猛地跳出来大声吆喝,鸟雀受到极大惊吓,纷纷逃之夭夭,很久都不敢再飞来。
多年前的一个清晨,缺巴从寮棚里守夜回来,走在山路上,隐隐听见婴儿的啼哭声。他跟着声音寻去,在一水沟边看见一个背篓,背篓里竟躺着一个女孩儿,在哇哇大哭。心地慈善的缺巴,赶紧将女孩儿抱在怀里。或许也真是一种缘分,他一抱起来,这女孩儿便停止啼哭,对着他笑了起来。他便给这孩子取名为“笑笑”。从此,缺巴便东家一口奶,西家一口饭,又是当妈又是当爹,精心将笑笑抚养。他常对人说,笑笑正是天老爷赐给他的一个宝贝,苦点累点都不算啥,只要能把她养大成人,就是自己最大的心愿。
笑笑长到五岁,便能在田埂上四处奔跑,学着父亲“哟嗬哟嗬”地驱赶鸟雀。晚上则和父亲一起住在寮棚里,跟着父亲数星星、看月亮,阵阵蛙鸣虫吟作了她的催眠曲。在无数个睡梦里,她常与草木对话,与小兽嬉戏。
笑笑长到十八岁,自小爱笑的她,转眼便成了一个更加爱笑的大姑娘。同样,她也跟着伙伴们到广东去打工了,只是她比别人多了一份更重的牵挂。她也比别人更舍得吃苦,进厂子当工人,进酒店当服务员,她啥都愿做。她在城里也从来舍不得乱花一分钱,她将钱一分分攒下,就是想着要让父亲过上好生活,能享享晚年的清福。
或许爱笑的人的确是更加有福气。几年后笑笑便幸运地结识了一个同样勤快能干的好小伙儿。两人结为夫妻,一起打工挣钱,一起攒钱持家,还一起年年回家陪父亲过年。每次回家,都要给父亲购回好多新衣裳和高级糖果,让父亲穿着新衣裳,吃着香甜的糖果,在寨子里四处转悠,逢人便说,你瞧,这是我笑笑给我买的。
很快,笑笑又生下了一对好儿女,让缺巴当上了外公。寨子里的人更是羡慕不已,都说他为寨子护秋,驱赶鸟雀野兽,苦了一辈子,真是好人有好报。
后来,缺巴日渐变老,笑笑便把他接进城里一起生活。可缺巴却像只候鸟一样,每年秋后都会回到寨子住上一两个月。有趣的是,每次回来,他从不住在自家房中,而是独自住进山中的寮棚。他说,只有躺在寮棚里,才能让自己睡得更踏实,更舒心,还能梦见过去护秋时的幕幕情景。
作者简介>>>>
魏佳敏,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永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秘书长。现供职于永州市文联,任文学杂志《潇湘》执行主编。出版长篇散文《怀素,一个醉僧的狂草人生》、散文集《云上的年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