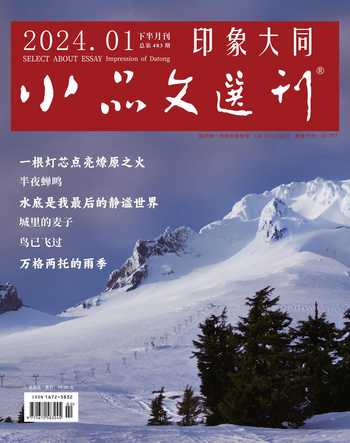文学的来路和去向
罗伟章 张杰
每个人的骨髓里都敲打着古歌
张杰:您的小说爱用“史”命名,比如《声音史》《寂静史》《隐秘史》等等。小说运用“史”的概念,肯定不是历史学的概念,应该更倾向于哈罗德·布鲁姆对史诗的解释,即审美的历史,包含着人类不懈奮斗的精神,通往最深的智慧。为什么对“史”这个字这么情有独钟?
罗伟章:也不是情有独钟,我写了那么多小说,以“史”命名的,除你提到的三部,最多再加个中篇,名叫《史官》,本名《冉氏春秋》,发在《十月》上的,最近出集子,改名《史官》。但的确,我对这几部小说的名字很满意,很喜欢,首先是贴切,再是有异质感、穿透力,比如声音、寂静和隐秘,难得有人为它们写史,而我写了,既是审美史,也是命运史,人和万物,都被赋予了来路和去向。来路是历史,去向也是历史,是未来的历史。我们都活在历史的境遇里。我曾在《谁在敲门》的后记里说,每个人的骨髓里都敲打着古歌,也是这个意思。
张杰:在《隐秘史》里,文本追求的志向非常凸显,但故事冲突又很强,甚至都涉及凶杀案。写这个小说的契机或者起意是怎样的?
罗伟章:你说有故事冲突,这太好了。这是一个心理小说,是主人公和他的另一个自己博弈的小说,我还担心读者会有隔膜。事实上不会,很好看。凶杀案是表,由表及里,不断深化。契机是有一次我回老家,听我哥说一个山洞里发现了一具尸骨,完全成了白骨,但未能破案,不知死者是谁,是自杀还是他杀。这让我为那具尸骨揪心,揪心于他死得“不明白”。我想让这件事明白起来,让白骨回到皮肉、回到体温、回到种子,便写了这个小说。选择的写法,与题材有关。我们说内容决定形式,有它的道理,但也绝不是真理。对形式的选择,同样会左右内容的走向。形式内在于内容,内容又何尝不内在于形式。
张杰:《隐秘史》的责编在介绍这本书时,用了这样的句子:“通过对普通人无法言说的软弱、苦恼、恐惧乃至罪孽进行聚焦显影,用诚恳、坚实而平等的对话,分担精神的痛苦,从而修复人们无法自知的平庸、匮乏与残缺。”我觉得说得非常好。您觉得这是您想要到达的目标吗?
罗伟章:确实是。责编也是从文本出发,概括出小说的意蕴。至于我完成了多少,让读者去评判最妥当。我觉得我做得很好,但我说了不算。
张杰:除了写虚构作品,您还写了非虚构作品《凉山叙事》《下庄村的道路》,面对这样的题材,您有怎样的写作体会?
罗伟章:这类题材有其特殊性,要写好,确实有难度。我要做的,不是简单地歌颂,也不是粗暴地批评,而是本着作家立场,悉心融入又冷静观察,思考其中的逻辑,梳理可能性路径。总之是审视的态度。我不光审视别人,也审视自己。通过这两部作品的写作,特别是对《凉山叙事》的写作,我有一个感触:人与人,表面上看起来差别很大,但深入内核,发现一些人并没有比另一些人高明多少。这也提醒我,谦逊不仅是品德,还是自我生长的可靠空间。还有一点,作为写作者,要切实知道自己生活的大地正发生着什么,这种“知道”不是来自新闻,而是来自自己的脚步、感官和头脑。
张杰:对凉山的叙述有没有什么创新的、不同于以往的表达方式?
罗伟章:《凉山叙事》这本书,重在阐发“移”和“易”、“变”和“守”,因此得纵论古今,找出根源。我希望进入这个地域和这个民族的内部,对他们为什么有那样的传统、有这样的今天,从历史积淀、意识形态和文化观念的角度,系统打量。但还不够,它必须是审美的,是有艺术匠心的。既然去写,我就立志完成一部书的价值,不仅在今天,还在未来,都有存活的理由。
张杰:现代作家爱谈论“人性”,您是怎么看待这个词的,或者在您的文字里是如何叙述的?
罗伟章:人性当然要谈。人性的复杂本身就让人着迷。我们着迷,是因为我们想从中认识自己,同时还可以窥见转化的可能。最近我听说,有人规定,影视作品中的坏人不能流泪,比如一个坏人杀死了自己的儿子,也不能流泪,因为坏人不应该有柔软的情感。这样的粗暴比坏人更坏,它不仅装瞎子、装正义,还直接剥夺了坏人向好的通道。他们只能看见黑和白,这本身就是有病。
同时我要说,作家喜欢谈论人性,却又往往陷入人性的泥淖。只有责任感和使命感出现之后,人性才能真正焕发出耀眼的光芒。这首先体现在作家自己身上,然后才会出现在文字里。目前的情况是,我们可能有态度,却没有精神。态度是长在脸上的,是给别人看的,精神却是生在骨子里的,别人看不见,却是支撑性的存在。一个作家,当然也包括批评家,没有文学精神,就很难谈到价值。
张杰:英国当代著名作家朱利安·巴恩斯在他的文学随笔集《透过窗户》中写道:“比起任何其他形式的写作,小说更能阐释并拓展生活。当然,生物学也能解释生活。传记、生物化学、生物物理、生物力学和生物心理学也能解释生活。但所有的生命科学都没有小说来得高超。小说告诉我们生活的终极真理:什么是生活,我们如何生活,生活何为,我们怎样享受和珍视生活,生活是如何走入歧途的,我们又是如何失去它的。”对您来说,小说意味着什么?
罗伟章:巴恩斯说得非常好。我曾在一篇文章里说:“小说是最具张力的文体。”这里的“张力”,不是就文体本身论,是指小说能呈现的宽度。生命科学是给出唯一解释,是消除可能性,小说正好相反,是挖掘和发现可能性:我们有怎样的可能,又是怎样丧失了那些可能;我们遭遇过怎样的生存和精神困境,又是怎样在突破困境中奉献了我们爱、勇气和牺牲精神,或者怎样在臣服于困境中暴露出我们的脆弱与无奈;我们怎样被实用主义深深捆绑,又是怎样超越实用主义看见了美与大义;我们经历过痛苦,承受着痛苦,因而我们有理由呻吟或歌唱……如此等等,既是小说存在的理由,也是我们热爱小说的原因。
张杰:似乎存在两种类型的作家(这两种类型都出了很好的作家):一种是比较多地依靠自己的人生和生命经验写作,会写一个故事,让人一看就能知道,这件事离他的生活很近;另外一种是不太依靠自身的实际经验,而是靠一个想法,虚构一个跟自己的现实生活离得比较远的人和事件,把自己的观念、想法包裹起来。我觉得您属于后者。您觉得呢?
罗伟章:倒不是那么泾渭分明,某些时候经验的成分重些,某些时候想象的成分重些。但不管怎样,作家的生命体验都会成为文学最独特和最光彩的部分。生命体验具有轻和重两种特质:重的是人生,轻的是想象。也就是说,提到生命体验,就自带想象。如果只有经验,文学不会飞;只有想象,文学没有根。这两种写作都会变得廉价。所以我们不谈经验,谈体验。体验能力和感受能力,是最重要的。许多时候,深入生活之所以无效,原因就在于只是“看见”,缺失了体验和感受,更没有把看见的与自身命运联系起来。
阅读的根本目的,不是为了写作
张杰:您认为作家应该怎么表现时代的变化?
罗伟章:作家们不思考,时势就逼作家思考。比如疫情,造成全球经济深度衰退,使“全球化”遭遇挫折,作家们不思考这个,就说不过去。二战之后,出现了许多伟大作品,文学、电影、绘画、音乐等,都有深刻反思和表达,蔓延世界的疫情,也定会产生同样的功效。人类远不是真理在握,人类自身的局限性,包括科学的局限性,都会成为危机的根源。在规律性面前,在与大自然的关系面前,人类依然是弱者。弱者如何规范自身,建设自身,如何成为大体系中和谐的一员,都是作家们要思考的。但表现时代的变化,不一定要从这种大事件入手,一个不经意的小小的裂缝,甚至没有任何征兆,暖风习习,歌舞升平,也可能被敏锐的作家捕捉到其中的“变”,并加以书写,构成寓言或预言。
张杰:很多人饱览群书,知识渊博,但仍写不出好文章,对此您有什么想法或者建议?
罗伟章:阅读的根本目的,不是为了写作。知识渊博就很好,能否写出好文章,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们读一本书,学习其中的技法是次要部分,更重要的是仰望更高的尺度。当然作为写作者又另当别论。有些作家,比如马尔克斯,其作品是可以模仿的,但是像托尔斯泰那类作家,就模仿不来。还有莎士比亚,他的戏剧我通读过,却并没学到什么。也可能是,太好的作品,你确实不容易看出其中的奥妙,看到了也学不来,面对文本,眼前只有浩瀚,就像月亮,伸手确实摸不着。摸不着也没关系,能服气地欣赏,本身就是美。如果一个人,拿不出一些时间读一读托尔斯泰,不能跟这种级别的心灵对话,我认为是一个非常大的遗憾。至于是不是写作,能不能写作,倒还不是那么要紧。
张杰:米兰·昆德拉说过,一个作家,有童年就够了。这个说法尽管指意丰富,但其中必然包括成长环境的意思在里面。读您的小说不难发现,您的“特定地理”就是在作品中多处出现的那个有着三层院落的村庄,像福克纳笔下那枚“邮票”大小的地方,写不尽,是因为不断有新的想法、新的人物进去?
罗伟章:一个作家最好有自己的“特定地理”,它与写作者的生命有着深度联系,是成长期的联系——你在成长的同时,把你生存的环境也融进了血肉,就成为了你的一部分。写作的时候,将小说地理设定在那个环境里,你便胸有成竹,人物自在活动,生活的质感扑面而来。我将其称作“命定的写作方向”。如果一个写作者终其一生都意识不到这一点,只是东一锤子西一榔头,看到什么就写什么,听到什么就写什么,可能会产生单篇佳作,但很难产生持续的创造力。
张杰:您曾说,文学写作用词不要太油滑,哪怕生涩一些,笨拙一些,也比油滑好一万倍。但是同时我也听说,作家不要用生造的词,不要刻意用冷僻的词。如果故意用冷僻的词,显得很小气,很匠气。这两者之间如何平衡?
罗伟章:所谓笨拙并不是真笨拙,只是要老实一点,不要显得过于聪明。生涩也不是生造,是说不要像水管那样,龙头扭开就哗哗啦啦流,要像河水一样,该奔腾时奔腾,该有暗礁就有暗礁。其中强调的,是朴素、个性和自然。油滑恰恰背叛这些品质。油滑是文学的大敌。
张杰:很多小说故事讲得挺好,但读起来就是不高级,语言上没有特色,文学性欠佳。您如何理解“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这句话?
罗伟章:作品没有光彩,跟对字词的惯性选择有关。很多词语看起来很恰当、很好用,但就是平淡,甚至平庸,因为没有作家的体温。优秀作家往往会跟语言“过不去”,某个词语还不是自己百分之百想要的,就不停止努力,直到把那个词语抠出来。但我也在不同场合强调过,语言从来就不是语言本身,而是作家的人生淘洗以及对世界的看法,思维到了,情感到了,想象力到了,语言才会到。
张杰:文学创作很大程度上关联着作者的个体经验,如何去平衡虚与实的关系?
罗伟章:小说一旦进入叙事,也就同时进入了虚构。个人经历可能会成为小说的“核”,但不是核心。如果一个作品越写越像自己或身边人,这个作品就败坏了,越写越不像,就成了——是因为溢出去了,更大了,也更真实了。虚构是为了走向更深的真实。现实中发生过的,并不一定具有真实性。艺术所要表达的,终究不是特例。我很喜欢《未来简史》里的一个观点,说自我有两种:体验自我、叙述自我。“叙述自我”即是虚构。人每时每刻都在虚构自己,把自己戏剧化。所以一个写作者,要知道虚构很重要,但也不必过多担心自己的虚构能力,反而应该警惕“体验自我”的丧失,一旦丧失,就写不出属于自己的小说。
乡土是捕捉民族情绪的最佳场域
张杰:您一直很看重“情感”在文学中的地位,为什么?
罗伟章:文学从情感萌芽,情感是作家能量的象征,作家最为有效的想象,也是从情感来的。因此,情感是文学的本能,也是一切艺术的本能。曾听人谈到陈丹青,说陈丹青講,一个人听了贝多芬,泪流满面,另一个人听了无动于衷,但过后写了大篇论文,两个人谁更懂贝多芬?陈丹青说,当然是前者。这话我认同。艺术发源于情感,也作用于情感,感受能力是分析和评判能力的前提。所谓小说需要变革,这没错,变革和创新,是艺术的本质性特征,然而,并非所有变革都是朝前走,有些是向后看,向常识的低处看。当下的很多写作,不是从生活中来,是通过阅读,从阅读中找灵感,作家们对经典作品的技巧很精心,却忽略了技巧里埋着的情感,也就是那一粒种子。杰出的作家能够超拔,让你几乎看不到他的起点,就以为技巧是他们的起点。事实上,起点是情感,他们从情感起步,凝聚自己的人生经验、心智密度和思想深度,才走出了高天厚土。
张杰:以您的审美来看,卓越的文学作品应该具备怎样的气质?
罗伟章:好作品得有静气。静气很可贵。作家要懂得凝聚和内敛,让作品自己发光。我曾经读一个很著名的长篇,努力若干次都读不下去。因为写得太燃烧、太外露,静气不足。与之相应,好作品要安稳。“安稳”从何处来?从传统里来。我们之所以能理解安娜·卡列尼娜,理解林黛玉,是能看见她们的来路。再新的东西都有来路。最伟大的作品,其实都是在传统的基础上稍稍拓展。没有谁能进行完全彻底的创新。毕加索是颠覆传统的,具有海洋般磅礴的创新能力,但如果深入了解他的艺术之路,会发现他也就是向前走了一点点。这就牵涉到“卓越”的第三种气质:创新。虽然创新就是一点点,但有没有那一点点,品质判若云泥。需要指出的是,不要轻易把某些解构理解为创新。
张杰:如何写得让人能看见“来路”?
罗伟章:有人曾问泰戈尔:世间最容易的事情是什么?泰戈尔答:指责别人。这个“别人”,也包括历史。指责和否定历史,是很多人乐意做的。这对历史伤害不到什么,伤害的只是自身。比如你是写小说的,就会伤害小说。“祖先”这个概念在作家心里,是血缘,也是绵延不尽的时间。写“来路”,就是写时间。《百年孤独》写的就是时间。往小处说,“来路”是作家的主体性,是作家对书写事物的关怀,比如托尔斯泰哪怕写一只鸟,形成文字之前,他也会把那只鸟放到自己心里去过一遍,这样,那只鸟即使已经死去,也感觉还活着。
张杰:您刚才说情感过于外露、过于炽热的作品,很难读下去,难读的原因,除伤害了您说的“静气”,还有别的吗?
罗伟章:它还会损失作品的宽度。情感本身也是态度,作家的态度太过外露,太过强调,故事和人物的丰富性就被消解了。作家在创作过程中,被激情驱动,允许夸张和失控,修改的时候,就要特别注意打理。每部作品都有若干次创作,每次修改都是一次创作。作家个人的成长,也会在作品中显现,《战争与和平》是有夸张的,到《安娜·卡列尼娜》就没有了。当然后者也有败笔,比如伏伦斯基见了卡列宁后,托尔斯泰用了个类比,说一个人正在下游喝水,结果发现上游有条狗也在喝水。这话刻薄了,失了宽博和对命运充分理解之后的怜悯。
至于失控,也不完全是坏事,有时候还会成为对作家的奖赏,比如我写作通常不熬夜,偶尔熬一下,是失控了,而这种失控证明了欲罢不能。还有另一种失控,本来在作品中是个打酱油的人物,却乱了规矩,悄无声息地坐上了主位,如果他坐上去更像样子,同样是对作家和作品的奖赏。
张杰:《谁在敲门》篇幅很大,气息很绵长,故事似乎一直能流淌下去。许多评论家把它称为“长河小说”,您自己怎么看?
罗伟章:长的不是叙述时间,那不过几十天,而是生活的质感,是细节背后的纵深。在我的观念中,长篇小说的可贵处,是能把握一个族群和一个时代的情绪。无论乡村还是城市,那种情绪都在基因里流淌。在中国,因其个性鲜明的地理特征、源远流长的农耕历史和天道哲学,乡土成为捕捉民族情绪的最佳场域。
张杰:您多次提到您特别喜欢托尔斯泰,在您家书房,坐在电脑前,抬头就能看见墙上的托尔斯泰正凝视着您。为什么这么喜欢他?
罗伟章:托尔斯泰写的是大文学,也就是俯身大地又高居云端的文学。他给我一个很大的启发就是:当个一流的作家,并不构成最高目标。他的目标是探讨人,探讨人怎样变得更完整,更符合人的定义。事实上,如果仅仅把做一流作家当成最高目标,往往抵达不了一流的境界。
张杰:您最喜欢托尔斯泰哪一部作品?
罗伟章:《安娜·卡列尼娜》。一段时间,我睡觉时放在枕边,写作时放在手边。太好了。好到稍不留心就可能把它的好错过。比如安娜与伏伦斯基私奔,生了个女儿,这个女儿是他们爱情的结晶。要是普通作家去写,安娜一定是爱她的,比爱她跟丈夫卡列宁生的儿子还爱。可托尔斯泰的伟大之处在于,他是如此了解人性的深厚和宽广:安娜从女儿身上,看见了自己的罪恶,她即使想爱,也不能爱,也爱不起来。安娜有罪,但并不堕落,因此她不会去爱自己的罪恶。这是情感还是思想?都是。安娜有了这种情感和思想,就预示了她未来的命运。有罪而不堕落,就必然承受道德负担,安娜深感自己承受不起,也试着堕落,结果根本做不到。她后来走上绝路,并不是因为伏伦斯基顺利地回归了社会生活,对她的爱减少了,而她想回归,却不被接纳,便绝望了,其实,她绝望的核心不是来自别人的审判,而是自我审判,这也是安娜这个人物的更深价值。
张杰:现在不少作家也写一些阐释经典的文章,如果让您来写托尔斯泰,分析他的作品到底好在哪,您觉得容易吗?
罗伟章:怎么可能容易。托尔斯泰的力量来自何处,我至今还没有把握。他把某个人物一写就是几十页,然后丢下这个人,去写别的人,又是几十页,可当他把前一个人捡起来,你觉得那个人从来就没有离开过,这就很神奇。托尔斯泰展示了那么多人性的复杂,却几乎没有幽暗,只有敞亮和辽阔,这同样神奇。
张杰:您的审美偏好似乎更倾向于十九世纪文学?
罗伟章:也不能简单地这样讲。但十九世纪的文学的确壮阔。几年前我在北京和批评家李陀先生聊,之后两人还保持了一段时间的通信联系。我曾在给李陀的信中说:“您提出十九世纪文学高于二十世纪,我很赞同。托尔斯泰他们的写作,极大地提高了全世界作家的寫作难度,面对一堵墙,他们不是装着看不见,也不是聪明地绕过去,而是把墙推倒,让这面和那面打通,让光明扑面而来。所以托尔斯泰和那个时代的大师,笔下总带着原野的气息、辽阔的气息、奔流的江河的气息。二十世纪的作家,感觉到这种难,便另辟蹊径。他们的努力没有白费,为文学开辟了更多空间。但整体说来,十九世纪的文学是树干,二十世纪的文学是枝叶。正如您所言,二十世纪文学的最大问题,是不塑造人物,成了观念文学。这样的文学剥离了与日常经验的血肉联系,句句都很光亮,却是玻璃碴似的光亮,冷而碎,真正拿它照耀,是办不到的。我最不喜欢的作家,是那种自己面对一堵墙时无能为力,却去嘲笑把墙推倒的人,说他们手法太笨。”
张杰:在您家的书架上,我看到鲁迅的书有多种版本,您也很喜欢鲁迅?
罗伟章:绝大部分作家,我们看得见他们的成长过程,但是鲁迅的看不见,他像是突然出现,一出手就是顶级的,不仅在中国是顶级的,也直接与那个时代的世界文学接轨。他的思想能力和文学技艺,成就了他个人的伟大,也成就中国现代文学的光荣,并延续到当代。造就这些的,除了鲁迅的天才,更为重要的是他的文学精神。像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雨果、魯迅这样的作家,文学不是文学自身,更不是文学圈子,而是侦察社会、探究人生、重塑灵魂。他们所从事的,是有使命感的文学,是他们文学的终极“去向”。
张杰:您曾说,写作跟阅读是一体的,写作者天然地也是一个阅读者,但并不意味着读得越多,写得就越好。
罗伟章:那是当然的。我们形容古人学富五车,尽管是夸张,算起来也并没有多少书。古人读竹简,读书既是脑力活,也是体力活,秦始皇特别爱读书,经常让李斯给他推荐书,可读一阵就会得上严重的腱鞘炎。多读当然好,但读得多与写得好,没有必然联系。可以肯定的是,我比司马迁读得多,也比曹雪芹读得多,可我为什么没有写出《史记》和《红楼梦》那样浩瀚的作品?这里的浩瀚不是指体量大,而是耐得住时间考验,经得起无尽阐释。我觉得这当中除了写作能力之外,还有些关于阅读的、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作家究竟应该怎样读书?泛读和精读应该是一个怎样的比例?事实证明,精读或许才能称为真正的阅读。
张杰:现在推崇全民阅读,但每年出版物众多,一个人的时间和精力有限,所以如何高效阅读,一定要讲究方法。对此您有何心得和建议?
罗伟章:前面我已谈到一点。可以再说具体些。我们谈论作家的时候,会说“伟大的作家”。其实,谈论读者也有同样的短语:“伟大的读者”。是不是“伟大的读者”,试金石首先是能否识别作品的好,其次,就是能否在阅读中建设自身。后一点非常重要。我觉得,一个读者如果是幸运的,也是有意识和能力的,一生中就会发现几本终身读物,这几本书从年轻读到年老,在不同的生命阶段,会有不同的体会。它们不仅帮你培养判断能力,奠定阅读标准,还像酵母一样,使你的生命发散。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博览群书,你的阅读就有了方向。阅读也有方向,没有方向的阅读,更大程度上只是消遣式的“泛”读。“泛”的特征是多,这与人们贪多的心理刚好契合,因而特别容易沉迷其中。我经常说,我们有能力一个月读十本书,却已经没有能力把一本书读十遍。贪多型阅读,是读进肠胃里,把一本书读十遍,是读进心里,读进脑里。
此外,一个卓越的阅读者,还会具有一种能力:创新性阅读。阅读的创新就是从阅读中发现,从阅读中联想,从阅读中审视。不仅审视社会、审视生活、审视别人,同时也审视自身。学而不思则罔,思什么?就思社会、思生活、思别人、思自身,尤其是思自身。比如我们读历史,遇到一件事,如果是我自己,我会怎么做,再看看别人在怎么做,然后想一想,别人的做法高明在哪里,局限在哪里,难度在哪里,哪些可以原谅,哪些不能原谅。这么一想,我们就把自己置于时间的长河里,就成长了,也壮大了。
小说的最高境界,是本质和清澈
张杰:就算有阅读文学作品能力和兴趣的人,看长篇小说所需要的门槛也高了很多,在各种讯息短平快的今天,读一部长篇作品的必要性是什么?
罗伟章:前几天,中国作家网要我参与一个讨论,讨论的话题是:长篇小说究竟应该长还是短?这当然是在长篇小说的范畴内,究竟是写十多万字的长篇好,还是几十万上百万字的好?很显然,这是个伪话题,不必讨论,但讨论一下也可以,也有些意思。我给他们的题目是:《长篇小说为什么要长》。
如果你注意到我在多个世界读书日提出的阅读建议,其中都有这样一条:一年当中,至少要读一部大部头。也就是说,不仅要读长篇,还要读大部头的长篇小说。大到什么程度?在我心目中,四五十万字可能还不算大。
好小说不以字数论,这是常识,揭示人物命运,也非长篇小说的专利,两千多字的《孔乙己》,命运感已非常强烈。但落实到长篇,还是要大部头才能真正满足对“命运”的期待。太短的长篇,往往流于观念写作,情节设置性过强,追求寓意的企图过重。观念写作在文学史上有着特殊贡献,它专注于局部,并以局部成就深度,但在我看来,宽度大于深度,也难于深度,而且没有足够的宽度,便成就不了应有的深度,深度蕴含于宽度之中,反过来却不一定。
小说的最高境界,是本质和清澈:因为本质,即使清澈得透明,内在也必是宏深包涵。要完成这样的文学课题,没有相应的长度不行。它需要梳理,需要重构。哪怕简单到简陋的生活,也不会是完全清晰的,而任何一种清晰,都是对生活的损失,因此好小说不惧岔道,不是从街的这头直接到那头,从河的上游直接到下游,它要呈现这头到那头的人间烟火,上游到下游的波峰浪谷,包括旁逸的巷道、静谧的河汊、卑小的溪流,其喧闹与孤寂,干涸与丰茂,都被看见,被关注,被书写。作家并没忘记街的那头,也没忘记河的下游,但并不把那头和下游当成目标。生活和生命本身才是目标。生活的细枝末节、汤汤水水,多被欲望、远景以及由此衍生的激情、焦虑等等遮蔽,是随手抛掷、轻易遗失的,长篇小说以其工匠般的耐心,为我们捡拾和擦亮,把我们习以为常又视而不见的生活提取出来,把那些未经命名的经验揭示出来,让我们触摸日常的体温,感知生命的过程,让我们浸泡于生活又认清生活,修剪自身又丰富自身。
这就是读长篇小说的必要性。
在另一个层面,当今是被“快”统治的,未来大概更是,我认为,超级智能机器人的诞生,正是“快”催生出的果子。“快”驱赶着我们,让我们丧失自在和从容,感到不适和恐慌,把我们立体的生命扁平化。这时候,如果艺术只会“适应”,只会为“快”助纣为虐,又怎么可能抚慰心灵、启迪心智?我们还要艺术干什么?任何艺术都是一种抵抗,包括对平庸的抵抗,也包括对速度的抵抗,既如此,写作和阅读长篇小说,就不仅构成审美需求,还是勇气和态度。
张杰:看长篇小说,一是看语言风格,二是看故事里体现的生命况味、对生存困境的思考。从小说作者和读者的角度,分别谈谈您是怎样的感受?
罗伟章:你说得很对。这也是作家们追求的。我去北京领《谁在敲门》的一个奖,同为获奖作家的刘震云说,作家写出一个新小说,不是刚发表刚出版就叫新小说,要对生活有新的理解、新的见地才是新小说。他也是想表达这种意思。语言我已经谈过,作家个体对生活的感受,作家的想象能力,都会影响到语言。时代在变,但变里有常,所谓生命况味,往往表現在“常”里,生存困境,往往表现在“变”里。另一方面,不是“变”才新,“常”里也有新,这需要作家和读者去共同挖掘。
文学大于文学奖
张杰:您得了不少文学奖,也入围了一些文学奖。有些奖,在其他人看来您应该得,实际上并没有得。总之,文学奖这个事情,让人似乎很不淡定,哪怕是书斋里的作家,也需要很大很大的核心定力才更得体面对这个事情。毕竟它跟这个世俗世界、功利关系确实关系挺大。怎么看待文学奖?一个作家该如何锻炼自己拥有不为奖项所动的内核动力?
罗伟章:文学大于文学奖,这就是定力,也是动力。认识到这一点好像很难,其实也不难,想想我们当初为什么写作,问题就变得简单。但要保持定力,确实不容易,因为每个人都在“处境”当中,我们的具体现实是,文学界关心文学奖,远远大于关心文学,整个社会也是以奖去评判一个作家,这就会对作家形成挤压。没有对文学足够的忠诚,尤其是没有足够的文学创作能力,就会对“奖”投降和归顺,并不惜花费文学之外的功夫,乞求加冕。这种没有出息,是环境逼的,但归根结底,还是怪作家自己。对写作者而言,能得奖是好事,是锦上添花,不能得奖,就老老实实坐在书桌前。如果,作家们不为没得某个奖而焦虑,只为写不出好作品焦虑,文学生态就清正了,文学就变得有前途了。
张杰:评论家王春林在评论您的短篇近作《洗澡》的时候,起句就说:“曾经以‘底层叙事闻名于世的作家罗伟章,近些年来的小说创作真正可谓是风生水起……”还有不少文学评论家提到您的时候,往往会说,罗伟章的乡土小说创作,取得了很大成就,产生了很大影响。我们发现,对一个作家,包括对您,往往都会用一个标签化的命名。对此您如何看待?
罗伟章:这件事我在不同场合谈过。从批评家的角度,以标签进行区分和阐释,有其技术上的必要,否则无法言说整体性的文学景观。但从写作者的角度,我向来不太赞同以题材、地域之类去界定小说。小说只有好坏,没有类别。一个成熟的作家,写作时一定不会说,我要写个乡土小说或者都市小说、青春小说之类,更不会说我要写个“底层”“中层”……他就是在写小说。虽然我写的人物多为普通百姓,写的故事多发生于乡土,但那无非是个场域,是一粒沙,要反射太阳。无论外在景观,还是内在精神,如果我不能从个体命运中反映时代形貌,写不出大的格局和超越性的东西,就没有完成写作的任务。
张杰:您平常爱看电影吗?看电影和读小说的差别是什么?
罗伟章:说不上爱看,但是要看。看的量还比较大。我儿子是学电影的,他会给我规定任务。比较起来,电影是入眼,小说是入心;电影是具象的,小说更有想象空间。这当然是一般而论,真正杰出的电影,同样入心,相反,普通的小说既不入眼,更不入心。所以我们谈论艺术的时候,心里就没有普通,就必然装着杰出和伟大,不管哪种形式的艺术品,到了更高层面,就会殊途同归。
张杰:作为四川作家,您如何看待这里的文学土壤?
罗伟章:四川自古不缺文学人才,李白、杜甫、苏东坡、欧阳修、杨升庵等等,这些顶天立地的文学和文化巨匠,都与四川有渊源。现当代的许多文学大家,要么走出四川,要么留守四川,都为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做出了贡献。当然,土壤再肥沃,再丰厚,不是树的种子,就长不成一棵树;另一方面,再肥沃的土壤,如果长时间荒着,就会自动退化为荒漠。所以我们当下作家,更需努力。
张杰:作为《四川文学》主编,您认为文学杂志在当下的意义是什么?
罗伟章:办好一份高质量文学杂志,是体现一个省的文化实力特别是文学实力的重要标志。文学杂志有利于文学新生力量的培养,而且能带来长远的文化效应,就是前面说的,“种子性”效应。纸刊受到挑战,又不是今天的事,是早就如此,但文学刊物依然活着,因为必须活着。别以为读的人少,就没必要存在,要知道,众多优秀作家,都是从文学刊物走出来的。现在无论我们有多少东西可读,如果没有那些优秀作家写出的优秀作品,你能想象吗?
人工智能会进一步教育作家
张杰:当下时代,各种短视频社交软件成为年轻人热衷的对象。面对视频信息的冲击,文字应该如何保持笃定品格,文学应该何去何从?
罗伟章:首先,短视频是个好东西,但如果只知道短视频的好,不知道文字的好,那损失就太大了。上了年纪的也就罢了,要是年轻人也都这样,就令人忧虑。文字有一种功能,是其他任何东西都不能替代的,那就是文字里埋着祖先的信息,埋着一个民族的集体记忆。每种文字自创造以来,都经过了若干次变迁,但变迁本身,就是记忆的一部分。最伟大的写作者是最伟大的回忆者,作家以文字为工具,所以作家是有福的。在短视频时代,作家们用不着慌乱,应该慌乱的是还没有认识到文字之美和文学之深的人。
张杰:对于人工智能对写作者带来的重大冲击,您怎么看?
罗伟章:我们一定不要轻飘飘地轻视它。从历史上我们就可以看到,物质和技术的发展,都对文学带来了巨大的塑造作用。比如从唐朝到宋代,因为物质更丰富,人们开始关注生活,文学体裁上,就由诗过渡到了词。诗是宏大的、庄严的,词是微观的、松弛的。并不是宋代文人心血来潮,把诗丢开,要来写词,不是那样,而是因为时代的促成和塑造。现在人工智能产生,又会带来怎样的变革,真不好说。
但我想说的是,人工智能会进一步教育作家,就是要更加充分地保持主体性,否则很容易被替代。另一方面,作家要充分认识到自己是人,人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会难受、失望,有挫败感,人的肉身性、有限性,又会产生困倦感、疲惫感、对病痛和死亡的焦虑感,以及瞬间的情绪转化。这些在机器面前,全是劣势,但用于写作,又全都成了优势。我的意思是,作为写作者,要特别懂得珍惜自己的局限和脆弱,并且真诚地去直视它。如此,机器就打不败你,因为机器永远产生不了这些属于人的情感和情绪,而这些情感和情绪,正是文学的肌理。
张杰:这两年世界发生了很大变化,不少人有一种很深的断裂感,生活有一种比较大的不确定性。在这种状况下,人们对文学作品治愈力的需求提高了。一个优秀的作家,不大可能对此无动于衷。您是怎样的感受?
罗伟章:是这样的。但我们也发现,当不确定性成为现实,人们便越发死死抓住这种不确定,认为这毕竟是眼前物。即是说,人们对世界的信心在降低,不大相信眼前之外的任何东西。如此,寻求治愈的动力也跟着降低。这就是很多人更喜欢读非虚构作品的原因。但越是这样,越是呼唤有治愈功能的作品。时势造英雄,时势也造作品,呼唤声起,那样的作品就会出现,这是可以肯定的。
选自《绿洲》
- 小品文选刊·印象大同的其它文章
- 从“天地玄黄”到“大小舞台”
- 一根灯芯点亮燎原之火
- 芭蕉猫
- 过往的日子
- 去山里
- 城里的麦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