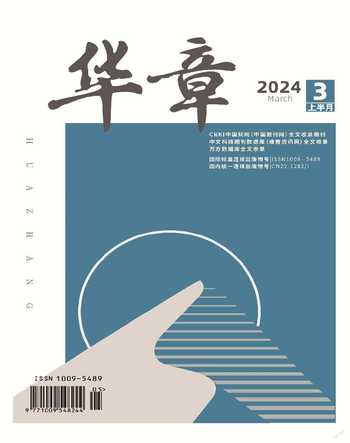网络直播侵权现象的剖析及法律规制
苏晗彤 何晴
[摘 要]各头部主播将网络直播引入网友的视线范围内,也逐渐形成了以网络直播为核心的内容传播模式,不仅延伸出“直播带货”等新兴电子商务模式,还引得UGC、PGC等内容生产者纷纷效仿。但在此过程中,网络直播陆续出现用户隐私数据泄漏、侵犯他人著作权、侵犯他人肖像权等问题,尤其是自媒体主播,其法律意识十分薄弱,又不断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甚至在直播带货的同时,引发虚假宣传及售卖、直播数据造假等现象。要知道,数字技术发展孕育出的网络直播等媒介形态隶属于网络空间,但其和物理空间一样拥有开放性、聚集性和交互性等特点,因此同属于公共交往空间,同样需接受法律的管控。基于此,文章采用文献分析法,深度剖析网络直播的种种侵权现象和法律问题,并进一步提出强化网络直播监管的具体对策,助力构建网络直播合法化的管理体系,推动网络直播平台及经济健康发展。
[关键词]网络直播;虚假售卖;直播带货;直播监管;直播侵权
基于4K/8K高清摄像技术,智能手机的拍照、摄像等功能不断优化升级,为网络直播提供了良好的硬件设施;与此同时,移动互联网资费的降低让网络直播变得“触手可及”:媒体可通过互联网实时直播影视剧或音乐会,UGC可直播游戏、带货等。早在2017年,我国网络直播的用户规模已达4.22亿,年增长率达22.6%,吸引了众多垂直内容的用户群体;同年,网络直播因其打赏功能、付费坑位带动了网络经济的高速增长,逐渐构建起完整的商业化产业链。现如今,5G时代的到来促使网络直播以更快的速度进入移动直播时代,直播产业越发壮大。然而,一些处于“灰色地带”的侵权现象也随之而来,因此,针对网络直播的监管,亟待重视。在构建合法化的管理体系的同时,相关法律法规亦需更新迭代。
一、网络直播行业存在的法律问题
(一)用户的隐私数据泄露
当今移动互联网便捷性强、开放度高,人人都可以直播讲述自己的故事。虽然网络直播少有平台侧视频存档现象,但屏幕前的用户仍可以自发录制、保存,导致主播的个人信息存在被公开泄露的风险,尤其是在面对“人肉搜索”等违法行为时,其敏感个人信息极有可能暴露于众,使其人身和财产安全受到威胁[1]。
此外,人工智能、机器学习等技术改变了直播平台的算法推荐机制,既为用户提供了个性化的直播内容,又被广泛应用在精准投放的效果广告中,导致用户数据泄漏与隐私侵犯时有发生。比如,直播平台未经用户同意,利用网站设置的cookie追蹤用户的网络浏览轨迹,收集其填写的资料等数据[2];或者非法盗用用户IP地址,未经用户同意从其他网站购买用户数据信息,并据此进行网络精准营销,提供地域性、关联性强的直播内容;再者,在没有事先告知征得同意的前提下,网站收集用户信息的范围超过用户协议规定等,以上行为都有侵犯用户隐私之嫌。
(二)容易侵犯他人著作权
网络直播同样存在侵犯知识产权的潜在风险。诸如游戏转播、体育赛事转播、直播中的音乐运用等,不可避免地涉及版权问题[3]。尤其是直播间所使用的音乐往往具有瞬时性特征——主播会根据用户的反馈或是直播间的节奏调整背景音乐,也正是这种瞬时变化的缘故,导致主播无法提前预判进行报备,加大了直播侵权的可能性。
此外,随着AR/VR等技术的发展,智能化“变装”软件应运而生,智能主播逐渐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之中,虽然智能主播的研发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直播内容的生产效率,却也容易被用于“洗稿”,侵犯原作者的著作权;而“洗稿”产业链的出现,延伸出“人工+机器”的洗稿方式,导致抄袭更加难以辨认。而且,直播这类实时发生的场景很难被判定为创意上的抄袭。
(三)容易侵犯他人肖像权
主播法律意识的缺乏导致其出格行为屡见不鲜。部分网络主播为了“蹭热点、蹭热度”,在某一社会热点爆火于网络后常常蜂拥至事件发生地或者热点主角的居住地,如全红婵夺冠事件、十元盒饭姐事件、大衣哥事件、B站二舅事件等。在热点主角的居住地对其亲属进行围堵等扰民行为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在他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将其肖像曝光于直播间,更是直接侵犯了公民的肖像权。无独有偶,曾有某网红在直播平台上直播虐狗,引起网友愤慨,遂有网友发动人肉搜索,在各大社交平台上披露了网红主播未整容时的照片以及相关家庭背景信息,捏造其与他人有不正当关系,侵害了网红主播的肖像权和名誉权。
(四)主播的法律意识薄弱
由于网络直播行业“热钱”流入增大、成为网络主播的门槛偏低等原因,大量人员涌入网络直播行业,部分主播为了吸引观众眼球、加强竞争力,不惜在直播中违反公序良俗,甚至涉嫌违法。比如,某些主播通过线上与同平台主播“约架”、教唆粉丝说脏话等行为展现所谓“男子气概”;还有一些主播有意造成“浴巾滑落”等事件来吸引人气,这些行为产生不良社会影响的同时,也可能间接导致违法行为。
(五)存在虚假宣传及售卖
网络直播的热度催生出了新的销售方式——网红带货,一般由所谓的“头部主播”即拥有百万以上粉丝的主播通过直播的形式进行销售商品。但是,一些主播所推销的商品渠道不明、监管不到位,商品的质量及售后问题屡见不鲜,甚至还存在不少“三无”产品。不仅如此,网络直播交易的消费者维权困难、维权成本高,导致带货商品售假的现象时有发生。
(六)网络直播的数据造假
表面看来,算法技术是通过挖掘用户个人喜好进行个性化推送,将趣缘群体引入直播间,通过技术赋能使电商直播实现全景式传播[4];然而,用户长期被大量同质化商品或同类商品的推送包围,被迫强化对某类产品的认同,其消费行为不可避免地受到技术及资本的隐性控制。与此同时,直播样态愈发丰富,为获取更大利益,直播带货行业的造假之风盛行,围绕“影响力”这一指标的造假俨然形成产业链。部分商家希望通过网红效应提高商品的销售量,因此“刷单”“买粉”“刷评论”等行为甚至成为行业潜规则。而高流量、高销量为电商平台带来了热度和人气,部分平台乐见其成,作为直接监管者疏于管理。
二、强化网络直播监管的具体对策
(一)加速网络直播专项立法
网络直播属于新兴事物,我国对于网络直播的专项法律法规尚不完善,这是导致网络直播乱象的重要原因之一。在没有相关法律条文约束的情况下,主播当然会将利益置于首位,倾向于做出种种越轨行为。尽管立法并非一日之功,但向专项立法过渡的过程中,可以采用2015年頒布实施的《新广告法》及随后的《互联网广告管理暂行办法》进行管理,打击网络直播中的虚假宣传、低俗传播等现象[5]。
此外,人们还应该完善著作权法,保护原创作品。现行的版权保护机制面对新兴的新媒体传播方式已明显滞后,故相关法律法规的出台迫在眉睫。洗稿现象需要由法律勒紧准绳。如杭州快忆科技有限公司“后羿采集器”因提供伪原创服务,抄袭他人文章,被法院判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及合理费用10万元。新的《著作权法》即将施行,侵权法定赔偿额上限将大幅提高至500万元,提高洗稿的法律代价,有利于遏制洗稿行为。
(二)发挥直播用户监督作用
大部分互联网用户对隐私数据不甚重视,应充分利用互联网、大众传媒等方式对用户进行网络信息安全宣传与教育,呼吁用户尽量少留或不留个人信息,留取后应及时处理删除,提高用户谨慎度,主观上加强对信息的防护。同时还应对用户进行普法教育,提升用户媒介素养,避免人肉搜索等违法行为。
为发挥直播用户监督作用,直播平台可以给予网络直播用户监督权——观众在观看直播的过程中,如果发现违法行为,则可以第一时间向平台方反馈,由平台予以制止,降低不良内容大范围传播的可能;此外,平台的上级部门应提供信访通道,如果平台故意纵容不良直播内容,用户也可自行整理相关证据上传至上级监管部门处,由其对违规平台和主播进行处罚[6]。不过,为规避恶意举报现象的发生,对于多次无效举报的用户,平台可禁止其在一段时间举报作为限制,减少对监管部门人力资源的浪费,也能够为广大群众营造一个健康、积极的网络直播氛围。
(三)完善平台监管技术手段
由于人工巡查和监督的人力成本较高,人们也可借助大数据技术研发出一套基本可应用于所有直播间的监管系统。这一系统可对直播间的声音和画面进行抓取监控,在检测到主播发言、行为有违法嫌疑时及时预警反馈到监督者处,再由人工对主播行为进行辨别。研发者可以定期上传违规模型和行为,以此提升系统的精确度。应当承认的是,在现有技术条件下,开发这样一套系统的技术架构和算法成本较高,及时性和准确性也相对较差,无法用于实际工作之中。因此,现阶段需要设计出符合要求的计算模型和架构,在控制成本的同时,增强实时性。
(四)实行实名制并严格审查主播
直播行业应当引入更加严格的主播资质核查制度。比如,主播填写身份证号码进行注册的同时,还需要通过手持身份证、人脸识别等方式进行认证,避免主播借用他人身份证进行违法直播;并且,在直播间出现异常情况时,监督者更容易在第一时间确定责任人、追查个人账户[7]。
同时,应适当加大对违法直播主体或个人的处罚力度。网络直播的利润巨大,现有法律条文的处罚上限对于如今的违法所得来说相对较少,因此很多平台和主播都为了高收益不惜以身试法,即使因违法行为受到处罚,也并不会对其起到威慑作用。对于上述问题,有关部门针对网络直播制定法律法规时应该加大处罚力度;对于监管不到位的直播平台应该一并处罚,要求其上缴违法收益并处罚金,严重者可限制其直播活动的进行甚至吊销营业执照,禁止该平台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一定年限内从事直播行为和有关经营活动。
(五)建立跨平台多级监管
直播平台是监管直播人员的责任方,并且对有关管理部门负责,应该在此基础上建立跨平台、多层级的监管体系。
首先,建立跨平台监督制度需要将曾进行违规操作的主播记录存档,在该主播转移到其他直播平台时,对新平台进行违规提醒,督促其重点监督该主播的直播行为[8]。
其次,实行“直播主题申报”制度,要求主播在直播前进行主题申报,由监督部门进行审核。平台应规范主播所使用的背景音乐和演唱曲目等,避免不良内容和侵权行为的产生;如果直播中出现了申报范围之外的内容,监督者有权直接中断直播。这种“先审后播”的方法可以有效避免违规内容。
最后,引进主播责任金机制,要求直播带货的主播上交占其直播收入一定比例的押金,用于产品质量纠纷的赔付,避免消费者售后无门的情况发生。
(六)建立并强化自律机制
一时的喧哗并不能为平台带来持续健康的发展,加强行业自律才能赢得长远的共同利益。执法者可联合网络直播平台,设定明确的直播内容标准,对在线直播行业的监管做好“违法-违规-低俗”的等级界定,真正做到执法、监管有的放矢[9];此外,“低门槛”并不代表着“低素养”,网络直播平台作为网络直播的内容提供方,有义务对签约主播提供媒体素养培训,执法者亦应督促相关平台开展培训,提高网络主播的法律意识;直播从业者也应该自觉维护行业的健康发展环境,维护行业和企业的声誉,尤其是网络主播应严格规范自身的传播行为,树立坚强、自觉的伦理意识,在自媒体时代“自把关”,扭转社会大众对直播的不良印象。
结束语
网络安全和信息化是一体之两翼、驱动之双轮,人们既要推进网络基础设施建设,鼓励网络技术创新和应用,推动网络直播活动积极开展,又要建立健全网络安全保障体系,用民商法、经济法等法律法规和行业自律,构建网络直播合法化的管理体系,提高网络安全保护能力,做到“双轮驱动、两翼齐飞”。
参考文献
[1]蔡琦琦.用户版权侵权时网络直播平台注意义务的判定规则研究[D].青岛:山东科技大学,2021.
[2]郭倩倩.网络直播平台演唱歌曲的著作权侵权问题研究[D].上海:上海音乐学院,2020.
[3]蒋一可.网络游戏直播著作权问题研究:以主播法律身份与直播行为之合理性为对象[J].法学杂志,2019,40(7):129-140.
[4]浦萌迪.经济法视域下直播带货虚假宣传的法律规制[J].中国价格监管与反垄断,2023(2):36-38.
[5]丁国峰,蒋淼.我国网络直播带货虚假宣传的法律规制:兼评禁止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规定(公开征求意见稿)[J].中国流通经济,2022,36(8):29-39.
[6]史东明.法治化营商环境视域下“直播带货”的经济法规制[J].辽宁公安司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22(2):18-23.
[7]姚锋,唐岳曦.网络游戏直播画面法律保护的前瞻性思考:再析“耀宇诉斗鱼”案[J].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20(3):25-31.
[8]林美辰,姚天冲.网络直播中音乐使用的侵权行为分析:以音著协诉斗鱼直播案为例[J].产业与科技论坛,2020,19(19):36-37.
[9]曹开研.加强监管,优化规则,完善秩序:网络直播营销管理办法(试行)治理亮点探析[J].青年记者,2021(11):83-85.
作者简介:苏晗彤(2002— ),女,汉族,黑龙江哈尔滨人,北京邮电大学,在读本科。
研究方向:网络法,知识产权法。
指导教师:何晴(1986—),女,汉族,江苏无锡人,北京邮电大学,讲师,博士。
研究方向:竞争法,网络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