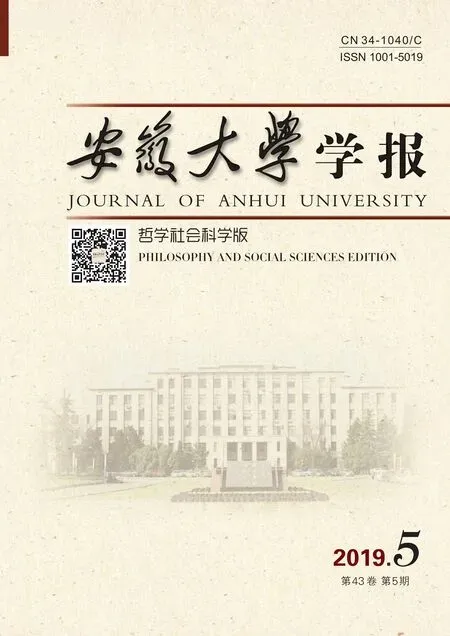论老子的环境伦理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陈发俊
自20世纪后半叶起,生态危机日益严重,人们开始反思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对自然掠夺式的开发方式,世界各国也开始致力于走可持续的绿色发展之路。然而,绿色发展之路到底如何开启,则是近年来全球共同探讨的话题。林·怀特在追溯生态危机的历史根源时说,如果人类要想改变对环境的做法,必须改变关于环境的观念(1)Lynn White, The Historical Roots of Our Ecological Crisis, Science, vol. 155, no. 3767(1967), pp. 1203-1207.。也就是说,要转变传统的发展模式就必须从改变人们的价值观与人们对于自然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态度开始。在关于如何对待自然方面,我国先秦时期道家创始人老子即提出独特而有价值的思想,其思想在今天仍有强大的生命力。
学术界已有学者从老子生态哲学或自然哲学视角对老子的生态伦理思想进行探析。本文拟在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独辟蹊径,运用现代西方环境伦理学中的生态中心主义环境伦理观、内在价值论等理论框架与分析视角,从环境伦理思想的哲学基础、价值论基础和环境伦理原则三个方面系统论述老子的环境伦理观,并探讨老子生态伦理思想对当下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建设生态文明的重要价值。
一、老子环境伦理思想的哲学基础
现代生态中心主义伦理体系是基于对人类中心主义伦理观的批判而逐渐建构起来的。在西方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伦理观看来,伦理正当性在于其诉诸理性主义的价值赋予性,而且只有人类才拥有理性(2)J. Baird Callicott, Environmental Ethics: An Overview, (2014-03-26)[2018- 01-18], http://fore.yale.edu/disciplines/ethics.。因此,人类中心主义伦理观认为,伦理规范只能是在人与人这样的同类之间才会有的正当行为规范。换句话说,只有在理性意义上平等的人类主体之间才存在伦理道德关系,也即只有人才具有道德重要性,只有人类才有终极的道德地位(3)Kenneth E. Goodpaster, On Being Morally Considerable, Journal of Philosophy, vol. 75, no. 6 (1978), pp. 308-325.。然而,这一思想却遭到了非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批判者认为,事实上,人在智力层面并非是均等的。这种智力不均等性表明,以理性为伦理施受对象的区分标准显然是不合适的。若将理性等级不同的人都包括在内,则伦理关系的主体便自然要扩展至有感知能力的一切实体。据此,动物便进入了伦理关照范围,这样,人对动物也应该讲伦理道德,伦理规范也适用于调节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在与动物发生关系时,人也必须遵守相应的伦理规范。如彼得·辛格(Peter Singer)认为,伦理关照的对象标准是具备感知快乐和痛苦能力的实体(4)Peter Singer, Animal Liberation: The Definitive Classic of the Animal Movement, New York: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2009, p. 7.。而汤姆·雷根(Tom Regan)则将伦理立场扩展至所有生命主体(5)Tom Regan, The Case for Animal Rights, Berkele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3, p.243.。生态伦理范畴便从人类中心主义转向动物中心主义。同样,与人的理性存在多层级的不均衡性一样,动物的感知能力也存在从高到低的层级序列,最低层级的动物感知能力接近于植物,这样,植物也理应进入伦理关照范围。于是,生物中心主义伦理观诞生了。生物中心主义伦理观认为,至少自然物都应该享有与人类类似的道德地位。如深层生态学运动之父阿伦·奈斯(Arne Naess)提出,生命中心主义伦理学的基本原则是每个生物都有生存和繁殖的权利(6)Cf. Roger Paden, Moral Metaphysics, Moral Revolutions, and Environmental Ethics, Agriculture and Human Values, vol. 7, no. 3-4 (1990), pp. 70-78.。利奥波德坚持的基本原则是:“当一个事物有利于保护生物共同体的和谐、稳定和美丽的时候,它就是正确的,当它走向反面时,它就是错误的。”(7)奥尔多·利奥波德:《沙乡年鉴》,侯文惠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13页。依此类推,伦理关照范围不断扩展,最终囊括整个生物圈以及全部的有机物乃至空气、水、土壤等生态环境中的所有实体,也即整个生态圈。生态中心主义伦理观逐渐取代了人类中心主义伦理观。由此可见,西方环境伦理的哲学基础就是万物同等性。不过,现代西方环境伦理的哲学基础产生于逆向推理,从人类理性的不均等性开始反推,最终推衍到生态自然中最普通最一般的实存,并得出结论:万物平等,万物都应该享有道德地位,并获得人类的伦理关照。
与现代环境伦理思想的诞生过程不同,老子一开始就提出宇宙万物同源、“物我平等”的观点。老子认为,万物是由道衍生而出的平等的实体。这一观点超越了西方人类中心主义(8)Karyn Lai, Classic China, ed. by Dale Jamieson, A Companion to Environmental Philosophy, Massachusetts: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2001, pp. 21-36.,奠定了老子环境伦理思想的哲学基础。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子·四十二章》)(9)本文所引《老子》版本为陈鼓应《老子今注今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 “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老子·四十章》)。虽然迄今为止学术界对于“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具体含义仍存在争议,尤其是对于“二”和“三”的意义诠释有不同理解,但却一致认同“道”是宇宙万物的本原,宇宙万物皆产生于道这一观点。而由“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可知,宇宙万物不仅同源于道,而且还同复归于道。在道的统摄下,宇宙万物融为一体,人只是永恒而持久的宇宙整体的一分子而已。在老子看来,宇宙这个现实整体是由各种形式的存在不停地相互作用而形成,其中的各种存在相互关联,“天人一体”。
那么,由道所派生出的宇宙万物之间有无等级差别呢?在老子看来,宇宙万物之间是物我平等的,没有等级差别。老子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老子·五章》) 王弼解之曰:“天地任自然,无为无造,万物自相治理”(10)《老子道德经注》,王弼注,楼宇烈校释,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13页。。老子之所以认为天地平等地对待万物,没有偏私,是因为他认为万物同源于道,均为道之子。在道的统摄下,人、天地、自然万物之间无尊卑贵贱等级之分别,亦无相互干预之权利。南怀瑾解释说:“假如从天地的立场,视万物与人类平等,都是自然的,偶然的,暂时存在,终归还灭的‘刍狗’而已。生而称‘有’,灭而称‘无’,平等齐观,何尝有分别,有偏爱呢?”(11)南怀瑾:《南怀瑾选集》第二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98页。也就是说,天地万物之间相互平等,物我平等,无分贵贱。既然自然界万物是平等的,没有等级高低之分,那么,自然生态也应一视同仁,人与人之间、人与物之间、人与自然生态之间都没有等级层次高低贵贱之分,人应该如同对待人类同伴一样平等对待自然万物。物种之间的平等是环境伦理存在的前提基础,这就意味着人与不同物种间都存在伦理关系。那么,适用于人与人之间的行为规范和道德伦理法则也同样适用于人与物和人与自然生态之间。于是,普惠自然的环境伦理便理所当然存在着。“圣人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圣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老子·二十七章》)。在圣人眼里,物与人齐同,不分贵贱等级,物和人一样都是圣人应该关照和救助的,没有被忽略或放弃的对象。善不仅要施予人,而且要施予与人平等的自然万物。老子告诉我们,“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老子·七十九章》),大自然对待所有事物都一视同仁,没有偏倚,我们人类也应该尊重自然规律,尊重自然万物,恪守环境伦理。这也是生态中心主义伦理学所强调的,我们不仅对人负有道德义务,而且对与人类平等的自然万物也同样负有道德义务。
在逻辑体系上,老子环境伦理思想的宇宙论哲学包含了三个问题组成:宇宙的本原是什么?世界万物如何生成?世界万物相互间是什么关系?针对这三个问题,不同的世界观理论给出了不同的答案。西方盛行的基督教宇宙观认为,上帝创造了世界万物与人类,并赋予人类管理、支配和控制自然的特权,这一观点直接为人类中心主义世界观和伦理观的形成奠定了理论依据,也是当代生态危机形成的历史根源之一。然而,在老子那里,宇宙的本原是道,道借助阴阳的作用形成了万物,万物同为道之子,万物之间相互平等,没有等级高低贵贱之别,万物平等,物我平等。简而言之,万物同源,与道为一;道法自然,天人一体;“万物为刍狗”,物我平等,这构成了老子环境伦理思想的哲学基础。
二、老子环境伦理思想的价值论基础
价值是现代环境伦理学的核心概念。通常价值被区分为内在价值、工具价值、原本价值和关系价值四种价值形式(12)Robert Audi, The Cambridge Dictionary of Philosophy, 2nd 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948.。而西方环境伦理学的价值论基础是事物的工具价值与内在价值的区分。工具价值是事物成为实现他者目的的手段的价值。而内在价值也叫非工具价值,是事物以自身为目的的价值,与其是否有利于充当实现他者目的的手段无关。环境伦理学中最早将价值区分为工具价值和内在价值的是罗尔斯顿(Holmes Rolston III),他指出:“价值有两种,内在价值和工具价值。内在价值是主体心理上的兴趣满足,没有外在的贡献指标,快乐本身就是善。工具价值有助于进一步促进兴趣满足。” 在罗尔斯顿看来,“动物、植物、物种和生态系统事实上都具备内在价值”(13)Holmes Rolston III, Environmental Ethics: Duties to and Values in the Natural World,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88, p. 110.,它们内在价值的存在不取决于人类。开明的人类中心主义者认为,人类之所以要保护环境,是因为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资源,如果这些自然资源枯竭,会直接影响人类的可持续发展。这种观点仍然是看重生态环境的工具价值,而非从环境的内在价值考虑。而生态中心主义的伦理观则认为,自然生态中的事物都有其自身存在的权利和内在需要,人类无权干预和改变它们的存在方式,更无理由剥夺它们存在的权力。内在价值赋予实体道德地位,我们在规定相关道德义务时必须要考虑这样的实体,也就是说,对待自然生态中的实体要遵循伦理规范。
关于事物的价值问题,老子提出“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老子·十一章》)的观点。“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从字面上理解,“有”给人便利,“无”发挥了作用。这里的“有”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指有形的存在,或者说人能通过感官感知到的存在;另一层意思是指能够明显认知到的显性功用。“有之以为利”意为能够明显感知到的有形存在或具有显性功用的存在对人是有利的。同样,“无之以为用”之“无”也有两层意思:一是指某种无形的存在;二是指某种存在没有让人感知到有显性功用。在《老子》十一章,“无”指的是车轮、容器和房屋的“中空”。这些“中空”看上去什么也没有,似乎没有作用,然而,正是它们的存在,正是它们看上去什么显性功用也没有,反而使它们发挥了大的作用,它们最终成就了车辆、容器和房屋之所是。推而广之,显现出明显对他者有用的存在为他者实现某种目的提供了便利,发挥了功用。但是,那些看不出对他者有用的存在其实也在发挥作用,它的存在本身就在发挥作用。就价值视角而言,“有之以为利”的“有”可以看作是现象界的有形价值——工具价值,而“无之以为用”之“无”并不是真的无,而只是事物自身存在的一种显现方式,且是一种必然的显现方式。事物的自身存在本身就是一种价值,相对于工具价值而言,事物的自身存在是一种内在价值。无论是工具价值,还是内在价值都是现象界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缺一不可,否则,生态世界就会残缺不全,最终失去平衡。正如老子所言,“有无相生”(《老子·二章》)。在自然界中,“有”可以理解为人类已经认识到的大量物种、物质及其作用,“无”则可理解为那些不为人知的物种、物质或它们的作用。自然生态系统之所以生生不息,除了有赖于大量人类所了解的物种和物质的功用,也离不开那些无数的貌似为“无”的事物及其作用。事实上,自然生态圈的持续存在与演化得益于生态系统中各种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依赖的要素时刻不停地进行着的质量、能量和信息的流动、交换与循环,以及由此产生的自然生态系统的内在价值(14)邬天启:《生态文明的一般价值论基础》,《自然辩证法研究》2014年第7期。。而且,这些内在价值产生的同时也伴随着生物群落中不计其数的物种的灭绝,这些可能被人类视为“无”的物种灭绝其实是自然生态的能量与物质循环过程所不可或缺的环节,是产生自然生态内在价值所必然要付出的代价。由此可见,自然生态圈是由具有工具价值的事物和只有内在价值的事物构成的有机系统,内在价值与工具价值对于维护生态系统的稳定同等重要,二者都是环境伦理考量的范畴。
老子的“无之以为用”理论还蕴含朦胧的价值客观性思想。“无之以为用”可以理解为:主观体验不到的东西或主观感受不到其功能的东西,实际上仍然在发挥作用,也就是说,事物的价值存在与否是不以人的主观体验为判断标准的,无论主观能否感受到,它都是客观存在的,这就是价值的客观性与绝对性。既然价值存在具有客观性,那么,这就表明客观存在的事物都是有价值的,只不过价值大小或体现方式不同而已,人的主观体验只是价值评判的一种方式,而不是判决性因素。以此类推,无论有无人类存在,地球本身都是有价值的,地球上的所有存在物也都是有价值的。而且,这些价值在人类出现以前就存在,而不是因为人类的出现,不是因为人类需要对地球上的资源加以利用,地球才有了价值。正如罗尔斯顿所言:“在自然的演化过程中,人类的出现也许是一个最有价值的事件,但如果以为是我们的出现才使得其他事物变得有价值,那就未免对生态学太无知且太狭隘了。”(15)霍尔姆斯·罗尔斯顿:《环境伦理学——大自然的价值以及人对大自然的义务》,杨通进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5页。尽管地球能满足人的各种偏好,为人提供有价值的体验,但是,这并不代表离开人类,地球及地球上的生态环境就没有价值,实际上,在人类出现之前,地球就一直是一个不断演化的生态系统,生态规律和生态价值也不是只存在于人头脑中的东西,而是客观性与主观性相统一的产物,无论人类是否感知到,它们都在发挥作用。有鉴于此,人类不能以工具价值为判断标准对自然万物妄加作为,胡乱取舍或改造。
实际上,“无之以为用”是老子道本体论在价值论上的体现。老子认为道是万物的本原,但道是无名、无形、无象、无声的。老子认为,“道常无名”(《老子·三十二章》),“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搏之不得”(《老子·十四章》)。从人的主观体验来看,道完全是一种“无”的状态。然而,这种呈现“无”的状态的道却无处不在,价值非凡,“天下莫能臣”(《老子·三十二章》),统摄万物并“衣养万物”(《老子·三十四章》)。道的作用既表现为显性的“有”,也体现为隐性的“无”,“有”“无”共存才是道的自然状态。推而广之,由道产生的宇宙或生态圈也是如此,当代科学已经揭示出宇宙是由明物质和暗物质共同组成,而且暗物质比重占绝大部分,暗物质的作用被称为暗能量。虽然人类目前还无法精确认知这些暗物质,但它们对于维系宇宙存在的价值是无可怀疑的。目前的观测表明在宇宙总能量构成中,常规物质只占4.9%,其余皆为暗物质(占26.8%)和暗能量(占68.3%)(16)P. A. Ade, et al., Planck 2015 results-XIII. Cosmological parameters, Astronomy & Astrophysics, vol. 594, no. 2(2015), pp. 1-67.。同样,生态圈也存在大量已知或未知的生物或物质,它们对于生态圈的维系做出了不少贡献。正如现代生态学第二法则所描述的:自然界中无所谓“废物”存在(17)巴里·康芒纳:《封闭的循环:自然、人和技术》,侯文蕙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30页。。也就是说,无论人类可感知的还是感知不到的客观存在,都有其应有的内在价值。
总之,在老子看来,宇宙万物的价值既有显性的,也有隐性的;既有主观体验性,也有客观存在性。从价值类型来看,事物的工具价值和内在价值同样重要,不能厚此薄彼。人们既要重视事物的工具价值,也要重视其内在价值。
三、老子提倡的环境伦理原则
正是基于事物的内在价值这一前提,现代环境伦理学形成了结果论和道义论两种学说(18)Robert Elliot, Normative Ethics, eds. by Dale Jamieson, A Companion to Environmental Philosophy, Massachusetts: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2001, pp. 177-191.。结果论伦理观通常根据行为的后果来考查人类行为的正当性,其中又可分为最大化结果论、改进结果论和维护结果论。最大化结果论认为,如果一种行为将事物预期的内在价值最大化,那么,它就是义务的。也只有那些将预期的内在价值最大化的行为才是被允许的,行为的义务性和可允许性本质上是一致的。功利主义就是一种最大化结果论,它只视快乐或幸福为内在价值。改进结果论则不要求内在价值效用最大化,而只要求对生态状况有一定程度的改进即可。维护结果论则以事物内在价值的自然状态相对完好为义务原则,不要求增加自然内在价值的功用,更不要求将其最大化。概而言之,结果论的核心思想就是,如果野生自然没有被保护好,其内在价值的作用因而没有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那么,人们就有义务去保护它。如果修复一个自然区域,能让它的内在价值最大化,那么就有义务去修复它。可见,自然价值通常被结果论者视为唯一的或最重要的内在价值。而当代环境伦理学中的道义论则起源于康德思想——人是有理性和自由意志的伦理人,因此,人负有伦理责任。道义论的核心概念是责任和权利。如果某行为所遵循的原则是合乎理性的,那么,该行为就是合伦理的,就具有合理性,是正当的。与结果论相比,对于行为是否是义务的以及是否是可允许的,道义论的判断原则除了价值以外,还有许多其他因素,其中价值评估不具备优先性。只要自然物有内在价值,人类就有义务不去毁坏它,但不计算价值损失量。判断行为是否错误与行为是否毁坏某物的内在价值无关,其主要强调的是权利不受侵犯,包括动物权利、植物权利、其他物种权利和生态系统的权利。
与结果论、道义论不同,老子主张的生态环境伦理原则是“自然无为”。“自然无为”不是消极不作为,而是顺应天性而为,戒绝逆天性的行为。美国物理学家卡普拉(Fritjof Capra)认为,道家把人类活动区分为两种类型:与自然相和谐的活动和反自然的活动,“无为”是戒绝反自然的活动(19)董光璧:《当代新道家》,北京:华夏出版社,1991年,第72页。。刘笑敢则认为,“无为”在积极意义上隐含着一种特殊的行为方式和风格——“几乎没有显现出来的或没被感觉到的行为”,或简单称为“自然行为”,老子“无为”学说提倡自然的、渐进的、适度的行为方式,反对集中的、强制性的、剧烈的大规模运动(20)Liu Xiaogan, Non-Action and the Environment Today: A Conceptual and Applied Study of Laozi’s Philosophy, eds. by N. Girardot, James Miller and Liu Xiaogan, Daoism and Ecology: Ways within a Cosmic Landscape, Harvar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 305-314.。“老子认为任何事物都应该顺任它自身的情状去发展,不必参与外界的意志去制约它。”(21)陈鼓应:《老子今注今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48页。因此,人类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时应遵循自然之道,因任自然,而不是强作妄为,妄加干预。老子还把“自然无为”称为宇宙中最高深的道德。在今天看来,老子的自然无为思想蕴含着对自然物权利的尊重,也有对其内在价值的认可。也就是说,老子认为,自然物有自我生长的权利,其能够自我展现,自在自为,人类不要乱加干预,也无权干预。人类若无为了,万物就会自化、自宾、自均、自定、自正,就会依靠自己的力量自发地达到生存和发展的最佳状态(22)陈鼓应、白溪:《老子“生态智慧”的现代意义》,《光明日报》2002年5月14日第15版。。而这种最佳状态也正是万物的本然状态,“生命的本然状态、理想状态就是生命的最佳状态”(23)陆建华:《生命的存在状态——以〈老子〉第三十九章、五十一章为中心》,《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因此,尊重自然物的自为权,让其享有自我展现的权利,充分实现自身内在价值,就是宇宙中最大的原则,也是人类最高深的道德。老子对此多有论述,在《老子》第二章,老子说:“圣人处无为之事”,“万物作而不为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圣人是遵循自然规律的,不会强作妄为,而是让天地间万物凭它们自己的内在生命力欣然兴作,自我展现。在《老子》第五十一章,老子又说:“道生之,德蓄之,物形之,势成之”。老子认为,万物之所以多姿多彩,是因为“各复归其根”(《老子·十六章》),每个生命都是依赖它自己的根本而活,人类没有权利去干预。自然物所呈现的丰富多样的形态则源于其自身的内在因素,这些内在因素促使自然物在适宜的气候和地理环境下生长完备。同时,老子也告诉人们,道赋予自然物生命,在它们的生命历程中,道起着最初的决定作用。万物遵循道的内在规定而生长,在其生长过程中人类应恪守不妄加干预的高深大德,既要履行适度蓄养的责任,又不能强作妄为,而是为其成就生命旅程保驾护航。道生万物,却“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老子·五十一章》)。“玄德”是“深层道德”,是真正的慈爱(24)谢阳举:《老庄道家与环境哲学的会通》,《北京日报》2015年2月2日第20版。,也是环境伦理的基础。道赋予万物生命,却没有去主宰万物,更没有对其发展进程和方向妄加干预。人也应该如此,效法道,“尊道贵德”,顺应自然,始终保持一种“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焉”(《老子·六十四章》)的心态,才能让自然休养生息。“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焉”,意即必须把自然作为万物本性的原始状态,即本性自然,对待本性自然的行为方式是辅助,而不是凭借人类的主观臆想来塑造万物,否则,势必会伤害万物本性的发展(25)许建良:《道家“无用之用”的思想及其生态伦理价值》,《哲学研究》2007年第11期。。如果人类对宇宙万物“莫之命而常自然”,那么,生态就能够保持平衡。如果不遵循老子的“自然无为”原则,而是肆意掠夺自然,干预自然,改造自然,并且试图征服自然,就会引发愈益严重的生态危机。正所谓“为者败之,执者失之”(《老子·六十四章》)。
老子认为人类还应该效仿自然之道,不能伤害自然万物,以“不害”万物为人类行为之正当性准则。他说:“天之道,利而不害”(《老子·八十一章》)。自然之道就是为万物生存、成长提供有利条件,但从不损害万物。“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老子·二十五章》)。既然天之道是有利万物而不损害万物,那么,人类也应该尊道贵德,为万物存在提供便利与保护,不能因一己之私损害它们,也不能将其据为己有或变成人类的私有财产,更不能任意干预其存在状态或存在方式。而且,不害万物也是人类的义务和责任。因此,人不损害自然万物并保护万物,这也仅仅是履行作为人应有的道德义务而已,不值得自我标榜,不该为此争功,更不能据此而争夺对它们的优先控制权。此即老子所言:“圣人之道,为而不争”(《老子·八十一章》)。
老子提倡对天地万物取自然无为之态度,不伤害万物,自然也反对人类使用违背自然本性、伤害自然物的技术或技巧。无论是传统技艺还是现代技术,本质上都是对自然力或自然物质的改变(26)Federick Ferre,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Georgia: 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1995, p. 19.。也就是说,使用技术(艺)就是对自然的干预,会给自然物带来不同程度的伤害,这显然与老子自然无为的理念是相悖的。因此,老子有言:“使有什伯人之器而不用”“使民复结绳而用之”(《老子·八十章》)。换言之,即使社会文明高度发达,人们也仍然要恪守素朴、返璞为真、“绝礼弃智,绝巧弃利”以及“见素抱朴,少私寡欲”(《老子·十九章》)等原则,遵循社会自然发展的内部动力需求,切不可肆意发挥聪明才智,对自然强加以外力干预(27)刘笑敢:《老子之自然与无为概念新诠》,《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6期。。
在老子看来,在自然生命的绽放过程中,内在的道会发挥微妙的调节作用,使其向着固有的方向发展,道的力量既不会让生命过程半途而废,也不会使其混沌无序。人若对事物的发展妄加干预,即使出于善意,也难保证其行为不会引发意料之外的负面后果。这样,“人为”不但不是救赎,反而可能扰乱自然事物内在固有的可靠的发展趋势。因此,我们的道德责任就是克制自己,不要对自然妄加干预(28)Russell Kirkland, “Responsible Non-Action” in a Natural World: Perspectives from the Neiye, Zhuangzi, and Daode jing, eds. by N. Girardot, James Miller and Liu Xiaogan, Daoism and Ecology: Ways within a Cosmic Landscape, pp. 283-304.。正因如此,老子说:“为者败之,执者失之。是以圣人无为故无败;无执故无失。……圣人欲不欲,不贵难得之货;学不学,复众人之所过,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老子·六十四章》)人类只有秉持无为的原则,才既能防止负面影响的产生,也才可以支持和帮助万事万物自然发展。而万事万物的自然发展本身就是宇宙万物和谐状态的体现。在此意义上理解老子的自然无为思想,也就意味着在面对自然时需遵循动力的内在性与发展的平稳性,只有这样的“自然无为”才能保持生态持久平衡,使得青山常在,绿水长流。
四、老子环境伦理思想的当代价值
面对当下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人们四处寻求化解良方。技术论者认为,之所以有今天的困境,是因为我们的科技还不够发达,解铃还须系铃人,科技发展带来的弊端应该由科技的进一步发展来化解,只有技术才能拯救人类与地球的未来。美国技术哲学家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则认为,技术解决不了自身引发的问题。然而,我们需要反思的是,人类如今面临的困境真的是技术带来的恶果吗?技术引发生态环境问题可能只是表面现象而已,其深层原因并非在于技术,而是在于人的认知与观念。因此,要克服技术应用之弊端,化解其引发的生态危机,实现绿色发展,需从改变人的观念入手。只有改变人的自然观念、价值观念以及人对宇宙存在与生命意义的认知,才有可能实现发展模式的转型。而老子环境伦理思想与当代绿色文明建设的方向相契合,其蕴含的生态智慧可为促进人们的观念转变提供重要思想资源。
首先,老子描绘的理想的自然生态图景可以帮助人们清理西方近代以来机械自然观的错误,推动人们树立系统自然观,培养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意识。17至18世纪的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最终在西方世界塑造了机械化的自然图景,自然界被看作只受数量关系和机械原理支配的客体,事物间的有机联系被忽视,自然被置于人类的对立面,成为人类征服与改造的对象,地球也被视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库和永远填不满的垃圾场。西方近代形成的这种机械自然观最终导致生态失衡,引发了今天的生态危机。相比而言,老子描绘的理想生态图景是道统摄下的天清、地宁、神灵、谷盈、物生。道赋予宇宙万物生机,“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老子·三十九章》),此处的“一”是指道,是道让天得以清明,地得以安宁,神得以灵妙,河谷得以充盈,万物得以生长。反之,“天无以清,将恐裂;地无以宁,将恐废;神无以灵,将恐歇;谷无以盈,将恐竭;万物无以生,将恐灭”(《老子·三十九章》)。离开道,则天失其清而崩裂,地失其宁而震溃,神失其灵而消失,谷失其盈而枯竭,万物不得生长以致灭绝,最终的结果是天、地、神、谷、万物纷纷毁灭,生态系统崩溃,人类也无处存身。因此,人类必须善待自然,向自然界索取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源时应该铭记老子的“自然无为”“尊道贵德”之伦理原则与规范,切不可肆意掠夺,浪费资源,污染环境,破坏生态,而应该营造天清、地宁、神灵、谷盈、物生的充满生机的理想的自然生态圈。
其次,老子提出的“无用之用”的价值思想有助于人们突破只有工具价值才是价值的陈旧观念,从而帮助人们形成正确的生态价值观。天地间万事万物都有其价值,有的有工具价值,有的有内在价值,有的既有工具价值也有内在价值。看上去似乎只有工具价值是有用的,能为他者实现目的提供手段。其实不然,工具价值和内在价值是事物不可分割的两种属性,各有存在的意义,并且共同构成了事物的价值整体,如老子说:“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然而,绝大多数人会以工具价值来衡量一切,尤其是以人类中心主义的工具价值来衡量自然物,忽视自然物的内在价值,或者不承认自然物有内在价值,导致对自然物的无视、破坏,甚至毁灭。但生态系统中所有要素都是具有内在价值的。此外,系统的形成与稳定依靠所有组成要素的有机构成与支撑,系统的整体性和有机关联性表明,系统中任何要素的毁坏、坍塌或缺失,都会导致系统的解体。生态系统同样如此,生态系统中任何要素都是不可或缺的,否则,生态系统会失衡、坍塌乃至最终毁灭。价值观念影响和决定着人的行为,只有纠正人们长期以来错误的价值观,正视和尊重自然物的内在价值,平等对待生态系统中的所有要素,才能维护生态平衡,实现绿色发展。
最后,老子提倡的万物共生共存的宇宙观与生命观有助于改变人们对宇宙存在和生命意义的人类中心主义认知模式,帮助人们形成善待自然、尊重他者生命的思想意识。宇宙实存是多元化的,是多样化存在的共生共存。老子告诉我们,这些共生共存的多元化存在都源自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子·四十二章》)。宇宙中的多元化存在处于相互平等的关系之中,不存在谁凌驾于谁之上,万物共生共存、相辅相成。同样,宇宙中的生命也是相互平等的,它们之间没有贵贱等级之分,一种生命不能主宰或改造另一种生命,老子是极力反对一种生命对另一种生命的改造的(29)陆建华:《建立新道家之尝试——从老子出发》,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68~72页。。因为生命是事物的内在价值,生命的意义不在于他者,不是充当他者的工具或成为他者实现自身目的的手段,而是在于生命的自我绽放与自我展开,这种绽放与展开也就是对宇宙实存多元化的呈现与诠释。生命是为其自身而期求的目的,生命过程不是为他物而展开,而是只为自我绽放的需求展开。这一为自身目的的善,是最高的善(30)苗力田:《亚里士多德全集》第八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4页。,理应得到人类的理解与尊重。即使人类为自然物生命的绽放给予了帮助,也不可主宰、改变甚至侵害自然物的存在。“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老子·五十一章》)才是老子心目中最高深的宇宙道德,也是人类要时刻谨记的伦理规则。
总而言之,在老子看来,万物由道产生,为道之子,万物之间相互平等,物我亦相互平等,因此,人应该平等对待自然万物。大道无形,“有”“无”共存是道的自然状态,这在价值论上体现为“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宇宙万物本身或其价值大多数情况下是以人类无法感知的状态存在,道对万物的发展方向和进程起着微妙的作用,让其自然发展而不妄加干预,从而使宇宙万物保持和谐状态。因此,老子认为,人应该效法自然之道,奉行自然无为的行为原则,这样才能不伤害万物,使自然万物和谐共存。因此,老子的环境伦理思想在当下不失为一盏明灯,为迷失于重重生态危机中的人们提供一个航向。正如董光璧先生所言:“在适当的条件下,长期被忽视的古代智慧也可以成为创造的源泉。……我确信重新发现道家具有地球船改变航向的历史意义,黄土文明与海洋文明的融合,有如黄颜色和蓝颜色调和出绿色,将产生人与自然和谐的新的绿色文明。”(31)董光璧:《当代新道家》,北京:华夏出版社,1991年,第4页。这段话同样适合当前生态文明建设语境下对老子环境伦理思想的诠释,老子的环境伦理思想有望为构建新的绿色发展框架指引方向。如果我们能够深刻理解和把握老子环境伦理思想的精髓,并将其运用于当下的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则一定有助于自然环境的长期保护和生态恶化问题的根本解决。不仅如此,20世纪以来正在急速复活、变异和生长的中国古代道家思想都有可能成为救治现代文明异化的要素(32)谢阳举:《老庄道家与环境哲学的会通》,《北京日报》2015年2月2日第20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