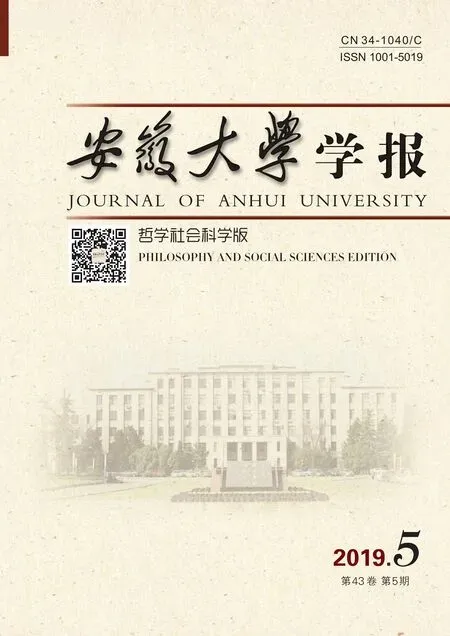论沃拉斯托斯的苏格拉底“德性主权”学说
黄俊松
沃拉斯托斯(Gregory Vlastos)是20世纪后半叶苏格拉底研究界(1)这里的苏格拉底研究界当然也是指柏拉图研究界,但考虑到沃拉斯托斯强调苏格拉底与柏拉图的分离,认为柏拉图的“早期对话”反映的是历史上实际的苏格拉底,而“中期对话”则体现了柏拉图本人的思想,因此,本文为了论述方便,就将对柏拉图“早期对话”的研究称为苏格拉底研究。关于沃拉斯托斯的对话分期观点,参见Gregory Vlastos, Socrates: Ironist and Moral Philosoph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46-49。最有影响力的人物,甚至被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苏格拉底学者”(2)Terry Penner, Socrates and the Early Dialogues,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Plato, ed. by Richard Krau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 147n1.。他在这一领域最突出的贡献在于:一是使“苏格拉底问题”再次成为研究界关注的焦点,二是在将苏格拉底与柏拉图相分离的基础上,他对苏格拉底独特的哲学方法和道德哲学进行了一系列具有独创性的研究。如今,随着学界对苏格拉底研究的深入,沃拉斯托斯的许多观点——比如论苏格拉底的无知、论德性的统一性问题等等都被其他学者所超越(3)Cf. William Prior, General Introduction, Socrates: Critical Assessments, vol. I, ed. by William Prior,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6, p. xiv.,而且,随着20世纪90年代以来柏拉图学界研究范式的转向(4)Cf. New Perspectives on Plato, Modern and Ancient, ed. by Julia Annas and Christopher Row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latonic Writings, Platonic Readings, ed. by Charles L. Griswold Jr., Pennsylvania: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2.,他所构建的柏拉图对话的发展图式以及分析对话的方法也受到了质疑。但是,在苏格拉底论德性与幸福的关系问题上,他所提出的“德性主权”(the Sovereignty of Virtue)学说依然受到众多学者的支持,其非常有助于人们理解苏格拉底在古代伦理思想史上的奠基性地位。因此,笔者希望探讨他所提出的这一学说的开创性意义,并且在他的问题意识以及柏拉图研究旧范式的背景下来考察其观点的贡献与局限,以期能够推进我们对苏格拉底道德哲学的研究。
一、缘 起
1977年,沃拉斯托斯的学生厄文(Terence Irwin)的《柏拉图的道德理论》一书出版(5)Terence Irwin, Plato’s Moral Theory: The Early and Middle Dialogue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7. 此书出版后,得到了C. Taylor、M. Burnyeat、Malcolm Schofield等著名柏拉图学者的高度赞誉,而且受到了一般读者的广泛关注。Cf. David Roochnik, Terence Irwin’s Reading of Plato, Platonic Writings, Platonic Readings, ed. by Charles L. Griswold Jr., p. 183.,沃拉斯托斯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力,于是开始重新思考苏格拉底。对他来说,柏拉图早期对话中的道德哲学究竟是不是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学说,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而当时以格思里(W. Guthrie)为代表提出的主流观点则直接将苏格拉底说成是功利主义的先驱,认为在德性与幸福的关系问题上,苏格拉底主张道德行为的最终理由是一个非道德的目的(6)Cf. Gregory Vlastos, Socrates: Ironist and Moral Philosopher, p. 6.。厄文的那本名作对此有所修正,他用“工具主义”(instrumentalism)替代了“功利主义”, 但在沃拉斯托斯看来,这一替换并无实质性意义,因为在德性与幸福的关系问题上,厄文依然认为苏格拉底主张德性完全不同于幸福,德性只偶然地同幸福相关,因而依然脱离不了功利主义的窠臼(7)Cf. Gregory Vlastos, Socrates: Ironist and Moral Philosopher, p. 7.。
厄文立论的一个基础是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分离,他认为他们分离的一个标志是苏格拉底经常在德性主题上使用“技术类比”(craft analogy),而柏拉图则拒斥“技术类比”。厄文认为,如果德性是一种技术性知识,那么,正如技术性知识的产品(production)不同于技术性知识本身,于是德性的产品即幸福也就不同于德性本身,因此,德性只是获得幸福的一种工具性手段,它们之间并没有必然的、内在的关联;而柏拉图拒斥“技术类比”,正是表明了柏拉图主张德性与幸福有内在的关联,德性是幸福的构成要素(8)Terence Irwin, Plato’s Moral Theory: The Early and Middle Dialogues, p. 1, pp. 82-85, p. 300n53.。
对此,沃拉斯托斯只同意厄文观点的一半:他完全赞同厄文对柏拉图的论述,但坚决反对其对苏格拉底的论述,他认为苏格拉底和柏拉图都不是“工具论者”(instrumentalist)。厄文的《柏拉图的道德理论》出版后,他与厄文在《时代文学副刊》(TimesLiterarySupplement)上展开了长达六个月的论战(1978年3月—9月),论战之后,沃拉斯托斯发表了《苏格拉底对希腊正义观的贡献》一文(9)Gregory Vlastos, Socrates’ Contribution to the Greek Sense of Justice, Archaiognosia I(1980), pp. 301-324.,他在其中驳斥了苏格拉底是“工具论者”的观点,但同时又将苏格拉底的观点推到了另一个极端,认为苏格拉底主张德性与幸福完全同一,即“同一性论点”(the Identity Thesis)(10)Cf. Gregory Vlastos, Socrates: Ironist and Moral Philosopher, pp. 7-10.。后来经过厄文的批评指正,沃拉斯托斯又发表了《苏格拉底道德理论中的幸福与德性》一文(11)Cf. Gregory Vlastos, Socrates: Ironist and Moral Philosopher, pp. 200-232.,他在其中又重点驳斥了“同一性论点”。最终,在苏格拉底论德性与幸福的关系这一主题上,沃拉斯托斯提出了既不是“工具主义”也不是“同一性论点”,而是偏向于“充足性论点”(the Sufficiency Thesis)的“德性主权”学说。
二、幸福论公理
在《苏格拉底道德理论中的幸福与德性》一文中,沃拉斯托斯首先澄清了“德性”(aretē)和“幸福”(eudaimonia)这两个词的翻译问题,然后据此论述了三种不同的关于幸福与德性之间关系的立场,并指出苏格拉底道德理论的独特性所在。
关于“aretē”,沃拉斯托斯提议将其译成“virtue”(德性)即可,并且强调它是指道德德性,其具体成分一共有五个:勇敢(andreia)、节制或明智(sōphrosynē)、正义(dikaiosynē)、虔敬(hosiotēs)、智慧(sophia)(12)Cf. Gregory Vlastos, Socrates: Ironist and Moral Philosopher, p. 200.。值得注意的是,沃拉斯托斯将这五种德性统称为道德德性,并没有强调它们之间的区别,这就给“德性主权”学说的内在缺陷埋下了伏笔。关于“eudaimonia”,他强调它是一种常识意义上的“自然语言”、市井语言,并且指出它可以同时表示人们在其中找到幸福的活动和主观的感觉状态,也即它兼具主客观两方面的含义,因而将其译成“happiness”(幸福)即可,但需注意,在前理论用法中,“eudaimonia”更侧重于“幸福”一词的客观因素(13)Cf. Gregory Vlastos, Socrates: Ironist and Moral Philosopher, pp. 201-203.。
在澄清了翻译问题后,沃拉斯托斯开始论述由苏格拉底所奠定的并且为其后的道德理论家所共有的“幸福论公理”(the Eudaemonist Axiom):“幸福是所有人都欲求的,它是人类所有理性行为的终极目的(telos)”(14)Gregory Vlastos, Socrates: Ironist and Moral Philosopher, p. 203.。需要强调的是,所谓幸福是终极目的,并不是说我们日常生活中面临选择时都要以幸福为理由,而是说它是最终理由,比如x是为了y,y是为了z,z是为了幸福,推论到此结束,再推下去就毫无意义(15)Cf. Gregory Vlastos, Socrates: Ironist and Moral Philosopher, p.203.。而面对“为什么我必须是道德的”这一问题时,古希腊道德理论家的具体观点可能千差万别,但他们会一致回答:“因为道德行为可以为我的幸福提供最好的前景”(16)Gregory Vlastos, Socrates: Ironist and Moral Philosopher, p. 204.。他们的分歧只会出现在德性与幸福的具体关系上,大致有如下三种观点:
1.对某些人来说,这种关系纯粹是工具性的;他们认为德性值得欲求仅仅是因为它是获得幸福的工具性手段,其自身根本不值得欲求。
2.对另一些人来说,这种关系是构成性的,但仅仅是部分的构成;他们认为德性自身是最值得欲求的,但不是唯一的因其自身就值得欲求的东西。
3.对还有一些人来说,他们在相同的方向上更进一步,认为这种关系的构成性是完全的(intoto):对他们来说,德性就是幸福——是唯一能够带来令人满意的好生活的东西。(17)Gregory Vlastos, Socrates: Ironist and Moral Philosopher, p. 204.
沃拉斯托斯认为,第一种立场以苏格拉底的密友阿里斯提波(Aristippus)为代表,其后则以伊壁鸠鲁(Epicurus)为代表。他们将幸福等同于快乐以及痛苦之缺失,认为之所以比起恶来应当更加偏爱德性,仅仅是因为德性更有可能产生快乐的益处。这种立场是快乐主义的(hedonist)立场。但沃拉斯托斯指出,在《高尔吉亚》(Gorgias)中,苏格拉底严厉批判了这种观点,认为这种观点会赞成令人厌恶的自我放纵的生活——娈童的生活(G. 494e),所以无论如何苏格拉底都不可能是一个快乐主义者(18)Gregory Vlastos, Socrates: Ironist and Moral Philosopher, pp. 204-205.。但我们要注意,《高尔吉亚》中的苏格拉底的确不是快乐主义者,但在《普罗塔戈拉》(Protagoras)的后半部分,苏格拉底则是某种意义上的快乐主义者(19)参见《普罗塔戈拉》353c-356c,中译本参见《柏拉图四书》,刘小枫编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第140~149页。另参见玛莎·纳斯鲍姆《善的脆弱性》修订版,徐向东、陆萌译,徐向东、陈玮修订,南京:译林出版社,2018年,第163~170页。。可见,沃拉斯托斯忽略了苏格拉底的多面性而只抽取了有益于自己论证的某些部分。
第二种立场以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为代表。沃拉斯托斯指出,现代学者认识到这一点花了不少时间,因为他们不能理解“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认为所有的东西被选择是为了幸福而同时又有些东西被选择是为了其自身,这是如何可能的”(20)Gregory Vlastos, Socrates: Ironist and Moral Philosopher, p. 205.。对此,他重点分析了亚里士多德的说法:即使智慧(sophia)和明智(phronēsis)不产生(produce)任何东西,它们自身也值得被选择,因为它们是德性;但它们又的确产生某些东西,不过其产生的方式与医术产生健康的方式不同,智慧产生幸福的方式就如同健康产生健康的方式;由于智慧是完整德性的一部分,因此一个人拥有它并实践它就是幸福的(E.N. 1144a1-6)(21)本文中《尼各马可伦理学》译文参考了廖申白译本(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沃拉斯托斯指出,这段话表明德性自身就是值得欲求的,其中“产生”是说德性是幸福的“组成部分”或“构成要素”。
这里要注意的是,沃拉斯托斯似乎直接就从智慧或明智过渡到包括道德德性在内的整个德性,他同样没有对各种德性加以区分。但如果我们参照《尼各马可伦理学》中的说法,即“严格意义的德性离开了明智就不可能产生”(E.N. 1144b15-16),那么就可看出亚里士多德这里注重的是理智德性而不是所有德性,由此可见沃拉斯托斯的论述极为笼统。不过另一方面,沃拉斯托斯澄清了理智德性“产生”的方式和上文提及的厄文所论述的技术“产生”的方式之间的区别,这有助于我们重新反思苏格拉底使用“技术类比”时的意图:他或许意在证明关于德性的知识不同于技术性的知识(22)Cf. David Roochnik, Of Art and Wisdom: Plato’s Understanding of Techne, Pennsylvania: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6.。但如此一来,苏格拉底的观点就和柏拉图以及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无甚区别,而这恰恰与沃拉斯托斯的总体观点相左。
我们将在第五部分再来总结沃拉斯托斯论证的缺陷,这里接着看他所论述的第二种立场。他指出,在亚里士多德看来,除了德性外,幸福的每个其他部分都可以为了其自身的缘故和为了整体的缘故而被欲求(23)Gregory Vlastos, Socrates: Ironist and Moral Philosopher, p. 207.。据此,他认为,第二种幸福论虽然有效防止了功利主义,但与苏格拉底的主张还是有一点细微差别,即它并没有认为德性对于幸福来说既是必要的也是充分的。
至于第三种幸福论,沃拉斯托斯认为它虽然可以保证德性是幸福的充要条件,但有点过度,因为它认为德性是幸福的唯一成分——德性就是幸福的全部。这种观点的代表是苏格拉底的密友安提司泰尼(Antisthenes),之后的犬儒学派和斯多亚学派都持这种观点,沃拉斯托斯将其表述为:德性与幸福同一,所有非道德的善都是无足轻重的事物。但他同时也指出,苏格拉底的“德性主权”学说并不持这样的观点,而且他还预先申明:苏格拉底对现代的道德理论,甚至是对希腊化时代和罗马时代的伦理学都完全无知(24)Cf. Gregory Vlastos, Socrates: Ironist and Moral Philosopher, p. 208.。
三、充足性论点与同一性论点
沃拉斯托斯申明了苏格拉底在幸福论上所持的是不同于上述三种立场的独特的“德性主权”原则。他主要抽取了《克力同》中的三段为证:
(1)但对于我们来说,由于这个论证的强迫(houtō...hairei),我们应当只考虑一件事情……我们是否行为正义……或者,事实上不正义……如果这个行为明显是不正义的,那么我不得计较待在这儿接受死亡或任何其他的悲惨遭遇,而应当念念在于免行不义。(T12Cr. 48c6-d5)
(2)那么根据我们所同意的,让我们考虑这一点:未经雅典人的同意擅离此地是正义的还是不正义的?如果是正义的,我们就离开;如果是不正义的,我们就不这样做。(T14Cr. 48b11-c2)
(3)“我们是否仍然认为,最高的价值不是生活而是生活得好?”
“是的。”
“生活得好与生活得体面、生活得正义是一回事:我们服不服膺这句话?”
“服膺。”(T15Cr. 48b4-10)(25)Cf. Gregory Vlastos, Socrates: Ironist and Moral Philosopher, pp. 210-214. 本文中《克力同》译文由笔者据沃拉斯托斯英译文译出,并参考柏拉图《游叙弗伦、苏格拉底的申辩、克力同》,严群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
沃拉斯托斯提醒读者注意《克力同》的背景:苏格拉底处于不幸之中,因而他不得不在相互冲突的价值或善之间作出非此即彼的选择,他选择的是道德的善,由此可见他认为在价值领域中,德性是具有统治地位的善(26)Cf. Gregory Vlastos, Socrates: Ironist and Moral Philosopher, pp. 210-211.。此外,沃拉斯托斯还指出,苏格拉底的这些说法必然会推导出反对以恶报恶这一观点(Cr. 49c10-d5),也会推导出遭受伤害要比伤害别人更好这一观点(G. 474c-476a),而这些观点正体现出苏格拉底的思想与传统道德规范之间出现了巨大分歧:他禁止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之类的古代复仇法(27)Cf. Gregory Vlastos, Socrates: Ironist and Moral Philosopher, pp. 211-213. 关于苏格拉底在这一主题上的创新之处,可参见此书第194~199页。。沃拉斯托斯认为,苏格拉底的禁止复仇原则正是源于其“德性主权”原则,同样,T14和T12也是如此:决定是生是死,仅仅要看那个事情是正义的还是不正义的,而不要有其他考虑。他提醒我们注意那些表示推理的句子:“由于这个论证的强迫”“那么根据我们所同意的”,并且指出如果T14和T12是“德性主权”原则的应用,那么T15便是“德性主权”原则的前提(28)Cf. Gregory Vlastos, Socrates: Ironist and Moral Philosopher, p. 213.。
T15初看上去似乎是在陈述幸福和有德性的生活方式是同一的,也即它似乎主张的是上述第三种幸福论即“同一性论点”。但沃拉斯托斯指出,“同一性论点”当然可以保证“德性主权”原则,但它过度满足了这个要求,因为它“仅仅告诉我们当我们要选择的东西分别是合乎道德的和邪恶的时我们应该作何选择,但并没有告诉我们当我们面对其他种类的选择时我们应该怎么办”(29)Gregory Vlastos, Socrates: Ironist and Moral Philosopher, p. 215.,而后一种情况正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遇到的。沃拉斯托斯举了选择床铺的例子:比如我要在一个奇怪的房间里过夜,那个房间里有两张床,一张干净整洁,另一张污秽杂乱,按照“同一性论点”,如果我是有德性的,那么无论选择哪张床我都会同样地度过幸福的一夜,这显然违背我们的常识(30)Cf. Gregory Vlastos, Socrates: Ironist and Moral Philosopher, p. 215.。
为了调和苏格拉底面临生死抉择时的原则和日常生活中的原则,沃拉斯托斯提出了“充足性论点”,为此,他对T15中的“一回事”(tauton,或译“同一的”)进行了极为精微的分析。他指出,苏格拉底虽然说幸福的和有德性的生活是“tauton”,但这里的“tauton”并不是表示“同一的”意思,而是表示“可换位的”(interentailing)意思。他援引了亚里士多德的说法(Topics103a23-31,b10-12):当说A和B是“tauton”时,一般有三种意思,沃拉斯托斯列出了两种:
1.A和B是同义词(synonyms),或A和B的定义相同。
2.B,用亚里士多德的术语来说,是A的“特性”(proprium,idion),也就是说,即使B不是A的“本质”(essence),它们二者也必定是可换位的。(31)Gregory Vlastos, Socrates: Ironist and Moral Philosopher, p. 217. 此处的术语翻译可参考亚里士多德《论题篇》,徐开来译,《亚里士多德全集》第一卷,苗力田主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360~362页。
1是“tauton”一词基本的和主要的用法,但“幸福”和“德性”显然不是同义词,2则既适合于“同一性论点”,也适合于“充足性论点”,所以这里说“幸福”和“德性”是“一回事”是说它们是可换位的(32)Cf. Gregory Vlastos, Socrates: Ironist and Moral Philosopher, p. 218.。
“充足性论点”与“同一性论点”貌合神离,表面上看来,它们都认为德性是幸福的充要条件,都支持“德性主权”原则,但如果细加审视就会发现它们的细微差别。按照“同一性论点”,德性与幸福完全等同,其他的善或有或无对幸福丝毫无影响;而如果按照“充足性论点”,德性虽是幸福的充要条件,但如果其他的善同德性结合则会稍微增进幸福。打个比方,如果一个有德性的人被剥夺财产,被关进监狱,被严刑拷打,按照“同一性论点”,只要这个人是有德性的,那么他遭受不幸就和不遭受一样的幸福;而按照“充足性论点”,那么他不遭受就要比遭受更幸福。简言之,“有关幸福的变量,按照‘同一性论点’,它就是个单一变量函数(a function of a single variable)”,即只有幸福和不幸福两种情况,“而按照‘充足性论点’,它就是个多重变量函数(a function of a many variables),其他诸多非道德的善可以作为增进幸福的微小成分,如果它们与德性相结合的话”(33)Gregory Vlastos, Socrates: Ironist and Moral Philosopher, p. 216.。
四、英雄主义立场与常识
在笔者看来,沃拉斯托斯竭力将苏格拉底的道德学说解释成偏向于“充足性论点”的“德性主权”学说,这在某种意义上和他的基督教信仰以及自由派思想有关(34)Cf. Richard Kraut, Gregory Vlastos on Justice and Equality, Apeiron: A Journal for Ancient Philosophy and Science, vol. 26, no. 3/4(1993), Virtue love & Form: Essays in Memory of Gregory Vlastos, pp. 99-109; Robert Meister, Is Moderation a Virtue? Gregory Vlastos and the Toxins of Eudaemonism, Apeiron: A Journal for Ancient Philosophy and Science, vol. 26, no. 3/4(1993), pp. 111-135; Bernard Williams, Pagan Justice and Christian Love, Apeiron: A Journal for Ancient Philosophy and Science, vol. 26, no. 3/4(1993), pp. 195-207.:一方面是耶稣受难的英雄图景,一方面是自由民主制下日常生活中的理性选择,如何调和二者是他的关切所在。在他看来,如果苏格拉底选择“同一性论点”,那么他便做了一个毫无意义的选择,因为这种论点会使所有非道德的价值或善都失去意义,这样便会在幸福论和日常慎思之间造成一道裂缝,而“充足性论点”恰好可以弥补这道裂缝。
首先,“充足性论点”可以捍卫常识:一个人拥有财富、拥有人身自由显然要比被剥夺财产、被关进监狱更幸福。而且沃拉斯托斯在讲到“eudaimonia”一词的翻译时特别强调它是“自然语言”、市井语言,提醒读者要在常识的意义上来理解它,此外,在讲到日常生活中的理性选择时,他所举的例子大多是选择床铺这一类。可见他时时刻刻都在捍卫常识。
但同时,“充足性论点”也对我们的行为提出了英雄主义的要求。沃拉斯托斯略为提到了这同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艰难岁月有关,而且苏格拉底所举的例子以及他本人被判死刑这一事例都是某种非常时刻的事例,在这种时刻,伸张“德性主权”尤为重要,“同一性论点”和“充足性论点”都能满足这种英雄主义的要求。但“同一性论点”过度地满足了这种要求,因为当海内承平的时候,人们所要面对的不是酷刑、放逐和死亡,而大多是一些平庸琐事,这时“同一性论点”就显得有些尴尬和无助。也许是要捍卫英雄主义这个“高”的东西,但同时也要照顾人们的常识(“低”的东西),而且要打通二者,给二者建立某种关联,于是沃拉斯托斯提出了“充足性论点”。这个论点可以保证“德性主权”这一原则,也可以保证常识,并且在德性的主导下也可以使得常识不那么低下。
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一点,可以参看沃拉斯托斯所排列的价值或善的等级:
1.最终的、无条件的善是幸福。它是唯一仅仅因其自身就值得我们追求、欲求的善,因此它是我们所有行为的“终极目的”(telos)。
2.最高的、无条件的但不是最终的善,对我们的幸福来说既是必要的也是充分的,因此我们的善的统治成分是德性(智慧以及相关的道德德性)。获得这种善应该成为引导我们所有行为的目标(skopos),因为不管我们能够获得或是丧失其他什么的善,如果我们获得了这种善的成分,那我们就拥有了最终的善:我们便是幸福的。
3.次一级的、不是最终的而且是有条件的善:健康、财富等等。它们对我们的幸福所造成的差异是微小的。但它们也是善;我们拥有它们要比没有它们更幸福,但只有当我们正确地使用它们时才是如此,因为它们不是“仅凭自身就是善的”:如果离开了智慧,那么它们就会使我们变坏,那么我们拥有它们就要比没有它们更坏。
4.被称作是既不好也不坏的“中间物”(intermediates),因为它们不是善的组成部分:它们的价值纯粹是工具性的;它们从不因其自身而被欲求,仅仅为了善它们才被欲求。(35)Gregory Vlastos, Socrates: Ironist and Moral Philosopher, pp. 230-231. 沃拉斯托斯此处的等级划分参考了《吕西斯》中论述“友爱的首要对象”(prōton philon)的段落(Ly. 219b-220b),在笔者看来,这恰是为了回应厄文,因为厄文论证苏格拉底是工具论者的主要证据除了上文提及的“技术类比”,还有就是《吕西斯》219b-220b处的原则。Cf. William Prior, Introduction, Socrates: Critical Assessments, vol. IV, ed. by William Prior,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6, p. 147; Terence Irwin, Plato’s Moral Theory: The Early and Middle Dialogues, p. 51.
如果按照沃拉斯托斯的引文T25(G. 467e1-468b4)、T28(Eud. 281d2-e1)以及《欧蒂德谟》中所开列的善的事物的清单(Eud. 279a-c),那么便可如此来理解上述划分:4是“非善”,它主要是指一些“物理的客体”,如石头、木棍等等,或“物理的行为”,如站、坐等等,它们仅仅具有工具性的价值。1、2、3是“善”。3可以看成是“非道德的善”,如健康、财富等等,它们作为善是有条件的,必须同德性(更确切地说是智慧)结合才善,才有益于幸福(作用是微小的,但不是一点益处都没有)。2是“道德的善”,可以专指希腊的五种典型德性,它们是德性的专有“成分”或“部分”,德性是幸福的充要条件,是我们所有行为的目标,也是其他善的统治者,其他善同它结合可以稍许地增加幸福,这便是“德性主权”原则。1是最终的、无条件的、内涵最广的善,可以称为“幸福论公理”,所有道德理论家的出发点和终极目的都是幸福。由此可见,从1到4,它们之间有着依次向下统摄的关系。
五、“德性主权”学说的缺陷
沃拉斯托斯似乎清晰有力地论证了“德性主权”学说,但正如上文所述,一方面要调和基督教信仰和自由派思想,于是他便努力将苏格拉底呈现为一位完全遵照常识的英雄,另一方面要强调苏格拉底同柏拉图以及其他道德理论家之间的区别,于是他便抽取了有利于自己论证的片段,而忽略了苏格拉底的复杂性或多面性。在这双重的先行预设下,他所论述的“德性主权”学说便呈现为他意在呈现的样子,但如果我们细加审视,就会发现这一学说存在某些缺陷。
首先,在论证内容上,正如本文第二部分所言,在谈论“aretē”一词的翻译以及在论述第二种幸福论时,他忽略了德性的成分即五种典型德性之间的区别,在笔者看来,这是他最为明显的一处疏漏。这里值得详细分析一下他在排列价值或善的等级时所依据的T25(G. 467e1-468b4)和T28(Eud. 281d2-e1)。他注意到T25和T28之间有着明显的不一致:按照《高尔吉亚》中的三分法(好、坏、不好不坏),智慧这个道德的善和健康、财富这两个非道德的善都被归到好的一类,但在《欧蒂德谟》中,只有智慧被归到好的一类,而健康、财富等等都被归到不好不坏的一类。对此,沃拉斯托斯将《欧蒂德谟》中的说法按照上下文解读成“健康、财富等等仅仅按其自身(just by itself)是不好不坏的”,他加上了一个“仅仅按其自身”,这样一来似乎解决了矛盾(36)Cf. Gregory Vlastos, Socrates: Ironist and Moral Philosopher, pp. 228-230.。但如果细查他所引的那段《欧蒂德谟》引文前面的对话内容(Eud. 281b-c),就会发现,苏格拉底同样也暗示了勇敢和节制若是没有智慧的引导也是很坏的(37)参见列奥·施特劳斯《论〈欧蒂德谟〉》,陈建洪译,《柏拉图式政治哲学研究》,张缨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2年,第105页。。如果按照沃拉斯托斯的解决方案,这就应该解读成勇敢和节制“仅仅按其自身”是不好不坏的,但这显然同他的中心论点相抵牾。而如果考虑到《欧蒂德谟》中的苏格拉底认为“勇敢和节制若是没有智慧的引导也是很坏的”,那么沃拉斯托斯所提出的“德性主权”就应该置换成“智慧主权”,或者至少要将“智慧”和其他德性区别对待。
在《理想国》卷六中,苏格拉底说哲人的天赋包括勇敢、节制等等(Re. 487a),又说如果具有哲学天赋的人被坏的教育环境败坏而远离哲学的话,那么他就远比一般人要坏(Re. 490c-491e),这同样也暗示了勇敢和节制若是没有哲学(或智慧)的引导就会很坏,如此一来,那么被沃拉斯托斯归为早期对话的《欧蒂德谟》和被他归为中期对话的《理想国》卷二至卷十——也就是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在这一问题上就毫无差别。此外,如果将智慧和其他德性区别对待,那么这同样也预示了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开头对理智德性和道德德性所作的划分,如此一来,苏格拉底和亚里士多德在这一问题上也就无甚区别。因此,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之间的区别并不像沃拉斯托斯所断言的那么巨大,苏格拉底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两人在很大程度上有着某种内在的一致性。
其次,在论证方法上,沃拉斯托斯主要是抽取柏拉图对话以及其他古希腊作品中的某些片段,并将这些片段作为一个个论题(T1、T2……),然后通过严谨的分析从这些论题中提炼出某些论点或是构建起这些论题之间的关联,这种做法很容易忽略对话的情境。比如刚刚提到,他在分析T28(Eud. 281d2-e1)时,完全没有考虑同书的281b-c,而如果考虑到这段,那么就会得出不一样的结论。
但另一方面,沃拉斯托斯有时又没有只关注那些论题的字面含义,尤其是当那种分析方法不能解决他的问题时,他就会考虑对话情境,比如上文第三部分提到,在分析T12、 T14和T15,也就是在分析同时适合于“德性主权”原则的“同一性论点”和“充足性论点”时,他对“tauton”一词进行了细致的辨析,并提醒我们要注意苏格拉底发言时所处的特殊情境,而且他还将与此类似的情况还原为日常生活中的情景,并由此揭示不同于字面含义的含义或语词背后的含义(38)Cf. Gregory Vlastos, Socrates: Ironist and Moral Philosopher, p. 219.。
由此可见,无论在论证内容还是在论证方法上,沃拉斯托斯所提出的“德性主权”学说都存在一些固有的弊端;而且由于他有着自己独特的问题意识,因而当那些内容或方法无助于解决他的问题或无法达成他想要达成的结论时,他就会采取另一种方式。
六、余论:沃拉斯托斯的贡献与局限
尽管存在问题,但沃拉斯托斯对苏格拉底道德哲学研究的贡献依然不可否定。在笔者看来,其贡献有二:一是通过还原古希腊的原初语境并对一些关键术语诸如“eudaimonia”“tauton”作出语义学上的澄清,沃拉斯托斯将苏格拉底的道德哲学与近现代道德哲学区别开来,并借此扭转了认为苏格拉底的道德哲学是“功利主义”或“工具主义”的偏见;二是确立了苏格拉底在古代伦理思想史上的奠基性地位,并展现了古代道德哲学的原初背景和较为全面的谱系,为后人的思考提供了指引:
在希腊思想的发展史上,苏格拉底的真正地位在于:他第一个建立了以幸福论为根基的伦理理论,这一根基是产生于苏格拉底圈子甚至圈外的所有学派的共同基础;他是非工具论形式的幸福主义的奠基者,这种幸福主义为柏拉图主义者、亚里士多德主义者、犬儒学派、斯多亚学派也就是所有希腊道德哲学家所共有,除了伊壁鸠鲁学派(39)Gregory Vlastos, Socrates: Ironist and Moral Philosopher, p. 10.。
这两个贡献也体现在沃拉斯托斯对柏拉图对话的整体研究上。首先,他强调并践行了分析哲学和古典学相结合的跨学科研究方法,恢复了柏拉图哲学乃至整个古希腊哲学的尊严。正如他的另一位学生内哈马斯(Alexander Nehamas)所言,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分析哲学一统天下,正是通过沃拉斯托斯等人的努力,才使得古希腊哲学被接受为分析哲学的一个分支,也正是由于这个背景,沃拉斯托斯才极为强调柏拉图对话中的论证部分,力图证明那些论证经得起形式分析以及数理逻辑的检验(40)Alexander Nehamas, Virtues of Authenticity: Essays on Plato and Socrat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xxiv-xxv.,因此,我们应该参考这一背景来同情地理解沃拉斯托斯的工作。其次,正如本文开头所言,沃拉斯托斯的苏格拉底研究有其方法论上的限制,尤其是随着20世纪90年代以来柏拉图研究界发展论范式的动摇(41)参见黄俊松《如何进入柏拉图对话?》,《现代哲学》2018年第1期。,他的局限也日益突显,但他毕竟勾勒了柏拉图对话的整体图景,提供了某种整全的研究视野,而且如今主流学界的新观点大多都建立在对他的批判上。
综上所述,虽然沃拉斯托斯的研究存在一些固有的弊端,但由于他在自己的方法论限度内已经做到了极致,因而我们会发现,他正在走向或促使别人走向他的反面。如今,如果我们在方法论转向的视野下来重新考察他的研究,就会发现在他的研究基础上,或是通过带入更多的对话内容或对话情境,或是通过扭转他的结论,都可以极大地推进对柏拉图对话的研究。在笔者看来,这便是沃拉斯托斯的意义所在。尽管他有许多错误,但这些错误绝不是简单的错误,因此,我们不能以一种后见之明来简单地否定他的贡献。沃拉斯托斯在为柏拉图辩护时说道:
只有那种幼稚的批评才会将免于逻辑错误定为衡量哲学家之伟大的标准。……我同意罗宾逊(Richard Robinson)的说法,“科学上的伟大主要在于你将你初次迈入科学时所面对的那一主题推进了一大步”。(42)Gregory Vlastos, Introduction, Plato: A Collection of Critical Essays I, ed. by Gregory Vlastos, Notre Dame: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1978, p. 1.
在笔者看来,这一说法也同样适用于沃拉斯托斯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