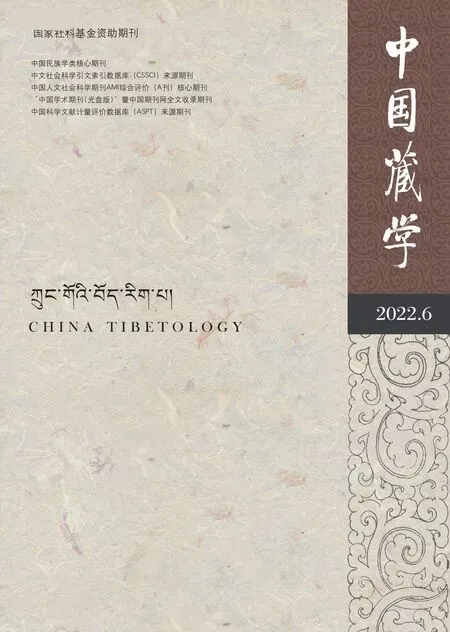西藏自治区山南市吉如拉康保存的部分早期写卷及其插图①
熊文彬
吉如拉康位于山南市乃东区结巴乡雅鲁藏布江北岸的小山谷温村,现存建筑由大殿、大日如来佛殿和一座小殿组成。大日如来佛殿保存有一组大日如来佛、八大菩萨和两位护法的泥塑,同时保存有大量写本残卷和一幅“幡画”。②索朗旺堆、张仲立主编:《乃东县文物志》,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1986年,第17页。2005年,笔者曾与西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的巴桑旺堆研究员对该寺进行调查。自2007年始,巴桑旺堆重点对其中两份写经愿文的书写、语法、时代、内容及其相关人名、地名和价值等进行了详细、全面的研究,并在国内外连续发表了4篇重要成果。①其成果分别是:Basang Wangdu,“Ke Ru Lha Khang:Cultural Preservation and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in Central Tibet”,in Deborah Klimburg-Salter,Kurt Tropper and Christian Jahoda eds.,Text,Image and Song in Transdisciplinary Dialogue,Brill,2007;巴桑旺堆:《藏文古写本研究》,《西藏研究》2008年第4期;《关于古藏文写本的研究方法的再探索》,《中国藏学》2009年第3期;“Paper,Patronage and Production of Books:Remarks on an 11th Century Manuscript from Central Tibet”,in Hildegard Diemberger,Franz-Karl Ehrhard and Peter Kornicki,eds.,Tibetan Painting:Comparison,Continuities and Change,Brill,2016.按他根据吉如拉康发现的《圣回向救护一切有情众生经》(下简称《救护一切众生经》)和《十万颂般若波罗蜜多经》(下简称《十万颂》)写经愿文的记载所作的考证,吉如拉康所在地温村在11—12世纪名为“温莫隆仁 ()”,为吐蕃时期贵族那囊氏的封地,其位置在今山南市乃东区所属结巴乡一带。吐蕃王朝灭亡后,达磨赞普的儿子永丹的六世子孙“额达衮乃”在此割据。吉如拉康是额达衮乃时期该地一所重要的寺院,并非意大利学者维塔利 (Roberto Vitali)认为的8世纪赞普赤德祖赞时期修建的扎玛噶曲寺 ()。②Roberto Vitali,Early Temples of Central Tibet,London:Serindia Publications,1990,pp.1-35.吉如拉康因此建于11世纪的额达衮乃时期,但不完全排除其前身为9世纪牟尼赞普时期修建的查纳拉康 ()的可能性。③Basang Wangdu,“Ke Ru Lha Khang:Cultural Preservation and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in Central Tibet”,in Deborah Klimburg-Salter,Kurt Tropper and Christian Jahoda eds,Text,Image and Song in Transdisciplinary Dialogue,Brill,2007,pp.45-49.与此同时,蔡巴噶举创始人喇嘛尚(1122—1193)曾参与《十万颂》写本的校对和审定。这些成果对于吐蕃王朝灭亡后西藏腹心地区11—12世纪的割据势力、吐蕃王室后裔的分布和贵族那囊氏的封地、吉如拉康的历史和写经等研究都提供了全新的视野。巴桑旺堆虽然公布了该寺写本残卷及其彩绘插图的一些图片,但未对其进行详细的整理,鉴于这批材料十分重要,本文在他研究的基础上,对写卷的内容和彩绘插图进行进一步梳理。
一、写卷内容及其年代
吉如拉康保存有大量写卷,但笔者只对其中部分写卷进行了调查。这些写卷均为残片,部分有火烧、水浸等明显痕迹。质地为藏纸,长度多在60—68厘米之间,宽度多在15—23厘米之间。绝大多数为墨书,少部分为瓷青纸金书,装饰彩绘插图,字体主要为邬坚体,每页文字介于3—8行之间,内容基本为佛经 (图1)。根据写卷扉页所题经名、品名和跋记、写经愿文等记载,现存佛经主要为显宗经典,其中《般若波罗蜜多经》(下简称《般若经》)较多,仅《十万颂》就保存有数个不同尺寸的写本。这些经典主要如下:

图1 吉如拉康写经残片
1.《十万颂》
(4)《十万颂》及其写经愿文,该写本尺寸为67×22.4厘米,墨书,8行,邬坚体,两侧对称设置红色圆圈,中心穿孔。其中后4行诗体写经愿文不仅记载了所写经典为“《十万颂》()”,同时对写经地的地理、历史、供养人、写经材料、写经者和校对、审定者等重要历史信息进行了记载:“……山高地洁悉补野吐蕃之地,祖孙三王对吐蕃恩重如山。殊胜之地温之那囊之域……勇武无双之勒如库扎帕……敬造《十万颂》,愿其加持护佑圆满证获菩提!三界之统辖者勒如喇贝,御敌于外之胞弟南喀,呵护亲人备至之施主帕巴加,父系兄弟内外之远近亲属,为此纷纷解囊美食资具。工布吉查之地纸张真神奇,汉地东京之墨真神奇,统协抄经事务者真神奇,缮写者曲巴·尼扎真神奇,掌管及校对者乃喇嘛尚,功劳最大施主皆满意,此文缮写者尚尊衮拉帕。”(图2)正如巴桑旺堆所指出,其中写经地“温”(温莫隆仁的简称)为吐蕃时期贵族那囊氏的封地,填补了相关文献记载的空白;“山高地洁悉补野吐蕃之地”表明了对该地与赞普所属家族悉补野所建立的吐蕃王朝的隶属和继承关系;“祖孙三王”为后世流行的“祖孙三法王”的早期记载;校对者“喇嘛尚”为蔡巴噶举派创始人喇嘛尚·尊珠扎巴,其出现表明该经缮写于12世纪;①原文为:,译文参照巴桑旺堆:《关于古藏文写本的研究方法的再探索》,《中国藏学》2009年第3期,第80—81页。与此同时,写经过程中“汉地东京之墨”的使用为12世纪以吉如拉康为代表的西藏腹心地区与宋代内地的交流提供了重要的史料。①关于“汉地东京之墨”的考证以及宋代西藏与内地的交流,详见熊文彬:《西藏山南吉如拉康写经愿文中的“东京之墨”记载:北宋西藏与内地交流的重要遗珍》,待刊。

图2 《十万颂》及其写经愿文
(5)《十万颂》写本跋记,该跋记断裂成两截,文字3行,大多漫漶,其中前2行为墨书,最后1行为朱书,均为邬坚体。其中第1行残存“…………(……八十七……[毕])”, 第2行残存“……(尚博约·强秋洛日缮写……为……善根而造)”,第3行残存“……(《十万颂般若波罗蜜多经》……承诺……从伍如迎请……)”。页面两端对称设置有红色圆圈,并在中心穿孔,孔洞有明显使用过的痕迹,在孔洞两侧装饰有两朵八瓣莲花。文字、字体、语法、装帧都具有显著的吐蕃写卷特点 (图3)。

图3 《十万颂》末叶背面题记和图案残片

图4 吉如拉康首题写经愿文
《十万颂》是藏传佛教最为重要、现存不同历史时期写本最多的经典之一。该经最早在吐蕃时期译入,为《丹噶目录》1号经典,共300卷,100000颂,相当于汉文《大般若经》第一会《王舍城鹫峰山说法》(400卷,79品),后收入《大藏经》。它在《大藏经》中有两个版本:一种为纳塘版和拉萨版《大藏经》收录的版本,全文75品,按跋记,由印度堪布胜友 (Jinamitra)、天帝觉(Surendrabodhi)和智军 ()等人翻译、校对并审定;另一种为其余版本《大藏经》收录的版本,全文72品,无跋记。②黄明信:《汉藏大藏经目录异同研究——〈至元法宝勘同总录〉及其藏译本笺证》,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3年,第17页;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大藏经》对勘局:《中华大藏经·藏文对勘本》,《甘珠尔》卷25,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年,第806、906页。吉如拉康现存的《十万颂》写本未见译经跋记。
2.《八千颂》
吉如拉康现存至少有两个写本:(1)扉页左侧严重被毁,尺寸为58(残)×19.5厘米,墨书,7行,邬坚体,左右两端装饰彩绘插图,其中左侧大部已毁,右侧略残,像下无题记; (2)第一品扉页页边略残,保存相对完整,尺寸约65×19厘米,墨书,7行,邬坚体,左右两侧配饰插图,中部两侧有红色圆圈,且在中部穿孔。
《八千颂》也是藏传佛教最为重要、现存不同历史时期最多的写本之一。该经最早在吐蕃时期译入,系《丹噶目录》5号经典,后收入《大藏经》。该经历史上经过多次译、校和审定,有不同版本存世。《大藏经》收录本最早由印度堪布释迦军 (akyasena)、智成 (Jñānasiddhi)和僧人法性戒 (Dharmatās'īla)译、校并审定。后在古格王拉德 ()时期,印度堪布善言(Subhaita)和译师仁钦桑布()根据拉德之令按其注疏再译。随后阿底峡大师 (Atis'a)和仁钦桑布根据印度 ()的注疏再改译、校正并审定。阿底峡和仲敦巴·嘉瓦迥乃 ()在聂塘纳摩且()讲解该经时又在且隆 ()对其审定。仲敦巴·嘉瓦迥乃在热振寺按照印度的三藏经典再次对其审定。后译师罗丹喜饶 ()又根据克什米尔和印度的梵本再次对其进行审定。①黄明信:《汉藏大藏经目录异同研究——〈至元法宝勘同总录〉及其藏译本笺证》,第26页;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大藏经》对勘局:《中华大藏经·藏文对勘本》,《甘珠尔》卷33,中国藏学出版社,2007年,第684页。
3.《圣回向救护一切众生经》
现存写本为末叶及其写经愿文,尺寸为62.5×17.8厘米,墨书,8行,邬坚体,左右两侧对称设置有红色圆圈,并在中心穿孔,页边略残 (图5)。其中前3行为跋记:“……(《圣回向救护一切众生经》毕,该经由天竺堪布作明光、智藏译,经校译师贝孜校对并审定)”。贝孜全名叫噶瓦贝孜,系吐蕃9世纪著名的藏族译师,因此该经在9世纪时译为藏文。将其与《大藏经》收录的版本初步比较发现,该经后来虽收入《甘珠尔》,但其经名和译者略有差异。《大藏经》收录本经名为“”,另外与作明光一起合作的译者不是智藏,而是吐蕃9世纪另一位重要的藏族译师智军 ()。②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大藏经》对勘局:《中华大藏经·藏文对勘本》,《甘珠尔》卷68,中国藏学出版社,2008年,第231—236页。由此推测,如译师名字抄写无误,吉如拉康藏本与《甘珠尔》收录本疑非同一译本。随后5行写经愿文的内容主要是礼赞佛祖、吉如拉康所在地及其执政者、施主、祈愿、纸、墨、写经者和校对者,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其主要内容如下:“诺,三界胜地释迦佛伏化之地,乃为世间领地蕃域大地。山高地净雪山环绕之中,殊胜之地乃为温莫隆仁。人中豪杰出了额达衮乃,尚论之首出了尚·敦扎帆,殊胜寺庙出了拉康吉如,殊胜堪布出了格西沃敦……殊胜之纸张,根布冬让也;殊胜之墨者,汉地之东京也;殊胜写经者,约布之克当也……”③藏文为:巴桑旺堆在2007年的英文文章 “Ke Ru Lha Khang:Cultural Preservation and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in Central Tibet”、2009年的《关于古藏文写本的研究方法的再探索》中对该愿文的第一行内容进行了英译和汉译,2016年又在 “Paper,Patronage and Production of Books:Remarks on an 11th Century Manuscript from Central Tibet”中对该愿文进行了全文英译。笔者此处译文参考了他的译文。按巴桑旺堆根据《德乌教法史》《德乌教法广史》和《汉藏史籍》等文献考证,其中的“额达衮乃”为吐蕃最后一位国王达磨赞普的第六代孙“衮乃赞 ()”,他是吐蕃王朝灭亡后在桑耶、乃东这一带地区割据势力的首领。由此可知,吉如拉康建于11世纪,该经也写于此时。①巴桑旺堆:《关于古藏文写本的研究方法的再探索》,《中国藏学》2009年第3期,第80页。笔者核对《德乌教法广史》,藏文,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89—390页)和《德乌教法史》(,藏文,西藏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53页)发现:第一,此处的 “六代孙”疑笔误。按前者,应为第7世孙,蔡纳益西坚赞为6世孙,但其子不是衮乃,而是赤巴;第二,二著所载之名与愿文吻合,为 “衮乃”,而非 “衮乃赞”,疑笔误;第三,二著对衮乃的记载出入较大,按《德乌教法广史》,衮乃系蔡纳益西坚赞的长子,但《德乌教法史》所载不同,蔡纳益西坚赞的长子为赤巴 (班觉桑布:《汉藏史集》藏文本,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年,第214页,与此记载同,但其中未记载 “衮乃”),而衮乃为其重孙。

图5 《救护一切众生经》及其写经愿文
4.《圣花 [积]陀罗尼》
尺寸为64.5×15.1厘米,墨书,7行,邬坚体,页面中上部被毁,页边多有残缺并有污渍,两侧有对称的红色圆圈,中心穿孔。该经收入《大藏经》,②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大藏经》对勘局:《中华大藏经·藏文对勘本》,《甘珠尔》卷97,中国藏学出版社,2008年,第461—466页。与汉文《佛说花积陀罗尼神咒经》为同一经典。③即汉文《大正藏》no.1356—1359号,参见宇井伯寿、铃木宗忠、金仓圆照和多田等观合编:《德格版西藏文大藏经总目录》,台北:华宇出版社,1986年,第92页。
5.《圣地王陀罗尼》
尺寸为64.5×15.1厘米,邬坚体,页面中上部被毁,页边多有残缺并有污渍,两侧有对称的红色圆圈,中心穿孔。此经收入《大藏经》,跋记云:“天竺堪布胜友、施戒和校对大译师智军翻译、校对并按新语修改、审定。”④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大藏经》对勘局:《中华大藏经·藏文对勘本》,《甘珠尔》卷88,中国藏学出版社,2008年,第195—198页,藏文为:同时见同著卷97,第469—472页。由此可知,该经在9世纪译为藏文。
6.《圣善门陀罗尼》
尺寸为63.5×15.8厘米,墨书,8行,邬坚体,页面两侧有红色圆圈,中心穿孔。跋记与《大藏经》收录本相同。按跋记,该经由“天竺堪布胜友、施戒和校对大译师智军翻译、校对并按新语修改、审定”。⑤跋记为:与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大藏经》对勘局:《中华大藏经·藏文对勘本》,《甘珠尔》卷91,第160—172页和卷97,第759—771页所载跋记,除个别正字拼写外,内容相同。由此可知,该经在9世纪译为藏文,并可与汉文《金刚秘密善门陀罗尼经》勘同。⑥即汉文《大正藏》no.1138—1140号,参见宇井伯寿、铃木宗忠、金仓圆照和多田等观合编:《德格版西藏文大藏经总目录》,第107页。
7.《圣无垢陀罗尼》
尺寸为63.5×15.8厘米,墨书,8行,邬坚体,页面两侧有红色圆圈,中心穿孔。该经收入《大藏经》,按其跋记,此经也在9世纪译入,由“天竺堪布胜友、施戒和校对大译师智军翻译、校对并按新语修改、审定”。⑦分别见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大藏经》对勘局:《中华大藏经·藏文对勘本》,《甘珠尔》卷88,第155—164页;卷97,第259—268页。
8.《圣十一面观音陀罗尼》
尺寸为64.5×16.7厘米,墨书,8行,邬坚体。边缘略残并有污渍,两端中部有红色圆圈,中心穿孔。该经收入《大藏经》,按其跋记,由天竺堪布戒帝觉 (S'lendrabhoti)和校对大译师智军在9世纪翻译、校对并审定。①分别见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大藏经》对勘局:《中华大藏经·藏文对勘本》,《甘珠尔》卷93,第379—384页;卷97,第621—626页。该经可与汉文本《佛说十一面观世音神咒经》勘同。②即汉文《大正藏》no.901、1070—1071号,参见宇井伯寿、铃木宗忠、金仓圆照和多田等观合编:《德格版西藏文大藏经总目录》,第119页。
9.《圣佛 [藏]陀罗尼》
尺寸为64.5×16.7厘米,墨书,8行,邬坚体。边缘略残并有污渍,两端有红色圆圈,中心穿孔。该经收入《大藏经》,按其跋记,在9世纪由天竺堪布胜友、施戒和吐蕃经校大译师智军翻译、校对,并按厘定的藏文新译语修改、审定。③分别见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大藏经》对勘局:《中华大藏经·藏文对勘本》,《甘珠尔》卷88,第141—144页;卷97,第195—198页。
10.《圣一切无畏施陀罗尼》
尺寸为64.5×16.7厘米,墨书,8行,邬坚体。边缘略残并有污渍,两端中部有红色圆圈,中心穿孔。按其跋记,该经于9世纪“由天竺堪布胜友、施戒和经校大译师智军翻译、校对,并据新译语修改、审定”。该经后来收入《大藏经》,跋记与《大藏经》收录版本的内容吻合,④分别见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大藏经》对勘局:《中华大藏经·藏文对勘本》,《甘珠尔》卷91,第132—135页;卷97,第822—825页。但《大藏经》收录本的经名题为,与此对照,吉如拉康写本经名缺 二字。可与汉文本《佛说施无畏陀罗尼经》勘同。⑤即《大正藏》no.1373号,参见宇井伯寿、铃木宗忠、金仓圆照和多田等观合编:《德格版西藏文大藏经总目录》。
11.《圣灌顶陀罗尼》
尺寸为64.5×16.7厘米,墨书,8行,邬坚体。边缘略残并有污渍,两端中部有红色圆圈,中心穿孔。该经收入《大藏经》,按收录本跋记,由天竺堪布胜友、施戒和吐蕃大译师智军等人在9世纪翻译、校对,并按照厘定的新译语修改和审定。⑥跋记参见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大藏经》对勘局:《中华大藏经·藏文对勘本》,《甘珠尔》卷97,第229—232页。
12.《大孔雀佛母经》
左侧残,尺寸为46(残)×15.5厘米,墨书,3行,邬坚体,两端装饰彩绘插图,并题写有尊像题记,其中左侧题记为“(大孔雀佛母)”,右侧题记为“(文殊菩萨)”。该经收入《大藏经》,按收录本跋记,9世纪“由印度堪布戒帝觉、智成、释迦光 (ākyaprabha)和经校大译师、僧人智军翻译、校对,并按新语修改、审定”。⑦跋记参见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大藏经》对勘局:《中华大藏经·藏文对勘本》,《甘珠尔》卷90,第254—330页。另,该经可与汉文本《佛母大金曜孔雀明王经》勘同。⑧即《大正藏》no.982、984—985号,参见宇井伯寿、铃木宗忠、金仓圆照和多田等观合编:《德格版西藏文大藏经总目录》,第98页。
13.《圣诸法议论大乘经》
瓷青纸,左侧残,尺寸为60×22厘米,金汁书写,4行,邬坚体,左右两侧配饰彩绘插图。其中左侧坐佛严重残毁,仅剩一半,右侧坐佛中下部残,像下残存题记“……(……如来)”二字。经初步检索,该经未见《大藏经》收录,待考。
根据跋记、写经愿文和《大藏经》收录本跋记等记载可知,吉如拉康现存上述经典绝大部分在吐蕃时期译为藏文,并在11—12世纪再次缮写,其语法、书写和装帧特征也与此吻合。在文法上,上述写本体现出如下几个特点:(1)藏文基字为、、、4组中的字母可以互换,例如(宝贝)经常拼写成(译师)经常拼写成; (2)基字加下加字,例如(无);(3)后加字、、等后面加再后加字,例如(去)、(彼岸)等;(4)元音反写,如“”(人)等;(5)单个基字加后加字,如(经); (6)保留了诸如(释迦)、(等) 和(完)等一些特殊的古词。字体以邬坚体为主,部分字母书写独特,具有吐蕃时期写卷和碑铭特征,以下两点尤为明显:(1)基字、、等书写独特;(2)部分带有上加字的词汇书写独特,即上加字与基字并不处于上下同一轴线上,上加字往往左移。巴桑旺堆将以敦煌写卷为首的这些古藏文书写的特点归结为“字体的特殊书写现象”。①巴桑旺堆:《关于古藏文写本的研究方法的再探索》,《中国藏学》2009年第3期,第61—81页。装帧为梵夹装,页面两端中心预留两个圆圈,直径3厘米左右,并在中心穿孔,以便穿绳装帧,有的则作为装饰。这些特点在13世纪之后都逐渐消失。
总之,吉如拉康上述写本中的佛经绝大多数在9世纪译为藏文,缮写于11—12世纪,但其中也有部分吐蕃时期译为藏文并缮写的佛经 (如图3)。
二、彩绘插图的题材与风格
吉如拉康上述写卷中保存的彩绘插图相对较少,仅有十余幅,且主要保存在《般若经》中。插图主要配置在扉页两端,左右对称,尺寸多在10×8厘米左右。插图主要如下:
1.《十万颂》彩绘插图
(1)《十万颂》第一品扉页彩绘插图《十万颂》第一品扉页两端对称配置有两幅彩绘插图(图6)。按前述尊像题记,左侧插图为日轮光德佛,右侧插图为日光菩萨,为一佛一菩萨配置。值得一提的是,无论是日轮光德佛本身,还是他与日光菩萨的配置,在藏传艺术中都十分少见。二者均出自《百拜忏悔经》,其中日轮光德佛属于十方佛中的西南佛,日光菩萨属于十方菩萨中的西南菩萨。该文本在吐蕃时期译为藏文,敦煌古藏文写卷中保存有P.T.22等多个残本。②分别参见西北民族大学、上海古籍出版社和法国国家图书馆:《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古藏文写卷》卷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105和107页;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大藏经》对勘局:《中华大藏经·藏文对勘本》,《甘珠尔》卷68,第23—31页。另按才让教授研究,《百拜忏悔经》不是从印度译入,而是在吐蕃时期编纂的一部佛教祈愿类经典。参见才让:《法藏敦煌藏文佛典 〈百拜祈愿文〉研究——兼论佛教初传吐蕃的传说》,《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第19页。由此可知,吉如拉康现存这部《十万颂》写本的插图极有可能是《百拜忏悔经》中记载的诸佛菩萨。

图6 《十万颂》第一品扉页插图
日轮光德佛身金色,螺发高髻,身着红色通肩袈裟,双手当胸结转法轮印,双脚结跏趺坐,正面端坐于多色覆瓣莲花座上。身后为舟形头光、马蹄形身光和背光;日光菩萨身蓝色,头戴多层三叶宝冠,裸露上身,下身着短裙裤,右手持白莲花,左手当胸结说法印,呈四分之三侧面像,面对日轮光德佛而坐。佛和菩萨的人物造型、装饰和色彩都具有比较浓郁的波罗风格元素。
(2)《十万颂》第一品扉页彩绘插图吉如拉康另一个《十万颂》第一品写本的扉页也有两幅插图(图7)。按照前述尊像题记,左侧插图表现的是梵光佛,右侧插图描绘的是莲花光佛。按《大宝积经》卷24《优婆离会》,题记中梵光佛的藏文的简称;莲花光佛的藏文的简称。③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大藏经》对勘局:《中华大藏经·藏文对勘本》,《甘珠尔》卷43,中国藏学出版社,2008年,第337页。汉译本的《大宝积经》和《三十五名礼忏文》将后者译为“莲花光游戏神通佛”,但不见前者译名。二者均为三十五佛之一,由此可知,该《十万颂》写本的插图表现的应为三十五忏悔佛。

图7 《十万颂》第一品扉页插图
梵光佛身金色,螺发高髻,身着红色袈裟,袒露右肩,右手当胸结说法印,左手置于跏趺的双腿上,结禅定印;莲花光佛身金色,螺发高髻,身着红色袈裟,袒露右肩,右手下垂结触地印,左手当胸结说法印,双脚结跏趺坐于莲座。除手印外,二佛的造型基本一致,头光、身光、背光、三角形焰肩等装饰也完全相同,体现出浓郁的波罗风格因素。
2.《八千颂》彩绘插图
(1)《八千颂》扉页插图左侧插图已毁,仅剩菩提树和背光残边,但右侧保存完整。坐佛构图在菩提树下,身金色,螺发高髻,穿着红色袈裟,袒露右肩,右手下垂结触地印,左手当胸结禅定印,双脚结跏趺坐于仰瓣莲台。胸部、面部和双手关节处有晕染的凹凸感。此幅插图除构图和晕染外,其余造型、装饰等都与前述两个《十万颂》写本第一品的插图如出一辙,只是技艺略逊一筹。
(2)《八千颂》第一品扉页插图(图8) 左图坐佛身金色,螺发高髻,身着袒右肩红色袈裟,右手下垂结触地印,左手当胸结禅定印,双脚结跏趺坐于莲台,疑为释迦牟尼佛。与前述插图相比,短颈宽胸是其造型上的显著特点。右侧插图损伤较重,但人物基本特征尚能辨认,描绘的应为一面四臂般若佛母。般若佛母身金色,头戴双重三叶宝冠,上身裸露,下身着裙裤,主臂当胸结转法轮印,另一右手上举持经箧,另一左手上举结说法印,双脚结跏趺坐于莲台。周身配饰耳珰、珍珠项链、璎珞、手镯、臂钏、脚镯,人物造型和装饰体现出较浓的波罗风格。

图8 《八千颂》第一品扉页插图
(3)《八千颂》常啼菩萨品插图与前述《般若经》写本不同的是,此写本插图为黑白,并配置在文本的右端。插图为线描,只勾勒轮廓,几乎没有细节表现,描绘的是一位坐佛。佛高髻,身着袈裟,双手当胸结转法轮印,双脚结跏趺坐于莲台。莲台之下,构图有一对相背回首的蹲狮。①参见张建林等:《西藏东部吐蕃佛教造像》,北京: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图79。从造型、手印和乘骑来看,此佛极有可能表现的是释迦牟尼佛,但蹲狮与9世纪初昌都市察雅县仁达大日如来佛与八大菩萨摩崖石刻中的双狮相似,同时结合文字具有吐蕃时期显著的古藏文语法、字体和装帧特点综合判断,此幅插图极有可能绘制于吐蕃晚期。
3.《圣诸法议论大乘经》扉页彩绘插图
该经扉页两幅插图表现的也是坐佛,左侧插图一半被毁,右侧插图相对完整 (图9)。右侧坐佛身蓝色,螺发高髻,身着红色袈裟,袒露右肩,右手下垂结触地印,左手当胸结禅定印,双脚结跏趺坐于莲台,疑为阿閦佛,背后为舟形头光、马蹄形身光、三角形焰肩和马蹄形背光。像下残存题记“……如来”二字,蓝色底色上点缀细花。左侧坐佛除双手当胸结禅定印外,其余造型和装饰与右侧坐佛相同。与前述插图明显不同的是,此处的插图在经文与图像之间装饰有两条纵向的多色宝石装饰条带,十分醒目并富有装饰性。从题记和造型推测,插图表现的“如来”疑与三十五佛或贤劫千佛有关。

图9 《圣诸法议论大乘经》扉页插图
4.《大孔雀佛母经》扉页彩绘插图
该经扉页也有两幅插图 (图10),左侧页面虽然残损,但插图基本完整。按图像下题写的前述尊像题记,左侧插图表现的是大孔雀佛母,右侧插图表现的是弥勒菩萨。大孔雀佛母为三面八臂造型,身金色;主面金色、右面绿色、左面红色;主右臂当胸持宝瓶,主左臂置跏趺的双腿上结禅定印,其余六臂呈扇形分布两侧,其中右侧三臂造型从上到下持剑、法轮、结与愿印,左三臂造型从上到下依次持孔雀翎、宝幢和宝瓶。弥勒菩萨一面二臂,身金色,头戴五叶宝冠,裸露上身,配饰珠宝,下身穿着碎花裙裤,双手当胸结转法轮印,双脚结跏趺坐于束腰莲台。二像的造型、水滴状的五叶冠等装饰体现出尼泊尔风格元素,身体比例略显失调,躯干明显过长。从装饰、法器的造型看,结合文字特征,与前述插图相比,其年代相对较晚,疑创作于13—14世纪。

图10 《大孔雀佛母经》扉页插图
5.文殊菩萨“幡画”
山南博物馆藏有一件出自吉如拉康的11世纪文殊菩萨“幡画”,①索朗旺堆、张仲立主编:《乃东县文物志》,第17页。1984年文物普查时,该画作仍保存在该寺,被定性为唐卡。此幅作品也体现出比较浓郁的波罗风格元素,与上述写本插图密切相关 (图11)。这件作品高77.5厘米,宽23.5厘米,棉布设色,正面为文殊菩萨和供养人像,背面为55行忍辱偈和缘起偈,2006年曾在德国展出。②Kulturstiftung Ruhr Essen,Tibet:Klöster öffnen ihre Schatzkammern,München:Hirmer Verlag,2006,Kat.Nr.31,S.244. 本文图11采自该著图31。德国的展览图录和《乃东县文物志》都将此画作称之为唐卡,但长方形细条状的唐卡绝少见到,其形制反而与甘肃敦煌、新疆等地出土的幡画一致,如系幡画,则缺少幡首、幡手和幡足。总之,该作品究竟属于唐卡还是幡画,有待研究,现暂称“幡画”。同时,感谢廖旸研究员为笔者翻译德国图录中的相关要点。文殊菩萨身金色,头戴层叠三叶形宝冠,裸露上身,下身着裙裤,右手下垂结与愿印,左手当胸结说法印并持青莲花茎,跣足立于双重仰莲座上。造型修长,上身宽实,周身配饰耳珰、项链、U形项链、手镯、臂钏和脚镯等珠宝饰物。莲花座下构图有两身四分之三侧面的供养人像,左侧人物头部略仰视,表情肃穆,身着翻领长袍,外套大氅,双手当胸合十;右侧供养人尺寸较小,亦抬头仰望,身着翻领夹克,双手当胸合十,虔诚礼拜。与文殊菩萨浓郁波罗风格的面相、装饰等元素相比,供养人像的面相、服饰体现出藏式本土文化风格特点。

图11 文殊幡画,现藏山南博物馆
吉如拉康写卷中的上述插图和“幡画”与拉萨、山南和日喀则等卫藏腹心地区11—12世纪艺术的风格吻合。此时期卫藏腹心地区重要的艺术遗存主要有扎塘寺、大昭寺、坚利寺、唐迦寺、卓卡寺、艾旺寺、夏鲁寺、乃宁寺和色喀古托寺的早期壁画,以及达隆寺的唐卡、杰拉康的石雕等。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都带有较为显著的波罗风格元素。其中夏鲁寺早期建筑建于1027—1045年间,扎塘寺建于1081—1091年间,色喀古托寺建于1078—1084年间,大昭寺虽然建于7世纪,但在吐蕃王朝灭亡后遭到严重破坏,在11世纪中叶和12世纪又先后由桑噶尔译师帕巴喜饶和杰贡巴·楚臣宁波进行过大规模维修,基本上与吉如拉康写本及其彩绘插图和“幡画”属于同一历史时期。风格类比显示,吉如拉康写本彩绘插图与“幡画”的风格基本上也与这些寺院艺术的风格一致。例如,《十万颂》的日轮光德佛和《八千颂》的释迦牟尼佛插图与大昭寺早期壁画中的千佛风格非常相近;《十万颂》的日光菩萨和《八千颂》的四臂般若佛母插图与唐迦寺观音菩萨和大昭寺《说法图》中的菩萨和佛母相似;①罗文华、宋伊哲:《大昭寺早期壁画调查报告》,《故宫博物院院刊》2021年第9期。文中16、17图分别采自此报告图三十四 (编号2-22壁画)线描图和图四十二 (编号3-20壁画)局部。而文殊菩萨“幡画”也与大昭寺胁侍菩萨立像的风格类似。鉴于上述寺院中的艺术遗存多为壁画,彩绘插图较为罕见,吉如拉康写卷插图的发现无疑丰富了卫藏腹心地区11—12世纪艺术的种类和形式。
三、小 结
写经愿文、跋记、历史著录,以及写本的语法、字体和装帧特点表明,吉如拉康前述写卷主要为9—14世纪译为藏文或缮写的佛经,其中主要为11—12世纪的写卷。正如巴桑旺堆所指出,其中的写经愿文不仅为吐蕃和宋代吉如拉康所在地区的地名、寺院、氏族、写经和供养人的关系提供了绝无仅有的材料,更重要的是填补了吐蕃灭亡后赞普后裔在卫藏腹心地区所建立的割据势力及其与宗教、社会关系等领域的史料空白。与此同时,写经中使用的“汉地东京之墨”的记载,为宋代西藏与内地之间的交流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史料。此外,写卷中的彩绘插图以《般若经》配置最多,通常对称地配置在扉页两侧。插图也主要绘制于11—12世纪,与同一时期卫藏腹心地区现存艺术一样,也体现出浓郁的波罗风格元素。鉴于同时期其他寺院的艺术遗存多为壁画,插图较为罕见,因此这些彩绘插图的发现丰富了这一地区艺术的种类,也具有重要的艺术和学术价值。

图12 《十万颂》第一品扉页插图日轮光德佛局部

图13 《十万颂》第一品扉页插图 日光菩萨局部

图14 释迦牟尼佛,《八千颂》第一品扉页插图局部

图15 四臂般若佛母,《八千颂》第一品扉页插图局部

图16 说法线描,大昭寺壁画局部

图17 胁侍菩萨,大昭寺壁画局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