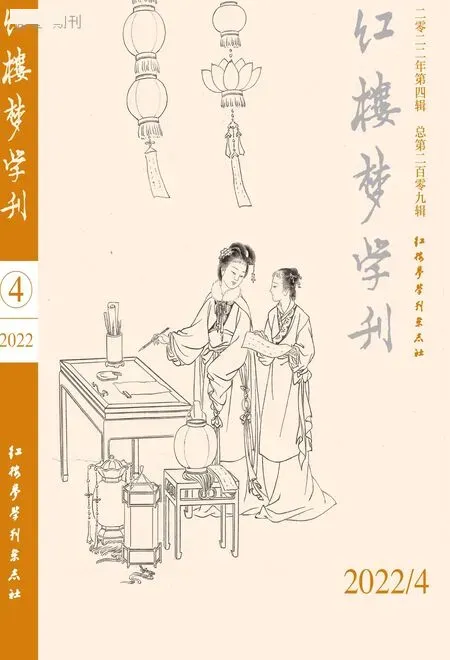《红楼梦》叙述分层的多重内涵*
李丹丹
内容提要:《红楼梦》复杂的叙述分层不是一个故弄玄虚的技巧问题,而是有着多重创作意图:其一,叙述分层是小说家对叙述主体责任的分化和转移,既是对小说“恐有碍语”的巧妙规避策略,也是造成小说真假互现阅读效果的客观原因。其二,叙述分层凸显了小说“命”与“力”的冲突,即超叙述层的“宿命”与主叙述层人物“自主”之间的巨大张力,及由此带出的价值观与存在论问题。其三,叙述分层体现出自传与自叙传小说的根本区别:从小说家的亲身经历到小说的故事呈现中间至少隔着三个层次的叙述。总之,小说家是有意借助叙述分层去“控制”其与叙述者、角色及读者之间的关系和距离,从而“客观化”其自身经验,并由此实现作品的意义从个体家族的兴衰转化成人类普遍性悲剧的可能。
作为鸿篇巨制的伟构,《红楼梦》的独特魅力不仅在于其审美艺术、文化价值的多元与立体,亦存在于其繁复精密的叙述技巧中。20世纪80年代,西方叙事学理论传入中国之后,为了催促中国小说迅速步入现代化,先锋小说家们曾进行了大量的“有意味的形式”的尝试实践,马原、格非等人创造的“元叙述”模式就成为当时文学形式革命的一个醒目标志。但其实早在明清时期的众多章回小说中,“元小说”的叙事模式已经初露端倪。读过章回小说的人,大约都会注意到这类小说普遍采用了一种先诗词(韵文)——再议论——然后开始小说正式叙述的故事结构类型。也就是说,章回小说在正文开始之前,基本都有一个引首、楔子,作为对小说故事来源、价值、作者写作意图的一种说明或暗示,这就是所谓的“入话”。这说明在中国古典小说中,已经出现了初步的叙事分层和叙述视角转移的文体自觉。这种自觉到了《姑妄言》中,则是出现了一种被称为“叙述套盒”的有益尝试,成为明清章回小说在叙述形式上的重大突破。而到了《红楼梦》中,这种对叙述形式的尝试已经被成功地运用成一个完整的艺术结构。可以说《红楼梦》以其繁复精妙的叙事策略宣示并实践着中国古典小说在叙述结构上所达到的最深处和最远处。
一、叙述责任的转移和小说真假互现的阅读效果
美国叙事学家马丁在谈到叙事形式对认识文本的价值时曾指出:“叙事形式是某些普遍的文化假定和价值标准——我们对于重要、平凡、幸运、悲惨、善、恶的看法,以及我们认为是什么推动一种状态到另一种状态——的实例。”陈平原在涉及此问题时也精辟地提出:
小说叙事模式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一种“形式化了的内容”,那么,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就不单是文学传统嬗变的明证,而且是社会变迁(包括生活形态与意识形态)在文学领域的曲折表现。
两位研究者的发现都在提醒我们,叙事形式从来都不只是形式问题,而是敏锐地凸显着一个作家写作意图、价值取向乃至一个时代文化变动的相关讯息。
“若无新变,不能代雄”,赵毅衡曾断言“《红楼梦》是现代之前世界文学中绝无仅有的复杂分层小说”。据他的研究,《红楼梦》至少有四个分层构成:
1.超超叙述层的“作者自云”;2.超叙述层的石头自叙经历,空空道人抄录,曹雪芹“批阅十载”;3.主叙述层的贾雨村、甄士隐、林如海故事及荣宁两府故事;4.次叙述层的石呆子扇子故事,林四娘故事等等。
表面上看,叙述分层不过是一个技巧问题,但是《红楼梦》为何要调用这样多的分层去增加叙述和阅读的难度?况且不同的分层势必会牵扯到叙述的权威问题,分层越多,叙述声音越多,创作者驾驭小说的难度也越大,读者的理解难度也越大。比如开篇那个作者自云的“我”、作为故事主人公的石头、传阅故事的空空道人以及负责批阅增删的“曹雪芹”,他们的叙述声音是否统一?小说家分化出这些不同的声音的目的如何?
从叙事理论上来讲,一个叙述者一旦开口叙述,他就不可避免地要对自己话语的真实性、可靠性还有可能产生的结果负责,这就是叙述者要承担的叙述责任。如果叙述者想要在叙述中卸去责任,就需要虚拟出一个叙述主体,也即韦恩·布斯所言的“隐含作者”,代替作者进行故事讲述。具体到《红楼梦》中,不难发现,作为小说真实创作者的曹雪芹一方面有讲故事的欲望,但又因叙述责任(尤其是文网的压力)显得顾虑重重。于是,在叙述冲动与叙述责任之间的摇摆,就会让叙述技巧上的分层成为一种必然,因为分层不仅意味着对叙述主体自我身份的掩护(石头、空空道人、“曹雪芹”都成为叙述主体的化身),同时也意味着叙述主体的分化,进而可以成功地转移作为创作者曹雪芹的叙述责任。
《红楼梦》的最高叙述层,即是开篇那个“作者自云”。这个自称“历过一番梦幻”的作者,一开口就用“梦”“幻”“假语村言”等语提醒读者此书的虚构性,但当读者当真准备将其读作一个真事隐去的虚构故事时,作者又调转笔墨,明确此书所记之人乃“当日所有之女子”,因其行止见识皆出于“我”之上,故作此书,为的是使闺阁昭传。这段“作者自云”一方面点出了作者是用以退为进的“幻化笔法”故意模糊故事真假之间的界限,如第一回甲戌本侧批所言是“自占地步,自首荒唐”。另一方面,作者通过自愧自悔的自谦姿态,卸下了叙述需要承担的责任,明确地告诉读者,本书不过是悔愧之余的“风尘怀闺秀”,并无伤时骂世之旨。考虑到《红楼梦》写作年代的特殊语境,作者前后矛盾的自云以及对叙述责任的推卸或可以理解。接下来作者又考虑到此书之新、奇、特,以及可能因此带来的误解,甚至担心开篇的梦幻之语和自愧自悔不足以打消读者疑虑,所以不惜再次动用一个叙述分层,层层遮掩和解释。
于是就有了《红楼梦》最独特的第二叙述层——石头自述、空空道人抄录、孔梅溪题名、曹雪芹增删组成的复合叙述层。《红楼梦》的核心故事本是一块“被弃”顽石对自己下世——历劫——返回的经历自述。但文本并没有在这一层让石头直接讲述故事,而是让故事延宕至第三叙述层,并且作者预设了一个并不欣赏石头故事的接受者——“空空道人”,还让两者形成了讲述者——读者的关系,双方就石头故事的朝代年纪、地舆邦国、书写内容、世人阅读口味、故事的新奇别致处,进行论辩。最终,空空道人思忖半晌,决定抄录回来,问世传奇。按理小说应该可以进入正文了,但《红楼梦》没有那样做,而是再一次迂回,设置了另两个接受者——孔梅溪、曹雪芹,最终题名、接受、欣赏并愿意增删、传播这个故事。
于是在这一层中,实际上出现了两个类似作者——读者的传播圈:
讲述者(石头)——接受者(空空道人)
转述者(空空道人)——接受者兼转述者(孔梅溪、曹雪芹)——真正的接受者(读者)
在这两个圈子中,空空道人的作用比较独特,一方面,他作为石头故事的接受者与转述者并不参与故事的发生,他与故事是间离的,因此他可以卸掉叙述责任,无压力地代替真正的读者对故事的可读性、真实性、可靠性发出各种质疑。同时他也不必提供关于这个故事的真实性、价值、意义的相关证据。另一方面,通过借助他与石头的对话,作者借石头之口亦回答了读者可能的质疑,完成了对自我书写(亦是石头经历)意义的辩白。这样,超超叙述层的作者将自己的叙述责任推到了石头身上,石头则借助空空道人完成了对故事真实性、价值意义的辩白,增强了自述经历的叙述权威,同时削减了作为第二个接受者兼转述者曹雪芹(曹雪芹在这里只是一个增删者)的叙述责任。于是当小说故事真正开始时,读者更强烈地感受的,这个故事似乎就是一个石头的自述,这种以第一人称开始的叙述,无疑又增加了自述的真实性和可靠性,让读者相信这个故事是实有其事。但同时,石头又是一个幻形入世又重返神界母体(符合出发——变形——回归的生命循环模式)的神话产物,读者并不会真正相信。于是阅读这个故事就会形成一种不停在神话、现实之间出入跳跃的真假难辨的阅读效果。因之,“假作真时真亦假”不仅是《红楼梦》作者主观创作意欲达到的目标,是虚构叙事留下的痕迹。同时亦是几个叙述主体在上述层面相互辩难、推卸叙述责任,最终由石头承担权威叙述者造成的文本的客观阅读效果。
二、命与力的张力冲突:叙述分层带来的悲剧美感和价值多元
由上论可知,对《红楼梦》来说,分层的复杂性,首先源自于作者这个叙述主体在多个层面上的分化,而这种分化又使得《红楼梦》成为一部充满价值冲突的小说。因为四个叙述分层的主体意图、价值立场和认同取向并非完全一致,而是在文本中相互辩难,体现出不同的叙述主体之间的竞争关系及叙述张力。因此,考察叙述分层,除了关注叙述主体意图可能具有的分化和转移外,更为重要的是分析这一技巧本身就蕴含着的价值的多元性与流动性,比如叙述分层如何凸显了小说命与力的冲突,这一冲突如何绵延贯穿乃至成为小说悲剧性的根源,在对这一冲突张力的描写中,小说又如何凸显出价值意义的多元?
在《红楼梦》的超叙述层中,跟随石头一起出现的还有僧道二人,作为神界的使者,“由于叙述层上高一层,一僧一道自然应有在命定范围内为主叙述层人物解救灾难或指点迷途的能力”。第三回甲戌本眉批亦曰:“通部中假癞僧跛道二人,点明迷情幻海中有数之人也。”这两个人物的出现,一方面加强了小说的虚构性和神话色彩;另一方面,也使小说有了一个超越在所有叙述层之上的外在视角,代表的是经历繁华之后的清醒和彻悟,继而与故事中人物的执着和沉迷形成张力。事实上,不止《红楼梦》,明清小说中的僧、道设置被很多小说家所偏爱,且大多有相似的叙事背景,只是这一背景多不约而同地被设置为某种固化的超凡脱俗的佛道本质。
当一部小说出现了超情节人物时,则无论其叙事怎样头绪纷繁、流动无序,都离不开被简化、抽象到最基本层面的佛道思想或命运观念的指引与制约。与此同时,僧、道或术士所代表的超现实力量,一方面强化了与小说家艺术追求一致的情节悬念与神秘性,另一方面又确定了情节不可移易的最终指向,从而展示出事物运行不偏不倚、因果分明的发展规律。
但在《红楼梦》中,一僧一道的作用并非仅仅为小说裹上一层宿命论的外衣,而是通过频繁地跨层,在第二(超叙述层)和第三层(主叙述层)之间自由跨越,从而将命与力之间的巨大冲突楔入小说的整体叙述中。
具体来说就是:一方面,作为神界人物,僧道拥有对主叙述层众生命运未卜先知的自觉,向下跨层的作用多是以“启悟”“点化”度脱世人,拯救灾难。如梅新林所言:“一僧一道又时时奔走于世俗凡间,具有‘补天济世之才,利物济人之德’,是凡间俗人的精神导师。”但另一方面,对处在故事中的角色人物来说,他们不能向上预知自己的命运,因此对僧道的救世、度脱并不信任,并频频加以质疑。比如甄士隐拒绝二人对甄英莲命运的预示,林黛玉无视(僧)对其总不能见哭声的提醒,贾雨村在智通寺无视(僧)对其的点化,贾瑞正照风月宝鉴以抗拒(道)的警示等。且僧道二人每一次跨层出现在主叙述层时,叙述者也都用差异化的笔法对其形象进行描述,比如在神界,两人是骨骼不凡、丰神迥异,而在俗界则是以不同形态的瘌痢头或者跛足邋遢姿态出现。这一方面是为了印证分层的叙述效果,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保证主叙述层中人物认识力的水平,因为他们不能预先得悉僧道二人先知的能力,故而他们看到的僧道形象并无神佛风采。
如此,僧道二人的救世与度脱责任,就与故事中人物的不自知且不愿被点醒的执着形成对峙,也即形成超叙述层中的宿命论与主叙述层中人物的自主性之间的矛盾张力。比如僧道二人及《好了歌》,是超叙述层在看过故事中的芸芸众生红尘翻滚后的一种告诫,它试图告知人们,即将到来的一切都是万境皆空,所有的尘世努力到头来不过都是“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所以红尘世人如果按照自己的意愿固执前行,最终只会“反认他乡是故乡”。关于《好了歌》,昔有张其信曾评曰:“透顶心凉,读之如冷水浇背。”近有俞平伯感慨:“不仅世态炎凉、而且翻云覆雨,数语已尽之。”其悲凉绝望之态,让人寒冷彻骨,不仅不能给人生在世提供些许帮助和启示,反而以否定主观努力的姿态,将人推入无可奈何的罔罔之中。若这样说,叙述者借《好了歌》究竟想要传达什么?虽然作者借助僧道二人与《好了歌》为《红楼梦》设置了一个宿命论的象征。但值得注意的是,小说的叙述者并没有完全站在僧道一边,而是在主叙述中,固执地赋予人物自主掌握命运的能力,并通过多种途径,比如贾宝玉摔玉,不接受警幻仙姑的训警,梦中大骂“和尚道士的话如何信得”等细节描写用以对抗宿命论的发生。
这样,僧道二人以及《好了歌》的作用就不再只是对尘世生活的直接否定和绝望,当然也不能简单理解为是对“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勇气的赞美。而是在提前预告了人生结局的前提下,给予并启示主叙述层的人物应该选择怎样的自主意识,去和看似既定的命运相抗争。正如余国藩的论述:“个人对自己行为的决定权以及天理或社会强迫个人必然要走的方向乃互斥互动,从而使人类的志节卯上一种‘具有敌意的天意。’”只是,在个人与天命的徒手搏斗中,个人的陨灭是必然的结果,因此主叙述层中各个人物最终只能以悲剧收场,这似乎见证了个人对抗天命的徒劳。但小说家启用《好了歌》的作用也非如此简单,既然一切都要既“散”且“了”,那么,人世的意义或者人活一次的价值就不再是随便的、糊涂的甚至是堕落的活,而更在于对活的过程中自我道路的选择:是如贾雨村那样走仕途经济之路?还是如贾宝玉退守大观园,与清净女儿一起活出自我本真本性的澄明之境?而这种精神启示其实恰恰类似于海德格尔后来所提倡的,在向死而生的条件下,人所能做的就是尽量选择诗意的栖居,作者对宝玉所做的选择正是建基于此。
总体来说,在超叙述层与主叙述层之间,是存在两种基本的叙述张力。其一,存在于上层的“知”与下层的“不知”之间的相斥相生,也即“旁观者的清醒与当事者的执迷构成一种艺术张力,导致一种深刻的悲剧感与宿命感的衍生”。这种张力既是叙述分层的结果,也是分层后小家设置的复合叙述主体(包括“作者”、“石头”、抄录者、增删者等)与故事角色之间视角差异造成的结果,因为前者为“梦醒之人”,而后者则是“梦中人”,故事角色是在对命运与未来的无知中成长、行动,而叙述者则十分清楚这些角色的身前身后事,掌握着他们的命运。其二,存在于主叙述层中甄、贾宝玉道路之间的对立互斥,这两种道路又延伸出男性社会的浑浊世界与女儿清明灵秀的本真世界对立排斥的另一种叙述张力。与此同时,甄、贾宝玉的道路选择又会与上层的宿命论构成矛盾,尤其是当贾宝玉代表的诗意、美好、澄澈等价值追求遭遇无情命运的碾压时,悲剧感的产生不仅体现为鲁迅所言的“把美好的东西毁灭给人看”,更重要的是呈现为作家对这种毁灭的精神满怀深情的肯定以及含泪执着的书写。事实上《红楼梦》的书写过程,就是上述这两种基本张力不断对话、冲突的过程,作为一个虚构的自足的叙述世界,《红楼梦》并不着意为读者提供一个清晰的终极选择,其意义只是蚀骨透心般地展示了上述张力在文本中的冲撞、对话以及造成的悲剧美感。
这样来看《红楼梦》的叙述分层,开头所设置的叙事圈套,以及那个套在石头自述故事头上的宿命环,就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技巧。因为一旦去掉这两个分层,读者很可能就会直接沉湎于故事本身,而当读者沉入故事与小说人物一起揣测未来命运时,《红楼梦》的意义就会被缩减成一个仅仅精彩的俗世故事。由此,叙述分层安排的背后,体现出的是叙述者如何看待“宿命”VS“自主”之间的巨大张力,以及由此带出的价值观与存在论问题:比如人物能否逃离命运的安排?能在多大程度上为自己的命运做主?以及如何选择适性生存的道路问题。由此必须承认“小说的叙事结构是作家的审美心理结构的对应物,是作家的情感与经验节奏的表现形式”。《红楼梦》的整体价值观就是在不同的叙述分层象征的不同价值体系内徘徊往复、犹疑不定。相信命运、但又不屈从命运,预知结局,但又固执地给予人物自主抗争的力量。于是,原本一个建立在真实历史基础上的悲剧故事(承认《红楼梦》是一个基于自叙传性质的小说),原本一种烂熟无奇的“命运不可违”的“悟空”思想,就在作家繁复缜密的关于叙述分层的设计中,获得超乎寻常的价值碰撞和多重意义,这或许就是叙述形式迸发出来的巨大价值。
三、从自传说到自叙传小说:叙述分层带来的理论支撑
《红楼梦》一面世,就面临着在体裁、内容和性质归属上的巨大争议,《红楼梦》究竟是家族自传?还是自叙传小说?此争议绵延两百多年至今仍未休止。抛开学界其他的讨论,这里仅从叙述分层的视角为《红楼梦》是自叙传小说提供一些支持。
20世纪80年代,西方叙事学理论的涌入曾为中国小说批评打开了一个全新的研究天地,尤其是韦恩·布斯关于作者与叙述者的区分,让研究者能够从理论的视角明确地将作品中隐含的作者与生活中真实的作家本人进行区别对待。
无论我们把他当做什么人——在创造作品之时,他创造出自己的一个更高超的版本。任何成功的小说都令我们相信一位“作者”,他等同于一种“第二自我”。这第二自我常常是一个经过高度细腻化和精选的版本,比任何真实的人都要更智慧,更敏感,更有洞察力。
布斯的思考,一方面帮助我们认识作者和“隐含作者”的不同,另一方面,也令读者有理由相信一部即使被视为具有自传性的作品,其自传的对象也是针对这个“隐含作者”的,而非现实中作家本人。布斯的区分,因为引入了叙述者的问题,使我们能够科学的理解《红楼梦》开头作者设置的一系列叙述者是否必要?其意图何在?另外,赵毅衡也曾将小说中的叙述者看作是作者主体分裂出来的一个代替人格,而小说的虚构叙述之所以能够发生,正是因为“作者主体分裂出来一个人格,另设一个叙述者,并且让读者分裂出一个叙述接收者,把这个文本当作实在性的叙述来接受。此时叙述者不再等同于作者,叙述虽然是假的,却能够在两个替代人格中把交流进行下去”。
由此可知,《红楼梦》开头那个复杂的叙述分层并非可有可无,这实际上暗示着作者如何处理他本人、作品的作者、叙述者以及故事主角的关系。实际上正是小说开头设置的多个叙述者,从形式上完成了《红楼梦》自传与自叙传小说的区分。某种意义上说自传说要成立,必须首先建立在上述几个身份的对等上面,比如周汝昌的自传说大厦的根基就是曹雪芹=叙述者=贾宝玉,曹、贾互证是其自传说在方法论上的唯一支撑。但如果仔细分析《红楼梦》的叙述手法,之所以能实现从自传向自叙传小说的过渡,正是借助第一回的叙述者的主体分化。《红楼梦》一开头,小说家首先虚构的就是小说中超超叙述层的“隐含作者”和超叙述层的复合叙述者,通过“作者自云”将叙述权转移给“隐含作者”,且直接出面介绍了这个小说的写法,所谓的真、假问题。然后“隐含作者”也隐身,将石头故事的缘起推卸给超叙述层那个复合叙述主体,由此小说家便疏远了自己与主人公宝玉的关系。并且当“隐含作者”宣布将用“假语村言”讲述自己的故事时,随后的一切便已经处在“假语村言”中。这有些像钱钟书所言的,讲故事前必须“献疑于先”,听者如果愿意听,就必须搁置对虚假的挑战,因为说者已经预先说好接下来听到的就是故事。实际上,所有的虚构叙述都或明或隐地设置这个“自首框架”。而对《红楼梦》而言,这个叙述分层的设置正是这个“自首框架”。也即一个人自己讲自己的经历,那可能是自传;但是一个人想象出一个人物来向我们讲述他的经历,那可能就是小说了。而《红楼梦》正是让作者、叙述者、故事的讲述者、接受者、抄写者、编撰者轮番登场,从而明确地区分了“讲故事的人”(作者本人)、石头故事的回忆者和叙述者“石头”、增删编纂者曹雪芹,并从亲历、写作、阅读三者关系的角度,向读者揭示了《红楼梦》这个小说如何由“真”而“假”、并由“假”而“真”的成书过程。
可以说正是借助这个叙述分层,小说家让我们看到《红楼梦》提供的不是“个体的真实经验”,而是一本虚构的“自叙传小说”,与此同时,小说家也正是这样与自己小说的主人公一步步拉开距离,而这个距离又恰好体现了自传与自叙传小说的根本区别——从小说家的亲身经历到小说的故事呈现中间至少隔着三个层次的叙述。这也意味着,小说家是有意通过叙述分层和叙述主体的分化,去“控制”其与叙述者、角色以及读者之间的关系和距离,从而“客观化”其自身的经验,并使自身经验转化为虚构的普遍性经验,并由此实现作品的意义从“自我”向整个“外界”的全面辐射。因此《红楼梦》的“真实性”或者“客观化”是来自叙述者对生活经验的转化而不是生活经验本身。
另外,也正是借助叙述分层,小说家区别了作者的声音/思想与主人公的声音/思想。对自传说来讲,其必然要求曹雪芹完全等于贾宝玉。但实际上在小说的诸多地方,都显然体现出小说家本人、叙述者与贾宝玉思想的不一致,这些不一致,主要体现在:其一,价值观的选择上,叙述者开头的忏悔姿态以及对补天石无才补天的惭恨,明确暗示出作者对待儒家入世思想的矛盾和复杂,而贾宝玉则显然简单的多。其二,在具体的女性观上,叙述者对女性的欣赏并不局限在未婚的少女,其对贾母、王夫人、李纨、王熙凤、香菱等已婚女性的赞美就是明证。而宝玉则通过著名的女性价值毁灭三部曲将其赞美限定在闺中少女身上。同时对女性才能的赞美,叙述者也并非局限在黛玉等裙钗的审美诗才,比如其对王熙凤探春等理家才干的由衷钦佩,而贾宝玉则显然仅局限于后者。其三,对情/淫的态度上。宝玉是“意淫”的具体表现者,其情不情思想表明其是“至情论”者,但是对小说家或叙述者而言,他对情的态度则显然矛盾的多。因此,第五回“谁为情种?”这一问题之后出现以下的脂批:“非作者为谁?余又曰,亦非作者,乃石头耳。”除这一条外,脂批还在多个地方暗示曹雪芹与贾宝玉的不同。再如第十九回中,己卯夹批的那一段批宝玉的名言:“按此书中写一宝玉,其宝玉之为人,是我辈于书中见而知有此人,实未目曾亲睹者。”都表明脂批亦明白宝玉身上虽然有作者的影子但不能等同于曹雪芹。
无疑,《红楼梦》是一部在传抄过程中逐渐成型的小说,但很少有小说家会像曹雪芹一样对自己的创作和小说的形成,做出如此之多的叙述层去限制和解释。不仅如此,实际上,伴随着上述叙述主体分化出现的还有小说命名的变化过程,这个变化过程不仅反向证明了各个视角的叙述者各自对故事主题的理解(多个名称对应了多个叙述主体),而且也从命名的变迁中再次印证了小说故事主题的多义性和价值观的多元化。比如石头自述其故事为《石头记》,暗示小说是一本关于石头生平经历的如实记述,强调小说的写实性和自传性。空空道人将其改名为《情僧录》,暗示其传抄中增加了“情”的部分,引进了关于情与悟、空的关系。而到了东鲁孔梅溪,小说家刻意安排一个儒家圣人的身份对其题名,其所题的《风月宝鉴》的暗示意图也很明显:以道德训诫,约束情、淫的过度泛滥。到了曹雪芹,“批阅十载、增删五次”的结果是将小说再次更名为《金陵十二钗》,而这一标题恰恰与小说开卷那个“作者自云”的目的一致,试图为“闺阁昭传”。
这样叙述分层、叙述主体分化以及小说多个命名的出现,最终造成的结果是拆解了小说文本的确定性,乃至价值选择的确定性,使得每一个叙述层的叙述都真假难辨,这样实与虚、真与假之间错综复杂的辩证关系,就编织出一张巨大的网,在每一个交界点上衍生出价值、意义和修辞的无尽悖论,从而将清初以降有关小说、历史和价值的论述带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因此,在18世纪中期,曹雪芹动用了新的叙述手段和修辞策略,带来的却是文人感知和呈现世界的新范式的出现。
① 有论者曾将这一引出小说正文的部分划分为引首类、楔子类、缘起类。参见李小菊、毛德富《论明清章回小说的开头模式及成因》[《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6期]。
② 具体论述可参见黄卫总著,张蕴爽译《中华帝国晚期的欲望与小说叙述》(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37—241页)。
③ 华莱士·马丁著,伍晓明译《当代叙事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91页。
④ 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3页。
⑤⑦ 赵毅衡《苦恼的叙述者》,四川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104、106页。
⑥ 亦有论者将《红楼梦》分为三个叙述层:超超叙述层与超叙述层合并,主叙述层和次叙述层,参见王彬《红楼梦叙事》(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7页)。另,陈维昭认为从人类思维和艺术思维的观点来看,《红楼梦》包含三个叙述层次:一是石头无材补天,便幻形入世,堕落情根,投胎于贾府中,怡情于大观园里,二是“太虚幻境—大观园”的叙述层次,它是“薄命司”的象征,是石头堕落之处,宝玉痴情之所;三是“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的“空—色—空”的叙述层次。参见陈维昭《〈红楼梦〉的叙事结构》(《红楼梦学刊》1991年第2辑)。另,张洪波把《红楼梦》的叙述层面分为五个:超叙述之“创作”层面、元叙述之“文本”层面、主叙述之“故事”层面、次叙述之“人物”层面、微观叙述之“心理”层面。参见张洪波:《试析〈红楼梦〉叙述层面的多重复合特点》(《红楼梦学刊》2005年第2辑)。
⑧ 第一回甲戌本在此处有眉侧批曰:“若云雪芹‘批阅、增删’,然则开卷至此这一篇《楔子》又系谁撰?足见作者之笔,狡猾之甚。后文如此处者不少。这正是作者用画家‘烟云模糊法’处。观者万不可被作者瞒蔽了去,方是巨眼。”或者正是担心读者会跟随石头进入故事,忘了曹雪芹才是作者,脂批故非得用此批语做一点醒。
⑨ 石头从神界之“石”出发变形为俗界之“玉”,再回归为神界之“石”,构成了小说主角石头“出发(石)—变形(玉)—回归(石)”的生命循环三部曲。参见梅新林《红楼梦的哲学精神》(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6页)。
⑩ 赵毅衡《当说者被说的时候——比较叙述学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70页。
[11] 刘勇强《一僧一道一术士——明清小说超情节人物的叙事学意义》,《文学遗产》2009年第2期。
[12] 梅新林《红楼梦哲学精神》,第39页。
[13] 郑红枫、郑庆山《红楼梦脂评辑校》,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版,第311页。
[14] 俞平伯《旧时月色》,《俞平伯论红楼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139页。
[15] 余国藩《〈红楼梦〉、〈西游记〉与其他》,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177页。
[16] 项仙君《论红楼梦前五回的叙事方式与结构意义》,《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1993年第4期。
[17] 陈维昭《〈红楼梦〉的叙事结构》。
[18] Wayne C.Booth,Distance and Point-of-View:The Theory of the Novel,edited by Philip Stevick,The Free Press,1976,p.92。
[19] 赵毅衡《叙述者的广义形态:框架——人格二象》,《文艺研究》2012年第5期。
[20] 参见拙作《从〈金瓶梅〉到〈红楼梦〉——明清小说从“欲”到“情”的动态演变》(《红楼梦学刊》2019年第2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