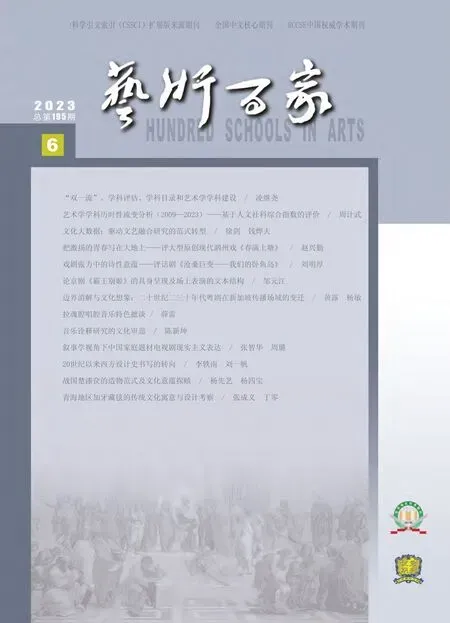青海地区加牙藏毯的传统文化寓意与设计考察*
张成义,丁零
(1.青岛大学 纺织服装学院,山东 青岛 266071;2.南京师范大学 美术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
一、青海加牙藏毯艺术的传承发展与实用价值
藏毯起源于我国青藏高原,是世界三大名毯之一。作为藏毯代表的青海加牙藏毯工艺有着悠久的历史,它以独特的形式、艳丽的色彩、浓郁的民族特色而闻名遐迩。其浓厚的地域文化特色,不仅彰显了青藏地区的民俗文化内涵,更在我国少数民族工艺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然而,在现代工业化的冲击下,如今这门古老的以家族式传承为主的手工艺也不可避免地面临着难以传承的命运。进入21世纪,现代社会的新环境和新时代的发展任务对于传统工艺的发展提出了新要求,在艺术价值方面需开启新探讨。随着经济社会和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人们对精神和物质文化的需要也发生了变化,工业化大机器生产占据主导地位,给藏毯的传承发展带来了巨大冲击。近年来,随着我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视,藏毯重新走进大众视野。然而,受诸多因素制约,藏毯的传承发展却困难重重;其市场需求持续低迷,亟待革新。
(一)加牙藏毯艺术的传承发展
青海藏毯的历史可追溯到3000多年前。根据吴汝祥《青海都兰县诺木洪搭里他里哈遗址调查与试掘》,1959年我国考古人员对青海省海西州都兰县诺木洪搭里他里哈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其中出土了大量公元前10世纪的毛布及其制品。这不仅是青藏高原发现的最早的用毛线平纹织成的地毯,而且也是我国发现的最早的毛织品实物。[1]39-403000多年前青海藏族人民不仅驯养牲畜,还掌握了原始藏毯的编织技艺和染色技术,可织出几何图案的彩色毛席,即编织地毯。这种地毯经纬紧密,毛簇匀整平齐。通过地毯残片可见“8”字结毛线编织技术,它们证明了青藏高原是世界上最早制作编织地毯的地区。
由于高原的特殊地理环境,藏族先民形成了独特的生活方式。随着畜牧业的兴起以及兽毛、兽皮在日常生活中的广泛应用,先民从动物身上汲取灵感,将动物毛发捻制成线,再将这些毛线交织在织物成品上。这就是栽绒地毯的萌芽。用这种编织方式制作的织物质感厚实,更具有保暖性、舒适性和耐久性。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从最初用植物茎叶编织到用毛织物编织,毯子的制作材料得到了改良,技术也有了极大提高。
明末清初是加牙藏毯的成熟期。清代康熙年间,著名藏传佛教圣地塔尔寺扩建,寺院装饰、僧人诵经亟需坐垫,于是附近的湟中县加牙村便开始为其制作藏毯。这促进了藏毯的发展兴盛,壮大了加牙藏毯的制作规模。塔尔寺的多次扩建和中央政府需求的不断增大,也对加牙村传统手工藏毯规模的进一步扩大产生较大影响。《湟中县志》记载,清代嘉庆年间(1796—1820),宁夏地毯工匠“二马”来到加牙村,村民马得全和杨新春拜师学艺。这两位工匠教授地毯编织技艺,使得藏毯的编织得以规范化。[2]133
清代道光年间,青藏高原喇嘛进京,将藏毯作为珍贵供品敬献给道光皇帝,深得他的喜爱。藏毯和当地编织技术逐渐融合,制作工艺得到改进,出现了竖毛集束起绒的编制手法,藏毯编织工艺得以丰富。因此,在清末到民国初的一百年间,加牙村逐渐成为一个著名的藏毯专业村。1913年(民国二年),加牙村成立了一所专门织毯的职业学校,与村民一起致力于藏毯织造。当时藏毯在湟中以及甘肃武威等地的年销售量达到了6000多条。到20世纪80年代,加牙村的藏毯已享誉全国,甚至走向国际,出口到尼泊尔等地。2006年,“加牙藏毯织毯技艺”被国务院列为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杨永良是加牙村传统藏毯手工艺第七代织毯传人,被认定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2013年,加牙村建立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习所。高原藏毯编制技术不断发展,持续吸收其他民族的先进编制技术,极具地域特色和民族特色。
近年来,青海省西宁市文旅局持续开展传承人研习培训班,加强非遗人才培养,传承地域民族文化特色,推动青海特色产业发展,促进加牙藏毯非遗创新工作,强化非遗融合赋能,助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在建党百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在调研青海时强调手工藏毯的重要价值,并表示“一定要传承弘扬好”藏毯工艺。
(二)加牙藏毯艺术的实用价值
青海藏毯在青藏高原地区被广泛使用,几乎家家户户都在使用藏毯,从起居室内的坐垫、地毯,卧室内的炕毯,到游牧民常用的鞍毯等等,藏毯是高原生活的必需品,兼具家具实用与艺术审美功能。按用途及使用场合划分,藏毯一般可以分为两大类:寺院用毯和民间生活用毯。寺院用毯,一般根据功能不同而有不同的细分,如禅毯、幡毯、柱毯、法舞毯以及门帘毯等。寺院藏毯既具有实用性又能传达佛教信息,图案和配色极为讲究,常见有龙纹、佛、八吉祥、金刚杵等具有宗教象征意义的图案。塔尔寺内古老的加牙藏毯随处可见。大经堂是塔尔寺内僧众每日集中诵经礼佛的重要场所,殿内的108根柱子均被“龙抱柱”式藏毯包裹,其上遍布云纹、龙纹等佛教祥瑞兽纹样。大殿里铺就一条条长达数十米的拜毯。寺院用毯兼具宗教象征意义和日常实用功能。寺院殿堂内阴暗潮湿,僧众进入活动场所不允许穿鞋,因此加牙藏毯制作得非常厚实,在僧人诵经时起到保暖防潮的作用。
民间生活用毯主要用于普通藏民家居环境中,一般以卧室的炕毯、坐毯和卡垫等最为常见。在传统藏族家庭中,人们通常会在房间内沿墙一圈或者沿两面或三面墙摆成直角形木制底床。床上铺着各种用毛或草絮制成的基垫,再铺上一层卡垫。这些床供人白天坐卧,晚上就寝。夏天外出或“过林卡”①时,卡垫可直接铺在地上当做坐垫。一些条件比较好的家庭还会使用一种类似椅垫的“毯上毯”。[3]122这样做既能保护卡垫,也能体现对贵宾的尊重。古代藏族上层人士聚会时,家中卡垫层数代表着官职和身份。民用毯配色大胆,其中常见的图案有花卉、吉祥瑞兽(龙、凤、虎、雪狮、鹿、鹤)、几何纹饰等。除了居家装饰毯,藏毯还用作马垫鞯,又称“马褡子”,是典型的集实用性与装饰性于一体的藏毯类型。青海海拔高,部分地区气温常年偏低。商队往来于茶马古道,马背上铺的藏毯要求结实耐磨,保暖效果良好,同时鲜艳多彩的马褡子也可以让人快速清晰辨认出自己的马匹。为了增强实用性,马垫鞯多为贴合马背、不规则的曲线造型,并且采用皮质包边设计。
二、传统加牙藏毯的材质与传统文化寓意
青海加牙藏毯的特点是材料优良、工艺精湛、图案丰富清晰,洗后似锦缎,剪后如浮雕。其原材料多为藏系绵羊毛、山羊绒、牦牛绒、驼绒等。加牙藏毯工艺讲究,采用的是植物染料染色、低温洗毯,织出来的毯子色泽艳丽,弹性好,不脱色掉毛。
(一)天然优质的羊毛及染色材料
青海位于世界海拔最高的青藏高原,拥有丰富的天然草场,面积达4186.7万公顷。青海盛产藏系绵羊毛(俗称“西宁大白毛”),其具有纤维长、毛色纯白、光泽度强、织密性高、弹性好、耐酸碱性强等优点,是目前世界上粗毛型地毯毛中品质最为优良的品种之一。“中国织毯羊毛以青海西宁的羊毛最好,弹性、染色性、可纺性、抗缩绒性都为全国之冠,是地毯栽绒最好的原料。”[4]251由“西宁大白毛”编织成的地毯坚韧耐磨,质地柔软,富有光泽。在藏毯编织过程中,经线需选用弹性好、结实的上好棉线。一块藏毯的编织过程历时几个月到几年不等,在编织过程中容易拉断织线,而上好的棉线可以有效避免这种意外情况。
传统加牙藏毯均用天然、无污染的颜料进行染色。主要颜料全部从青藏高原当地的植物、矿物中提取。其中部分颜料属名贵中药材,如板蓝根为蓝色,草红花、藏红花为红色,苏木为浅棕色,核桃壳、橡壳为驼色,槐米、大黄为黄色,茜草根为浅红色。植物染色的最大优点是色泽自然柔润,非常接近天然毛色,上色度高,颜色鲜艳而温和,颜料不伤毛质,经久耐用。[5]212
(二)加牙藏毯的图案寓意
加牙藏毯的宗教色彩浓郁,图案种类丰富多彩,按照构图可分为5类:江垫式、龙凤式、满地铺式、城廓式和嘎雪巴式。②江垫式构图灵感来源于锦缎上缠枝的西蕃莲式波状图案,织于卡垫之上。此类图案形式单一明了,特色鲜明。此外还有其他以锦缎为灵感的相似构图,但不如此类图案有代表性。龙凤图案卡垫分为二龙戏珠、龙凤呈祥、穿云龙、二龙逐凤、蛟龙闹海、凤凰戏牡丹等样式,其纹样也来源于锦缎,并在长期发展中形成了对称性的龙、凤、云、花、水等组合形态。满地铺式图案的纹样灵感来源广泛,如藏靴的绣花纹样、古代中原的绣花、藏族建筑装饰、印度丝绸和织锦纹样等。其特点是纹样布满全毯,分布均匀,通常无边。整个图案往往形成2~3个较为明显的节次,具有向心性。城廓式图案的特点是有边框装饰,带有丁字纹边缘,形如城廓。最常见的城廓式图案形式包括锦纹盒子边(盒子里多为暗八仙、佛八仙、国王七宝或三者混合的纹样)、水纹边、花草边等。嘎雪巴·曲杰尼玛(江孜贵族,曾任西藏地方政府的噶伦)对卡垫图案感兴趣,通过对内地近代丝绸刺绣的研究,吸收了剌绣被面和剌绣衣料上的大花大叶以及整枝花的形式,并结合卡垫的生产工艺特点,创造了嘎雪巴式图案。嘎雪巴图案特点是自由流畅,形象色彩突出,花纹分布均匀,四角有四块水纹,包含大朵大枝、三点交错、两点对称排列等花卉图案。[6]40
受独特地理位置及民俗文化的影响,青海加牙藏毯的图案和构图具有浓厚的安多地区藏式特色。青海是安多藏族与汉族等多民族的聚居地。受历史和地理环境的影响,安多藏区和康巴藏区在藏毯编织技艺和图案题材上存在差异。比较而言,康巴藏区更多地保留了传统藏毯的编织技艺,而自清代以来的长期民族交融,使加牙藏毯图案表现出藏汉文化融为一体的特点。加牙藏毯既有表现传统藏传佛教题材的纹样,例如吉祥八宝纹、法器图案等,也有老虎、雪狮、鹿等寓意雪域吉祥的瑞兽图案,同时还大量出现寓意汉族吉祥的龙凤、牡丹及传统汉族边饰纹样。改革开放以来,反映现代生活的图案形式出现。
加牙藏毯艺术文化底蕴深厚,它不仅印证了不同时期少数民族手工艺生产力的发展,更记录了藏族同胞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加牙藏毯在清末民初发展迅速,无论是技术工艺还是生产规模都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不仅如此,加牙藏毯的整体布局构造不仅延续了传统理念,更在此基础上融合创新。因此,进一步研究各个历史阶段的加牙藏毯作品,深挖其中所蕴藏的历史文化特点及地域民俗文化内容,能够深化我们对少数民族非遗手工艺文化脉络、文化价值的认识。一幅完整的加牙藏毯作品不仅仅是一张摆在青藏地区千家万户中的地毯,更是一幅描绘雪域之巅的画卷,是一种象征、一种精神,具有深厚寓意。
其一,宗教题材图案。佛教文化思想体系宠大,反映人类对生活的体验、理解和愿望,是人类思想文化的精华,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藏传佛教是藏族人民的主要信仰,也是藏族地区占主导地位的宗教,对藏族的影响是广泛而深远的。最常见的宗教主题藏毯的表现形式有吉祥八宝、佛像、礼仪密宗器具等。
吉祥八宝图,又称“扎西达杰”,由八种藏传佛教法器组成。[7]2这八种纹样是藏毯的重要题材,其寓意各有不同。最常见的八宝图排列方式是将八种纹饰并置于地毯中心位置,上下依次排开,如青海博物馆所藏驼色地八宝纹卡垫(图1)。这个卡垫将八宝纹放置在画面的最中心位置,主体物周边环绕以祥云彩带。毯周则围绕以传统“工”字纹及藏族传统吉祥色,配色大气,寓意吉祥。八宝纹有时装饰于地毯边缘,如喇嘛吹海螺图[8]16(图2)中主体人物周围的装饰,既丰富了画面内容,又统一了主题思想。此外,八宝纹样以连续纹样的形式,装饰于城廓式藏毯构图的边缘。

图1 驼色地八宝纹卡垫,藏于青海藏文化博物馆,图片来源:笔者拍摄(左);图2 贡毯喇嘛吹海螺图,80cm×230cm,图片来源:南文魁《藏毯》,青海民族出版社2014年版(右)
其二,花卉题材图案。花卉题材纹样是中国传统纹样的重要组成部分,被广泛应用于藏毯设计中。由于青藏高原地处高寒,气候恶劣,植物种类十分单一,艳丽的花卉难以生长,人民只能将美好的希望寄托于鲜艳的色彩中。藏毯中莲花和牡丹最为常见,或单独出现,或铺满全毯,或与其他类型图案组合出现。
明清两代的皇宫,一度出现“凡地必毯”的辉煌景象。[9]7由于统治阶级对地毯的喜爱,牡丹纹样被频繁运用于藏毯中。除单独以对称的折枝牡丹图案出现外,还有组合题材图案,如“龙凤牡丹”“凤凰戏牡丹”等。在满地铺式藏毯中,牡丹缠枝图案也被广泛应用,铺满整个地毯,呈现出繁花似锦的视觉效果。清代专供宫廷使用的藏毯常用多种花卉纹样进行组合搭配,并结合中原文化,其配色沿用藏区鲜艳大胆的特点,这是因为颜色使用制度严格,皇室贵族多使用黄色、杏黄、杏红、正红色等。
其三,瑞兽题材图案。“万物有灵”是所有原始宗教的普遍观念,在藏传佛教中虎、龙、凤、鹿、雪狮等都是千百年来流传至今的吉祥瑞兽,它们都有着独特的美好寓意。人们将带有吉祥寓意的神兽织在藏毯上,寄托对未来的美好期许。
虎在藏族文化中是无畏、力量与实力的象征,在藏毯中多以单体形象出现。人们相信虎皮能以怒相吓退牛鬼蛇神,保护主人、居室、寺院平安。早在5000年前,西藏阿里地区先民将老虎、豹子等纹样符号镌刻于大山之上,这种符号逐渐演化为盛大祭祀典礼符号标志,这种崇拜在藏地得以延续。文献记载,虎皮纹饰地毯距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老虎虽不是藏区本土动物,但作为吉祥瑞兽在藏传佛教教义中地位甚高,因此藏区人民在家中悬挂虎皮纹样藏毯以镇宅辟邪,寄托美好愿望。藏地虎毯传承至今仍然保留着高饱和度、强对比度的形式特点,民族风格强烈,极具视觉冲击力,是传统加牙藏毯艺术的典型代表。
清代汉藏文化交流频繁,藏毯得以走出雪域高原,出现了大量新题材。龙凤纹样、仙鹤纹样等最为常见,它们或单独出现或以组合形式出现。清代藏毯被广泛用作贡毯装饰宫廷。龙象征帝王,在藏毯中龙纹频繁出现,这类龙纹题材包括团龙戏珠、二龙戏珠、龙凤呈祥等。
其四,文化融合题材图案。费孝通先生曾提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思想。藏毯艺术是这种思想理念的形象表征。加牙藏毯中文化融合现象是不同民族文化共存共生、相互影响的见证。藏青地团鹤纹方形卡垫的四角处描绘了腾云而上的蝙蝠,每两只蝙蝠之间以如意云纹作为装饰,突出了中心的团鹤图案。(图3)蝙蝠在汉民间艺术中象征福气,如意云纹代表如意和好运,而团鹤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象征长寿。因此,整个卡垫的主题是长寿和吉祥。无论是如意云纹、蝙蝠图案还是团鹤图案,它们都是汉族传统文化图案,而这块卡垫体现了汉藏文化相融的特点。

图3 藏青地团鹤纹方形卡垫(左);
驼色地暗八仙团鹤纹卡垫(图4)上采用两种不同文化的符号性图案的组合搭配方式。四个角落的大边饰使用蝙蝠图案,而其他部分则采用藏八宝图案,这是藏族人民非常喜爱的图案。中央图案是一只口衔“三多”的团鹤,周围环绕着暗八仙图案和福寿“三多”图案。这组装饰图案中,藏八宝图案代表藏传佛教文化,暗八仙图案代表中原道教,而团鹤和福寿“三多”图案则代表中原民俗。这种在一张毯子上同时出现藏传佛教文化图案和中原汉文化图案的现象,是汉藏文化相融的结果,也是明清河湟地区文化交融的体现。

图4 驼色地暗八仙团鹤纹卡垫(右)(图片来源:青海藏文化馆)
(三)加牙藏毯的色彩寓意
加牙藏毯的色彩搭配保留着纯正的传统藏式风格。早在千百年前藏族就已形成了独特的色彩观念,不同颜色有着不同的寓意、次重和等级,其中最常用和最受尊崇的主要有白、蓝、红、黄、绿等。这五色是藏族原始宗教苯教中代表五种本源的象征色,后来被佛教所借用:蓝色代表天,白色代表云,红色代表火,黄色代表地,绿色代表水。藏毯的常用底色有红、黄、黑、藏蓝、藏青和深紫等。红色被藏族先祖赋予神秘力量,象征光明、太阳,能驱邪避灾。在藏毯的底色中以大红、朱红褐色较为常见。[3]118在藏传佛教中黄色又被称为“喇嘛色”,是神圣、至高无上之色,是高等活佛袭用的颜色,因此在民间有所禁忌。在藏毯中黄色一般用于高等活佛的坐垫与靠背上。而黄色系中的各类土黄、驼色以及米色则没有使用禁忌,是最为常见的民间藏毯底色。土黄、驼色给人以温暖、安宁的视觉效果,多用于装饰居民客厅、卧室。黑色在藏传佛教中代表“护法”,象征护法神的神职与威严。将黑色作为藏毯的底色,在视觉上具有沉静、庄重的效果。除红、黄、黑三种颜色外,将藏蓝色、藏青、深紫三种颜色作为底色的藏毯也十分常见,整体色系都与千年来藏族工艺古朴又不失华丽、新颖又保留传统的风格相一致。
三、加牙藏毯艺术的当代设计考察及传播途径
2006年,加牙藏毯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发表讲话时提到:“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决定了中国各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和谐格局,决定了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这给加牙藏毯艺术设计的现代转化及国际传播途径提供了理论指导。然而,加牙藏毯的发展依旧不容乐观,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迫在眉睫。
(一)加牙藏毯艺术的当代设计创新
第一,创新技术、材料和工艺。传统的加牙藏毯通常使用羊毛作为主要材料,未来可以在保留主体材质及效果基础上,考虑加入部分其他纤维材料或混合材料,如棉、麻、丝或合成纤维以创造出不同的质感和效果。同时,探索新的工艺技术和处理方法,如染色、织造、编织技术,进一步提升加牙藏毯的制作效率。
第二,创新图案和色彩。传统的加牙藏毯常常以自然元素、动物或几何图案为主题,可以尝试融入现代主题或符号。使用现代科技元素、城市景观、当代符号表达现代社会的观念和价值;吸收和借鉴中亚、南亚、中东、欧洲等国家和地区地毯的色彩搭配和图案设计,展现具有民族性而不失世界化的审美特征;通过运用造型简洁、线条清晰的几何图形,或者将传统图案进行抽象化处理,以打破传统的形式和结构,创造现代感。
第三,激发功能性创新活力。激发加牙藏毯艺术的全新功能,制作应用于现代生活的设计作品,或者使之成为展览中的艺术品。设计适用于家居装饰的地毯、抱枕、墙挂等,将加牙藏毯艺术融入日常生活;举办加牙藏毯艺术展览和展示活动,将其介绍给更多艺术爱好者;通过在艺术馆、画廊、文化中心等举办展览,邀请专业人士、学者、观众参与交流和讨论,加强与不同国家地区、不同文化背景的艺术家、机构的合作;通过文化交流活动、合作项目、艺术家驻留计划等形式,促进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互鉴。
第四,讲好中国藏毯文化故事。在加牙藏毯的设计中融入故事性元素,赋予作品更深层次的意义,引发情感共鸣。通过图案、图像、符号讲述藏毯故事,将消费者的思绪带到雪山绵延、天空澄澈、美丽而神秘的青藏高原,让都市居民感受藏地原始而勇猛的力量,驰骋想象,体验与自然共生。通过对藏毯的现代化创新设计记录中华文化的生生不息和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编织新时代的藏毯文化故事。
(二)元宇宙展厅的创新性传播实践
古代中国藏毯的传播及影响力倍受时空制约,使内陆、沿海地区的绝大多数普通消费者无从了解。而当下,根据市场调研,青海加牙藏毯仍停留于传统的销售模式。好在国内已涌现出一批新藏毯品牌,比如“山赴品牌”(Atelier Changphel)除了在作品内容上与国际知名艺术家联名外,还在传播、营销上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使藏毯频现于各大自媒体社交平台,走进元宇宙展厅,吸引了更多年轻观众。
山赴品牌在展陈方式上尝试使用元宇宙概念,建立元宇宙品牌展馆,观者可穿梭于虚拟世界,实现沉浸式体验,感受传统手工藏毯的艺术魅力。元宇宙在同步性与高拟真度、开源与创作、闭环经济系统及永续发展等方面极具特点,这为非遗传承提供了新的解决思路。数字科技赋能藏地纹样和编织技艺,使之具有沉浸感、互动性和体验感。传统实体艺术与前沿科技媒介相互作用,使观者在视觉体验中感知现实与虚拟的边界,想象未来艺术。元宇宙技术突破文化传播地域、空间的限制,使非遗文化更好地融入现代城市生活。年轻消费者得以通过元宇宙了解藏毯。将非遗产品进行数字化改造,可以为全社会提供数字化建模服务,创造个性化、时尚化、数字化藏毯产品,为藏毯的发展传承提供新思路。
(三)加牙藏毯在现代家居中的应用
藏毯作为藏族人民生活中的必需品,如同藏民性格那样粗犷、自然、古朴。传统藏民家中式样各异的生活用毯随处可见。但经笔者实地考察发现,当地已鲜有专门售卖传统手工藏毯的门店,传统手工藏毯的消费群体多局限于当地藏民,影响大多还停留在青藏地区。创新设计符合现代家居使用场景要求的新式藏毯迫在眉睫。
经过前期对市场上藏毯创意设计产品的整理和归纳,笔者发现,传统藏毯因载体的限制,在图案应用中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因此将传统加牙藏毯元素转化为数字形式,其载体将会得到进一步扩展。得益于现代技术,藏毯元素呈现于多种载体之上,如运用打印技术、激光雕刻技术等以突破传统的羊毛织物的材料限制;建立图形纹样电子数据资料,在图案实验创作中选取素材。笔者经过图案、色彩的提取、重组、创新,完成系列家居设计方案。将家居产品如地毯、空间隔断等作为应用对象,通过整体图案、局部图案的展示及变化创造不同的设计风格。同时,方案打破藏毯的平面展示形式,达到全新的互动性展示效果,兼顾藏毯的功能性、观赏性、时尚化。创新设计方案《雪域灵虎》灵感源于古老藏毯中的虎元素。虎在藏族文化中是力量的象征,虎毯在藏毯中最具代表性。因此,笔者经过前期调查研究,选取传统青海加牙藏毯的主体老虎图案,融入藏族传统五色,使其不失传统、形式内容丰富。此方案包括地毯、空间隔断等家居用品。
其一,地毯系列。地毯系列通过不同尺幅地毯的表现形式,结合上文对图案进行重组排列、分解重构;重新排列组合传统藏毯纹样中的祥云纹样,使之嵌入现代时尚图案、几何波普纹样之中,运用波普几何元素的视觉效果打破传统藏毯的视觉节奏,使之更具层次感、冲击性。(图5)

图5 创新虎纹地毯在家居场景中的运用,图片来源:笔者绘制
其二,空间隔断系列。空间隔断系列根据不同场景的个性化需求,结合上文图案设计进行重新组合排列、分解重构,打破传统形制,创新构图形式,采用现代几何元素构成形式对藏毯进行规则或不规则的分割、变形,增强藏毯的趣味性、时尚感。
四、结语
充分挖掘和创新具有中国特色的传统手工艺,是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和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路径。非遗手工艺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形成民族凝聚力、提高文化自信有重要作用。非遗手工艺的再设计应重点把握手工艺物质形态与文化抽象形态的深度融合,系统梳理非遗手工艺的内在文化脉络。本研究旨在探索传统手工艺的再设计,从文化构成角度出发思考藏毯在当代艺术中的发展定位:分析非遗手工艺的艺术特征和青海加牙藏毯的历史审美、图形分类、材料工艺、文化寓意及其现代应用。藏毯不仅表现出我国传统的民族文化艺术特色,更蕴含着独特的青藏高原地域语言。加牙藏毯主题图案丰富多样,在题材上表现出藏汉文化融为一体的独特风格,不仅有反映藏传佛教的宗教类题材,也有大量表达汉民族美好寓意的民俗题材。加牙藏毯具有强大的艺术生命力,是民族文化大融合的缩影。
探索藏毯的传播推广路径,建立元宇宙地毯展览馆以实现数字化改造,能够打造、传播更多个性化数字藏品,更好实现保护传承。藏毯产业的个性化、时尚化、数字化产品为藏毯的传承发展带来了新思路。在整个设计实践过程中,重组藏毯元素,探索藏毯元素的新形式,须要尝试转化多种现代艺术表现形式,以现代家居产品为载体探索藏毯图案的创新应用及发展路径。
① “林卡”在藏语中义为园林,“过林卡”即郊游、踏青,是藏族人民最普遍的休闲娱乐方式,多在每年6-9月间开展。
② 《非物质文化遗产:青海加牙藏毯》,中国藏族网通,https://www.tibet3.com/tibetcul/content/2011-01/27/content_449337_4.htm,2011-0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