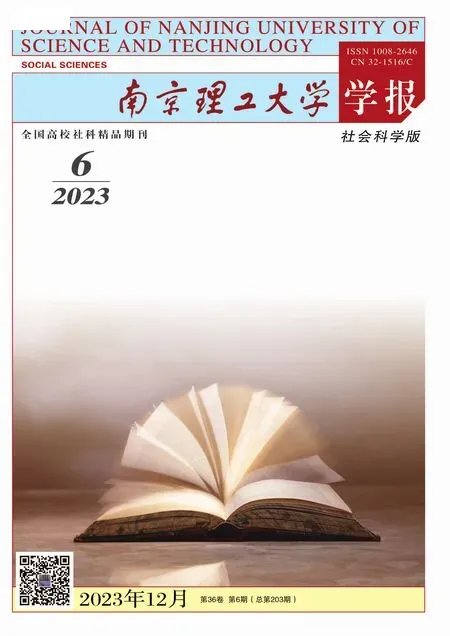美术作品中母爱题材创作动因及风格类型
魏骏瑶
(南京师范大学 美术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7)
艺术创作中母爱情怀是现实世界母与子关系的反映,自古以来一直都是艺术家颂扬和表现的对象和题材。广义地看,母爱题材可以延伸到女性对人类、自然、动植物、社会等方方面面的关爱。母爱是伟大的,它包含了极其广泛的内涵,既有人类情感的普遍性,表达了慈爱、奉献、勤劳、善良、坚强等丰富的寓意,同时也受制于社会经济、文化、政治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艺术家根据不同的创作对象、场景及感受,用个人视角观察并进行艺术加工,使得母与子的主题呈现出不同的艺术风貌。从图像出现初始,母爱题材就是其灵感来源,正是母爱题材的不同表现形式,丰富了研究社会文化历史变迁的路径方法。母爱根植于千姿百态的社会现实生活,是艺术创作的来源,赋予了艺术家鲜活的创作题材和艺术灵感,把艺术情感融入作品创作活动中,为社会大众带来美的感受。
一、母爱情怀贯穿艺术发展的历史进程
母爱情怀伴随着社会的变迁而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反映了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程度。史前文明的母与子关系虽然没有具体的文字记载,但从遗留下来的美术作品中也能够窥见一斑,这些带有实用性的艺术形象向人们展示了先民们的技艺和智慧,也表达了对女性生殖能力的颂扬。约公元前28000至25000年的《维纶多夫的维纳斯》展现的是女性壮硕的身体、丰满的乳房等器官,暗示其生育能力,表达人类繁育后代的美好愿望,几何形状的组合结构构成自然和谐、饱满的体量感,特别是在面部的减省处理上有一定的现代主义美术的抽象特征,这种创作风格为后世艺术创作带来了灵感。现存于希腊斯蒂里斯圣路加隐修院卡索利孔教堂的镶嵌画《宝座上的圣母子》(约1020年),画面仍采用平面化处理,圣母身着象征神圣、高贵的蓝衣,背后的金光暗示天国的上帝,成人面貌的耶稣端坐于圣母腿上,画面整体显露出庄严肃穆的气氛。圣母的形象及表现出的母爱情怀超出了世俗母与子的关系,更多的是展示宗教的神圣,几乎没有世俗女性的审美风格。整体上看,宗教精神多于艺术的表现。现存佛罗伦萨皮蒂美术馆的拉斐尔作品《座椅中的圣母》(约1516年),则充分表现了文艺复兴盛期的人文主义精神,画面营造了温馨、亲切、圆满,流畅、细腻的氛围,其中母亲紧紧环抱孩子,母子间紧凑的关系以及母亲呈现保护者状态的肢体语言展露无遗。同时,圣母和耶稣外视的眼光、约翰仰视的眼光与合十的双手,成为圣母形象的标准定式。从每个时代不同的母爱题材作品中,可以追溯其背后的社会等级制度、文化习俗、生产水平等,由此,能够对艺术创作活动与社会发展的关系给出有效的阐释,如古希腊时期普遍流行男尊女卑的观念。现存的一些书籍插图中描绘的妇女坐在织机边劳作,而男性威武地站立一旁的权威形象就是对这种观念最直接的诠释。值得注意的是,早期西方包括绘画、诗歌、小说等艺术类别的发展中,所描绘的女性形象、母爱形象、母子关系往往强调的是女性的从属地位,正如玛丽·比尔德所指出的那样,“在我们所知的西方历史的最早阶段,无论在现实、文化还是想象之中,女性和权力间都存在一种彻底的分离。”[1]
对母爱情怀的刻画是艺术家表现美的一种方式,它指代了母亲对子女的爱护、关爱、照料等基本的母爱行为,进一步看,母爱还可以预示和平、丰饶、宽容、勤劳等女性身上共同的品质。艺术家把母爱题材当成美的载体和表现路径,借此向世界传达真善美的信息,引导社会大众发现美、鉴赏美。在中西方美术发展的历程中,母爱都是艺术家热衷于表现的主题,文艺复兴之后,母爱题材的作品不仅受西方上流社会推崇,也是艺术家展现劳动妇女生活的重要素材。母爱题材反映的作品美的内涵十分广博,西方世界的艺术作品一方面表现上层社会的高贵,形成了一种超凡脱俗的美,另一方面,在表现劳动大众的母子情怀时,又显得真实可亲,进而启发观者对劳动女性和其子女的赞扬和同情。在中国古代的美术作品中,母爱情怀更多地是表现道德行为规范,大多传达了人类对美好社会、生活的追求,而女性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往往是对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的遵从。例如,《女史箴图》是以图形的方式为封建社会女性树立标准,尽管母子关系的图像风格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但是,中国古代对女性的家庭和社会定位有着严格的标准,贯穿其间的基本道德理念没有发生本质变化。巫鸿指出:“《女戒》把女子立身的准则总结为“妇德”“妇言”“妇容”和“妇功”四项。虽然每项着眼不同,但四者实际上相互联系、对儒家理想女性来说缺一不可。”[2]现存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女孝经图》描绘的是唐代邓氏《女孝经》前九章内容,画中仕女身着素装,神态雍容大方、端庄优雅,生动地图解了母仪、贤明、仁智等封建妇女必须遵守的道德规范。此幅作品主要的观赏对象为封建女性,灌输的是女性道德标准,起到了一定的教化作用。“美育培养的人文素养主要指对艺术有一定的文化理解能力,具备高雅的生活情趣、超越私欲的宽阔胸怀和超越世俗的精神气质,这种通过学习高雅艺术养成的人文素养实际上是学生道德成长的坚实而真诚的情意基础。”[3]
母爱情怀的艺术图像具有广泛的社会文化接受性和情感渗透性,社会大众对美的接受更容易通过图像的形式来实现,除了传递图像的主题寓意外,艺术图像还能够引起美的愉悦。一旦特定时期的图像模式固定下来,社会大众的审美偏好也随之形成,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中世纪的母子图像比较僵硬,而文艺复兴时期的图像比较自然亲切。如17世纪荷兰的母与子的绘画形式,往往是通过表现母亲特定的动作形成母与子的互动关系,德·霍赫、特鲍赫等都致力于荷兰风俗画的创作,“两位都忠实于当时荷兰的绘画精神,而且,即使一位生活安逸,另一位穷困潦倒,他们都歌颂了眼前所见的事物。”[4]具体的艺术作品表现了母亲的平静以及孩子的活泼,而且孩子往往处于视线的中心,这种模式成为荷兰那个时期的范例,带有明显的可识性,在荷兰人的日常生活中流行开来。由此可以推断,艺术作品的接受程度与现实生活的关系密不可分,只有在对生活深入观察的基础上,才能创作出为社会大众喜闻乐见的作品。任何美术形式的图像结构都有一个预成的过程,表现出艺术发展的自律性,如欧洲美术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古罗马古希腊时期,也能够进一步地追溯到埃及的美术形式。每一种美术形式都有其发展繁荣和演变的过程,艺术正是在不断的吸收借鉴和创新中构造了新的艺术形式。康定斯基认为:“每个艺术就是这样在相互渗透,这种渗透只要利用恰当,就可以产生真正不朽的艺术。”[5]艺术渗透不仅体现在同一种艺术类型之内,而且常常发生在不同的艺术门类间,从艺术传播的角度看,可能带有更为广泛的内涵,也更具感染力,进而引导公众审美观的走向。
母爱情怀根植于深厚的社会经济文化土壤之中,艺术发展所受的影响因素众多,而社会经济文化是其中十分重要的条件。意大利文艺复兴的产生除了彼得拉克等人文主义者提出了人性解放理念、促进了人的觉醒外,当时意大利的商业、贸易经济比较发达,资本主义的萌芽已经初步显现,也为文艺复兴提供了物质条件。在这些因素的综合影响下,母与子的关系在艺术作品的表现上就呈现了更加生活化的一面。拉斐尔《西斯廷圣母》描写的是圣母子的故事,采用了稳定的三角形构图,但是,与中世纪的圣母子图像相比,拉斐尔的圣母子图像的表情显得更加亲切,凸显了文艺复兴所倡导的人文主义精神,这种创作风格的改变与当时的赞助体系有关。由于社会大众及新兴的资产阶级的经济实力增强,在艺术领域的话语权也得到加强,他们鉴赏品味更加趋向于人文主义的审美取向,这种变化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决定作品的风格。同样,一些教会的赞助者能够左右教堂艺术品的创作,并用新的人文主义理念影响艺术家的创作活动。艺术风格的形成同样受制于社会制度及文化的引导,17世纪的法国,路易十四大力推行发展艺术的政策,扶持古典主义美术风格。把艺术作为服务王权和宫廷的工具,再次引发了古希腊古罗马艺术的复兴,形成了带有较强理想主义色彩的法国古典主义风格,普桑的《台阶上的圣母》几乎背离了传统宗教画的手法,以圣母子等人物组成稳定的三角形结构,圣母像世俗母亲一样环抱着孩子在自己身上站稳,动作自然仿佛是在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的场景,体现了母亲对孩子的关爱之情。画家遵循古典艺术之规范,画面融自然、庄重、静谧与一体,但人物的神态、动作却充满了现实世界人性的光芒。
二、母爱题材图像的风格类型及审美特征
美术作品的风格是分析研究图像的基础方法,西方绘画中有关母爱或母与子的题材比较广泛,风格模式多元化。在综合形式因素、时代背景、艺术流派等多种因素的基础上,可将母爱情怀或母与子的关系图像分为5个风格类型。
1.原始崇拜型。绘画元素的产生可以追溯到史前的抽象图形,这些图形的产生是史前人类活动的产物,“原始人类从事的实践活动,可能既是巫术活动,又是活动,同时也具有生产劳动的性质。”[6]人们试图通过对超自然力量的崇拜,来解决由于生产力极其低下、缺乏对世界的科学认识造成的生活状况,而超自然崇拜的结果造就了艺术的最初雏形,从已发掘出来的史前雕塑、洞穴壁画中可以证明。前文提到的《维纶多夫的维纳斯》就是史前生殖崇拜的典型代表,而比之晚几千年,现存法国波尔多阿基坦博物馆的《洛塞尔的维纳斯》(约公元前25000—20000年),虽然类似维纶多夫的维纳斯,同样突出了乳房、盆骨、生殖器官等部位,表达繁衍后代的愿望,但在形态上有了一定的女性姿态美。值得注意的是,其身体上的红色可能暗示孩子降生的寓意,女性持的牛角可能代表了母系社会权力,或象征狩猎的成果等。根据现存资料,到了新石器晚期,有关女性形象的抽象图形已经出现,母爱题材出现在一些岩画中。现藏巴塞罗那考古博物馆的《妇人与动物》,据考证为约公元前4000—2000年岩画摹本,表达了人与动物之间的相处方式,最有意义的是女性形象虽然略显抽象,也没有透视技法,但已经初步具备了绘画的结构特征,可能反映的是人类群体定居后社会生活场景的变化。畜牧业发展时,动物们被驯化成功,在一群妇女的前面,牛、猪、羊、鹿、马等形象出现,体现了人与动物的和谐,女性的裙摆、轻盈姿态、纤细婀娜的身材也进一步突出了原始社会的审美标准,而原始社会初期畜牧业主要由女性负责,这也使女性的地位提高,母性的情怀得以加强。
2.知识表现型。在人类幼年期,由于母亲普遍与孩子相处的时间更长,教授基本知识或常识便成为母亲与孩子之间的重要互动,也是传递母爱的一种途径。追求知识、崇尚知识也是女性所追求的目标,知识型的女性在一定意义上更能体现母爱的精神。西方社会长期由男性主导,女性获取知识的权利和渠道常常被剥夺,每一次的思想解放运动都能够使得女性获取更多受教育的机会。即便如此,直到19世纪西方女性才得到正规受教育的机会,弗朗西斯·波泽指出:“直到19世纪70年代才开始有数量较多的女性得益于机构性的艺术教育。”[7]英国皇家艺术学院直到1893年才允许女性参加人体写生课,法国朱利昂学院在19世纪70年代之后才开始欢迎女性学员,国有资金的资助直到20世纪初才出现对女性艺术创作的资助。从某种程度上看,表现知识型女性或者女性教孩子学习知识的内容,能够很好地表现母爱精神。《写作的年轻女子》是现存展现知识型女性最早的艺术形象,为公元1世纪罗马帝国时期作品,现存于意大利那不勒斯国立考古博物馆。时髦年轻的女子形象生动逼真,面部线条圆润柔和,装饰和穿戴即使在今天也不显得落后,眼睛高光等细微处的处理技法精湛,执笔思索的姿态是知识型女性的典型动作。这个女性形象又被称为萨福(Sappho,别名女荷马),常用来指代约公元前630年至前560年古希腊著名的女抒情诗人,说明当时许多上流社会女性曾接受过文化教育,集知识、地位、思想于一身。如果将其图像与文艺复兴时期许多女性形象进行比较,也能够发现一些风格的联系。在近现代西方社会中,中产阶级家庭常常聘请女性担任家庭教师,由于当时女性接受教育的机会不多、程度不高,可以理解这些女教师既承担了教育的职责,也会帮助照看孩子,一定程度上代替了母亲的部分责任。当然,这些女性只能进行初级的启蒙式课程教学,冈萨雷斯认为:“担任教师的妇女大多只教授最基础的课程,并且往往只能在未受家庭义务约束时工作。”[8]现存英国伦敦国家美术馆的夏尔丹作品《年轻的女教师》(1736年)就属于典型的这类角色,女教师前倾的上身、耐心专注的表情、与孩童一起指向识字卡的手势,彰显出一种独属于母性的温柔与爱,非常具有时代的寓意。
3.宗教情怀型。相当数量母爱题材的作品是有关宗教寓意的,圣母子成为西方世界广泛接受的圣经教义的图像标识,即使没有接受过教育的人,看到圣母子的图像也会明白圣经的故事和教义,圣母子也是崇高的母爱精神的体现。圣母的母爱虽然是崇高神圣的,但是,也有其接受教育的源头。西班牙马德里普拉多美术馆现存的油画《圣母的教育》,由17世纪著名画家巴托落梅·埃斯特班·穆立罗绘制,讲述了圣母玛利亚的母亲圣安娜教育孩童时期玛利亚的情景,带有古典主义构图和巴罗克色彩的画面营造出了庄重与崇高感。同时,母爱的慈祥、耐心、沉静与玛利亚的凝神专注相互和谐,也说明西方世界一直在推动女性从小就接受教育。宗教故事及艺术作品中母爱的题材大多是关于圣母玛利亚与耶稣的故事,在3世纪罗马普丽西拉墓室壁画中已有圣母子的图像,只是艺术手法还比较简单。中世纪,艺术成为宗教宣扬教义的工具,母爱精神也被打上了宗教的烙印,大部分作品呈平面化、线条刻板,以金色、蓝色、红色等为主,色调变化少、相对单一,人物头部有金色光环,人物表情僵化,脱离了世俗化的生活气息,如希腊斯蒂里斯圣路加隐修院卡索利孔教堂的镶嵌画《宝座上的圣母子》,约完成于1020年,带有典型的中世纪拜占庭绘画风格。到了文艺复兴时期,尽管人文主义精神被广为接受,但是圣母子仍然作为绘画题材被众多的艺术家采用,只是创作风格发生了改变,文艺复兴初期的一些圣母形象虽然在技法上创新,使得审美及相关人物形象具有立体感和个性特色,但总体还是以构图严谨对称来彰显圣母形象高大及等级高贵,如1308至1311年杜乔为意大利锡耶纳主教堂创作的木板蛋彩贴金画《庄严圣母》。到了文艺复兴盛期,圣母子的图像风格发生巨大的变化,圣母的表情、神态、举止也更加贴近世俗生活,达·芬奇的《岩间圣母》,拉斐尔的《西斯廷圣母》《座椅中的圣母》《圣母玛利亚》,提香的《圣母升天》等一系列艺术精品把圣母的形象和母爱精神推向一个高峰,从这些作品中,人们既能够感受到圣母的世俗之爱,也能够体会到画面营造出的超越现实世界的真善美和崇高境界。
4.日常生活型。艺术的起源可以追溯到远古时期的劳作活动,但是,西方艺术经历了古希腊、古罗马的艺术繁荣之后,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创作的题材并非以日常生活及劳动场景为主,这是由于艺术追求古典美,艺术创作高于现实生活,包括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巨擘也是按照古典美的形式标准和价值判断进行创作,文艺复兴之后,欧洲各国的艺术各自发展,日常生活型的场景也登上了艺术的舞台。17世纪的荷兰经历了反对天主教和反对西班牙统治的斗争,最终成立了荷兰共和国,成为世界上首屈一指的经济贸易强国并享有“海上马车夫”的称号,荷兰画派得以兴盛,画家们立足民族特色,从形式生活中汲取题材,创作了广泛的绘画类别,包括风景画、肖像画、生活场景画、各类静物画等,受到新兴资产阶级和普通市民阶层的欢迎,与文艺复兴后其他欧洲国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哈尔斯的《快乐的饮酒人》、伦勃朗的《夜巡》等艺术家及作品流传后世,而涉及女性及母爱题材的作品也表现得十分精彩。如维米尔的《花边女工》《倒牛奶的女仆》、霍赫的《庭院》等,较好地反映了女性在世俗生活中扮演的角色,宁静安详又略带一些神圣隐喻,注重运用侧光及宁静有序的光色安排,增强平常场景的神圣感,女性形象也刻画得质朴动人,使观者在她们劳作生活的日常动作中想起自己的母亲,感受到母爱情怀的力量。尽管如此,17世纪的荷兰依然是男性主导的世界,特别是在一些正式的场合,需要男性来代替女性来行使权力,“即使某个妇女被允许在法律文件或会议记录上留下信息,也要由某个男人把她对其他男人提出的问题的答案写下来,在较低层的社会尤其如此。”[9]从整体上看,荷兰关于女性和母爱题材的绘画反映的是比较繁荣和安逸的生活场景,相较而言,16世纪尼德兰的风俗画更多强调世俗的场景,其中也包含了大量表现母爱或女性的主题,如彼得·勃鲁盖尔的《乡村婚礼》等。17、18世纪法国涉及日常生活场景的母爱题材绘画也很有代表性,有勒南创作的为温饱操劳忙碌的《农家室内》、夏尔丹表达质朴农民生活的《餐前祈祷》、维热·勒布伦表现母女情的《带女儿的自画像》、格勒兹创作的反映平民婚姻道德观的《乡村婚约》等。19世纪法国艺术家杜米埃更是大胆直陈底层人们的生活,代表作有《三等车厢》,通过生动传神的描述,充分表达了对贫困大众和劳动妇女的同情,这些作品主题都涉及女性和母爱,只是艺术的风格和手法、观察的视角有所差别,从社会背景、风格特征和艺术思潮等角度去比较不同流派的异同,有助于深入理解艺术创作从古典主义模式转向现实主义美术的重要意义。
5.风景融合型。风景在文艺复兴中后期仍是作为人物的陪衬出现在画面中,如提香的《欧罗巴的劫掠》、达芬奇的《蒙娜丽莎》等作品,风景与人物完美融合,对画面起到了很好的渲染作用,这些宗教和神话题材的作品也在一定程度上诠释了母爱的寓意和审美取向。17世纪荷兰、法国的风景画逐步形成独立的画种,女性题材的作品也展现出独特的魅力,在风景与人物的融合协调方面,法国风景画独具特色。普桑的绘画虽然出现了大量作为背景的风景,但仍然是以神话和宗教故事的人物描写为主,形成坚定的古典主义绘画风格,如《诗人的灵感》《阿卡迪亚牧羊人》等,画中的缪斯女神、达芙妮女神、仙女等传达出女性智慧、坚贞、喜悦的神情。克劳德·洛兰开启了风景人物融合的先河,与之前的画家不同,洛兰采取以风景远景为主,其间小的神话人物、历史人物或普通民众作为点缀,他的《有舞者的风景》中出现了带孩子与友人玩乐的母亲,在风景的衬托下显得十分自在,可见母爱情怀在艺术创作中的普遍性以及母子关系的紧密性。19世纪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印象主义美术形式纷纷登场,在这个时期的很多作品中能够发现母爱精神的光辉。德拉克罗瓦的《自由引导人们》,体现了浪漫性与现实性的结合,象征性的风格把女神所代表的追求自由精神与摧毁的旧城市结合,女性形象强壮有力,激昂奋进的情绪表露出对人民的爱;柯罗的《孟特芳丹的回忆》,营造出极为恬静的自然美景和温馨欢乐的母子情怀;米勒的《拾穗者》刻画了收割后的麦田里家庭妇女劳作的场景,她们的辛劳同样是出于母爱,为了给家人带去更好的生活。这些作品的风景与人物相得益彰,女性多展现了高贵品格的一面,很好地表现了艺术家的创作动机,也使得观者产生思想的共鸣,这是艺术家在深刻地观察和艺术取舍加工后的成果,“对画家来说,每个形象都有特殊的意义,以及大量隐含的意义,而他对作为构图和大量形式细节的整体的构思,会受到他想要将这种意义呈现出来的影响”。[10]
结 论
母爱题材的绘画作品既涵盖了艺术本体论的内容,也汇集了社会、历史、文化、政治、经济、教育、心理等多方面的知识,是近年来美术研究、创作、教学等领域中较受关注的焦点,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也为社会大众普遍接受。“只有坚持洋为中用、开拓创新,做到中西合璧、融会贯通,我国文艺才能更好发展繁荣起来。”[11]当下,在艺术创作中,应积极引导正确的艺术导向,坚持扬弃的态度、批判的眼光,立足国情,服务社会,探索创新,形成自己独特的思考,客观、辩证地学习借鉴西方艺术,不断推出优秀精品力作。
——战斗的圣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