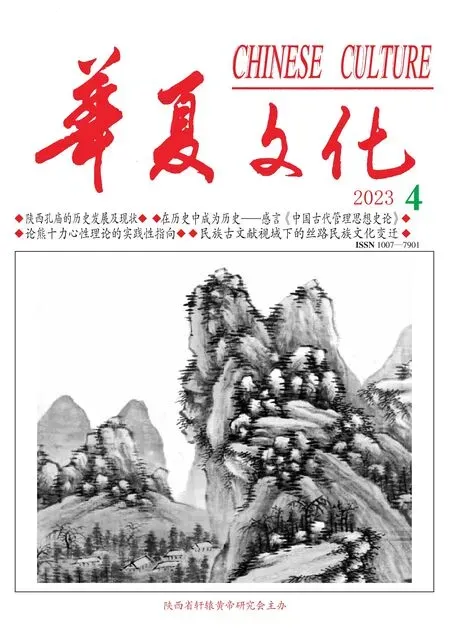云冈石窟的历史记忆与文化认同
□刘世明 高红萍
云冈石窟是北魏王朝的艺术杰作,也是当今世界著名的文化遗产。北魏时期,国家力量强盛、百姓安宁,四方朝贡者不计其数。其第五位帝王拓跋濬在位时,命沙门统昙矅于平城(今山西大同)西武州塞凿山石壁,开窟五所,这便是今天赫赫有名的“昙曜五窟”。之后,修建工程不断完善,最终成为历史上永恒的奇迹。如此艺术瑰宝,蕴含了太多的历史记忆与文化认同。以下,便从三个方面对其进行详细阐说。
首先,云冈石窟造像的鲜卑特色与国家、宗教认同。云冈石窟的一个鲜明特征,便是帝佛合一。正如《魏书·释老志》所言:“为太祖已下五帝,铸释迦立像五。”(魏收:《魏书》,中华书局,1974年,第3036页)我们今天所见到的第16—20窟,即是依照拓跋濬、拓跋晃、拓跋焘、拓跋嗣、拓跋珪五位帝王的真容所造。这种帝王佛陀化、佛陀帝王化的构造,正是向民众宣示北魏王朝的政权乃上天神授,无论何人皆须遵从。拓跋鲜卑的帝王,认同当时中原信仰的佛教,是为了更好地控制思想、维护统治。当然,他们也希望以此做法,得到汉族与其他少数民族的认同。
除此之外,“昙曜五窟”的五方佛设计又凸显了鲜卑拓跋氏的敬“五”情结。北魏太祖皇帝拓跋珪一登基,便“平五权,较五量,定五度”。之后,文成帝拓跋濬“开窟五所”,孝文帝拓跋宏议定五德,宣武帝元恪使“五典沦而复显”,孝明帝元诩更是“迎气五郊”“制五时朝服”“祭五世之礼”。可见,北魏帝王对于数字“五”是多么推崇。他们治理国家,也一依五行生克之理。逢水旱灾厉,必向山川祈谒;遭五行异象,则立刻修德慎刑。战国末年的邹衍曾说:“五德从所不胜,虞土、夏木、殷金、周火。”(李善注,萧统:《文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2561页)于是,五德终始之说开始盛行。对此,北魏帝王深信不疑。《魏书·序纪》曰:“昔黄帝有子二十五人,或内列诸华,或外分荒服。昌意少子,受封北土,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黄帝以土德王,北俗谓土为托,谓后为跋,故以为氏。”(《魏书》,第1页)《魏书·太祖纪》又说:“诏百司议定行次,尚书崔玄伯等奏从土德,服色尚黄,数用五。”(《魏书》,第34页)黄帝以土德王,北魏的行次便定为土,这正是向世人宣布自己是黄帝的后人、昌意的子孙,乃华夏正统。于是,拓跋鲜卑便融入了中华民族的大家庭之中,其政权当然也得到了同一时期其他民族的认同。这一点,由宋之刘骏、齐之萧赜以及鄯善、龟兹、高丽、波斯、西天竺、吐呼罗等国频频朝贡即可印证。云冈石窟是皇家工程,其帝佛合一的设计与敬“五”情结的彰显,不仅展现了拓跋鲜卑的民族特色,同时,也蕴含着北魏王朝的宗教认同及其政权合法性的国家认同。这一点,不容忽视。
其次,云冈石窟北魏造像题记的忠孝观念与道德、伦理认同。云冈石窟现存北魏造像题记共35处,有的已残缺不全,有的依然清晰可辨。这些题记记叙了1600多年前的历史与文化,是北魏时期民众信仰的真实写照。如《太和七年邑义信士女等五十四人造像记》中所言:“愿以此福,上为皇帝陛下、太皇太后、皇子,德合乾坤,威踰转轮,神被四天,国祚永康。”(员小中:《云冈石窟铭文楹联》,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14年,第27页)明明是民间组织,其发愿之文却是为君王祈祷,为国家祝福。此并非虚语,因为崇尚忠正之道是北魏一朝的风尚。就拿拓跋宏来说,其“五岁受禅,悲泣不能自胜”。显祖问之,答曰:“代亲之感,内切于心”(《魏书》,第186页)。其对父王的忠诚,天地可鉴。等到拓跋宏成为孝文帝后,他立刻去祭拜殷商忠臣比干。并说到:“謇謇兮比干,藉胄兮殷宗。含精兮诞卒,冥树兮英风……呜呼介士,胡不我臣。”(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华书局,1958年,第3551页)这样的忠贞耿介之士,为什么不是我的臣子呢?悲凉的背后,是对儒家忠正之道的全面认同。《论语》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2009年,第38页)我们敬佩屈原、诸葛亮、岳飞的人格,正是对他们忠诚精神的一种认同。
当然,除了以“忠”为代表的儒家道德之外,云冈石窟北魏造像题记还体现了一种以“孝”为核心的根祖情怀,即落叶归根、认祖归宗以及对祖先的思念、感激之情。如刻于第17窟明窗东壁的《太和十三年比丘尼惠定造像记》,其文曰:“愿患消除,愿现世安稳,戒行猛利,道心日增,誓不退转。以此造像功德,逮及七世父母、累劫诸师、无边众生,咸同斯庆。”(《云冈石窟铭文楹联》,第33页)此发愿者为七世父母消灾祈福,是对宗族生命的敬重。因为这里有血脉的延续,有人间的亲情。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感恩祖先,正是孝心的体现。北魏王朝,不孝有罪,“比其门标,以刻其柱”(《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3550页)。显祖曾患痈疽,孝文帝竟亲自吮脓,真令后人叹服。《礼记·祭义》曰:“君子生则敬养,死则敬享。”(孙希旦:《礼记集解》,中华书局,1989年,第1209页)北魏民众维系宗族之血脉、安顿祖先之生命,实则是对以“孝”为中心的儒家伦理的接受。忠与孝,乃道德规范与伦理信条,拓跋鲜卑既然走向汉化,那么就必须选择认同。
最后,历代吟咏云冈诗歌中的情感、地域认同。云冈石窟虽冠绝一时,然因地处荒僻、交通不畅,历代诗人题咏者并不多。现存作品不过百首,作者也大多来自明清,但仍可窥见文人墨客对于北魏文化的认同。如清代作家胡文烨,其于顺治七年被升为大同府知府,曾主持编纂《云中郡志》十四卷。他在《游石窟寺》中说:“香花金粟现,钟磬白云悠。俯此众生劫,何缘彼岸舟。”(韩府:《历代咏云冈石窟诗萃》,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第46页)愿百姓安宁,愿芸芸众生一切苦难,都可解脱。同样的主题,清人陈禹谟亦有《游石窟寺》一首。其诗曰:“雨翻花石动,月印海波悠。亿万恒河筏,婆心渡铁舟。”(《历代咏云冈石窟诗萃》,第49页)云冈众佛皆有悲悯之心,诗人相信他们一定可以解救众生。关爱百姓、体恤万民,如此宽广的胸襟、宽大的胸怀,正是对北魏云冈诸佛的一种情感认同。
除此之外,南人入北,也带来了许多云冈诗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明末清初的学者曹溶。曹溶本是浙江嘉兴人,于康熙二年由广东布政使降调为大同备兵道,官居大同五年。在此期间,其留下了《游云冈寺》《云冈石佛记》《云冈寺燕集》等诗文。在《云冈寺燕集》中,曹溶说道:“法幢随雾雨,宝座即谽谺。佛国游堪借,军容静不哗。”(《历代咏云冈石窟诗萃》,第57页)在北地借游,军容整齐、四方臣服,其胸中之抱负,可见一斑。又如雍正七年任朔平府知府的刘仕铭,其在《石泉灵境》一诗中说道:“在昔鸾旗朝鹫岭,于今水月照瞿昙。灵湫清澈浑如境,手把龙团望朔南。”(《历代咏云冈石窟诗萃》,第65页)千年以前,拓跋弘云游石窟寺,今时今朝,康熙帝回銮武周塞。深潭明净,手斟清茶,北地悠然,何须再眷恋南方。此类诗人,南来北居,喜欢上了塞外的辽阔与壮美,自然也体现了他们心中对北魏文化的地域认同。
孝文帝拓跋宏之时,鲜卑人不说胡语、不着胡服、调整官制、更改姓氏,与汉族大姓通婚。他们在用一种消灭自己的方式强力汉化,不留一丝余地。同时的南方,刘昶归魏、王肃北逃、萧综叛梁,直至陈庆之入洛,竟说:“吾始以为大江以北皆戎狄之乡,比至洛阳,乃知衣冠人物尽在中原,非江东所及也。”(司马光:《资治通鉴》,岳麓书社,1990年,第955页)可见,胡汉已然一体,华夏本是一家,这些都是云冈石窟留给我们的历史记忆与文化认同。难怪邓拓先生会如此赞美云冈:千载云冈紫塞边,我来飞雪正漫天。危崖万佛迎风笑,艺术人间第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