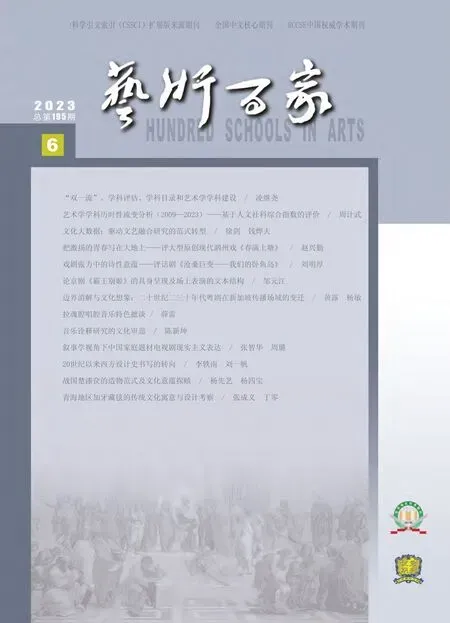20世纪以来西方设计史书写的转向*
李轶南,刘一帆
(1.东南大学 艺术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6;2.东南大学 中国艺术发展评价研究院,江苏 南京 210096)
一部西方设计史,可以说亦是一部设计史书写的变迁史。设计活动自260万年前人类远祖“能人”(Homo habilis)用石头砍伐、造物即已展开,可谓源远流长。我国的设计史书写可上溯到春秋战国之际记载手工业技术、制度、管理等的综合性典籍《考工记》。该书系齐国官书,英国科技史家李约瑟盛赞该书为“研究中国古代技术史的最重要文献”,中国科学院院士钱临照认为“《考工记》乃我国先秦之百科全书”[1]30。太史公司马迁在《史记》的《货殖列传》中提出“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的著名观点,并且敢于打破常规,破格记载百姓日常生活所用的手工业产品(“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这对于新史学而言,不啻手辟鸿濛[2]7553。但是,有意识的、纯粹的设计史书写却是相当晚近的事。18世纪后期西方工业革命轰轰烈烈地展开,催生了以机械化批量生产为特征的现代大型企业、公司,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刺激了市场对产品的旺盛需求。设计与制造分离,设计旋即独立成为一种专门职业而登上历史舞台。设计史的书写由此成为可能。设计史的变迁,可以说是其背后社会变动的监测浮标和清晰投射。
20世纪以来,西方设计史书写,从深度、广度与方法论角度来看,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即以扬弃精英史观、走出艺术史笼罩为特征的早期设计史研究阶段(20世纪初到20世纪中期),以新文化史兴起与物质文化研究的开拓为代表的设计史学科独立发展阶段(20世纪70到90年代)和以全球化、多样化与更高起点的回归为表征的新发展阶段(20世纪90年代以来)。这三个阶段之间并非存在一条判然有别的“楚河汉界”,各阶段之间可能存在交叉、重叠甚至千丝万缕的相互缠绕。为了便于行文,我们暂且借助这副时间的“脚手架”,力求梳理和展现20世纪以来西方设计史书写的各个不同侧面。
一、20世纪早期的设计史:走出艺术史的笼罩
受艺术史书写传统的影响,西方现代早期设计史撰述往往追溯那些近乎完美的代表性作品之审美演变历程,而忽视恒河沙数的各式日常生活物什。例如被誉为现代设计史奠基人的犹太裔学者尼古拉斯·佩夫斯纳(Nikolaus Pevsner,1902—1983)于1936年出版的奠定其设计史学界重要地位的《现代设计的先驱者:从威廉·莫里斯到沃尔特·格罗皮乌斯》一书,受到黑格尔“时代精神”(Zeitgeist)、“民族精神”(Volksgeist)等哲学观念的影响,佩夫斯纳认为民族特色必然反映于艺术之中。在书中他讨论了各路现代设计急先锋作品的特征,例如杰出设计师霍夫曼(Josef Hoffmann,1870—1956)作品的简洁优美、赖特(Frank Lioyd Wrignt,1867—1959)作品的恢宏阔落、格罗庇乌斯(Walter Gropius,1883—1969)作品的坚实直率等,论证民族精神或特质在这些优秀设计师身上的展现。佩夫斯纳将各种现代运动视为设计史的关键,强调设计师而非产品,重视创意而非生产方式,除了突出设计师的个性对设计作品所发挥的影响外,还引入了类型学研究方法,开一时风气之先。
“风格”是艺术史家常用的重要批评概念之一。早在1893年,奥地利艺术史家阿洛伊斯·李格尔(Alois Riegl,1858—1905)出版了《风格问题:装饰历史的基础》,首次围绕装饰的风格问题做出历史的研究。其后,瑞士艺术史家海因里希·沃尔夫林(Heinrich Wolfflin,1864—1945)出版《艺术风格学》(1915),大力倡导“无名艺术史”观,并提出线描与涂绘、平面与纵深、封闭形式与开放形式、多样性与同一性、清晰性与模糊性五组对立法则,颠覆了往昔以艺术家为中心的艺术史书写传统,挑战了乔尔乔·瓦萨里(Giorgio Vasari,1511—1574)的《意大利艺苑名人传:辉煌的复兴》等以知名艺术家为中心的写作方式。沃尔夫林的艺术史研究不再关注杰出艺术家及其生平、代表作,而是着眼于艺术“风格”演变的说明与阐释。受此影响,一批聚焦“无名历史”或“风格”研究的设计史著述得以涌现。例如沃尔夫林的学生希格弗莱德·吉迪恩(Siegfried Giedion,1888—1968)撰写的《机械化掌控》(MechanizationTakesCommand,1948)一书的副标题即为“献给无名的历史”,着重研究日用品所受到的机械化生产的影响,并强调出自无名氏之手的设计。可以说,此举开创了设计史书写的另一渊源。不过与乃师不同的是,吉迪恩所采用的分析方式是类型学的,而非着眼于风格的辨析。他提出,“风格史”处理主题的方式是对其进行横向划分,而“类型学”则将主题加以纵向划分。为了看清设计史时空中的事与物,两种划分都是必要的。对于某一类型的设计史而言,时点需要上溯多远应该因“类”而异,并无一定之规,因为这取决于历史材料,而非历史学家。
“风格”通常被视为拥有一定的生命周期,因而风格可分为诞生期、青少年期、成熟期、衰退期和消亡期,或者被冠以早期、中期、晚期等进行特征分析。套用王国维《宋元戏曲考》中的“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我们也可以说,一代有一代之设计。历史上特定时期的设计表现出某种主要的、统一的风格倾向,或者显现为某种时代样式、共同的时代精神。沃尔夫林曾注意到哥特式建筑与哥特式服饰在形式上存在某种一致性:一个表现为高耸入云的尖顶,一个呈现为细如长针的尖头。论及“风格”,一只鞋能传达给我们的消息,与一座大教堂所蕴含的内容似乎相差无几。艺术史中的希腊化、罗马式、哥特式、巴洛克式、洛可可式、路易十四式、新古典主义、新艺术风格、现代主义风格等名词均被借用到设计史的书写中,正如法国哲学家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所言,出自无名氏之手的设计堪称史诗题材。以“风格”研究为关键词的史著例如《优良外形:1900—1960年的工业产品风格》(InGoodShape:StyleinIndustrialProducts1900to1960,1979)、《风格战争》(StyleWars,1980)、《世纪风格》(TheStyleoftheCentury,1900—1980,1983)等雨后春笋般纷纷涌现。事实上,“风格”对设计史的影响远不及对艺术史的影响那样深远。客户需求、制造工艺、机器美学和“形式服从功能”等原则基本决定了建筑、工业产品的最终外观,设计只能“戴着镣铐跳舞”,设计师的作用即是寻求合理解决设计问题的最佳方案,而非立足于形式和品位的“风格”一词所能简单概括。现当代艺术有统一风格吗?答案也许是否定的。因为随着社会变得日益复杂多样,我们看到的是多元化、多维度的风格差异、并置、拼贴、矛盾、断裂、连续,以及包罗万象、五光十色、风起云涌的设计文化。
传统的设计史往往把那些具有较高美学价值的设计作品以及设计大师、设计观念、设计运动、设计制度的变迁纳入研究视野,将审美视为关注的核心,因而将“风格”列为研究的关键词。20世纪80年代以来,设计史的书写范围几乎涵盖了各种可能的主题。1980年,约翰·赫斯克特(JohnHeskett,1937—2014)的著作《工业设计》(IndustrialDesign)问世,他批评传统设计史书写流于形式分析的方法论,批评低俗甚至忽视人造物生产过程与使用场景的多样化。他还提出,要对20世纪70年代以来逐渐抬头的“文脉决定论”表示警惕,因为该倾向存在令工业设计史滑向艺术社会史或设计社会史的风险。[3]31该书通过梳理近200年来设计发展的历史流变,通过丰富翔实的案例与详略得当的分析倡导设计史书写的新方式——注重平衡。他摈弃了诸如“装饰艺术”“实用艺术”“工业艺术”等传统概念,从工业设计学科自身的概念出发,不仅考察了设计的工业化生产制造环节,还整合了生产语境与消费语境,深入研究了长期以来被设计史忽视的消费环节,促进公众对工业设计的理解,从而超越了以明星设计师和杰出设计作品为线索的“点将录”、鉴赏式书写模式。他主张设计史的撰写需要基于广泛调研,可能涉及专业化工业组织和商业结构、经济和政治政策、社会环境的影响等方方面面。与此同时,一批学者如德国的吉特·塞拉(Gert Seller),英国的彭妮·斯帕克(Penny Sparke)、乔纳森·伍德姆(Jonathan M.Woodham),意大利的保罗·弗萨第(Paolo Fossati)等出版的设计史著述均存在一个共同点,即试图运用工业设计学科自身的术语而非将设计史视为艺术史的分支来撰写工业设计史,旗帜鲜明地宣告设计史的写作不再基于博物馆藏品或艺术史中的精英史观,堪称走出艺术史笼罩的一种富有新意的大胆尝试。
二、视线下移:新文化史的兴起与物质文化研究的开拓
设计并非纯艺术,虽然它可能包含某些艺术趣味。因此,设计史不应等同于艺术史或者成为艺术史的组成部分。设计是一种文化现象,其史学从早年关注精英史继而转向社会史,探讨精神、物质层面的文化史则在近几十年的研究中蔚然成风。俟林·亨特(Lynn Avery Hunt)主编的《新文化史》问世后,同道日多,逐渐形成了绵延至今的“新文化史”热潮。
物质文化研究的主要推动者丹尼尔·米勒(Daniel Miller)曾说,“(物质文化研究)作为既定的学科,其主题并不存在”[3]49。事实上,物质文化研究作为一种松散的综合研究领域,它重点聚焦于文化的物质方面。丹尼尔·米勒在其所著的《物质文化与大众消费》(MaterialCultureandMassConsumption,1987)一书中,采用文化人类学的视野与方法,指出叙写一部消费社会的商品文化史,须考察如何通过消费某些品牌构建身份认同,从而区隔不同阶级或阶层的消费者,借大众文化造就大众消费。这部著作明显受到社会学及人种学理论影响,并且特别强调了民族志取向。在消费社会,广告、传媒、时尚文化纷纷阐释着浮现于商品上的符号,符号价值成为解说商品的有力语言,商品审美化、消费符号化大众化以及主体的匿名化成为消费社会的主要特征。[4]171
物质文化研究对于设计史书写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文化人类学与民族志、博物馆学、考古学与科学技术史的介入。传统的设计史专注于人造物的生产,特别是物的设计概念化形成、创建过程和生产系统等,从而忽略了物的营销、流通、零售、消费以及使用、反馈、废弃、循环等问题。对于物的阐释而言,博物馆学研究方法的优势在于它肯定了物所具有或传达的意义具有多种类型,考察物在历史的、实用的、情感的、符号的以及政治方面的意义,这亦被视为物质文化研究的常用手法。
(一)开掘日常生活:大众文化史的发现
20世纪40—50年代,生活在英国的中欧流亡学者弗里德里克·安塔尔(Frederick Antal)、阿诺德·豪瑟尔(Arnold Hauser)及弗朗西斯·克林根德尔(Francis Klingender)提出了“另一种文化史,一种艺术和文学的‘社会史’”[5]185-186。这批史学家在思想上亲近马克思主义,将文化与经济、社会的矛盾变化相联系。在20世纪中期“自下而上”的社会史大潮助推以及文化史自身发展的合力作用下,大众文化史崭露头角。设计史由早先关注的精英文化转向未被充分认识的大众文化或亚文化、次文化。日常生活之物往往最易被忽视,而它们常常饱含着司空见惯之物所特有的深度与广度。就本质而言,设计文化并非精英文化,它代表着日常大众文化,内置了理论与实践、精神与物质、商业与文化、生产与消费、实用价值与符号象征、传统与创新之间的矛盾张力。日常生活之物犹如一架透视镜,观察者借助它可真切探测到社会与文化之间矛盾纠葛的主线,发掘日常之物及形塑它们的思想及其存在的价值与意义,共同构成了文化史研究的丰茂沃壤。
英国设计史教授彭妮·斯帕克(Penny Sparke)所著《设计与文化导论》(AnIntroductiontoDesignandCultureintheTwentiethCentury,1986)以国际文化、社会和经济为背景,阐释了20世纪以来现当代设计的发展流变史。她探讨了后现代主义和设计的新主题、技术与设计如何结合、设计怎样体现身份认同,尤其关注设计话语的发展变迁,并通过丰富的设计案例对各时期的设计运动进行追溯。
美国学者保罗·贝茨所著《日常物之权威:西德设计文化史》(Paul Betts,TheAuthorityofEverydayObjects:ACulturalHistoryofWestGermanIndustrialDesig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8)立足文化史立场,指出工业设计乃是一种有趣的文化现象,他有意选择日常生活用品这些“平凡之物”[3]66,旨在通过对日常物的设计、制作、交易、使用、品味等方面的多维度考察,全面深刻地认识其所处社会的文化和价值取向,凸显日常物品在特定时期(例如20世纪50年代)所散发的文化史意义,揭示物品与思想、精神与实质、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关联互动,从而打破设计史的通常界限与传统范畴,进一步拓宽设计文化史的研究领域。
1977年,英国设计史学会(Society of Design History)成立,标志着设计史学科的独立和相关研究活动的系统展开。在此之前,英国设计史研究隶属于该国艺术史家协会下设的设计史家分组,例如,伦敦米德尔塞克斯理工大学(Middlesex Polytechnic University)首次设立设计史硕士学位课程时,不仅由当时的艺术史系负责,而且后者因其注重“新艺术史”的研究方法而广为人知。[3]201987年,隶属于英国设计史学会的杂志《设计史期刊》(TheJournalofDesignHistory)创立。该刊致力于从跨学科视角探索设计史与其他学科的关联,特别是从物质文化角度探讨建筑史、商业史、设计管理、文化研究、经济与社会史、科学与技术史以及人类学等问题。与之相对照,美国的设计史研究组织较为松散,研究涉猎的主题范围比较宽泛。比如美国设计史论坛(2004年更名为设计研究论坛,Design Studies Forum)创办于1983年,而后《设计问题》(DesignIssues)于1984年创刊,其研究范围正如其副标题“历史·理论·批评”所示,并非仅仅局限于设计史。斯堪的纳维亚国家虽然早在1982年即已宣告成立“北欧设计史论坛”(Nordic Forum for Design History),但其设计史学科势单力薄且呈现较为零散的发展状态。北欧设计史论坛和《斯堪的纳维亚设计史期刊》合作举办两年一届的年会,为北欧设计史家提供难得的学术共同体活动。
20世纪70年代以降,伴随着设计史学科的独立和相关研究活动的展开,设计史研究获得长足发展,然而设计史家却未能提出基础研究主题或者一套能够指导设计研究的方法与准则。彼时其他领域的跨学科研究正如火如荼地展开,整合设计领域中涉及的科学和技术主题与哲学、人类学、社会学以及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并加以研究,成为一个方兴未艾的新议题。爱德华·卡尔(Edward Hallett Carr)说:“历史研究越注意文化,文化研究越注意历史,则对两者愈有利。”[6]84这句话预示了文化史研究将取代社会史研究而成为史学主流。换言之,若将设计史看作设计文化的历史,或者视为设计的文化史,那么不仅会增进设计史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相关性,而且也有助于推动设计史与其他学科实现跨学科协作,促进新课题与新方法的探索与整合。
20世纪80年代,新文化史旗手林·亨特(Lynn Hunt)提出“新文化史”一词以区别于传统文化史。传统文化史研究主要关注思想、艺术、制度、习俗、精神等非物质的、观念形态的因素。“新文化史”之“新”在于抛弃了传统的“文明—野蛮”二分法,提出“文化”是一个复数形式:对文化的概念进行重新界定,特别是借鉴了英国人类学家布罗尼斯瓦夫·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的观点,即“文化包括在社会上传播的手工制品、商品、技术流程、思想、习惯和价值观”之中[7]157。一些新文化史家开始尝试对物质文化进行研究,其主要研究对象是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物”。多数物质文化研究聚焦于若干主题,涵盖衣、食、住、行诸领域。生活中习焉不察的庸常物什,在新文化史聚光灯的照射下,散发出耀眼的诗性光芒。不少新作即从日用之物入手,解读和诠释其中蕴含的文化意义,例如《内衣:一部文化史》《服饰时尚800年》《鞋的风化史》《世界鞋史》等等。时尚堪称社会文化的风向标,“服饰史告诉我们许多有关文明的事情;它透露了它们的代码”[8]5。法国第四代年鉴史家丹尼尔·罗切(Daniel Roche)认为,考察服装的设计、制作、消费、穿着、品位等方面,更能全面深刻地认识其所属社会的文化和价值取向。
关注物质文化的设计史代表作诸如《想象消费者:从威奇伍德到康宁的设计与创新》(ImagingConsumers:DesignandInnovationfromWedgewoodtoCorning,2000)。该书作者雷吉娜·李·布拉什奇克(Regina Lee Blaszczyk)对日常物品消费研究感兴趣,提出设计史研究应对准不登大雅之堂的日常大众用品,并试图通过考察涉及制造环节的设计师、市场研究人员、广告人员、批发商、零售商、销售员等来研究消费者的需求和欲望,尝试弥合横亘于生产和消费之间的鸿沟,从而设计开发出更多成功的商品。她重点关注作为创新先锋的时尚经纪人,将设计史的镜头从内转向外、从上移向下,表现出扬弃大师杰作“英雄史观”的方法论取向。
(二)民族国家的崛起与区域国别设计史的涌现
经设计而成的产品往往来自特定国度,出自一定民族的设计师之手。20世纪以来民族国家的纷纷独立和发展,助推区域国别设计史的书写呈现生气勃勃之势。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在其著作《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Communities,1983)一书中曾提出三对矛盾:史学家所述的国家的客观现代性与民族主义者心目中的主观传统性之间的矛盾,民族主义作为社会—文化概念的普遍性与具体表现的特殊性之间的矛盾,民族主义政治权利与其哲学观的缺位与混乱之间的矛盾。厄内斯特·盖尔纳(Ernest Gellner)在其著作《民族和民族主义》(NationsandNationalism,1983)中指出,20世纪诸多国家的建立都是帝国主义政治博弈或战争的结果,民族主义表面上虽以种族为基础,其内里即是一个意识形态概念。设计师受到所属国家或民族、地域文化、时代精神等的制约,故设计的地理学阐释成为解释特定国家、民族文化和环境影响的设计史著书写的重要内容。
民族主义的兴起使得民族特征成为一个国家理想的象征,民族特征是维护国家身份所依赖的产品及其传播、交流的根源。在这方面,20世纪初的魏玛德国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观察范例。分析德国工业联盟奠基人赫尔曼·穆特修斯(Hermann Muthesius)等设计改革先锋的早期论述,审视彼得·贝伦斯(Peter Behrens)为德国通用电气公司所做的系列设计,我们方能理解何以通过设计表现国家文化理想的艺术形式,理解何以将这些形式植入消费过程以促进德国的经济发展,进而加强设计和工业之间的紧密联系,其背后隐含的逻辑至今仍在发挥效用。
众所周知,英国在设计史学科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发挥了引领作用,就设计史出版物和从业者数量而言,都是所在多有。例如《维多利亚式的舒适:1830—1900年的设计社会史》(VictorianComfort:ASocialHistoryofDesignfrom1830—1900,1961)、《维多利亚时代的乡村别墅》(VictorianCountryHouses,1971)、《所有光明美好的事物:1830年至今的英国设计》(AllThingsBrightandBeautiful:DesigninBritain1830toToday,1972)、《英国建筑样式》(ThePatternofEnglishBuildings,1972年再版)、《30年代:战前的英国艺术与设计》(Thirties:BritishArtandDesignbeforetheWar,1979)、《设计中的民族特色》(NationalCharacteristicsinDesign,1985)、《新英国设计》(NewBritishDesign,1986)等。此外,还有《德国手工艺品、家电文化与形式的历史》(DeutschesHandwerksgut,eineKultur-und-FormgeschichtedesHausgerats,1939)、《美国制造》(MadeinAmerica,1945)、《法国革命至今的品位和时尚》(TasteandFashion:FromtheFrenchRevolutiontothePresentDay,1945)、《日本建筑史序说》(太田博太郎著,1947)、《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城市规划的失败》(TheDeathandLifeofGreatAmericanCities,1961)、《哥特与古典:17世纪意大利的建筑项目》(GothicversusClassic:ArchitecturalProjectsin17thCenturyItaly,1974)、《德国设计:品质的形象》(GermanDesign:ImagesofQuality,1987)、《斯堪的纳维亚的现代主义》(ModernisminScandinaviaArt,ArchitectureandDesign,2017)等著述相继问世,作者或围绕某一设计类型展开论述,或以问题为中心探讨来龙去脉,为区域国别设计史的撰写增添了新的华章。
英国设计史家彭妮·斯帕克指出:“虽然德国以科学的名义,意大利以艺术的名义,斯堪的纳维亚以工艺的名义,美国以商业的名义来销售设计,但所有这些国家的设计形象,在战后高度竞争的世界市场上都是必要的战略。”[9]48此语一针见血地道出了区域国别设计史书写背后隐含的国家意志和战略擘画。
(三)企业史或公司史的兴起
企业史或公司史的诞生并非偶然,可以说其来有自。从历史角度看,企业作为一个经济实体,其初期并未充分认识到设计在企业形成和发展中所起到的作用。早在1907年,德国著名建筑师彼得·贝伦斯(Peter Behrens)即已受聘于德国通用电气公司(AEG),专事设计该公司从工厂建筑、工业产品到标识、字体、海报、广告册页、产品目录等方方面面的业务,他强调设计风格的一致性,通过设计的形式语言别出心裁地塑造了公司产品、企业形象的整体统一性,开创了现代公司引入企业形象识别计划的先河。但是直到二战爆发前夕,德国的工业设计整体上相较美国而言,仍然普及不足。20世纪初,设计活动在发达的美国制造业中已开展得如火如荼,虽然美国芝加哥学派的代表人物路易斯·苏利文(Louis Sullivan)提出“形式追随功能”(Form follows function)的响亮口号,但在实用主义至上的激烈竞争中,实际遵奉的却是“形式追随市场”的原则。对于美国企业来说,设计是否有利于销售是其核心关注点,而非社会效益、理想主义或其他。一战期间,战场对军用品和武器的巨大需求刺激了美国工业的发展。一战结束后,美国制造业随即转向民用消费品生产,科学管理、标准化规范化制度、大批量流水线生产方式等得以广泛运用。20世纪20年代,设计师的职业化已在美国大城市如纽约、芝加哥等地遍地开花,势将燎原。由于设计业务日趋频繁,著名设计师雷蒙德·罗维(Raymond Loewy)在20世纪30年代成立了自己的设计公司,其名言“最美丽的曲线是销售上涨的曲线”[10]177成为美国设计富于商业气息的最佳注脚。
20世纪初期以来,“设计”在西方企业界一般被视为发挥涂脂抹粉、类似“外科美容术”的修饰作用。例如1928年,通用汽车新成立的设计部便被命名为“艺术与色彩部”(Art and Colour Section)。1938年,由于庞大的业务发展需要,该部又更名为“式样设计部”,其雇佣人员多达数百,即便如此,设计依然被视为一件可随潮流更换的时髦外衣。二战结束后,“工业设计”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和职业日渐成熟,伴随着职业设计师登上企业舞台的中心,以往研究者那种重视基于生产过程及效率的组织模型,让位于关注产品和市场模型的发展趋势。于是,相对于生产过程处于外在或次要地位的“设计”,“工业设计”的定位转变为向企业提供全方位的问题解决方案。
企业史学原是以企业家和企业为研究对象的一个历史学的分支学科。20世纪20年代美国初步形成了企业史学派,该学派创建了企业史学会,并创办了《企业史通报》和《经济史与企业史》杂志,以之为阵地展开企业史的研究与争鸣。早期的企业史研究仅仅着眼于个别企业的创建过程,或者为少数企业家树碑立传,影响不甚大。此时期企业史研究有一个显著特点,即企业在很大程度上寻求通过线性时间序列呈现已有成功产品以展示自己的企业形象、体现其发展方式。一些讲述公司历史的出版物总是从创新和产品特性的角度描述其技术和生产的演变。这些出版物审视公司发展的各个阶段,向读者展示与不同发展阶段对应的相关系列产品,辅以大量图片并逼真地搭配于各章节概要中,使得读者能对不同模型进行比较分析,同时准确描述产品创新历程中的不同时期,清晰展现产品的技术和功能特征,有时甚至强调生产周期中的局部创新(例如强调1924年设立流水线生产熨斗的工厂的合理性)。其不足表现为缺乏系统的研究理论贯穿其中,属于一种实用性研究,所以从严格意义上说,初期的企业史或公司史写作尚不够成熟。
二战后,伴随着美国经济的腾飞和企业发展的蒸蒸日上,企业史学派日趋活跃、成熟。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初,新企业史学派崛起,并从批判旧企业史学派中分离出来,其代表人物是小艾尔弗雷德·D.钱德勒(Alfred D.Chandler)。钱德勒吸收了角色理论(Role theory)和结构功能主义(Structure-functionalism)学说,注意运用社会学理论研究企业史,以管理方面“看不见的手”的著名论断取代了亚当·斯密(Adam Smith)市场运行中“看不见的手”的论断[11]8。
之所以历史学家对企业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兴趣,主要源于以下事实:这些企业往往是新工业部门的领头羊或先驱,它们引领革新或创新风潮,开启了产品制造、营销增长的新方式。例如,在英国韦奇伍德公司的案例中,企业家被描述为标志性人物,除了推动陶瓷生产工业化外,韦奇伍德还认识到产品制造属于更广泛系统的组成部分,该系统涵盖了用户研究、设计、生产以及营销、售后等各个环节。同样的因素激发了学界对福特和通用汽车等美国汽车制造业巨头的兴趣,并研究考察大型汽车制造公司对整个运输史所起的作用。研究者们对这些公司的关注无法摆脱重要设计师在场的影响。一方面,早期的工业设计史研究者们没有认识到,企业变迁史为他们了解产品发展史和工业设计师的职业演变史提供了一个理想的切入点;另一方面,企业不愿将旗下产品的设计特征视为自身身份的决定性因素。正如约翰·沃克(John Walker)所指出的那样,早期工业设计史研究企业的方法并未脱离艺术史家研究赞助人的窠臼——他们仅仅遴选工业产品世界中富有特殊意义的设计作品加以研究。
1964年,拥有汽车行业五十多年管理经验的职业经理人艾尔弗雷德·斯隆(Alfred P.Sloan,1875—1966)以自传体形式出版了《我在通用汽车的岁月》(MyYearswithGeneralMotors),一时洛阳纸贵,被尊奉为“公司圣经”(迄今销量累计已突破200万册)。斯隆担任通用汽车公司首席执行官、董事会主席长达三十余年,是公司的掌舵者和历史亲历者,他不仅带领公司实现弯道超车——超越竞争对手福特公司,而且将通用公司缔造为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制造商,他本人亦成为美国企业界的传奇人物。书中,斯隆讲述了半个世纪岁月里通用公司的分权组织架构原则和思想,为应对汽车市场的激烈竞争和转型而制定相应的产品政策,比较分析年度车型的演变历程,展现不同阶段——早期扩张阶段、短暂的收缩期、迈向稳固的时期、新的扩张期、经济衰退和复苏期、二战时期和战后时期——如何审时度势地实现汽车的创新发展,特别是从设计管理、经营的角度将“通用往事”娓娓道来,将观念的分析和历史的回顾结合起来。实际上,该书是一部以美国通用汽车为研究对象的大公司管理和发展史,甫一问世即引发各界关注,奠定了新企业史研究的基础。
随后,从企业史角度研究设计创新、设计政策、设计管理等的著作陆续出版,例如:《设计为生:五角星设计事务所》(LivingbyDesign:Pentagram,1978) 、《汽车项目:52个月的工作,他们是如何设计福特塞拉的》(TheCarProgramme: 52MonthstoJobOneorHowTheyDesignedtheFordSierra,1983)、《哈利·厄尔与美国梦想机器》(HarleyEarlandtheAmericanDreamMachine,1984),《飞利浦——设计的企业管理研究》(约翰·赫斯克特,1989)等。克劳斯·克伦普(Klaus Klemp)的《少与多:迪特尔·拉姆斯设计的精神气质》(LessandMore:TheDesignEthosofDieterRams,2010)翔实解读了博朗电器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历史,图文并茂地论述了效力该公司的著名设计师拉姆斯的经典设计案例。拉什·穆勒出版社(Lars Muller Publishers)出版的《汉莎航空和平面设计:飞机的视觉历史》(Lufthansa andGraphicDesign:VisualHistoryofanAirplane,2012)是研究德国汉莎航空设计历史的著作,系统展现了汉莎航空各个时期的视觉设计方案,通过纵向比较来体现汉莎航空视觉形象对二战后德国“民主”“科学”的国家形象重建的深远影响。战后德国知名公司的工业产品和视觉设计充当了德国当代文化的代言人,学者们通常用“客观”“理性”“冷峻”“严谨”等词语描述德国设计的优良品质、先进技术和形式特征,从而潜移默化地修复了德国因纳粹战争而受损的国家形象。
由于文化史等跨学科研究的影响,一些企业史的写作开始转向从文化叙事的角度讲述自身的组织架构及其缘起和历史演变脉络。从企业文化的角度研究企业史,使该领域的研究实现重大突破,例如,《丰裕的神话:美国广告文化史》(FablesofAbundance:ACulturalHistoryofAdvertisinginAmerica,1995)、《宜家的设计:一部文化史》(DesignedbyIKEA:ACulturalHistory,2014)、《韦奇伍德:创造与创新的故事》(WedgewoodAStoryofCreation&Innovation,2017)等,皆属此类。
《宜家的设计:一部文化史》(DesignedbyIKEA:ACulturalHistory)的作者系斯德哥尔摩工艺美术学院设计史论系客座教授莎拉·克里斯托弗(Sara Kristoffersson),她好奇于这个庞大的商业帝国——截至2013年,宜家在全球逾38个国家拥有298家门店,年营业额高达277亿欧元。宜家快速扩张的规模和仿佛骤然而至的成功激发了学者们的研究兴趣:宜家如何通过有效结合公司历史和运营策略,通过富有技巧地“讲好故事”、浸染文学化倾向的“公司叙事”而使宜家品牌深入人心?宜家商标如何由红白双色改用瑞典国旗的蓝黄两色而“借光”瑞典高水准、民主福利的国家形象,成就自身的国际大牌形象?宜家作为一个商业品牌,如何在形塑瑞典国家形象、传播瑞典文化和意识形态进程中发挥作用?宜家和瑞典之间如何有效互动、相得益彰从而实现双赢?宜家如何在被指责“抄袭”的质疑声中为品牌注入“瑞典风”,从而走向“风格主导”的多元化发展?在全球竞技的激烈市场竞争中,宜家如何以其独树一帜的设计改变了全球各地的消费方式?该书从文化研究的崭新视角,揭示了一个诞生于瑞典穷乡僻壤,靠卖火柴、钢笔等小物件起家的迷你公司,如何在逆境中寻找机遇、不断创新、形成与众不同的经营模式;如何“在穷人的世界打造自己的市场”[12]5,滚雪球般缔造了今日庞大的宜家商业帝国,令人耳目一新。
(四)从理性到感性:对心理、情感因素的关注与“她”设计史的崛起
法国史学家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曾指出:“惟一真正的历史就是整体的历史。”[13]154这就要求史学家对人类社会各个层面进行全方位、整体式研究:不仅要研究重大运动、重要事件、重点人物,也要研究日常生活和升斗小民;不仅要研究物质世界,还要研究人们的心理活动、情感和思想。这就意味着史学研究的对象发生转移,历史不再狭隘地钟情于精英权贵,而转向人民大众的广阔天地。
在近代以前,感性或情感因素曾是历史书写的重要内容之一,例如奇迹、怪异事件等曾受到古代史家的关注。年鉴学派史家吕西安·费弗尔(Lucien Febvre)早在1941年时便明确指出,史家应该注意情感的历史作用。20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社会学家彼得·斯特恩斯(Peter Stearns)伉俪在《美国历史评论》中提出了研究“情感学”的必要性。美国认知心理学家唐纳德·诺曼(Donald Arthur Norman)于2004年推出《情感化设计》(EmotionalDesign:WhyWeLove(OrHate)EverydayThings, Basic Books)一书,此书副标题为“我们为何热爱或憎恶日常用品”,分别从本能层、行为层和反思层这三个不同层面考察、阐述了情感在设计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当前情感史研究的特点是注重采用文化人类学方法,针对研究的某一特定文化进行“深描”(thick description),兼顾心理学、社会学和行为学的探寻,深入挖掘其中蕴藏的文化意涵。[14]154情感史研究的理论因而得以推陈出新,例如,本诺·加梅尔(Benno Gammerl)和马克·西摩(Mark Seymour)分别提出了“情感风格”(emotional styles)和“情感舞台”(emotional arenas)的概念,将情感史的研究纳入空间、制度和文化语境的探讨之中。
20世纪70年代以来女权主义运动的高涨,激发了研究者对女性设计师及其作品的兴趣,而这一问题正是以往设计史研究所忽略的。1987年,美国历史学会主席娜塔莉·戴维斯(Natalie Zemon Davis)的史著《马丁·盖尔归来》热销,她在演讲中提出,历史女神克丽奥应为没有性别的神祇,亦非附属或听命于男性的侍婢,女性视角在史学研究中应占有一席之地。她进而提出,史学研究就其本质而言,必然具备复杂性、责任感和多重视野,在此她对女性主义的历史关怀表露无疑。[15]528-529风行草偃,女性主义的学术思想和设计研究成为新课题的一时之选。着眼于女性设计师或女性主义设计的著作,如《工作室里的天使:艺术与手工艺运动中的女性》(1979)、《女性设计工作资料手册》(1986)、《从室内设计的视角:女性主义、妇女与设计》(1989)等相继问世。
可以说,情感史研究的兴起得益于“全体史”研究的拓展,史学研究、书写的对象从传统的外在领域延伸向揭示人的心灵和情感的内在世界。史学家视角触及“她”历史、性别史等新兴史学领域,从而使设计史书写呈现多姿多彩的崭新面貌。
三、全球化、多样性与更高起点的回归
20世纪60年代,世界史学会(World History Association)成立,《世界历史杂志》出版,这与全球化进程加剧、各国之间的联系日趋紧密、布罗代尔“长时段”理论的深入人心有关,历史学家开始重新思考时间和空间这些历史研究的基本要素,一股世界史或全球史的研究热潮随之兴起。作为理论的先驱,英国史学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Geoffrey Barraclough)在1955年出版的论文集《处于变动世界中的史学》中率先提出全球史的议题。1962年,美国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Leften Stavros Stavrianos)主编的《人类全球史》出版,此书试图避免以往世界史写作中以西方为中心的历史叙事。这一点在其后来的《全球通史》一书中获得更清晰的表达:“新世界需要新史学……就如一位栖身月球的观察者从整体上对我们所在的球体进行考察时形成的观点,因而,与居住伦敦或巴黎、北京和新德里的观察者的观点判然不同。”[16]191967年,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 H. McNeill)的《世界通史》出版。这两本书被学界视为全球史的代表作,其开创之功得到公认,标志着西方史学界从西方中心论向全球史观的转变,客观上要求研究者“思接千载,视通万里”,也激发了学者对全球史书写的新探索。
21世纪以来,“大历史”观念的异军突起,将历史研究的跨度直接拓展至史前时代,对设计史而言,则意味着不再将时间上限设为人造物基本活动所发生的260万年至170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早期,而是旨在推动促成人类历史与地球历史(自然历史)之间的对话。
近几十年来,“后现代”的西方社会对“大叙述”“元叙述”进行不断解构,逐渐导致历史书写的线性发展观成为明日黄花,传统的思辨哲学和西方中心论逐渐瓦解。然而,史家对宏大叙事的兴趣却并未终结,全球史或贯穿全球视野的环境史、科技史等跨文化、跨区域的研究著述犹如千帆竞发、百舸争流,昭示着新的宏观历史学的诞生,例如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两卷本)的问世。与此同时,非西方中心、非人类中心、非线性的多元文化史观犹如几支引人瞩目的劲旅而屡建奇功,以底层研究、微观史、日常生活史、跨国研究、情感史、女性史、少数族裔史等为旗号的新文化史研究在在呈现出非中心化、非同质化的多元书写倾向,重提“历史经验”的概念,在设计史研究的实践层面力求提倡多元视角、建构多重意义的历史观。这两大平行发展的史学潮流,一端是越做越大(全球史),一端是越做越小(新文化史)。此书体现了在当代文化变迁的大背景下,对以利奥波尔德·冯·兰克(Leopold von Ranke)为代表的近代史学的省思,旨在突破学科界限、民族国家藩篱的新的知识建构。在这种史学潮流影响下,学界涌现了不少吸纳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经济学、地理学、考古学、统计学等各类学科研究成果的新设计史著。[17]15、261
2015年维克多·马格林(Victor Margolin)《世界设计史》[18]问世,标志着设计史领域再现了一种新的研究趋向。此著试图在新的宏阔视野中重写“大历史”,对人类设计史的总体走向和发展趋势提出宏观的看法和解释,而这也是对20世纪70年代以来史学领域“重写世界史”特别是“全球史”兴起的一种回应。其叙史的起点也上溯至人类出现伊始,而非通常设计史书写中以18世纪后期英国工业革命的发生为起点。
马格林在书中借鉴法国年鉴学派第二代史家巨擘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的长时段理论,建立了一个极富社会文化学色彩的设计史框架。三卷本从时序上依次划分为三个长时段:史前时代至一战、一战至二战和二战结束后至今。作者宛如手持望远镜,尝试对世界设计活动开展总体性、综合性研究。尤其是在追溯各民族文化的设计缘起时,总体史的跨学科研究方法为史前及农耕时代丰富庞杂的日常设计活动提供了阐释范式,凸显了设计对于建构早期人类社会的重要价值。
马格林认为,讲述国家、民族和其他政治实体如何利用设计来推进它们的政治和经济进程,同时展现设计物与图像如何促进国家形象的建构和全球情感的形成,是世界设计史书写的目的。将设计与更为广阔的世界史问题勾连起来,旨在寻求和确定设计在人类文化发展中的核心作用。[19]25这一段夫子自道式观点表明作者试图以一个新的全球性视角讲述一部不同版本的世界史。该书以人造物的世界为中心展开跨学科叙事,特别是受赫伯特·西蒙(Herbert Alexander Simon)“人工科学”理论的影响。该书容量庞大,涵盖了军事、交通、桥梁设计等方面的内容,可谓上下百万年、纵横数万里。处理世界各国、各区域设计史所采取的方法是混杂交错与平行叙述相结合,使它们尽可能地以复线、多元、多样貌的形式呈现在读者面前。此外,受“新文化史”研究思潮的影响,马格林对设计主流文化持批判态度,并补充了大量关于有色人种、女性、少数族裔的设计内容,细大不捐,旨在为被传统设计史轻忽、遮蔽或遗忘的书写对象正名,彰显了文化批评理论对设计史书写潜移默化的影响。
然而,世界设计史并非简单地等同于平行罗列世界各国、各地区的设计史,因为那样很容易丧失对全球性设计图景的整体性认识和多元历史表现形式共生的综合性视野,易于重新陷入各种设计史孤立发展的窠臼。全球史不同于传统世界史之处,正在于强调处于同一或相近的时间维度上、不同地域之间的横向沟通、交流互动与相互影响。此外,书中大量征引二手资料,史料考辨不够严谨,局部论述存在空白或断层,这些都需要我们清醒认识。尽管如此,马格林在古稀之年凭借一己之力,首次尝试书写一部宏大叙事的“世界设计史”,堪称空谷足音、弥足珍贵。
德国当代著名学者、荷兰莱顿大学史学教授伯恩哈德·里格尔(Bernhard Rieger)所著《甲壳虫的全球史》2014年荣获哈格利商业史奖——这是美国历史学会下属的企业史学会设立的奖项,颁发给年度最优秀商业史著作。书中作者研究了文化与科技、政治与经济、国家意志与民众心理、工业设计与广告策略,揭示了这款在20世纪30年代由德国汽车设计大师费迪南德·保时捷(Ferdinand Porsche)设计、以“甲壳虫”为名的德国元首希特勒(Adolf Hitler)倡导的“民众之车”,何以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蜚声全球、好评如潮,跻身为全球消费文化的翘楚,又何以在时代大潮的激湍澎湃中黯然谢幕。甲壳虫汽车跌宕起伏的兴衰故事堪称一部浓缩的全球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历史。
在全球化、多样性等新潮流的引领之下,年轻的设计史学善于吸纳新元素,展现出丰沛而活跃的生命力。《制造消费者:消费主义全球史》《筷子:饮食与文化》《棉花帝国:一部资本主义全球史》等著作纷纷问世,它们大多突出问题意识、注重细节并强调叙述性,关注经济、社会环境的变化,探究设计如何改变人与物、人与世界的关系,借助小小之“物”透视宏大之“史”,成为新的设计史书写力求摆脱旧有史学局限的努力方向。
四、设计史向何处去?
进入21世纪,设计史书写日益呈现纷繁复杂、日渐多样的面貌。“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设计史家的书写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但同时也拥有了更加广袤寥廓的天地而自由驰骋才思。全球史的兴起似乎代表着一个新趋向,即在新的基础上重写“大历史”,对人类设计的总的趋向和发展进行宏观综合,提出新的看法和解释。这些宏观书写的新尝试,意味着承认世界各地文明所孕育的设计史表现形式,各自皆有其存在价值及合理性。不能孤立地看待这些迥异的历史表现形式和史学观念体系,因为它们之间有着多维度、开放性的彼此联系和相互作用,尝试突破近代史学建立的条条框框——如以往仅仅采纳原始的第一手史料,事实上史学家无法掌握所有的文字语言,无力穷尽所有的相关史料。于是,当代设计史家似乎又重新回归希罗多德的时代。不过,这并非重走老路,而是在更高起点上的回归,因为当代史家的治史手段和方法已今非昔比,量化研究、统计学、心理分析等社会科学方法的普遍采用,超越了单纯定性、个别性的分析而成为史学家获取信息、建构模型的重要辅助手段。究其本质,设计史书写也是人类记忆的延伸,其目的是在总结过去、解释当下和展望未来的基础上,予人以种种启发或借鉴。从这个意义上说,西方古典史学中希罗多德的文辞华美与修昔底德的严谨练达互为补充,至今仍未过时。
从新文化史、微观史等“小写历史”层面着眼的设计史写作,则反映了西方经验历史学家回应后现代主义写作而做出的另一番努力:他们在新的思想视域中,审视理论与历史、宏大叙事与微观研究之间的张力并进行批判性反思。设计史家表现出应对后现代主义挑战的积极姿态,力求克服既有史学观念的束缚,他们的设计史研究主题日益转向广义的、日常生活的文化层面,将目光投向下层研究、性别研究、新文化研究等更广阔的天地,探索可容纳多重视角与多元方法,拓展多维度、异质性、多线并存、更具综合性色彩的设计史发展之路。正如英国新文化史家彼得·伯克(Peter Burke)所言,20世纪70年代以来,“‘新文化史’或‘社会文化史’的兴起,它常被视为更广义的‘文化转向’的一部分”[20]25。设计史受这种思潮影响,出现了从分析向叙事的转向,其不足则表现为研究的碎片化、解构主义倾向。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西方设计史为应对后现代主义对史学的挑战,形成了“大写历史”(全球史)和“小写历史”(微观史、新文化史)两大平行发展潮流。如何见“木”又见“林”,如何在设计史书写中把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个案剖析与结构透视加以结合,成为一个摆在史学家面前的“历史之问”。然而毋庸置疑,新文化史、微观史的兴起,是对崇尚“宏大叙事”所引发的大而无当历史书写方式的纠偏和补充,但随之产生的琐碎饾饤之弊,又不能不引起警醒。
美籍华裔史学家唐德刚曾提出他的史学观,即“六经皆史”“诸史皆文”“文史不分”“史以文传”[21]512的十六字真言,这几乎与西方后现代主义的史学取径不谋而合,即把史学与文学相提并论,或曰二者均需要借助语言的独特阐释。后现代主义史学家海登·怀特(Hayden White)指出,自古希腊以来的西方史学以“叙述体”为基本形式,必然要求史学家书写时收集、整理、剪裁史实,通过“情节安排”使所述故事生动感人。从这个角度来看,史学家的工作与文学家的创作并无二致。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而“德”除了指“德行”之外,一说是指写史的技术。无独有偶,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卡尔(Edward Hallett Carr,1892—1982)曾在他的《历史是什么》一书中提出,历史是“过去和现在之间永无止境的对话”[14]362,历史学是关于时间的学科,它不仅探寻事实,更是意义的建构。设计史当然也概莫能外。史学家吕森(Jörn Rüsen)提出:“只要历史研究还是一门学术性学科,我们就得谈论真理,我们就得对意味着客观性和真理的认识策略进行反思和强化。”[16]24
在我国,1997年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调整时,“设计艺术学”成为“文学”门类“艺术学” 一级学科下设的二级学科;2011年,艺术学独立升级为门类,设计学成为该门类下的一级学科,其下包含设计史、设计理论和设计批评;2022年,教育部再次调整学科专业目录,设计学成为第14个学科门类“交叉学科”下的一个一级学科,其未来的蓬勃发展值得期待。通过从整体上揭橥20世纪以来西方设计史书写的变化及其所提出的问题,撷取代表性个案,综合探讨交互性,把握其间的转捩点和关键因素,本文试图勾勒出20世纪以来西方设计史书写的发展脉络。20世纪西方设计史书写可被视为一个整体,它从20世纪之初吹响新的行动号角,尝试走出艺术史的笼罩,到20世纪70年代“新文化史”的兴起与物质文化研究的开拓,及至20世纪90年代迄今的全球化、多样性与更高起点的回归,体现了设计史的生生不息和不懈前行。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回顾20世纪以来西方设计史学的发展动向,构建和发展当代中国新的设计史学,首先不忘我国传统史学,其次关注外来史学——主要是西方史学。我们可以从中汲取有益的养分,以求真探索的精神、科学宽宏的眼光、人文主义的观念和艺术创新的手法,谱写我国当代设计史的精彩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