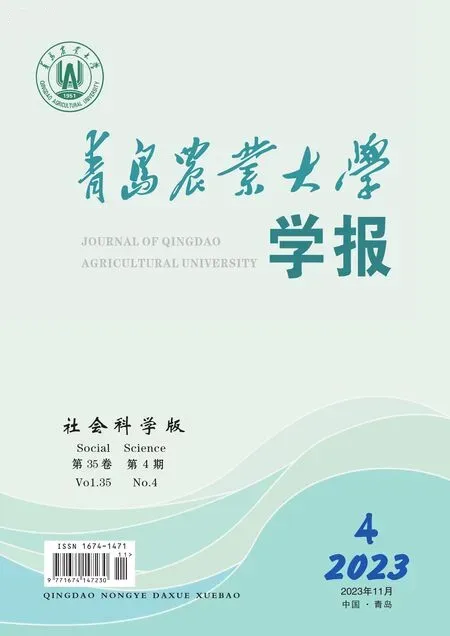德占时期台柳路的修筑与青岛城市空间拓展
吕绍勋
(青岛市社会科学院 文化与历史研究所,山东青岛 266071)
台柳路在中国交通史上极其重要,占有独特的历史地位,它的修筑和通车,成就了多个“之最”和“第一”。但是学界对于台柳路的研究却十分滞后,目前还没有一部研究台柳路的专著。有关台柳路的研究,大致散见于两类成果:一是公路修筑史类,会略及台柳路的修筑缘起和过程①;二是城市规划史和旅游史类,也会略及台柳路在城市规划、市政建设和城市交通等方面的功能②。另外,互联网上也有一些关于台柳路的文字、图片或者短视频,但大都失之零碎,甚至存在错谬。台柳路这一宝贵的学术资源,还未能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得到应有重视。以台柳路为切入点,探讨道路交通与城市空间格局,以及与社会结构变迁的研究成果,更是付之阙如。台柳路究竟给中国交通史带来了什么?成就了何种意义上的“第一”?以及对于当时的青岛(德占时期),无论是城市空间,还是城市定位,或者更深层次的社会结构,带来了怎样的影响?都需要进一步考察和界定。通过对一条道路的考察,厘清中国交通史上的节点性问题,撬动对城市空间演变的深层理解,也许正是台柳路研究的意义和价值所在。
一、德占时期青岛城市与道路的基本状况
(一)德占之前青岛的基本状况
一个地方的命名,或者一个地名所涵盖的范围,往往随着历史的变迁而发生变化。原本,历史上并没有一个叫做“青岛”的城市,而只有叫做“青岛”的海中岛屿以及青岛村、青岛口等相关称呼。“青岛”作为一座现代意义上的城市进入人们的视野,乃是在德国占领之后。德国管理当局城市建设的核心区域,即在青岛口一带。
青岛口原属即墨县管辖,据清同治版《即墨县志》所绘《七乡村庄图》,在青岛口这片土地上,散落着一些村庄,如会全、斩山、仲家洼、豹岛、扫帚滩、杨家村、亢家庄、四方等[1]。光绪十七年(1891年),清政府内阁明发上谕:“另片奏拟在胶州、烟台各海口添筑炮台等语,著照所请,行该衙门知道”[2]45,议决在青岛口设防。翌年,登州镇总兵章高元带领四个营的兵力,移驻青岛口。清兵入驻后,修建了总兵衙门,以及兵营、炮台、码头等军事设施。为满足军营的日常所需,这里的村落逐渐衍生出一些商业活动。自此以后,青岛口及其附近区域日渐发展,成了一座初具规模的市镇。据胡存约《海云堂随记》载,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青岛口“商董首事集议本口禀县商铺数目。除新近由即墨、平度、金口、海阳来此赁屋暂营者六家外,……计六十五家,航载写船多由广洋、杂货木材诸店号兼业”[2]25。算上临时租赁的商铺,青岛口已有各类商铺、作坊计71家,另外在天后宫附近,也开辟有市场。
德国占领胶州湾后,胶澳总督府每年向国会提交一份在青岛的施政和发展工作报告。在第一份报告《胶澳发展备忘录(截止到1898年10月底)》的《附录1》中,记载了德占之初整个德租地区的情况:“这一地区的居民人数,至今尚无精确统计,估计为6~8万人。主要生计依靠捕鱼尤其是种地。……在青岛、女姑口、沧口、沙子口和大鲍岛定居有一些中国商人,他们与中国沿海其他口岸进行商品买卖”[3]19。
(二)德占青岛的城市定位
自1897年德国以巨野教案为由占领胶州湾,到1914年被日本战败撤出胶州湾,共统治青岛17年。德国管理当局给胶州湾的定位是:德国在东亚重要的军事基地和商业中心。这一定位在德国占领胶州湾之前,就已广泛讨论,如1987年8月,时任德国代理外交大臣的布洛夫,记录了德皇与俄皇会见的重要内容:“德国东亚商业的发达使它有必要在东亚海洋内常驻一些帝国军舰保护这个商业,因此需要像其他东亚商业有关的国家一样,有一个在中国沿海地点……帝国海军认为山东半岛南的胶州湾是特别适宜于这个目的的一个地点”[4]139-140。《胶澳发展备忘录(截止到1898年10月底)》也印证了胶澳租界地作为军事基地和商业中心的定位:“胶澳地区海军当局所采取的一切措施都首先着眼于经济方面。在不损害该地区作为舰队基地的军事上的重要作用前提下,对这一地区的未来具有决定意义的是:首先把它发展为一个商业殖民地,即发展成为德国商团在东亚开发广阔销售市场的重要基地。”[3]3
1898年,中德签订《胶澳租界条约》,随后又签订了《租地合同》《潮平合同》和《边界合同》,明确了胶澳租借地的各处界限和总体范围。据《胶澳志》卷二《方舆志·境界》记载,胶澳商埠的范围沿袭了德占时期的计算,其区域为:“南北:自北纬三十五度五十三分三十秒起,至三十六度十六分三十秒止;东西:自东经一百二十度八分三十秒起,至一百二十度三十七分四十秒止”[5]方舆志·境界。《胶澳志》卷二《方舆志·面积》记载,“胶澳商埠区之陆地面积并所属二十五岛屿,合计共五百五十一平方公里又七五三。领海面积,即团岛岬以西之胶州湾全部满潮为界,计五百六十平方公里,又青岛湾领海(即前海)面积十六平方公里又五”[5]方舆志·面积。按照上述记载,胶澳全区海陆总面积共计1128.253平方公里。
1900年,德国管理当局发布《德属之境分为内外两界章程》,将胶澳租借地分为内、外两界。内界是市区,“分为九区,即:青岛、大包岛、小泥洼、孟家沟、小包岛、杨家村、台东镇、扫帚滩、会前等处”[6]11。后来九区合并为四区,即:青岛、大鲍岛、台东镇和台西镇。外界是乡村地区,以李村为中心。为达到分区建设的目的,德国管理当局又将内界划分为欧人区和华人区,对应于四区大体是:欧人区即青岛区,主要涵盖城市南部沿海一带(不准起盖华式房屋,仅容欧人雇用的华人限数居住);华人区主要指大鲍岛一带(其功能定位是华人商业区),以及台东、台西两镇(其功能定位是华人劳工区)。
(三)德占青岛的道路与交通
青岛位于丘陵地带,地势崎岖不平,地质多为岩石,修筑道路十分困难。“在德占胶州湾前,青岛的道路交通十分落后,既无县道,更无省道、国道,仍滞留在中国几千年来的农村旧有的传统状态。”[7]3据《胶澳志》记载,“在胶澳未经租借以前,旧有街道可通骡车者计有四路……可通独轮车者约有六路……”[5]交通志·道路。这些道路,主要用于青岛口、沙子口、沧口、李村和张村等之间的连接,总长约136里,其他“则小路崎岖,仅供步行,不堪通车”[5]交通志·道路。至于交通设施、法规和管理等,更是无从谈起。
德国占领青岛后,规划了包括铁路、港口、市内道路和市外道路的交通大格局。“规划市区选址于青岛西南海岸与山丘之间较平坦的地段,正当胶州湾入口。南面是青岛湾,由两侧伸入海中的团岛和汇泉角控制湾口;西北面是内海胶州湾,为建筑港口之地;东部有群山屏障。铁路线沿市区的西边缘、胶州湾的东岸布置,市区北侧沿铁路设置大、小港码头,使水陆交通连成一体。”[8]2
通常,道路的布局主要有两种,一是棋盘式,方向整齐,左右平行;二是放射式,以一点为中心,如日光四射。我国古代多采取棋盘式,欧洲近代多采取放射式。“德人之经营青岛,亦尝以青岛市及李村二地为中心,而筑成放射线之道路网。非惟因山川趋势之自然,亦以行政军事均有此必要也。”[5]交通志·道路
市内道路归筑城部管理,有一纵一横两条干线。《胶澳志》载:“市内之路,以今之德县、保定、大沽三路为横干线,以山东、馆陶两路为纵干线,其余纵横岐出,逐次推修。市道之设计,中央为车行道,而两侧为人行道。”[5]交通志·道路因分区治理的缘故,虽同在市内,欧人区和华人区的街道宽度并不一致。“横干线以南为欧人住所,路宽二十公尺左右……横干线以北,原名大鲍岛区,路面宽约十公尺……台西、台东两镇,街道形势纵横如两棋盘,而仍与青岛市之放射线相联络,其宽度约十公尺……台西街道尤为狭窄,其要塞道路宽度六公尺……”[5]交通志·道路托尔斯藤·华纳使用的数据和《胶澳志》虽略有出入,但大体相符;而欧人区比华人区街道宽阔整齐,却是不争的事实:“在青岛欧人区,因建筑物的最大高度为18m,所以街道宽度在18m和25m之间。……在华人商业区大鲍岛许可建造两层高的房子,道路宽度为12m或15m”[9]145。作为中国劳工聚集区的台东、台西两镇,道路宽度为8米或10米[9]114。
市外道路主要归李村警区管理,据《胶澳志》记载:“其村道之首先修筑者,为青岛-沧口一路,次则青岛-李村一路,其后逐次兴修计有十四路”[5]交通志·道路。即按《胶澳志》记载,德占时期共修筑市外道路16条。而有研究认为:“至1914年德日战争爆发时止,德帝国主义在青岛市郊筑成的公路共计15条,总长度为165.8公里……”[10]35二者之所以有16条与15条之别,是因为后者将台柳路算为1条(台东-柳树台),而《胶澳志》则将其算为2条(台东-李村,李村-柳树台)的缘故。台柳路的修筑和通车,在中国交通史和城市发展史上,是一个极为重要、极具代表性的事件。
二、德占时期台柳路的修筑、营运与作用
(一)台柳路的修筑
“台(东)-柳(树台)公路,于1903年动工兴建,1904年建成通车,全长30.3公里……路基宽度为6~9米……公路当中用碎石铺筑了宽度4米的路面,公路两旁植树。全线修建大小桥涵217座……”[10]35-36台柳路上的桥梁,桥型多样,技术先进,开始有了钢筋混凝土桁架桥和混凝土拱桥。“钢筋混凝土桥,以台柳公路王子涧、九水庵之间的最大。因为是第1次用水泥修建较大的桥梁,故当地人称‘大灰桥’。”[10]39“混凝土拱桥,以台柳公路九水庵西弹月桥为最大,因拱圈是用直径六七十厘米的方块石砌成月牙形,故名‘弹月桥’。”[10]39台柳路是德占时期青岛修筑路线最长、桥涵最多的一条公路。
按照《胶澳志》记载,德国管理当局修筑的16条市外道路(村道),台柳路其实涵盖其中两条,即“(一)由青岛经台东镇、东吴家村、保儿、河西,以达李村;(二)由李村经东李村、下河、南龙口、九水,以达柳树台”[5]交通志·道路。总体来看,德占时期修筑的市外道路,多以李村为中心,或向外辐射,或与市区相连,初步构建了青岛的市外交通系统,既方便了市区居民到乡村地区游玩、疗养,也方便了管理当局对乡村地区的统治和控制。
(二)台柳路的汽车营运
“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德帝国主义强租胶州湾后,德皇给驻青岛的胶澳总督府两辆汽车,山东境内始出现机器车(汽车)。”[11]132当时汽车被称为机器车或机动车,车的外形与从德国引进的客运马车相似,木制敞开式车身;有4个钢圈木辐条的车轮,外缘嵌固胶皮,前轮小,后轮大;方向盘在车的前方,双排座,可乘坐4人。车前部是机器,后连方向盘和变速操纵杆。汽车初时引进青岛,主要为达官显贵的私人用车,未用于经营。
“随着胶济铁路和大港码头的修建,人力客货车、马车,在承担日益增多的港、站物资集散运输和来往客商旅客运输中迅速发展。一些中外商人开始创办从事营业性客货运输的大车店、人力车行和马车行,如德商开办的‘汉斯’马车行,‘飞龙’马车行,中国商人开办的‘悦来’车行等。”[12]2211907年,德国商人开办的费·理查德商号,在台柳路上经营由市区至崂山柳树台的汽车客运。这无论是在青岛还是山东,都是最早的汽车客运路线;在全国范围内,也是最早的休闲旅游性质的汽车客运路线。“据1907年6月27日和1910年5月11日两次胶澳总督日令,规定了去柳树台和沙子口的发车时间和票价,全由德人运营。”[10]37-38其中1907年6月27日胶澳总督日令规定,每星期三、六下午1点从市区出发,每星期四、日下午5点从柳树台返程,服务对象主要是政府及其所属单位人员,每人每次2元(墨西哥元)。1910年5月11日胶澳总督日令,则增加了往复次数和频率,每星期二、五、日上午7点从市区出发,同一天下午3点半返程,主要服务对象是军人和士兵,每人每次2元[10]38。台柳路的汽车客运业务,从每周两个往返班次,增加到每周三个往返班次;其服务对象,则主要是德国驻青政府人员和士兵。
(三)台柳路的重要作用
德国管理当局除了要将青岛建设成为军事基地和商业中心外,也将旅游纳入城市的重要功能,以度假、休闲等为目的,开展旅游设施建设。市区比较著名的旅游区有别墅疗养区、维多利亚湾(今汇泉湾)等;乡村地区则主要是开发崂山的旅游。
崂山历史上曾称为劳山、牢山、不其山、劳盛山、辅唐山、鳌山等,位于青岛市中心东北部约40公里的临海处,是一座海上名山,拥有丰富的自然和人文旅游资源。“清代以前,崂山的道路交通始终处于未开发的原始状态,进出崂山的道路很少,山区道路更是崎岖难行。”[13]395虽有不少文人墨客游览崂山的事迹,但崂山还算不上现代意义上的旅游目的地。
德国占领青岛后,致力于崂山的旅游开发。1904年,德国管理当局在崂山脚下的柳树台建成“麦克伦堡疗养院”,供驻青官兵及外侨登游崂山时住宿和娱乐。麦克伦堡是当时崂山最大的疗养院,“这批建筑物所用的砖瓦、木材、水泥、钢材、玻璃等建筑材料和装饰材料,全由德国国内从海上运来青岛”[10]36。台柳路的修筑,一方面是为了转运材料的方便;另一方面,是为了德国官兵到柳树台度假休养,进山游玩。台柳路建好后,“自用汽车可直接行驶到海拔450米高处的麦克伦堡疗养院。出租车辆通常停在低处的查里车库,距疗养院大约有半个小时的徒步路程”[14]330。
台柳路的汽车营运大大改变了过去的交通面貌,人们从青岛市区进入崂山更加便捷,这在中国交通史和旅游史上,都具有里程碑意义。“1908~1909年,柳树台疗养院、疗养楼增多,成为著名的风景疗养区,每年接待疗养者和进山游客数千人,基本都是通过台柳路抵达的。”[14]330除了台柳路的汽车营运外,德国人还开通了青岛市区至太清宫的汽船,由海路至太清宫,然后登山。对于登山路线,德人也进行了详细考察,“又于山中刻石立志,辟为登山路径十有六线,依次编号,间数百步立一标志,第几路之号数刻于其上。游山者按图觅路,循标往还。内则以之锻炼市民,外则籍此招来游侣,其用意甚深远也”[5]民社志·游览。
随着胶济铁路、大港码头、台柳公路等海陆交通体系的形成,以及麦克伦堡疗养院、海滨饭店等相继投入使用,舟车利达,设施完备,外来游客逐年增多,当地游客流动性更大,青岛的旅游业开始兴旺起来,城市的旅游属性得到进一步加强。“由于旅馆规模无法满足游客的需要,旅游者纷纷预定次年夏季的客房。又引发各种旅馆、疗养院、私人别墅的建设高潮,满足游客需要的各种娱乐场所也应运而生。”[14]166
三、台柳路与青岛城市空间拓展
(一)城市空间与道路交通的辩证关系
城市是相对于乡村而言的建制区域。从生态要素看,城市的人口规模和密度都大于乡村,空间更加拥挤,对基础设施建设的要求更高。从经济要素看,城市的经济活动主要是第二或第三产业,几乎不参与农业或原材料的生产,而是通过与乡村交换,来获取这些产品;城市有更大的劳动力供给和需求市场,需要发达的交通网络,保证人流和物流的通畅。从社会要素看,城市与乡村有着不同的生活方式,城市代表着更加复杂和多元的世界观、价值观和行为模式等。从行政要素看,城市的管理更加复杂,拥有多功能的管理机构、庞大的行政队伍和广泛的政府权力。城市空间是城市范围内生态、经济、社会和行政等要素系统的空间投影,决定着各要素之间的关系是否合理性,运作是否有效。
城市空间与城市交通,二者存在复杂且重要的互馈关系。“在城市发展的每一个特殊阶段总能观察到城市交通规模或交通方式的相应变化,而城市交通的相应变化又对城市空间演化产生巨大的反作用。”[15]430交通路线、运输方式、配套设施的完善程度,决定着城市空间内各种要素之间的组合方式,塑造着城市的空间规模和空间形态。好的交通可以促进城市发展,反之,差的交通则对城市发展形成制约。交通就像城市的血液循环系统,承载着人口和物资的流动,决定着城市的活力,“只有当城市交通发展达到一定水平,人们才能够更多地参与多样化的活动,才能创造出一个富有活力的城市”[16]365。
德占时期青岛的城市空间,同样和交通紧密相关。欧人聚集的青岛区,华人聚集的大鲍岛、台东镇和台西镇等城区的建设,促进了道路的修筑和交通的发展。反之,道路的修筑,以及现代交通方式的出现,也深刻影响着青岛城市空间的演化。其中,台柳路的修筑及其汽车营运的开通,对于青岛城市三维空间的拓展(外延式),以及青岛城市旅游属性的强化(内涵式),均产生了相当深远的影响。
(二)台柳路对青岛城市空间的影响
大致来讲,城市空间状态有三个不同尺度,即建成区、都市区和城市群。建成区是一个相对闭合的完整区域,指的是非农业生产建设用地所达到的范围。都市区是指在建成区的周围,具有城市功能而又难以明确划分城乡界限的区域。城市群则是指多个城市相互联系,所构成的相对完整的集合体。
城市空间的拓展,既包括横向的城市用地面积的扩大,也包括纵向的非农业生产建设密度的增加。横向的城市空间拓展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即总是从建成区出发,沿着重要的交通干道或设施,向联系紧密的都市区推进。所以,拓展城市空间的有效途径,便是修筑道路,改善交通,扩大都市区。“对交通设施的投资会使一块原本可达性很差的土地变得更有吸引力。换言之,在城市开发中,交通设施投资通过改善可达性可以提升土地供给能力。”[16]365随着时间的推移,都市区往往最容易蜕变成建成区。崂山就是非常典型的例证。从德占之前的乡村地区,到德占时期的都市区,再到如今,崂山已是青岛的一个现代化新城区。
首先,台柳路的修筑及其汽车营运的开通,大大增强了崂山的可达性,使崂山与市区的联系更加密切,土地供给能力不断提升,空间属性也逐渐发生改变,从原来的乡村地区转变成青岛的都市区。无论是人口密度、产业结构,还是生活方式和管理模式,崂山都有了从乡村向城市转型的迹象,从而拓展了青岛城市空间的规模。
其次,台柳路的修筑及其汽车营运的开通,改变了人们的空间观和距离感,使得人们在特定时间内的出行距离更远,或者特定出行距离花费的时间更短。交通的便利、交通成本的下降,促成了人们活动场所的空间属性分离,如居住空间、就业空间和娱乐空间的分离:人们在一定的空间内居住,却在另外的空间内工作或娱乐。活动场所的空间属性分离,加上可达性的提升,刺激着人们异地消费的欲望,促进了旅游经济的发展。
再次,台柳路的修筑及其汽车营运的开通,使得海滨城市青岛,更进一步增加了“山”的内涵,使得“山海城”一体的城市形象得以确立。同时,随着旅游业的发展,青岛休闲旅游的城市内涵进一步加强,城市空间的利用方式和组织方式,不再局限于原来军事基地和商业中心的定位,而变得更加丰富和灵活。
但应该看到,城市空间拓展作为空间被开发、使用和改造的过程,其内在本质,乃是亨利·列斐伏尔所说的“空间生产”。空间生产指的不是空间内具体事物的生产(the production in space),而是指空间本身作为实践对象而被生产(the production of space)。城市空间从根本上讲,不是中性的物理空间或抽象的数学空间,而是作为社会关系综合的社会空间。城市规划往往秉持着科学的旗号,认为空间是中性的、非政治的。然而列斐伏尔指出,“空间并不是某种与意识形态和政治保持着遥远距离的科学对象(scientific objects)。相反地,它永远是政治性的和策略性的”[17]62。促进城市空间拓展的真正驱动力,绝非城市规划这类行为。城市空间作为生产关系的外显,当它不能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时,便需要进行拓展和更新,调整其内在的生产关系,从而再度激活生产力,实现有效的再生产。
(三)青岛城市空间拓展背后的社会冲突
在清末民初的历史语境下,青岛因为德国占领这一特殊机缘,而具有了某种现代属性,其发展模式在中国城市史上甚属罕见。首先,青岛与中国传统城市的现代化进程不同,“它突破了以往作为封建古国贸易口岸和海防重镇的传统发展模式,由偏僻的、无现代气息的渔村,突兀发展为一座带有明显西方色彩的现代化城市”[18]12。青岛就像一个楔子,提示着西方现代社会对于中国传统社会的强行介入。其次,青岛与其他被殖民城市相比,如北方的天津、威海,南方的澳门、香港等,也大不相同。德国管理当局对于青岛有一套完全不同的考虑,“人们希望通过这个‘模范殖民地’来展示一种特殊的、德国的殖民主义,用科学规划、专业性实施和国家监督为‘现代的’、‘讲究效益的’殖民政治提供一种典范,以区别于在香港实行的带有盎格鲁-萨克逊特色的殖民主义,即主要由私人商业利益承载的殖民主义”[19]1。
德占青岛激发了西方外来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碰撞,这种碰撞发生在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上。从宏观上看,德占青岛是楔入中国传统社会一个楔子;从微观上看,在青岛,台柳路也是楔入中国传统社会的一个楔子,是在城市内部激发西方外来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碰撞的一个重要机缘。
如前所述,德占时期的青岛分为内界(城市)和外界(乡村),内界又分为欧人区和华人商业区、华人劳工区。从内向外,整体上构建了“欧人区-华人商业区-华人劳工区-乡村地区”这样一种越往外越边缘化的阶梯状空间结构。
青岛城乡空间结构的阶梯状,其内在机制,乃是社会结构的等级划分。欧人区是德国管理当局的统治中心。距欧人区较近的华人商业区(大鲍岛),居住的主要是中国上层人士,具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而居住在华人劳工区(台东镇、台西镇)的,则多是底层劳工,他们主要服务于青岛的各类工程建设,社会影响力较弱。再往外,乡村地区(李村)距离较远,主要是农民,他们和管理当局的接触就更少了。
从欧人区到华人区再到乡村地区,越往外,德国管理当局的活动就越少,政治控制力和文化影响力越弱;相应的,中国传统意义上的社会结构和文化秩序就越鲜明。当时的青岛,其实受到两种不同文化传统的交替辐射:一方面,以欧人区为核心,经过华人区,再到乡村地区,处在西方文化从强到弱的辐射之下;另一方面,从乡村地区,到华人区,再到欧人区,则处在中国传统文化从强到弱的辐射之下。两种不同的文化传统,相互叠加、交错,形成了一个张力场;在这个张力场中,东、西文化各种元素相互碰撞,此消彼长。
但是台柳路的修筑,却大大改变了这一格局,打破了原来青岛城乡空间的二元对立和清晰界限,改变了城市空间渐进式、外推式的拓展,实现了急剧的跳跃式拓展。这种跳跃式拓展,使得德国管理当局的活动范围,从城市迅速伸展到了乡村。也就是说,台柳路表面上承担着沟通城市和乡村,实现城市区位主体入侵和接替非城市区位主体,从而拓展城市空间的角色;其实,在更深的层面上,它承担的乃是沟通东、西两种社会和文化,实现西方入侵和接替东方,并拓展西方影响力和控制力的角色。
①参见王传铎、李茂贤编著《青岛公路交通史话》(青岛出版社1990年版)、青岛市公路史编撰委员会编《青岛市公路史》(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青岛市史志办公室编《青岛市志·交通志》(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山东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山东省志·交通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刘晓燕《浅析德占时期青岛公路建设》(《黑河学刊》2016年第2期)、刘晓燕《青岛公路建设发展研究(1898—1945)》(青岛大学2016年硕士学位论文),等。
②参见叶春墀《青岛概要》(上海商务印书馆1922年版)、青岛市工务局编《青岛名胜游览指南》(青岛市工商局1935年印)、青岛市史志办公室编《青岛市志·旅游志》(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青岛市史志办公室编《青岛市志·崂山志》(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青岛市史志办公室编《青岛市志·城市规划建筑志》(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谭文婧《德占时期青岛城市规划研究》(青岛大学2009年硕士学位论文)、刘春玲《青岛近代市政建设研究(1898—1949)》(吉林大学2010年博士学位论文),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