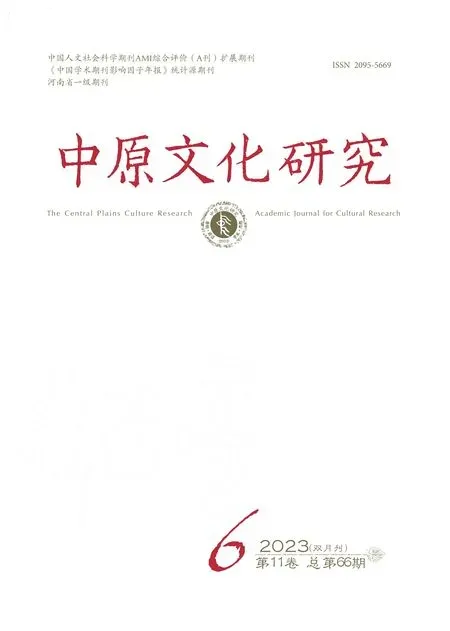中晚唐邑客的地方化与地方社会治理*
刘 顺 张笑雷
“邑客”在中晚唐的各类文献中,又有“客”“诸客”“官客”“措大”诸种称谓,乃指侨寓异乡的衣冠士流①。此处之“客”,兼有“客居”与“(食)宾客”之义。相较于高宗至玄宗时期,士人的群体流动因科举、仕宦之需而展现出以向两京迁移为目标的中央化特征,中晚唐邑客因避乱、仕宦及经济压力而侨寓他乡,呈现出再度走向地方的趋势。在此过程中,邑客成为构建地方新秩序的重要参与者,甚而为改造旧制度、形成新惯例进而凝定思想与共识提供了可能。若以长时段的观察而言,中唐而后,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调整、理学的兴起、地方精英的士绅化、地方社会生活新秩序的形成,虽有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两种相互影响的路径,但上下之间却需有一个对于自我所承担之制度角色有着明确认同与践行能力的群体。因社会动荡的直接推动走向侨寓之地的邑客,则成为士人“萃处京畿”[1]417以后,被迫适应或主动承担此种制度角色的先行者。在此意义上,观察邑客对于在地的认知、体验及其与不同群体的互动,应是理解唐宋社会转型内在机理的适恰方式。虽然,在中晚唐的士族流动中,北方中国同样是士人或士族流动的目的区域,但北方的相对动荡以及地域文化上的准军事性格,却弱化了其对于世家高门的吸引力②。以河朔三镇为典型的北方强藩,在仕宦与婚姻上的地域性与封闭性,也自然使得北方社会在社会凝聚上更易表现出路径的单一性与制度层面的地方性。相较之下,“避地衣冠尽向南”[2]的士人群体,则身处更为复杂的社会境遇之中,其与南方社会的博弈互动,也由之更具有历史的纵深意味。
一、邑客的地方化及在地认同
陈寅恪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曾言及“武后—玄宗”时期,作为李唐乃至中古社会转折点的历史意义。在此半个世纪左右的时段中,世家大族应政治生活的变化,大体完成了中央化与官僚化的角色转变,个体化官僚制及双家与多家形态构成了唐代士人日常生活的常态③。世家大族在向以两京为焦点的迁徙中,也自然经历了其与地方社会之间制度关联的脱离,并由此经历了另一种意义上的“邑客”生活。及安史乱发,以“走向南方”为主的异地寓居,于士族而言,已殊非一种陌生的生活形态。甚而,迁徙目的地的高度重合,会为士族间的关系网络增加新的触角延伸空间。与此同时,两京的安定以及新的均衡态势的大体形成,亦为寄寓异地的邑客群体提供了与政治高层强化关系网络的可能。客观的关系网络的存在与邑客对于此种关系网络社会功能的理解与期待,共同构成了邑客如何理解自我与在地关系的重要参照。但相较于借助科举寻求向上流动,以假、摄等方式获取地方的制度性角色与收益,更易见出邑客在地方的路径特色。
邑客对于地方的认同,虽然可因其代际绵延而自然生成,但维持相对地方社会阶层优势的利益诉求,却使得邑客必须依赖于国家层面的制度保障。只有通过制度并善于利用制度,方能实现个体与家族之社会角色和功能的稳固及有序提升。虽然,邑客在中晚唐科举中被逐步边缘化,其与两京核心权贵家族的关系更趋疏离,但中晚唐地方行政及财政制度的新变化,却在一个半世纪的历史进程中,为邑客提供了另外一种应对生存危机的制度渠道。《唐会要》卷七十九载大中五年(851 年)十月,中书门下奏:“河东、潞府、邠宁、泾原、灵武、振武、鄜坊、沧德、易定、夏州、三川等道,或道路悬远,或俸料单微,每年选人,多不肯受,若一例不许,则都俸不在给留别限,仍勒知后判官,不许则都无王官,今请前件数道,除县令、录事参军外,其判司、尉、县丞、簿,每年量许奏三员。”[3]1452安史之乱后,因节镇体系的确立与盐铁转运体系的形成,以及官员人事任免中使职的职事官化,中晚唐已难以维持一官之任尽出吏部的旧制度,而不得不认可地方节镇、观察及度支、盐铁诸使对于人事选任权力的分享,并予以明确的制度规定。大中五年的中书门下奏议,不过为李唐中晚期颇为常见的政治议题④。虽然制度规定会对此种选任权力构成限制,但同时也是对此种权力正当性的认可。地方州牧长官对于吏部的分权,会体现出形式上的“僭越”,在习于以中央集权与制度的统一性为“大一统”之判准的认知传统中,会不免以之为国家治理中亟待治理的病态。但如此理解,则不免会忽视唐人的当世接受。在中晚唐人关于士人选任诸弊端的言论中,“修身与及物”出现的频次极高⑤,而甚少对地方人事任免权的激烈批评。中晚唐人斥责对抗王廷的地方强藩,但并不否认节镇体系对于王朝安全的贡献。相较于后人的“时代意见”,时人的“历史意见”,应更能体现出唐人对于王朝“有效治理”之难度的清醒。
地方对吏部的分权,为流寓他乡、“所业唯官”[4]763的邑客提供了科举与吏部铨选之外的另一条维持生计或重振家声的制度路径。但正如邑客在科举中的边缘化,在地方征辟选任的制度实践中,也越来越少有邑客通过特定的历史机遇与人际网络向高层跃升。在地方系统的官员选任中,使府幕僚的辟召为人瞩目,颇为难得。邑客任职地方以州县基层文官的假摄、差摄最为常见。李商隐《前摄临桂县令李文俨》曰:“右件官,我李本枝,诸刘贵族,能彰美锦,令肃阳鱎。临桂既有正官,丰水方思健令。无辞久假,勉慰一同。已闻言偃之弦歌,更伫潘仁之桃李。事须差摄丰水县令。”[5]1397李文俨在差摄丰水县令之前,已有差摄临桂县令等职的经历,且政绩较佳。若衡以文意,李文俨应出身李唐皇族,但代际更迭,族属疏远,已与一般士人无别。所谓“差摄”,“皆使自辟召,然后上闻。其未奉报者称摄。(其节度、防御等使僚佐辟奏之例,亦如之)”[1]890。差摄虽并非经由吏部除授程序之确认的职任代理,有临时差遣的特点,然在实际的地方政治运作中,差摄行为不免常态化。文宗《谕刺史诏》曰:“刺史分忧,得以专达。事有违法,观察使然后奏闻。如闻州司常务,巨细所裁,官吏移摄,将士解补,占留支用刑狱等,动须禀奉,不得自专,虽有政能,无所施设,选置长吏,将何责成?”[6]752宪宗对于刺史职责的明确,乃是元和时期强调州之独立性以弱化节镇、观察权力的制度设计,王廷以诏令的方式确认刺史拥有的官吏移摄的职权。相较于唐代前期官员假摄多见于边远州县,且以在任官员兼领他职为主,中晚唐的差摄则以未曾任官者或前资官代领相应职务,其区域亦自边远区域、地方强藩扩展而至内地州县⑥。州县摄官非正员官,上升的前景有限,俸禄应相对微薄。李德裕《潞磁等四州县令录事参军状》曰:“右,缘地贫俸薄,无人情愿,多是假摄,破害疲甿。”[6]7208状文中所言及的州县归属昭义,素有贫乏俭朴之风,州县官多为差摄之人,其他边远州县的官员选任应大体相类。以此,既满足地方治理的需要,也可为在地方寓居而艰于谋生的邑客提供生活的保障。《太平广记》卷二百五十六“苏芸”条曰:“岭表多假吏,而里巷目为使君,而贫窭徒行者甚众。元和中,进士苏芸南地淹游,尝有诗云:郭里多榕树,街中足使君。”[7]1993同书卷三百八十五“崔绍”条云:“南越会府,有摄官承乏之利,济沦落羁滞衣冠。绍迫于冻馁,常屈至于此。”[7]3068然即使前景黯淡,俸禄难言丰厚,但相较于庞大的邑客群体,差摄依然是艰于谋生者难得的机遇。这也使得邑客与在任中高层官员间的姻旧关系变得尤为重要。此种关系网络在内地使府僚佐、州县差摄之职的竞争中,影响更为明确。
崔致远为前湖南观察巡官裴璙致书高骈曰:“右件人是某座主侍郎再从弟……伏请太尉相公,念以程穷计尽,愍其柱促声哀,特赐于庐、寿管内场院,或堰埭中补署散职,所冀月有俸入,便获安家。”[8]435-436在推荐裴璙的信中,某座主侍郎再从弟的身份是崔致远刻意强调的信息,即使在裴璙未能获得任职机会而前去襄阳时,“侍郎”依然是左右裴璙行动选择的主导因素。崔致远如此处理,自然是根据政坛惯例推敲高骈心理,以提升推荐成功的概率。而另据《唐语林校证》卷一所载“李蠙”事,更易见出关系网络的影响:“李尚书蠙性仁爱,厚于中外亲戚,时推为首。尝为一簿,遍记内外宗族姓名,及其所居郡县,置于左右。历官南曹。牧守及选人相知者赴所任,常阅籍以嘱之。”[9]21但关系网络的维持,依赖于构成者相互间情感的厚薄及资源的丰俭,难以承受代际更迭与宦途升沉的挑战。无论邑客如何经营和依赖此种关系网络,受益者只能是其中的少数。大多数人终究要尝试寻找合乎在地特点的治生持家的方式,这也是邑客在地化过程中颇为重要的一步。
《太平广记》卷一百六十五《郑浣》篇载其官河南时,有务农之五服之孙干谒。此故事中有唐人颇为熟悉的“因食而叹”情节[7]1204,也让故事处于疑信之间。然郑孙久居乡里,以农事为家计,乡里也以农人待之,则是邑客寄寓生活的一种有文献为佐证的新变化,颇为可信。郑孙本期望通过与郑浣间的亲缘关系,获得承乏一尉的机会,以改善寄寓的生存状态。但故事以近乎刻意为之的情节设计,终使其期望落空。如若不执着于情节的个体真实,故事所表达的乃是亲缘网络终难以依靠的现实。正是关系网络维持的艰难,持家治生的压迫之下,邑客的行为选择亦将会有更为现实的转向。《唐故右金吾卫仓曹参军郑府君墓志铭并叙》曰:“府君乃喟然南来,复垦于是,疏卑为溉,陪高而亩,及今三年,而岁入千斛。是岁分命迓二嫂氏洎诸孤于二京。”[10]2558-2559郑鲁迫于生计,选择离京入荆而以南亩之业维持家庭生活。虽然,依据墓志的简短文字,难以推知郑鲁是否有亲身耕作的经历,但参照刘轲“日有芟夷畚筑之役”[11]759和杜牧“烈日笠首,自督耕夫”[4]763的描述,亦可想象其对田间劳作应有的参与程度。从事南亩之业,对于曾经“所业为官”的邑客而言,乃是固化其与地方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以南亩收益治生持家,通常并非依赖邑客自身向田间劳作的投入,而是以地产田亩的购置为主导方式。邑客曾经拥有的政治、经济优势,也为其地方的田亩购置提供了便利。与田亩购置相联系的即是房屋(别业)的修葺,以及因“衣冠多难,归葬则稀”[12]所导致的归葬地的新选择,邑客也将面临着向乡村富民的身份转化,其间亦偶有以商而富者。虽然,此一过程的发生需要较长的时间,但其预示着新的变化的开始,却也是难以否认的事实。
与邑客购置田亩以治生持家相类,其婚姻关系的选择,也会表现出新的变化。“(关图)后寓居江陵,有鹾贾常某是,囊蓄千金,三峡人也,亦家于江陵,深结托图,图亦以长者待之。数载,常公殂,有一子,状貌颇有儒雅之风纪,而略晓文墨。图竟以其妹妻之,则常修也。”[11]949关图寓居江陵时,嫁妹于盐商之子,不合士族婚姻选择的惯例,与其寓居江陵的生存处境及盐商财力雄厚,应甚有关联。而盐商之子通过读书习业亦可参与科举,则更便于寄寓士人与地方有力者的联合,以提升家族的社会地位,对抗阶层滑落的危机。虽然,关图的选择相左于依然强大的士族圈内联姻的传统⑦,但却无疑展示了一种新的地方关系网络的可能,只是,此种可能由特例而常态,却至两宋之时方始达成⑧。崔致远《双女坟记》记双女议婚之始末曰:“致远乃问曰:‘娘子居在何方?族序是谁?’紫裙者陨泪曰:‘儿与小妹,溧水县楚城乡张氏之二女也。先父不为县吏,独占乡豪,富似铜山,侈同金谷。及姊年十八,妹年十六,父母论嫁,阿奴则订婚盐商,小妹则许嫁茗估。姊妹每说移天,未满于心。郁结难伸,遽至夭亡。’”[8]762崔致远所遇之姊妹二人,乃地方富豪之女,希望能与士人结缘,因不满父母的婚姻安排郁郁而终。在崔致远对双女婚姻心态的转述中,可以推见士商之间的联姻已是地方社会之新趋势。
不过,整体来看,寄寓士人与地方社会间的关系并不融洽,“江陵在唐世,号衣冠薮泽,人言琵琶多于饭甑,措大多于鲫鱼。……大凡无艺子弟,率以门阀轻薄,广明之乱,遭罹甚多,咸自致也”[13]。邑客与地方社会之间的冲突,或缘于士族子弟“轻薄”,对于地方规则或惯习缺乏尊重,而更为根本的原因,应是邑客群体对于基层利益的侵夺。邑客与地方社会关系的转变,或须等到门第社会消融、地方豪强成为王朝权力之新基础时,方始有真正的可能⑨。在此过程中,邑客与乡村有力者之间的直接对抗,构成了新型地方关系生成的主要表现。
二、邑客在地方治理中的制度空间
侨寓他乡的邑客,于地方社会而言,在其迁入之初,自然是一种相对陌生的社会力量。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邑客与地方势力之间即使并不必然和畅融洽,亦不妨碍前者对于地方社会的认知与体察程度的提升,更遑论邑客中本即有“前资官”这一有地方任职经历的群体。而邑客对于政治制度及其运作所相关之程序、惯例的谙熟,也使其更能有效感知政治风向的变化、揣摩政治行动的意图、体察行动参与者的诉求与底线,进而应和政治实践的节奏。相比于基层胥吏与民众,邑客群体无疑具有更为强大的、依托政治制度及其相关资源参与地方治理的能力。虽然,邑客在地方的生存及向两京社会的阶层流动,依赖于士族间的利益与情感关系网络,但对于国家治理的制度性权力的分享,方是其能够适应地方、维持影响,甚而参与地方性与全局性制度生成的关键所在。
世家大族向两京的迁徙,是地方势力以中央化与官僚化的方式对于制度变迁的适应,但由此而形成的士人与乡里社会的分离,却不免导致李唐政治、文化势力与社会势力之间的脱节,进而弱化了王廷对于基层社会的管理能力。当此种管理能力的不足因安史之乱的发生被焦点化时,对于基层的陌生即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地方治理趋于实务取向时,如何有效掌控地方信息,成为王廷调整地方行政及赋税制度,并由此明确官员的身份、职任与权力边界的基础。作为权力末端的胥吏,虽然是王廷基层社会管理的主要执行者,但胥吏群体因其政治德性的不足,极易成为以权谋私、残害民众的秩序破坏者,难以有效承担王廷与地方社会信息沟通的职责⑩。而出任地方的州县长官又多频繁迁转,难久在其任,自然须依赖谙熟地方风土者,以建立顺畅的信息沟通渠道。
长庆元年(821 年),张弘靖任幽州节度使时,曾密奏挽留已赴京应监察御史之命的张彻,其理由为“臣又始至孤怯,须强佐乃济”[14]2604。开成五年(840 年)十一月,岭南节度使卢均奏曰:“当道伏以海峤择吏与江淮不同,若非谙熟土风,即难搜求民瘼。”[3]1371卢均以岭南僻远,非仕宦乐土,若以吏部铨选方式选任官员,则难得干能之官,无法承担岭南地方治理的责任。故而,奏请以节度使便宜征辟选任的方式,回应了官僚铨选在政治实践中的制度缺陷。
以其言及的江淮而言,“谙熟风土”同样是州县长官僚佐选任的重要标准。罗隐《妖乱志》述吕用之事,言其久客广陵“公私利病,无不详熟”[15]。吕用之虽非严格意义上的邑客,但其通文字、久客广陵且有议政能力,已大体近于邑客。其所以能够引起高骈的关注并成为节度使府的重要幕僚,得益于对江淮风土的谙熟。杜牧为黄州刺史时,以“刺史知之”[4]902为地方治理的关键。“知之”是州县长官对于地方历史与现状的掌握,涉及经济、文化、社会民生诸多层面。对于多为异地为官的中高层官僚而言,殊非易事。其所以能“知之”,则不仅需要州县长官相应的德性与能力,亦依赖熟悉当地民情者的信息提供。在州县长官的日常行政中,常可见到“宾客”的身影。州县长官应接宾客,甚至引起王廷关注而以诏令予以训诫。武宗会昌元年(841 年)正月诏曰:“州县官比闻纵情杯酒之间,施刑喜怒之际,致使簿书停废,狱讼滞冤。其县令每月非暇日不得辄会宾客游宴。其刺史除暇日外,有宾客须申宴饯者听之,仍须简省。诸道观察使任居廉察,表率一方,宜自励清规,以为程法。”[16]州县长官应接宾客,自然有构建关系网络与诗酒娱情的考量,然宾客的往来流动,既是信息的流通与人际网络的构建,也是信息网络的形成过程。州县长官对于信息的依赖以及地方治理的策略选择,于日常宴饮之风皆有助成之功⑪。而“宾客”对于信息的获取,则不仅依赖久客地方的生存经验,更依托于此一群体在基层社会的以“摄”“假摄”为任官方式的为官经历。此种经历,既提供了其认知与体验地方社会的制度便利,亦有效磨炼了其参与地方治理的行政经历及行政能力。邑客在地方社会中所承担的角色,使得邑客的“摄”“假摄”超越了个体或家族之私而有了“公”的制度性权力的特点。“右件官,顷佐一门,实扬二职。……勿耻上官,以渝清节。事须差摄柳州录事参军。”[5]1407韦重在差摄柳州录事参军之前,即有任职地方的经历,并有一定的为政口碑,其本人具经学之优长且有崔琰之貌。故而,当柳州录事参军之职空缺时,韦重遂有谋求假摄的机会。在此种地方官员的任命奏请过程中,“邑客”多依赖于地方长官的垂青拔擢,故而易于表现出相应的人身依附关系。其对于州镇长官而言,其不仅是地方治理的协助者,同时也是其政绩及形象制作的主要发起者或参与人。而当邑客所承担的信息沟通职责不再以地方治理为焦点,呈现出向更高阶层流动的特点时,舆论制作的意味便由之凸显。
《全唐文》卷七百四十六卢子骏《濠州刺史刘公善政述》曰:
客有自濠梁来者,余讯之曰:“濠梁之政何如?”客曰:“今刺史彭城刘公,始受命至徐方,与廉使约曰:‘诏条节度团练兵镇巡内州者,悉以隶州,今濠州未如诏条,请如诏条。廉使多称军须卒迫,征科若干,不如期以军法从事,皆两税敕额外也,今请非诏敕不征。’廉使曰:‘喏。’‘濠州每年率供武宁军将士粮一十万石,斗取耗一升送廉使,州自取一升给他费。吏因缘而更盗,则三倍矣。自今请准仓部式外不入。’廉使曰:‘喏。’刘公至止,坚守不渝,由是州无他门,赋无横敛,人一知教,熙熙然如登春台矣。”……刘公治郡,嘉绩长美,详举则繁也,亦取大遗小之义耳。其书以备太史氏采录焉。[6]7729
在地方政治舆论的制作中,相较于地方民众,邑客因其学识与政治经验更能敏锐捕捉王廷政治的新动向,从而策略性地凸显符合高层期待的治理事迹与官员形象。邑客在与滁州长史卢子骏的对谈中,刻意描述了濠州刺史对于王廷处分节镇与州郡权责诏令的坚持。此一点,若衡之于宪宗而后王廷调整德宗朝政治惯例,强化州郡相对于节镇的军政与民事权力,从而确立新型的中央—地方关系的政治意图,则可见出邑客在舆论制作上的判断力。由于政绩考课事关官员的仕途迁转,官员政绩的舆论制作也更易展现其渠道的制度化及展演内容的模式化。“大和四年,高陵人李士清等六十三人思前令刘君之德,诣县请金石刻。县令以状申府,府以状考于明法吏,吏上言:‘谨按宝应诏书,凡以政绩将立碑者,其具所纪之文上尚书考功,有司考其词宜有纪者乃奏。’明年八月庚午,诏曰:可。”[17]德政碑本为中央王廷褒奖官员的政绩激励工具,须遵循特定的奏请规定方能刻石立碑⑫。对于基层民众而言,德政碑的奏请理应为一种颇为陌生的政治实践,无论是动议的发起、群体意图的表达,还是文本的书写以及制度渠道与程序,若无熟悉相关政治运作者的引领,即难以成为地方社会一种具有仪式景观效应的政治事件。出于不同际遇与动机而走向地方的邑客,无疑是此种政治舆论及政治景观极为适恰的引领者与制作人。但毫无疑问,“邑客居人,攀辕隘路”[18]的舆论制作总不免掺杂诸多的私利考量而失实过度,难以取信⑬。
孙樵《书褒城驿屋壁》曰:
有老甿笑于旁,且曰:“举今州县皆驿也。……凡与天子共治天下者,刺史、县令而已,以其耳目接于民,而政令速于行也。今朝廷命官,既已轻任刺史、县令,而又促数于更易,且刺史、县令,远者三岁一更,近者一二岁再更,故州县之政,苟有不利于民可以出意革去其甚者,在刺史曰:‘明日我即去,何用如此!’在县令亦曰:‘明日我即去,何用如此!’当愁醉,当饥饱鲜,囊帛椟金,笑与秩终。呜呼,州县真驿耶!矧更代之隟,黠吏因缘,恣为奸欺以卖州县者乎?”[19]
虽然,唐代前期内重外轻的任官心态已不尽为中晚唐官僚所接受⑭,褒城老者之言或有过当之处,但其对于官员频于迁转的描述,则符合中晚唐的官员任免的惯例。短暂的任期,难以培养州县长官对于任职地的情感认同,若再同时考量其德性的良窳与治理能力的高低,所谓地方治理的实绩自然不免有刻意制作的成分。但地方人员构成的复杂以及舆论可能存在的分歧,为自上而下的信息获取提供了参考比对的可能。如此,均为邑客的地方生存提供了制度空间。
文宗大和七年(833 年)七月,中书门下奏曰:
应诸州刺史除授序迁,须凭显效。若非责实,无以劝人。近者受代归朝,皆望超擢,在郡治绩,无由尽知。或自陈制置事条,固难取信。或别求本道荐状,多是徇情。将明宪章,在核名实。伏请自今已后,刺史得替代,待去郡一个月后,委知州上佐,及录事参军,各下诸县,取耆老百姓等状。如有兴利除害、惠及生民、廉洁奉公、肃清风教者,各具事实,申本道观察使检勘得实……如事不可称者,不在荐限。仍望委度支、盐铁分巡院内官同访察,各申报本使录奏。[3]1205-1206
对于地方官僚群体由于能力不及与自利取向所可能导致的“拼凑应对”与“共谋行为”⑮,王廷本既有极为清晰的认知,亦尝试通过制度设计予以应对。其过程即是在国家治理的运作实践中,多重行动逻辑交互影响,进而推动制度变迁的历史过程。作为个体或群体的政治行动的参与者,其对于关联群体行动逻辑的感知越清晰,生成与维护自我群体行动逻辑的能力越强大,也即意味着在政治生活中有着更高的参与制度生成的概率。邑客自两京或本籍向异地的流动,虽然削弱了此一群体在科举以及仕途迁转上所享有的部分便利,但再度走向地方社会,却增强了其与地方社会的关联度。这一具有“游客所聚,易生讥议”[4]737之接受印象的群体,因所具有的政治经验与学养,在本土地方势力逐步崛起的进程中,确保了其在国家治理中不可替代的位置。
三、邑客的“经典”像
中晚唐的社会变化,自地方社会的变化而言,不仅为邑客的移入所带来的问题与机遇,同时也缘于自开元、天宝以来的唐代乡村基层组织结构的变化。伴随户口的增长,作为自然居民点的“村”的功能得以扩张与强化,并逐步取代“里”的位置,形成了“县—乡—村”的基层组织结构⑯。安史之乱后,王廷为应对财政危机,增大了对于乡村的控制力度,村落作为管理实体的角色越趋明确,胥吏阶层在地方治理中所发挥的影响也日益重要,赋役、户籍(保簿)以及日常生活秩序等与地方社会相关的诸多事务,均有此一群体的深度参与⑰。此外,因经济或宗族势力而影响一方的地方有力者,也是地方生活秩序的主导者之一。邑客在地方社会,其所要分享的制度权力、社会财富乃至民间舆论,常会和胥吏与土豪之间形成交叉而产生不同层面的冲突。也正是在此博弈中,邑客逐步形成了对于自我形象的经典想象,并同时为地方“士绅”的形成提示了生成的基本路径。
胥吏虽大多处于权力的末端,却是官方政令的主要执行者,体量庞大并直接管理基层民众与地方社会。州县胥吏之职任多与庶务相关,本难有为国史载录或士人记述的机遇,但玄宗时期强化乡里控制的括户、造籍诸行为,提升了州县胥吏的被关注度,并多聚焦于此一群体与基层民众的冲突。安史之乱后,财税领域的相应调整,则更使地方胥吏的形象趋于恶化。《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二载:“租庸使元载以江、淮虽经兵荒,其民比诸道犹有资产,乃按籍举八年租调之违负及逋逃者,计其大数而征之;择豪吏为县令而督之,不问负之有无,资之高下,察民有粟帛者发徒围之,籍其所有而中分之……民有蓄谷十斛者,则重足以待命,或相聚山泽为群盗,州县不能制。”[20]相较于胥吏偏于身份说明的中性表述,“豪吏”作为地方有力者,则具有更明确的作为政府“爪牙”且有极高自利取向的意味。此种依违两间的特性,让豪吏既无法成为地方民众利益的维护者,也无法成为州县长官依赖的地方治理的合作者。在中晚唐的各类文献中,“豪吏”每以被利用、打压的形象见之于人。
王谠《唐语林》载韩滉之事云:“韩晋公镇浙西地,痛行捶挞,人皆股慄。时德宗幸梁洋,众心遽惑,公控领十五部人不动摇,而遍惩里胥。”[9]62由于中晚唐节镇类型与治理方式的地域差异,加之经济方式与自然环境的影响,北方中国地方势力的兴起,以中下层军士影响节镇性格及其权力格局为表现形式⑱;南方中国,尤其是江淮社会,则重点表现为土豪势力对原有地方权力结构与利益分配机制的冲击⑲。由豪而吏是地方势力利益诉求的表达,而以出于土豪者为吏,则是王朝官员对于地方关系格局的顺应与利用。在上下互动与博弈中,有所谓“狡吏不畏刑”[21]之说。豪吏既难以突破自利取向的限制,成为地方利益的维护者,也难以在短期内适应政局变化所带来的政治规则与惯例的调整,并具有相应的自我正当化的言说与论证能力。进退难得其中之际,豪吏在社会治理中的形象亦颇为负面。虽然,韩滉的应对策略并不能改变土豪崛起的趋势,但所赢得的赞誉,却是此时期官员群体心态的自然展露。
皇甫湜《吉州刺史厅壁记》曰:“御史中丞张公历刺缙云、浔阳,用清白端正之治。诏书宠褒,赐以金紫,移莅于吉。下车之初,视薄书,薄书棼如丝;视胥吏,胥吏沸如糜。召诘其官,皆眊然如酲;登进其民,皆薾然而疲。”[6]7082皇甫湜对于吉州州政不理的分析,首言簿书,次及胥吏,其次序非出偶然,而是中唐以来士人自省风气中,对于地方治理之要因的流行认知。在王朝对乡里社会的控制中,以田制、户籍与乡里制度为支柱,而户籍与乡里制度则是王朝实现乡村控制的根本保障⑳。开元、天宝时期,胥吏群体随着王朝控制乡村意图的强化而渐次增加其在地方政治中的曝光度,并逐步成为理解官员地方治理的参照系。胥吏熟悉乡村社会,又长于庶务尤其是簿籍的编制,故而成为最为熟稔地方社会相关信息的群体。当此一群体尚未完全摆脱道德水准低下的接受标签时,即成为地方政治败坏的主因或推手。而中唐士人自省风气中,对于吏干之能的强调㉑,也形成了地方长官熟悉簿籍编制、赋役调节及底层信息的任官理念,豪吏遂成为上下其手、亟待打击整顿的对象。元稹长庆三年(823 年)《同州奏均田状》曰:“臣自到州,便欲差官检量。又虑疲人烦扰,昨因农务稍暇,臣遂设法各令百姓自通手实状。又令里正书手等傍为稳审,并不遣官吏擅到村乡。百姓等皆知臣欲一例均平,所通田地,略无欺隐。臣便据所通,悉与除去逃户荒地及河浸沙掩等地,其余见余顷亩,然取两税元额地数,通计七县沃瘠,一例作分抽税。”[22]996地方长官对于地方行政的掌控依赖于对地方信息的了解,及以簿籍编制为基础的赋役分派。唯有如此,方能弱化对豪吏群体的依赖㉒。同时,则须强化法令规则在地方治理中的作用,以达成对于胥吏群体权责的明确约束,限制其利用法令谋利或享有超越法令的特权。元稹在同州的治理,大体即以上思路。邑客作为寄寓地方且与两京保持关系网络及文化认同的群体,在以假摄为主要制度路径的地方治理中,自然延续了压制胥吏的为政策略。
李商隐《为荥阳公桂州署防御等官牒·李克勤》曰:“右件官,始在宦途,便彰政术。……事须差摄修仁县令。”[5]1404李克勤在假摄修仁县令之前,即有任官经历,且政绩较佳,对地方治理诸问题应有较为真切的体会。在此差摄官牒中,李商隐既强调了实务之能及勤于吏治的必要,同时又言及洁己奉公及抑制奸豪的为政德性与举措。虽然,官牒作为日常政府公文不免有模式书写的倾向,但无论是刻意强调,抑或惯习使然,“奸豪”均是地方治理中的难题。而若放大邑客所含摄的群体,考察曾有寄寓经历而终有幸升入中高层的官僚群体,则抑制豪吏的举措可屡见于文本书写:
先府君讳让,字逊叔……公佐三府,倅三镇,皆以重德大度,仪刑宾阶。三原剧邑,多豪强,公春秋三十有三,人以为难。既下车,杖桀黠者一,他皆屏束。……去豪右,恤茕独,收葬枯骨一万余所,招复流庸五千余户。未数月报政,周岁乞留,清在人谣,著于州状。宾客因远而至,日月相属。[10]2334
吕让近四十年的仕宦生涯,有丰富使府及州县的任职经历,深谙地方社会的运作逻辑。在其子对他仕宦生涯的回眸中,抑制豪右是值得一书再书的重要政绩。无论是近畿之地,还是东海之滨,地方豪强均是地方社会有效治理的对抗力量。虽然,此种书写并不必然反映基层社会的现实,但并不影响“豪吏束手”作为官员政绩之重要参照的位置㉓。凡此,均可见出此一治理模式的影响。而“豪吏束手”缘于地方长官的为政理念而外,也因在争夺地方官吏任职资格的过程中,邑客对于假摄之权的诉求,能够得到姻旧关系网络与王廷制度的支持,从而实际降低了豪吏假摄地方州县主要职任的概率,形成事实上对于豪吏地方影响力的限制。
“豪吏束手”指向以王廷为主导的基层社会秩序的构建,无论是地方治理的现实,抑或是纸上的构拟,作为地方秩序的引领者或重建者,邑客均须承担对于基层民众之教化职责。这也意味着,邑客将实际扮演着地方“名望家”的角色㉔。“(孙抃)其系出于富春……七世祖曰朴,始徙富春,籍于长安……大中五年,从辟剑南节度使杜悰府为掌书记。其子曰长儒,摄彭山县令,既以秩满罢,因家眉山。大治居处,又构造重楼以贮书,日延四方豪彦,讲学其间。于是蜀人号为‘书楼孙家’。自尔子孙不复东归,遂占眉山名数。高曾以来,历五代丧乱,晦遁不出,力田以自给,取足而已,不求赢蓄。”[23]邑客在地方社会逐步的在地化,会自然强化其对地方社会的认同,只是此种认同的发生需经代际的更迭方始可能。而地方社会对于邑客的认同,则需要邑客凭借自身的文化与经济诸优势,成为乡里社会利益的维护者。孙抃的家族经历就中晚唐五代的历史发展而言,可视为邑客在地方博弈的过程中,对于地方领袖责任的逐步分担。在此地方新秩序的生成过程中,邑客也自然逐步承担起救济乡里的责任。元稹《与史官韩郎中书》曰:“(甄逢)耕先人旧田于襄之宜城,读书为文,不诣州里……岁穰则施余于其邻里乡党之不能自持者。”[22]848符载《邓州刺史厅壁记》曰:“夫人君在上,百辟在下,其欲正生人之性命,敷大中之教化,扶淫僭之风俗,行明白之刑赏。”[6]7056无论是利益的分享,还是礼仪教化、风俗整顿,均是邑客对于王廷所倡导的政治伦理的具体实践。也是在此实践的过程中,邑客与豪吏之间的博弈,将会呈现出既对抗又合作的共生形态,这意味着邑客对于地方社会运作逻辑体悟和参与度的深化。其典型的表现即是对地方“富商大贾”的态度转变。
地方富商大贾的崛起,有王廷在安史之乱后对榷盐、茶的制度助推,也与地方节镇争夺利源存有关联㉕。地方富商在势力发展的过程中,会寻求节镇与州县长官不同层面的支持以获取利益,由此,会带来地方治理的难题。同时,富商阶层对于地方乡村日常伦理的冲击,“广占良田,多滞积贮”[24]对乡村利益的侵占及经济的操控,亦引发激烈的社会批评㉖。在富商所受的诸多批评中,自然有其为富不仁的因素,但更为根本的,是对商业之社会功能的认知。相较而言,柳宗元则认为“夫富室,贫之母也”,故而“诚不可破坏。然使其大幸而役于下,则又不可”[25]。其观念更为务实,亦颇有深度。与此同时,韩愈在此类问题上的理解,亦能预示中唐儒学问题回应的方向:“(张)平叔请限商人,盐纳官后,不得辄于诸军诸使觅职掌把钱捉店看守庄硙,以求影庇。请令所在官吏严加防察,如有违犯,应有资财并令纳官,仍牒送府县充所由者。臣以为盐商纳榷,为官粜盐。子父相承,坐受厚利。比百姓实则校优。今既夺其业,又禁不得求觅职事及为人把钱捉店,看守庄硙,不知何罪,一朝穷蹙之也?若必行此,则富商大贾必生怨恨。或收市重宝,逃入反侧之地,以资寇盗,此又不可不虑也。”[14]3029-3030地方富民本身即是豪吏的主要来源,难以通过社会舆论与制度规定的影响,主张自身的群体利益。这也意味着,具有在地文化优势的邑客,不仅在治生方式上会有“学商人逐十一之利”[7]3362的选择,而且需在体认富民社会功能的基础上,为其利益保护及相应的政治与文化权力,提供更为有效的舆论支持。
综上所述,邑客在中晚唐社会的出现,既缘于“中央—地方”关系调整意图下的制度变革,亦是此种制度变革的政治与社会效应。在门第政治的余晖中,作为具有相应政治、文化诸优势的外来群体,邑客对于科举及两京姻旧人际网络的依赖,延续了士族政治生活的旧传统。但科举竞争的圈内压力以及人际网络在代际更迭中的松散倾向,迫使邑客与地方势力在竞争中,逐步走向合作共生。邑客在主要以假摄基层文官的方式治生持家的同时,增进了对于地方社会的体认与理解,并进入经商、营田诸领域,拓展了“所业唯官”的生存选择。在融入地方生活的过程中,邑客对于地方文化、经济、伦理教化诸领域均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其与在地有力者的合作实践,逐步生成了两宋而后基层生活的基本权力结构与日常治理模式。在此意义上,邑客的出现,意味着“中央—地方”关系的新调整,也意味着出现地方新秩序的可能。
注释
①周鼎:《“邑客”论——侨寓士人与中晚唐地方社会》,《中国史研究》2020 年第4 期。②盛会莲:《从墓志看中晚唐幽州社会与政局——以周玙墓志为中心》,《北方文物》2019 年第3 期。③王德权:《为士之道——中唐士人的自省风气》,政大出版社2019 年版,第61 页;毛汉光:《中国中古社会史论》,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 年版,第332 页。④按:同类型的奏议,有宝历二年(826 年)十二月吏部奏议、大和四年(830 年)五月中书门下奏议、开成三年(838 年)四月中书门下奏议等。参见王溥:《唐会要》,中华书局1960 年版,第1342、1351、1382 页。⑤按:如刘禹锡《答饶州元使君书》云:“太史公云,身修者官未尝乱也。然则修身而不能及治者有矣,未有不自己而能及民者。”参见刘禹锡著,瞿蜕园笺证:《刘禹锡集笺证》,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 年版,第257 页。⑥周鼎:《侨寓与仕宦:社会史视野下的唐代州县摄官》,《文史哲》2020 年第3 期。⑦刘彦谦《唐故乐安郡孙府君墓志铭并序》所言及之婚姻关系,更合乎士族生活的常态。参见周绍良、赵超:《唐代墓志汇编续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年版,第1133 页。⑧黄宽重:《宋代的家族与社会》,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 年版,第250 页。⑨谭凯著,胡耀飞、谢宇荣译:《中古中国门阀大族的消亡》,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 年版,第244 页。⑩⑯张国刚:《唐代乡村基层组织及其演变》,《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 年第5 期。⑪韩延寿为颍川太守时,以接对郡中长老为治理之策,对于重视循吏的中晚唐官员群体而言,应具有一定的样本效应。参见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75 年版,第3210-3216 页。⑫按:《唐会要》载:“(贞元)十四年十二月十二日,考功奏:‘所在长吏,请立德政碑并须去任后申请,仍须有灼然事迹,乃许奏成。若无故在任申请者,刺史、县令,委本道观察使勘问。’”参见《唐会要》,第1214 页。⑬《册府元龟》卷六百九十五:“柳公绰为山南东道节度观察使,司农少卿李彤前为邓州刺史,坐赃钱百余万,仍自刻石纪功,号为善政碑。公绰以事闻,贬吉州司马同正。”参见王钦若:《册府元龟》,中华书局2003 年版,第8287 页。⑭《新唐书·李泌传》载:“是时,州刺史月奉至千缗,方镇所取无艺,而京官禄寡薄,自方镇入八座,至谓罢权。薛邕由左丞贬歙州刺史,家人恨降之晚。崔祐甫任吏部员外,求为洪州别驾。使府宾佐有所忤者,荐为郎官。其当迁台阁者,皆以不赴取罪去。”参见欧阳修、宋祁:《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 年版,第4635-4636 页。⑮周雪光:《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一个组织学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 年版,第239、201 页。⑰朱雷、唐刚卯选编:《唐长孺文存》,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年版,第520-554 页。⑱李碧妍:《危机与重构:唐帝国及其地方诸侯》,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年版,第544-545 页。⑲蔡帆:《朝廷、土豪、藩镇:唐后期江淮地域政治与社会秩序》,浙江大学出版社2021 年版,第292 页。⑳鲁西奇:《中国古代乡里制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 年版,第6 页。㉑中唐官员对于吏能的重视与开元时期的士人一般理解存有明显的差异,参见萧颖士著,黄大宏、张晓芝校笺:《萧颖士集校笺》,中华书局2017 年版,第75页,《赠韦司业书》。㉒吴树国:《赋役制度变迁视域下的唐后期乡村社会治理》,《史学集刊》2022 年第1 期。㉓周绍良,赵超:《唐代墓志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519 页;胡可先、杨琼:《唐代诗人墓志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 年版,第309 页;杜牧著,吴在庆校注:《杜牧集系年校注》,中华书局2015 年版,第734 页。㉔谷川道雄撰、马彪译:《中国中世社会与共同体》,中华书局2002 年版,第280 页。㉕周鼎:《晚唐五代的商人、军将与藩镇回图务》,《中国经济史研究》2020 年第3 期。㉖如张籍《野老歌》,徐礼节、余恕诚校注:《张籍集系年校注》,中华书局2011 年版,第22 页;姚合《庄居野行》,吴河清校注:《姚合诗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年版,第282-283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