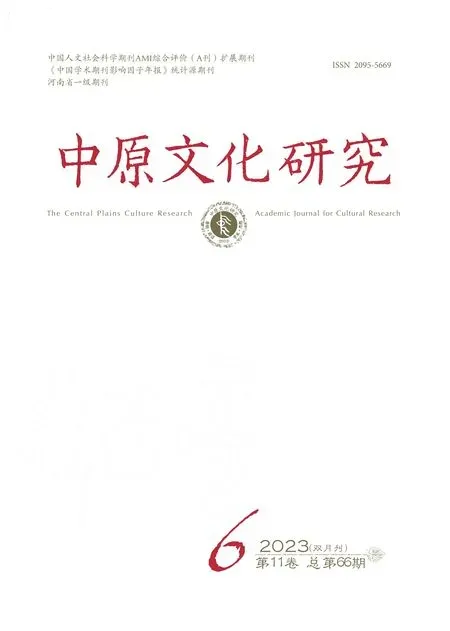唐五代南方城市民众的墓葬安放*
——以扬州为例的探索
张 莹 张剑光
随着唐五代南方城市的发展,城市规模扩大,人口增多,居住在城市的人们将面临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即当一个人走完生命历程,最后将葬在哪里?按照今天的想象,如果人死后都葬在城里,过不了多少年城墙内的空地就会不够用。唐五代时期,州级城市的城区面积有限,一般在二十多平方公里,而城市中的人会一代接着一代地生活,然后又一代代地死去,墓地肯定会不够用。但是,每个人最后总得有个安放的地方,那么唐五代的城市民众,他们最终的归宿在哪里?
一、城郭外的墓地及其方位
如果是世代生活在农村里的人,死后多半会葬在自己的土地里。但世代居住在城市的人死后,墓地的选择就会碰到问题,因为城内是没有多少空地的,即使有钱也不容易购买。为了弄清城市里的人在当时的生活状态,不妨以唐五代的扬州为例,来看看具体情形。
唐五代时,扬州有少部分人逝后会葬在城内,如僧人一般会葬在寺内。慧海于北周大象二年(580 年)来到扬州,创建安乐寺,“修葺伽蓝,庄严佛事,建造重阁”。隋大业五年(609 年)五月“疹患增甚”,不久圆寂。慧海平时与官员有接触,“宰官居士之流,老病贫穷之侣,并情遗重轻,德施平等”。他死后,江都县令辛孝凯“崇信是投,内外通舍,解衣撤膳,躬自指”。他让慧海弟子慧炳“架塔筑基,增其华丽,仍建碑旌德于寺之门,秘书学士琅琊王昚为文”[1]。辛孝凯自己是信佛教的,受帝王的影响,对慧海死后的事情十分关切,“架塔筑基”,应该是在寺内。
由于僧人去世后常采用火化的形式,因而起塔造坟一般都是在寺庙内部。扬州长生寺僧本智,乾元二年(759 年)四月十六日“归寂于扬州江阳县道化坊之长生禅寺”,他“遗命火焚,建塔东偏嘉禾村地内,即于其年十月乙亥八日丙辰归焉”。圆寂后火化,然后将骨灰放入新建的塔中。塔上刻有塔铭,“石方约一尺小,真书甚端整”[2]21-22。尼姑死后也有火化。如尼善悟,“以乾符六年九月六日归寂于信州怀玉山应天禅院,享龄四十三,道腊有二。遗令火焚,从拘尸城之制也。嗣子寇七号痛罔极,见星而行,请收灵骨,以起塔焉”[2]281-282。善悟的儿子是收了她火化后的灵骨,在扬州起塔下葬的,虽然不知是在哪个寺院里,但估计在城内的某个地方。
然而葬在城内的人应该不会很多,文献中常会提到扬州城里人的墓地,一般是就近葬在城郊。广陵人张嘉猷,“唐宝应初为明州司马,遇疾卒。载丧还家,葬于广陵南郭门外。永泰初,其故人有劳氏者,行至郭南,坐浮图下,忽见猷乘白马自南来”[3]710-711。中唐时期的张嘉猷死后,葬回到广陵的南郭门外。张嘉猷在明州为官,卒于任上,于是回扬州老家归葬。这应该是扬州城民众下葬的常见情况,即城里人的灵柩安葬在城外近郊。至于为何安排在南郭门外,不在城市的其他方向,文献里没有谈到。
另有一条资料也大体上能说明这种情况。南唐保大年间,“广陵理城隍,因及古冢”,发现了石质墓志一方,上有诗云:“日为箭兮月为弓,四时射人兮无穷。但得天将明月化,不觉人随流水空。山川秀兮碧穹窿,崇夫人墓兮直其中。猿啼乌啸烟蒙蒙,千年万年松柏风。”①可以看出唐代中期人死后就埋葬在广陵城墙外很近的地方。保大年间修治城隍,并没有扩大广陵城垣,只是原地将护城河挖深挖宽一点,就碰到了唐代中期人的墓,说明墓就在城的周围。
另有一条资料,虽然谈的是扬州的属县,但同样可以反映出人们葬在城外附近的习惯没有改变。南唐昇元二年(938 年),“城海陵县为郡,侵人冢墓。有市侩夏氏,其先尝为盐商,墓在城西。夏改葬其祖。百一十年矣,开棺唯有白骨,而衣服器物皆俨然如新,无所损污”[4]。即海陵县升为郡,城市要扩大,就碰到了人家的坟墓,那家人就要改葬祖宗。市侩夏氏祖先的墓在城西,已有一百多年了,应是唐宪宗或唐穆宗时的墓葬,这时只能挖开重葬,说明县城里面的人也是葬在离城不远的地方。
选择临近城市的地方作为墓地,应该是当时人们的通常做法。李文才编著的《隋唐五代扬州地区石刻文献集成》几乎将历代扬州地区出土的石刻墓志文献悉数收录。这些石刻墓志中反映的墓葬资料,可以看出扬州城里的居民死后,一般是下葬在州城附近。而且通过这些石刻,还能看出人们通常会将墓地选择在城市四周的某个方向。城市与城市之间具体的地理环境的不同,带来的喜好是不一样的,扬州城里的人们有他们的习惯和爱好。
笔者曾对该书中的实例进行统计,可以清晰地看到当时人安排墓葬的习惯。扬州下辖七县,其中的江都、江阳两县“在郭下”,之后又分置扬子县,因而这三县的范围实际上包括了扬州城及其周围地区,因此笔者统计的这些墓葬是指以州城为中心的方向。此外,有部分墓志是海陵县的,指在海陵县城的不同方向。
通过统计发现,扬州城里人的墓葬,大部分都是在城外不远的地方。大多数人的家庭住宅和葬地是在同一县域内,说明两者的距离并不很遥远,一般是在几公里范围。由于扬州有三个附郭县,江阳、江都和扬子三县各有一部分区域在州城里,但更大的区域是在州城之外,因而有的城市里的人也会葬到相邻的县域内。有江阳县的人葬到扬子县、江都县,也有江都县的人葬到扬子县和江阳县,似乎是以方便和就近为原则,城市里的人在县域的选择上没有很明确的讲究。也就是说,大多数扬州城里人是在本县区划中的城外地区寻找一块墓地,少部分人是在本县之外的地方安排了墓地,但实际上也是以就近安葬为主要选择标准。
扬州城里的人大多是葬到了城外,但在城市的哪个方位,是否有一些特殊的规律?除了个别情况不明,没法进行统计外,大多数的墓葬可以看出人们的习惯做法。通过统计可以看到,墓在城东的约有50 人,位于城南的约有13人,位于城西的约有16 人,位于城北的约有10人②。城东的墓葬最多,也许与笔者统计时把东南、东北方向都计入到城东有关,同时也与考古发掘到的墓葬较为集中有关。但不管怎么说,扬州城东墓葬的数量最多,其他三个方向墓葬数量相差不多。如果就三个附郭县而言,江阳县的墓一般都在城东,江都县的墓在城东或城东偏北地区,扬子县的墓以城西和城南为多,不同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墓葬选择的方向。至于海陵县的墓葬,位于县城东的有2 人,位于县城西的有4 人,县城南、北没有。由于发掘到的墓葬数量比较少,海陵县的情况说服力不强。不过从总体来看,扬州和海陵县,更习惯把墓葬营建在城市的东西两侧,南北两侧虽然也有,不过比起东西两侧就要少很多。
二、城市民众墓地的选择和条件
扬州城市里的民众,很多人是城市周围地区迁移到城内,他们能寻找到新的生活方式,在城市中有经济来源,也有不少人是外地迁来的,有的是各级官员及他们的家属,也有的是士兵,还有不少是经商而留在扬州。唐代中期以后,北方人大量南迁,看到江淮地区美丽的环境、富庶的生活,自然是不再挪动脚步,留在扬州生活。因此,这些人中的大多数是没有土地的,他们一辈子在城市里生活,但到了生命的尽头就要寻找安葬之地。
安葬牵涉到墓地的挑选问题。宋人云:“天下之言葬者,皆宗郭璞,所谓《青囊书》是也。”意谓晋代郭璞建立了挑选墓地的一套理论,从此人们就看重墓地风水。又云:“今之俗师,必曰:‘某山某水可以求福,可以避祸。’其说甚严,以为百事纤悉,莫不由此。”[5]这是北宋人对墓穴风水的看法,唐五代民间对此看法略同,也认为祖先的坟墓与后代的祸福之间有必然的联系,“古有宅墓之书,世人多尚其事”[6]。
由于唐五代人将坟墓的好坏与后代子孙的祸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所以十分看重墓地位置的挑选。唐五代扬州城里的人们挑选墓地,一般要经过严格的占卜程序。田侁贞元三年(787 年)七月七日去世,“且欲卜其宅兆,即以其年八月四日归葬于江都县山光寺南原之茔”[7]1846。占卜挑选了好地方后才下葬。李崇贞元八年(792 年)三月十六日得病去世,“以其年八月己酉二十四日卜葬于□□(城)东道化场(坊)之原”[8]751。再如张仕济,元和五年(810 年)四月二十八日去世,才二十二岁,没过多久“卜葬于扬子县曲江乡东五乍村鸣雁里之原”[8]817。臧暹,长庆四年(824 年)七月十七日死后,几个儿子“并卜期宅兆,以其月廿九日窆于嘉宁乡五乍村之原”[8]866-867。再如鲁敬复,开成元年(836 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卜地于扬州海陵县祯实坊常乐里”[8]929。封氏,大中十三年(859 年)六月十一日遘疾去世,他的儿子封绾“卜兆吉辰,以营丧事,克其年七月廿日,窆于嘉宁乡五乍村之原”[8]1024。到唐代末年,扬州城内占卜找墓地的做法依然为大家遵守着。如张弼,咸通十一年(870 年)十二月九日因病去世后,“龟筮叶吉”[8]1099,以次年十月三十日窆于三阳乡五窄村之原。尽管这里举的例子都是有墓志铭的人,应该属于社会中上层,但足可以说明占卜选择墓穴位置不是个别现象,而是当时大多数人的做法。
选择墓地的条件,文献里很少记载,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坟墓的安放大多是要求在地势较高的地方。如宋初王洙说:“昔有一士人,病其家数世未葬,亟出钱买地一方,稍近爽垲者。”③这里是说唐末五代的一位士人挑选墓地的标准是“稍近爽垲”,意谓路不要太远,地势干燥且高一点的地方。高爽的地势,一般都是面向平阔低平地区,是上吉之地。
除了高爽,还有周围自然环境的要求。开成三年(838 年),海陵县的唐范氏得病去世,占卜后“窆于海陵县之东南凡十八里永吉乡羊村之原”。这个墓“东西长岗,南即近湖,北接岭庄”,属于比较好的位置。在唐范氏的墓志铭中,是这样写的:“百草芊芊兮,百花始迷,泉户永闭兮,将来何期?树松与柏兮,依彼原野。筑坟识石兮,以俟来者。”[2]185也就是说,当时扬州人选的坟墓,四周多是花草树木,且有泉水或河流在周围流淌。再如张士节大中十三年七月二十日葬于江都县兴宁乡赵墅村,选中的墓地风水极佳,“回抱蜀岗,四植松槚”[8]996。墓地和蜀岗比较接近,自然地形上有环抱之势,应该是坟墓背依蜀岗高地,前是开阔平地,周围种植了松树和槚树。面向开阔平地、背依高地的坟墓,显得十分有气势,有居高临下的感觉。
在笔者的统计中,扬州人最常见的坟墓位置在城东,也许和当时人的风水观念有一定关系。总体上说,扬州城的地势是西高东低,因而城东的地势比较开阔,坟墓选得合适,背依州城,东临平地和运河,在当时人的心目中可能这是比较理想的。
三、城市民众墓地的购买
农村人的墓地,一般是利用自己家里的土地,但家里没有土地的农村人,或者离开了农村来到城市居住者,又或者到异地生活者,死后的墓地必须出钱购买。一部分城市人有钱,是否会大量购地,风风光光造个大坟?按照官方的要求,墓的大小要和政治等级挂钩。从目前资料可以看出,其时墓的大小,因人而异,按等级享受着不同的规模。《南部新书》卷丙谈道:“旧令:一品,坟高一丈八尺。惟郭子仪薨,特加十尺。”[9]说明官员的坟墓按等级分成不同的规模。但实际上对一般人来说,政治等级并不是个问题,关键还在于经济上是否允许。如果钱多,当然可以买大一点的墓地,钱少就买小一点的,量力而行。
受土地和财力的限制,一般普通官员的墓地并不会很大,也不会超过官方的标准,通常是挖穴下葬棺木,刻石或砖质墓志,坟堆上封土,种植树木。比如何允,大和元年(827 年)五月廿五日卒,“权窆于广陵嘉宁乡陆遂里,凿隧封榇,引植松栢……惧陵谷将变,刻石纪事”[7]2096。何允的官职是“文林郎、试左金吾卫兵曹参军、武骑尉”,职务是正八品下,散品文林郎是从九品上,属于低级官员。
墓地是怎样买卖的?扬州人徐及家里买墓地的记载可以透露一些信息。徐及,大和八年(834 年)四月死于扬州,第二年“合祔于杨子县曲江乡五乍村先殁夫人故茔”。其妻刘氏先逝,之后建园造坟。徐及终年八十四,去世后合祔到夫人的墓中。这个墓的土地是怎样来的?在墓志铭中有详细的解释:“其墓园地:东弦南北,径直长肆拾壹步。西弦南北,径直长肆拾壹步。南弦东西,径直长阔贰拾肆步。北弦东西,径直长阔贰拾肆步。南至官路,北至卖地主许伦界,东至许界,西至王珍界。其墓园地于大和伍年叁月拾肆日立契,用钱壹拾叁仟(原文作‘阡’)伍佰(原文作‘伯’)文。于扬州县百姓许伦边买此墓园地。其墓园内,祖墓一穴肆方,各壹拾叁步。丙首壬穴,记地主毋河宫,同卖地人亲弟文秀,保(人)许林、保人许亮、保人苌宁。”[7]2164在这段话里,可以看到刘氏逝于大和五年(831 年),当时徐家从许伦家买了一块墓地,墓地的大小、四至、价格都说得十分清晰。土地买卖时除双方外,还有卖地人的弟弟及三个保人。墓地呈长方形,南北较长,东西狭窄。徐及父祖及他本人都没有但任过一官半职,但他的两个儿子担任殿中省掌御服七色主衣,和宣节校尉、行常州兰山戍主之类的官职。因此,这个墓园实际上是布衣之家买地后建造起来的,是徐及家里花了较高的价钱买来的墓园。由此可以猜测,南方地区居住在城里的富裕百姓,一般都是这样买地建墓园的。
购买土地葬家人的事情,在当时是比较普遍的。如张士节大中十三年去世后,葬于江都县兴宁乡赵墅村。他的墓“元买地一段,东西壹拾步,南北壹拾伍步,当价钱肆贯文。地主李知权,同卖人李知柔,同卖人母许七娘,保人孙满、夏达”[8]996。这个墓地的买卖记录也比较清楚,有两位中间人,价格并不高,规模比较小,没有谈到墓地的四至。与徐及墓地相比,这个墓长、宽都要小很多。张士节“至于壮岁,投笔军门,武艺当戎,久曾破敌。晚年退迹,却咏闲居,浩然襟怀,自乐情性”,他当过兵,却没有担任过一官半职,估计家里并不富裕。从这两个购买土地作为墓地的例子中,可以看到当时墓的大小相差很大,张士节墓比徐及墓小了三分之二左右。
再如万氏于大中六年(852 年)十二月死于扬州江都县,当月就窆于扬子县界江滨乡白社村。她的墓“其地东西十丈,南北十五丈”[7]2305。万氏是个普通百姓,死的时候只有三十九岁,墓志说她“笄年,归于阎氏之室,育三男三女”。至于阎姓丈夫是什么身份,墓志并没有交代,估计也无官职,但其墓地有一定的规模,与前述徐及家的墓园大小相差不多,远比张士节家的墓大。再如钱匡道,天祚三年(937 年)葬于江都县同轨里,墓“东西贰拾步,南北壹拾伍步”[10],明显要小很多,比张士节的墓略大一些。
当然,对扬州的大多数城里人来说,他们对墓的大小并没有太过分的追求,一般是以适合下葬为宜。如唐彦随乾宁四年(897 年)下葬在扬州扬子县江滨乡颜村里,墓志说他的墓是“广狭得中,制□(作)合度”[8]1162,并未提墓的具体大小,而是以合适为宜。唐彦随是常州军州事,“以□围越,公授帅命,提兵赴援”,死在外地,归葬扬州。虽说是在唐末,但像他这样有一定官职的人按理说有财力建个较大的墓,不过他的家人并没有这样做。
此外,还有一个附带的问题。城里人死了,通常要到城外找一块土地,那么城外的土地所有者是否会乘机要个高价钱?这一点似乎不太可能。因为当时人死后,有一定的停灵时间,且时间长短不固定。笔者曾对李文才搜集的扬州地区石刻文献进行统计,有明确停灵时间和下葬时间的墓志主人共87 人,具体情况是这样的:停灵10 天以下的,为3 人,最少的为3 天;停灵在11—20 天的,为16 人;停灵在21—30 天的,为10 人;停灵在31—40 天的,为11 人;停灵在41—50 天的,为4 人;停灵在51—60 天的,为7 人;停灵在61—70 天的,为7 人;停灵在71—80 天的,为2 人;停灵在81—90 天的,为3 人;停灵在91—100 天的,为6 人;停灵在101—200 天的,为8人;停灵在201—300 天的,为3 人;停灵在301 天至1000 天的,为5 人;超过1001 天的,为2 人,其中最长的为2257 天。按稍长时间段来划分一下,停灵在11—40 天的,计有35 人;停灵在41—70 天的,有18 人;停灵在71—100 天的,有11人;100 天以上的,有18 人。这个统计显示,扬州地区人们停灵的时间没有具体的规定,人们以自己的实际情况来确定停灵时间,相当多的人选择20—40 天。如果其中有一部分人在死亡来到之前家人就已着手购买墓地,那么多数人是有一个月左右的时间甚至更长一点时间来决定墓地购买的地点、大小和价格,墓地一般来说是不会突然遭人涨价,价格和正常的土地交易应该是差不多的。
四、影响墓地选择的几个因素
扬州是“徐方奥壤,泗水名区”[11]143,自然环境优美,地理位置重要,历来就是政治、交通重地。唐代在扬州设置大都督府,又置淮南节度使,是长江下游地区江北的政治中心。隋朝贯通大运河后,扬州便处在长江与大运河交汇之地,所谓“淮海奥区,一方都会,兼水陆漕挽之利,有泽渔山伐之饶。俗具五方,地绵千里”[12]。官商往来,商旅辐辏,南来北往的人员数量众多,扬州是唐朝东南最为重要的交通中心。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本就地位重要的扬州成为唐中后期最重要的经济都会,“走商贾之货财,引舟车之漕挽”[11]280,是四方物资的汇集和贸易中心。
扬州人口众多,城区规模大,商业繁荣,《太平广记》引《唐阙史》言:“扬州胜地也,每重城向夕,倡楼之上,常有绛纱灯万数,辉罗耀烈空中。九里三十步街中,珠翠填咽,邈若仙境。”[3]2151沈括《补笔谈》谓:“扬州在唐时最为富盛,旧城南北十五里一百一十步,东西七里三十步,可纪者有二十四桥。”[13]许浑《送沈卓少府任江都》谈到扬州城“十万人家如洞天”“重重云影寺墙连”[14],意谓扬州是个有十万户人家的大城市,城内寺庙众多。虽然诗里的“十万”并不一定真达到了这个数字,但鉴于天宝年间扬州区域已达七万户,因而在中晚唐时期扬州城内有四十至五十万人口是有可能的。如此大规模的城区,为各种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也丰富了城市生活。中唐以后,扬州城内非常繁华,权德舆谓:“广陵实佳丽,隋季此为京。八方称辐凑,五达如砥平……层台出重霄,金碧摩颢清。交驰流水毂,迥接浮云甍。青楼旭日映,绿野春风晴。”[15]有着浓厚的都市生活气息,同时也可以想见扬州城内车水马龙,各种贸易喧嚣的场景。唐五代的扬州“包淮海之形胜,当吴越之要冲,阛阓星繁,舟车露委”[16]3653,异常繁荣。扬州的城市经济辐射到周边地区,沈珣谓:“禹贡九州,淮海为大,幅员八郡,井赋甚殷,分阃权雄,列镇罕比。通彼漕运,京师赖之。”[16]3513对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由此推知,拥有数十万人口的扬州,特别是中晚唐时期,商业和手工业特别发达,从业人口众多,决定了扬州城里的大多数人死后必须埋到城外去,城内是没有这么多空地来修筑坟墓的。
此外,短期路过扬州的人员越来越多,增加了扬州城外修筑坟墓的数量。在李文才搜集的墓志中,大部分人是死在自己家里,但也有相当一部分人是死在寺庙、客舍、旅舍、官舍,他们实际上都是外来人员,有不少人还是短期路过。但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一旦死在扬州,大多数人只能下葬在扬州城外购买的土地上。这些临时来扬州的人,虽然死后葬在扬州,但其墓地是临时性的,只能先将就着安葬在某个地方,时称为权厝、权葬、权窆。权葬者大多是在扬州城外。
曾任扬州大都督府长史、淮南节度观察使的陈少游,建中四年(783 年)十二月,率兵讨伐李希烈叛军,屯守盱眙。因为与盐铁使包佶意见不一,他夺了包佶钱帛800 万、士兵3000 人,被怀疑与李希烈私通,贞元元年(785 年)惊惧而死。德宗闻陈少游病卒后,赠太尉,赙布帛,葬祭遵常仪。陈少游夫人窦氏,是跟随丈夫前来的,于贞元三年五月二十日终于广陵郡太平里之私第,“其年六月三日权厝于郭东北一十里临湾之原”。墓志说到这一段话,令人思索:“人谁不逝,哀夫人之盛年;家谁无丧,叹夫人之偏祸。夫灵犹在,父舋又钟,不闭苫庐,已开泉室。复缘择日未便,尚乖同穴之文;移天所从,终冀合坟之义。”[2]44-45按墓志的意思,陈少游的灵柩似没下葬,而夫人去世,俩人却没有同穴,原因是“择日未便”。似乎是陈少游的灵柩运到了北方,但窦氏的灵柩回不去,只能在扬州“权厝”,暂时安葬。“权厝”表示陈夫人的灵柩最终还是要和陈少游葬在一起。
再如田侁,京兆府泾阳人。曾入淮南节度使陈少游幕,又任试殿中监、泗州长史,贞元三年七月七日告终于江都县赞贤坊之私第。尽管田侁在扬州有私第,但他并不认为扬州是自己的家乡,“未得归其枌榆”,还是认为棺木要回老家。“其时道路艰阻,未获还乡,权卜葬于扬州江阳县临湾坊之原也”[2]48-49,66-67,田侁在江阳县只是暂时下葬。李颉,开元中释褐兖州参军,次任邢州司仓参军。“乾元初授此任。到官未几,避地江淮”,应该是发生了战乱,才从河北到了江苏。乾元元年(758 年),“因调选终于扬州旅舍”,“遂权窆于江阳县东郭之外”[2]64。李颉是外地人,到江淮来避乱,之后住在扬州旅馆中,所以他的灵柩葬在扬州是临时性的,自然是想迁回到老家。
韦署元和末年来到扬州,诏授扬州大都督府法曹参军,长庆元年(821 年)八月死于扬州法云寺之官舍。按理应该归葬回京兆府,但“孤子式己,荒毁迷谬,不知所从。泣遗诫而莫闻,仰苍天而摧绝。内无强近之亲,外无投寄之友”,没有能力葬回到关中,只能葬在江阳县嘉宁乡五乍村,“从权□□”[2]113-114。韦署妻郑氏死于大和八年九月十六日,也就是韦署死后十三年,郑氏“奄弃背于扬州江都县来凤里之私第”,“以其年十一月廿日权祔于先府君旧茔”。虽然丈夫死在官位上,但郑氏却没有回到北方,一直住在江都县来凤里的私第,应该是自己购买的房子。等郑氏去世了,还是没有葬回去,因为“孤子式己,孑然在疚,形影一身,候年月□大适,启扬子之祖殡,归祔故国”[2]143。按当时的说法,儿子没有能力将父母葬回故乡,所以就葬在扬州,还是权葬。郑氏是合祔到韦署墓中,夫妻二人葬到了一起,用个标准的词就是“权祔”。
另外,唐五代的扬州,一些人继续推崇族葬,希望几代人葬在一起。这种数代人一个家族葬一起的墓,在城市内是不可能出现的,只能修在农村空旷之处。如长庆四年二月十七日,朱叔和及妻子范氏俩人“□祔于五乍之先茔”[2]120-121。“先茔”指的是祖宗墓,而朱叔和夫妻下葬在祖先墓的边上。董惟靖大中六年“殒于江都县赞贤里之寝舍也”,“于其年六月十九日克堋于先考茔侧域内”[2]202-204。也就是说和自己的父亲葬在一起。有可能这是一个祖上几代人在一起的家族墓,葬在一起,说明能一代连着一代。李辞的祖父李岩,“徙居广陵而家焉”,从此就成了扬州人。李辞乾符三年(876 年)八月死于润州延陵县让贤乡之别业,三个月后“返葬于扬州江阳县临湾坊之古原先茔之侧,礼也”[2]265-266。这个先茔里应该有李辞的祖父母、父母二代人。□顼,广明二年(881 年)七月廿四日终于杨州江阳县家里,其年秋九月廿八日葬于“江都县弦歌里禅智精舍隋氏河沈氏太夫人大茔之侧”[2]286-287。这里说的大茔,可能就是一个家族墓。
由此可知,随着城市的发展,人口在增多,流动人口越来越多,传统的丧葬礼仪仍须遵守,这几个因素叠加在一起,扬州城里人的墓葬选择就以时代的特色展现在后人面前。
结 语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这样几点结论:其一,如扬州这般的州一级城市,大多数人死后是葬在城外不远之处,仅少部分人是葬在城区内。死者的家与城外的墓葬并不会很远,也不会太讲究在城市的哪个方向。不过,很多扬州人的习惯,比较喜欢将墓修筑在城东。其二,扬州人的墓葬一般都会经过占卜这个程序,讲究风水,以自然环境高爽、四周绿化优美为选择标准,或许选择城东建墓葬也是与风水有关。其三,大多数城里民众的墓葬是通过购买土地而修筑的,购买土地时双方一般有一个合理的价格,协议上规定四至,价格明确,有见证人。墓的大小一般人不追求过分庞大,以适中为宜。其四,造成城里民众死后葬在城外这一现象的因素是多方面的。由于扬州城市商业繁荣,人口激增,城市容纳不下更多坟墓的需求。扬州交通方便,流动人口众多,死在旅舍、寺庙中的很多人一般是会临时在城外建墓地。一些传统的丧葬习俗,如家族葬等,也是葬在城外。
通过对扬州城市民众坟墓安置在城外这一问题的全面考察,我们认为这既有当时人的习惯因素,也有不少社会发展和自然环境的因素,是在多种合力的作用下出现的一种社会现象。这种现象对唐五代社会造成了很多影响。
一是为城市内的民众带来了更为舒适的生存环境。唐代大多城市是沿袭了前代建筑,对旧城进行维修和扩建,除少数几个城市外,唐代州一级的城市规模一般都不大。扬州经历多次修缮,外城的范围略略扩大了一些。不过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城市内的人口越来越多,死人的坟墓和活人争夺生活空间会形成无法调和的矛盾。实际上城市内人们生活的平均空间不断在缩小,因而就有意识地不再将坟墓安放于城墙内,这是人们生存智慧的体现。死人不和活人争空间,不再为邻,对城市内的民众来说,这是最大的环境福音。二是为城市的发展和城市管理创造了有利条件。唐五代南方的城市一般是有城墙的,城市管理者对城墙内的空间会作一定的设计和安排。将死人葬到城外,城区内不再安排坟墓区,更便于城市发展。可以这么说,坟墓安放在城外,对城市内部交通的发展、里坊街区的形状、道路和桥梁等城市交通设施的建设等,都会起到有利的作用。三是城内民众有相当一部分需在城外数里至数十里的地方购买土地建坟墓,促进了城市附近的土地买卖。整个唐五代时期私有土地买卖不受限制,从法律角度来说允许城外设立墓园。购买墓园的数量增加,实际上是促进了城市周围地区土地产权的流动,钱财进入土地流通领域,促进城市周围地区吸纳财富。从经济的角度而言,能带动城市周围地区的富裕,加快其他行业商品的流动。四是城外坟墓越来越多,或多或少会改变城内人的一些生活习惯。每到寒食节时期,盛行出城踏青、放风筝等娱乐活动。因为祖宗的墓在城外,人们就会出城祭扫。罗隐《寒食日时出城东》云:“青门欲曙天,车马已喧阗。禁柳疏风雨,墙花拆露鲜。向谁夸丽景,只是叹流年。不得高飞便,回头望纸鸢。”[17]便是说寒食节,熙熙攘攘的车马带着人们纷纷出城扫墓,怀念先人的同时也出城踏青,观赏春天的景色。
从扬州城的大体情况,我们可以推测一些南方城市的丧葬习俗。当然各城市的地理条件、经济发展和城市民众的贫富程度等具体情况会有不同,表现出的下葬习俗有所差别,但还是会有很多共性的内容。总的来说,城里人死了,会通过一定的选择,把墓安置在城外不远的地方,这是南方城市在唐五代时期出现的一个共同点。
注释
①参见郑文宝:《南唐近事》佚文,《全宋笔记》第一编第二册,大象出版社2003 年版,第229 页。佚文引自《诗话总龟》前集卷五十《鬼神门》。此条郑文宝《江表志》卷中(《全宋笔记》第一编第二册,第264 页)亦有记载,云:“苏洪至扬州版筑,发一冢,不题姓名,刊石为铭曰:‘日为箭兮月为弓,射四方兮无终穷。但见天将明月在,不觉人随流水空。南山石兮高穹隆,夫人墓兮在其中。猿啼鸟叫烟濛濛,千年万岁松柏风。’”时人猜测诗可能是李白写的,存疑。②按:有一些墓葬其实是位于扬州的东南、西北、西南、东北方向的,因为统计的原因,笔者均计入东或西。③参见王钦臣:《王氏谈录》之《论阴阳拘忌》,《全宋笔记》第三编第三册,大象出版社2008年版,第7 页。按:学者研究唐代两京、河东、河北等地的墓葬,认为“多数未脱离‘六甲八卦冢’取四吉穴的范畴,应是当时民间最广泛流行的葬法”,并且认为可能南北存在着差异。又说墓地取吉穴,可能受到墓地身份等级的影响,“但主要取决于丧家自身的选择”。参见何月馨:《唐代墓田取吉穴葬法的初步研究》,《中原文物》2020 年第5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