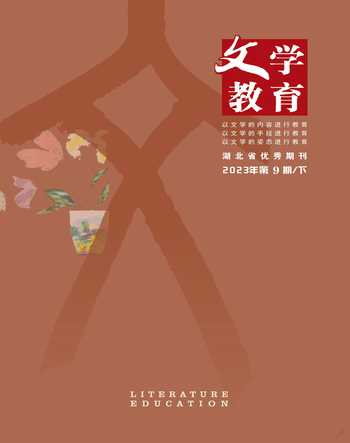朱彝尊和宙亭禅师的清初洪涝灾害诗歌研究
王栩
内容摘要:清初洪涝灾害频发,影响了朱彝尊、纪荫的诗歌创作。他们一个是以遗民身份入仕、晚年退居返乡的博学鸿儒;一个是从俗家背景出世、不避方外往来的寺庙住持。二者身份虽然殊异,却都不约而同地承担了历史使命、自觉用大量笔墨书写灾况。本文将以二者的洪灾诗歌创作为重点,结合相关历史背景,从同中存异的记录功能、不谋而合的抒怀价值与各具特色的现实意义三方面,分析其诗歌创作特色,并总结其成因。
关键词:朱彝尊 纪荫 洪涝灾害 诗歌
有清以来,洪涝灾害频发。据统计,自顺治初至清朝覆亡的268年间,全国“共发生水灾19009县次,年均约71县次”[8]。可见灾情之严重。
水患泛滥,废生产、伤民财,在造成毁灭性后果的同时,也促进诗歌的繁荣发展,形成史料之外的灾难书写样式。这些诗歌作者的身份各不相同,他们或是朝官茂宰:如时任江淮巡抚的宋荦;或为地方绅士:如嘉庆六年中举后应试礼部不第、返乡侍母的焦循;甚至还有生长于斯的平民:如盐民出身、入清不仕的吴嘉纪。尽管诗人的背景殊异,他们的创作却有共通性,即都致力于反映见闻,具备写实抒怀乃至沟通干预的价值。朱彝尊与纪荫也以诗叙灾,其身份则更加特殊——朱彝尊早年作为布衣漫游南北,对当时水患的认识颇为深刻;后受变易动摇的观念、出处两难的境遇影响,他开始从不同的立场出发理解现实、关怀社会。纪荫少时积极进取,罹难而落发为僧,但他学贯儒释、以诗为媒,与众官僚文士交往密切,又兼行躬耕之事、注重民生,并不全然超脱于世俗。此二者用独特的经历涵养文气,使自身创作得江山之助而别具价值。故笔者将以朱彝尊与纪荫为重点,参阅他们的生平交往始末,对相关诗歌予以考察分析。
一.朱彝尊、纪荫生平及其诗歌创作概述
朱彝尊(1629-1709),字锡鬯,号竹垞,浙江秀水人。祖朱大竞为明朝官吏,清廉;父朱茂曙、嗣父朱茂晖则为文士——故耳濡目染之间,朱彝尊亦精通古文,兼工诗句。
1644年,崇祯帝自缢,明朝灭亡,朱彝尊时年16岁。受政权更迭、家世背景的影响,他对新朝的态度有所变易。以五十一岁(1679)的经历为界,其生平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期作为明朝遗民、一介布衣,朱彝尊积极参与反清复明的活动,却遭遇挫折。通海案发,他“踉跄走海上”、“乃赋远游”,常年入幕寄食,多与志士交往;到了第二阶段,也就是康熙十八年(1679)、朱彝尊以博学鸿词登科释褐后,他先除翰林院检讨、参加《明史》编纂,继而入直南书房,可惜不久即遭弹劾降职,直至康熙二十九年(1690)才官复原职。但此次复职并未给朱彝尊带来太多荣耀与安慰,仅仅体验了两年的官场生活,他便又引疾罢官,返归嘉兴、漫游终老。[2]16-18
尽管朱彝尊的思想几经变化,其创作却始终坚持关注民生,留下不少记录灾难的诗歌:《平陵东》(1646)反映强盗横行勒索的现实;《捉人行》《马草行》(1646)讽刺酷吏强征的暴行;《地轴》(1669)展现地震下万家惊悲的场面;《常山山行》(1698)感叹赋税苛重带来的民怨……朱彝尊的洪灾诗歌创作亦遵循此路,体现出他对儒家诗教传统的贯彻。
纪荫(约1644-1710)与朱彝尊活动时期大体接近,二者的经历却不尽相同。[3](前言)最初,纪荫以俗名游启甲应试科举,舞勺之年便得秀才功名。然而1659年前后,他受时局影响而被迫流亡、颇为失意,遂于1661年祝发出世,得法名纪荫,字湘雨,号宙亭。进入佛门伊始,纪荫行脚前往各寺参学,此一活动持续到1674年。这十三年中又有两个时间节点需特别注意。第一是1669年,由于先师卑牧式谦退居,纪荫开始住持盐城兜率寺。随后数年,黄河决口,纪荫多有詩歌叙述灾情,如《鼠渡江》、《河决》、《与射阳周居士谈淮南灾异书此慰之》等。第二个节点是1672年,师翁弘储担雪老人圆寂,卑牧式谦继住苏州灵岩寺庙,纪荫随之前往担任记室,居两年而返,在此期间与众官员、遗民文人交往,留下无数诗作,如《钱大可观察斋》、《九日同宋射陵晚登琴台》、《同顾子云美看浣花池前孤鹤》……其中宋曹(字射陵)等人与纪荫结下终身友谊,在1674至1704年纪荫住持祥符禅、天宁二寺时仍有诗歌往来,构成他一生中较为重要的交游经历。可惜到了1705年,纪荫知交零落,他本人在受命住持高旻寺后,亦仅历五载而寂。故这一阶段《宙亭诗集》并不存稿,其往来状况亦无从知晓。
通过对朱、纪二人的分析可知,虽然他们的生平经历相异,但双方都关注社会、用大量的笔墨书写灾难现象。以下将从同中存异的记录功能、不谋而合的抒怀价值与各具特色的现实意义三方面进一步对照研究,从而归纳这类诗歌的创作特色及其成因。
二.同中存异的记录功能:诗史互证、构建记忆
朱彝尊与纪荫主要生活于顺治、康熙二朝,此间洪涝灾害不绝,成因复杂。其中最为典型的便是由“黄河决口”带来的祸患。黄河夺淮入海多年,当二者逐渐合流之时,“黄河南行”,则“淮先受病,淮病而运亦病”、“人民田庐之频岁受灾,未有甚于此者”[4]3770,如康熙七(1668)至十一(1672)五年间,高邮、兴化、宝应、清河等地一度出现的连岁洪涝现象就与“黄河决口”事件关系密切,有“康熙七年淮安山阳等州县水灾”[6] 《乾隆淮安府志(一)》264页、“七年七月十二日河决邳州城”[5] 《乾隆徐州府志(二)》233页等文字为证。
河决则淤泥易积、风波四起,而人力忽微,自然难以抵抗。康熙八年(1669)秋,朱彝尊过淮安城时,曾作《度骆马湖》一首,对灾况进行详细记录:“自从前度黄河决,董口填淤骆马过。夫柳至今喧里巷,客帆终觉厌风波。东南民力愁先竭,西北源泉弃尚多。安得岁星长守越,年年挽粟上盘涡。”[1]卷七骆马湖跨宿迁、徐州二地,在董口淤塞之时充当了联系南北的重要通道。然而“湖浅水面阔,纤缆无所施,舟泥泞不得前”[4]3773,行船依旧困难。与此同时,陆上百姓要面对淤泥堆积、西北决口余波的双重威胁:每年水灾卷土重来之时,贫苦大众只能被动地“挽粟上盘涡”,可叹可哀。作者从灾难的大背景出发,聚焦巷柳客帆、东南民生,从因到果,观察细致。“至今喧”、“终觉厌”,“愁先竭”、“弃尚多”,推己及人、善用对比——故作者纵为游客之身,亦能写出灾后实感,使作品具有“在场性”特征。
关于这场水灾,纪荫亦有《鼠渡江》、《河决》[3]卷一(约1669-1671)二诗作为印证。前者以1668年淮北鼠衔尾渡江而南之事为背景:“食君田,无半菽;栖君梁,水漂屋……子衔我尾江南陌。明年后年且看君,欲如我辈渡江浑不得。呜呼!欲如我辈渡江浑不得。”用鼠之口吻寄言于人,语言诙谐而有悲意;后者化用李贺、武帝等文学典故,渲染水灾与兵祸下,人民的痛苦无奈,兼有呼吁之功:“天潢一夕裂秋涛,四望平畴雪浪高。应有鱼龙从变化,更无薮泽可逋逃。酸风黑夜吹茅屋,寒雨空村哭石壕。宣室何年歌瓠子,绘图人自卧渔舠。”
无论采取何种角度书写,这些诗歌对于水灾的描绘都与方志资料基本一致,实现了史诗互证、以诗存史的记录价值。这种记录受制于主体行为,因此它不仅是对现实的直陈,还具有“构建记忆”的意义,体现在:
1.对诗歌场景、内容选择的主观差异性
记忆可以是集体性质的,但更是私人的。尽管朱、纪二人都有描绘灾情与民生之作,二者所采取的书写立场并不全然一致。
(1)朱彝尊:民生的观察者
“秀水朱氏,始以医术显,继以科举兴”,“而门望清正,为世所称”[9]。朱彝尊作为名门之后,先天便拥有良好的教育环境与广泛的人脉关系,故纵使家族“易代而衰”,他也能漫游各地,通过做寄食幕僚的方式谋生。加上儒教经义的影响,朱彝尊的诗歌多与寻常百姓的生活保持距离,实际是将创作主体定位成“劳心者”的身份进行社会观察。
且看《淮南感事》[1]卷七(1669)与《旱》[1]卷八(1671)。前者重点叙述大水下淮安堤坝倾圮、连年灾荒的现实状况:“城楼高见碧湖悬,湖堰将倾近百年。比岁凶荒耕未得,自来修筑计谁先。预愁四渎江河合,直恐三吴财赋捐。开济何人翰上策,升虚急诵楚宫篇。”后者则通过江淮旱情回顾其久被洪灾的历史:“水潦江淮久,今年夏旱荒。翻风无石燕,蔽野有飞蝗。桎梏惩屠钓,橧巢迫死亡。虚烦乘传使,曾发海陵仓。”在创作这两首诗时,作者都选择从高处(“楼”)、广处(“悬湖”、“蔽野之蝗”)出发,以俯视的姿态交代因果、描绘现实、呼吁赈济,眼界开阔又不乏淑世情怀,是典型的儒士之作。
(2)纪荫:农事的参与者
纪荫虽与朱彝尊一样关心民瘼,但他的思想呈现出贯通儒释的特殊形态。此外,少年时父母见背、祝发出家的经历让他常有朝不保夕之感。故其诗歌对灾下农事的重点书写,一方面是出于佛家的慈悲心肠,另一方面则是他躬耕畎亩之间,自觉关注的结果。
如《秋馑》(1695)[3]卷二十四:“今年春夏雨,已坏我二麦。一秋复苦暵,菜畦兆龟坼。晚稼虽登场,收成亦逼迫。去岁谷价贱,今更贱于昔。菜蝗及青虫,蟠旋泥潦迹。嘉蔬不充盘,苦荬淹齑液。曳杖每行圃,灌溉怜日夕。嗟哉藜藿情,空对高天碧。”水旱交替、菜坏谷贱,不仅是纪荫的困境,更是无数百姓苦难的缩影。相似的笔触亦可见于《悯雨》[3]卷二十(1690):面对“瓜菜烂坏”“无米路艰”的现状,作者以忧心对孤灯,显示出一个以慈悲为怀,却又自身难保的释子的无奈情绪。
2.内容更加细腻、抒情更具感染力
尽管诗歌是作者实录精神的体现,且对灾难记忆的“构建”具有能动作用,但这种记忆仍以人为载体,以历史为基本框架,通过生活细节加以填充,因而是细腻、丰富,有温度的。无论在《旱》、《淮南感事》,还是《河决》、《秋馑》中,作者的文字都不仅仅停留于对基础事件的把握,而是大胆勾勒“碧湖高悬”、“飞蝗蔽野”、“酸风寒雨”的恶劣环境,通过民无生计、迫近死亡的具体场景,使得一切都可哀可感,如在目前。朱、纪二者的洪灾诗歌成功做到将读者与历史的距离拉近,让个体经验通过文字媒介进行跨时空的交流,由构建记忆走向唤醒记忆、重建记忆,从而展现出极富感染力的一面。
三.不谋而合的抒怀价值:含忧吐愤、托物以讽
洪灾诗歌具有无可比拟的感染力,归根到底是因为它发自人心。即便诗歌所描绘的题材具有公共性质,甚至其写作目的也只是为了示众,但作为个人写作的产物,灾害诗歌不可避免地要包含有作者的主观倾向。无论是朱彝尊还是纪荫的诗歌,都体现了对“民胞物与、仁民爱物”这一思想主题的重视。
1.悲悯百姓遭遇,忧虑农家生计
“国以民为本,民以衣食为本,衣食以农桑为本”,在洪灾之中,百姓不仅要面对“惊涛压城堙,狂澜洗乡曲”、“东家屋塌复壁倒”所带来的生命威胁,还需处理“岂徒涤釜嗟无米,那得黑烟炊湿薪”[3]卷十一的生存困境。这种困境并不如大水初降、一夕致命,反似久治不愈的痼疾,将那些“幸存”的个体磨损至于形销骨立的状态,更加惊悚,也更能牵动诗人的内心。
且看纪荫《苦雨仍用前韵》[3]卷六。此诗作于康熙十五年(1676),当时马山雨水成灾,使得田间一片荒芜:“陂塘麦乱漂,鱼鳖供咀嚼。秧畦水满路,草根生郭索”。然而积水久不退去,釜上流泉、镈满泥苔,阻止农民重操就业,更加重了这番苦难:“稼樯食艰辛,对此宁不戄”。居则“樵青烟不兴”、“破屋漏茆茨”,行则“米价涌溪桥,舟杭黯业薄”。百姓无以谋生,在恐惧中度日,其残酷程度,竟有“过于鼎镬”:这一句既写出百姓精神上的煎熬,也暗示了他们饱受摧残的肉体状态,令人闻之心惊。
“田中麦与禾,民生命所托”。纪荫以《苦雨仍用前韵》一诗,点出民生之要害,不仅是出于躬耕者的共鸣。作为佛门弟子,他也冀图承担救世的使命。然而“救荒无策可搜寻,血泪枯来只此心”[3]卷二,唯有诗歌成为他抒发满腔悲悯情怀的出口。在《书感》[3]卷十五(1683)中,纪荫目睹雨水毁田的惨象,为大眾生计而忧:“河润沮洳九里田,长林丰荫草阡眠。烟霞敢遂忘忧世,畎亩唯知望有年。鼙鼓东南方歇手,凶荒吴越又随肩。沉沉日夜梅花雨,菜麦千畴尽可怜。”;写作《闵雨用韵二首 其二》[3]卷十一(1680)时,他见田有未收之麦、满地受灾之民,更是“自愧此身非药材”。
与纪荫“呕心沥血”之态不同,朱彝尊虽亦有悲忧民生之作,其语言却更加克制。如《送乔舍人莱还宝应》[1]卷八:“今秋甲子雨不绝,小池残暑风凄凄。栈车难行瘦马滑,终朝兀坐愁云低……湾头清水闻更决,上流未筑归仁堤。千村庐舍总昏垫,可知雁户犹悲啼。漕船万斛挽不上,荒冈断岸何由梯。太仓红粟渐已贵,曷归长水亲锄犁。期君岁暮白田上,班草城南手重携。”此诗作于康熙十二年(1673),时乔莱因兄乔迈辞世,告假返乡,朱彝尊前往送别。
按乔莱为人洞达、清正爱民。时淮扬久罹水患,他拒绝厚利贿赂、不惧权贵报复,率同僚慷慨进言,揭露河臣假治水之名而侵吞民财的私心。[5]《民国宝应县志》181-182页故朱彝尊写作此诗,颇有深意——“班草”、“携手”,实为知交共进之旨。朱诗以秋天久雨、氐惆昏昧的环境切入,逐步转向对宝应现状的描绘——水决侵户、流民悲啼、交通阻断。这是耳闻之事,朱彝尊却凭借“寸心千里随轮蹄”的想象,反复切换叙述视角,如同亲睹现场:于百姓,“漕船万斛挽不上”;于己,则太仓粮贵,萌生归去躬耕、知交重逢的愿望。故此处“背面敷粉”,语淡而意不淡。可见对于流离失所的贫苦大众,生存境况之艰难,已不忍直叙。朱彝尊通过对灾情的描绘,与友人产生了心灵的沟通,在换位思考、精神共鸣中隐含着对百姓命运的忧虑与悲悯。
2.批判催科强征,讽刺尸位之官
洪涝灾害之下,农田被毁、粮价抬高——“山厨尚苦樵苏尽,城市难教珠桂”,人民生活无以为继。但自然环境显然不是压垮百姓的全部因素:小吏横征暴敛、长官无所作为,给劳苦大众的身心又一次带来创伤。
纪荫《山行口占》[3]卷十(1678)有言:“数千里内尽啼饥”、“年荒更苦征输迫,地僻犹欣盗贼稀”,可见饥荒、征输、盗贼,常被百姓视为洪水猛兽。当民生凋敝之时,“但愁催科吏打门”[3]卷十更是普遍的心态。
除了岁岁难逃的赋税之灾,徭役之祸也时有发生。如《追呼行同杜石壕吏韻》[3]卷十一(1680):“……昨岁告乾荒,入奏十分苦。蠲免仅三分,馀欲轮征戍。今年大水灾,十室九病死。死者不须哭,生不如死矣。耕田努力作,将以养子孙。宁知旱复潦,典贷尽钗裙。官司岂不闻,沟壑速之归。釜蛙阁阁鸣,何以问朝炊。生趣已决绝,吞声徒更咽。流离向他方,骨肉甘抛别。”水灾过后,百姓十之八九,经历死别。然“幸存者”更不幸:纵财与力尽,亦难免生离。作者用“死者不哭,生不如死”之语,给人以普遍的价值观下,是非倒错的震撼。同时,耕户的勤勉在灾难下化作徒劳——平民的渺小卑微与自然、奸吏的残酷任性形成鲜明对比,令人扼腕。
小吏之所以跋扈,多因为主官懒于政治,不能以身作则。对此,朱彝尊有《水带子歌》[1]卷二十,托物以讽:“……中流踏浪如御风,过涉不愁灭顶凶……黄梅时雨水稽天,甓社湖流人罢市。无朝无暮虑覆舟,且喜今朝得到此。挂之驼钩壁上悬,与论往事增凄然。初闻淮南减水坝,开设天子谓是一坝一口决。俄而佥谋滋异同,尔考直前奏事真剀切。迄今黄流泛滥轸,帝情雁户岂得安其生。桃花春水纵不发,河堤使者毋遽誇平成。吁嗟乎,河伯不仁亦无害,准备家家蓄水带。”
“水带子”:“环外虚其中”,形似当今的救生圈。朱彝尊结合高邮洪水稽天的现实,阐述“水带子”的用法及效果,明确得此物可免覆舟丧命之虑,故不禁与民同喜。然而这“喜”中又含着“滑稽”、透着“悲”:采购“水带子”并非治本之策,若以“准备家家蓄水带”对抗洪流,则不免可笑;百姓本应以安居乐业、丰衣足食为人生理想,但此时免于死亡已经成为一大幸事,故其情甚哀。此诗以物为题,以水灾为背景,最终目的却是要引向对现实的反思与批判——与乔莱“剀切直言”相反,当今“河堤使者”尸位素餐、虚夸功绩,令人不齿。末句以戏笔、反语出之,在看似松弛的氛围中灌注浓烈的讽刺意味,增强了诗歌的艺术魅力。
四.各具特色的现实意义:沟通请命、宣政参政
纪荫、朱彝尊忧心民生,以诗歌写残酷之行,对尸位素餐的官僚极尽讽刺,具有动人心弦的情感力量。但二者的志向远不止于此,以洪灾诗歌为媒介,他们还取得了沟通请命、宣政参政的现实成果。
1.沟通与请命
这是纪荫诗歌的特色。作为住持,纪荫承担着维持寺庙运转的责任。“残僧约有三十口,饥来冷眼看甑缶”[3]卷十,每当缺粮肠饥之时,僧人便会组织“分卫”活动——“半钵尚烦金粟借,一茅难刈绿萝荒”[3]卷十九,被视作纾解困难的最快途径。
但事实上,身处凶年,五谷不登,“分卫”往往收效甚微。于是寻求更有力的支援就显得尤为重要。故纪荫居留石岩寺二载,与众文士唱和留赠,是因为情投意合,亦是前者出于谋求援助的现实考量而有意促成的结果。当结交的官僚、遗民纷纷伸出援手,纪荫也积极沟通,并传达谢意。《绣衣衲子饷粟书感》[3]卷十七(1684)即是纪荫感念许之渐所作:“赍来莫谓等监河,减旨分甘及绿萝。纵使虚空消受得,讵能毛孔不香多。诸天较色应输白,大地轻拈试问颗。一饱忘饥无所事,却将高卧答维摩。”许之渐字仪吉,号青屿。性好参禅、通佛法。据《光绪武进阳湖县志》记,约崇祯六至十五年间,许之渐曾作《天宁寺饭僧田记》[7] 《光绪武进阳湖县志》741页。而纪荫在《和青屿侍御病起感秋十首》[3]卷十(1679)中亦有“今年更比去年荒,一饱因缘杳莫偿”的感叹,可见许之渐十分关注禅寺状态,在与纪荫的交流中多次给予其援助。1684年,常州府屡遭雨雪侵袭,祥符寺众僧举步维艰,年届七十、退居数年的许之渐遂济以米粮。能够再度得到这位长者的支持,纪荫喜不自禁,故其诗大赞“减旨分甘”之举,字里行间充满了崇敬、愉快的情绪。
除了以诗歌沟通、解决自身温饱问题,纪荫还心系苍生。江淮流域水旱交替,康熙十七年(1678),先是淮南射阳“清水潭口夜冲湱”[3]卷九,至六月而常州酷热。纪荫胸怀天下,主动写诗《赠郭邑宰虞修》[3]卷九,赞美武进县令郭萃仁德双修,同时为民请命、呼吁赈济:“我公循良命世才,轶群作略驰风雷。来为蒼生作霖雨,行将鼎铉需盐梅……今年旱虐几千里,六月炎炎苗槁矣。我公茹檗且餐冰,呼天吁地勤祷祀……立德立功名不朽,山高水远足人思。”此次请命结果全如纪荫所愿:按“十八九年两逢水旱大灾”,郭萃“蓋厰哺饥,按户授粟,尤见抚綏”[7]《民国上杭县志》368页,拯救了无数落难的百姓。
2.宣政与参政
当纪荫作诗劝勉郭萃之时,朱彝尊正初涉仕途。康熙十七年(1678),清圣祖玄烨下令征召旧朝文士,次年朱彝尊便以博学鸿儒的身份授官。然而天有不测,康熙二十三年(1684),他在数月之内便经历了侍宴、降职等重大变革。与此同时,山东境内,潍河、小清河“湮道横决”,刚刚上任山东巡抚的张鹏“浚河、建闸道”,并“力言于主者”,请求豁免税银、米麦,终“活人不可胜计”。[6]第124册《憺园文集》卷二十九《通议大夫吏部左侍郎张公墓志铭》
朱彝尊与这位张巡抚是旧雨。故九月二十八日,康熙帝南巡,过山东,“命(张)公陪祀阙里”时,朱彝尊闻此倍受精神鼓舞,热情洋溢地“寓书张鹏,请立周公后”,并作《嘉禾篇颂张先生》[1]卷十二(1684)一首:“康熙二十三年冬,天子将登日观峰。十行诏下轸三农,薄徭放税宽租庸……先时水旱频告凶,北达河泲东潍灉。晨炊不举夜不舂,夫子下车忧 。请发仓粟救鞠讻,乡师为粥吏佐饔。饥者得食皆欢悰,有如雁唼鱼噞喁……灵苗驿驿芒茸茸,八月其穫崇如墉。输之天庾惟正供,我闻乐事舒心胸。大贤美政孰比踪,不贪为宝民吏宗。主圣臣良时乃雍,五风十雨殊乾封。”此诗叙述水旱灾后的场景,侧重点却与往日不同:起首一句交代天子登峰日程,有昂扬之气,接着详述圣主下诏安民、轻徭薄赋;张公上策忧民、荣获嘉奖;百姓受赈欢悰、恢复生产,以至粮足输库、有备无患——总体基调趋于祥和。
如果说应试博学鸿词科是他作为明遗民的第一次妥协,此处的高歌则体现出朱彝尊思想上的进一步迎合:虽才罹降职之祸,但登科后所受的侍宴荣宠、张鹏的仕进历程让他依旧对清朝政权抱有希望,期待一次起复的机会。 “大贤美政”、“主圣臣良”、“五风十雨”等具有鲜明的思想倾向性语词,在一定程度上折损了朱彝尊诗歌原初的艺术魅力,扼杀了个性。但一方面,通过对明君的揄扬,朱彝尊表露自己的心迹,冀图以拥护态度实现一种政治上的靠拢;另一方面,对张鹏的表彰,实际上是在为统治集团树立一个榜样,有促进后来者踔厉奋发之效,契合王朝“颂美时政”的需求,能够发挥宣政抚民的作用,巩固了社会稳定的基石。
康熙二十九年,经过长久的留京等待,朱彝尊终于官复原职。然而,统治者的冷遇、官场倾轧的乱象让他惴惴不安,在思想的再度摇摆之下,朱彝尊引疾致仕,转而用另一种方式表达自己对社会政治的关心——康熙三十九年(1700),在《陈君缄寄普光王寺二碑索余游记复成三十韵兼寄钱上舍高处士》[1]卷十九中,朱彝尊记录自己游于吴地,目睹“波潮息广泽,禾麦交平畬”的景象,于是“忽念淮泗冲,浊河苦填淤”,针对水患提出明确的治理方案:“沽有七十二,可以通沮洳。淀有九十九,可以兴耰锄”。尽管这只是朋友间的一次通信,朱彝尊并未能直接参与政治治理。但此诗已有更为深广的社会意义:它不仅提取出“忧”的意识,还尊重“患”的实在。伴随着对“忧患”理解的更加深入,诗人开始主动探讨灾难下的出路。
退职还乡的朱彝尊,以诗歌的特殊形式参与社会政治——这种“主动”让他把自己从抒情者提升到了谋划者、干预者的地位。明末清初,各方治乱思潮涌起,前朝遗民纷纷强调儒士责任。尤其是黄宗羲,一度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学校议政”的口号,主张经世致用。朱彝尊与这位长者相识,对其颇为尊敬,更曾在《黄徵君寿序》[1]卷四十一中坦言自己变节的懊恼,有学习之意:“予之出也,有愧于先生……明年归矣,将访先生之居而借书焉……冀先生之不我拒也。”虽然二者对于前路的选择并不一致,但朱彝尊借书写水灾提出治理方案,有意无意地与黄宗羲的理论暗合,颇具公共理性与民主思想萌芽的意味,这是作者在进退失据的历程中寻得的自洽方式,与清初思想相互促进,同时也与其晚年的赈济行为相互配合,发挥了参与政治、干预社会的功能。
清代洪涝灾害频发,引起了诗人的广泛关注,朱彝尊、纪荫亦投身于书写灾难的行列。二者巧妙利用诗歌的叙事传统,记录灾情、构建记忆;充分尊重诗歌的抒怀本质,悲悯百姓、讽刺昏官;并进一步结合自身经历,突破文学的价值,使诗歌发展出沟通请命、宣政参政的现实作用。故这些创作与历史相比更为细腻可感,与公文谏书对照更加委婉含蓄,成为举步维艰的僧人谋求援助的手段、进退失据的文士寻求自洽的方式。
参考文献
[1]朱彝尊.曝書亭集[M].上海:上海商务印书馆,缩印原刊本.
[2]张宗友.朱彝尊年谱[M].江苏:凤凰出版社,2014.
[3]纪荫.宙亭禅师诗集[M].江苏:广陵书社,2021.
[4]赵尔巽.清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1976.
[5]江苏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江苏历代方志全书[M].江苏: 凤凰出版社,2017.
[6]清代诗文集汇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7]中国地方志集成[M].江苏: 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
[8]张琨佳,刘璐,苏筠.中国清代历史水灾时空特征研究[J].自然灾害学报,2015,(4):104-110.
[9]张宗友,薛蓓蓓.“谁怜春梦断”,“相期作钓师”——朱彝尊的江湖之行、仕宦之旅与难归之隐[J].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19,(4):44-56.
项目:江苏省高等学校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面对灾难,诗歌何为——清代江淮地区洪涝灾害的诗体叙事研究”。
——朱彝尊与书法篆刻家的交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