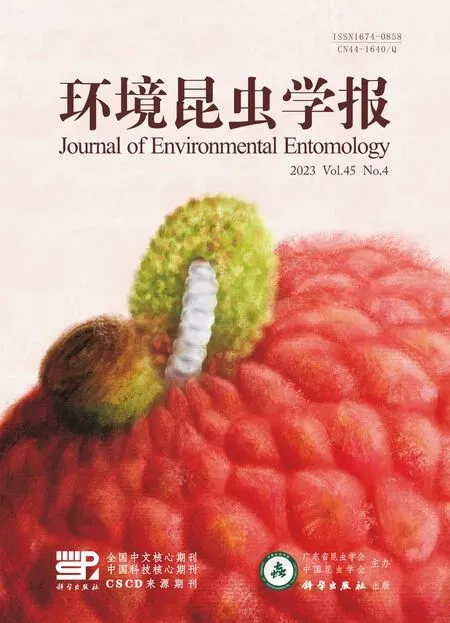我国新入侵害虫长林小蠹研究进展
李承锦,赵文霞,淮稳霞,林若竹,姚艳霞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森林生态环境与自然保护研究所/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森林保护学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091)
长林小蠹HylurgusligniperdaFabricius,又名红毛小蠹,英文名称为red-haired pine bark beetle,主要危害松属Pinus植物。长林小蠹很容易通过松树木材贸易活动进行传播,是世界各国在松树进口原木中截获最多的昆虫之一,该小蠹入侵能力强(沈鑫,2011;Chase,2018),目前已扩散至整个欧洲以及非洲、澳洲、亚洲、美洲的部分国家与地区(Hoebeke,2001;Brockerhoffetal.,2006;Mauseletal.,2007;Meurisse and Pawson,2017;Faccolietal.,2020),因而受到世界各国的高度重视,许多国际性或区域性组织将其列为重要的检疫性害虫,如国际植物保护公约(International Plant Protection Commission, IPPC)将其归为需要进行检疫处理的有害生物种类,北美植物保护组织(North American Plant Protection Organization, NAPPO)将其列为Alert Pest List A2类有害生物等。
长林小蠹也是我国口岸检疫中截获次数最多的林业害虫之一,根据现有文献记载,我国最早于1986年在天津塘沽口岸从智利进口的松树原木中截获该小蠹(刁彩华,1988),随后,多个口岸从新西兰进口的松树原木中发现长林小蠹(杨晓军和安榆林,2002;梁琼超等,2003;梁琼超等,2004;安榆林,2012),并且在过去的十余年里,我国口岸多次截获该小蠹(董文勇,2010;张总泽等,2014;林玲玲,2015;黄蓬英等,2018;惠瑜,2019)。据统计,仅在2005-2015年间,上海、天津、青岛、深圳、福建、南京、宁波等口岸,共截获长林小蠹4049批次(梁振等,2017)。2006年,我国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入境检验检疫行业标准《长林小蠹检疫鉴定方法》,2007年,将其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境植物检疫性有害生物名录》(农业部公告862号2007-5-28)。
我国是世界上木材消费大国(安榆林,2012),木材需求量大、进口量逐年增加,针叶树木材进口来源广泛,来自包括新西兰、俄罗斯、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乌拉圭在内的130多个国家和地区(安榆林,2012;张嘉然,2019),其中不乏长林小蠹危害严重的国家,因此,长林小蠹传入我国的风险极大。自2019年7月以来,我国山东省泰安市、威海市和烟台市陆续发现长林小蠹(Linetal.,2021;任利利等,2021),目前已明确长林小蠹在我国定殖并造成严重危害(任利利等,2021)。本文对长林小蠹外部形态特征、分布范围、生物学、分子生物学、我国种群来源及潜在分布区、检疫与防治措施等方面进行介绍,旨在全面了解和掌握该新发外来种的基本信息,为进一步开展深入研究,进而制定有效的检疫管理和防治措施奠定基础。
1 外部形态特征
长林小蠹属鞘翅目Coleoptera象鼻虫科Curculionidae小蠹亚科Scolytinae林小蠹族Hylurgini林小蠹属HylurgusLatreille(殷蕙芬等,1984)。迄今为止,林小蠹属全世界仅记录3种,即长林小蠹、米林小蠹H.micklitziWachtl和印度林小蠹H.indicusWood(Wood,1985;Alonso-Zarazagaetal.,2017;任利利等,2021)。米林小蠹主要分布于欧洲克罗地亚、法国、德国、希腊、匈牙利、意大利(包括撒丁岛和西西里岛)、西班牙、俄罗斯南部,亚洲以色列、土耳其,非洲阿尔及利亚、埃及、利比亚、摩洛哥、突尼斯等,主要危害意大利松Pinuspinea、海岸松P.pinaster、P.halepensis等(Wood and Bright,1992;Mifsud and Knizek,2009;El-Khouryetal.,2019);印度林小蠹仅分布于印度孟加拉地区,危害P.roxburghii(Wood,1985)。
长林小蠹成虫体长约4.0~5.7 mm,红褐色到黑色,触角和足的裂片红褐色;触角索节6节,触角棒节圆锥形;前胸背板两侧着生浓密刚毛,且明显长于鞘翅两侧刚毛;后胸与腹部近等长;鞘翅前缘粗糙,毛被分布不均匀,在斜面上较厚密。幼虫体长约4.1~5.9 mm;粗壮,黄白色,无足;头部黄褐色,有光泽;下唇须2节;老熟幼虫头上颚以上部分,有两个几乎为圆形的黑色突起。该小蠹成虫具有明显的雌雄二型性:雄成虫可见腹节7节,第6腹节明显硬化且有褶丛;而雌成虫可见腹节6节,第6腹节长度与雄成虫第6、7腹节长度之和相等(Liuetal.,2008;Bedoyaetal.,2019)。
2 分布范围
长林小蠹原产于小亚细亚半岛、俄罗斯、地中海地区和附近的大西洋岛与非洲北部地区(Fabre and Carle,1975;Wood and Bright,1992;Hoebeke,2001;Wood,2007;Meurisse and Pawson,2017;CABI,2022),近一个世纪以来,已经传入、定殖于许多国家和地区,分布较为广泛,目前在整个欧洲,亚洲(中国、日本、韩国、土耳其、斯里兰卡等),澳洲(澳大利亚、新西兰),非洲(南非、摩洛哥、突尼斯、斯威士兰),南美洲(阿根廷、巴西、智利、乌拉圭、哥斯达黎加等)和北美洲(美国纽约和加利福尼亚州)均有分布(Bain,1977;Hoebeke,2001;Haacketal.,2002;Ahamedetal.,2005;Wood,2007;Liuetal.,2008;Meurisse and Pawson,2017;Parketal.,2017;Faccolietal.,2020;Linetal.,2021;任利利等,2021)。我国最早于2019年在山东省泰安市诱集到长林小蠹(Linetal.,2021),此后,在山东威海市和烟台市也发现了该小蠹(Linetal.,2021;任利利等,2021)。
3 生物学特性
3.1 寄主与危害
长林小蠹主要危害松属Pinus植物,寄主树种达20余种(Hoebeke,2001;Wood,2007;任利利等,2021;CABI,2022),主要包括辐射松P.radiata、日本黑松P.thunbergii、意大利黑松P.brutia、加拿利松P.canariensis、湿地松P.elliottii、地中海松P.halepensis、山松P.montezumae、欧洲黑松P.nigra、展叶松P.patula、海岸松P.pinaster、意大利伞松P.pinea、北美乔松P.strobus、欧洲赤松P.sylvestris、樟子松P.sylvestrisvar.mongolica等,其他寄主还包括冷杉属Abies、落叶松属Larix、云杉属Picea和黄杉属Pseudotsuga的部分树种(Wood,1989;Wood and Bright,1992;Hoebeke,2001;Brockerhoffetal.,2006;Wood,2007;顾忠盈和吴新华,2009;王倩,2014;王焱和叶建仁,2017;El-Khouryetal.,2019;任利利等,2021),目前,长林小蠹在我国主要危害日本黑松P.thunbergia(任利利等,2021),也可能危害华山松P.armandii、赤松P.densiflora、油松P.tabuliformis等(Linetal.,2021)。
长林小蠹为次期性害虫,主要危害濒死木、衰弱木、新伐原木和伐桩(Hoebeke,2001),但当长林小蠹在入侵地种群密度较大时,也可能对活树和幼苗产生危害(Hoebeke,2001;Lanfrancoetal.,2001;Mauseletal.,2007;Kirkendall,2018;Faccolietal.,2020),在智利发现长林小蠹取食原始次生林和人工林的幼苗细根(Hoebeke,2001;顾忠盈和吴新华,2009;安榆林,2012),导致10%的人工林幼苗死亡(Hoebeke,2001)。长林小蠹通常危害部位为树干基部、根茎基部或裸露的根部(Brown and Laurie,1968;Hoebeke,2001),也可危害主干,并能够穿过土壤进入根部进行危害(任利利等,2021)。受害树木的树皮表面和根部表面可见侵入孔和羽化孔,幼虫在坑道内取食时排出灰暗色蛀屑(Brown and Laurie,1968;Fabre and Carle,1975)。目前,长林小蠹在我国胶东半岛危害较为严重,对枯死日本黑松根系的侵害率达100%,危害部位从距地面以上1.8 m的树干至土壤内1.5 m的根系(任利利等,2021)。
3.2 生活史
长林小蠹的生命周期受季节性影响较大,在其适生范围内较冷的地区1年1代,但在较热的地区1年2~3代(Hoebeke,2001),世代重叠使其在1年内多数时间都能够侵染传播(田家怡,2004;顾忠盈和吴新华,2009;任利利等,2021),成虫喜好在凉爽高湿时期活动(田家怡,2004)。在法国东部,长林小蠹1年2代,春季(第一代)为主要活动高峰期,秋季(第二代)活动期较短,第一代有两个连续的产卵期,第二代只有在理想条件下才会发生两个产卵期(Fabre and Carle,1975);在法国南部,当温度为25℃时,从卵发育到成虫需要45 d(Fabre and Carle,1975)。长林小蠹在美国纽约至少1年完成2代,5-7月中旬出现第一次高峰期,7-9月为第二次高峰期(Haack,2002),成虫在9-11月为活动高峰期,与第二代的爆发相对应(Hoebeke,2001)。智利和南非全年可见长林小蠹活动(Tribe,1991;Wood,2007),在智利通常一年3代(Kirkendall,2018),南非较冷的月份成虫多(Tribe,1991)。在新西兰,该小蠹的主要活动期在春季到夏末,从幼虫开始取食蛀道至羽化大概需要10~11周(Reay and Walsh,2001)。
此外,Clare and Geoge(2016)人工饲养长林小蠹并连续繁殖了6代,每代最少72 d,绝大部分幼虫经历4个龄期后化蛹、羽化为成虫,与野外观察结果一致(Brown and Laurie,1968;Hoebeke,2001)。目前,长林小蠹在我国分布区的生物学尚不清楚,人工饲养可为长林小蠹生活史相关研究提供便利,但人工饲养技术还需进一步研究,以确保人工饲养的成虫生命力更强(Romoetal.,2016)。
3.3 交配和繁殖方式
长林小蠹成虫可以在新伐木桩、原木、新枯死木、垂死木、倒木中繁殖,也可以在活树根茎处繁殖(Hoebeke,2001)。长林小蠹实行严格的一夫一妻制(Lanfrancoetal.,2001),在进行繁殖活动之前,雌成虫首先侵入树皮,在韧皮部形成一个短的侵入孔和一个倾斜的交配室并诱集雄虫进入(Fabre and Carle,1975;Hoebeke,2001;Ruizetal.,2003;Wood,2007),交配过后,雌成虫沿木质纹理的方向啃食形成长而曲折的母坑道(Fabre and Carle,1975;王春林等,2005),并将卵产在坑道两端的刻槽中,产完第一批卵后,再将母坑道延长10~20 cm,随后产第二批卵,每头雌成虫最多产卵500粒(Fabre and Carle,1975)。当大规模繁殖发生时,活动范围随之扩大。一般在细树皮的根茎中,幼虫在木材里化蛹,然而在厚树皮中,化蛹发生在树皮和木材之间,或在树皮内(Rudnev and Kozak,1974)。
3.4 鸣声
长林小蠹雄性可发出鸣叫声,而雌性无鸣叫声(Sunil,2017;Bedoyaetal.,2019),据推测,这可能与雌雄腹部的二型性有关(Liuetal.,2008;Bedoyaetal.,2019)。有研究表明,在长林小蠹痛苦、交配、竞争、交流、聚集等不同情景下的声音行为存在差异,因此,可通过声波来震慑或改变其行为、从而进行防治。Bedoyaetal.(2019)也因此提出了一种可自动提取和识别长林小蠹个体之间声音的方法,该自动检测声音的方法在海关检疫、虫害防治等方面应用前景广,可大大提高工作效率。
3.5 自然扩散与传播能力
长林小蠹成虫飞翔与扩散能力较强,据报道,在澳大利亚,长林小蠹18个月扩散了25 km(杨晓军和安榆林,2002;田家怡,2004);在新西兰,Chaseetal.(2017)于寄主松林之外至少25 km处诱集到了其成虫;长林小蠹传入智利5年后,就已经扩散到辐射松的所有种植区域,且其飞行和定殖具有同步性(Mauseletal.,2007);从新西兰首次发现长林小蠹至扩散到全国,仅用了3年的时间(Bain,1977;Clare and George,2016);韩国于2017年首次发现长林小蠹传入(Parketal.,2017),现已迅速蔓延至其大部分地区(Linetal.,2021)。此外,该小蠹在黎明和黄昏时刻飞行活动频繁,且飞行速度随风速增加而增加,最高可达2 m/s(Pawsonetal.,2017)。
4 分子生物学
长林小蠹分子生物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DNA基因片段序列特征分析方面。截至目前,在NCBI中已提交长林小蠹核酸序列共计52条(表1),包括线粒体细胞色素氧化酶Ⅰ(COⅠ)、核糖体28S D2-D3扩展区、核糖体18S、蛋白延伸因子(EF-1α)、Arr2等15个基因(Sequeira and Farrell,2001;王银竹,2010;Jordaletal.,2012;Reayetal.,2012;常虹,2013;Susoyetal.,2014;Rugman-Jonesetal.,2015;黄蓬英等,2018;Pistoneetal.,2018;Linetal.,2021;任利利等,2021)。

表1 GenBank长林小蠹核酸序列信息Table 1 Nucleictide sequences of Hylurgus ligniperda Fabricius in GenBank
根据研究目的,这些序列特征主要用途可分为3类,一是用于种类检测与鉴定,二是用于种群溯源分析,三是用于高级阶元系统发育研究。对于种类检测与鉴定,主要是针对口岸截获的不同有害生物,通过分析其COI基因序列,进行种类鉴定,特别是实现幼虫的准确鉴定(黄蓬英等,2018),并在此基础上设计种特异性引物或探针,对昆虫种类进行分子诊断与检测(王银竹,2010),或者建立包括长林小蠹的小蠹虫DNA条形码数据库(常虹,2013)。种群溯源方面,主要运用COI、28S等基因,对来自不同采集地的种群进行聚类分析,探讨近缘关系,推断种群来源与扩散路径(Linetal.,2021;任利利等,2021)。在高级阶元系统发育方面,主要集中在亚科分类水平,其中最为典型的是Pistoneetal.(2018)曾通过考察18个基因片段,对包含长林小蠹在内的小蠹亚科182个种进行系统发育分析。此外,在小蠹亚科(包括长林小蠹)及其与共生真菌和线虫相互关系的研究中,运用28S、18S、EF-1α等基因检测鉴定共生生物种类,构建宿主和共生生物系统发育关系(Jordaletal.,2012;Susoyetal.,2014)。
5 携带真菌与线虫
与小蠹亚科其他大多数种类相同,长林小蠹不仅能够直接攻击松属树木造成危害,还可通过携带的真菌和线虫对寄主植物造成危害。经研究发现,长林小蠹可携带大量真菌,Davydenkoetal.(2014)在乌克兰东部的长林小蠹上鉴定出了40种真菌,其中,长喙壳菌属的种类最为丰富,以Ophiostomapiceae最多。事实上,大量的研究证实,长喙壳类真菌是其主要的伴生菌(de Beeretal.,2001;Zhouetal.,2001;Zhouetal.,2004;Reayetal.,2006;Zhouetal.,2006;Kimetal.,2011;Jankowiaketal.,2013;Davydenkoetal.,2014;de Errastietal.,2017),最常见的类群有Ceratocystiopsis、Grosmannia、半帚霉属Leptographium、蛇口壳属Ophiostoma、球壳孢属Sphaeropsis等,其中Ceratocystiopsisminuta和Ophiostomagaleiformis
在长林小蠹新入侵地最为普遍(Zhouetal.,2004),并且在这些类群中,既有通过蛀道传播的蓝变菌,可造成木材蓝变,影响材质,如Ophiostomagaleiformis,也有可引起松树针叶及根部病害的病原菌,如Leptogmphiumlundbergii。另有研究表明,螨虫在长林小蠹-携播螨-真菌-松树系统中相互作用,间接威胁松木健康(Vissa,2017)。


表2 长林小蠹携带伞滑刃属线虫Table 2 Bursaphelenchus species associated with Hylurgus ligniperda Fabricius
6 我国长林小蠹种群及潜在分布区
目前,已明确长林小蠹于我国山东泰安、烟台市和威海市有分布(Linetal.,2021;任利利等;2021)。Linetal.(2021)于2013-2021年在中国(福建福安、福州,广东珠海、深圳,云南昆明、西双版纳,山东泰安、烟台、威海)及韩国分别设置诱捕器监测长林小蠹,并于2019年 7-8月在泰安诱集到长林小蠹,随后于2020年10月-2021年6月在烟台和威海的黑松伐桩上发现了长林小蠹。与此同时,任利利等(2021)在山东省烟台市牟平区沿海防护林带日本黑松根皮下也发现了长林小蠹。根据COI序列分析结果表明,目前我国长林小蠹种群与韩国种群一致,且均来自新西兰(Linetal.,2021;任利利等,2021),由此推测,长林小蠹可能随新西兰进口的松树原木入侵至我国。
此外,根据文献报道,长林小蠹在我国适生面积较广,潜在分布范围大(王倩,2014;王焱和叶建仁,2017;宋光远等,2018)。该小蠹在我国的适生区主要位于18°~50°N,90°~134°E,亚热带、暖温带之间,其中,中高度适生区主要分布在我国辽东半岛南北部、河北南部及秦皇岛地区、北京部分地区、山东半岛地区,以及云南、贵州、广西、湖北、陕西、甘肃、台湾、安徽、浙江、福建、江西、湖南等省份的部分地区,包含了秦巴山区和云贵高原等高山地区。秦巴山区主要有华山松、马尾松PinusmassonianaLamb.、白皮松PinusbungeanaZucc.等多个松树物种,而云贵高原分布大量马尾松和云南松。因此,长林小蠹在我国继续扩散的风险较大。低度适生区主要分布在吉林、辽宁两省东部的长白山,内蒙古中南部的阴山、贺兰山等山区,新疆北部的天山地区,西藏中部地区,云南和贵州部分地区,以及四川、广西、广东、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山西等省的大部分地区。
7 检疫与防治措施
7.1 检疫处理
在长林小蠹实际检疫检验中,常用溴甲烷进行熏蒸处理(Zondag,1979;魏厚德和邵培泽,1991;Somerieldetal.,2013;Pranamornkithetal.,2014;Huanquilefetal.,2021)。长林小蠹的溴甲烷耐受性较高(Pranamornkithetal.,2014),各个国家熏蒸处理标准不一,就我国而言,进口原木在到达我国口岸前,需要在5~15℃下采用120 g/m3剂量熏蒸16 h,或在大于15℃下采用80 g/m3剂量熏蒸16 h才能达到我国进口标准(安榆林,2012;Somerieldetal.,2013;Pranamornkithetal.,2014)。常采用60 g/m3剂量的溴甲烷处理48 h,对进出口货物进行熏蒸灭虫(Zondag,1979;魏厚德和邵培泽,1991;Huanquilefetal.,2021),即可获得稳定的熏蒸效果,同时也要对掉落的木材残渣、装卸场地、土壤进行消毒(魏厚德和邵培泽,1991)。
此外,根据相关研究,在木材加工和储存时使用一定的光照,可以改变长林小蠹的视觉能力,从而减少其对寄主的趋向能力,进而减少其危害(Pawsonetal.,2009)。电辐射也是害虫检疫处理的常用方法之一,目前,国际昆虫杀虫和不育数据库(International Database on Insect Disinfestation and Sterilization, IDIDAS)中记载的小蠹亚科电辐射耐受性上限为150 Gy,而长林小蠹成虫电辐射耐受性为175 Gy,因此,在实际应用中对其各生活期有效的电辐射强度应超过150 Gy(van Haandeletal.,2017)。
7.2 防治措施
7.2.1人工防治
砍伐焚烧处理、溴甲烷熏蒸和拟除虫菊酯类杀虫剂是目前应用最多的防治措施(Huanquilefetal.,2021)。砍伐处理可以减少长林小蠹栖息地的数量,然而即便死亡的宿主树木被砍伐移除,长林小蠹仍然可以对地下根部进行侵染(Ciesla,1993),因此,砍伐后还需要对伐桩和树根残余进行消杀。
7.2.2生物防治
小蠹的天敌种类较多,最常见的天敌有捕食性和寄生性两类(殷蕙芬等,1984)。根据现有研究结果,长林小蠹天敌以捕食性鞘翅目甲虫为主,如LonchaeacolliniHackman、PityophagusferrugineusLinnaeus、线方阎甲PlatysomalineareErichson、长方阎甲PlatysomaoblongumHisteridae、RhizophagusbipustulatusFabricius、RhizophagusdisparPaykull、RhizophagusferrugineusPaykull、蚁形郭公甲ThanasimusformicariusLinnaeus(CABI,2022),捕食性甲虫的成虫可以取食长林小蠹的卵、幼虫和蛹(CABI,2022),而寄生性天敌仅发现长痣罗葩金小蜂RhopalicustutelaWalker(Zondag,1979;Reayetal.,2012)。
此外,致病微生物也可用于防治长林小蠹。我国学者经过初步实验,发现斯氏线虫SteinernemafeltiaeFilipjev对长林小蠹具有较强的致病性和寄生性(胡学难等,2004)。此外,白僵菌Beauveriacaledonica、B.bassiana、B.malawiensis对长林小蠹和欧洲根小蠹HylastesaterPaykull均有致病性(Glareetal.,2008;Brownbridgeetal.,2010;Reay,2018)。
7.2.3诱捕技术
用原木引诱是诱捕长林小蠹最原始的做法(Tribe,1992);寄主树种的挥发性物质(醇类和萜烯类等)对长林小蠹引诱效果显著(Kerretal.,2017),甚至可以远距离诱集(Meurisse and Pawson,2017)。因此,常用带有乙醇、α-蒎烯或β-蒎烯的诱捕器对长林小蠹进行诱集,作为主要监测手段(Reay and Walsh,2002;Brockerhoffetal.,2006;Meurisse and Pawson,2017)。据报道,含有α-蒎烯或β-蒎烯和乙醇的诱饵对长林小蠹成虫的引诱能力强(Reay and Walsh,2002;Petriceetal.,2004;Reay,2018),其中用乙醇和高浓度α-蒎烯混合的引诱剂引诱效果则更好(Petriceetal.,2004),齿小蠹烯醇和单甘醇、天牛信息素和α-蒎烯等组合也具有引诱效果(Linetal.,2021)。研究还发现,寄主挥发物的释放速率可影响诱集效率(Kerretal.,2022),而诱捕器的密集程度对诱捕结果几乎不产生影响(Meurisse and Pawson,2017),但将诱捕器置于宿主树种附近可能会诱捕到更多的长林小蠹(Brockerhoffetal.,2006)。此外,不同光波(黄、红、绿、白、UV-black light、UV-black-light-blue)对长林小蠹的诱集效果不同(Pawsonetal., 2009),在不同地区使用相同成分诱饵对长林小蠹的诱集效果也不同(Faccolietal.,2020)。另有研究表明,使用绿叶挥发物(GLV)((E)-2-己烯-1-醇和(Z)-3-己烯-1-醇)作为趋避剂,可明显降低诱捕量(Kerretal.,2017)。
8 讨论与展望
生物入侵对生态系统和林业生产构成重大威胁,国际贸易全球化促进了外来入侵物种的传播(Linetal.,2021)。长林小蠹的成功入侵有两个可能的因素,一是它体型微小,常钻蛀生活于植物体内而不易被发现,且该小蠹的所有虫态都易随木材运输(安榆林,2012),近一个世纪的传播很大程度上归因于针叶树原木在全球贸易频率的增加;二是有证据表明它在扩散前可以与姐妹种进行交配,因此,雌性在到达寄主后可能不需要寻找配偶,从而增加其成功定殖的概率(Chaseetal.,2017)。此外,虽然Lanfrancoetal.(2001)报道该小蠹为一夫一妻制,但Sunil(2017)的观察结果表明雄性可以与多个雌性进行多次交配,从而提高繁殖后代的能力,有利于种群增长。
目前,Linetal.(2021)和任利利等(2021)利用分子手段(CO I和28S)初步判断了我国长林小蠹种群可能源于新西兰,从而推测长林小蠹入侵我国可能与我国近年来木材贸易频繁有很大关系,但也不排除从邻国传入我国的可能,因此,进一步追溯入侵源头、入侵路径,了解该小蠹入侵的分子生物学机制,是防止该小蠹二次入侵和继续扩散的关键。此外,Wood and Bright(1992)记载我国“Manchuria”是长林小蠹原产地之一,Linetal.(2019)指出“Manchuria”意为“关东”,CABI依据Wood and Bright(1992)误将“关东”写成“广东”。事实上在2019年之前,除了口岸截获的报道外,我国并没有任何关于长林小蠹危害的记录,且在东亚地区长林小蠹依次入侵日本、韩国、中国(Linetal.,2021),因此,应在全球范围内开展长林小蠹种群遗传学研究,摸清种群分布格局和地理谱系。此外,长林小蠹频繁在我国口岸检疫中被截获,在识别鉴定工作中,分子生物学技术是传统形态学方法的辅助和补充,可弥补形态学方法研究的局限,特别是在幼虫阶段,因此,应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基于全基因组、SNP、环介导等温扩增等手段,进一步研发长林小蠹检测技术,实现对该小蠹各个虫态快速、精准、高效地检测与鉴定,满足口岸与海关检疫的实际需要。
从长林小蠹生物学特征来看,在不同国家和地区具有不同的生物学特性,也显示出该小蠹有较强的环境适应能力(Faccolietal.,2020;任利利等,2021),而且在新传入地区,其种群数量往往很高,根据在美国、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国家的监测数据显示,同地区长林小蠹诱捕数量远大于其它昆虫,常成为区域性优势种群(Reay and Walsh,2001;Petriceetal.,2004;Faccolietal.,2020)。因此,为了确定其危害程度、活动高峰期、最佳防治时期等,应对长林小蠹在我国的生活史、生物生态学等展开深入研究。并且,同其他小蠹虫一样,长林小蠹有多种伴生菌,但在不同国家地区造成的危害程度不同:乌克兰东部长林小蠹伴生菌种群丰富,但普遍致病性不强,对松树林危害甚小(Davydenkoetal., 2014);相反,新西兰、智利等国家时常发生木材蓝变、真菌侵染木材等问题(Zhouetal.,2004;Reayetal.,2006);而在我国,长林小蠹所携带的伴生真菌种类、致病性等特点尚不清楚。此外,目前研究结果表明长林小蠹可以携带伞滑刃属部分种类,但暂未发现该小蠹携带松材线虫,二者是否具有伴生关系,还需进一步研究。
在长林小蠹防治方面,如果频繁进行砍伐焚烧处理、溴甲烷熏蒸或施用拟除虫菊酯类杀虫剂,不但会破坏生态环境,降低生物多样性(Huanquilefetal.,2021),还会提高害虫抗药性(D’Incaoetal.,2012),因此,应开展以天敌与植物源药物为主的绿色防控。然而,目前可应用于防治的天敌较少,仅新西兰于上世纪70年代曾释放捕食性天敌蚁形郭公甲和寄生性天敌长痣罗葩金小蜂用来防治长林小蠹和欧洲根小蠹,但防治效果并不明显(Zondag,1979;Reayetal.,2012),我国仅在实验室发现斯氏线虫对长林小蠹具有较强的致病性(胡学难等,2004)。同时,国内外关于长林小蠹植物源药物研究也非常少,仅智利学者发现智利夜来香Cestrumparqui(Lam.) L’Hér.的乙醇提取物可以作为长林小蠹的拒食剂,并在实验室条件下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效果(Huanquilefetal.,2021)。故此,应开展长林小蠹天敌的系统性调查与开发利用、斯氏线虫田间释放技术、拒食剂和植物源趋避剂开发等工作,为实现长林小蠹绿色防控和可持续治理提供科技支撑。
此外,长林小蠹传播途径广泛,既可以自主飞行扩散,也可以随寄主材料(原木、木质包装物)远距离传播(田家怡,2004;滕凯等,2012;Somerieldetal.,2013),因此,应开展长林小蠹专项调查,除了在出入境口岸进行监测外,重点在胶东半岛周围地区、进口木材的口岸周边松林和我国松树主要分布区进行排查,摸清其在我国的实际分布范围,为检疫性害虫风险管理实践提供可靠信息,便于切断该小蠹入侵途径,减少扩散。
致谢:衷心感谢中国林业科学院森林生态环境与自然保护研究所吕全研究员和北京林业大学任利利副教授在长林小蠹文献查阅和资料收集中给予的指导与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