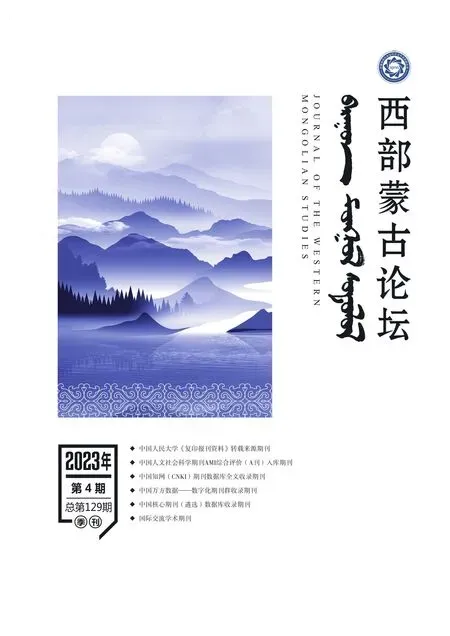区域共同性视角下的民俗文化交融*
——以呼伦贝尔地区各蒙古部落服饰为例
阿木尔
(中央民族大学 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北京 100081)
[内容提要] 费孝通先生提出的“民族走廊”研究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均强调从区域来看民族。呼伦贝尔地区的蒙古族部落主要指巴尔虎、布里亚特与厄鲁特三个部落,三者在该区域内创造了丰富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其中服饰是重要载体。历史上由于三个部落迁徙路线不同,受到不同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其服饰呈现出了不同的风格与偏好,其中典型服饰呈现出了差异性。然而这三个部落在呼伦贝尔地区共处百余年间,相互吸收彼此优秀的文化,在服饰上呈现出了区域共同性的特点,其成因主要是三个部落共同的生活习俗、宗教信仰、审美等导致。呼伦贝尔地区蒙古族各部落服饰共同性一方面体现了民众对区域内的文化认同,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各部落的交往交流交融。
引言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费孝通先生提出了藏彝走廊、西北走廊、南岭走廊等“民族走廊”的说法,其中还提到了一个地区包括东北几省。①费孝通:《谈深入开展民族调查问题》,《中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3期。他在文中提出:“倘若这样看来,中华民族差不多就有一个全面的概念了。所以,我在一篇文章中提出来,我们需要一个宏观的、全面的、整体的观念,看中国民族大家庭里的各个成分在历史上是怎样运动的。”②费孝通:《谈深入开展民族调查问题》,《中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3期,第5页。1988年,费孝通先生提出“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其中提到:“它(中华民族)的主流是由许许多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合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①费孝通等著:《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1页。对此,有学者评论道,“从费孝通的‘民族走廊’研究,到支持对岷江、大渡河、怒江、澜沧江、雅砻江和金沙江等六江流域的民族调查研究,再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的提出,都是在强调通过从区域来看民族。”②麻国庆:《费孝通民族研究理论与“合之又合”的中华民族共同性》,《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期,第19页。不同的历史文化区域是在各民族社会交往、经济往来、文化交流的基础上形成的共同区域文化。呼伦贝尔地区是多民族聚居区,众多民族共同创造了该地区丰富的区域文化,服饰文化是其中重要的一点。
目前学界对蒙古族服饰文化的探讨已有一定的规模,尤其对蒙古族服饰形制、文化内涵的探讨较为深入,但是对蒙古族服饰的区域性关注的较少,尤其呼伦贝尔地区各蒙古部落服饰的区域共同性尚无专文讨论。本文以区域共同性为视角,对巴尔虎、布里亚特、厄鲁特等三个蒙古部落服饰进行考察。呼伦贝尔地区各蒙古部落的服饰丰富多彩、异彩纷呈,系统阐述其区域共同性并作出文化阐释,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一、呼伦贝尔地区各蒙古部落及其典型服饰
呼伦贝尔地区主要有巴尔虎、布里亚特与厄鲁特等三个蒙古部落,各部落均有其独特的发展脉络,其服饰也呈现出了不同于其他部落的特征,其中典型服饰更是独具特色,呈现出了差异性。正如马歇尔•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指出的那样,我们正在目睹一种大规模的结构转型进程,各种文化的世界文化体系、多元化的文化正在形成,因为从亚马孙河热带雨林到马来西亚诸岛的人们,在加强与外部世界接触的同时,都在自觉认真地展示各自的文化特征。③M.Sahlins,Goodbye to Tristes Tropes:Ethnography in the Context of Modern World History,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Vol.65,1988,pp.1~25.
(一)巴尔虎部落及其典型服饰
巴尔虎部落是蒙古部落之一,他们迁至呼伦贝尔地区的时间是清雍正年间。“1732年,清廷将驻防于布特哈地方的巴尔虎甲丁275名及其家属移牧呼伦贝尔驻防,并把他们编入索伦八旗中的左翼正蓝、镶白二旗,驻牧于呼伦贝尔城北部。史称该二旗巴尔虎人为‘陈巴尔虎’。”④明锐主编:《中国蒙古族服饰》(上卷),远方出版社,2021年,第207页。“1734年,共有2984名巴尔虎兵丁及家属移住今呼伦贝尔地区。按‘索伦兵制’,其中2400人编为新巴尔虎两翼八旗。”⑤吴玉霞、彭全军:《新巴尔虎左旗志》,内蒙古文化出版社,2002年,第3页。后迁至呼伦贝尔地区的被称为“新巴尔虎”。自此,来到呼伦贝尔地区的巴尔虎人过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用牛羊皮毛以及打猎而来的猎物皮毛等作为他们服饰的主要来源。
呼伦贝尔地区巴尔虎服饰中以陈巴尔虎靴子“巴尔虎索海固图勒”与新巴尔虎妇女袍服“阿巴盖德勒”最为典型。
“巴尔虎索海固图勒”主要使用皮、白布、黑革、牛皮筋等材料。⑥朝•都古尔扎布:《巴尔虎风俗》(蒙古文),内蒙古文化出版社,2017年,第137页。冬季穿的靴子用山羊皮做靴靿,用生牛皮做靴底。冬季加穿毡袜子,既轻巧又暖和,非常适合野外作业。夏季穿的靴子靴靿用白帆布密纳而成,用生牛皮做靴底,用绿色和黑色大绒镶边,沿边、后脚跟两侧加镶漂亮的云头。“靴靿两侧贴图形(普斯贺)图案,后根、靴靿口用绿、黄、红、黑色皮子装饰云纹、盘缠、回纹和叶形纹,一般由多种图案搭配组合,彩皮或彩布沿口。”①明锐主编:《中国蒙古族服饰》(上卷),远方出版社,2021年,第258页。男靴与女靴式样基本相同,男靴的图案较女靴简单。“索海固图勒适应北方游牧生活,美观大方、结实耐用,体现了马背民族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理念,是巴尔虎人在生产、生活中制作的具有民族特色的纯手工艺精品。”②内蒙古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网:http://web.ichnmg.cn/project/detail.shtm l?ichId=942.
“阿巴盖德勒”,即妇女袍。“阿巴盖德勒”是新娘与新婚不久的妇女必穿的袍服,同时也是外出参加庙会、那达慕或看望长辈时必穿的服装。“阿巴盖德勒”由十三个部分组成,分别是:领子一个、后背与后下摆一个、内前襟一个、下摆两个、“宝古布其”(遮挡前侧褶皱部分的装饰)一个、马蹄袖两个、肩部两个、连接的袖子两个、前襟一个。巴尔虎妇女袍以下摆宽松肥大,灯笼式接袖、大马蹄袖口、断腰结构,裙片部分的抽褶等独具特色。妇女袍的最大特色是“两种颜色组成”和具有“蓬松立体的肩部”。“两种颜色组成”指的是后背与后下摆、内前襟、手臂后部的料子颜色均为红色,而其余的部分都用其他颜色的料子剪裁缝制。“蓬松立起的肩部”是指与其他蒙古族部落妇女袍类似,都有着蓬松立起来的肩部。巴尔虎“阿巴盖德勒”的肩部形状类似于人的胃部,整体无锐角,因此也被为“胃形肩部”。③哈斯图娅等:《巴尔虎民俗》(蒙古文),内蒙古科学技术出版社,2012年,第128页。一般来说,穿上“阿巴盖德勒”标志着女性从少女到已婚妇人身份的转变,象征着从此进入了人生的新阶段。新巴尔虎妇女袍较多保留了古代巴尔虎部落服饰特点和传统风格,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吸收欧亚各民族服饰文化的元素,整体给人一种气势恢宏、古朴华贵、做工考究、精美绝伦的感受。④包晓兰:《蒙古族巴尔虎部落服饰艺术研究》,《民俗民艺》2010年第3期,第99~101页。总之,巴尔虎服饰无论外部造型设计、内部结构设计还是装饰设计,均形成了独特、古朴、完整的文化设计体系,体现了巴尔虎蒙古人对生活与自然的热爱。
(二)布里亚特部落及其典型服饰
布里亚特也是蒙古部落之一,二十世纪初迁至现在的呼伦贝尔地区。“1918年初,在宗教和封建上层分子的煽动和裹胁下,一部分布里亚特牧民和鄂温克当时称哈木尼干牧民从俄国贝加尔省带着家眷连同畜群,迁入呼伦贝尔新巴尔虎和陈巴尔虎地区。之后,其头人那木德格和阿尔德那•阿毕德、扎木斯仁•阿由西等人请求呼伦贝尔副都统衙门给予居住区域。副都统衙门将这批布里亚特人安置在鄂温克自治旗锡尼河地区。”⑤鄂温克族自治旗志编纂文员会:《鄂温克族自治旗志》,中国城市出版社,1997年,第12页。
呼伦贝尔锡尼河地区布里亚特服饰以衣襟“恩格日”、妇女袍“哈么根德勒”以及尤登帽、尖顶帽最为典型。
锡尼河地区布里亚特部落男子和未婚女子传统袍服都是立领,领角略圆,领口外缘镶一道黑边,里缘为红色。右衽,上襟边直线,襟角方形。袍长而肥大,马蹄袖。值得一提的是,其袍服的三色锦条镶边儿衣襟,从下往上依序缝红、黑、蓝三色宽沿边儿,布里亚特语称“恩格日”。“恩格日”是整个袍服中最彰显部族特色的部位。据锡尼河地区布里亚特部落老人们解释,最上面的蓝色象征蓝天,中间的黑色象征大地,下面的红色象征火。表示伟大的苍天、无畏的大地和兴旺的圣火。把这三种颜色放在胸前,表达了对自然的尊重,与自然万物和谐相处的美好愿望。以前锡尼河地区布里亚特人缝制袍服时还在红色布条里缝进三根公骆驼的鬃毛作为心脉,祈愿一切邪恶远离身边。①武战红:《锡尼河布里亚特蒙古族服饰研究》,中央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第28页。对于“恩格日”三种颜色的解释,也有学者认为,白色象征着布里亚特人在沙俄的统治下生活;黑色象征着他们曾在浓雾中迷失方向;红色象征着他们浴血奋战的历史。另外,布里亚特人喜穿贝加尔湖般水蓝色的袍服,用宽下摆象征湖水的波纹,黑色的镶边象征着地域的边界。②〔蒙〕扎•乌力吉著:《巴尔虎蒙古史》(蒙古文),内蒙古文化出版社,2013年,第319页。
布里亚特妇女袍“哈么根德勒”,立领,右衽,分割式结构,由九部分缝合而成,包括领、前襟两片、后片、四块袖子和袍摆。高泡袖、前后裉捏褶皱,袖根宽大。肘上用彩绦和库锦镶三指宽的袖箍。腰间一周捏褶,装饰彩带,马蹄袖,大裙摆,大襟和下摆镶青色、棕色宽边。夏装不镶边饰,平袖口。已婚妇女穿坎肩不束腰带。坎肩与长袍配套穿着,一般与长袍的颜色相同,有短坎肩、“敖吉”两种。短坎肩,无领(圆领口),对襟,短至胯上,紧身,袖窿较宽。领口和袖窿口、对襟和下摆之缘三道三色细边。“敖吉”,蓝色、褐色团花织锦缎、樟缎、云锦做面料,无领(圆领口),对襟,窄肩,袖窿较宽,大下摆,下摆后开裾。腰际两侧有六厘米宽的彩色装饰带,上下沿镶黑、红、黄三色细边。领口和袖窿口、对襟和下摆边、腰际和开裾处也镶三色细边。③明锐主编:《中国蒙古族服饰》(上卷),远方出版社,2021年,第185页。
尤登帽和尖顶帽,这两种是布里亚特部落较为典型的帽子。尤登帽主要在春夏佩戴,用蓝、黑或褐色毛呢缝制,尖顶,无衬里。④明锐主编:《中国蒙古族服饰》(上卷),远方出版社,2021年,第198页。秋冬佩戴红缨尖顶帽,由水獭皮和貂皮、猞狸皮、羔羊皮镶帽檐,用绸或缎做帽面,红和紫色为多。顺帽胎横绗明线,绗纳十一条横线,每条线的间距为1厘米或1.5厘米宽,缝制时追求匀称平整,帽顶缀红缨穗子。关于布里亚特尖顶帽有传说道:“十三世纪时的布里亚特蒙古族隶属于贝加尔湖周围的11个部落联盟。后来,在历史的演变过程中,布里亚特人为了不忘自己的历史,在制作最为尊贵的帽子时,‘以帽子的顶珠象征太阳,红穗代表阳光,帽身上缝制11—14条横向网纹标志部族的组成’。”⑤内蒙古腾格里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编著:《蒙古族服饰图鉴》,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12页。另外,有学者认为,布里亚特尖顶帽三角形样式来源于贝加尔湖向南北延伸的竖长形状。⑥〔蒙〕扎•乌力吉著:《巴尔虎蒙古史》(蒙古文),内蒙古文化出版社,2013年,第319页。
总之,布里亚特服饰的形制、色彩、纹样等方面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美学特征,表现出了浪漫的审美情趣。同时,布里亚特人将其历史记忆、部族标志、信仰习俗等融入服饰中,保持并延续了其服饰文化的旺盛生命力。
(三)厄鲁特部落及其典型服饰
厄鲁特也是蒙古部落之一,其迁至呼伦贝尔地区的时间应为十八世纪。“十八世纪,原属于准噶尔的一些卫拉特部落,被清朝从西蒙古和阿尔泰山迁到今中国东北和呼伦贝尔地区。”⑦〔日〕柳泽明著,吴刚译:《清代迁入中国东北和呼伦贝尔的卫拉特诸部》,《中国边疆民族研究》2017年,第297页。清朝时期,呼伦贝尔的厄鲁特人分别在1732年与1758年从阿勒泰地区经由喀尔喀、察哈尔地迁至呼伦贝尔地区。⑧乌日汗:《呼伦贝尔厄鲁特蒙古族话语元音声学语音学研究》,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1页。
呼伦贝尔地区厄鲁特服饰中的妇女袍、坎肩以及陶尔其克帽子较为典型。
厄鲁特妇女穿长袍,圆立领,无开衩,不束腰带,衣边有各种图案的绣花边或金银丝缝边。在蒙古袍外套穿长坎肩。长坎肩黑色丝绸或贡缎缝制,对襟,肩部微翘,不开裾,两侧佩挂银质“孛勒”,“坎肩左右两侧垂挂白、红、黄、绿、蓝五彩方丝巾,代表乳汁、火种、宗教、绿地、长生天。”①内蒙古腾格里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编著:《蒙古族服饰图鉴》,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60页。右侧孛勒中间挂针线包、银三饰。厄鲁特服饰呼伦贝尔市级非遗传承人斯普乐玛②来源于笔者2022年6月份在鄂温克旗对厄鲁特服饰呼伦贝尔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斯普乐玛的采访。认为,厄鲁特男女坎肩的肩部均微上翘,可能从铠甲演变而来,其作用应该是防身护体。
陶尔其克帽,可以分为男子帽、女子帽、喇嘛帽三类。男子、女子的陶尔其克帽子用蓝黑色的布制作,喇嘛的陶尔其克帽用红、黄、褐色的布制作。陶尔其克帽子的正面一般用蓝、红、褐色的棉线进行刺绣。③纳•巴生编著:《卫拉特风俗》(蒙古文),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10页。女子陶尔其克帽有三指宽的帽围檐,帽胎竖绗明线,帽胎正中镶圆形(普斯贺)图案,红顶结下垂红色丝线穗子,顶结周边贴绣红色六角顶子。女子陶尔其克帽子的佩饰有“图哈”以及“扎拉嘎”,“扎拉嘎”是用黑色棉线金银线缠绕的饰品。另外,还有蝴蝶样式的佩饰,发套上绣有卷草花纹。男子陶尔其克帽,帽檐镶二指宽绿色边饰,帽胎竖绗明线,缀有红顶结。
巴尔虎、布里亚特、厄鲁特是呼伦贝尔地区以畜牧业为主要支柱产业的蒙古部落,历史上由于这三个部落迁徙路线不同,受到不同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其服饰呈现出了不同的风格与偏好。然而,草原文化特征在三个部落的传统服饰中均有明显的体现,即服饰以袍服为主,由帽饰、坎肩、长袍、腰带、搭护、裤子、套裤、靴子、袜子、饰物等组成。④闫茹:《蒙古族服饰色彩分析对比—巴尔虎、布里亚特、厄鲁特三部落》,《纺织报告》2021年第5期,第105页。然而,这三个部落在呼伦贝尔地区共处有百年之余,其服饰文化相互影响,相互融合,产生了区域共同性的特点。
二、呼伦贝尔地区各蒙古族部落服饰的共同性
费孝通先生在其文章《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中提到了地区性的多元统一,他以中原和北方两大区域为例,阐释了牧业与农业的区别各自发生相适应的文化。⑤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4期,第17页。另外,费孝通先生《关于中国民族基因的研究》一文中讨论了区域和民族关系。在他看来,中国境内的民族集团所在的地域空间中,不同区域之间、不同民族之间都存在相似性和联系性。对此,麻国庆教授解析道,“民族和文化是民族融合的两个层面,探讨一个多民族地域内的民族文化,既要强调民族的特殊性,也要强调地域内文化的共同性。”⑥麻国庆:《费孝通民族研究理论与“合之又合”的中华民族共同性》,《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期,第19页。从服饰角度看,呼伦贝尔地区各蒙古部落都呈现出了诸多的共同性,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服饰共同性
呼伦贝尔地区巴尔虎、布里亚特、厄鲁特三个部落的服饰在帽子与头饰、袍服、靴子、佩饰等方面均呈现出了共同性。
1.帽子与头饰
帽子。巴尔虎、布里亚特、厄鲁特等三个部落男子都喜戴礼帽,这是目前在呼伦贝尔地区各蒙古部落中广泛流行的,也是呈现出的区域共同性之一。另外,布里亚特与厄鲁特的男女均戴尤登帽;巴尔虎与厄鲁特的男女均戴陶尔其克帽;布里亚特与巴尔虎的男女均戴风雪帽。从帽子的穗子上看,厄鲁特和布里亚特的男女帽顶都带有穗子,而且样式基本相似。
女子头饰。不管是妇女头饰还是姑娘头饰,巴尔虎、布里亚特、厄鲁特等三个部落都采用金银为主要的材质,尤其对银质的使用很是广泛。除金银之外,这三个部落的女子均喜欢用红珊瑚、绿松石、琥珀、玛瑙、蓝绿宝石珠装饰头饰。在女子头饰中,巴尔虎与布里亚特的女子头饰都带有头围箍,大多为银质,后来人们也喜用锡、铁等其他材质。女子头饰中辫套是较为普遍的饰品之一,布里亚特部落与厄鲁特部落已婚妇女均用绒布的辫套,有些辫套的样式基本相同,呈现出了一定的共同性。
2.袍服
日常袍服。巴尔虎、布里亚特、厄鲁特等三个部落四季的袍服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尤其是男子、老人、儿童的袍服样式基本相同。“德勒”作为日常袍服,在生活劳作中均以实用舒适为主,并且在草原上放牧时,宽下摆的“德勒”不仅可以作为御寒的衣物穿着,也可作为被子、枕头等生活寝具使用。除此之外,袍服前襟腰带以上部位,不仅可以装盛东西,下摆也可以作为暂时的盛器。例如,在呼伦贝尔草原上经常可以看见男子在前襟腰带以上部位装哈达、烟酒等物品,女性用袍服下摆装柴火、干牛粪等。各级非遗传承人在访谈中也提到了这三个部落袍服共同性的问题。非遗传承人赛•乌仁其木格与牡丹在采访中表示,这三个部落的袍服具有蒙古族袍服的基本样式。另外,厄鲁特迁至呼伦贝尔草原后受到了区域内布里亚特服饰的影响,“男女都穿宽下摆马蹄袖长袍,男子长袍开裾,女子长袍不开裾,袍边用金、银丝线或库锦镶单边,不论男女蒙古袍多缀银、铜扣或布扣。”①明锐主编:《中国蒙古族服饰》(上卷),远方出版社,2021年,第285页。从袍服的色彩角度来看,这三个部落女装的主色为蓝色系,辅以红色系以及棕色系,主色的色彩明度和纯度都比较适中,给人以沉稳的感觉。除此之外,蒙古人对蓝色有特殊情感,使得其服装多用蓝色作为主面料颜色。辅色主要为黄色系、红色系、绿色系等,色彩纯度和明度相对较高。②闫茹:《蒙古族服饰色彩分析对比—巴尔虎、布里亚特、厄鲁特三部落》,《纺织报告》2021年第5期,第107页。
皮袍。呼伦贝尔地区纬度较高,自古冬季严寒,人们必须穿裘皮衣物才能够达到御寒保暖的效果。总体来说,巴尔虎、布里亚特、厄鲁特等三个部落不管男女皮袍,大致都有吊面皮袍、白板羊皮袍两种。男子除了穿以上两种皮袍之外,还有答忽(翻毛大皮袍)、皮马褂两种,皮马褂又可以分为吊面皮马褂与翻毛皮马褂。③明锐主编:《中国蒙古族服饰》(上卷),远方出版社,2021年,第148~285页。这些服饰原料都是五畜(即绵羊、山羊、牛、马、骆驼)产物,也是他们赖以生存的生产方式中可直接获得的物品。巴尔虎、布里亚特、厄鲁特等三个部落有着共同的生产生活方式,也有着共同的生活环境,因此相互影响呈现出了共同性。在与非遗传承人的交谈中,他们也提到皮袍具有的共同性。非遗传承人阿拉坦古日古台举例称,“陈巴尔虎人的熏皮袍镶边与布里亚特的‘恩格日’类似,女孩的皮袍用红、黑、蓝三色镶边,男孩的皮袍用绿、黑、蓝三色镶边,而且都佩上绿或蓝色腰带。”④来源于笔者2022年6月21日下午,在陈巴尔虎旗对“巴尔虎索海固图勒”的内蒙古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阿拉坦古日古台的采访。另外,非遗传承人赛•乌仁其木格认为,这三个部落服饰具有严寒地区袍服的特点,即皮袍的下摆较长,冬天骑马劳作时可以覆盖住腿脚,起到保暖的作用。⑤来源于笔者2022年4月15日至6月18日,在新巴尔虎左旗对巴尔虎服饰呼伦贝尔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赛•乌仁其木格的采访。这三个部落的皮袍呈现出了共同性特点。
马蹄袖。一般在皮袍上缝制马蹄袖,或另接马蹄袖。非遗传承人斯仁吉木认为,这三个部落的服饰中都有马蹄袖,而且形制相同。根据笔者的调研,这三个部落对马蹄袖的称呼主要有“图如”与“尼德如嘎”两种。陈巴尔虎人与布里亚特人都称马蹄袖为“图如”,而新巴尔虎人与厄鲁特人称其为“尼德如嘎”。另外,从马蹄袖的材质上看,非遗传承人巴达玛汗达称,“马蹄袖一般可以用猞猁、貂、旱獭、羔羊、大羊皮来制作。”①来源于笔者2022年6月20日在鄂温克旗对布亚特服饰呼伦贝尔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巴德玛汗达的采访。从马蹄袖的材质可以看出,基本都是五畜皮毛或兽皮来制作,这与其生活环境与生产劳动中需要保暖、实用的追求有关。
妇女袍与坎肩。巴尔虎与布里亚特的妇女袍有许多相似点,例如,均为立领,右衽,分割式结构。两袖向上隆起高泡袖,彩绦装饰三指宽的袖箍,袖根宽大,前后裉捏褶。腰处捏褶,装饰马蹄袖,大裙摆。另外,布里亚特妇女袍与厄鲁特妇女袍也呈现出了诸多共同性。原来厄鲁特妇女袍的连接线在膝盖处,随着服装的演变与发展,连接线慢慢向上移,直到演变成目前布里亚特妇女袍的样式,即连接线达到了腰部位置。坎肩一般与长袍搭配穿着,巴尔虎、布里亚特、厄鲁特等三个部落的坎肩下摆均较宽大且后开裾,妇女穿坎肩均不束腰带。布里亚特与巴尔虎的坎肩被称为“敖吉”,圆领口,对襟,窄肩。除此之外,巴尔虎与厄鲁特妇女坎肩均在腰间捏褶皱。
腰带。这是呼伦贝尔地区巴尔虎、布里亚特、厄鲁特等三个部落服饰中必备的服饰,它也是蒙古服饰的特征之一,尤其男子袍服必须戴腰带,这也是作为蒙古族男性的标志,称为“布斯太”,即戴腰带的人。
3.靴子
巴尔虎、布里亚特、厄鲁特等三个部落男女均穿皮靴与布靴,皮靴一般为黑色或棕色,高靿翘尖样式,牛皮做底,靴靿口前高后低,用黑布、彩布或彩皮沿口。陈巴尔虎与厄鲁特都有穿索海靴子的传统,样式与制作方式基本相同。这三个部落所有男靴与女靴的式样均基本相同,只是男靴装饰相对简单一些。
4.佩饰
女子佩饰。巴尔虎、布里亚特、厄鲁特等三个部落的女子均佩孛勒(坠饰)、荷包、针线包以及银三饰(牙签、耳勺、镊)等。一侧的孛勒下挂银三饰、针线盒等,另一侧挂绢绸帕。
男子佩饰。这三个部落的男子均佩戴蒙古刀、火镰、褡裢等,有时也佩戴烟荷包、碗袋等。一般右侧腰带上悬挂蒙古刀,左侧腰带上佩挂褡裢。另外,原来巴尔虎人与厄鲁特人结婚时,新郎均佩戴弓箭,这一点两个部落有着相同的传统,然而现在这种习俗已然消失。在笔者的调研中,各级非遗传承人也认同这三个部落男女佩饰所呈现出的共同性。
从符号学的角度来看,以上巴尔虎、布里亚特、厄鲁特等三个部落的服饰是一个符号系统,其款型、色彩、佩饰、图案等等都具有符号象征意义,甚至还包括了袍服的制作工艺。总之,不同服饰符号系统中的符号能指也许相互有别,但他们却有相似的所指,或者共同指向民族的迁徙历史,或者共同象征民族生存的地域环境,或象征他们的审美观念,或涉及宗教信仰,总之博大精深。②白永芳:《哈尼族女性传统服饰及其符号象征》,中央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年,第73~74页。呼伦贝尔地区作为各蒙古族部落服饰符号系统产生或发展的地域环境,服饰当中显示出一定的共同性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二)服饰工艺共同性
从袍服、靴子以及饰品的工艺上来看,具有一定的共同性。
1.袍服工艺共同性
巴尔虎部落、布里亚特部落和厄鲁特等三个部落的袍服,在造型、剪裁、缝纫、镶边、扣袢、刺绣等工艺上,呈现出了共同性。
造型工艺。“造型工艺是蒙古族传统袍服制作过程的第一步,人体的外形特征、运动机能、生活环境、生活方式以及传统习俗等均是袍服造型的主要依据。”①苏日娜、徐子淇:《新型城镇化背景下蒙古族传统袍服的工艺传承》,《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6期,第132页。这三个部落的袍服从外形轮廓上看是T型与A型的组合,内部造型工艺主要由分割线、镶边、绲边、扣袢等制作工艺组成,外形轮廓以及内部造型工艺共同组成袍服的基本造型,体现出宽松、舒适以及精致朴素的风格特点。
裁剪工艺。由于这三个部落的袍服大多情况下使用团花丝绸、织锦缎、丝绒、蚕丝绸、布等为面料,因此用剪刀来进行裁剪。根据非遗传承人色•乌仁其木格老人的介绍,剪裁工艺的步骤可以简化为以下四个步骤:(1)了解人物。(2)选择袍服材料。(3)量体。由于每个人的身体都不尽相同,因此要根据穿戴者的高、矮、胖、瘦以及男、女、老、少的不同而量体。(4)剪裁。对此,有着多年制作巴尔虎袍服的裁缝花日②来源于笔者在2022年6月23日对陈巴尔虎旗花日民族服装加工店的田野调查。也认为,这三个部落袍服的剪裁方法相同,也与其他蒙古族部落相同。
缝纫工艺。缝纫工艺包括缝纫工具、缝纫方法和技巧。其中缝纫工具包括缝衣针、线和顶针,缝衣针的粗细选择要根据所缝制袍服质料的薄厚而定,缝衣线的粗细及纤维质地的选用也是如此。缝纫时,大多数人使用蒙古族传统手针缝纫技法,其具体操作顺序为:左手拿需要缝制的袍服衣料,用戴牛角雕制顶针的右手食指顶住缝衣针的针头,拇指和食指捏紧针体,使针尖穿过袍服衣料,连续进行一上一下的缝制。通过这种独到的持针、运针的方法和技巧,可以手工缝出驱针、缲针、㩟针、攻针、缉针等多种针法。③苏日娜、徐子淇:《新型城镇化背景下蒙古族传统袍服的工艺传承》,《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6期,第132页。
镶边工艺。“镶边工艺包括沿边工艺、绦条装饰和滚边工艺三个部分。其中沿边工艺和绦条装饰工艺主要起到装饰美观袍服的效果,绲边工艺主要是对袍服衣片边缘进行包边和加强牢固度。”④苏日娜、徐子淇:《新型城镇化背景下蒙古族传统袍服的工艺传承》,《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6期,第132页。镶边工艺使用的质料一般多采用棉布、库锦、绦子、化纤布等,位置主要在传统袍服的领边、大襟、袖口、下摆边缘等部分适用。
扣袢工艺。不管是巴尔虎、布里亚特还是厄鲁特,扣袢工艺是其袍服制作过程中重要的一个环节,尤其巴尔虎人的扣袢工艺是其“德勒”(袍服)最为突出的一点,这些扣袢既实用又美观,是实用性和审美性的统一体。新巴尔虎人与陈巴尔虎人的袍服扣袢都用库锦对折,然后用缝纫机轧一道之后用长针翻正成袢条,以10厘米左右长度剪成一个袢条,三三为一排手工钉在“德勒”上。一般来说,扣袢和镶边的面料、宽细、风格保持一致,与袍服的整体部分融为一体或相互呼应,呈现出和谐对称的美。
刺绣工艺。刺绣是蒙古族袍服的装饰工艺,在巴尔虎、布里亚特、厄鲁特的服饰中刺绣工艺也较为普遍,尤其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审美的多样化发展,刺绣也有了多样化的发展,除了在帽子、袍服、靴子上有刺绣工艺之外,目前人们也喜欢戴刺绣的佩饰。
2.靴子工艺
呼伦贝尔地区巴尔虎、布里亚特、厄鲁特等三个部落的民众有穿蒙古靴的传统。以制靴材料来分,蒙古靴有毡靴、皮靴和布靴之别。按照学者的分析,蒙古靴制作需要经过50多道工序才能完成。①关晓武、董杰、黄兴等:《蒙古靴传统制作工艺调查》,《中国科技史杂志》2007年第3期,第246页。呼伦贝尔地区的制靴工艺中,除了陈巴尔虎靴子“巴尔虎索海固图勒”工艺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之外,这三个部落的大多数靴子的工艺具有共同性。
靴底制作主要是做千层、盖板和粘皮底以及纳底子。靴筒制作主要是制作帮、靿和云子,以及将云子契在帮、靿上,并将帮、靿缝合在一起。上靴子,即靴底和靴筒两个部分的缝合。排靴子,即用即用楦头、腰板、打芯、后跟等辅助工具从内部将靴子撑起,再往靴筒里加入一些微湿的荞麦皮、麻絮等材料将楦头等充塞住,然后用锤子在靴筒外敲打,使靴子成形。②关晓武、董杰、黄兴等:《蒙古靴传统制作工艺调查》,《中国科技史杂志》2007年第3期,第246~249页。
3.佩饰工艺
呼伦贝尔地区巴尔虎、布里亚特、厄鲁特这三个部落的民众喜爱佩戴金银饰品,例如金银头饰、发饰等,而制作金银饰的工艺主要有铸炼、锤打、编结、雕镂、錾刻、浮雕、掐丝、鎏金、挫金、挫银等。
捶揲工艺。捶揲工艺是绝大多数器物成型前必须经过的工艺工程,又称锻造、打制,出土金银器铭刻中称“打作”。该工艺利用金、银质地较软、延展性强的特点,将金银片放在模具上反复捶打成型的一种金银器制造工艺。捶揲工法可以将金银器做得非常轻薄,比用铸造法消耗的金银材料较少,而且方法也相对简单。“一些形体简单、较浅的器物可以一次直接捶揲出来。”③潘嘉来编:《中国传统银器》,人民美术出版社,2004年,第59~60页。在捶揲法技术广泛应用后,铸造法便在金银器制作上很少使用。金银器捶揲工艺有两种基本方法:一种是自由捶揲法,主要用于金银器成型;一种是模冲捶揲法,主要用于金银器纹饰的制作,需要事先将纹样刻制好底模,加工时将模衬在金银板下,反复捶揲,底模上的纹样就能翻印到器物上。用模冲技法制成的纹饰富有立体感,明暗对比强烈,装饰性强。新巴尔虎盘羊角头饰的制作中就使用模冲捶揲法,是节省时间,效果较好的工艺。④王烨编著:《中国古代金银器》,中国商业出版社,2014年,第99~100页。唐代金银器皿中的大多数碗、盘、碟、杯等都是用锤揲技术制作的。
錾刻工艺。錾刻工艺的具体方法是用小锤打击各种大小纹理不同的錾刀或錾头,使之在器物表面留下錾痕,形成各种纹样,錾刻一直作为细部加工最主要的手段而被使用。錾刻工艺中给最常见的技法是浮雕錾花,佩饰上所刻画的纹饰与图案惟妙惟肖,细腻入微。由于錾刻工艺具有独特的装饰效果,在现代金属装饰制作中仍在沿用。
掐丝工艺。掐丝工艺是两汉时期从西方传入的。⑤潘嘉来编:《中国传统银器》,人民美术出版社,2004年,第64页。如果说錾刻工艺是一种讲究转折结构、线条粗细搭配的艺术,那么掐丝工艺却更加精细,是将纤细如发的银丝在薄薄的银片上凹出各种造型的艺术。“掐丝是先将白银制成薄片,剪成细丝,编成一定的花纹图案,再焊接在器物的表面。其后,再将宝石、琉璃等物嵌入。”⑥潘嘉来编:《中国传统银器》,人民美术出版社,2004年,第64页。掐丝工艺的具体操作一般来说,一只手取一块比所需纹样面积略大的玻璃,确保掐出来的花丝自然平整,另一只手握着镊子,掐出精密细小的花纹。
镶嵌工艺。又称实镶工艺,主要工序如下:①制作零部件,通过锯割、插花、翻卷和锉削方法,将经过多次过火的金属原料制成具有一定图案的部件。②焊接,将制作好的零部件按设计要求严丝合缝地拼攒在一起,用焊药焊接起来形成主形体。③抛光,制作好的饰品用玛璃刀、酸洗、抛光机等进行抛光。④镀嵌宝石,将宝石固定在饰品的主形体上,常见的镂嵌方法有爪镶、槽镶、包镶等。
鎏金工艺。鎏金是我国传统的镀金方法,战国时期就已经广泛应用。其方法是首先将成色优质的黄金锤揲成金叶,剪成细丝,放人坩埚中加热烧红,按一两黄金加七两水银的比例加人水银混合成金汞,俗称金泥。然后将金泥涂抹在所需鎏金器物的表面,其后在火上烘烤器物,水银遇热蒸发,金留存于器表,鎏金器遂成。鎏金工艺可分通体和局部鎏金两种。局部鎏金即只在纹饰部分鎏金,也分两种,一是刻好花纹后再鎏金,二是鎏金后再刻花纹。①潘嘉来编:《中国传统银器》,人民美术出版社,2004年,第60~62页。
焊接工艺。焊接工艺是把器物的部件以及纹样同器体连接成整体的一种工艺。具体方法是通过加热使焊药熔化,把被焊部件与主体黏结牢固。焊药的主要成分一般与被焊物相同,加少量硼砂混合而成,也有用银与铜为主合成的焊药。焊接后需对焊痕进行处理,高超的焊技几乎看不出焊接的痕迹。②潘嘉来编:《中国传统银器》,人民美术出版社,2004年,第66页。
三、呼伦贝尔地区各蒙古部落服饰文化共同性的成因
呼伦贝尔地区巴尔虎、布里亚特、厄鲁特等三个部落共同的生活习俗、宗教信仰、审美等使得服饰文化呈现出了共同性。
1.生活习俗共同性
巴尔虎、布里亚特、厄鲁特等三个蒙古部落均为游牧部落,放牧不仅是其赖以生存的生产方式,也是其所处的地理环境造就的生活方式,该生产生活方式造就了共同的生活习俗,进而在其服饰上也呈现出了共同性。
蒙古族的服饰适应游牧民族的自然环境和游牧经济的特点而产生。蒙古高原气候寒冽,生活于此的蒙古诸部以游牧为生,在马上活动的时间较长。因此,其服饰必须有较强的防寒作用而且便于乘骑。牧人所穿的长袍、皮裤、腰带、坎肩、皮毛、皮靴等一系列别具风采的服饰正是这样产生的。这三个部落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不断适应北方环境及游牧经济特点,服饰文化也呈现出了鲜明的区域文化特点。
根据笔者的调查访问,巴尔虎、布里亚特和厄鲁特等部落的民众一般都会有若干服装,这些服装既包括传统袍服,也包括现代服装。民众制作和穿着主要因场合不同,目的不同而有所区别。例如传统服饰分为仪式礼仪场合服饰、日常生活服饰两种,而日常生活服饰又可以细分为在城镇的日常生活与牧区的日常生活服饰。具体来说,这三个部落的民众一般在城镇与牧区两个场域内流动,当进入城镇,人们普遍选择现代服装,轻便保暖的服装就可以满足城镇生活的需求。而在牧区,人们普遍选择传统袍服,戴帽子,穿靴子,这主要因为更加保暖适用,适合野外劳作。可以看出,这三个部落民众由于生活习俗的原因,在服饰的穿着方式上呈现出了一定的共同性。
2.宗教与信仰共同性
巴尔虎、布里亚特、厄鲁特等三个部落的民众有信仰藏传佛教、萨满教的传统,另外也有自然崇拜、图腾崇拜、动物崇拜、祖先崇拜等信仰的存在,而这些信仰在服饰中有所体现,而且呈现出了共同性。
巴尔虎、布里亚特、厄鲁特等三个部落的服饰无不体现着他们的宗教信仰,例如这三个部落的女性盛装佩饰中有一种装佛像的银饰品,这与蒙古地区深受藏传佛教的影响有关。另外,在蒙古族传统文化中帽子是备受崇尚的服饰之一,这与其信仰习俗息息相关。这三个部落的民众在日常生活中十分重视帽子的摆放,不允许摆放在低处,不许他人随意穿戴玩弄,尤其这三个部落的男性普遍认为帽子关乎个人的尊严与运气,是至高无上的象征物品。除此之外,从这三个部落帽子的红穗到袍服的领子,从腰带到靴子的纹样等均呈现了他们的宗教信仰习俗。
3.审美共同性
生活于呼伦贝尔地区的巴尔虎、布里亚特、厄鲁特等三个部落的服饰具有共同的审美特征。例如在服饰色彩搭配上,崇尚白色、天蓝色、红色、绿色等与生活环境相和谐的颜色,并且注重色彩之间的和谐统一,杜绝过于张扬与跳跃。另外,在袍服的剪裁与穿着上,当代这三个部落的女性特别注重体现自己的曲线美,因此都以量身定制为主,男性则为了体现自己的伟岸雄壮,都将腰带系在腰部以下位置,这些都体现了服饰审美的共同性。
四、结语
“中华民族就是在一个地理地貌、气候条件存在较大差异的自然框架里形成。复杂的自然框架形成了诸多不同的文化区。在不同的文化区以及同一文化区中,各民族之间既相互竞争又相互吸收彼此优秀的文化。”①费孝通等著:《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6~7页。巴尔虎、布里亚特、厄鲁特等三个部落生活在同一个文化区中,虽然在历史上由于迁徙以及受到不同文化的影响,然而在呼伦贝尔地区共处百余年时已经在诸多方面呈现出了共同性。服饰作为物质与精神文化的载体,它可以最直观地体现一个区域内的差异性与共同性。作为典型服饰的各部落服饰是其彰显独特性的符号,然而共同的区域、习俗、观念、审美导致了其共同性更加明显。
中华民族共同体建立在不同民族共同性的基础之上。民族和文化是融合的两个层面,在统一多民族国家的任何区域里,文化具有共生性,它们之间互相吸收和借鉴。不管是从历时的角度还是从共时的角度来看,这三个部落间的服饰及其文化内涵是具有共同性的,其主流是趋同的。具体来说主要体现在帽子与头饰、袍服、靴子、佩饰以及其工艺等方面。其成因是这三个部落共同的生活习俗、宗教信仰与审美。呼伦贝尔地区巴尔虎、布里亚特、厄鲁特等三个部落服饰的共同性,一方面体现了一定区域内的文化认同,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一个区域内部落间交往交流交融。呼伦贝尔地区巴尔虎、布里亚特、厄鲁特等三个部落长期混合杂居,共同地域、共同心理、共同文化模式造就他们对本土服饰文化的认可,同时在这样的基础上形成了交往交流交融的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