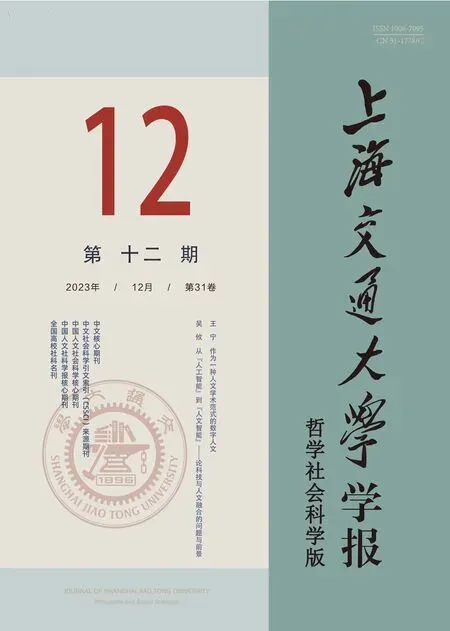作为一种人文学术范式的数字人文
王 宁
(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上海 200240)
“数字人文”(digital humanities)这个概念一经诞生就引来了人们的持续关注和讨论,甚至争论。也许陷入争论一端的人们并未注意到,“数字”在这里与“人文”是两个并列的概念,并不意味着二者之间的对立。因此这个概念在过去的十多年里已被相当一部分锐意创新和拥抱科学的人文学者接受,并自觉地用于自己的人文学术研究。与此同时,从事数字化实践的技术人员也开始关注人文学科的研究及其成果。近期横空出世的ChatGPT,也即对话人工智能或对话机器人,又将这其中的技术比重推进了一步,大有用科技手段取代人工研究的趋势,因此引来的非议便不足为奇。本文继续笔者以往的研究,在进一步讨论数字人文之于人文学术的范式意义之前首先简略地回应这一新出现的现象。
一、 面对ChatGPT的挑战
确实,在当今诸多热门话题中,ChatGPT的热度一直在持续升温,并使相当一部分学者,尤其是从事人文学术研究的学者,感到忧心忡忡。人们也许要问,究竟什么是ChatGPT呢?它之于我们的工作和生活有何意义呢?我这里仅综合概括公共媒体对它的介绍,并加以自己的理解: 在我看来,首先,对于使用这一模型的人来说,它是一款可以使人与机器或人工智能对话聊天的软件,你可以与人工智能进行热烈的讨论,在对话和聊天过程中也许会出现一些可以引发你兴趣和讨论的相关话题,用户可以在这里了解软件的人工智能思维是怎样一种形态,或许它对任何问题都会有自己的见解。我们甚至可以从网上下载ChatGPT软件,并可以看到对它的介绍: 该对话软件2023年官方正版是一款人工智能对话软件,可以实现与用户进行智能交互,实时对话,对于用户提出的问题进行回答,还能以各种拟人化的对话方式,进行软件编写、模仿人物发送推特、构建虚拟机等,十分便捷,且功能强大,整体上显得十分智能化。毫无疑问,ChatGPT的诞生使我们的工作和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且随着我们与它的交流和对话,参与我们对话的人工智能也会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化。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自己培训这样一种人工智能模型,使我们看到由此产生的有趣效果。质言之,ChatGPT是人工智能技术驱动的自然语言处理工具,它能够通过学习和理解人类的语言来进行对话,还能根据聊天的上下文进行互动,真正像人类一样进行聊天交流,甚至能帮助我们完成撰写邮件、视频脚本、文案、翻译、编码等任务。(1)一些公共网站上对ChatGPT的介绍很多,尽管各类介绍经常重叠,但有时有些互补。本文在此综合了百度和360导航网站的介绍并融入笔者本人的理解。
从以上的这番简略概括,我们不禁惊讶地发现,凡是人类所能从事的语言文字信息处理工作几乎都可以由人工智能或ChatGPT代为完成。难怪它的出现首先使人文学者和从事语言文字工作的人感到惶恐,生怕自己的饭碗被夺去。有鉴于此,那么以人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人文学术研究还有什么独特的地方可言呢?确实,在此之前,不少人文学者,包括我本人在内,也已经开始在新文科的视野下频繁地讨论“数字人文”这个话题,(2)这方面可参阅以下拙作。王宁: 《走向数字人文的新阶段》,《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8卷第1期,第10—11页;王宁: 《科学与人文的冲突与共融: 兼论后人文主义语境下的数字人文》,《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7年第70卷第4期,第7—15页;王宁: 《科技与人文: 对立还是互补?》,《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21卷第3期,第1—6页;王宁: 《科技人文与中国的新文科建设——从比较文学学科领地的拓展谈起》,《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29卷第2期,第11—16页;王宁: 《科学技术与人文学术的辩证关系——兼论远读与细读的对立与互补》,《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54卷第4期,第88—97、177页;Wang Ning, “The Rise of Posthumanism: Challenge to and Prospect for Mankind,” Fudan Journal of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vol.12, no.1 (2019), pp.1-13; Wang Ning, “Introduction: The Interactive Relations betwee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Literary Studies,” Comparative Literature Studies, vol.57, no.4(2020), pp.585-594.仿佛数字人文真的能提供给我们有效的科学技术方法使人文学科摆脱危机的境地,并且在科学与人文之间架起一座桥梁。但是对其持怀疑甚至抵制态度者也不在少数。毫无疑问,任何一种良好的愿望能否实现尚有待于实践和时间的检验。尽管如此,数字人文确实已经对人文学科的教学和学术研究产生了某种革命性的影响,它促使我们不得不对我们传统的人文学术研究方法进行反思。今天,面对ChatGPT的挑战,我们也不得不对数字人文这个概念进行重新认识和思考。但可以肯定的是,数字人文的诞生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一种新的学术范式以及阅读和研究方法的崛起。
有鉴于此,本文首先从一本书的阅读谈起,因为这本书的作者凯瑟琳·海尔斯(N. Katherine Hayles)是美国杜克大学的一位比较文学教授,她早年先后从事自然科学和人文学科的学习和研究,这两方面的造诣都很深,是美国最早倡导数字人文的文学研究者之一,她的专著《我们如何思维: 数字媒体与当代技术创新》(HowWeThink:DigitalMediaandContemporaryTechnogenesis, 2012)与当前的人文学术研究有着密切的关系,并能带给我们一种全新的思维模式和研究方法。(3)参阅N. Katherine Hayles, How We Think: Digital Media and Contemporary Technogenesis,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2. 我2014年去杜克大学讲学时,在该校书店里买了这本书,立即被其介绍的数字人文方法所吸引。回国后我便向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推荐此书,其英文影印本于2022年出版,笔者应邀为之撰写了导读。这本书最初出版时,数字人文这个术语虽然在中国学界也许闻所未闻,但在西方学界方兴未艾,并已为文学研究者用于文学批评和研究,而该书作者正是这方面的一位先行者。作为一位以比较文学研究为主的人文学者,海尔斯的思考并不仅限于文学,而更是一种跨学科的人文学术研究,她的这部专著被认为是一部具有引领人文阅读和研究范式之变革作用的著作,对整个人文学术研究都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和作用。确实,作为一位比较文学研究者,海尔斯对于当代高科技之于人文学术,尤其是全球化时代的人文学术研究的作用异常敏感。
因此她提出并试图回答这样一个在平常人看来十分简单的问题:“我们如何思维?”但是她提出问题的方法却不仅仅基于人文学术的视角,同时也基于她所热衷于讨论的“后人文”研究视角,此外还更是一种类似于我们当下在中文语境中热烈讨论的“新文科”的视角: 它不同于传统的人文学科思维模式,但又摆脱不了科学方法和人文情怀的结合。如果我们仔细阅读海尔斯这部具有“阅读革命性变革之范式”意义的著作,就不难发现,她在科技探索之开始就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我们是如何思维的。她认为伴随着这种探索的正是我们与媒体的同步思考。随着当今高科技的迅猛发展,数字学术与印刷学术之间的裂痕不断扩大,恪守传统的老牌人文学者固然对数字化时代的来临持一种抵制的态度,但海尔斯却从一开始就以极大的热情拥抱并支持了数字化对当代技术的创新,认为这是一种关于人类与技术共同进化的观点之必然。
海尔斯在该书各章节中对数字化时代的到来作了详尽的阐释。在她看来,数字媒体必然要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传统的印刷术,但同时又无法全然摆脱与传统印刷的干系,因而它是一种将数字作品定位在印刷传统中的新的方法。除了研究数字人文是如何改变学术研究、教学和出版的,海尔斯还描述了在数字媒体中工作的一连串后果,在这种媒体中,浏览和扫描,或者说“超级阅读”(hyper reading),以及通过机器算法进行分析,都是像细读一样有效的阅读形式,它们之间并非全然对立,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作为对细读的必要补充。因此她认为,我们必须认识到所有这三种类型的阅读都同样是有效的,它促使我们理解传统教学方法的局限性和在未来的可能发展前景。除了说明比较媒体的角度需要什么,海尔斯还探讨了技术创新的螺旋性整体复杂性。她思考了早期数据库带来的影响,对我们在数字时代对时间和空间不断变化的认知提出了挑战。为了深化我们今天对数字技术带给人文学者的巨大变革的理解,我们确实应该思考如何才能提供一个强有力的理由来应对当下人文学科所面临的各种挑战。在这方面,数字人文概念的提出也许能够使得传统的人文学术研究取得某种范式转变之效果。
二、 之于文学研究的数字人文
作为一种人文学术范式变革的产物,数字人文对整个人文学科的研究都有着重要的影响和意义。由于我本人主要是一位文学研究者,因此本文的讨论主要聚焦于文学研究,或者更精确地说,聚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诚然,关于数字人文之于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研究的作用和意义,海尔斯在她的专著中也作了介绍并加以讨论,她讨论的对象之一就是在当下颇为人们所热议的“远读”(distant reading)方法及策略。熟悉当代世界文学研究的学者都知道,“远读”是美国意大利裔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比较文学学者佛朗哥·莫瑞提(Franco Moretti)针对长期以来占据文学批评和研究界的“细读”方法提出的一种反其道而行之的阅读策略。尽管之于文学研究,细读早已成为文学研究者和批评家必须掌握的一种方法,或者说,这种方法已经具有范式意义。我们从事比较文学教学就必须从细读具体的文学文本开始,但是我们的研究又不能仅局限于细读几部作品,我们还必须对世界文学的发展脉络有一个总体的把握。实际上,莫瑞提本人也是一位细读文本的高手。正是由于他对细读方法的娴熟运用,他便看出了其中的一个短板,也即用于世界文学研究,这种方法显然是不可能奏效的。莫瑞提经过仔细研究发现,我们的文学研究者一生所能阅读到的世界文学作品,只占真正的世界上所有国家文学中的极小一部分,而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各国用不同语言发表的文学作品则因为种种原因而被文学史或文学阅读者“屠宰了”,或者说全然受到我们的忽视。为了了解这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文学的概貌,我们只有采用一种远距离的阅读方法。当然,莫瑞提的“远读”方法提出后就引起了相当的争议,在某种程度上倒是实现了他的初衷: 世界文学并非是要阅读更多的文本,也不只是文学本身,而是更大的问题,也即世界文学概念于本世纪初的重新提出和建构意在引发讨论,因此它是一个“问题导向”的概念。(4)Cf. Franco Moretti, “Conjectures on World Literature,” New Left Review, vol.1 (January-February 2000), pp.54-68.莫瑞提早在本世纪初就利用大数据的筛选方法远距离地阅读世界文学作品,尤其是小说作品,他的这种前所未有的创新和方法论方面的革命标志着一种新的阅读和研究范式的诞生。关于他的世界文学研究以及远读与细读的辩证关系,我已做过专门的讨论,此处无须赘言。(5)关于远读与细读的辩证和互补关系,参阅拙作王宁: 《科学技术与人文学术的辩证关系——兼论远读与细读的对立与互补》,《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54卷第4期,第88—97、177。
当前,在中国的人文学界,人文学科的学者也开始频繁地谈论“数字人文”这个话题,除了研究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的学者,专事古典文学和古文献研究的学者也发现这种方法的便捷和有效,并有意识地将其运用到自己的研究中。(6)这方面可参阅刘石: 《大数据技术与古代文学经典文本分析研究》,《数字人文》2020年第1辑(创刊号),第24—31页;孙茂松: 《诗歌自动写作刍议》,《数字人文》2020年第1辑(创刊号),第32—38页;刘石: 《文献学的数字化转向》,《文学遗产》2022年第6期,第10—13页。它至少可以把学者们从繁琐的资料检索中解放出来,使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对这些文献资料进行分析和阐释。因此就数字人文这个概念本身的内涵而言,它包含了两个关键词: 数字与人文,也即将数字化的科学方法用于带有学者主体个性特征的人文学术研究;此外,也可以通过数字化这一手段使得人文学术的成果得以快速有效的传播。这样看来,数字人文的诞生,在一定程度上在科学与人文之间架起了一座可以沟通的桥梁。当然,这也是人们的一种美好愿望,至于能否实现这一美好的愿望则是另一回事。尽管如此,一些观念保守的人文学者依然对这一新生事物的出现感到忧心忡忡,担心它会消弭人文精神和人际交流活动。因此,他们试图通过坚持自己的传统人文立场来抵制科学技术对人文学术的冲击和影响。这一点尤其体现于文学研究中。在西方国家,一些人文学者宁愿通过书信保持与亲朋好友的联系,也不愿使用电子邮件,更遑论用即时通讯社交软件交流了。在中国,一些老派文学研究者仍然坚持手写自己的学术著作和论文,而不愿直接用电脑写作,在他们看来,一旦坐在电脑旁,本来尚存的一点写作灵感也骤然消失了。
同时,2020年以来的新冠病毒大面积蔓延使得传统的人文学术研究也受到冲击,一切教学工作都改为线上授课,老派教师的那种手拿粉笔夹着一本书走进教室面对学生授课的方式改为面对电脑屏幕看着课件授课,一旦碰到机器故障或网络卡顿就会令这些不熟悉技术的老教师一筹莫展。因此毫不奇怪,这些老派人文学者并不欢迎科学技术干预人文学科的研究。但是,将科学技术的手段运用于人文学科的教学和学术研究已经成为一大潮流,对此任何人也是阻挡不了的。既然阻挡不了,我们作为比较文学学者将如何面对这种影响呢?我认为当下人们所热议的所谓“数字人文”也许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或者说至少可以在科学与人文之间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在这方面,海尔斯对新的技术和阅读方式的介绍对我们十分有用,而她对莫瑞提的远读方法的赞赏和讨论则更是值得我们思考和借鉴。
在海尔斯看来,远读的价值至少在于弥补了这样一个缺憾,即我们不能通过细读的方法看到世界文学的全貌,更无法掌握世界上那么多的语言了。但问题是,远读仅能获得世界文学的发展概貌,如何才能深入地理解和欣赏世界文学经典作家的作品呢?在我看来,它留下的这一缺憾自然应当由细读来弥补。因此,我认为世界文学研究的理想模式应该是“远读”与“细读”这两种方法的有机结合: 远距离阅读可以使我们对世界文学的全貌有一个较为全面的了解和把握,而细读则使我们对某一位伟大的作家甚至某一部文学经典作品有一个深入细致的理解和把握。总之,我们不能说这两种方法孰优孰劣,因为它们是一种互补的关系。
三、 人文学术研究的数字化
现在再回过头来谈谈我本人对数字人文及其之于比较文学研究的意义的看法。人们也许会进一步追问,既然数字人文是一个崭新的领域,那么它只是科学与人文相结合的一个产物吗?显然,数字人文顾名思义,确实是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并且是大学的计算机系科与人文学科相交叉的一个项目。它从人文学科的电脑化、电脑的人性化以及数字人文实践发展而来,同时涉及多个研究课题。它融合了数字化和天然数字材料,以计算机和数字发表所提供的工具将由传统的人文社会科学学科衍生而来的各种方法加以结合。这样看来,我们便可以很容易地发现,作为一个新的跨学科领域,数字人文的诞生,使我们得以使用当代计算机科学技术来更新传统的人文学科研究,使得人文学者从繁琐的资料搜集和检索中解放出来,从而能在理论阐释和建构创新方面多进行思考,同时也可以使得人文学科各分支领域的研究成果“数字化”,从而为更多的本学科领域之外的学者所共享。因此可以说,它给人文学者的研究带来的更多是便利和效率,同时它也使得人文学科的研究更接近科学研究。
如前所述,数字人文的诞生确实使得传统的人文学科研究带有科学的方法论和科学的精神,因而标志着另一种新的学术范式的革命性变革,同时也标志着具有转折和范式意义的新文科已诞生,在这一过程中,数字人文所起到的作用是举足轻重的。因此数字人文命题的提出绝不只是科学技术加上人文,而是可以同时含括这二者,并达到其自身超越的一个新的领域。新文科理念在中国的诞生就是这种超越的一个直接成果,因此,它更加具有范式的意义和引领人文学术研究的作用。
谈到范式(paradigm),我们会立即想到创立这一概念的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 1922—1996)的划时代著作《科学革命的结构》(1962),在他看来,范式是经过实践检验被证明是成功和切实可行的经验之总结:“范式作为共享的例子,是我现在认为的这本书中最新颖、最难以被理解的部分的核心元素。”(7)Thomas S. Kuhn,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 4th Edition,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2, p. 186.确实,如库恩所言,一种范式一旦确立,就在一定的时期内有着相对的稳定性和可持续发展性,并能吸引一大批践行者。另一方面,范式的确立也可以为一个学科的长久发展路径定下基调,并为之指明新的发展方向。这在西方学界是如此,在中国学界也基本得到人们的广泛认可。这一范式的转变带来的结果表明,使用科学的手段和计算机技术,人文学科的研究将变得越来越便利和高效。
就文学创作而言,网络文学早已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创作中的一支生力军。按照中国作家协会的一份权威性报告所称,网络文学已经日益进入文学生产的主流。确实,随着网络文学的诞生和网上书店的创立,一大批实体书店关闭了,中国当代几乎所有的文学杂志的订数都急剧下降。毫不奇怪,我们今天会经常听到这样一些耸人听闻的哀叹:“文学死了”“文学研究已寿终正寝。”虽然这只是数字化文学生产和发行带来的不利结果,但已经使不少人文学者陷入了恐慌。情况果真如这些人所描述的吗?显然并非如此简单。
一些唱衰人文学科的人甚至提出这样的问题: 我们今天学习文科还有什么用?如果没有什么用处的话还有必要在大学里设置文科系科吗?这在中国的外国语言文学界也是如此。曾经有过自己蜜月的外国文学研究如今也江河日下,无可奈何地呈一种萎缩的状态: 除了一些紧缺的稀有语种外,英语文学专业的毕业生已经不再是就业市场上的有力竞争者。正是在这样一种语境下,新文科的概念提出了,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使得传统的人文学科走出危机的境地,也使得外语学科的毕业生更加适应国家战略需求,满足市场竞争的条件。在这方面,数字人文应该是大有作为的。不看到这一点就有可能被滚滚而来的时代潮流所淹没。
不可否认,数字人文确实给我们带来了诸多便利。我们今天无须像过去那样伏案写作,写完草稿后一遍又一遍地修改,直到最后誊清交稿。结果,那些手稿最终将伴随着其作者的知名度而进入不同级别的博物馆,而绝大多数小人物的手稿则很快被销毁。而现在的情况则大不相同: 我们只需要在电脑上修改书稿,最后不留痕迹地将终稿发给出版者,而出版者则会尽快地将其排版付印,有时只是在线出版而无须印制成纸质书刊。诚如美国学者凯瑟琳·菲茨帕屈克(Kathleen Fitzpatrick)所总结的:“在我看来,它所做的就是介于数字媒介和传统人文研究相交叉的工作。它以两种方式运行。一方面,它运用数字媒介的工具和技术来解决传统的人文学科问题,但同时又使得人性化的研究模式通过数字媒介来承担。”(8)Cf. Kathleen Fitzpatrick, “On Scholarly Communication and the Digital Humanities: An Interview with Kathleen Fitzpatrick,” interview by Andrew Lopez and Fred Rowland, In the Library with the Lead Pipe, January 14, 2015.这样便使得科学技术与人文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了,所起到的作用无疑是过去单一以人工为主的研究方法难以起到的便捷和高效作用。
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可否认,确实,长期以来,人们总是习惯地认为,人文与科学技术是两个迥然不同的知识领域,因而各自诉诸不同的研究方法。而且自从古代以来,人们就有这样一种流行的看法: 科学技术在大多数场合总是与人文相对立的,尽管偶尔也有例外,这一点尤其体现于文学和文学研究。人们通常认为,在科学技术领域,越是当下出现的东西就越是先进;而在人文学科领域,越是古老的东西则越有价值,因为它经过了时间的考验和历史的筛选。虽然这种看法不错,但也绝非无懈可击。确实,在评价科学技术成果时,我们完全可以说某一项发现或研究取得了颠覆性的突破,已经完全取代了先前的成果。但在评价人文学科的研究成果时,使用这样的措辞就不免失之偏颇。我始终认为,对人文学术研究的成果进行评价时,我们更应该强调其对前人的研究及学术观点的继承和发展,也即我们经常说的传承和创新。因为文化或人文需要长久的历史积淀,这应该是科学技术与人文学术的一个主要差别。
这也正是为什么人们逐渐达成了一个共识: 科学技术与人文学术天然就是对立的。除非你有很高的天赋,否则你无法同时做好这两样事。在人文学科内部的跨学科方面,圣经和莎士比亚剧作分别是宗教和文学两个领域内的经典,但在对这二者都有精深研究的美国批评家布鲁姆看来,“圣经和莎士比亚的共同点,比大多数人想象的要少得多,我自己怀疑这种共同之处只是某种普遍性,也即全球性和多元文化性”。(9)Harold Bloom, Shakespeare: The Invention of the Human, New York: Riverhead Books, 1998, p. 722.确实,对于布鲁姆这样的人文主义者和老派文学批评家而言,文学或人文学术就是他们的安身立命之本,放弃了这一资本,他们也就一事无成了,所以他们面对一切有可能威胁人文学科生存的理论思潮都会持反对的态度。这也是不足为奇的。因为,在他们看来,人文与科学技术的融合有可能消弭人文学术研究中人的主体性和价值,其结果将必然给传统的人文学科带来强有力的挑战。
从人文学科,或更具体地说,从比较文学研究的角度来看,我们通常认为科学技术与文学和文学研究无甚关系,更不用说与其他人文学科领域有何关系了。但是,如果我们从科学与人文的互补和互动关系认真地考虑这一点,就会发现,文学和文学研究确实与科学技术有着割舍不断的关系,这种关系在当今的高科技时代已经变得愈益明显。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不懂一些科学技术知识,即使从事纯文学研究也会变得困难重重。因此,科学技术与文学研究的关系就体现于这二者既相互对立又可以进行互补和对话。
在最近的二十多年里,伴随着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也不断地呈现出新的气象: 当代科幻小说的崛起就是科学技术与文学想象相结合的一个产物。科幻小说的崛起唤起了这个缺乏想象力的物质主义时代的创作欲望,既然世俗世界的素材已经被作家们使用殆尽了,那么对于有着非凡想象力的作家来说,建构一个虚拟的幻想世界去寻觅新的创作素材便成为必然。就这一点而言,科幻小说在全球化时代中国的兴起,加速了中国当代文学走向世界的进程。我们都知道,文学和科学都诉诸想象力,这正是二者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的相通和融合之处。同样,在理论批评界,以解构为己任的理论思潮,诸如生态批评、动物研究、后人文主义批评等,向习来已久的人类中心主义发起了强有力的攻击,大写的“人”被从至高无上的“神”地位拉下,回复到了人作为自然界的一个物种的本来状态。因此,传统的人文主义需要注入新的成分,传统的人文学术研究也需要科学技术的支持。就此而言,数字人文正是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应运而生的。它的范式意义不仅体现于人文学术研究,同时也体现于人文学科的评价。
四、 人文学科的评价问题再识
人文学科的评价问题,一直是我过去二十多年来思考的问题,我还在这方面发表了一些文章。(10)这方面可参阅以下拙作。王宁: 《国际英文权威学术期刊评介及写作策略》,《中国研究生》2003年第5期;王宁: 《对人文社会科学现行学术评价系统的确认与辩护》,《学术研究》2006年第3期,第5—9页;王宁: 《人文社会科学评价的多元化和国际化标准》,《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5卷第4期,第83—89页;王宁: 《人文社会科学的多元评价机制: 超越SSCI和A&HCI的模式》,《清华大学学报》2014年第29卷第4期,第82—85页;王宁: 《再论人文社会科学的国际影响及评价标准——兼论中国实施文科院士制的可行性和必要性》,《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17年第3期,第109—116、128页。我始终认为,正如当今的国际学界所一般认为的,任何一门学科,不管是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社会科学学科,都需要经过评价才能展示出其存在的价值和发展潜力。也只有通过客观数据和同行专家相结合作出评价,其评价结果才有可能成为向政府部门或国际有关机构申请资金投入和人员编制配备的重要依据。这一点已成为当今的自然科学甚至某些社会科学学科的共识。那么,究竟如何实行人文学科及其研究成果的评价呢?是依靠某个权威人士或权威机构的主观评价还是凭借科学技术的手段进行量化评价?这也一直是学界争论不休的一个问题。
作为一位长期从事人文学科教学和研究的学者,我本人认为,尽管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都必须得到评价,但这二者又不尽相同,它的评价标准也不能完全机械地照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量化指标。特别是当前我们在大力发展科学技术的同时,也不应该忽视人文学科的繁荣和发展,在建立中国自己的世界一流大学和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的过程中,人文学科的学者应该是大有作为的。这已被长期的实践和历史的经验所证明。
纵观当今的世界一流大学,我们不难发现,一所公认的世界一流大学,如美国的哈佛、耶鲁,英国的牛津、剑桥等,除了有一批世界顶级的科学大师和众多诺奖得主外,还必定拥有一批杰出的人文思想家和学术大师,这些著名的学府还不断地向国际学界和世人提出具有原创性和广泛影响力的理论和思想,从而产生影响世界学术同行的人文思想家和理论大家。在中国当代学界,自诩为思想家和理论家的学者并不在少数,但是得到国际学界认可者却寥寥无几。(11)参阅(澳) 麦肯齐·沃克: 《21世纪的21位思想家》,姜昊骞译,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2023年。在这本书中,作者展示了当今世界具有影响力的21位思想家的思想理论,其中也不乏几位日本和韩国及有着第三世界背景的流散知识分子,但是却没有一位中国或华裔思想家进入作者的视野。这一方面说明作者仅代表自己的一家之言,其思维定势依然受到西方中心主义的影响和束缚,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中国的理论家和思想家在英语世界确实缺乏广泛的影响力。这就需要我们扪心自问: 为什么中国的一些顶尖大学在国际上的排名持续上升,但却未能产生影响世界的理论大家和思想家?所谓“钱学森之问”同样也适用于我们的人文学科。
我们可以宣称,在自然科学界,中国的自然科学家已经在很多学科领域走在了世界的前列。根据汤森路透科技集团(现改名为科睿唯安)每年发布的论文发表数据,中国科学家在该集团研发的数据库SCI(科学引文索引)所收录的期刊上发表论文的数量已超过美国,达到世界第一。尽管我们不唯论文,但也可以自豪地认为,中国无愧为一个科技大国。中国科学家们的这种探索和拼搏精神完全值得人文学者学习。同样被纳入科学范畴的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SCI)的数据也显示,中国的社会科学也奋起直追,学者们直接用英语著述,通过在英美学界的国际权威刊物上发文或自己主办英文刊物由英美的出版社出版,收录该数据库的中国学者的论文数量也达到了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而与他们的成就相比,中国的人文学者在艺术与人文引文索引(A&HCI)国际期刊上的发文则少得多,所产生的世界性影响也小得多。许多在国内如雷贯耳的一流学者的著作长期得不到英译,或者即使被翻译成了英语,所产生的影响力也十分微弱。中国的人文学术虽然通过中华学术外译项目的资助已经“走向”了世界,但未必真正“走进”了世界,尤其是进入占据西方思想理论主流的英语世界。
毋庸置疑,这种较大的反差实际上是很不正常的,与中国目前所拥有的世界大国地位也是很不相称的。从国际范围来看,中国人文学者的发文量和影响力确实远远不够。虽然国内学界对汤森路透集团开发的数据库SSCI、A&HCI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在我们自己尚未拿出一个足以与之相匹敌和影响力与之相当的数据库之前,在中国的语言尚未成为国际公认并通行的学术语言之前,将其当作衡量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国际影响力的标准之一仍不失其客观性。
当然,我们并不主张所有的国内高校都去效法这一标准,都让学者们去争相用英文写作论文在国际刊物上发表。这既是不现实的,也没有必要。作为中国的人文学者,我们首先要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并发表在国内的权威刊物上。但对于一个优秀的理论家和人文学者,这还远远不够。如果说科学无国界的话,那么我们照样可以论证,人文学术也没有国界。特别是在当下美国政府竭力阻挠中美顶尖科学家就某个世界尖端学科的课题进行交流的大背景下,民间的人文交流依然可以进行,有时甚至还能起到政府间交流不能起到的作用。我们人文学者照样可以在英语世界的权威刊物上发表讨论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式现代化的论文。(12)我本人在这方面深有体会,并作了一些有效的尝试,自21世纪初以来,我应邀为二十多个国际英语刊物编辑了关于中国研究的主题专辑,产生了较大的国际影响。下面是其中的一些主题专辑的信息: China in the 20th Century, in Modern Language Quarterly, vol.69, no.1 (March 2008); Rethinking Modern Chinese Fiction in a Global Context, in Neohelicon, vol.37, no.2 (2010); Comparative Literature: Toward the (Re)Construction of World Literature, in Neohelicon, vol.38, no.2 (December 2011); Towards a Third Literature: Chinese Writing in the Americas (co-edited with Evelyn Hu-Dehart and Russell C.Leong), in Amerasia Journal, vol.38, no.2 (2012); Modern China and the World: Literary Constructions (co-edited with Liu Kang), i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Studies, vol.49, no.4 (2012), Global in the Local: Ecocriticism in China, in ISLE: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Environment, vol.21,no.4 (Autumn 2014); Rediscovering China: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co-edited with John Aldrich), in European Review, vol.23, no.2 (March 2015); Global Maoism and Cultural Revolution in the Global Context, i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Studies, vol.52, no.1 (2015); Twentieth-and Twenty-First-Century Chinese Fiction (co-edited with Charles Ross), in Modern Fiction Studies, vol.62, no.4(2016);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East Asia, i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Studies, vol.54, no.1 (2017); Cosmopolitanism and China, in Telos, vol.180 (2017); Chinese Encounters with Western Theories, in Modern Language Quarterly, vol.79, no.3 (2018); Ecocriticism in East Asia, i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Studies, vol.55, no.4 (2018); World Drama and Modern East Asian Drama, in Neohelicon, vol.46,no.1 (2019);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Context of World Literature (co-edited with Peng Qinglong), in Journal of Modern Literature, vol.44, no.2(2021).我这里仅想提醒那些在国际学界有着很好声誉和很大学术影响力的国内顶尖高校,这些高校在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建成世界一流大学和使其中的若干个学科跻身世界一流。每年国家对这些高校投入巨大,因而这些学校的教师和研究人员理应产出世界级的科研成果和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人文学术著作和理论。但是令人遗憾的是,迄今国内学界,尚有相当一批学者,甚至包括一些双一流大学的人文学科教授,也仅仅满足于做自己某个狭窄领域的学术研究,或在国内的某个学科领域内发挥有限的影响,至于这一研究成果能否推进该学科的发展则与己无关,更遑论去引领国际学术同行了。长期以来,西方汉学家的学术研究影响了西方学界对中国的看法和研究,主宰着国际主流媒体关于中国国家形象的建构。
这样做的结果之一便是造成了一种极大的反差: 一些在本国学术地位并不高的汉学家竟然在中国被奉为人文学术大师,而相比之下,中国的一些一流人文学者却鲜有机会受邀去世界一流大学演讲,他们的著作长期以来在异国他乡仍处于“死亡”或“边缘化”的状态。与自然科学相比,中国的人文科学所取得的世界性成就和所产生的国际影响确实小得多。如果我们从繁荣中国人文学术的历史使命和构建中国人文学术话语体系来看,中国的人文学者应该具有一种宽广的国际视野,努力以自己的研究实绩跻身国际一流,以适应时代的需要和国际学界对中国的期待。中国学者不仅要在国际中国问题研究中引领潮流,起到主导性作用,而且还要以产生自中国土壤里的经验和成果影响国际学术主流的研究,进而为解决全人类所共同面对的问题提供中国的智慧和拿出中国的方案。
但是究竟什么才算是世界一流呢?这就涉及对学者及其研究成果的评价。从事人文学科的评价,应该确立这样两点: 首先,人文学科也像自然科学一样,既然是一种学术研究,那就应该有自己的评价机制和评价标准,真正优秀的人文学术成果应该是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和评价标准的衡量的。其次,人文学科的评价也应该划分层级: 对于顶尖的一流大学,应以公认的国际标准来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表明该学科的成果在哪一个层级上是一流的。再者,人文学科的评价不能像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那样,仅仅用量化的标准来衡量。一个人的学术影响可以凭借客观数据来衡量,每年发布的爱思唯尔全球高被引和中国高被引学者榜单就是如此。但是,不管是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社会科学,对一项成果的价值判断则应该主要依靠同行专家的评价。只有兼具这二者,人文学科的作用和价值才能得到普遍认可。
我在前面讨论了当代高科技、数字化时代的来临,及其对人文学术研究的挑战。那么在即将结束的部分,我再回到我本人一贯坚持的人文立场。在这里我应该指出的是,在所谓的“数字人文”中,我们仍然没有放弃必要的“人文”情怀和人文精神,这应该是人文学者赖以安身立命之本,只是我们需要在传统的固化人文观中增添一些科学技术的含量和科学的精神。这样我们才能说服那些轻视文科的人,使他们重视人文学科之于社会和世界的不可忽视的作用。
作为人文学者,我们在人文学术研究中想要做的,就是要引入一种新的学术范式,这种范式比哲学的思辨和推理更加科学,比依赖人的主体性的传统人文学术范式更带有数字化或技术化的元素。但是,我们在人文学术研究中突显技术手段并非意味着摒弃人文情怀和人文精神。因为毕竟是人在从事人文学术研究和生产,是人在著书立说,并对前人的著述和思想理论进行评价,因此在人文学术研究和评价中,人的作用应该是放在第一位的。即使我们可以说,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文学创作和翻译在相当程度上已经由机器和人工智能所取代了,我们还需要那么多人文学者从事人文教育和学术研究吗?要回答这个问题自然应该是另一篇文章的任务,但我这里只想指出,文学创作和人文学术研究是带有鲜明个人特色的一种创造性劳动和研究,不同的人做这项工作所取得的效果是不同的;文学翻译也是一样,像林纾、傅雷、杨宪益和许渊冲这样的文学翻译大家有着广博的多学科知识和独特的翻译风格,他们的译著是任何其才华和知识稍逊于他们的译者都无法取代的,更遑论机器和人工智能翻译了。(13)就在即将结束本文之际,我偶然读到张辉发表于《中华读书报》上的一篇文章《了解中国文化,才能讲好中国故事》,文中提及他测试了ChatGPT的讲故事和翻译才能,发现对于复杂多义的文学作品的深层含义,ChatGPT也无能为力。在此特别感谢张辉教授用实验证实了我的看法。张辉: 《了解中国文化,才能讲好中国故事》,《中华读书报》2023年7月12日,第13版。
在评价科技成果时,我们可以说某一项发现或研究取得了颠覆性的突破,完全取代了前人的成果。然而,在评价人文学术的研究成果时,使用这样的措辞则不可避免地会误入歧途。因为人文学术的研究需要长期的积累,这也正是不少科学家可以“少年得志”名满天下,而人文学者则常常是“大器晚成”的原因所在。因此,在对人文学术成果进行评价时,我们更应该强调其对前人已有成果的继承与发展,或曰传承与创新。即使某个全新的成果也是基于前人的先期研究的,绝对不可能横空出世。
我们还可以据此进一步推论,人文学科中优秀的文学作品和学术著作也是由富有天才想象力的作家和知识渊博、思想深邃的学者创作出来的,因此不可能被任何其他工具所复制,也无法被任何翻译工具准确地用另一种语言转达出来,当然也包括机器或人工智能翻译,因为只有那些具有极高智商的人才能理解并欣赏高雅的文化和艺术产品,包括文学。同样,文学史也证明,只有那些文学天才才能创作出具有永久价值的优秀作品,而那些才华不如他们的人则不可能创作出他们的那些作品。
鉴于以上讨论,我们不难得出这一初步的结论: 那些以阅读纸质书刊为主的人文学者也应该学习一些数字技术,这样他们就可以很方便地收集资料并且有效地传播自己的知识、思想和著作。同样,那些依靠数字化进行研究的人文学者也不应该就此而不去阅读优秀的人文学术著作,或者过分地依赖技术手段来代替自己的阅读和研究。因为毕竟是人类创造了世间各种奇迹,发明了先进科学技术。无论科技多么先进,拥有这些科学技术手段的还是人,因此人文学者仍然应该具有以研究人为主的人文情怀,并且不任意地贬低人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