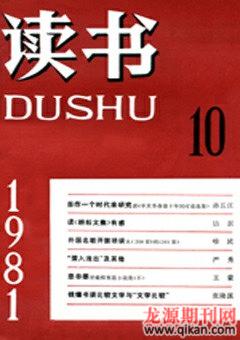怀念出版战线的老战友——华应申
徐雪寒
应申同志逝世已经两个月了,但是他纯朴、坦率而真挚的音容笑貌,一直萦回在我的脑际,不能去怀。
“维古昔以怀人兮,心徘徊以踌躇。”由近谈起罢!
那还是关在牛棚的时节,一批批从广西来的人向我调查应申的历史。调查,当然并无不好,但在那个时期,它是另有含义的;我断定,对于这位象金子那样纯净的人,也正经历着烈火的“煅炼”。以后,远道辗转传来有关他的遭遇,尽管广西的秩序恢复较早,“四人帮”在那里不能为所欲为,但听到的种种,也够令人毛骨悚然,啼笑皆非。一九七七年底,他调回北京工作,过年后,他和储继同志一起来看望我们,我和他有二十四年不见了,感到他清癯瘦弱,音容憔悴。他对我问长问短,关怀备至,也谈到十年中几位被整死的老同事,就是不谈他自己的遭遇,问他,也顾左右而言他,完全没有从个人出发的怨愤。多宽敞的襟怀啊!
但是,精神创伤可以痊愈,体质损害却不能不有所遗留。不久,医生宣告他已患有后期肺癌。对于这一不治之症,他沉着镇定,无所畏惧。他承受了放疗、化疗等的煎熬。去年,从上海回来,毛发秃尽,食欲全无,我去探望他时,他用低不可闻的完全硬挤出来的声音,反复地询问我关于国家的经济形势、调整方针的落实等等,而不屑多谈自己的事。每次一见到我,必定问我孙冶方同志的病情,当我告诉他冶方神奇般的治疗效果时,他展出发自心底的笑容,好象他自己是一个完全健康的人。
我问过他,你的儿子在广西百色,两个女儿留在南宁做工,你打算怎样?他回答我说,我们前后两次在广西工作,近二十年,让他(她)们留下去吧,报答边疆人民对我们的恩情。
我问过他,你一九三四年入党,因组织破坏失去关系,以后一直在党的影响和领导下干革命,一九三七年又入党,事迹昭然,应否申请恢复党龄?他回答我说,党的组织部门会关心党员的政治生命,我不应为自己提出申请。
他就是这么一个人。
这是四十六年前的往事了。一九三四年秋,他因南京党组织被破坏,流亡来上海,参加我们在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和中国经济情报社的研究、学习和政治活动。我们知道他在一九三二年被捕过,经王昆仑同志营救出狱的。他沉默寡言,但政治态度积极,中英文都不差,还会些美术、书法,懂会计。一九三六年秋天的一个夜晚,我去他家串门,他同孙克定同志合住一个小亭子间,当时他被迫离开生活书店,正从事译书工作。桌上放着一本绒面精装、庄严肃穆的书——《海上述林》,封面下方印有“诸夏怀霜社出版”字样,他看到我有些不解的样子,就如数家珍般告诉我,鲁迅先生如何为秋白同志编印文集的内幕。我当时就想,他真是一块搞编辑出版工作的好料子。夏天,组织委托我和他筹办新知书店。如果没有应申,看来我是不会有信心接受这个任务的。我们都是两手空空,勉勉强强靠卖文为生的人。为了有一个自己可以绝对控制的出版机构,我们决定办一个革命书店。
靠五元、十元地筹募资金,靠捐献卖文所得的稿费,终于凑起六、七百元,就挂出牌子,出书了。他对当时出版事业颇有所见,知道不但政治风险很大,而且经济上也要冒收不回书款、吃倒账的风险。于是我们决定,一方面力争公开合法,一方面尽量撙节日常开支,降低成本,多出好书。我们租了一个十来平方米的厢房,应申是唯一的专职干部,每月拿十八元生活费,住在这个办公室兼货栈的小房子里,还得贴回公家(我们当时对书店的称呼)几元房租。一本书定稿后,有关版面设计、买纸、跑印厂、核算成本、确定售价以及书店设计帐册、记账、开票等等工作,主要都是他承担的。新知书店的方针,是出版严肃的社会科学书籍,探讨中国经济问题。除了出版已经颇具声誉的《中国农村》月刊外,从一九三五年十月起,开始出书。当时国民党实行卖国的法币政策,我们出版了《中国法币往何处去?》一书,加以揭露。意大利侵略阿比西尼亚(埃塞俄比亚),我们马上出版了两本支持阿比西尼亚人民的书,还出版了应申翻译的苏联科普作家M.伊林的《人类征服自然》和应申、克定合译的《苏联的发明故事》等书。在短短三个月里,我们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书店就站住脚了,应申日日夜夜的辛劳得到了结果。以后,我因另有任务,由姜君辰兼任经理,出面负责,应申主持实际业务。在他的精心擘划下,一九三六年至抗战前,新知业务有了飞速发展,相继出版了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编的、包括钱俊瑞、薛暮桥、孙冶方等人文章的《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薛暮桥的《中国农村经济常识》、《农村经济基本知识》、狄超白的《通俗经济学讲话》等书,以及吴大琨翻译的《大众政治经济学》、吴清友译、孙冶方校的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增订本)》和巴比塞著、徐懋庸译的《从一个人看一个新世界》(斯大林传)等名著,除了《中国农村》外,还出版了姜君辰编的《新世纪》月刊、叶籁士编的《语文》月刊等刊物。
我们既获得了读者广泛的好评,也引起了国民党的仇视。记得出版《斯大林传》之前,应申曾和我商量,估计国民党可能因此对书店下手,但考虑到这本书在当时的政治意义,决定还是要出版,但新知书店只署名为经销者(这是钻国民党出版法的空子),并将纸型存书单独租房放置,以减轻受突然袭击时的损失,受袭击后还可以继续秘密发行。我听了他的周密考虑,自然同意他的决定。这时店里的工作人员也逐渐扩充到五、六人,多是决心献身革命文化事业的青年,有王益、朱希、徐律(文化大革命中被迫身故);还有个刚刚刑满出狱的一九二二年入党的老革命吴渊(原名吴亚鲁,一九三九年平江惨案七烈士之一)。这些人,多是应申吸引、物色来的,他们团结成为一个战斗的集体。新知太穷了,但对于每一本书的出版,务求政治观点正确、内容充实,决不马虎,决不损害党和读者的利益。记得一九三六年春,苏联版画展览在南京、上海展出,我建议应申请人选编一集子。后来选编就绪,版子(包括彩色版)都已制就,付印前,为了慎重,又由钱俊瑞同志(他是新知书店理事长)请史沫特莱转请鲁迅先生审阅,鲁迅先生审阅后说,编得不行,不能用。应申就决定停印,不惜资金遭受损失。应申这种认真负责、一丝不苟的作风,终身不变。
在十里洋场的上海,书店全体工作人员包括应申在内,过着极为清苦的生活。一九四○年周总理还赞许地说过,比根据地的供给制还要艰苦。
一九三七年七月,组织上决定我重返新知工作,没几天,八·一三抗战爆发了,新知这时除了存书和账款外,现金极少。工作人员大都去摆地摊卖书,一面筹款将存书运往内地。我因组织上另有任务,离沪北上。这副重担又完全压在应申身上了。
一九三八年三月我从华北前方绕道返抵武汉,当时应申历尽千辛万苦,已把书店搬到武汉,开始筹备出书了。群众的抗战热潮使新知出版物销路激增,资金周转加速。我们的工作干部逐渐增加到十来人,沈静芷、岳中俊、张朝同、曾霞初、陈敏之、周德炎、储继都是这时陆续进店的。也是应申出的主意,我们把湖北省委创办的扬子江出版社和长江局正在筹办的中国出版社都同新知书店合并了,党对书店的领导加强了(归凯丰同志领导),得以充分发挥新知已有的成套机构、熟练干部、带有全国性的发行网,为党更好地完成出版、发行的任务,使党可以免去另组干部、另筹资金的种种困难。总计在武汉六、七个月,我们出版了新书几十种,开设了包括香港办事处在内的十几个分店。我的组织关系不在店内,店内党的工作由应申负责,由他把同志们的政治思想情况随时告诉我,以后一直成为一种制度,以适应国民党地区的特殊环境,而我们互相配合,融洽无间,从来不曾偾事。这多半由于他的高度原则性和作风正派造成的。
八月,武汉紧张了,我们共同商定,总店迁到桂林,应申前去筹备,将来由他坐镇;派钱歧同志押运纸张书籍随同新华日报先去重庆,钱同志在中途遇炸殉难,又追派徐律前去筹设重庆分店,我将有较多时间在重庆,以便接受南方局的领导,办理中国出版社的业务。九月底我们撤离武汉,十月间我绕道到桂林时,应申已经把一切都妥善地布置好了,还开设了门市部,并且已经开始出书了;足见他的工作效率之高!
应申在桂林待了两年多,充分利用当地较好的条件,在姜君辰、邵荃麟等同志帮助下,几乎每月都有新书出版,这为当地进步文化界生色不少。也用按月预支稿费的办法约一些同志写稿,到后来因为种种原因,稿子落空,书店固然受到损失,但应申注意照顾大局,每每不加计较,帮助了一些同志解决实际困难。一九三九年书店开始受到摧残,金华、丽水、衡阳、湘西等地分店先后被封闭,货物被没收,经理被逮捕;因封店撤来的干部要安顿,被捕的同志要营救,应申紧紧地依靠八路军驻桂林通讯处党的领导,妥善地加以处理。党还先后给我们输送一些撤退到桂林的党员来新知工作,应申善于做政治思想工作,常说:“一个革命者,在任何困难面前,没有消极悲观的理由。”因而越困难,越能把同志们团结在一起,做好工作,并在工作中,不断审慎地发展党员,使支部真正起了巩固的堡垒作用。尽管环境险恶,生活艰难,但全店士气旺盛,精神面貌很好;我从重庆到桂林时,可以一目了然地感觉到。店里每月要开一二次时事会,有时还请夏衍、长江等同志来做报告。每周有读书会,一个时间学习《联共党史》,还逐章书面测验,应申同大家一起受测验,做答题,所以大家学习情绪很高。书店虽是做生意的,但又是革命的学校。这个小小的队伍,党员大体占一半以上,非党员也多半是有理想的革命青年;所以队伍虽小,战斗力颇强,一个人顶几个用;而他们的头头就是应申。
一九四○年冬天,我到桂林,各自根据党的指示,共同预筹应变之策,并且成夜地打包,转移存书。这时,分店只剩下桂林、重庆、昆明、贵阳四处了。一九四一年一月七日皖南事变爆发,广西当局也放下面纱,真相渐露了。昆明、贵阳先遭到封闭,桂林迫在眉睫。当时知道,应申已被列入黑名单,随时有被捕可能,我们商定:他尽速离桂,打前站去上海,准备必要时转移到苏北敌后,我留下料理后事。当月,应申撇下他的爱人和才一岁的孩子走了,是循着一条最辛苦但最省钱的路线走的,他对化公家的钱,一文如命。四月间我到上海时,他已经支起了泰风公司,作为和大后方及香港联系的公开机构;同时出《苏联文学丛书》,短短几个月,就出版了五六种二百余万字,梅益译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就是丛书之一,这些书,在当时租界的特殊环境里还是可以出版的。当我们共同商量用什么书店名义出版时,最后定为“远方”书店;我们身在“孤岛”,而瞻望着远方——圣地延安。
我住在新知书店办事处,这里一向是秘密的,主要印刷中国出版社的书,甚至《中国共产党党章》,也前前后后成万本印刷,秘密地出卖。当时,汤季宏同志负责秘密地给苏中、苏北、胶东根据地供应书报,采办和偷运敌人禁运物资。我不让应申他们到我们这里来,也禁止季宏等到应申那里去,以免牵累他们。但这些同志迫于工作需要,有时去利用泰风公司,应申也乐于帮助他们。由于单方面交通,应申常常有急事找不到我。我这种决定对应申而言是不恰当的,但他从未抱怨过,至今想来,我还感到惭愧和不安。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进占租界后,我们不能再干出版工作了。经商定,撤销公开机构,应申先去苏北根据地,我留下,组织存书秘密转运去苏北根据地的工作;国民党地区的店,交沈静芷负责。次年二月,他同恰巧从苏北来上海采购物资的王益先走了。从此,他离开了新知书店。
次年夏天,我辗转飘海到了苏北新四军军部;那时应申在中共盐阜区党委宣传部任出版科科长,兼盐阜报编辑部主任,尽管出版工作的物质条件确实困难,但政治条件大好,更加能够发挥他的长处,他的精力饱满,神态奕奕。我根据组织决定,一九四三年也到了苏皖边区,在华中局工作,从此改行做财经工作了。而应申呢,以后创办了华中新华书店,领导了山东新华书店、北京人民出版社,直到一九五四年出版总署结束为止,他一直从事党的出版工作。他从一九三五年创办新知书店起,前后二十年之久,全心全意地为了党的出版事业,贡献了他的智慧、忠诚和生命。
俗话说,隔行如隔山,但我们不然。无论抗日战争胜利后在苏皖边区政府的淮阴,还是解放战争中在山东益都,我们都谋求见面的机会。全国解放后,他在北京,我在上海,每次来京出差,公毕,一定到东总布胡同同他畅叙别情,那怕半小时也行,我总渴望见到他那纯朴的才不外露而给人以潜移默化的力量的形象。一九五二年秋,我也调到北京工作,还是常去看他;“安得促席,说彼平生”。一种内在的力,吸引我去看他。
然而一九七八年再见后,他不久即陷入肺癌这不治之症。他象一个共产党员那样同痼疾勇敢地斗争,并留下了深深启发我的遗嘱(诗):
效法杨老(杨东莼),
改革丧事套套。
什么向遗体告别一一
千万别搞。
死了赶紧烧掉,
骨灰不留、作肥料。
也不要去八宝山追悼,
本单位开个小型座谈,
工作检讨,生活检讨,
缺点错误也不饶,
不是光说好。
四月十四日我出差去成都,行前告别,他神志清醒,精神尚好,我以为回京一定可以再见。五月三日返京,谁知他早一天去世了。如果有上帝的话,我真愿向上帝祈求,让应申能活到七月一日,听一听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听一听胡耀邦同志在党的六十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应申就有福了。在二年多的痼疾煎熬中,他为了党和祖国的前途,一直十分苦恼地反复地驱使已经不太听话的脑神经思索问题。现在,历史的功过和经验教训已经分明,航道更加准确地拨正,十亿人民正在光明大道上稳步前进。应申,你安息吧!
一九八一年七月九日深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