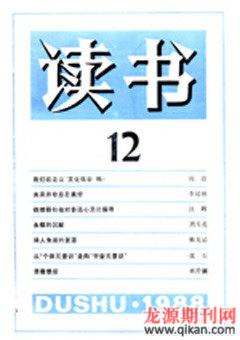曹禺的苦闷
令 华
在《曹禺传》的全书之首,作者提到曹禹曾对他说:你要写我的传,应该把我的心情苦闷写出来。读完这本传记掩卷以后,确实感到:曹禺似乎生来就是一颗苦闷的种子。苦闷(不是愤怒,不是忧伤),好象是曹禺进行艺术创造的一种个人情感特征。身世的苦闷,家庭的苦闷,社会的苦闷,交织在一起,在曹禺胸中郁结,躁动,遇有罅隙,便会奔泻而出。不论是郁热闷燥的雷雨天气,还是阴沉黑暗的日出之前,那使人透不过气来的官宦世家,那黑压压阴沉沉的原野平林,无一不是曹禺苦闷的真实体验,也是旧中国苦闷的确切象征。是否可以这样认为:没有苦闷,就孕育不了《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家》等脍炙人口的巨著;没有苦闷,也创造不出繁漪、陈白露、仇虎、愫方、瑞珏等光彩夺目的人物。苦闷出作家。而作家曹禺代表着中国现代话剧的里程碑。
而今,曹禺已是接近耄耋的老人了。他的名望,他的待遇,他拥有的鲜花和荣誉,似乎应该使他满足了。但曹禺心中仍然埋藏着深深的苦闷。这种苦闷比起青年时代的苦闷是属于另一种性质的,但也许更为深沉,更惹人烦恼。因为当年的苦闷,还可以通过自己的创作得到宣泄,而如今的苦闷却使得他无可奈何,难以名状。书中介绍了这样一件事:一九八三年春,美国戏剧家阿瑟·米勒到曹禹家做客,曹禺突然向客人读了黄永玉给自己的一封信:“……我不喜欢你解放后的戏,一个也不喜欢。你心不在戏里,你失去伟大的灵通宝玉,你为势位所误!从一个海洋萎缩为一条小溪流,你泥溷在不情愿的艺术创作中,像晚上喝了浓茶清醒于混沌之中。命题不巩固,不缜密,演绎、分析得也不透彻。过去数不尽的精妙的休止符、节拍、冷热、快慢的安排,那一箩一筐的隽语都消失了。……”这封信措辞如此严厉,但曹禹特意将它裱好珍藏起来,并且恭恭敬敬地念给朋友们(包括外国友人)听,这正是曹禺的真诚处,同时也透露了他内心难言的苦闷。书中还提到曹禺向作者谈到这封信时,举了王佐断臂的故事,感慨地说:“明白了,人也残废了,大好的光阴也浪费了。让人明白是很难很难的啊!明白了,你却残废了,这也是悲剧,很不是滋味的悲剧。我们付出的代价是太多太大了。”读到这一节,我想没有人能不为之动容。
解放以后,曹禺始终怀着强烈的创作欲望。他是一位严肃的作家,写不出来是不肯硬写的。我们知道,这三十多年他只写了三个剧本。虽然也获得一片赞扬,但毋庸讳言,过去那种令人迷醉的魅力消减了不少。一些著名的老作家似乎也有类似的情况,他们原有的、独具的、迷人的创作个性哪里去了?他们手中的五彩神笔是怎样失落的呢?除了频繁的社会活动,占用了太多的时间以外,还有更深层的原因。在这方面,曹禺的经历是有代表性的。解放初期,他曾以极大的勇敢,真诚地否定了自己过去的剧作,主动将《雷雨》、《日出》、《北京人》作了修改。实践证明这些修改是失败的,它暴露了曹禺在同旧的一切决裂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最可贵的艺术上的自信心。其后,他写了试图表现新社会的戏——《明朗的天》,大体上是走“主题先行”的路子,他后来自己承认:“是硬着头皮写的,现在看来,是相当被动的”,虽然当初他确是发自内心的真诚。以后,他又写了两部历史剧,在这个领域里,他的艺术才华又得展现,但思想上仍有无形的束缚。正如周恩来谈到《胆剑篇》时所说:“是新的迷信造成的。”《王昭君》则是为了完成周恩来总理的嘱托,曹禺也竭尽心力来进行创作。但他思考的重点,似乎是放在领会周恩来的意图上,努力塑造出一个崭新的、促进民族团结的王昭君形象。这个过于理想化的人物,总使人感到缺少了某些历史的真实感,而且那游离于人物之外的政治味道也未免太浓了一些,这些都不能不损害作品的艺术美。
我们还是回到黄永玉的信。曹禺对此是清醒的,正因为清醒又无可奈何,所以才分外苦闷。他说:“解放后,总是搞运动,从批判《武训传》起,运动没有中断过。虽然,我没有当上右派,但也是把我的心弄得都不敢跳动了。”“多年来,我写戏都是领导上交给我的任务”,但即使是为自己十分敬重的领导人,欣然命笔,倘若不是基于自己强烈的生活感受,不是受自己情感激流不可遏制的驱动,也不可能写出震撼人心的作品。“明白了,人也残废了,大好的光阴也浪费了。”这位才华横溢的老作家的肺腑之言,难道不值得我们三思吗?
《曹禺传》的作者充分利用了与传主多次长谈的第一手资料,不仅比较准确地写出了传主的历史风貌,性格特征,艺术成就,同时也揭示出他晚年的心境,他的追求与苦闷,这也可说是本书的一个特色吧!
(《曹禺传》,田本相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一九八八年八月第一版,5.3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