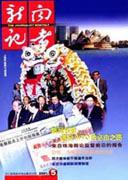我敲门我追赶
罗 鸣
一、危机还是良机:对意义的两种认识
中国面对“入世”,机遇和风险并存。新闻理论界和媒体对“入世”的经济意义评说比较多,从经济角度对其积极意义有较高的认同度;面对“入世”的政治意义则少有提及,从政治角度对其负面影响的耽心则更多一些。有一种观点认为如果说“入世”在经济层面是机遇大于挑战的话,那么在政治层面,则似乎是挑战大于机遇。报业从它的社会属性来讲属于政治领域,加入世贸组织对于中国报业意味着什么呢?我不赞同上述把经济层面和政治层面的意义分别看待的观点。我认为“入世”对于中国报业的发展同样是一个很好的机遇,是一个良机而不是危机。
回顾改革开放20年的历史,有两个特点值得重视:一是“危机推动型”。就是事物的内在矛盾还没有发展到旧的体制框架容纳不下的程度,有关方面不会主动进行下一轮的改革。二是“开放推动型”。就是对热力学第二定律的一个诠释。在一个封闭的系统中,熵只会越来越大,最后趋向“死寂”。要保持一个系统的有序和生命,就只能通过开放来增加“负熵”。人们通常说80年代是以改革为先导,以改革促开放,90年代则是以开放为先导,以开放促改革。实际上,80年代的改革同样离不开开放的推动作用,试想如果不是首先打开了深圳特区等“窗口”,我们是不可能找到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城市改革路子的。
进入新世纪,还有一个特点凸现出来,这就是“科技推动型”。国际上知识经济和“新经济”的出现和崛起,“撬动了整个地球”,对中国的改革和发展也必然起到极大的催化作用。
归纳这三个特点,审视新闻界的现状,我认为中国报业正在面临和跨越一个历史门坎。
目前对报纸,特别是各级党报,一个普遍的现象是,领导不太满意,批评和黄牌警告时有发生;群众也不太满意,认为报纸宣传和受众的要求还有一个较大的差距。领导不满意往往是用“头”来投票,就是对报纸领导班子的“帽子”进行变动;群众不满意则往往是用“脚”来投票,就是对那些办得不好的报纸敬而远之或者是畏而远之,总之是不买你的报纸。这种矛盾经过多年的演化,看来在旧的体制框架中已走到尽头。也就是说,出路在于深刻的制度变革。而20世纪末新科技、新经济的异军突起更是加剧了这个体制矛盾。互联网这个“第四媒体”的迅猛发展使传统的“高筑墙”管理传媒方式日益显得苍白无力。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世界传媒一体化恐怕已是一个难以回避的潮流。
就是在这样一种形势下,中国敲响了“入世”之门。“入世”从本质上说是一个开放的行为,而且是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最大的开放,因此它对中国各个领域改革的影响和推动作用是极为深刻和难以估量的。
我之所以认为“入世”对中国报业来说是发展的一个良机而不是噩运,就是因为它符合上述的三个推动改革的力学分析。“入世”要求它的成员国遵守在最惠国待遇、国民待遇和服务等方面的共同章程,国外媒体或早或迟会把它的须角伸到中国来,这迫使中国的媒体“壮士断腕”,寻求在新的制度框架下的生存和运作方式。没有这种推动,传统的体制壁垒恐怕更加难以打破,新闻改革恐怕要在口号和文件上兜更多年的圈子。因此,“入世”对中国报业发展的积极意义,绝不亚于对其他经济领域的意义。
二、追赶还是拒绝:对路径的两种选择
加入世贸组织是中国从市场经济的初级阶段向高级阶段的一次历史跨越。这个跨越是采取“软接轨”还是“硬接轨”;是平滑过渡(如像过去20年改革的成功路径那样)还是急剧转折,对社会的稳定和发展会带来截然不同的后果。如果没有做好必要和充分的准备,“入世”将对报业带来很大的冲击和震荡。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产品能否真正变成商品,实现它的价值,要在市场上进行“惊险的一跃”。“入世”对中国报业来说也意味着要进行“惊险的一跃”。我们的报纸,特别是党报能不能跃得过去,能不能成为现代意义上的大众传媒,可以说是风险和机遇共存,新闻世界的决策层和操作层都要作出艰苦的努力。
我认为目前报界对“入世”有三种值得注意的心态。
一是“鸵鸟型”。把头埋在传统体制的“沙堆”里,拒绝发展。盲目“乐观”地认为只要我们坚决关上大门,国外报纸就永远不可能登陆中国市场。还有一种观点沿袭十九世纪末洋务派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一厢情愿地希望“入世”就是引进外资,只要国外的资金、技术,而拒绝国外的媒体进来。这种心态可以称之为“一闭(眼)方休”。
二是“高枕型”。把头靠在得过且过的枕头上,认为“入世”尚未成为事实,入世后对报业还有保护期,总之是离狼真的来了还早得很,何必着急?这种心态可以称之为“一睡方休”。
三是“待兔型”。把头沉在守株待兔的梦幻里。认为一“入世”,天上就会掉馅饼,“船到桥头自然直”。这种心态可以称之为“一醉方休”。
很明显,这三种心态都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因而是有害的。
首先,WTO要求所有成员国最终遵守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因此,无限期地把外国媒体拒之门外是不可能的。其次,虽然服务贸易总协定允许少数成员国在2005年前,可以存在与最惠国待遇不符的暂时性措施,但在2005年以后,新闻业开放的承诺表,终归要制定出来。第三,从现在起到2005年这几年的过渡期是长还是短?如比起目前国内媒体与国际强势媒体的差距来,我认为这个时间是太短了,太紧迫了,从机制到运作,从借鉴到创新,我们实在有太多的事情要做。就是一天都不睡觉,我们也可能来不及追赶上国际强势媒体的发展,来不及填补与中外报业的巨大落差。怎么还有心情闭上眼睛高枕无忧呢?如果不抓紧时机快马加鞭地追赶,到时候“惊险的一跃”就可能成为“致命的一跳”,从天上摔下来的不是馅饼,而是我们自己。
四川省委书记周永康提出四川在“十五”期间要实现追赶型、跨越式发展。我认为“追赶型、跨越式”这六个字不仅适合四川和西部的经济发展,也适合于四川日报报业集团,适合于中国报业。
跨越,是质的飞跃,是目标;追赶,是量的积累,是路径。跨越不能一蹴而就,只能通过扎扎实实地工作,一步步地追赶上去。我们应该眼睛盯着2005年这个时限,倒计时地安排工作,把我们自身的实力提升到与世界接轨的平台上。只有这样,中国报业才会在转型期以主动的姿态实现平滑过渡,立于不败之地。
三、“开环”还是“闭环”:对引导的两种调节
“政治家办报”,“用正确的舆论引导人”,是党中央提出的办报方针。事实上,不管提法是否一样,这两个原则在任何国家都是真理。在资本主义国家,办报的同样是政治家而不是商人,他们同样要引导舆论,甚至控制舆论。尽管在表面上他们办报实行的是登记制而不是批准制;他们标榜新闻的“纯客观性”,“无党派性”。对这个问题我们应有清醒的认识。加入WTO,我们报纸的党性原则不能丢,舆论引导的功能不能丢。问题的关键在于政治家办报应该怎么办,舆论引导应该怎样引。有一种片面的认识,好像政治家办报就是一个“卡”字。这件事不要报道,那件事不能报道,报纸成了“不报”纸,把宣传的阵地拱手让人,使群众对媒体产生不信任,从而使报纸发行量萎缩。这种片面的做法对报纸从有形资产到无形资产的损害是难以估算的。
从控制论的角度讲,对舆论有两种不同的引导方式,一种是开环调节的方式,另一种是闭环调节的方式。所谓“开环”,就是系统没有自我调节的能力,只能一级一级照抄照转,不能根据实际情况作任何修正。计划经济就是一个典型的开环调节系统。这种系统的好处是听话。但只能适用于简单系统,一遇复杂情况,开环调节系统的缺陷就是致命的。首先一个缺陷就是言与行之间,动机与效果之间有误差,而且越到基层误差越大。就算是采用通稿,不同的报纸在标题的制作、版面的安排、字号的采用上也不可能做到完全一致。事实上,不同的媒体有不同的受众,同样一篇新闻稿对不同的读者起到的效果是不一样的。因此,应该鼓励媒体根据自己的读者需求体现自己的特色,不到迫不得已,对通稿的采用应采取谨慎态度。第二个缺陷就是媒体对新闻反应迟钝,缺乏主动精神。老百姓关心的问题报纸上往往不说或少说,表现出一种对群众疾苦的冷漠和麻痹。由于缺乏及时有效的反馈功能,开环系统对干扰信息的调控能力是很差的。这种调节机制运用到媒体管理上,对舆论的引导作用也是低效的。
从控制论的观点看,较为高级的调节方式是闭环控制系统。我理解所谓“入世”,就是加入世界经济一体化这样一个极为复杂的巨系统,这个系统的每一个层次,每一个部分都有很强的反馈和调节功能。媒体就是一种重要的快速的反馈通道。因此,如果我们企图以开环的方式去实现全球巨系统的闭环反馈功能,这显然是南辕北辙。
目前媒体亟需实现从“开环”到“闭环”的变化,增强对读者的亲和力,提升对舆论的引导实效。在这方面有许多课题值得研究。比如党报如何更好地起到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桥梁纽带作用的问题。在今天,老百姓了解党政领导主要是通过媒体而不是直接面对面的交流。因此,媒体这个“形象塑造师”的作用就十分重要。官员在媒体上的形象是什么样,群众就认为我们的党和政府的形象是什么样。如果我们从“耳目”上听不到真情,“喉舌”讲的话又是空话、套话、官话,那么我们的媒体就是在帮倒忙而不是帮真忙。这是新闻界的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的表现。比如会议新闻很容易搞成千篇一律的老一套,重视的是议程、名单和座次,传播的是正确然而无用的空话。我们有些媒体天天在塑造庸官昏官的形象,但是我们的一些领导却感觉良好。媒体和官员在一种封闭的体制下互相熏陶,媒体塑造领导的昏庸,领导还在表扬媒体做得好,这是一件很可悲的事情。如果把对新闻宣传的审美观比作美容的话,那么我们一些官员只有“村姑”的水平。他们不管报道的内容是否有新闻性,群众是否爱看,只要求文章写得长,标题做得大,版面要显著。这就像会打扮的女士不显山露水,不会打扮的村姑,追求“红眉毛绿眼睛”的强烈效果。但是我们现在的开环体制没有负反馈功能。“懒汉”的媒体糊弄领导,糊涂的领导表扬“懒汉”。媒体、领导封闭在一起,互相影响。“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入世”后,国际上的强势媒体一旦进来,面对面,硬碰硬地竞争,我们就会感到自己的美容技术不行,党和政府的形象塑造得不好,这是我们的党报功能发挥得不好。我认为,当前我们的报纸要在说真话、听真情、帮真忙上下功夫。媒体要勇于承担起培养、提升官员的新闻审美观的政治和社会责任,让官员知道什么样的报道才是他的亲民形象,怎么报道才是帮真忙的有效宣传。在舆论引导上还有一个重要问题是对热点新闻的处理。现在有一普遍的现象是,一谈“导向”,热点、敏感的新闻就没有了。采取一种闭眼不看的态度。在互联网已高度发展的今天,这种做法日益显现其愚蠢。如果根本不报道群众关注的热点和敏感问题,就等同把阵地拱手让人,还怎么来引导?
我认为媒体特别是党报应正面承担起热点报道的政治责任,要在新闻分析和评论上下功夫,逐渐增强群众对敏感新闻的承受力,同时也锻炼新闻从业人员对报道热点和敏感新闻的应变能力。
四、大众还是小众:对发行的两种追求
党报应该办成大众传媒还是小众传媒,这似乎是一个毋庸置疑的问题。但从历年各级党报发行的趋势看,前景堪忧。现在国外媒体的“狼”还没有来,党报的发行就在国内报纸的激烈竞争中难以稳定。事实上,不少地方党报发行任务的完成主要依赖各级财政的经费和农村的提留款。“官办、官订、官看”的格局已经形成,在报刊的零售市场上基本看不到党报,党报在无形中变成了“内部刊物”,机关报成了只有在机关里才能找到的文件一类。今年农村税费改革和县以下机构改革,将对公费订报这块“蛋糕”带来巨大的冲击。
有一种观点认为,党报就是办给领导干部看的,因此它不是商品,无需进入报刊市场。对这种观点我不能苟同。试问一个执政党的机关报老百姓就是不买不订不看,这和中国古代的“邸报”有什么两样?群众对党报的关注程度实际上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执政党的群众基础的牢固程度。因此它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是一个政治问题。
五、数量还是质量:对规模的两种扩张
成立报业集团是迎接“入世”的一个重大举措。现在全国已批准成立了16家报业集团。但是集团的成立是一种形式的变化还是一种实质的变化,还有待观察。应该说报业集团的出现是适应行政管理规律、产业发展规律和新闻规律的结果。但是在全国报业一窝蜂争上集团的浪潮中,确有重名不重实的“翻牌”现象存在。有的领导仅仅从行政管理上考虑问题,认为把若干报纸归到一个“集团”中,宣传上的“招呼”打起来更方便,经济上出现亏损也有人管,各行业报纸的利益冲突政府也可不负责任。这种思路恰好忽视了集团产生、发展的内在动力和内在规律,使某些报业集团成为新瓶装老酒的翻牌公司。
六、官道还是商道:对资本的两种运作
资本运作是报业发展的经济动力之一。目前报界普遍感到新闻人才好找,经营人才难求。似乎只要把资本运作搞起来,报社就有现代企业的味道,就和WTO接轨了。实际上我们忽略了一个问题,这就是我们的资本运作是在什么背景下进行的。我们处在市场经济的初级阶段,许多所谓的资本运作并非真正的市场行为,而是依托官方的背景来进行的,走的是官道而非商道,有特殊的优惠政策。因此,目前报业真正缺乏的还不是一般的经营人才,而是熟悉国际资本运作的“游戏规则”,靠规范的市场行为进行资本运作的经营人才。这支经营人才队伍能否建立,是关系到“入世”后,我们的报业能否在与国际媒体的竞争中站稳脚根的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