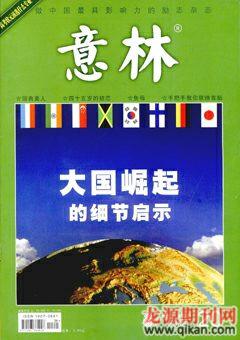吃喝的自白书
朱大可
关于吃喝,我又能说些什么呢?在童年时代,这个问题曾经如此深切地困扰着我发育不全的心智。在迎接大跃进的时代里,我不合时宜地降生了。1957年一个冬日的正午,越过阳光,我躺在徐家汇附近的一所医院里,因饥饿而哇哇大哭。不知所措的母亲把乳头对准了我的小嘴,而我却吸吮不到任何乳汁。在生命的黎明,我面对的第一个困境就是食物的匮缺。这似乎是一个生命的谶言。
我7岁前的食谱是被大饥荒年代所限定的。我们全家骨瘦如柴,状如幽灵,靠面疙瘩汤度日。那种食物是令人作呕的,散发着菜叶被过度烹煮后的恶心气味,尽管加入大量味精可以增加食欲,却引发了味精中毒。每天吃完面疙瘩后,我都要大口喝水,像一头在旱地里打滚的小狗。在味蕾迅速萎缩的年代,味精是维系我们与食物之间的危险纽带。
在炎热的夏天,我和隔壁邻居的小孩——一对姐弟在家门口共进午餐。我坐在小板凳上,从小碗里扒着难以下咽的面团和菜叶,眼里噙着失望的眼泪。惟一支撑我进食的信念是坐在对面的女孩,她的秀丽容颜就是佐餐的美味佳肴,也是我熬过大饥荒年代的最高慰藉。我们芦柴棒似的小手,紧密地缠在了一起。
父亲远在浦东工作,只能每周回家一次。星期六的黄昏是个美妙的节日。我趴在窗口上,远眺着父亲的身影,然后飞也似地滚下楼去迎接他的手提包。每次父亲都会取出搪瓷杯,里面是期待已久的四个锅贴,有时则是两个热气腾腾的豆干菜包。童年的美食节就此降临在我的生命里,向我打开世界美妙的大门。我小心翼翼地咬开锅贴的表皮,用舌尖轻舔着香气四溢的肉馅,周身的毛孔都舒张开了。这真是一个令人心醉的时刻,我的感官瘫痪在了粗粝的食物面前。食物成了我和父亲之间伟大友谊的纽带。
不久父亲因慢性肝炎而病休在家。为了治疗,他开始了凶猛的进补。而我则在一边助吃。他的冰糖炖蹄膀,成了我最喜爱的点心。有一次,母亲不知从哪里搞来一只燕窝,为剔除混杂在胶状物里的羽毛,我和父亲分别用拔毛钳清理了整整两天,我至今都还记得它半透明的果冻似的形态。还有一次,母亲搞来了一副不知什么动物的睾丸,烧熟后呈现为酱红色,父亲把它切成薄片,坐在餐桌前慢慢嚼着,表情似乎有些尴尬,而我在一边观看,发出大惊小怪的声音。这是短暂而富足的时光,但它仅仅延续了三年,就被1966年的“文革”烈焰所焚毁。
由于政府禁止农民私自养鸡和贩卖,吃鸡成了一种罕见的奢侈。有一次,父亲的农学院朋友从单位里搞来一只巴基斯坦种的公鸡,我们全家沉浸于节日式的欢愉之中。父亲亲自动手杀鸡和烹饪“客家葱油鸡”。他把鸡切成小块,烧熟后再改为慢火炖煮,用葱油不断浇淋,让葱香透入鸡肉的深处。我从未品尝过如此鲜美的菜肴,连续好多天都在回味它的奇妙滋味。从此我坚持认为鸡是世界上最高贵的食物。在整个“文革”期间,这是我家惟一的盛宴。
食物是偷情者点燃对方的火柴。我曾经从家里偷了半斤大白兔奶糖给一个心爱的女孩,并且骗我妈说是老鼠吃的。这个拙劣的谎言被母亲当场识破,我为此还挨了一顿打。但我还是感到了生命中最脆弱的甜蜜。女孩回赠给我的,是一副用旧毛线编织的无指手套,上面有一些深蓝和杏黄色相间的波纹,散发出若有若无的香气。我戴着它度过了那些寒冷的冬天。几年后,我把其中的一只丢在了公共汽车上,而另一只则被我收藏起来,像藏起一个爱的秘密标记。但后来,在一个突如其来的深秋,它从我的抽屉里神秘消失了,仿佛被风吹走了似的。
父亲去世后,母亲与我相依为命。我们形影相吊地行走在“文革”晚期的黑夜里。她提前退休,而我则在一家照相机厂里当了钳工。我们生活小康,无所欲求。母亲有时会带我去附近的乔家栅点心店,吃两毛五分钱一碗的鲜肉馄饨——半透明的面皮下面,暗褐色的猪肉馅隐约可见,面汤里漂浮着葱粒、紫菜和蛋皮。店堂里空空如也,没有什么顾客在这种高档食店里流连。而我们却在那里悠闲地小坐,望着大玻璃窗外的襄阳路风景,心情庄严得像个贵族。
“文革”结束后,国家食谱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在那个美妙的时刻,好像所有的顾客都感到了某种叫做希望的事物,他们的眼神里露出了暧昧的笑意。
(钧天选自《记忆的红皮书》花城出版社 图/李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