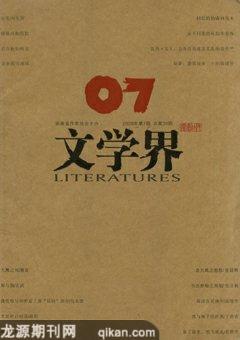阅读在灵魂中
高维生
山脉上的精神家园
(约翰·缪尔1838—1914)
1869年6月,约翰·缪尔像快乐的鸟儿,把笔记本缚在腰间,和一条名叫圣伯纳的狗,随着牧羊主和2500头瘦弱的羊群,在母亲呼叫自己的小羊声中,走进了内华达山区。他并不是以作家的身份,戴着“浮光掠影”的眼睛旅游,滋润在城市中变得不安的心。他的行走,是寻找家园的过程,让大自然清爽的风,吹开浮躁的灰尘。
童年是约翰·缪尔最幸福、最自由的时候,大自然给了他不尽的欢乐。苏格兰北海岸的乡村,充满了野性,蕴藏丰富的情感,像父亲似的教会了他勇敢。在这里,约翰·缪尔和它做着童年的游戏,它向约翰·缪尔讲授道理,磨练他的意志。1849年,约翰·缪尔随家人迁至美国的威斯康星州波蒂奇附近的农场,这片独特的土地,给了他热烈的大自然的情感。他帮助父亲开荒种地,做农活,打井、修栅栏、耕地、播种,在收获的季节,品尝到劳动的快乐和亲近土地的拥抱。他很多的时间是在森林度过的,以纯真的心观察鸟儿和林间的小动物。约翰·缪尔的传记作家,林尼·马什·沃尔夫写道:“对于这个未来的自然主义者,在整个世界上,他再也找不到像方丹湖、沼泽草原,以及环抱着它们的丛林这样丰富的宝库作为训练和培养自己的课堂了。”人生如果是一座建筑,童年的地基打得是否牢固,影响一生。即使将来在漫长的岁月中,再苦的风雨只能让其褪色,也不能倒塌,变作一堆废墟。约翰·缪尔的人生是在乡野打下的基础,露水调拌的泥灰,砌出来的墙基漫着草的气味,永远散发不尽。
童年的晨光,照耀一个人的成长,决定未来的走向。大自然在约翰·缪尔的内心形成了一股山脉,山的高峰是精神的家园。在以后的日子里唱着童年的歌,迈着长大的步子,开始了一次次寻找。《夏日漫步山间》是约翰·缪尔的旅行日记,记录了在内华达山区四个月的经历。约翰·缪尔记有60本日记,他的日记不是在书房中写的,而是听泉水的流淌声,目送鸟儿飞过,感受风的拂动写下的。空旷的山野,清新的空气,约翰·缪尔坐在草地或岩石上,野草簇拥着双脚和他交流。约翰·缪尔的文字像素描一样,简洁流畅,没赘言和苍白的夸张,不敢玩弄虚假,只是忠实地录下情景。约翰·缪尔面对山的教堂,想推开大门,感受里面的情景,让阳光投进去,他真情地说:“在劈开的岩石之中,矗立着一个自然的教堂,其外观承袭了古风,约两千英尺高,上面点缀着高贵的尖顶和尖阁,像鲜活的丛林圣殿似地在耀眼的阳光下闪烁,而人们形象地称它为‘教堂峰。”朝圣者缪尔的心灵和身体是在自然的合唱中,接受了神圣的抚爱。约翰·缪尔是大自然的教徒,在山的教堂中滋生出崇高的情感。阳光的光影,像一把刻刀,在生命的石头刻下的每一个文字,都是独立的灵魂,它和自然是不可分离的。约翰·缪尔一点点地靠近“教堂峰”,他想看清黑夜和白天的交替,四季的变化,在“教堂峰”上留下的装饰花朵和文字,读出它们的不朽。
约翰·缪尔的文字节俭,却充满了情感,没板着严肃的面孔说教,深深地读进去,就会有一番惊奇被吸引住。那些文字经过作家的抚摸,渗出的汁液,润泽阅读者的心灵。“在约塞米蒂南圆顶峰上,宛如一只苍蝇的我凝望、绘画、沐浴阳光,不时陷入默默地赞叹。我并不奢望通晓众多奥秘,只是怀着扣响希望之门的渴望和不安,谦虚地拜倒在神力的壮景前,希望献出一生,不懈地努力学习这神圣手稿中的任何奥秘。”约翰·缪尔把自己比作苍蝇,人在大山的面前太微弱了。他经受了大自然的洗礼,身体的每一个细胞,祛除了浮躁之气。约翰·缪尔把宁静叠成小船,放到山间的河流中,帆上挂满了野花野草,露珠串成的花环戴在船头上,在山风的吹动下,伴着水声向远方驶去。
这不是一般的旅程,是一次精神的朝圣。《夏日走过山间》是约翰·缪尔用文字写的内华达山,不是对自然的摹仿,而是原生地写在纸上。掀开书页,山野的风携着粗犷的狂热铺天盖地地吹来,河流一路歌声地奔走,留下一片丰沛的土地。约翰·缪尔被人们称为“山之王国的约翰”,经他倡导建成“优胜美地国家自然保护公园”,开创了自然保护区的建设,后人誉他为“国家公园之父”。
1999年,我买过三联书店版的《夏日走过山间》,扉页上有一幅黑白照片,约翰·缪尔右手托腮,在看书,我很想看清他眼神的表露,但照片的质量不好。1999年的阅读有些匆忙,并没读透这本书,放在书架上再也没读过,时过境迁,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环境污染”“沙尘暴”“耕地消失”的新闻,每天在电视、报刊中出现,在生态破环的今天,我们意识到自然的意义。“教堂峰”的钟声悠扬和庄重,回荡在我们的心中。这钟声不是金属撞击的清脆声,它是大自然千百年修练的声音。钟声浑厚,疗治现代人的疾病。2007年,春节的前几天,我买了新版的书,重读约翰·缪尔感受大不一样。约翰·缪尔的文字像掩天遮地的暴风雪,塞满了阅读,让情感颤动。冻僵的感觉使头脑更清醒,洁白如雪的文字干净、简洁,在时间中走过这么久,还是那么清新。文间的暖意,像跳动的毛绒绒的火,烘烤寂寞的心。我举着这团火,又一次走进约翰·缪尔的世界。
诗意的火焰在心中燃烧
(约翰·巴勒斯1837—1921)
约翰·巴勒斯在哈德逊河西岸买了一个农场,在那里建了一间“河畔小屋”,抛开尘世的烦恼,定居山野。
约翰·巴勒斯是博物学家,自然主义作家,被后人称作“鸟儿王国中的约翰”。《鸟和诗人》这本书准确地、朴素地把人文精神和大自然,这两种不可分割的精神,像两条河流汇聚一起,互相渗透,淌出了一片文字的湿地。1912年4月3日,在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鸟类馆的大厅前,75岁的约翰·巴勒斯和来自不同国家的孩子们在一起,孩子们朗读他的作品,巴勒斯告诫他们:“一只被打死并被做成标本的鸟,已经不再是一只鸟了……不要去博物馆里寻找自然。让你们的父母带你们去公园或海滩。看看麻雀在你们的头顶上飞旋,听听海鸥的叫声,跟着松鼠到它那老橡树的小巢中看看。当自然被移动了两次之后便毫无价值了。只有你能伸手摸得到的自然才是真正的自然。”巴勒斯不是在普及科普知识,走上讲坛,生剥硬套,销售自己“夹生饭”似的知识。把鸟儿包装成消费品,精心策划下诞生“大众”的偶像。巴勒斯笔下的鸟儿,充满了人情味,更多了人文关怀。他从不把鸟儿当动物看待,始终看作是人,是朋友。
四月是特殊的季节,巴勒斯从声音、色彩、触觉、视觉和气息,向读者吹来春天的风。一根野草,一只飞鸟儿,一头母牛,一株树,一棵草,一条河流,一块岩石,一座山峰,一挂瀑布,一缕炊烟,没一丝修饰,这些普通的景物,不仅泛出春天的信息,更重要的是表现了情怀。“起初,音符听上去一般都很虚弱,仿佛霜冻还没完全从这个动物的喉咙里清除干净,而且仅能听到一个声音。它是勇敢的预言家,可以说春天的第一道迅速的光辉就是通过它传送过来的。”巴勒斯的文字平静,这种平静像冰层的表面,下面却涌动着思想的水流。阳光调制的墨水,写出的字,不会随时间的流逝而褪色。大地是纸张,还没被俗气污染和侵扰,树枝笔醮着阳光墨水,写下的是真诚,没夸大的、贫血的文字。每一个字,像圆润的果实,剥开皮,露出健康的果肉,淌出浓浓的汁液。巴勒斯鲜明的个性,不是炒作、大声叫骂出来的,而是通过他富于简洁、朴实的文字和对自然的挚爱表现。巴勒斯是有责任的作家,他不可能先读一些野史、地方志、山水指南,然后,向自然撒一次“文化的娇”。卡茨基尔山区像一本厚重的大书,巴勒斯发现山野铸造的文字,蕴藏了神秘的意趣。他精心地研读,对每一段落,每一句话记下感受。“一个带着双筒望远镜的诗人,一个更为友善的梭罗,装束像农民,言谈像学者,一个熟读自然之书的人。”杨向荣在序言中写道:“从留下的照片看,巴勒斯有着犀利的目光又充满阅世很深的大家特有的那种宽容和温情气质。”巴勒斯不是把自然中的鸟儿做为写作的背景,当一面镜子折射自己的思想,他向人们昭示了人和自然是唇齿相依的,人在自然中得到连接的地气,坚实不飘摇。
这本散文集是巴勒斯精心挑选的,充满了景仰,和对诗人的解析。爱默生是美国自然主义文学的前辈,也是巴勒斯敬爱的作家,他没有一味地吹捧,作出无骨的媚态。他准确而真情地赞美爱默生,同时指出了他的不足之处。巴勒斯说:“我强烈地感觉到,他们作品中有某种高于文学的东西,高于天赋的东西。这就是真实、质朴的坦率和诚意,以及某种强烈而基本的特质。”作家走得多远,不是他的技巧玩得多么花哨,文字多么华丽,而是他的精神背景有多大。在爱默生和惠特曼的作品中,有着高贵的风格,没添加文学的“味精”,灵魂摊在阳光下。
《鹰的飞翔》是巴勒斯对另一位大诗人惠特曼的内心世界的探索和分析,他像中医号脉一样,把摸着惠特曼的精神矿脉。巴勒斯迷恋他的诗,被诗人的气质和独特的个性征服,他不无深情地写道:“在美国,我们面临的危险并不是脂肪的退化,而是钙质化。情感道德和肉体正在被蒸发掉,表面正在遭受揭壳性的破坏,血管和动脉中沉淀太多的杂质,身形显得异常消瘦和僵硬,什么都不经过溶解,一切都匆匆沉淀到精确定义好的思想和观念之中。”惠特曼的诗,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巴勒斯获得了阳光,嗅到了晨露的清爽,享受到大地的气息和灿烂的野花。惠特曼不是在文字中寻找营养,他是在大自然中吸收养份。巴勒斯对时代的浮躁,流行的文字深恶不绝,充满了忧心。
1921年远去了,时间像一个保险箱,完整地保存了巴勒斯的作品。在长长的岁月中,很多文字,像河流上漂浮的脏乱的泡沫顺水流走。巴勒斯如同一株野草,根茎和大地紧紧地相连,不会被时光抹光,留下一段空白。巴勒斯的文字经过了这么长久,不但没有霉味,却有了清草气息。
倾听自然的秘语
(约翰·布罗斯1837—1921)
一个人为了观察大自然的变化,把一座谷仓改建成书房。空气中存留干草和粮食的气息,在这里写作和思考,目光越过窗口,看动物在眼前的田野、树林和果园中跑来跑去,这是何等的快乐。他记录下的大自然是我们这个时代远离的东西,一只小心翼翼的金花鼠,警惕地注视,一只红松鼠百米冲刺,一路转着圈跑来;一只野兔出现在视野之内,胆怯而小心,一只金啄木鸟儿,落在果园的空地上,寻找喜欢的蚂蚁。书房是他读书、写作的地方,更多的是接近、亲密大自然。
约翰·布罗斯不是闹腾的作家,一夜之间窜红,变成一位文学的明星,作品一路畅销,升至排行榜的首位。在中国很少有关于他的书,他的评论,我在网上搜寻他的讯息,少得可怜。布罗斯的文字,像一粒种子,是在大自然的子宫中孕育而生,在风雨中,在阳光的爱抚下,一点点地长大。这样的文字,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是不朽的。他的自然不是凭空幻想的,为观念而写作,在书上临摹出来,加上情感的“酵母”,摇身一变,成了仿自然主义者。布罗斯深有感触,不想变为“温室”的写作者,他在写作的经验中写道:“我不能设想我的书是‘作品,因为在写它们时很少有‘作的意味。那一直都是我的活动反映。我去钓鱼,野营,划船,文学的素材就成为这些活动的收获。”布罗斯不是科学家,严格地记下鸟儿的特征,生存的情态,写成研究报告,向世人公布。布罗斯笔下的动物和自然,表现了人与动物的关系,充满了人性。
在美国进入高速的工业时代,社会发生了大的变化,人与人之间的冷漠,疯狂地追求物欲,享受金钱带来的欢乐。布罗斯离开了城市,他朝着相反的方向走去,定居乡村。他并不是保守主义者,抱着传统不撒手,而是以敏锐的眼光,感觉浮华外的东西。1872年,布罗斯在哈得逊河畔的西园买了一块地,建立了自己的农场,取名为“河边”。1885年布罗斯辞掉银行的工作,放弃优厚的物质生活,在乡间种植果树,专心写作。《布罗斯散文选》是一本综合集子,其中选了很多的日记。日记是自然主义作家喜爱的表现形式,爱默生和梭罗的日记,在美国文学中是重要的一部分。被称为“美国国家公园之父”的约翰·缪尔的《夏日漫步山间》,是他的旅行日记。爱默生写道:“要保持一部日记。对真理访问你的心灵,要作为荣誉加以重视,并记录下来。”日记对于布罗斯也很重要,这些日记,像他的素描本,表现个性和对自然的了解。布罗斯的日记,传达了生命的信息,他想了解另一种生命的状态。他并没记生活的流水账,什么时间和某人会面,喝茶聊天,接到名人的电话和签名的书,花多少钱买了一本书,炫耀小资的优越性。这些琐碎的东西没鲜活的内容,生命的品质,语言显得苍白无力。布罗斯的日记透着诗性,每一个字都是“绿色”的,它像山上的岩石一样,有着自然的个性,纹理,坚实、真情、淳朴无矫情。1866年1月27日,布罗斯写道:“自然不愿被人征服,但自愿献身于她的真正情人——那痴情于她的人——在她的在海里沐浴,在她的河流上航行,在她的森林里野营,只要没有什么唯利是图的目的,她接纳他们所有的人。”布罗斯的叙说,没大段大段的说教,他对自然的感受不是肤浅的直白,停留事物的表面上,而是极为清新和亲切。日记像一片土地,文字像刚冒出芽的小苗,嫩绿带着清香气。
人在大自然中,不会有太多的欲望,一整天呆在林中听鸟儿叫,呼吸清爽的空气,人世间的烦恼,被自然的堤坝阻挡得远远的,在宁静里和自然对话,心干净得像树上的叶子。在棚子里躲雨的布罗斯,和一些农用的东西挤在一起,一只古旧的摇篮,引起了他很多的思绪。“当外面大雨滂沱,树枝剧烈摆动时,我多么想听听它的历史和它曾经摇过的人的生平故事。在摇篮上面是一只北美翁的窝,它筑在椽子后面的柴枝上;巢的主人没有飞走,它的故事不难读到。”这一天,在人生中,不过是普通的一个日子。这一情景,没什么猎奇的经历,在乡村的棚子里,闻着尘积的气息,鸟巢和旧摇篮不是遇到的新鲜玩意,而是阅读岁月中人的故事,自然与人生。布罗斯写出如此动人的文字,他的大自然不是“创造”,是真实地观察自然界。大自然是最好的老师,它教会了布罗斯的写作方法,没有多余的铺垫,没有宏大的论说。布罗斯是安静的作家,他的文字很少有浪漫的色彩,而是真情实意,“在文字中除开真实就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了。”这是布罗斯的创作道德观,也是衡量文学的标准,文学离开了真实,就没底线了。
布罗斯的书,是给有着“精神贵族”的人读的,在他的书中,找不到所谓的“有意思”,他不属于哪个时代,而是永远的。
像山那样思考
(奥尔多·利奥波德1887—1948)
一个人为旅鸽写下的文字,像一座纪念碑,竖立心间。这不是一些奇闻趣事,书读多了,故弄玄虚,卖弄“知识”。他是对生命的敬畏之情,才写下这样的文字。他真实地感受大自然的一切,观察林中的一喜一乐,不同季节动物的生存规律,情感丰富的素质,使他成了非同凡响的科学家、大作家。
天空阴沉着脸,憋一肚气似的要发泄出来,天气预报说,这几天有沙尘暴,有的地方甚至发出了橙色预报。“浮尘” “扬沙”这些曾经陌生的专业用语,现在频繁地出现在报纸和电视上。这样的日子,读奥尔多·利奥波德的书,心情沉重,不可能轻松。砭骨的悲凉,像一股巨大的暴风雪,袭击人的灵魂。峭壁上的旅鸽纪念碑,像孤独的眼睛审视山野,它和人类居住的城市是对立的。奥尔多·利奥波德焦虑地感受和听到旅鸽纪念碑发出的深沉的、绝望的叫声。“我们立起一座纪念碑,以纪念一种鸟的葬礼。为这座纪念碑象征我们的悲伤;而我们之所以悲伤,是因为没有人可以再见到那些凯旋之鸟成群疾飞的方阵,它们辟出一条穿越三月天空的春之路径,将溃败的冬天逐出所有威斯康辛州的森林和草原。”奥尔多·利奥波德的文字中没有伤感,更多的是痛苦,碱水一样浸泡他的心,发出撕裂的疼痛。这不是电影中的表演,挥挥手,流几滴泪水,说几句伤感的话。这是消失的告别,既使今后投入大量的金钱,人们想恢复野生的鸽群,是不可能的。在山野里看不到旅鸽,寻找它们,只好到博物馆和鸟谱上查寻。这些图像僵死,没生命的温度,它们不再有翔动的喜悦。三月的天气,鸟群不会排着队列,让带有体温的翅膀划破春寒,驱逐冬天。猎人躲在大树后面,草丛中,来福枪冰冷地等待飞翔的鸽子。手指没一点罪恶感和怜悯之心,像饥饿的、贪婪的野兽,藏在角落里窥探,等候时机,一跃而出。文明的子弹高速飞行,一只只曾经搏击风雨的鸽子,飞得再高,无法逃脱追杀,瞬间被毁灭,倒在枪口下。人类为了自身的利益,强暴大自然的行为,突破了道德底线,这是沉重的教训,终究有一天遭报应。作为知识分子,奥尔多·利奥波德对着大自然,虔诚地忏悔。知识分子不是名词,更不是头衔,像一顶漂亮的帽子戴在头上,闪耀自傲的光环。这是良知,是责任,是灵魂的呼喊,一种扑不灭的精神。
奥尔多·利奥波德的生活简朴,不喜欢热闹,1935年4月,他在威斯康星河畔买了一个荒弃的农场。在这以后的13年中,奥尔多·利奥波德一家在这里度过了很多的时间,扛着铁锹走向土地,种下一株株树,树林像大鸟笼子,里面装着各种鸟类,破旧的木屋带给他们温暖、快乐的日子。奥尔多·利奥波德想恢复生态上的平衡,每年和家人一起栽种上千株树,这期间不断受大自然的挑战,干旱的侵袭,兔子的毁坏,洪水和火灾瞪着一双眼睛,在伺机偷袭。在大自然的生生死死中,他有了许多新的发现和思索。“木屋”生活,不是逃避城市的喧嚣,躲清静来了,也不是做秀,到这儿故作深沉,吸引人们的眼球。奥尔多·利奥波德完全是劳动者,脸朝土地,背向青天,在与土地打交道中产生了深厚的情感,更重要的是认识了生命与死亡。奥尔多·利奥波德开始研究环境的内在关系,人的行为,对环境的破坏,起了很大的作用。“我们要总体上去尊重它(土地),不仅要把它当成一个可供使用的东西,而且还要把它当成一个具有生命的东西。”土地是根,人离开了土地是不能存在的。风挟来泥土的气息,在木屋中除了阅读、观察和思考,他的思想形成了一条丰富的河流,流淌在土地上。对土地的敬畏,就是对生命的敬畏,他越来越感受到要改变人们的意识,和使用土地的态度——土地是有“伦理道德”的。《沙乡年鉴》的翻译者,侯文蕙在利奥波德和《沙乡年鉴》一文中写道:“利奥波德的土地伦理学是一个科学上的结论,但是,在他论述人与土地共同体的关系时,又加入了充分的想像力——尽管,这种想像力也并没有脱离科学的分析。加之,他对当今世界过分重视经济价值的倾向的严厉批判,便容易地被戴上了‘理想主义甚至‘天真的帽子。”
1948年的春天,奥尔多·利奥波德带女儿和妻子来到“木屋”,他每年都要在这个季节种树,看白头翁花一朵朵绽开,冒出嫩芽的红柳吐露心语,山雀与情人对歌,表达爱情。四月是美好的,土地从冬眠中醒来,大自然生机勃勃,奥尔多·利奥波德在农场种树,在“木屋”中写作、读书和观察。4月21日,邻居农场起了大火,利奥波德在奔赴火场的路上,心脏病突然发作,猝然死去,倒在热爱的土地上。
《沙乡年鉴》记录了奥尔多·利奥波德的科学生涯,他与土地的对话,是生命和生命的交流。这是一部美国环境保护主义理论的经典作品,与梭罗的《瓦尔登湖》同等重要的伟大著作。奥尔多·利奥波德的文字,像一株株松树,散发树脂的香气。
责任编辑:易清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