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公开博弈
韩 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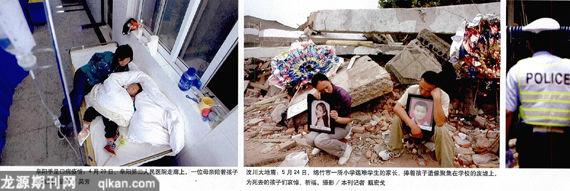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实施两个月的实践已经表明,推动信息公开的最主要的力量来自各种各样具体的诉求
黄由俭至今没有收到湖南省高级法院对自己的起诉是否立案的任何通知。到7月14日,距离寄出起诉书的时间已经有20天了。
湖南汝城县自来水厂的几位退休职工,因对企业改制中出现的问题不满,几年来一直在上访。当他们听说汝城县政府曾就改制中的问题进行过调查并“形成了一份颇为客观的调查报告”后,转而要求县政府公布这一报告。
因为选择在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简称“条例”)实施后的第一时间提起诉讼,因而此一案例被广泛视为衡量“条例”实施情况的一个标本。
虽被媒体称为“信息公开第一案”。但迄今没有任何一家法院立案,甚至不予立案的裁定也没有拿到。
此案的曲折,也预示政府信息公开的艰难。
“第一案”无路可走
各种材料都齐全?为什么法院就是不予立案?
67岁的黄由俭夜里11点多才回到家。诉讼的形势“越来越严峻”,他不得不连夜与20多位退休的同事商议对策。这是7月13日。
达成一致的意见是:联系媒体,争取支持。
从寻求司法救济到转向寻求媒体支持,这一转变的背景是:县法院到市中院、省高院,黄由俭和他的同伴“已经看不到解决问题的希望。”
比起5月1日看到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宣传横幅在县政府门前迎风招展时的兴奋心情,黄由俭说他现在“又重新回到无助中”。
事实上,在汝城县法院认定此案超出他们的管辖范围时,黄由俭还对下一步的司法救济充满希望,他给郴州中院写过两封信,表达了对立案的殷殷期盼。
郴州中院先是将此案“奇怪”地转给了检察院,继而又多次要求黄由俭补充起诉的材料。为此,黄由俭5次往返汝城与郴州之间。直到6月23日,中院一位法官告诉他,你们这个案子,影响巨大,不仅在国内有影响,在国际上也有影响,要向省高院和最高院请示后才能做出决定。
此时距离5月5日他们将起诉书快件寄往中院,已有50天。
6月24日下午,省高院一位工作人员明确告诉他们不可能受理这一案件,理由是“郴州中院没有做出一个书面的裁定”。
而根据相关规定,受理或者不予受理,法院都应在7天之内给出书面的答复。
此前的一天,黄由俭曾向郴州中院要过“书面裁定”,中院称此案事关重大,要在请示最高院后才能给出答复。
对省高院会否受理黄由俭心里没底,因为法律专业人士告诉他,如果上一级法院直接受理本属于下一级法院管辖范围内的案件,会严重侵犯法院的管辖原则和两审终审制原则。
黄由俭还是将起诉书寄到了省高院立案庭,这一行为的一个重要支撑是:高院院长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过对这个案件的关注。
此前,黄由俭很少同法院打交道,这段特殊的经历让他感慨颇多。他始终搞不明白的一个问题是:各种材料都齐全,为什么法院就是不予立案?
救济:3条道路“全不通”
他几乎遭遇了申请信息公开所有可能的拒绝:答非所问、信息不存在、不宜公开。
而北京市海淀区四季青镇居民朱福祥针对土地规划和环评所提出的一系列申请,更能全方位地考察“条例”实施的现实状况。
5月8日,朱福祥向北京市规划委申请调取四季青常青通达建设项目的环境规划意见书。规划委给了他一个规划设计的条件说明书,当他向工作人员反映这并非自己想要的东西时,对方告诉他:领导说了,就给这个答复。
在向市国土局申请公开四季青门头新村建设项目土地使用的信息时,类似的情形再次上演。“我们跟他要的是安置农民的用地有多少亩,商品房开发有多少亩,结果他拿那个征地的批准文件给我们。”朱福祥说。在四季青镇政府,当朱福祥对该镇辖区内的两栋楼的使用性质申请信息公开时,对方的答复是:“你申请的信息不存在。”
6月23日,朱福祥又去规划委,申请查询常青通达在四季青的某商务楼规划许可证。工作人员告诉他,要想调取信息,首先得知道要调取信息的文件号,否则不予提供。“我们没见过这个文件,怎么可能知道文件号?”朱福祥纳闷。
朱福祥还就北京市土地出让金的违规使用情况,提请国家审计署公开,对方给了他一个3页的答复,意思是公开可能危及社会稳定,因而不宜公开。
两个月内,朱福祥几乎遭遇了申请信息公开所有可能的拒绝:答非所问、信息不存在、不宜公开。
在四季青镇政府给出“信息不存在”的答复后,朱福祥向海淀区政府信息办提请行政复议。一位工作人员向他表示,按照“条例”,信息公开救济的渠道只有两个:一是举报,二是诉讼,没有行政复议。
朱福祥给海淀区政府信息办留下了两份申请,一份作复议,一份作举报。但至今他没收到任何一个来自海淀区政府信息办的通知。
法律专家认为,政府机关不依法履行信息公开义务的,可以看作是对申请人知情权的侵害,因而可以援引“条例”第三十三条第二款申请行政复议。
在行政复议和举报都未能提供有效救济后,朱福祥以四季青镇政府不履行公开义务为由,将其诉至海淀区法院。但立案庭法官认为,镇政府“信息不存在”的答复已算是履行了职责,因而不予受理。
在法律专业人士的建议下,朱福祥将诉讼请求进行了变更,在“履行职责”前加上了一个“实际”,再次提起诉讼。海淀区法院再次做出了不予受理的裁定,这次的理由是“所诉事项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与黄由俭一样,朱福祥已经感觉“无路可走”。
为何害怕信息公开?
县级政府并无对某一信息是否属于国家秘密进行定性的权力,
刘成现在最怕见到的一种人,就是像朱福祥、黄由俭这样将“条例”视为“尚方宝剑”对信息公开纠缠不休的人。
刘成是河南省某县信息科负责人,每天的主要工作就是将政府信息披露和公开。对他而言,“条例”实施带来的主要变化是工作量骤然增加,压力也骤然增加。以前公开的东西不多,遵循“不公开是原则,公开是例外”,现在则相反。
“一旦与法律扯上关系,就得备加小心。”刘成说。“‘条例规定了4类主动公开的信息,要细纠起来,工作量非常大。”
“条例”要求主动公开的信息,第一类是“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切身利益的”信息,第二类是“需要社会公众广泛知晓或者参与的信息”。“这样的信息差不多占了所有信息的80%以上。”刘成说。
现在,刘成上班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先浏览一下挂在信息科名下的信息公开网站,看看有没有网友的留言——在政府信息公开的所有媒介中,网站是上级要求的首选。
“每天既怕漏掉一个留言,又盼着上面
没一个留言。”刘成说。“最怕有人提出一些难缠的事。”
“幸运”的是,到目前为止,这种“难缠的事”只碰上过一桩。今年5月上旬,一位家在该县的西南政法大学的学生,在网站上留言,希望能公布手足口病在这个县的发病情况和防治情况。
“一下子就紧张起来了。”刘成如此描述自己当时的心情,“因为从来没有碰上过这样的事。”
利好的一个因素是:手足口病最为敏感的时期已过,准确地公布信息成为上上下下的一个共识,数据的收集也非常到位。
刘成向领导汇报此事,获得批准。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省以下的政府信息公开的负责人一般是市或县政府办公室主任。
然后向县卫生部门索要数据,领导最终核准将这些数据在网站上公布。
完成这些事后,刘成与这位学生取得了联系。没想到这让他忙得不可开交的留言,对方竟没太当回事,“我就是想看看‘条例好不好使。”他说。
“就怕遇上三种人:律师、记者和法律专业的学生,他们懂法,较起真来不好对付。”刘成说。
“老百姓提出信息公开的还不多。”刘成说。当地经济发展平平,多数人整天忙于生计,权利意识并不是很强,刘成对此颇为“庆幸”,“如果都来要求信息公开,压力不知道会有多大”。
但领导有时候会以涉密为由,规避一些敏感信息的公开。遇到这种情况,刘成就要先把文件拿到法制室,看能不能在法律上找到一些依据,哪怕“依据有些牵强”。
依据主要是1989年5月1日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这部法律因与普通人相距甚远,多数人不解其祥,因而常被利用,给一些攸关政府利益的信息戴上“国家秘密”的帽子,拒绝公开。
而事实上,根据保密法规定,县级政府并无对某一信息是否属于国家秘密进行定性的权力。
大家不再是观众
在原来空谈信息公开的时候?这种权利是虚的,“条例”的实施让这种权利成为实的,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公众参与研究与支持中心主任王锡锌,将“条例”公开后这两个多月看起来充满了混乱逻辑的时期,称为特殊时期。
这一时期到目前为止最为重要的特点,是公众对信息公开寄予了超乎寻常的热情,信息公开方则竭力避免信息的公开,而司法救济软弱无力。“公众的热与政府部门的冷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一位法律学者总结。
“公众充满热情是因为大家对知情权的长久期待,终于从‘条例身上找到了释放的途径。”这位法律学者说,“政府部门的冷则是要努力使由于不公开带来的利益,不至于在‘条例的冲击下损失殆尽。”
看来双方的行为都有点过火。“可能要经过一段时间,双方才能回归到一种理性的状态。”这位法律学者表示,这种状态的特征是双方都能认识到有些事情不可为。
司法机关的作用应是用判决把双方的行为指引到正确的轨道上,现在看来亦有些“水土不服”——朱福祥拿到了一个不予受理的裁定,黄由俭至今没有见到法院的书面回复。“不予回复是一种消极的策略。对于起诉人来说,等于釜底抽薪,司法救济没法进行下去了。”一位律师分析,“这等于间接地鼓励政府部门不作信息公开,因为即便你不遵守‘条例,也不会受到法律的制裁。”
王锡锌不主张对法院予以严厉的指责,因为“即便法院愿意受理,也不可能完全自己做主,因为体制本身对它构成了很大的制约”。王锡锌认为,更何况,从长远来看,法院还是唯一可依赖的救济力量,“骂得一无是处,建设性的方案何在”。
即便司法尚不能很好地发挥救济作用,王锡锌仍然认为,“条例”实施后两个月的实践已经表明,情况正在发生着积极的变化,最主要的力量来自各种各样具体的诉求,“我不说财政公开,我就要你公开养犬管理费的使用情况,官员就会感受到具体的压力,而当每个人都能提出这种具体的诉求时,官员面临压力的来源就是无限广泛的。只要有了渠道,一点一点地挤都不怕。”
“在原来空谈信息公开的时候,这种权利是虚的,‘条例的实施让这种权利成为实的,现在的问题是要把它从软的变成硬的。”王锡锌说,硬的标准是所有法律上规定的权利都能实现,这一方面可以期待司法,但同时也要依赖逐步地推动和方法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