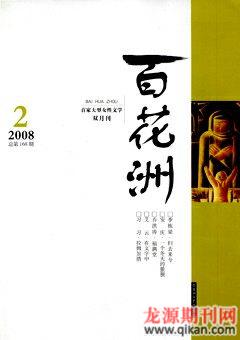命若琴弦(外二篇)
兰燕飞
乡村二胡手王麻石死去的那年我正好十二岁。当我伫立在2007年的时间坐标上,回首眺望,看见我的少年和青年如娇嫩的花瓣纷纷坠落,它们在黄尘与风雨中退尽颜色,零落成泥,灰飞烟灭。
怀旧之水如此清冽,倒映着色泽陈旧的乡村背景。记忆斑驳、杂乱,许许多多的事情没有结局,它们如烟一样袅袅上升,淡入渺远的暮天。
当我再次写下“命若琴弦”四个字,眼前似乎展开了一条奇妙的时光隧道,我一次次地往返其间,期待在某个瞬间,发现一些线条,它们或模糊或清晰,却暗指着命运的走向,顺着它,我能进入事件的内核。
是的,正如你猜想的,我不是第一次写他或她。事实这是第三次。我第一次动笔是在十年前,那次我虚构了一个残酷而绝望的结尾。王麻石在一个灼热而焦躁的中午,扼住了哭闹不休的婴儿的咽喉,他心中的魔狰狞着,在杀死孩子,杀死希望之后杀死自己。
第二个版本静静地躺在我的电脑里,我曾经把它贴在一个小说论坛。我看着它如一枚滑进湖水的卵石,悄无声息地沉入水底。那个骇人的尾巴已被我一刀割下,我试图在悲苦的弦律里凸现一缕温情,像天边的早霞,挣脱黑暗的羁缚,温暖婆婆与儿媳盛大的苍凉。在那两个虚构的版本里,这是永远朝着一个方向的两个女人,她们合力摧毁了一道道防线,不遗余力地为自己制造了一出悲剧。
所有的悲剧,归根结底,都是人性的悲剧。邪恶缘自人心,冷酷缘自人心,疯狂也缘自人心。而我要说的却并不是邪恶、冷酷与疯狂,它或许只是无奈。
我为什么要顾左右而言他?为什么闪烁其词?而不把事实真相说出来呢?长期以来,这个乡村故事一直纠缠着我,它们像一根根蒺藜,扎进我的身体里。
我曾经把它说给我的一个朋友。在那个陌生的城市,我的语言絮叨,冗长,如纷乱的落叶,它们没有方向,风是引领,我的语言磕磕碰碰、跌跌撞撞,在迷宫般的黑暗里,如一只懵懂的蛾子寻找着死亡的人口与虚无的光明。我坚持着把它讲完,我感觉到她隐忍的焦躁,她的脸在诡异而夸张的霓虹里渐渐失真。那一层微笑却一直都在,她微笑着说:这有什么意义呢?你想表达什么?
我愣住了,愣在微笑里,我感觉自己身体里的热浪正迅速退却,它们潮湿而冰冷。
是啊,这有什么意义呢?而且我确实不知道自己想表达什么,首先,这样的故事毫无新意,你给它一个乡村背景或者你给它一个城市背景,有什么区别呢?
我在他的微笑面前沉默下来。我不知道是不是所有的话语一定需要穿上意义的盔甲,一件事情的发生与结局和一朵飘忽的云彩,它们的意义是否一样?有的时候,看见与说出也许就是意义本身。
回到故事。
回到故事的时候,我也回到了童年。我在那样的年龄势必不能完全读懂隐藏在事情后面的真相,那么我就撇开真相,只端出自己知道的,好吗?
王麻石无师自通地学会了二胡。听过他琴声的人都知道,他的二胡拉得好。在那个京剧盛行的年代,公社宣传队里没有京胡手,王麻石凭借一把二胡,竟也可以拉得激越、高昂,将一台戏衬托得丰满而热闹。他的琴子一响,可以扯得人笑,也可以拉得人哭,这样的本事自然吸引了一些姑娘的眼眸,金花就是因为爱听他的琴声,走进了他的家门。但这个故事发生的时候,王麻石已经轻易不操琴了,他总是说,人老了,弦也调不准了。这是一句电影台词,经了王麻石的口,好像真添了无限的沧桑。王麻石那时也就三十出头,但他已经认为自己老了,看上去,他也确实已经老了。青灰灰的一张瘦脸,颊部深深地陷落。他的眼白不是白色的,而是黄晶晶的,和他早逝的父亲一般模样。三十岁的王麻石娶了金花多年,却没有生下一男半女。金花人高马大,脸上红桃花色。不能养孩子可是件大事,一个不能养孩子的女人通常是会遭到婆家的唾弃的。但婆婆是个明白人,她知道问题多半出在自己儿子的身上,而她不能坐视不管。
婆媳俩一个推波助澜,一个半推半就。一切就这样开始了。王麻石被母亲与妻子推到一个尴尬而屈辱的境地。
这不是简单的偷情,性一旦上升到生育的高度,上升到家族的传承,付出就是整个家庭的付出,牺牲的也是整个家庭的牺牲。
当金花的肚子山包一样隆起的时候,王麻石像枯枝渐渐失去了最后一抹青痕。现在想来,王麻石得的应该是肝病,他经年喝着黑色的汤药,那些液体渗透到他的身体里,像一株植物经过长期的浇灌,散发着苦涩的气息。他面对金花变化着的身体,长时间地沉默,没有喜,没有恨,好像那是一件与他完全无关的事,至于他的内心,煎熬也罢,平静也罢,那似乎已经不是一件值得关注的事了。但他终于没能等到那个生命的降临。
这当然并不是结束。真正的结局像一块黑色的礁石,搁浅在许多人的记忆之河里,无法轻易绕过。
婆媳反目成仇,为了孩子,对簿公堂。一边是年轻的母亲,一边是年迈的祖母,谁更有能力抚养这个孩子?法律公正、冷漠,对艰难生长着的枝蔓视而不见,它直视着挺拔的枝干,认为这就是结果。不错,这正是该有的结果。
所有的人都看见了婆母的泪。她是王麻石的母亲,她是金花的婆婆,她还是孩子的祖母。现在她什么都不是了,什么都没有了。不仅是她,所有人都认为金花绝情寡义。不明白金花为何要夺走这个孩子,她还那么年轻,她以后可以再生再养。但金花这时好像鬼附了体,谁的话也听不进去。
金花带着三岁的孩子借助法律成功地逃离。
那块礁石浮出了水面,它冰冷、坚硬,冒着森森的寒气,多少年来,我一而再、再而三的不成功的表达,或许正缘于此。它既简单又复杂,它的简单与复杂都可以用人性二字来概括。
王麻石的母亲淹没在绝望的死海,她拉住一只只熟识或不熟识的手,就如抓着了救命的草,在“我的命好苦呀”这歌唱般的长叹后,开始周而复始的哭诉。她的眼泪和诉说,在黄昏的路口与河滩,在初春的青草与冬日的严霜中,萧萧而下。她稀薄的白发如乱草般没有方向,只有风的方向,只有时间的方向,只有在时间与风中,渐渐遥远与黯淡的声音,苍老而无助。
金花的决绝也许正是缘于内心的软弱与恐惧。她害怕面对那双幽怨的眼睛,她不敢看那把落满尘土的二胡。它有时突兀地响起来,在黑夜深处,绵绵不绝,她怎么敢把孩子留在这里呢?怎么敢?她要把这些破碎的夜晚和不堪回首的往昔从记忆中抹去,她只能选择走,必须走。
这是一场没有结局的战争,没有真正的胜利者。只有纤弱的生命的叹息,在时间的旷野漫散,如隐隐的琴音,飘忽、不可紧握和把持。静谧的空间里,我听见时间的指针轻轻颤动了一下,而那块礁石已经不是黑色的,它复杂模糊,有着太多我不能破释的谜和说不透的理。但我终于把这个故事说了出来,或许我落入了俗套的陷阱,正以一种自由落体的姿势跌落,但我说出来了。
无论如何,这才是最重要的。
午后
一
祖父坐在厅堂里看电视,慢慢地把自己看睡着了。电视里那些后生、姑娘唱歌不好好唱,跑来跑去的,扭胯甩胳膊,让他的眼累得慌,于是他像一只老猫那样眯起了眼睛,这一眯就把
自己眯睡着了。
和祖父一起看电视的少年对视一眼,会意地俏皮一笑。他们一前一后溜出屋,黑狗尾随着,他们同时瞪了它一眼,低声地呵斥着,它抗议地轻吠两声,垂头丧气的往回走。
哥哥走下那个斜坡时,弟弟已经等在那里。天热得使人脑袋发懵,午后的太阳如一盆越烧越旺的火,舔得人身上火辣辣的。
少年横穿公路,拐上了一条依傍着河流的小路。小路行人杳杳、荒芜杂乱,摇曳的野芒还是一柄绿色的剑矛,它们调皮地抚摸着少年的脸,不时拉拉他们的衣角。少年甩开它们,一直向前走,黝黑的脸上淌着亮晶晶的汗珠。
我的文字此时变得非常的困难和艰涩。我不想继续下去,我希望这是我的文字制造的一个噩梦,我停下来,梦就醒了。我希望停留在这里,停留在某一个午后,寂静而喧哗的阳光下。
“后来我看见了别的东西,我永远只在事后才看到东西。”
我看见了结果。看见死亡的黑色的羽翼下覆盖着少年与祖父,他们彼此相邻,但却是孤零零的,他们再也不能听到彼此的话语。
那些水还在那里。静悄悄的,一副无辜的样子。但你不能轻易地相信它们,你瞧,现在连风也抛弃了它们。
我一直想把这些告诉你,那六十天前的事情。但我一日日地拖着,我不知道自己应不应该把一个突发的、孤立的事件说出来。
天空有着海一样的颜色,蔚蓝的颜色。少年的脸绽开了明亮的笑。他们同时看见了安静的、清凉的水,看见了水里飘着的云朵和羊群一样的洁白。弟弟跳起来,他的衣服如长了翅膀的鸟快乐地飞进了草丛。
水笑了。水一直在笑。先是羞涩的浅笑,直至大笑,狂笑,以至抽搐。
哥哥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他的记忆停留在2005年的夏天,那摇篮般温存、富有张力的水留给他的无边的快乐里。
二
我无数次地设想过另外的结果。哥哥在那一瞬间胆怯了。他只有十五岁,没有能力把十一岁的弟弟从命运的漩涡里的解救出来。他能做的只是求救。他朝四周望了望,他看见了绿色的庄稼,他的前方、后方、左边、右边,都是单一的让人绝望的绿。没有人影,人正在午后灼热的大汗淋漓的梦中。满眼满世界的绿连麻雀都看不到一只。只有蝉子在尖锐地嘶鸣:快去!快去!别去!别去!
蝉躲在浓郁的叶丛里。它的外壳黑乎乎的,老谋深算的眼睛被阳光晃得迷糊了起来。柳树的枝条低垂着,蝉藏在低垂的柳条间,它看见了一切。
蝉一直在犹豫,它也不知道该不该去。因此他喊着喊着就渐渐地喊得模棱两可了起来,这样听起来就是一声急过一声的去——不去!?去——不去!?去——不去!?少年压根没听清蝉说的话,他一个猛子扎了下去,没有犹凝,没有朝我设想的路径眺望。他应该找到了他的弟弟,他拖着弟弟挣扎着往岸边游,那些松软的河沙突然像峭壁千仞。
少年落下悬崖。
少年别无选择。
我设想的结果永远不会到来。
如果它到来了,真的就可以改变这一切?裂缝、阴影、猜忌、怨恨、自责……少年能够从中走出来吗?
生活总是漏洞百出,充满了这样那样的悖论。
三
母亲看着自己的儿子,他们那般安静,安静得陌生。他们的头发湿漉漉的,脸色灰白,他们的头挨在一起,圆脸、浓眉,他们的脚一长一短地平伸着。他们什么时候这样乖过呢?她喊、她摇,但任她嗓子喊哑,手臂摇酸,他们的眼睛一直闭着,嘴里没有半句话语。她生气了,啪啪给了他们两耳光。她还想伸手,手却被人拉着。她看着那些人,那些人眼泪涟涟,她听见了那些话,很多的话云里来雾里去,她听不明白,只觉得自己的心被插上了一把尖刀,眼看着自己的心被那刀一点一点剜出来,血拉拉肉糊糊的,她知道自己就要没有心了。一声哀嚎冲出了母亲的咽喉,这终于哭出来的声音让众人松了一口气。哭泣的母亲把自己像一棵树那样的放倒,她在地上翻扑滚打,她一次次挣脱众人的手臂,像子弹那样向墙壁、桌沿射去。这样的情形维持了也许一天,也许两天,也许更长。她的眼里交迭着的灼热与呆滞的火苗,在某个瞬间,扑地一声,熄灭了。
人们说她疯了。她疯得有道理。她没理由不疯。疯子的眼里都是黑暗,疯子的眼里都是光明。陷于永恒的黑暗或永恒的光明里的疯子自我救赎。他们救赎的方式就是成为一个疯子。多么简单又多么残忍。
四
黑暗如一个巨大的洞穴,神秘、幽深,波澜诡异。父亲像一个失去方向与动力的水手,再也无力操纵那柄单薄的浆。他任凭黑暗的潮水漫上来,他绝望地看着自己的儿子化作一缕轻烟,它们飘啊飘啊,一会就飘得没了踪影。他想他也化成烟罢,和他的儿子一起。但他不仅没飘起来,反而坠入了永劫不复的深渊。
黑暗黑得那么纯粹,没有半点缝隙。黑暗就是黑暗,没有时间与空间。
他躺在黑暗里,慢慢想着这一生。他们从修水来到铜鼓,他们都是老实巴交的人,没有技术,书也念得不多。他们选择了种菜这个行当,他们的一些老乡也在铜鼓种菜。他们租了十几亩地,没地方住,就在地里搭个棚子。那是十几年前的事了,他和老婆都很年轻,干起活来又舍得卖力。他们都知道力气是用了又会长出来的,用不着像钱那样地攒着。靠着四季菜蔬,他们不仅将孩子慢慢养大,还把老父亲也接了过来,又买了一套二手房。他觉得生活没有亏欠他,他和老婆除了干活,没有一点别的嗜好。他知道和他们一起种菜的好些人都打起了麻将,但他连看也不看,好像麻将会扑上来咬他一口。他想,他有两个儿子要养,他虽然拼命干好像多么喜欢种菜似的,但他不想他的儿子也种菜,他希望他的儿子好好读书,将来读一个好大学。他对自己的人生已经没什么要求了,白天流汗,晚上看看电视,困了倒头睡到天亮,这样的生活他觉得已经够享福了。
可是现在黑暗严丝密缝地把他锁了起来。许多的事物都在远处,儿子在菜地里扑蝴蝶、捉蚂蚁、网蜻蜓,风吹过来,那些紫茄子、青辣椒、红番茄和天边的霞光般美丽,他的老婆笑意盈盈,这些说没就没了。只有他独自呆在黑暗里,黑暗铅一样沉,他掀不动它,掀不动啊!
他多么希望日子就像一张饼,可以翻来翻去,从今天出发,翻过去可以是明天,也可以是昨天……一直回到那个让人诅咒的日子之前。日子真的就是一张饼,它一下子碎了,碎得如扬花一样。
黑暗驶过他的身体。穿透他、碾碎他。他想,天再也不会亮了。
五
祖父走出屋,不知不觉就到了河边。月光明晃晃地。他已经老了,已经老糊涂了。他一个盹就打掉了两个孙子。他艰难地蹲下来,用手拨了拨水,水像孩子般围了上来,把他的眼睛都溅湿了。它们从他的眼里流人心里,又温和、又熨帖,它们牵着他,一步一步地往前行。
水把他喂得白白胖胖的。他肥白的身体在七月的潮讯里出现在距我家不足百米的河湾里。他和那些丰茂的水草纠结在一起。晨曦渐现,晨曦从遥远的地平线赶来,晨曦到来的时候,所有的事物、一切的事物都袒露出真相。
包括黑暗与死亡。
电影
我最后一次踏进电影院大概是十年前。那场电影如狂飙席卷全球,我被裹挟着,完全是在不自觉的情状下看那艘永不沉没的泰坦尼克如何决绝地与冰山相吻。一段亦真亦幻的爱情如莲一般高高的擎于水面,随风起舞,逐浪而歌,它们浪漫、哀艳、惊绝,有着闪电一样的光芒,很轻易地抓住了风尘俗世里那一颗颗年轻或已不年轻的心。
那时我的心大抵还是年轻的吧,但相对于这种令人眩晕的爱情,更能够打动我的是人类在突如其来的灾难与死亡面前表现出来的人性的光辉。那些在倾斜的甲板上从容演奏的乐师,那个自负却从容赴死的船长,还有在有限的救生艇面前默默后退的那些不知名姓的人们。他们才真正地打动了我。
在这之后的漫长时间里,我对电影院和与它有关的一切视而不见,置若惘闻。虽然我依然在电视或碟片里看自己真正喜欢的电影,但我再也没有涉足过人头躜动的影院。它像一个废弃的词汇,完全淡出了我的生活。关于它的所有记忆都停留在日渐老迈的铺里和渐次遥远的童年。
电影是我们眺望童年的最好方式,因为这是我全部童年生活的核心。它像一座桥梁横跨于时间的河面,那些爆米花的香气、那些零落响起的爆竹、那些暗香浮动的女人、那些泥土与植物的气息、那些神秘高远的月光星芒,踏河而来,如电影般一幕一幕,使人瞬时间模糊了记忆。
电影幕布通常挂在学校的操场。因此我们总是第一个得到消息,我们远远的望着那块镶着黑边的白布,它如云朵般在风里飘,我们不怀好意地吃吃地笑,我们知道它是跑不了的,那四根绳子像拴牛一样把它的鼻子拴住了。我们只希望快点熬到下课铃响,然后旋风一般直扑操场,在自己选定的最佳位置摆上一条上课用的板凳。操场泥尘漫起,叠印着童年的影子。操场的外侧是田野,那里恰似电影前的幻灯卡片,更替着四季的色彩,绿浪汹涌抑或空旷荒凉,只有操场永远是纷乱喧嚣,散发着迷人的气息。它是开放的、自由的、明亮的,蹲、坐、立,可以随意调整自己的姿势,还可以无拘无束地从东走到西,再走到南,再走到北。电影一般都是已经看过的,《地道战》《地雷战》《列宁在十月》《列宁在一九一八》……我们几乎熟知每一个细节,但还是担心着某一句对白或某一个我们心仪的画面如一只山雀一般地飞走。因为每场电影几乎都会烧片,我们眼睁睁地看着银幕上突然出现一枚秋天的枯叶,焦黄、顺着叶脉分裂,最后如烟一样消失。
时光如水一般漫过,模糊了多少往昔?一些留在记忆之筛上的沙砾经过时间的润泽散发着宝石般的光芒。我记住了这些电影,但对如鱼一样游动在银幕前的伙伴,我已经完全混淆。他、她、他们,是谁和我一起度过?度过这一部或那一部的电影之旅?我只记住了那次一个人的电影,孤独、忧伤,它们如此清晰地一次次爬上我记忆的额头。
那天放的是《列宁在一九一八》,本来我已经躺下了。我不得不躺下。中耳炎,发着烧,耳朵流着脓。发烧于我是奇妙的旅行,我闭着眼,却看见了那些云朵、它们浓艳、热烈,如泼上去的油彩。它们先是如水一样地流淌,但速度越来越快,终于像一只旋转的陀螺,我觉得自己飞了起来,这样的飞翔或许很短,或许很长,它来得突兀,去得嘎然。当我结束飞翔,窗外一片宁静,月光悄悄地挤进来,斜斜地一道亮光,如银子一样。我又躺了一会,突然非常的不放心,深怕今晚不能擒获那个向伟大的列宁同志射出了罪恶子弹的女特务。
一个人穿过铺里狭长的老街。那些熟稔的房子在夜的合围下变得居心叵测。我的心似要跳出咽喉,跌跌撞撞地来到操场,电影已经进入了尾声。我不知道那个女特务到底来没来,也不知道女特务会不会被愤怒的人群撕碎,就像我希望的那样。我一个人站在那里,脚下的土地如棉花一般的松软,它让我既欢喜又恍惚,银幕上的声音似从天边传来的回声,遥远、虚幻,毫无真实感。我静静地站着,看见天上的月亮就像一个盘子,又大又干净又明亮,照得我泪眼婆娑。迷迷糊糊中电影散场了,一操场的人好像突然没了踪影。我踏着月光一步一步往回走,心里非常委屈,觉得自己就像一个被遗弃的孤儿,噙在眼里的泪终于涌了出来。
操场上凌空而起的幕布有一天转移到了公社的礼堂。就像一个姑娘成了媳妇,从此很少出门。隔三岔五的公社的门前就会出现一张海报,这些颜色各异的纸张为我们带来了电影的消息。它的上方书写着两个大字:海报,下面是今晚上映×××,时间×点×分,地点:公社礼堂,票价:一角。这样的海报,就像一朵开在崖畔的山花让我们既兴奋又沮丧。我飞快地在心里做着算术,兄妹八个,除大哥和两个幼小的妹妹外,结果很快就出来了,是五角。我非常吃惊,这样一个数字让我不得不否定买票入场的计划。但电影就像钩子一样钩住了我们的魂,礼堂的门外游走着一群失魂落魄的孩子,我们等待观望,幸运的时候就会被哪一个熟悉的叔叔阿姨牵了进去。
我是多么地喜欢电影开始前的那一幅图画:一轮金色的满月,一片蔚蓝的海面,一杆挺拔的椰树,一切都将从这里出发,一切都将在这里抵达。我是多么喜欢那些在换片间隙出现在银幕上的动物,一只奔跑的兔子,一条汪汪叫着的小狗,它们惊慌失措,上蹿下跳。我是多么的爱电影里的好人,每逢他们与坏人搏斗的时候,我都捏紧双拳,生怕他们打不赢,好在这样的场面永远不会出现。但对女特务,我的情感却复杂而暧昧(只有苏联电影里的那个女特务让我恨之入骨),她们通常面容姣好,头发翻卷,绰约多姿。暗哑的光线、阴晦的音乐也遮挡不住她们的光彩。她们的修长的指间袅娜着香烟,她们的眼睛在顾盼流转间风情万种,她们胸脯高耸,腰肢纤细。她们在遭到唾弃的同时又被多少人暗暗喜欢过?
“中国新闻简报,越南飞机大炮,朝鲜哭哭笑笑,阿尔巴尼亚莫名其妙。”这样具有高度概括性的顺口溜有一天传人铺里,让我如遇知音。我一直不敢承认自己没看懂阿尔巴尼亚的电影,《第八个是铜像》与《脚印》,我已经至少看了三次以上,但不知道它们到底要说什么。关于《脚印》我只记住了一个场景,但它模糊,含义不明。那是两个黑衣男人,非常平静地坐在一起,他们瘦削而苍白。其中一个忽然说:你永远过不了国境线。另一个掏出枪,啪的一声,说话的那位就伏在桌上,睡着了一般地死去。这不是莫名其妙是什么?怎么能这样一声不吭就死呢?我连谁是好人坏人都没弄清。一部好人坏人都弄不清楚的电影当然不是好电影。我们希望好人永远不死,实在要死的话,也要像《打击侵略者》中的志愿军战士一样,手指前方,喊着:红旗、红旗……或者像王成那样跃出战壕,在燃烧的阵地与高亢的音乐中,拉响爆破筒,让美国兵闻风丧胆。然后画面一转,青松、翠柏、蓝天……这才是牺牲,是重于泰山的牺牲。
更多的时间我们被挡在了门外,这让我们心急如焚,但我们绝不会坐以待毙,我们如侦察员般四处寻找着可乘之机,竟然发现了一条通道,它是隔壁粮站的下水道,从公社厕所前逶迤而过,最妙的是恰在穿过围墙处是敞开的,我们只要从粮站的那边爬过来,就在厕所门前了,这不等于进了礼堂吗?都说天上不会掉馅饼,但现在馅饼掉下来了,铺里的孩子欣喜若狂,成群结伙地通过下水道,在礼堂班师凯旋。
这样长期的角逐,一方面昂扬了我们的斗志,但也让我们的心里蒙上了一丝不易察觉的阴影。而除夕的那场免费电影在某种程度上给了我们全部的补偿。
吃过一年中最丰盛的晚餐,铺里的孩子大摇大摆地走出家门。礼堂已经洞开,它将成为除夕夜铺里狂欢的营地。我们的衣兜和裤兜都饱满地膨胀着,爆米花、炸薯片、炒山栗……我们炫耀着,在那条铺满沙砾的马路上追逐打闹。我们眼见群山由黛而灰,由灰而黑。电影正沿着神秘的时光之箭射向铺里,我们已经看见了它的微笑。奇怪的是,我没有记住任何一场除夕之夜的电影,或许在那一天,电影只是一个快乐的道具。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快乐,我童年的快乐就是如此简单。
那些在耳边炸响的爆竹,男孩得意的坏笑,女孩明亮的尖叫,从未在我的心里黯淡。太多的除夕夜是属于电影的,它们彼此重迭、彼此交叉,同样的温暖或者同样的寒冷,在时间的汪洋里相互过渡,但有一个除夕如一座兀立的峰峦,升起在生命的河面。
我为什么会在电影的中途回家?是手中的火笼没了热气,还是想再抓把瓜子?总之我回家了,童年时我所有的除夕几乎都在电影前度过,我不知道家在那个夜晚会如此的寂静与空荡,父亲坐在火盆旁安静地抽着烟,母亲还在灶前忙碌,最小的妹妹在母亲的背上有一声没一声的哭着,母亲嘴里唱着歌谣,手在大铁锅里洗洗涮涮,水缸盖、大锅盖、小锅盖、碗橱……厨房里每一样木质器具,经过碱水的清洁,变得白净、清香。我愣在那,等着母亲的训斥。我看见母亲侧过脸,母亲是微笑着的,她问我怎么没看电影?还问我电影好看不好看。在我记忆里,母亲很少有好脾气,她总是毫不留情地把我们从梦里揪醒,然后开始数落,我一直怀疑,如果我们不上学,她是不是会数落到天黑。
那天母亲一直微笑,只是微笑。母亲的微笑是多么美丽啊,浅浅的笑黡,弯弯的嘴角,我在母亲的微笑里回到自己的电影中,并在远离电影的时代融化在母亲的微笑里。
责任编辑刘伟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