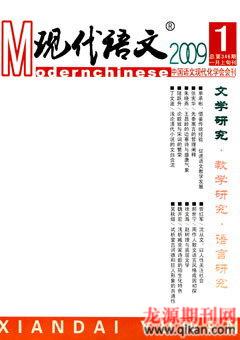试论《白鹿原》中社会矛盾产生的多重性因素
叶澜涛
摘要:《白鹿原》改变了以往小说常见的将社会矛盾的根源片面归结于经济因素的观点,而将更多的因素纳入视野来进行考察,因而发现民族矛盾、家庭环境、个人道德水平在不经意中同样会导致矛盾冲突的发生。
关键词:《白鹿原》社会矛盾多重性
无论是处于何种历史阶段,也不管它有怎样的社会形态,社会从它诞生之日起就有了各种各样的矛盾和斗争,也正是这些社会矛盾的产生与解决才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和历史的进步。社会的发展史可以说是一部与社会矛盾的斗争史,在与种种矛盾对抗的过程中推动了自身的进步。
社会矛盾的产生原因多种多样。其中既有经济方面的原因,也有政治方面的原因,甚至个人的思想道德状况与各种偶然性因素也会成为重大历史事件的导火索。情况因复杂琐碎的外表而变得难以分析。在“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中;有的作品往往忽视了社会矛盾产生的多重动因,将社会矛盾产生的原因简单地归结为各阶级因为社会财富分配不均而导致的阶级对抗。归根到底,经济原因成为社会矛盾产生的唯一因素,从而排斥了其他阐释的可能性。而在《白鹿原》中,作者力图改变这种观点,将产生社会矛盾的诸多因素纳入自己的视野,理性地分析社会矛盾产生的各种因素。这其中既可能有经济方面的原因,也可能有个人道德的原因,甚或民族之间的斗争对抗。这种经济实力、个人道德乃至民族的对抗共同构成了社会的各种矛盾。经济之间的差异既可能有家庭方面的因素,也会因为个人的素养而有所不同,而民族对抗产生的觉醒意识并没有因经济因素在不同阶层之问有所不同,反而更多地与个人的教育水平和道德修养息息相关。前一种情况以黑娃、田小娥、白兴儿为例,后一种情况以鹿兆鹏、鹿兆海、白灵为例。
黑娃、田小娥、白兴儿等可谓是白鹿原上生活得最低贱的一群人。这样。一群被鹿兆海称之为“不干不净有麻达”的下等人,在遭遇到各种压迫和歧视之后,终于通过各种方式——革命或非革命,暴力或非暴力——报复着一切压迫他们的人们。他们这种反抗属于农民阶级中最下等的人群进行的有意识的反抗。黑娃作为一个长工的儿子,从内心深处来讲,隐藏着强烈的反抗意识。当白孝文给他各种照顾并将自己的零食分给他的时候,黑娃感受到的不是荣耀而是耻辱,因而将点心扔进了草丛。学堂的戒律让他自由的个性受到压抑,便带着孝文和兆鹏去看牲畜配种。长大的黑娃看不惯白嘉轩,毅然出了村子外出熬活。黑娃性成熟后与受到性压迫_的田小娥不顾一切地相恋,结果却是不被人们承认,不能回祖祠认祖归宗。这一切已将黑娃完全打入了下等人的生活,经济上的贫困和来自乡党的巨大精神压力,使原来骨子里就反叛的黑娃义无返顾地去冲击一切不合理的秩序,烧粮台、进农讲所、参加农协、砸祠堂、铡恶棍、斗田福贤、当土匪等等,这些行为将这个“从前站在一切人之下”的人一变而成为“站在一切人之上”。而田小娥、白兴儿的社会地位比黑娃还要低下。田小娥没有做人的价值,只不过被看作是一个“泡枣”的工具,当她被发现与黑娃私通后,被赶回了娘家。黑娃再见她时,娘家如驱逐一只苍蝇般地将她赶出了家门。鹿子霖看她有两分姿色,上了她的炕。可在鹿子霖眼中她也只不过是报复白嘉轩的一个性工具罢了,没有丝毫作为人的价值。被自己的婆家亲大用梭镖捅死后引起了一场瘟疫,可是白嘉轩和朱先生毫不犹豫地造了塔让她的魂魄永世不得翻身,可谓从头到尾都是个悲剧。而白兴儿因为祖祖辈辈都长着一双像鸭蹼一样的奇特的手,只能做给畜生配种的事。这种特殊的工作使他比原上所有人都低贱。他义无返顾地参加了农协,可在反攻倒算时被田福贤拉上了戏台,羞辱性的展示完手掌后挑了手上的蹼肉,终于在文化大革命中,砸了朱先生的书院招牌,改做养殖场,也算是报了当年的一箭之仇。
这样一批下等人没有受过系统的阶级压迫和阶级反抗的教育,他们只是从身边的事情真实地感受到了生活的不公正。这种不公正的地位促使他们抵制一切来自他人的歧视和压迫。他们会对社会产生恶性的报复心理,这种报复心理大多是生命本能式的挣扎。但也有一些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他们家道殷实,并没有所谓的天然的阶级压迫的“嗜好”,相反会主动接近贫下中农,去帮助他们。他们与封建军阀、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势力之间存在本性的分歧和矛盾。而且他们之间也会因各自的政见不同而产生龃龉,以至分裂。其中以白鹿两家的第二代最有代表性。
鹿兆鹏、鹿兆海、白灵都来自地主家庭,他们幼时便在乡间念过学堂和书院,而后又到城里的新式学校受过新思想新文化的教育,参加过学校办的国民革命培训班,各种民主思想和观念已经在他们的头脑生根开花。他们的反抗不同于黑娃、田小娥、白兴儿等人来自生命本能的报复,他们的反抗范围也不仅限于自己所熟知的乡里,而是将整个不合理的社会作为自己斗争的对象。这种对于自我精神和人生价值的不断拷问与追求,最终促使他们拿起武器,同自我、同社会、同各种反动势力作斗争。他们面临的是一个极其残酷的生存环境。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中国,国军不断沦陷和退守;围城后的西安古城,尸体如草芥般被埋葬;白鹿村流年不利,不断遭受瘟疫和饥荒;滋水县县长如走马灯般地换了几茬,无人认真管理这一切。他们面临的现实与从小所憧憬的未来如此迥异,以至他们纷纷不顾家庭的阻挠,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兆鹏不喜欢家里选的媳妇,几次过家门而不入,弄得鹿兆恒不得不用拐杖把他打回家。他希望像黑娃一样能“选择自己喜欢的女子作媳妇”,并将这种行为视之为冲破封建枷锁的壮举。可见,兆鹏的行为已是有意识地和不合理的社会进行抗争。兆海与白灵一同参加了围城后的埋人的行动,认识到了军阀势力的凶残性,不久就共同参加了学校办起的国民革命培训班。出于“两党合作一致推进国民革命”的崇高目的,兆海和白灵分别加入了国共两党。这时的兆海和白灵并没有对两党的斗争纲领和革命的目标有过明晰的认识。出于对革命的向往,对现实强烈不满的情绪,他们义无返顾地加入了这场异常残酷、旷日持久的革命洪流中。当国民党开始对共产党进行剿杀,用“扎紧袋口”的麻袋填入“干枯的深井”时,她一下子成熟了。她“看轻了自己:死了不算什么,一个对异党实施如此惨绝人寰的杀戮手段的政权,你如若对它产生一丝一毫的幻想都是可耻的,一切必须推翻它,打倒它,消灭它。”当剿杀达到高潮时,她毅然地提出加入共产党。“我看见他们剿杀才要加入。”“你们少了,我来填补一个空缺。”这时的白灵己不同于当初懵懂地用抛铜元来决定命运的小姑娘,已经成长为一个坚定同一切黑暗势力作斗争的革命战士。
《白鹿原》中颇有深意地写到“两次决裂”。一次是兆海和白灵的爱情决裂,一次是兆海与兆鹏的兄弟决裂。第一次由于兆海和白灵的政党选择不同,双方均想说服对方,然而随着革命的深入,对于主义的讨论与政党的争辩由浅入深,由朦胧而清晰,各自政治信仰的分歧越来越大,爱情的成分也越来越弱,最后不得不分道扬镳,用“看看谁的主义真正救中国”作结束语。第二次分裂发生在鹿家长子和二子之间。兆鹏很早就参加了革命活动。对于穷人,他充满了同情心,鼓励黑娃组织农协闹革命,并对黑娃的自由恋爱表示肯定,而兆海则将黑娃视为“死猫赖狗”,将黑娃的革命视为“吃大户的盲动”。不同的态度决定了不同的命运,当兆海一看见他所护送的嫂子竟是自灵时,便发誓与兆鹏决裂。这种决裂不仅仅意味着两人在爱情问题上的分歧,更多象征着两人由于政见的不同导致的不同命运。兆鹏一心为下层群众而奔走,最终赢得了白灵的爱情。兆海在进犯边区的战役中被打死,徒有一颗救国之心。
作者正是如此真实地写出了同是革命青年的一代人,在不同的革命形势下对于革命理解上的差异。这种差异也决定了他们各自的命运,如同大浪淘沙,终要洗尽铅华,淘出真金。也正是这一批热血的革命青年,用自己的热血和青春推动了历史巨轮的前进。“保命”一类的生存哲学在他们身上是看不到的。更多的是对于祖国贫弱状况的焦虑和改天换地的豪气。当他们自觉地团结在一起,各自为了自己的目标而奋斗,努力实现自我目标时,个人冲突与国家民族命运联系在了一起。
而他们所代表的也不仅仅是他们本身,更多的是寄托着各自家族的人格理想,成了各自势力较量中重要的砝码。家族的斗争也就延伸到每个个体身上,个体的政治性无疑使这种由于血性不同而导致的家族斗争增添了更多的、更复杂的政治色彩。作为读者,已不太容易在各种倾轧和争锋中明晰地辨别出两者的区别。家仇与国难之间通过年轻一代的分化和组合而变得模糊不清,双方各怀理想的青年人已不再将自己的视野仅仅局限于将对方压倒,而真正试图从根本上解决一些当时中国所急迫解决的问题,但由于他们不可能摆脱各自不同的家庭教育和人格理想的差异,让人始终感觉到他们的身后有一个巨大的家族身影的存在,破茧而出成了一次振翅而滞重的飞翔。